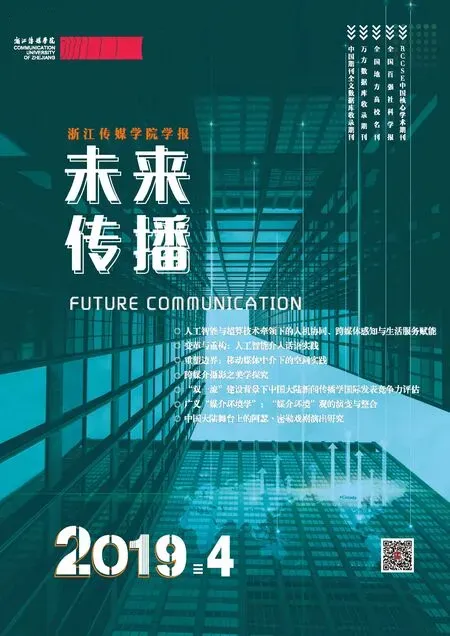新闻文体“文学范式”的生成与型构
——基于对“散文式新闻”的历时性考察
2019-12-17李娟
李 娟
新闻文体是表征新闻事实的载体。不论文字新闻还是音视频新闻,抑或是数据新闻,其呈现方式都需要借助特定的话语体式与结构方式,这些均属于新闻文体的范畴。从历时维度看,脱胎于古典文学的新闻文体始终与文学保持着某种特殊的关联:一方面,从确立主题的方式方法到文章起承转合的结构布局,从记叙、议论、抒情等不同的表达方式到文章的遣词造句,新闻文体都深受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许多新闻报道常常直接调用文学观念和创作手法来呈现新闻事实。于是,“散文式新闻”“新闻特写”“报告文学”“新新闻报道”“非虚构写作”等渐次成为新闻文体“文学范式”的重要文体形态。近年来,伴随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的兴起,传统新闻报道的话语与结构模式正在不断被新媒介所解构,越来越多的新闻报道开始广泛使用散文笔法和散文结构,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散文式新闻”遂再度被“征用”。基于此,本文尝试从新闻文体史的维度,展示“散文式新闻”的生成过程,继而探讨新闻文体“文学范式”的型构路径。
一、“散文式新闻”的“命名”
作为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四大文类,散文与新闻文体的渊源深远。文学学者袁勇麟教授就曾指出,“中国大陆新时期之前的散文创作,主要继承40年代解放区以记叙为主的纪实性散文和古典散文,前者导致建国初期‘通讯’‘报告’‘特写’盛极一时,后者则促成60年代初期‘诗化散文’的创作热潮。”[1]新闻学者樊凡教授也曾撰文指出:“新闻的母体是古代散文,大概由于‘遗传基因’的作用,当代散文的文化个性,包括题材广泛、灵活自由、亲切率真、朴实优美、自然深刻、情境交融、文理合一等,对新闻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并不断滋养着新闻的园地。”[2]作为一种杂交文体,“散文式新闻”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其“命名”经由从记者文体实践到最终在新闻共同体内形成相对共识,体现了新闻文体对于散文的借鉴与吸纳。
建国初期,从革命战争中走出来的党的新闻工作者大多缺乏基本的新闻学知识,多是从实践中不断学习、总结,并在继承根据地时代党报的优良传统基础上予以创新。这一时期的新闻工作者大多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故被称为“三八式”老记者。《人民日报》前总编辑李庄在其回忆录中就曾提及他们这一代记者的基本特点:大多都是文学青年出身,其新闻写作的方法几乎都是从文学中借鉴、改造与摸索而来。[3]因此,当时很多新闻作品虽然略显稚嫩,甚至不够“专业”,但容纳了多样化的新闻写作方式,其中很多新闻都是按散文模式来写。尽管其时没有“散文式新闻”的提法,但借助散文等文学笔法写新闻成为一种“过渡性文体”。例如,李庄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特写》(1949年9月22日)、杨刚的《给上海人的一封信——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1949年10月6日)等都是其中的典范性文本。应该看到,当时,从革命战争走过来的记者们并无太多新闻专业的意识和新闻写作的基础知识,加之大多记者是文学青年出身,因此,借鉴散文,转向文学,自然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1956年,“新华体”新闻写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型构完成,并逐渐呈现出“一体独大”的态势,但同时又开始出现诸如公式化、形式僵化、缺乏可读性等问题。于是,新闻界开始向文学“求援”,“散文式新闻”又成为“新华体”框架下新闻文体的一种“调适性文体”。
穆青率先看到了这种“调适性文体”的意义,并公开予以肯定和支持。1963年1月,他在《尝试用散文笔法写新闻》一文中首先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新闻就非受一定的格式束缚不可呢?为什么散文可以有个人风格,而新闻就只能按照死板的公式去套呢?”有鉴于此,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新闻写作可以“充分吸取散文写作中那种自由、活泼、生动、优美、精练的表现手法。”[4]虽然穆青没有正式使用“散文式新闻”的提法,但这却是有关“用散文笔法写新闻”观点的首次阐发。遗憾的是,1966年“文革”爆发,新闻退回到政治一元化的夹缝中,继而沦为政治的工具,失却了新闻文体的独立性与创新力,文学本身也蜕变成“斗争文学”,“散文式新闻”的尝试旋即中断。
1978年,第三次新闻改革大幕开启,新闻界首先从新闻写作技法、文风等层面切入改革,拨乱反正,成效显著,并逐渐寻找到新闻文体的一些规律性认知,明确认识到“新闻才是报纸的根本”,于是,“写新闻,写好新闻,写短新闻”成为当时新闻改革的潮流。1981年,习仲勋同志提出新闻写作要“真、短、快、活、强”的五字方针,其中“活”涉及新闻的呈现方式和文采,给予新闻界相当大的启发与创新动力,此后越来越多的记者开始关注新闻的表现力,尝试写法上的突破。
然而,积重难返,僵化的观念、拙劣的文风、蹩脚的写法,始终都是困扰新闻界的历史痼疾。举步维艰之下,穆青再次将眼光转向散文,向散文“求援”。1982年1月,他明确提出新闻要“向散文式方向”转向的观点。与1960年代相比,这一次他更加坚定,阐释得也更加清晰。穆青将“散文式方向”聚焦为两个层面:其一,新闻的形式与结构。“我们的新闻报道的形式和结构也可以增加自由活跃的散文形式,改变那种沉重的死板的形式,而代之以清新明快的写法。”其二,新闻的语言表达。“我们的新闻报道不仅内容是健康的,积极的,向上的,而且语言文字、表现形式也是新颖的,也是美的。”[4](191-193)这些恰恰是散文的文体优势所在:形式多样、结构灵活,讲究文采。在穆青的倡导下,此后新闻界开始了“散文式新闻”的大规模文体实践。
1982年7月,新华社记者郭玲春采写的消息《金山追悼会在京举行》,从文体实践层面为新闻界灌注了一股“散文式新闻”的“清流”。该篇报道首先在形式上与传统同类报道具有显著不同,篇幅大为缩短,段落明显增多,全文只有900多字,却分了9个段落。多段落、短段落、短句子使报道的传播效果大为凸显。特写式导语打破了传统追悼会惯常写法,“鲜花”“翠柏丛中”“默默”等表述将追悼会场景描摹得细致入微。主体第一段随即引用挽联勾连出后文对金山一生经历与贡献的生动再现。这样的写法,一改追悼会新闻程式化窠臼,率先突破“新华体”的僵化模式,报道获得当年度“全国好新闻评选”一等奖,之后被新闻界公认为“散文式新闻”的典范之作,引发了新闻界的如潮好评。有研究者形容这篇稿子的反响——“好似平静的湖面突然落进一颗石子,激起层层涟漪”。据说,当时不少人投书新华社和《新闻业务》编辑部,“表达了欣喜感奋之情。有的赞扬稿件具有优美的艺术魅力,有的称它犹如一块镶嵌在报纸上的磁石,深深地吸引了读者,有的兴奋地说,一股清新的改革之风从字里行间扑面而来,不禁为之击节叫好。”此外,新闻同行们的基本看法“几乎是一致的”——“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创新,突破了追悼会消息千篇一律的老框框,而且写得有文采,在新闻写作改革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5]
事实上,追悼会新闻的“散文式”呈现并非始于这篇报道。郭玲春在谈及该文采写体会时就曾指出:“在一些几经筛选的新闻通讯集里,我们的前人留下精粹的文稿,它表明固定的文体未必是‘传统’,近年许多有识之士在这一领域里探求,一篇篇好新闻也向我们展示,划一的格式并非牢不可破。它鼓励着新闻界的晚辈也来学步。金山追悼会消息,就是一次粗浅的尝试。”[6]这表明,郭玲春也是在受到前人散文式新闻的影响后,才开始这种写法的尝试。而早在1980年,中新社记者殷金娣撰写的《永别了,赵丹》就部分采用了散文式写法,全篇大量使用白描手法,结合大量细节化描写,有力地刻画了场景,渲染了气氛。两相比较,《永别了,赵丹》行文更简洁,结构更简单,而《金山追悼会在京举行》的文学性则更强,结构更精巧。当然,这也说明新闻界关于“散文式新闻”的文体实践已经在80年代初开始逐渐铺开。
1989年出版的《新新闻体写作》一书第一次将“散文式新闻”作为一种新出现的新闻文体类型加以推介,“散文式新闻正是吸收了散文和新闻的优势及长处而形成的一种新新文体。”[7]这表明,“散文式新闻”已经获得正式“命名”。1991年,《新华社中青年记者散文式新闻选萃》一书出版,时任新华社总编辑的南振中在该书的“序”中指出:“今天,‘散文式新闻’以其一定的‘质’和一定的‘量’构成了一种独立的新闻文体。”[8]换言之,这本书的出版是“散文式新闻”这一“命名”获得新闻共同体共识的标志性事件。
二、“新闻散文化”的论争
在“散文式新闻”的型构过程中,从“散文笔法写新闻”到“新闻要向散文式方向发展”,从“新闻散文化”再到“散文式新闻”,新闻学界与业界展开的“新闻散文化”论争也促发了“散文式新闻”的最终命名与边界确认。这场争鸣始于1985年,绵延十多年,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1)散文式新闻的内涵是什么?(2)新闻能不能散文化?(如果能,边界在哪?)(3)新闻与文学的关系何在?
关于第一个问题,新华社60位中青年记者在《散文式新闻选萃》一书中对于“散文式新闻”的表述,大体囊括了国内新闻界的基本观点。试举几例:
结构如流水般自然流畅,不拘一格;情节完整、生动,步步推进;行文不事雕琢,尽量用形象语言,为读者勾出有声、有色的立体画面。[8](26)
散文式新闻不必如诗、如画、如史、如传,但应兼具诗画史传的气韵神采散文式新闻是边缘文体的边缘文体,因此要求记者不仅是知识的杂家,还应将如下各家的气质特色集于一身:高屋建瓴如政治家,思想深邃如哲学家,感情丰富如音乐家,观察精细如艺术家,文笔优美如文学家。[8](32-33)
写成的新闻是一幅画卷,不需题名,则可尽观其意;画中有诗,不必朦胧,喜怒哀乐跃然纸间。笔尖流出的皆是实事、新事、有意识的事。难的是形象性地概括出新闻眼,寻求以一当十的细节,剪辑组合满含意味。[8](79)
散文式新闻文体是探索增加新闻可读性的积极尝试。摒弃“新华体”中的八股腔,删去沉闷的叙述和繁冗的铺陈,采用清新活泼的语言和较为松散、自由的结构,并尽可能使文章短下来。用眼睛写新闻,是散文式新闻的突出特征。摘取最重要的事实,更多地调动描写的手法,使新闻更加可亲、可信、可读。[8](216)
不难看出,这些记者对于散文式新闻的表述虽然不尽相同,但总体内涵大体趋于一致。“散文式新闻”的提法针对的是新闻写作中出现的“八股化”倾向,其意在坚持新闻真实性的基础上,调动记者的情感,借鉴、吸纳散文的结构与写法,从而增强新闻的可读性与生动性。四川大学张惠仁教授认为它是新闻题材与散文笔触的结合:“散文式新闻用的是散文笔触,写的却仍属新闻。我们在新闻写作中所提到的‘散文笔触’,实际是有别于传统的散文笔触,是一种散文与新闻结合的笔触。它驾驭的题材,必须是新闻,并有新闻价值及时效价值,它必须写真、写实,‘W’必须确凿而明白。但它的题前蓄势、起笔、运笔、起承转合、收束全文的方法,又必须借鉴散文之长处。用散文笔触写新闻时,要求不削足适履,而要新意倍出。力求克服‘千文一面’的模式化。”[9]
关于上述第二个问题即新闻能不能散文化,其时的讨论非常激烈,且呈现截然相反的态势,大体形成三派意见:
“支持派”认为,“新闻散文化”着意打破日趋八股化、公式化的“新华体”,是新闻业务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因此,“在各种新闻体裁中,最需要(散文)化的是消息,在消息当中最需要(散文)化的又是非事件性的新闻。”[10]那么,新闻该如何借鉴散文?学术界的共识包括:“新闻要象散文那样讲究‘立意’和‘意境’,象散文那样加强形象的描写,象散文那样加强细节描写,象散文那样使用生动凝练的语言,新闻报道的领域要象散文那样广阔、丰富。”[11]
“反对派”大多从“新闻的职能”“新闻的可读性”“编辑编稿需要”三个层面,指出新闻不能散文化。[11](77-78)梁衡先生则从文体形态的差异上指出新闻散文化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消息与散文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体形态,缺乏“化”的前提和依据——“新闻是用直白的风格突出客观的信息,文学是用含蓄的风格表达内心世界。所以新闻的典型文体——消息与文学的典型文体——散文,二者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消息不可能散文化。”[12]
“统合派”则试图结合前两派的意见,既坚持新闻文体的独立性,又强调有条件地借鉴散文笔法。面对越来越泛化的新闻散文化现象,南振中做出了相对清醒的判断:“对于任何事情,都应辩证地思考,对散文式的新闻亦应如此。几年之前,当人们还不承认它的存在之时,我们通过理论上的探讨和新闻写作的实践,为这种新的新闻文体争得一席之地;如今,当人们高度评价这种新型的新闻文体之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文体应有范围的局限性。应该说,有些新闻题材宜于采用散文式这种文体,有些新闻题材如果勉强采用这种文体来表现,就会‘弄巧成拙’。”[8](5-6)因此,所谓“散文化”也是有限度的,并非所有的新闻都能“散文化”,“新闻散文化”不是要用散文替代消息,“提倡写散文化新闻无非是为了让新闻少些八股味,更多样,更生动可感,更美。但若把所有的新闻都写成散文,是可笑的,正如要求所有散文都是新闻一样。”[8](126)
关于第三个问题新闻与文学的关系,新闻界的观点多从维护新闻文体独立性的维度出发来探讨二者的关联。名记者艾丰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指出:“新闻可以向文学‘求援’,不可以向文学‘求救’前者的努力方向是把新闻作品越写越像新闻;后者把新闻作品越写越像文学——但那是行不通的。”[13]这即是说,在具体的文体实践中,必须遵循“新闻为体,文学为用”的原则——“与其提倡一种类似的散文的新闻,不如强调,不管在消息中、通讯中、言论中,只要是有生命力的散文笔法,又能够适合新闻要求的,都应更多地吸纳融汇进来,以丰富我们的新闻武库。”[8](189-190)
总之,通过绵延十多年的学术争鸣,新闻界基本厘清了散文式新闻的内涵,进一步廓清了新闻与文学的关系,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有二:“一是新闻的形式要多样化,要不拘一格;二是在内容的表现上,要借用各种文学手法,把新闻写得生动一些,活泼一些。”[10](75)
三、“散文式新闻”的意义
“散文式新闻”从提出到最终命名,是当代中国新闻文体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无论60年代的初次实践,还是80年代之后新闻界大规模的文体实践,以及关于“新闻散文化”的争鸣,对新闻文体的发展都具有不可小觑的意义。
一是直面新闻写作的现实问题,促发新闻文体观念的变革。“散文式新闻”出现的最直接原因是为了应对新闻写作领域的现实问题和历史积弊:写法上的八股化、公式化,形式上的僵化,语言干瘪,缺乏文采等。散文笔法的“代入”是为了谋求新闻呈现的“生动”,也契合了80年代中国新闻界对于可读性的追求。所谓“可读性”,其要求是新闻写作要力求“通俗易懂、饶有兴味、真切感人、喜闻乐见。”[14]这些技法要求恰恰与“散文式新闻”的文体旨趣不谋而合:新闻写作必须首先满足受众的需要,符合受众的审美需求,为受众所喜闻乐见。简言之,散文式新闻的倡导与实践实质促发了新闻文体领域受众观念的崛起以及传媒功能的多元化转向。
二是型构新闻文体的“文学范式”,厘清了新闻与文学的关系。“散文式新闻”型构了新闻文体的“文学范式”,展示了文学因素对于新闻文体的意义与价值。一方面,散文题材广泛多样,结构自由灵活,表达方式无所不包,语言优美自然,这些特点被新闻文体吸纳与借鉴之后,“散文式新闻”遂成为“文学范式”突破新闻僵化体式的主要文体样式。“散文式新闻是新闻的简练与散文的形象生动之间的交叉。是文学对新闻的渗透。”[8](79)另一方面,新闻与文学之间的张力又通过“散文式新闻”的实践得以充分显露,新闻与文学的关系也通过“新闻散文化”的论争得以厘清。“文学创作中有许多手法可以借到新闻中来,但它始终是新闻的俘虏,而断不能导致新闻对文学的投诚。”[15]由此,记者们也在明确新闻文体实践基本规范的同时,找到了新闻借鉴文学的底线与边界。
三是实现了新闻界的思想解放,开启了新闻文体创新的大门。上世纪80年代初,“散文式新闻”的提出实质为新闻界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一个重要“切口”,也开启了新时期记者新闻文体创新的大门。穆青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就明确提及了这一点——“我提出‘散文式’的新闻,对此有褒有贬,有不同看法,这可以讨论在新闻写作方面要提倡创新,可以有不同的风格、特色。”[4](455)由此可见,穆青倡导“散文式新闻”的终极旨归是为了唤起新闻界的创新意识。思想解放的闸门一旦打开,新闻界此后创新迭起,“实录式新闻”“视觉新闻”“大特写”“思想性报道”等不同新闻文体形态层出不穷。1989年出版的《新新闻体写作》一书列举了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间出现的新新闻文体就达到22种。这一切均与“散文式新闻”的提出与实践密不可分。对此,新闻学者黎明洁女士的评价最为中肯:“散文式新闻的出现不仅是一次对报道模式单一化的成功革命,而且开启了新闻结构创新的大门,影响深远。”[16]
四、结语:新闻文体“文学范式”的型构路径
通过返观“散文式新闻”在当代新闻文体史上的生成与嬗变,我们发现,新闻文体“文学范式”的型构存在两个重要因素,其一是新闻文体本身包孕着文学的“基因”,这是“内因”,体现了新闻与文学之间的融通性,为新闻文体借鉴文学理念与手法提供了可能性。其二是社会公众对于新闻可读性、表现力的根本诉求与新闻文体僵化形式之间的“张力”,这是外因,尤其是当这种“张力”表现为新闻文体的现实困境时,新闻界就会调用文学资源“为我所用”,原本厕身于新闻文体“基因”的“文学”素质与外在于新闻文体的文学因素(理念与方法)就会被有机勾连,新闻文体“文学范式”遂得以型构。在这一点上,不论是“散文式新闻”对于散文笔法和结构的“挪借”,还是“特稿”“非虚构写作”等对于小说笔法与结构的借鉴,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