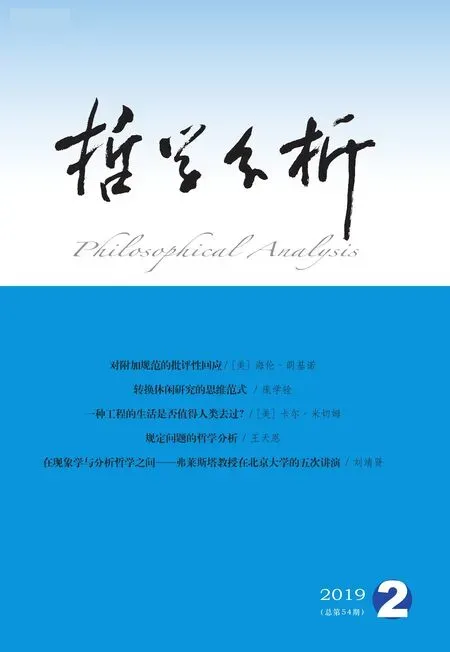如何理解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中的多样性?
2019-12-16克里斯滕因特蔓
[美]克里斯滕·因特蔓/文
张贵红/译
一、导 论
朗基诺的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CCE)提出了四个标准(公认的批判场所、接受批评、共同的标准以及知识权的平等分享),这些标准对于科学中的可转变的批判和提高科学共同体的客观性而言是必不可少的。aHelen Longino, 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 Values and Objectivity in Scientific Inqui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76.很明显,朗基诺也将参与者的多样性作为客观的科学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特征。bIbid., p.74, p.80.科学共同体内的多样性有助于确保能够考虑到更广泛的理论、模型和解释,并促进对那些偶尔限制或偏向研究的语境假设的批判性评价。尽管如此,目前尚不清楚科学共同体的多样性是不是由CCE目前提出的四个标准所保证的。本文的目的是对科学共同体的多样性是否应被理解为CCE的第五个标准的问题详加考察,如果答案为是,那么就要思考将怎样的多样性标准纳入其中才是最好的。我将论证应该将何种程度的多样性作为CCE的附加标准,尽管这也需要对我们如何构思多样性以及如何理解CCE的其他标准进行微调。我建议CCE从立场理论中吸取资源,以帮助解决多样性与其他客观性标准之间可能发生的潜在张力。
二、多样性对实现客观性重要吗?
批判语境经验论认为,并非个体科学家,而是整个科学共同体,才是客观性和知识的基础。aHelen Longino, 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 Values and Objectivity in Scientific Inquiry,p. 80; Helen Longino,The Fate of Knowled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p. 51.朗基诺承认,虽然个人独特的价值观可能导致有偏见的推理,但这些价值观的负面影响可以在科学共同体中被最小化。bHelen Longino, The Fate of Knowledge, p. 128.价值观的某些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即使正确地遵循,也没有可供选择的能够必然地阻止道德和政治价值观影响个别科学家的推理的理论规则。科学家必须依赖大量的背景假设来测试理论,包括许多在无意识中采用的理论。因此,这些背景信念总是可能受到或将包括个别科学家的价值判断的影响,其中一些可能会使科学推理发生偏向或扭曲。然而,如果以允许识别和批判性评估背景假设的方式构建科学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实现更高程度的客观性。
在朗基诺看来,科学知识是越来越客观的,因为科学共同体的组织满足以下四个条件cHelen Longino, 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 Values and Objectivity in Scientific Inquiry, p. 76.:
(1) 必须有公认的对证据、方法、假设和推理进行批判的途 径;
(2) 必须存在能够引起批判的共同标准;
(3) 整个共同体必须对这种批判作出回应;
(4) 必须在有资格的实践者中平等分享知识权。
必须有公认的批判途径,以便科学共同体的成员能够指出其他科学家采用的背景假设或方法中的问题。与此同时,必须有一些关于证据的共同标准,批判者可以利用这些标准来提升他们的批判的强度。如果没有对于什么是好证据的共同标准,那么其批判就会缺乏力量,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最终只是自说自话。当然,仅仅呼吁允许批判的共同标准还是不够的。对于批判而言,共同体成员必须是可响应的,特别是因为它还是对整个科学共同体是否被采纳进行评价所依赖的标准。相应地修改一个人的观点或者捍卫一个人的假设、方法论决策或者反对批判的数据解释(再次诉诸共同的评估标准),这样就能够实现对批判的回应或批判的不断升级。参与者还必须具有平等的知识权,他们的批判和研究才能被认真对待。批判不应该因为认识论上无关的特征而被驳回——例如科学家的种族或性别。
如果科学共同体以符合这些标准的方式被构建(当具有同等知识权和共享评估标准的参与者对研究进行充分审查时),那么就可以识别并批判地评价和纠正对科学推理产生不当影响的负担价值的假设。aHelen Longino, 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 Values and Objectivity in Scientific Inquiry, pp.73—74, p.80; Helen Longino, The Fate of Knowledge, p. 51.个别科学家很难认识到其工作何时受到他们自己的道德和政治价值观的影响,但是在共同体层面上可以确定这种偏见,因为共同体是按照 CCE的规范组织的。当然,共同体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满足这些规范,因此CCE的客观性也可达到一定程度。然而,随着这些规范日益得到满足,共同体就实现了更大的客观性。
对于CCE而言,多样性对于实现客观性的最大化也至关重要。如果在科学共同体成员之间广泛持有负担价值的假设,则它们就不太可能被识别和批判地评价。当这种价值观与某个成员本人的价值观不同时,更容易看出它们何时影响研究问题的框架、方法的选择和应用,或数据的表述或解释。因此,由具有多种道德和政治价值观的个人组成的科学共同体将能够更好地识别或捕捉价值观影响个别科学家推理的方式。bHelen Longino, 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 Values and Objectivity in Scientific Inquiry, p. 73.在价值观和利益的多样性程度更高的参与者中,更有可能在必要时识别和修正任何有问题的价值判断。实际上,一些经验研究建议,科学共同体中的多样性对于产生质量更高、影响更大的科学成果更有效。cLesley Campbell, Siya Mehtani, Mary E. Dozier, and Janice Rinehart, “Gender-Heterogeneous Working Groups Produce Higher Quality Science”, PloS one,Vol.8, No. 10, 2013, e79147; Richard Freema & Wei Huang,“Collaborating with People Like Me: Ethnic Co-Authorship within the U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Vol. 33,No. S1, 2015, pp. 289—318.因此,多样性很重要,因为它可能产生更多不同的批判观点。dIbid.
此外,那些具有不同价值观和利益的人更有可能提出和追求不同的探究路径,并持续将研究工作分配到不同的经验研究项目中。eMiriam Solomon, Social Empiricism,Boston: MIT Press, 2001, p. 151.多样性可以增加创造力fMiriam Solomon, Miriam. “Norms of Epistemic Diversity”, Episteme,Vol. 3, No. 1—2, 2006, pp. 23—36.,并引导科学家们寻求新的探索路径,寻找新的证据,提出新的假设和理论,并开发新的探究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多样性不仅可以通过纠正错误的假设,而且可以通过确保检查更全面的替代方法和模型来增强客观性。只要理论或假设经常是在替代方案中进行比较评价,就可以通过确保考虑更多的替代方案来提高客观性。
同样,当所研究的问题以不同方式被构建和探讨,这也可能增加由此产生的知识或科学产品使社会中的更多群体受益或不发生偏倚的可能性。根据他们的经验和背景,个体科学家倾向于调查对其而言重要的事情。由此产生的知识或干预措施可有助于解决不成比例地影响特定群体的问题。拥有更加多样性的科学共同体可能会增加科学知识使所有人受益或解决更广泛的问题和利益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它更有可能以更公平和更不偏倚的方式分配科学知识的益处。
科学家之间的多样性也可以通过揭示或挑战证据的趋同或集中化来增强客观性。当具有不同利益和方法的科学家以不同的方式探究问题时,它可以产生不同类型的证据,这些证据可能以集中或者非集中的方式支持更一般的假设。从多角度实现证据的集中或契合的情况更可能是客观的。
最后,科学家的多样性可以通过提高共同体内个别科学家的展示机会来促进客观性。一些研究表明,不同群体的成员更有可能在他们自己的工作中更仔细地思考并且更为严谨,因为他们知道那些具有不同观点的人会对其进行批判性的评价。aKatherine W. Phillips, “How diversity works”,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311, No. 4, 2014, pp. 42—47.也就是说,多样性可以产生一种更具创造性和竞争性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个体科学家更有可能被鼓励提出新思想、可替代的思维方法或质疑自己的假设。如果科学家知道他们可能会受到其他人质疑,他们就不太可能将某些假设视为理所当然。
可以肯定的是,(甚至在经验主义者之间)关于何种多样性对实现这些认识论效益方面有益也存在分歧。b参见Kristen Intemann, “25 Years of Feminist Empiricism and Standpoint Theory: Where Are We Now?”, Hypatia,Vol. 25, No. 4, 2010, pp. 778—796,以及 Kristina Rolin, “Can Social Diversity Be Best Incorporated into Science by Adopting the Social Value Management Ideal?”, in Current Controversies in Values and Science, edited by Kevin Elliott and Daniel Steel,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p.113—129。朗基诺认为,价值观和利益的多样性尤其重要,因为它有可能产生多个关键视角,并有助于识别和评价背景假设。但目前尚不清楚这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的多样性概念。有些人认为,所需要的是理论方法或研究策略的多样性。c参见Solomon, Social Empiricism;Kristina Rolin, “Contextualism in Feminist Epistem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Feminist Epistem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ited by Heidi Grasswick, Dordrecht: Springer,2011, pp. 25—44; Kevin Zollman, “The Epistemic Benefits of Transient Diversity”, Erkenntnis, Vol. 72,2010, pp. 17—35。随着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论方案的出现,研究精力将更加公平地分布于全方位的经验上所允许的替代方案中——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立场论的女性主义者认为,社会地位的多样性也可以产生知识层面上的益处。dKristen Intemann, “25 Years of Feminist Empiricism and Standpoint Theory”; Carla Fehr, “What Is in It For Me? The Benefits of Diversity in Scientific Communities”, in Feminist Eepistem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pp. 133—155; Sandra Harding, “A Socially Relevant Philosophy of Science? Resources from Standpoint Theory’s Controversiality”, Hypatia, Vol. 19, No. 1, 2004, pp. 25—47; Kristina Rolin, “Values, Standpoints, and Scientific/Intellectual Movements”,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56, 2016, pp. 11—19;Alison Wylie, “Femin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 Standpoint Matters”, Presidential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Pacific Division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2012.只要经验受到社会地位和交叉身份的影响,来自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就更有可能获得对某些背景假设而言更具有合理性的经验。aKristen Intemann, “25 Years of Feminist Empiricism and Standpoint Theory”; Alison Wylie, “What Knowers Know Well: Women, Work and the Academy”, in Feminist Epistem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p. 157—179.虽然可能有不同的构思多样性的方式,但大多数经验主义者无疑会同意:在任何特定研究背景下什么样的多样性能产生认知益处,这是一个经验问题。bKristen Intemann and Inmaculada de Melo-Martín, “Addressing Problems in Profit-Driven Research: How Can Feminist Conceptions of Objectivity Help?”, European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4, No. 2, 2014,pp. 135—151; Kristina Rolin, “Can Social Diversity Be Best Incorporated into Science by Adopting the Social Value Management Ideal?”虽然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来确定不同类型的多样性所可能产生的认知效益的程度,但已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参与者之间某种程度的多样性将增加科学共同体的客观性。
三、多样性是CCE的其他标准的结果吗?
人们可能会认为,根据现有CCE的四个标准,多样性已经可能产生了。如果批判的途径是公开的,那么原则上这将有助于参与对不同的科学家所组成的科学推理的评价。此外,朗基诺认为科学家不仅要对批判持开放态度,而且必须积极鼓励从不同角度进行批判性评价的机会。cHelen Longino, The Fate of Knowledge, p.132.由于要求知识权利的平等,参与者不能根据认识论层面的随意因素而被排除或忽略(例如种族、性别、价值观或利益)。此外,科学共同体必须采纳从多元视角提出的批判,而不是因某些认知无关的特征将其忽视——特别是当他们所呼吁的是共同体成员所接受的共同标准时。因此,没有任何初始原由表明为什么我们并不期望在由CCE规范构成的共同体中的科学家中找到价值观和利益的多样性(大致反映了科学所实践的更广泛社会语境下的多样性) 。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科学界的多样性是否能被CCE的四项标准所涵盖。虽然CCE的四个标准可能会消除参与科学共同体的表面障碍,但这可能不足以在实践着的科学家之间建立多样性。例如,这可能会违背知识权的平等、忽视批判或出于某些与认识论无关的特征(例如一个人的价值观)拒绝其参与,但这并不能保证科学共同体自动包含具有不同价值观和利益的参与者。科学共同体可能有义务在多元的观点中鼓励批判的公共渠道,但由于只有那些具有合适的或相关专业知识的人才被认可为有知识权,因此并不能保证具有不同价值观和利益的人能够对等地获得专业知 识。
相反,某些价值观和利益在科学史上不具有历史代表性,而其他方面则被参与者广泛认同。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某些群体的成员受到明显的歧视或者没有被给予知识权的平等——即使应该这样做,更多的微妙力量也会导致阻碍参与者的结果,即使关于知识权的正式判断并没有受到威胁。
首先,获取促进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学科利益和培训的资源并不能在人群中公平分配。aKris De Welde and Sandra Laursen, “The Glass Obstacle Course: Informal and Formal Barriers for Women Ph. D. Students in STEM field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nd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3, No. 3, 2011,pp. 571—595; Wylie, “What Knowers Know Well”.例如,在美国,三分之一的K-12学校是农村学校,五分之一的学生就读于农村学校。bLeanne Avery, “Rural Science Education: Valuing Local Knowledge”, Theory Into Practice, Vol. 52, No. 1,2013, pp. 28—35.然而,农村社区获得的教育资金少于城市的同行cKai Schafft and Alecia Youngblood Jackson, Rural Educa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dentity, Place, and Community in a Globalizing World, College Park: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对于互联网等技术的接触程度较低dLeanne Avery, “Rural Science Education: Valuing Local Knowledge”.,在招聘和留住合格的STEM教师方面有着更大的难度。eJohn W. Sipple and Brian O. Brent,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Associated with Rural School Settings”, in Handbook of Education Finance and Policy, edited by Helen Ladd & Edward. Fiske, New York: Routledge,2008, pp. 612—630.这些挑战也出现在中国的农村,农村学校有超过两千万学生。fQiao Xuefeng, “Internet Plus: Integration in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in Chinese Education, IGI Global, 2018, pp. 289—306; Wang Qiang, “Rural Students are Being Left Behind in China”, Nature News, Vol. 510, No. 7506, 2014, p. 445.许多农村的、贫穷的和本土的STEM学生也指出在学校的STEM知识与他们的当地知识实践之间存在脱节,他们认为当地知识与“现实世界”更接近,也是他们关心的事物。gLeanne Avery and Karim-Aly Kassam, “Phronesis: Children’s Local Rural Knowledge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Journal of Research in Rural Education, Vol. 26, No. 2, 2011, p. 1.这些因素对那些推行STEM教育和职业的群体更具有挑战性。
其次,即使在没有明确的知识权相区别的情况下,学院中STEM学科的文化往往也不具备广泛性。例如,对科学家的工作需求可能与养育他的家庭的责任要求不相容。hLouise Morley and Rosemary Lugg, “Mapping Meritocracy: Intersecting Gender, Poverty and Higher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Vol. 22, No. 1, 2009, pp. 37—60; Mary Ann Mason,Nicholas H. Wolfinger, and Marc Goulden, Do Babies Matter?: Gender and Family in the Ivory Tower, Rutgers: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3.某些群体可能会产生骚扰、冷漠或冷氛围,即使一个人的科学工作没有被公开对待,他也能感觉到在科学共同体中不受欢迎。iJacob Clark Blickenstaff, “Women and Science Careers: Leaky Pipeline or Gender Filter?”, Gender and Education, Vol. 17, No. 4, 2005, pp. 369—386; De Welde and Laursen, “The Glass Obstacle Course”; Wiley,“What Knowers Know Well”;Chandler Puritty, Lynette R. Strickland, Eanas Alia, Benjamin Blonder, Emily Klein, Michel T. Kohl, Earyn McGee et al., “Without Inclusion, Diversity Initiatives May Not Be Enough”,Science, Vol. 357, No. 6356, 2017, pp. 1101—1102.教学实践、指导、雇用及任期决定、引用和补助评估中的隐含偏见也为整个STEM渠道实现多样性设置了障碍a参见 Corrine A. Moss-Racusin, John F. Dovidio, Victoria L. Brescoll, Mark J. Graham, and Jo Handelsman,“Science Faculty’s Subtle Gender Biases Favor Male Student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Vol.109, No. 41, 2012, pp. 16474—16479。,因为科学家们相信他们致力于知识权的平等,所以隐含偏见的证据甚至会被恰当地忽视。bIan M. Handley, Elizabeth R. Brown, Corinne A. Moss-Racusin, and Jessi L. Smith, “Quality of Evidence Revealing Subtle Gender Biases in Science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112, No. 43, 2015, pp. 13201—13206.
特定价值观倾向于主流科学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我们当前的全球语境下,那些具有某些价值观和利益的人拥有更多的权力和资源来引导科学趋向于这些利益。科学的主要资金来自私营部门,他们可能不成比例地为具有特定价值观和利益的科学家提供资源(例如,对利润驱动研究的兴趣)。在生物医学研究中,商业利益的存在往往将研究指向能够影响医疗效益的资源。有充分证据表明,90%的生物医学研究集中于只会影响世界10%的人口的疾病。cSameera Al-Tuwaijri, Louis J. Currat, S. Davey, Andres de Francisco, Abul Ghaffar, Simon Jupp, and Christine Mauroux, “10/90 Report on Health Research 2003—2004”, Geneva: Global Forum for Health Research, 2004;Norman Daniels, Just Health: Meeting Health Needs Fair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利润驱动的研究也倾向于推动有利可图的治疗方法的研究,而不是药物研发或预防措施。dKristen Intemann and de Melo-Martín, “Addressing Problems in Profit-Driven Research”.私人资助的科学家和智库也有更多的资源来散播他们的意见或质疑对他们的经济或政治利益的不利研究,这就会使他们的批判看起来比他们在公众和政策制定者的心目中所做的更具有认识论力度eInmaculada de Melo-Martín and Kristen Intemann, The Fight Against Doubt: How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Scientists and the Publ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并转移那些一定会质疑他们的科学家的研究资源。fDavid Michaels, Doubt Is Their Product,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Naomi Oreskes and Erik M.Conway, Merchants of Doubt:How a Handful of Scientists Obscured the Truth on Issues from Tobacco Smoke to Global Warming,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0; Kevin C. Elliott, Is a Little Pollution Good for You? Incorporating Societal Values in Environmental Resear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在这些情况下,知识权的平等本身并没有受到侵犯,但某些价值和利益更有可能被过度表现而其他的则被忽 视。
实践中的科学家可能有批判的公共渠道,可能会分享评价标准、采纳彼此的批判,并在认真对待批判中互相给予知识权的平等,但这并不能保证科学共同体的组成是多样的或具有代表性。CCE客观性的四个标准是管理科学共同体的结构和实践的规范,但它们并不管科学共同体该由谁组成。因此,在使共同体的客观性最大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情况下,参与者的多样性应该被理解为CCE的第五个附加条件。
四、多样性与CCE其他标准之间潜在的张力
然而,将多样性作为CCE的第五个标准可能导致与其他客观性标准的某些张力或冲突,这取决于如何理解它们。本节将考虑这些冲突如何产生以及如何解决这些冲突。
(一) 共同标准
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共同标准需要什么,以及它如何与多样性的要求相冲突。从广义上讲,共同标准是对构成有充分理由或证据的科学探究和标准的价值承诺。aHelen Longino, 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 pp.77—78.这可能包括探究的目的以及在竞争理论之间进行选择的标准。这些标准可能包括对认识论价值的承诺,或者对产生真理论具有工具性价值的标准——如经验充分性、内部一致性或与外部其他公认理论的一致性。它们还可能包括一些所谓的“认知价值”,即能促进其他认知的或实用的科学目标的价值,如知识的扩展、简单性或解释力。bThomas Kuhn, The Essential Tension: Selected Studies in Scientific Tradition and Chan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Larry Laudan, “The Epistemic, the Cognitive, and the Social”, in Science, Values,and Objectivity, edited by Peter Machamer and Gereon Wolters, Pittsburgh: Pitts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pp. 14—23; Heather Douglas, “The Value of Cognitive VBalues”,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80, No. 5, 2013,pp. 796—806.它们也可能涉及与某些研究项目的目标相关的社会价值,例如:与特定社会需求的相关性或满意度cHelen Longino, 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 p. 77, p. 97.,或者在为公共政策提供信息方面的有用性。dHeather Douglas, Science, Policy, and the Value-Free Ideal,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9.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具有不同价值和利益的人不太可能分享这么多的标准。不同的个人价值观和利益可能导致不同的探究目标,因此不同的认知价值可以促进这些不同的目标。在共享社会或政治价值的情况下,参与者之间价值观的多样性将会降低。当然,CCE并未承诺必须共享所有的评价标准。朗基诺承认,不仅在批判性地评估背景假设,而且在评估标准本身中,都有显然存在着的认识论益处。正如朗基诺所说:“标准不是一个静态的集合,而是可能会通过参考其他标准、目标或暂时不变的价值观而被批判和改造。”eHelen Longino, The Fate of Knowledge, p. 131.朗基诺是一个关于科学的目标fHelen Longino, Studying Human Behavior: How Scientists Investigate Aggression and Sex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以及可能因不同目标而产生的潜在理论德性的多元论者。gHelen Longino, “Gender, Politics, and the Theoretical Virtues”, Synthese, Vol.104, No. 3, 1995, pp. 383—397.虽然她确定了将良好解释作为科学核心目标的宽泛目的,但她也指出有多种方法可以理解是什么构成了“良好解释”,这可能导致与这一目标的不同概念相关的各种交叉但不同的共同标准。hHelen Longino, Studying Human Behavior, p. 13.
目前尚不清楚,必须在任一时间点分享多少标准才能使可转变的批判成为可能。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论述的那样,我们可能将共同标准的需求理解成一个更强烈的需求——因为参与者必须分享多个标准并以类似的方式解释这些标准。aKristen Intemann and Inmaculada de Melo-Martin, “Are There Limits to Scientists’ Obligations to Seek and Engage Dissenters?”, Synthese, Vol. 191, 2014, pp. 2751—2765; de Melo-Martín and Intemann, The Fight Against Doubt, pp. 49—53.然而,在这种强有力的解释下,共同标准的要求将与寻求多样化的价值观、观点,甚至可能是方法论的途径之间存在张力。也就是说,共享的标准越多,某些形式的认识论多样性越可能会降低。或者,我们可能更弱地理解共同标准的要求,因为在任一时间点仅需要至少一个共同标准。bKristen Intemann and Inmaculada de Melo-Martin, “Are There Limits to Scientists’ Obligations to Seek and Engage Dissenters?”.如果参与者没有分享任何标准,那么很难看出可转变的批判是如何可能的。尽管如此,朗基诺认为共同标准可能会在不同的研究语境下发生变化、加权或解释。cHelen Longino, 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 p. 77.因此,有些人认为共同标准的需求被弱化解释只是出于对经验充分性最小承诺的需要。dKirstin Borgerson,“Amending and Defending Critical Contextual Empiricism”, European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1, No. 3, 2011, p. 435; Kristina Rolin, “Can Social Diversity Be Best Incorporated into Science by Adopting the Social Value Management Ideal?”
因此,也许CCE可以被理解为提倡某些共同标准,或者至少是对具有不同的社会、道德和政治价值观的参与者的经验充分性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共同标准将成为对多样性需求的相当小的约束。 参与者将分享对经验充足性的最低承诺,但可能仍然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这可能会导致不同的认识论益处。这种多样性会让参与者能够比较和批判性地评价不同标准下构建的假设知识,并让参与者能够从不同的视角看待事物。eHelen Longino, The Fate of Knowledge; de Melo-Martín and Intemann, The Fight Against Doubt;Wylie,“Femin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它还将有助于识别可能会不恰当地影响科学推理的价值案例。
但是,经验充分性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那些具有不同价值观和利益的人甚至可能对必须考虑哪些证据以及什么能构成经验的“成功”作出不同的判断。fKristen Intemann and de Melo-Martin, “Are There Limits to Scientists’ Obligations to Seek and Engage Dissenters?”; de Melo-Martín and Intemann, The Fight Against Doubt, p. 51.例如,那些具有不同政治价值观的人,在确定气候变化研究中的全球平均温度记录时,对纳入或排除某些数据是否合理有着不同意见,双方都坚持认为另一方忽视经验证据或有选择地采用数据。当然,我们想说某些关于经验充分性的主张是不合理的,但是对于哪些解释或理解经验充分性的方法是合理的,则需要诉诸其他关于证据的公用标准或关于是什么构成了经验充分性的共同标准。因此,认为参与者只需要分享一种评价标准是不合理的。其他标准可能是必要的,以便在具有不同价值观和利益的人之间实现可转变的批判。
尽管如此,认为可以(在共同标准和促进参与者间的多样性之间)找到一些平衡的观点是合理的。 科学共同体可能包含在价值方面不那么多样化的成员,但他们对证据标准有着稍微强一些的认同。或者,他们在尊重价值观方面可能更加多样化,并且只分享一些最低限度的评价标准。但实现这种平衡可能需要一种权衡——在参与者之间提高多样性,而这些参与者也许不会共享标准或以牺牲多样性为代价来共享标准。CCE的问题是:提高客观性的平衡点是什么?
如果我们将社会地位的多样性作为应该在科学共同体内提倡的那种多样性,那么这种张力可以被减轻,但需要略强一些的承诺来分享一些指导特定研究语境的目标和价值观。有些人认为,像公共资助的科学之类的情况,应该旨在改善社会中每个人的生活和期望,特别是那些最贫穷的或受迫切的健康或社会问题影响最为严重的人。aJanet Kourany, Philosophy of Science After Femi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这种承诺显然会限制价值观和利益的多样性,但它会以一种允许对那些分享这一目标的人提出更多关于证据标准的可转变的批判的方式来作出,并且仍然允许那些具有不同经验和社会地位的人进行批判。
(二) 采纳批判
在那些具有不同价值观和利益的人不能分享标准的情况下,他们也可能对何时适当采纳批判作出不同的判断。bKristen Intemann and de Melo-Martin, “Are There Limits to Scientists’ Obligations to Seek and Engage Dissenters?”; de Melo-Martín and Intemann, The Fight Against Doubt, pp. 46—48.采纳标准要求所有参与者要对其他人提出的批判和回应进行处理。个体的科学家必须对其他人的批判作出回应,批判者也必须积极应答异议。这并不意味着参与者必须接受某个反对意见,但他们要积极应对他人提出的批判。他们可以通过捍卫他们的方法、证据的解释和背景假设并说明反对意见为何没有根据,或相应地修改他们的观点来做到这一点。若未能参与其中,则会阻碍推进辩论所需的那种批判性论述。
然而,确定某人是否参与这种有意义的事业并非易事。cde Melo-Martín and Intemann, The Fight Against Doubt, pp. 46—47.例如,可以考虑一下在儿童疫苗安全方面的分歧。许多科学家坚持认为,他们已经提供了关于此类疫苗安全性的令人信服的证据。d参见Sander van der Linden, “Why Doctors Should Convey the Medical Consensus on Vaccine Safety”, Evidence-Based medicine, Vol. 21, No. 3, 2016, p. 119; Paul Offit, Deadly Choices: How the Anti-Vaccine Movement Threatens Us All,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1。他们使用流行病学数据来支持他们的案例并抱怨疫苗安全的批判者只是忽视了证据并重复关于自闭症与使用某些已经无信誉的疫苗之间的关系的旧论点。然而,一些关注疫苗安全性的人认为,那些持有一致观点的科学家并没有弄清楚他们的反对意见。aPru Hobson-West, “‘Trusting Blindly Can Be the Biggest Risk of All’: Organised Resistance to Childhood Vaccination in the UK”,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Vol. 29, No. 2, 2007, pp.198—215; Mary Holland,Louis Conte, and Robert Krakow, “Unanswered Questions from the Vaccine Injury Compensation Program: A Review of Compensated Cases of Vaccine-Induced Brain Injury”, Pace Envtl. L. Rev. Vol. 28, 2010, p. 480;Mark Navin, Values and Vaccine Refusal: Hard Questions in Ethics, Epistemology, and Health Care, New York: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6.他们认为,使用流行病学证据作为疫苗安全性的证据是不当的。异议者可以同意疫苗是一种良好的公共健康指标,即它们相对于人口是安全的且能获得利益。但他们坚持认为,关于疫苗安全性的说法忽视了一些儿童实际上受到伤害的事实。反对者想要的是研究为什么特定的孩子受到了伤害。也就是说,异议者关注疫苗对他们的子女的安全性,因此他们不会采取流行病学研究来应对他们的担忧。bMaya Goldenberg, “Public Mis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Reframing the Problem of Vaccine Hesitancy”,Perspectives on Science, Vol. 24, No. 5, 2016, pp. 552—581.因此,双方都认为他们的批判者没有切中要点。这种分歧的基础是各方有不同的价值观、背景假设、目的和其他评价标准。一个人是否实际采纳批判,这个问题预先假定了共同的评价标准。如果没有这样的共同标准,就无法确定什么算作挑战或回应,从而确定是否已经发生了采纳的行为。因此,当研究共同体由具有不同价值观和利益的人员组成时,他们在某些评价标准方面容易存在分歧,也就更容易出现关于采纳批判的分歧。
因此,在多样性和共同标准之间存在张力的情况下,多样性和采纳之间也存在张力。参与者的价值观和利益的多样性越大,他们越有可能具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这导致他们对是否或何时进行批判有不同的判断。
因此,解决这种张力的关键是解决多样性和共同标准方面的张力。同样,这可能需要有对于共同标准稍微强一些的概念(此处对特定研究项目中的目标和价值观要有更多的一致性)及将多样性视为关注社会地位多样性的标准及经验,而不是价值观和利益的多样性。
(三) 知识权的平等
如果我们将多样性作为CCE更进一步的要求,那么也有人担心这看起来会使价值观的表征与承认参与者之间的知识权平等相对立。如果我们以代表具有不同价值观和利益的参与者来构建科学共同体,那么有人担心这会给那些具有明显令人反感的价值观的人(如新纳粹分子)参与的权利。cDaniel Hicks, “Is Longino’s Conception of Objectivity Feminist?”, Hypatia, Vol. 26, No. 2, 2011, pp. 333—351; Kristen Intemann, “Diversity and Dissent in Science: Does Democracy Always Serve Feminist Aims?”, in Feminist Epistem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tied by Hiedi Grasswick, Dordrecht: Springer, 2011.然而,有些人认为,知识权的平等可被视为对科学共同体中可能助长的多样性的适当检查。dKristina Rolin, “Contextualism in Feminist Epistem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Kristina Rolin, “Can Social Diversity Be Best Incorporated into Science by Adopting the Social Value Management Ideal?”朗基诺对知识权适当度的要求是:具有适当专业知识的人被认为有认真地对待他们的观点的平等权利。然而,新纳粹的价值观似乎与能够将(例如)非白人视为智识上是平等的有着直接冲突。对于所有科学家的知识权平等的承诺,不应该受其种族或性别的影响。因此,这种明显的张力可以简单地通过将知识权平等视为对可能适当表征的不同价值观和利益范围的限制来解决。这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多样性与可转变的批判的其他必要条件相冲突。
然而,在确定什么构成“适当的专业知识”方面,价值观和利益的多样性和适度知识权平等之间存在更深层次的张力。科学专业知识通常以相当窄的方式进行衡量——基于诸如相关专业科学博士、同行评议的连续出版物或成功认可的著述历史等因素。aDavid Harker, Creating Scientific Controversies: Uncertainty and Bias in Science and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56.然而,采用严格的科学专业标准(或者寄予应得的适度知识权平等)可能会降低科学共同体的多样性,并提升某些主导价值观和利益的普遍性。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基于经验而非形如正式培训的知识可以产生有价值的异议。bSandra Harding, Objectivity and Diversity: Another Logic of Scientific Resear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Nicholas James Reo and Kyle Powys Whyte, “Hunting and Morality as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Human Ecology, Vol. 40, No. 1, 2012, pp. 15—27; Araújo de Sousa, Thiago Antônio,Nelson Leal Alencar, Elba Lúcia Cavalcanti de Amorim, and Ulysses Paulino de Albuquerque, “A New Approach to Study Medicinal Plants with Tannins and Flavonoids Contents from the Local Knowledge”, 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Vol.120, No. 1, 2008, pp. 72—80.
那么,科学专业知识的解释可能不那么严格,而将知识权平等给予任何可能具有批判地评价特定研究项目的背景假设、方法、目标和价值观等相关经验的人。这可能与科学共同体内多样性的最大化更加相容,但它也为那些价值观和利益可能有问题的人及有更多权力和资源来传播他们观点的人提供了便利。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私人利益集团和智库利用非经同行评审的出版物传播对气候变化的质疑,而且所利用的往往是那些有问题的专业知识。cOreskes and Conway, Merchants of Doubt, pp. 130—131.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似乎需要承认将多样性的承诺作为科学共同体客观性的一个规范,还需要对权力影响科学的产生和参与科学的方式进行批判性检验。也就是说,以提高科学共同体客观性的方式实现多样化需要识别和纠正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力量非正式地阻碍或阻止参与科学或影响科学活动和批判科学活动的传播。
我认为,这实际上是立场论者们所捍卫的观点。立场论者呼吁实现一种立场,或批判性地检验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如何排除科学中的某些特定内容并允许某些利益和价值观更具主导性的方式,以实现更多样化和更具包容性的科学共同体。要达到这一立场,就必须批判性地意识到科学知识产生的社会条件。它涉及识别边缘化群体的成员受影响的方式,包括获得较少STEM培训的机会、面临参与中的额外的社会障碍、较少对其工作的承认、对其领域的发展影响较小等。它涉及致力于改变科学实践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它正在改变这种对提高科学共同体的客观性至关重要的社会条件。此外,这是一种可能与某些价值观和利益不相容的承诺,其中一些价值观和利益往往在科学史上占主导地位。因此,实现立场就要求参与者分享某些道德和政治价值观。这表明,就多样性作为CCE的第五个规范而言,我们最好将其理解为要求参与者的社会地位和经验的多样性,而不是价值观和利益的多样性。
五、结 论
科学共同体的多样性,对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所研究的种类和最大限度地审视背景假设,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并不能仅仅通过公开的批判途径,或者要求具有知识权平等的专家接受这些批判,来实现多样化。此外,被理解为具有不同价值观和利益的参与者的多样性,可能并非增加客观性的正确的多样性,并可能导致其与CCE其他规范的张力。然而,通过将多样性理解为来自不同社会地位(种族、性别、阶层、国籍)或多个交叉身份的参与者的要求,可以消除这些顾虑。实际上,正是因为那些具有不同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人所可能有的不同的经验,使得他们能接触到不同的经验证据,这些经验证据可能正是应对背景假设和科学推理及其他方面的批判性评价所需要的。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补充和推进CCE的精神和合理的主张。当然,促进这种多样性也需要实现一个立场——或者承诺批判性地检查权力对参与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进行限制的方式。虽然CCE赞同在科学实践方面对机会均等的正式承诺,但尚不清楚这是否足以实现在认识论上有益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