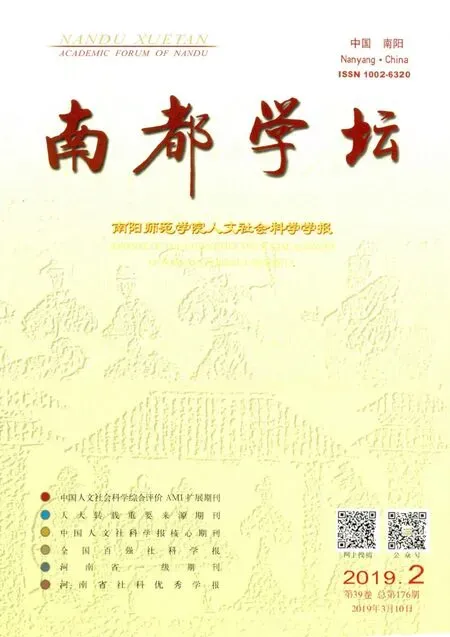政治化的民间书写
——关于赵树理创作的一种思考
2019-12-15马晓玲
马 晓 玲
(南阳师范学院 文史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
在《大戴礼记》中,有这样一段谈论士与知识分子的话:“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所由焉;虽不能尽善尽美,必有所处焉。”用这段话形容中国现代作家赵树理,再恰切不过。自20世纪40年代在解放区文坛异军突起后,赵树理的创作一直毁誉参半。而且无论是“毁”是“誉”,又常以一对关键词作为立论依据:民间/政治。可以说,政治与民间,就是赵树理创作的所“由”,就是赵树理的所“处”,得失成败,皆源于此。批评者认为赵树理很多作品都是对现实政治的形象图解,作家只不过充当了一个政治话语转述者的角色,赞扬者则认为赵树理是真正的民间文化的代表,“典型地表达了那一时期新文化传统以外的民间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抗争”[1]136。其实,这两种评判思路都有意无意地将政治与民间截然分割开来了。事实上,是“政治化的民间”,才真正构成了赵树理创作的所“由”和所“处”。所谓“政治化的民间”,简单说来,就是虽也与民间休戚与共,却又将政治化为神祇式的幽灵,让它以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方式影响、统领、支配、掌控着民间的一切。或者说,在赵树理那里,政治之于民间是灵魂、心脏、脊梁,最低也得是骨骼。只有从这个角度,或许才能真正把握赵树理创作的本质以及传统型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一
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先从最简单的两个方面来看:赵树理叙述了什么样的民间以及怎样叙述这样的民间?——这实际上就是文学书写中最基本的两个问题即“写什么”和“怎么写”的扩展性说法。
先看“写什么”。对此,赵树理说的很清楚,“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2]183。用现代文学理论术语来说,他这里的“主题”并不是“思想(theme)”,而是“素材(material)”。类似的话他还说过很多。显然,在赵树理那里,“写什么”或“不写什么”,主要取决于革命实践遇到了什么或没遇到什么。政治就像一个过滤器,民间生活尽管纷繁复杂,但哪些值得写哪些不值得写,要看它能不能与政治挂钩。赵树理把自己的写作方式形象地称为“赶任务”,“每当一个事件或运动来了之后”,“赶总比不赶好,赶得多总比赶得少好”[2]243。尽管“为政治服务”是所有政治化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将政治进一步具体化为“事件”和“运动”,仍然体现了赵树理所“为”的高度自觉。结果,如果把赵树理的所有作品按年代顺序依次排列,几乎就是一部在民间展开的中国革命史,而每部作品所使用的主干材料也都可以被简缩为具体的政治事件。比如按他自己的概括,《李有才板话》是写“减租斗争的”,《李家庄的变迁》是“动员人民参加上党战役的”,《地板》是推动“反奸、反霸、减租、退租运动的”,《两个世界》是揭露“国民党庞炳勋部队在陵川的血腥统治的”,《灵泉洞》是“响应大跃进号召的”,等等[3]376-384。至于在此期间乡土中国还发生了哪些与政治事件无甚关联的纯粹的民间事件,并不是赵树理感兴趣的题材。这当然不是说赵树理不写民间生活,相反,他提供的民间材料比许多作家都要多,对民间细节的捕捉能力也时时让人叹为观止,若干评论正是从这一点推崇赵树理的,认为“先验的观念并没有导致他对生活的简单化处理”[4]。但实际上,应该说从微观上、从表面上、从枝节上看,赵树理写出了民间的复杂,而从宏观上,从骨子里,从根本上看,这都是极为简单的复杂。打个比方,赵树理小说中的那一则则民间材料就像水面上的一圈圈波纹,作家之所以关注它们,是因为希望(也只能)借助波纹去观察那激起波纹的石子,这个石子就是政治,如果这个激起物不是石子(政治)而是其他物,赵树理就没有兴趣了,更不用说对其余平静的水面。
再看“怎么写”,也就是说如何处理民间材料,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它包括很多方面。但借巴特的看法,所有的政治化写作都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一种价值被表达出来以作为另一种价值的说明”,这“另一种价值”就是政治价值,甚至连每一个字词都“另有它意”,即政治之意[5]17。赵树理的作品就是如此,在他那里,政治就像一个编码器,民间的任何东西最终都要被编译为政治存在,都要被赋予政治意义,都要被施以政治判断。写事是这样:比如一个农民将路上的驴粪踢到自留地里而不是集体地里这种琐事,赵树理认为很值得写,但究竟“怎么写”?缺乏政治眼光的人可能会认为它至多表现了农民的小自私,虽不怎么高尚,却也没有必要上纲上线。但赵树理认为这远远不够,理所当然应该让它升华到政治高度:“靠这种人拉大车去卖(合作社的)棉花,准靠不住。”[2]542写人也是如此:比如赵树理作品中所有政治落后的形象,也同时都是违背民间伦理者。像《三里湾》中的“糊涂涂”“常有理”“能不够”“惹不起”等人,要么尖酸刻薄,要么喜欢欺负儿媳和妯娌,要么“骂死公公缠死婆,拉着丈夫跳大河”,要么整天挑拨女儿和婆家的关系。这些人物在乡土道德中肯定都不受欢迎,但赵树理这样塑造人物的目的并不是要从事文化批判,而是要将道德落后与政治落后同构起来,让前者“隐喻”后者。结果,即便一个并不赞成合作化的读者,也难以对这些人物报以好感,因为他们不仅政治落后,品德也同样令人讨厌。但在民间生活中,一个政治上不积极的农民是否在伦理上也一定存在缺陷?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赵树理并未逸出当时作家的套路:否定人的政治品质,更要否定他的道德品质,前者往往还必须通过后者来完成。虽然赵树理从来没有对这些落后人物进行严厉的清算,但这不代表他像一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真的做到了从民间看民间,在对民间同情和理解的背后,政治眼镜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甚至连写(场)景都是这样:王宝全家的院子错落有致、窗明几净,马多寿家的房子却都是“黑咕隆咚”。这自然也是作家“政治赋值”的结果,王家都是拥护合作化的人,马家却是一帮落后分子。
谈到“怎么写”,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赵树理作品中,政治被处理成了一把几乎万能的钥匙,无论民间面临什么困境,它必定都能轻松解决,这也是政治化写作的典型做法。艾艾和小晚的爱情原本困难重重,可是“因为区里说是模范婚姻,村里人除了太顽固的,差不多也都另换了一种看法”(《登记》);阎家山原本恶人当道,然而老杨等县里的干部迅速召开斗争会,“结果是老恒元把八十四亩押地全部退回原主……刘广聚由区公所撤职送县查办”,犯了错误的章工作员也做了一番“比较长期的反省”(《李有才板话》);下河村的土改原本问题百出,但上面来的工作团一驻村,立即又是“邪不压正”(《邪不压正》)。对此,日本学者洲之内彻说过一段著名的话,“读了赵树理的幸福的故事,我不知为什么有一种虚无之感。然而,这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感受吗?受到祝福的年轻恋人们形影不离,无忧无虑地生活着。他们之所以受到祝福,是因为历史的必然性,是因为他们是属于进步势力方面的人。他们之所以受到祝福,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立场正确。赵树理创造的人物,只不过是具有社会意义、历史价值的影子而已,实际上他们连反对社会权威的战斗都没参加过。新的政府和法令,如同救世主一般应声而到。道路是自动打开的”[6]406。这样的叙事方式,说轻了是浅薄,说重了是对生活和世界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的遮掩。
二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赵树理的这种写作特点?“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在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使人一目了然”,这四个要点就是“艺术家、作品、欣赏者、世界”[7]4。分析赵树理的“作品”,似乎也可以从其他三个要素着手。
先从艺术家本身来看。赵树理的身份(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首先是党的工作者,其次才是作家。一方面,政治文化对这类作家的定位是意识形态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他们被要求必须“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写作[8]848;另一方面,赵树理也真诚地认为的确应该如此,他说过,“我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做农村宣传员工作的,后来做了职业写作者只能说是转业。从这种工作中来的作者,往往都要求配合当前政治宣传任务,而且要求速效”[2]282。因此,文学创作在他看来不过是一种“助业”方式,这个“业”就是政治实践。至于写作的目的,不过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6]177,而让“老百姓喜欢看”,终究还是为了更好地“在政治上起作用”。既然如此,赵树理的作品用政治统领民间就再正常不过了。
再从世界来看——这里不妨将世界具化为时代、社会等,尽管二者并不能完全等同。谈起赵树理时代的文学生态,很多研究者都喜欢用“一体化”来概括。这个“一体化”中的“一”,就是政治,就是政治高于一切,政治统领一切。而且更确切地说,“政治一体化”并不仅仅只是体现在彼时期的文艺中,它实际上是当时整个时代方方面面的特征,大到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小到个人的思维习惯、兴趣爱好、穿着打扮等,莫不如此。赵树理作品中用政治统率民间的做法,其实就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政治一体化”追求在文学中的投影:既然在生活中政治希望掌控民间,“为政治服务”的作品自然也会如此。所以,不管作家的主观意图如何,当在小说中完全以政治过滤、编码、评判民间时,这种文学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一体化”精神的一部分。举个简单例子,不少人都注意到赵树理小说很少有风景描写,其原因一般都认为这是为了照顾农民的阅读习惯。其实关于风景问题,美国学者达比说得更深刻,文艺中“风景的再现并非与政治没有关联,而是深度植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之中”[9]9。政治权力可以将乡村的很多东西都“一体化”,但唯独对风景恐怕不能轻易改造得同质起来。同样,作家可以让政治话语统领起乡村的很多方面,却很难为一切乡村风景都进行政治编码。因此,如果一部小说充满了太多风景描写,它就必然削弱其政治性。扫描一下乡土作家及其文本,可以发现凡是热衷于风景描写的,其政治价值一般都不太强烈,孙犁喜欢写风景,结果他只能成为“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文革”期间对他的批判之一就是“作品里,风花雪月”。如此看来,政治文化能将赵树理树为一种“方向”,恐怕也是考虑到了方方面面。
再从欣赏者的角度看。这一点很好理解,受众群体的审美趣味与其所处时代的特点密切相关,或者说前者正是由后者塑造而成。在一个政治支配一切的时代,总会导致社会共同体形成普遍性的政治文化心理,这种心理会支配人们的态度、情感、习性、看待问题的方式,自然也包括艺术上的审美趣味。电视剧《赵树理》中有个镜头,《三里湾》出版后,读者欢呼雀跃、争相传诵,现在虽然无法证实其真实性,但这部小说出版时首印就是30万字,而且还被改编为电影、评剧、花鼓戏及其他地方戏,也能旁证这种现象并非绝对的虚构。实际上,在当时,情况常常是一部作品越具政治性,发行量往往越大,这也并不全是意识形态机构操控的结果,读者普遍性的政治文化心理也以普遍性的文学期待和阅读需求对政治化写作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作品如果没有政治性,人们甚至根本就没有兴趣阅读,因为他们生活的世界本身就是政治的世界。
也就是说,赵树理对民间进行政治化叙述的写作范式,既是作家的一种自觉选择,更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必然。王国维曾经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种观点也深为中国新文学作家所认同。因此,面对赵树理的政治化写作,不管如何褒贬,至少都要抱有一份“同情的理解”,也就是现在很多研究者所提倡的要尽力“触摸历史”,要尽力“回到现场”。
三
问题是,应该如何评价赵树理政治化的民间书写呢?
一方面,应该看到这种叙事范式是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特定语境下的一种必然选择。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一种启蒙型文学和启蒙型知识分子。赵树理及其创作也是如此。赵树理说自己在学生时代就爱上了新文艺,总想将那些现代思想介绍到农村,却发现很难被民众接受,于是才决定“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6]14。也就是说,这些“小本子”在内容上、思想上、精神上、价值观念上,绝不媚俗绝不迎合大众。终其一生,凡是精英知识分子批评的民间的缺陷,赵树理也都给予了同样关注。但中国现代启蒙事业总是存在着局限于抽象的话语演绎的不足,结果只能停留在“解释世界”的层次上,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借助进步的政治之手,恰恰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在现代中国,以中共为代表的政治力量与启蒙力量一定程度上是存在契合的,赵树理能走上革命道路,也是从革命中看到了能使乡村中国现代化的希望。不错,投身政治事业之后,他在作品中用政治统率起了民间,但政治也并不完全等于负面力量:三仙姑的装神弄鬼、二诸葛的阴阳八卦、老秦们的混沌懵懂、小昌们的“轮到我来捞一把”、孟祥英的婆婆对儿媳提出的种种“老规矩加上新条件”、金斗坪跪到龙王爷感动为止的求雨方式以及张家庄前现代的婚姻观念,凡此种种,都是进步的政治文化所要否定的,也是现代知识分子文化所要否定的。面对这些问题,赵树理用政治之眼观照民间,不应该受到任何指责。
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真正的启蒙并不仅仅只是批判民间,它同时还批判政治,只要政治违背了现代性方向。赵树理的政治化写作显然存在不足。由于毫无保留地确信自己投身的政治力量必定能为民间带来福祉,也唯有它才能完成这一任务,所谓的政治批判也因之打了折扣,“经是好的,让和尚念坏了”“不是如来有错,而是妖怪作孽”“不打老虎,只打苍蝇”“光明所到,黑暗自消”,这就是赵树理的政治批判的特点,自然也是局限。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终生热爱农民,愿为农民说真话”的“地之子”,如果政治力量与民间利益不尽吻合,作家又该站在哪一边?由于赵树理的人格节操令人肃然起敬,于是不少研究者就在“文如其人”的思维前提下,竭力从他作品中寻找、证明与意识形态不符的声音,以使其人其文统一起来,甚至把作家塑造成一个反主流者,这是很成问题的,也没有必要。事实上,在赵树理那里,民间性从来就没有真正压倒过政治性。最典型的就是20世纪60年代他创作的《互作鉴定》《卖烟叶》《“出路”杂谈》《复“常爱农”同学》等作品,都是批评农村青年不安心务农的。当时很多农村学生“只愿到城里找出路,只愿当干部不愿回农村”[3]264,赵树理在这些作品中对他们进行了严肃批评,引起不少青年“来信谩骂”。但这实在怪不得那些农村孩子,当时城乡差距不啻“一个在九天之上,一个在九天之下”,他们如何能不向往城市呢?不是说赵树理不明白乡间之苦,而是作为一个体制中人,他真诚地相信而且也必须相信政治表述:“劳动者最光荣。”否则他也不会将女儿送到农村,并教导她“愿你决心做一个劳动者”[3]269。再比如1956年底,一个农村青年向时任全国人大代表的赵树理写信,向他反映农村的种种困境,现在看来,这位青年所反映的还算属实,但赵树理在回信中却对他进行了一一驳斥。有意思的是,在同时期写给长治地委的信中,赵树理自己描写的农村情况竟然与这位青年的基本相似。显然,赵树理并非不相信这位年轻人的话,而是其政治身份决定了他不能不去“纠正你(来信者)的一些错误观念”。即便在农村问题最严重的那几年,赵树理也是一方面时时“为农民争口粮”,另一方面却又时时“说服农民应当如何关心国家”。这就是作家的身份分裂:一个是属于民间的赵树理,一个是属于政治的赵树理,总体上,前者要让位于后者。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后,当要代民间立言时,赵树理一般都是采用会议发言、给领导写信等方式,而不是用创作。在他看来,前些方式不仅是他作为一个体制中人应有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不会为政治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
同时,当赵树理将政治视为解决民间问题的神祇时,他并没有意识到民间的很多问题本身就是政治介入的结果。像《邪不压正》中所谓的“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10]234,就是革命自身的产物。革命到来,多数农民畏畏缩缩,流氓无产者常常首先揭竿而起,窃取尊位进而鱼肉百姓,这种事情几乎伴随了中国革命的始终。赵树理的可贵在于揭露出了这些流氓,但也就此为止,他不会也不能将思考推进一层,去反思革命本身的局限,而是又匆匆地借革命之力剪除恶霸,最后,具有自我除尘能力的革命不仅无损形象,反而更加崇高。但如果政治不能、不愿自我除尘,民间问题因之无法解决,赵树理又该如何做?他有勇气或者说有可能写出生活的真实吗?这就是建国后赵树理面临的困境:“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只好不写。”[11]153作为“有机知识分子”,赵树理将他投身的政治视为万能者,绝对相信它能为民间带来福祉,如果说这在1949年前尚能勉强维持的话,1949年后,赵树理恐怕不会想到,“无论是哪种革命的成功,通常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更具强制力的国家机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压榨农民以养活自己”[12]2。这时,作家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诚如有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如今,“随着中国‘左翼文学’地位的下降,赵树理也淡出人们的视线”[13]111。然而如果只是将赵树理“淡出人们的视线”的原因归结为“‘左翼文学’地位的下降”的整体社会语境,并不太恰当。毕竟,同是“左翼作家”,应该看到鲁迅、萧红等不仅没有“淡出”,反而在新一轮的经典化过程中,愈益巩固着自己的经典地位。回到《大戴礼记》中的那段话:“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所由焉;虽不能尽善尽美,必有所处焉”,问题是在“道统”与“政统”之间,是像鲁迅那样“空无依傍,自铸伟词”地寻求独属于知识分子的“道统”,还是像赵树理那样借助“政统”实现“道统”,这不同的所“由”和不同的所“处”,长远来看,尤其是在后革命时代,才是决定一个作家是否“淡出人们的视线”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