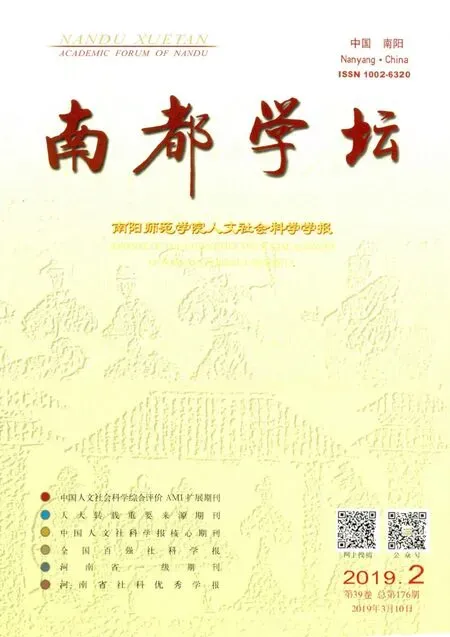《歧路灯》定位百年研究述论
2019-12-15杜贵晨
杜 贵 晨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李绿园《歧路灯》自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问世,至今(2018)已有241年。以民国七年(1918)商务印书馆出版蒋瑞藻《小说考证》,其卷八“《歧路灯》一百六十六”转录《缺名笔记》记载[1]206,第一次向全国介绍此书为界:之前百余年为传抄、评点时期;至今100年为进入了现代学术研究时期。百年《歧路灯》(以下简称《歧》)研究最早提出并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成为争议热点的问题之一,是其在文学史上的定位即“排位”,主要是与同时期成书的《儒林外史》(以下简称《儒》)、《红楼梦》(以下简称《红》)相比较,孰为高下优劣或一流、二流作品之争。当时参与者众多,留存文献亦多,是后人对这一问题“复盘”重估的根据和进一步研究的起点,也是《儒林外史》《红楼梦》研究的有益参考。至今又过去20余年,当年绚烂早归于平淡。为复活并留住记忆,方便学者了解把握这一脉学术的历史,同时促进《歧路灯》在中国小说史上定位的讨论,乃“考镜源流”,试拟名目分述诸说如下。
一、“超《红》胜《儒》”说
《歧路灯》问世流传,至《缺名笔记》作者不明就里,漫称《歧路灯》“纯从《红楼梦》脱胎”[1]206,还不曾有把《歧路灯》与《儒林外史》《红楼梦》相提并论者。至1927年朴社本《歧路灯》第一册卷首载董作宾《李绿园传略》附《(李绿园)年谱》,把《歧》和《儒》《红》三书作者生平与成书时间作一排序,突出三者在时序上的错落与衔接,虽限于《(李绿园)年谱》的体例而未做具体论述,但明显寄有三家三书并列之意,实为一种潜在的比较[2]。
最早论《歧路灯》以与《儒》《红》作三家比较的是郭绍虞《介绍〈歧路灯〉》(以下简称郭文)一文。郭先生是文学家、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家,他的文章并论三书以说《歧路灯》是一部“有价值的伟著”,曰:
然则《歧路灯》的价值又安在乎?或有人说,《红楼梦》爱情虽极细腻,而不免劝过于讽,易动人淫亵之思;《儒林外史》每写世故虽极透脱,而不免过分刻薄,亦不足动人的反省。论其影响,前者易流于为恶,后者不足以为善,至于《歧路灯》则诚如彼自序所谓,善者可以激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于彝常伦类间是煞有发明的。这样,所以他的价值要高出《红楼梦》《儒林外史》万万。此由其作用与影响来衡定文学的价值,依旧不脱旧日文以载道的见解,或不为时人所乐闻。但是,我们假使撤除了他内质的作用与影响而单从他文艺方面作一估量的标准,则《歧路灯》亦正有足以胜过《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者在。[3]
虽然郭先生的文章所据应主要是其当时所能见到的朴社本《歧路灯》第一册二十六回,但是这一册已有全书回目,所以上引郭文的判断代表了作者对《歧路灯》总体的看法。他看法的要点是说《歧路灯》思想的“价值要高出《红楼梦》《儒林外史》万万”“他文艺方面……亦正有足以胜过《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者在”,故以互文见义,概括为“超《红》胜《儒》”说。此说等于把《歧路灯》推到了中国古典小说至尊的地位,是包括大多数《歧路灯》研究者在内,古代小说的爱好与研究者大概都不知道也想不到的吧!却是百年来有关《歧路灯》文学史定位的第一说,是有人或感到不爽,但也不好无视的。
郭先生的文章之后,此说暂归于沉寂。至1980年栾星校注的《歧路灯》出版,《歧路灯》出豫省而真正走向世界,老作家姚雪垠为《歧路灯》作“序”,他认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发展有三阶段,第三为成熟的阶段,始于《金瓶梅》:
又过了大约两个世纪,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古典长篇小说发展的第三阶段才达到完成。这一阶段的标志是产生了《儒林外史》《歧路灯》和《红楼梦》……《歧路灯》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古典长篇小说由写英雄传奇转到写社会生活这一历史潮流的产物,标志着长篇小说发展史的第三阶段已经成熟。[4]3-5
《歧路灯》既然是中国长篇小说“第三阶段已经成熟”的标志,当然就是顶峰之作。虽然姚先生的《歧路灯》“序”并没有说超过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但他为什么没有说《儒》《红》也一并是“第三阶段已经成熟”的标志?而通常的理解在无特别说明的情况下,这样的“标志”应该是最典型也就是最好的,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所以姚先生此说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不好说了,但读者从字面上能理解到的意思,与上引郭文应是没有实质的差别,属“超《红》胜《儒》”说的延续。
以笔者近年的观察与感受,以上郭、姚两位先生“超《红》胜《儒》”说在今天中国大陆已作《广陵散》,当下重提也恐有读者以为怪说。但是当年郭、姚两位先生一前一后,皆大作家,深于文学创作;又皆大学问家,视学问为性命者,其说绝非戏言,更非妄语。而如今读者几个不被“红学”洗脑?又笔者岂好辩哉?实话实说而已。信不信由你,笔者是相信的[注]按据孙振杰《“文学经典”与“可居”奇货》认为,冯友兰主持出版《歧路灯》的目的“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在商业的利润上”,为此曾两次致信请胡适帮助“鼓吹”以扩大销路(张清廉主编《首届〈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然而是否郭绍虞、朱自清也是受冯之托为文“鼓吹”?则是说不定的。这里就文章论文章,不及其他。。
二、“平《红》超《儒》”
此说概括台湾学者吴秀玉教授论述而称。她于1996年出版的《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一书的《结论》中说:
不能把《歧路灯》当作一般的“世情小说”看待。而李绿园撇开文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民俗学家不说,不可否认的也是位杰出的小说家,更是一位思想家、道学家、教育家,就其《歧路灯自序》所谓的“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于彝常伦类间,煞有发明”,这个表现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师生、主仆等各方面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深具淑世教育意义的实用价值,就足以胜过《红楼梦》和《儒林外史》。[5]399
但她又说:
《歧路灯》虽在艺术成就上不如《红楼梦》,在对八股科举制度的尖锐讽刺和批判不如《儒林外史》,但在描写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作为“历史的书记官”,记录远比《红楼梦》《儒林外史》更为多彩多姿,丰富翔实……从另一个角度看,它确实补足了《红楼梦》《儒林外史》所没有写到的社会生活面……堪称是一部清初社会普通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5]382-383
笔者阅览所及,从吴教授的这部书中没有留意到有对三书比较更综合的评定,那么据此可以认为,她的看法是在思想内容上《歧》胜《儒》《红》,艺术上则《歧》不如《红》,也有“不如《儒》”的地方,但在“描写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却有“补足”《儒》《红》之所缺,从而只有《歧》“堪称是一部清初社会普通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所以她对三书比较所持的观点,虽未十分明确,但笔者从她说思想内容《歧》是第一,艺术则《红楼梦》第一,或三家各有短长,以综合并折中的结果,应该表达为“平《红》超《儒》”,即《歧》与《红》并列第一,《儒》为第二。此或有不中,还请吴教授指正。但当下自信亦不为远矣。
三、“鼎足而三”说
《歧》与《儒》《红》同在乾隆朝先后成书,是同时代的作品,又正好三部,就有了被并推为“鼎足而三”的可能。此观点最早见于1982年发表的牛懋庸《我看〈歧路灯〉》一文:
清代中叶的三部文学名著,《儒林外史》只写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范围比较狭窄;《红楼梦》主要写荣、宁二府中的人物,对荣、宁二府之外的下层社会人物写得很少;《歧路灯》则偏重对下层社会人物和生活的描写。这三部书合起来,才算是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芸芸众生思想和生活情状全貌的反映。因之,这三部书都是研究清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如果谁想了解封建社会,就应该阅读这三部巨著。从这个意义上讲,《儒林外史》《红楼梦》和《歧路灯》堪称鼎足而三的作品。[6]46
这是从描写“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芸芸众生思想和生活情状全貌……这个意义上讲”《歧》与《儒》《红》“鼎足而三”,是有前置条件的判断而不是全面的评价。但他又说:
《儒林外史》《红楼梦》和《歧路灯》三部现实主义巨著同时在这个时期出现是合乎规律的,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应运而生,都应该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6]48
这段话虽然讲得不是很具体,但是统称三者为“现实主义巨著”,又一连用了三个“都”字,强调三者价值、地位同等重要,可见上引其说“鼎足而三”又不仅是在他所说“这个意义”上,而是扩大到了“三部现实主义巨著”总体(思想与艺术)的意义上,是关于三书各自总体水准势均力敌的全面判断。
同时有刘彦钊《一部不被忘却的书》一文,认为:“李绿园……的长篇白话小说《歧路灯》是介于《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之间的一部了不起的文学巨著。”[7]也似乎接近于上引牛懋庸的“鼎足而三”说。而稍后关贤柱《〈歧路灯〉札记》的第二则标题就是《鼎足而三》,说“三书各具特点,各有千秋”。虽然还说到《歧路灯》写清代吏役、市井无赖,“则似乎又较《儒林外史》《红楼梦》二书略胜一筹”等[8],但对三书地位的总体判断仍在“鼎足而三”说之内。
以《歧》与《儒》《红》为“鼎足而三”说的实质,一是三者互相补充,缺一不可;二是三者水准相当,虽各有长短优劣,但整体上三者不必轩轾,亦难以轩轾。若作最简单的概括,此说是以三者并列第一。看起来是把《歧》也提高了,但是比较“超《红》胜《儒》”说和“平《红》超《儒》”说,还是略有下调,而且说法本身不免有些含混暧昧的嫌疑。
四、“逊《红》越《儒》”说
此说谓《歧路灯》或逊《红楼梦》一筹,而比《儒林外史》有余。最早见于上引佚名《评〈歧路灯〉》一文,开篇首列“十八世纪英国及中国最重要之小说作者数人生卒年及其书著作出版之年”,属于中国的先后是《儒林外史》《红楼梦》《歧路灯》三书,然后申明:
上表中以《歧路灯》与《石头记》《儒林外史》并列,读者或疑为不伦;而以吾人愚见,《歧路灯》比《石头记》固不足,比《儒林外史》则有余。[9]265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明确给《歧》以《红》之下、《儒》之上唯一“老二”的地位。同时又说:“《歧路灯》诚中国小说之巨擘也。”“乃写真实主义之上乘,而作者之工力技术殊为可佩者矣。”[9]269-270这篇包括各种《歧路灯》研究综述和论著都不曾引用的早期的“歧学”佳作,颇具实事求是之意,又视野宽阔、高屋建瓴,开《歧路灯》与外国小说比较研究之先河,更对《歧路灯》的文学史地位给予了较多读者容易接受的认定,是李绿园《歧路灯》定位研究的重要一环。
后来实际发挥此说的是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张国光先生。他于1982年撰文认为:“李绿园也不仅是一位小说家,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张先生又说:
我认为这部小说反映后期封建社会生活面的广度远过于《红楼梦》。若以之与“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儒林外史》比,则《歧路灯》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的深度与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较前者犹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无论它的篇幅远比《儒林外史》为浩繁了。[10]137
还说:
它确可看作是新发掘出来的一部有价值的古代小说,即使不能与稍后的《红楼梦》并驾齐驱,但也足使《儒林外史》相形见绌……而据个人浅见,《红楼梦》所反映的不过是封建社会的一角,是被围墙隔断了的小小的大观园;而《歧路灯》则在反映封建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暴露当时的魑魅魍魉的丑恶本质的深度方面超过了前者。它对我们的认识价值之大,也就不言而喻了。[10]173
上引佚名《评〈歧路灯〉》一文发表于1928年《大公报·文学副刊》第十六期,张国光先生著此文时,应该还没有读到,但他所谓“即使不能与稍后的《红楼梦》并驾齐驱,但也足使《儒林外史》相形见绌”的话,却正是佚名所说“《歧路灯》比《石头记》固不足,比《儒林外史》则有余”的翻版,实质是同一的“逊《红》越《儒》”说。两位学者悬隔50余年而能各自独立得出这一共同结论,即使不证明其结论之一定正确,也足说明总有可以如是认为的一定的根据,值得认真对待。
五、“逊《红》平《儒》”说
此说以为《歧路灯》固不如《红楼梦》,但可以与《儒林外史》“并驾齐驱”,首见于朱自清《歧路灯》一文。该文发表于郭绍虞《介绍〈歧路灯〉》同年稍后,作者虽然声称“我对本书的意见,差不多完全与郭先生相同”,实际差异颇大。朱先生肯定了《歧路灯》“在结构上它是中国旧来唯一的真正长篇小说”等观点与郭文的看法相近,但对《歧路灯》总体的评价就大不相同了。朱先生说:
若让我估量本书的总价值,我以为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11]
这就比以上诸说各下降了一定的层次,尤其比郭绍虞、姚雪垠两位的“超《红》胜《儒》”说下降了不止一两个层次,到了与《儒林外史》并列第二的地步了。
值得注意的是,为整理校注《歧路灯》“十年辛苦不寻常”(《红楼梦》语)的栾星先生持论其实相当低调,也差不多就是《红》为第一,《歧》与《儒》并列第二的意思。他在《〈歧路灯〉校本序》中比较这三部书说:
《歧路灯》的艺术成就,我初步给予这样的评价:是清人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之外,又一巨著。手笔逊色于雪芹,视之敬梓则伯仲之间,各有短长,难分高下。至于《野叟曝言》《儿女英雄传》,则难望其项背……然视之《红楼梦》及《儒林外史》,《歧路灯》有较多的毒素。[4]10-11
与上引相关,冯友兰为朴社本《歧路灯》所作“序”中提及《红楼梦》,而没有与《红楼梦》作比较,但他后来即1964年5月16日给栾星的复信中说:“我同意你对《歧路灯》的估价。不过艺术上不能跟《红楼梦》比,但也是难能可贵的了。”[5]399可见栾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持这样的看法,并且与冯友兰先生有过这方面的交流。这两位先后为整理《歧路灯》付出极大努力的大学者,作为“河南老乡”,出语谨慎,有心谦抑而无意“恭维”。
六、“远逊《红》《儒》”说
此说以为《歧路灯》虽有一定成就和特点,但总体远不如《儒林外史》《红楼梦》,当属于“第二流”甚至三流小说。首见于已故河南大学教授著名文学史家任访秋先生,他于1982年著文认为:
就这三部小说比较起来,假若把《儒林外史》《红楼梦》列为第一流,那么《歧路灯》就不能不属于第二流。因为不论是思想同艺术,较之前两书都是大有逊色的。[12]
同时又有署名雁枫《评介〈歧路灯〉》一文认为,虽然“它是与《红楼梦》《儒林外史》几乎同时并可与之并列的社会小说巨构”,但“毕竟是一部开明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小说……在思想性和社会意义上看,它还未能望《红楼梦》《儒林外史》之项背”[13]。
同年蓝翎《“埋没”说质疑——读〈歧路灯〉札记之一》一文则进一步认为:
《歧路灯》的确要宣传儒家的正统思想,把这种腐朽的思想看成人生指路的明灯……创作思想的确是中国古代小说现实主义传统精神的大倒退,大大发展了开创“人情小说”的《金瓶梅》本来就有的说教因素的落后面,使“人情小说”的发展岔向了歧路。[14]87
又说:
平心而论,《歧路灯》是一部思想平庸艺术平平的古代小说……即使比《红楼梦》开笔早十六年,它也占不了第一……(与《醒世姻缘传》)就二者思想的落后和艺术的平庸来看,“则伯仲之间,各有短长,难分高下”。它们是同一创作思潮的产物,是“人情小说”发展过程中一股混杂着更多的泥沙和腐物的浊流。[14]88-89
赞同蓝翎文章的质疑而申论之的,有1982年胡世厚先生《试论〈歧路灯〉的思想倾向》一文认为:
(《歧路灯》)迎合了清代统治阶级的需要,为其加强思想统治、笼络钳制知识分子的政策服务,它的总的思想倾向是落后的,是逆潮流而动的。[15]
1984年胡世厚先生又有《〈歧路灯〉何以遭受冷遇和流传不辍》一文认为:
《歧路灯》思想倾向落后,艺术平庸,是客观事实,因此对它评价不能太高,无论思想意义,还是艺术成就,它都远远逊色于《红楼梦》《儒林外史》,根本不能与它们比肩而立、相提并论。[16]
研究吴敬梓《儒林外史》的著名专家陈美林先生也颇为关注三书特别是《歧》与《儒》比较定位的讨论,先后有写于1983年的《〈歧路灯〉不能与〈儒林外史〉等量齐观》[17]和写于1992年的“《试论〈金瓶梅〉对〈儒林外史〉和〈歧路灯〉的影响》两文,前者主张如题,后者“意在说明《歧路灯》虽不能归之于一流作品,但也自有其价值……”[18]
《歧路灯》栾星校注本出版引起大陆古代小说学术界热议的同时,台湾读书界和出版界也及时响应。当时在台湾除有多家《歧路灯》刊本先后出现之外,也有学者著文评介研讨。据孙振杰《台湾〈歧路灯〉研究平议》一文述评,研究者除个别认同大陆肯定此书价值的主流看法,“多持对抗姿态”,“批评多于赞赏”。其中有关《歧路灯》的文学史定位:
1983年1月12日,台湾《中国时报》刊发王孝廉《〈歧路灯〉的再发现与再评价》一文指出:“这部被埋没了两百多年的小说是一本相当可读的小说,但充其量只能和另一本类似的小说《蜃楼志》相等;将它与《红楼梦》《儒林外史》并列而为清代三大小说,是有些言过其实的。”
1983年1月13日,《台湾联合报》刊登曾敏生的《再放光芒的〈歧路灯〉》)也指出:“就小说技巧及文字感染力来说,是远比不上《红楼梦》的。而《儒林外史》的嘲弄手法及‘反制’思想,也令其别树一帜……尽管如此,在《红楼梦》出现之前,《儒林外史》之后,《歧路灯》无疑是一部相当重要的作品,其整体成就实高于《野叟曝言》《儿女英雄传)等清人小说,而不应该为文学史家所忽略。”
……
1983年1月13日,《台湾联合报》发表了蔡源煌《透视〈歧路灯〉的光影》一文,文章指出:“发现了埋没两百年的作品,而这部作品如果又在水平线以上,介绍的人自然如获凤毛麟角,激情而热烈地去恭维它。若是换上我自己,必然也是这种心情和态度。然而重新评估、肯定一部被埋没的作品,倘若一味地拿它来和已成定识的经典相提并论,东比较西比较,打骨子里便不是一桩高明的事。每一部作品均有特色,各有优缺点。[19]
以上转述台湾诸家之言各有一定参考价值。如蔡源煌先生文说“每一部作品均有特色,各有优缺点”自是平情之论,但他说大陆“发现……介绍的人”(当指栾星、姚雪垠先生等)“激情而热烈地去恭维它”并非事实。如上所引及,“发现”的栾星先生比更早郭绍虞、佚名等先生的评价低调得多,而“介绍”的姚雪垠先生实际不过是支持了郭绍虞先生的论定。
顺便说到当年大陆对《歧路灯》最不看好,甚至持激烈批判态度的,一是蓝翎先生,他曾在河南“下放”多年;二是胡世厚先生,他自己就是河南人,当时还是河南社科界的官员。由此可见,对《歧路灯》褒贬两极的代表,都是在河南与此书离得最近的人,一般人情世故上看应该是高调维护此书的人,但他们的观点却几近于相反,可见论者皆出以公心,未必有私心妄意掺杂其间。而考虑到当时两岸交流初启,渠道不畅、沟通欠缺,讨论中意见较多相左,是很正常的,未必就是台湾学者“多持对抗的姿态”,还是不如此推测为好。
七、余论
李绿园《歧路灯》研究百年,以之与《儒》《红》比较“排位”只是20世纪最后20年的话题之一。当时颇显热闹,其后渐归于寂寥,至今虽亦偶见与《儒》《红》比较的说长论短,但是多属局部的斟酌,整体论定为三书“排位”的几乎没有了。而当年参与者,老成多有凋零,更几乎都退出了学术研究,唯文献犹存。今时移世易,读其文,想望当年盛况,仍不能不感慨系之。
首先,以《歧》与《儒》《红》比较“排位”有一定必然性。一是中国人最讲究“排位”的,从开会到酒筵,小说描写中也是如此,最著名的是《水浒传》写多次“排座次”可以为证。因而有《歧》《儒》《红》在小说史上的“排位”,不说顺理成章,也绝对不足为怪。二是这三部书创作问世虽有先后,而大致也是同时,又皆“人情”或“世情”题材,所以很容易引起读者作三书比较之想,甚至不有这种比较才真正不可想象。三是对事物的认识,本是有比较才有鉴别,作家作品研究用比较的方法,古今中外莫不有之。所以上引蔡源煌文说“倘若一味地拿它来和已成定识的经典相提并论,东比较西比较,打骨子里便不是一桩高明的事”,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但当时以《歧》与《儒》《红》比较“排位”的皆非专文,或是论定《歧路灯》的一种表达方式,或是顺笔而及的行于所当行,纵使算不上“高明”,但也绝非干了什么傻事,是不可以轻言废弃的。四是《歧》后出,“挺”《歧》者欲向同行读者表明自己对《歧》之价值的看法,以《歧》与《儒》《红》比较“排位”是最简当之法。即使这样做有“傍大款”甚至招摇的嫌疑,但是严肃的读者肯定只关心是非,而不会随之起舞的。总之,这个比较“排位”,本质上绝非《歧路灯》研究硬拉了《儒》《红》为之站台,而是势所必然的严肃的学术讨论;也不是“挺”《歧》者对《儒》《红》地位蓄意的挑战,而是历史上迟到“走红”的《歧》需要一个客观的参照,而恰好就有已经立足高处的《儒》和《红》,最合适地做了《歧》之位置说明的两个标杆,从而有以上褒贬不一诸说,成一段精彩,留一脉文话。
其次,“排位”之无果即是结果。上述六说虽皆不出于专论,但亦非泛言,而各有其资料与理论上的证据和分析论证。然而产生分歧和不能形成共识的根本原因,却不在任何具体的方面,也不仅是讨论得不够深入细致,而有另外的原因。一是所持标准不同。如郭绍虞在五四运动过去不久的1927年发文说《歧路灯》思想的“价值要高出《红楼梦》《儒林外史》万万”,显然是站在孔孟程朱等所谓“封建思想”无害而有益的立场上。而后来虽然过了半个多世纪,蓝翎、胡世厚两先生激烈批判的态度与言词,则根源于他们是把“儒家的正统思想”视为“腐朽的思想”。这在今天就是值得斟酌的了;又如以《歧路灯》的结局“大团圆”为“虚假”“不真实”[20],是由于认为《歧》所描写时代已是封建社会的“末世”,再有“败子回头”家业复兴之事,已经不具有文学的典型性;而郭绍虞认为这个结局的合理,则是从全书情节发展逻辑的分析得出的认识,是分歧双方审美立场标准的不同所致。二是文学作品虽然可以比较,且多半能比较出异同,也可以在个别或局部的问题上做出高下优劣的判断,但若总体上分一个输赢,其实不必要,也几乎不可能。三是读者不同,“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而作品多维多解,“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此,正如世界是多样性的,人即使能够主宰世界,也不可能完全统一世界,《歧》与《儒》《红》比较是必要的,但不会也没必要有统一的结论,过程比结论更重要。
再次,《歧路灯》地位的提高是“排位”争议的无果之果。争议本因《歧路灯》研究而起,争议的结果虽然并没有形成对《歧路灯》历史地位的明确认定,甚至还被蓝翎等学者说成了“混杂着更多的泥沙和腐物的浊流”,但这不妨在实际上仍然提高了李绿园《歧路灯》的文学与社会地位。因为很显然,中国古代“人情”或“世情”小说中,除《金瓶梅》外,不曾有任何一部长篇小说有过这样大范围内与《儒》《红》等名著一较高下的讨论机会。《歧路灯》能引出学界作这样的比较讨论,先就证明其有不凡的实力,也就是伟大的对手成就挑战者的伟大。《歧》有此被与《儒》《红》比较以在中国小说史上“排位”的荣幸本身,就是其自身价值有不让《儒》《红》处的体现。至于说法不一,不过见仁见智,而都确证了《歧》已跻身《儒》《红》之列,为同一级别“朋友圈”成员的事实。
最后,《歧路灯》的定位终将由“历史的筛选”[14]85注定。栾校本问世的近40年来,《歧路灯》定位的争议虽然大大提升了《歧路灯》的文学与社会地位,但是作家作品的历史定位归根结底不由学者们议决,而是如蓝翎先生所说经由“历史的筛选”[14]85注定。《歧路灯》广为世知的近40年虽已不短,但是比较“四大奇书”和《儒》《红》等先有定评之作,毕竟还缺乏历史的检验,我辈一方面只能耐心等待,另一方面也应积极参与促进“历史的筛选”这一过程顺利发展。如上产生过诸说的讨论就都是这参与“筛选”过程的细节,本述论则是上述“细节”的延伸,相信以后还会有人继续延伸下去。
作为《歧路灯》“历史的筛选”迄今最新的“细节”,本文有必要表明基本支持郭绍虞、姚雪垠两位已故老先生给予《歧路灯》高度评价的论定。但是,鉴于《儒林外史》的另类结构和《红楼梦》或由他人续作完成的不明确状态,笔者在郭、姚二位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歧》与《儒》《红》是可比的,已如诸说;又是不可比和不必比的,即李绿园《歧路灯》是中国古代小说独品一流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