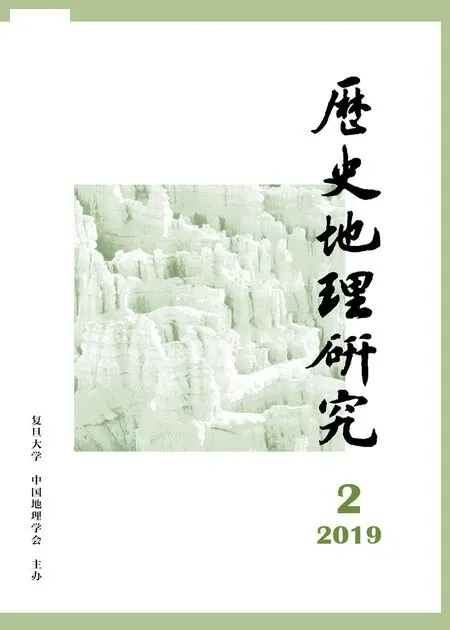《舆地纪胜》版本流传考
2019-12-15郑利锋
郑利锋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38)
学术界对《舆地纪胜》版本有所研究的,主要有谭其骧、邹逸麟、李德清、李勇先、林璜等人(1)谭其骧: 《论〈方舆胜览〉的流传与评价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24页。邹逸麟: 《〈舆地纪胜〉的流传及其价值》,《古籍整理与研究》第7期,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49—164页。李德清: 《〈舆地纪胜〉的成书年代》,《古籍整理与研究》第7期,第165—168页。李勇先: 《〈舆地纪胜〉研究》,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4—31页。林璜: 《广东粤雅堂本〈舆地纪胜〉的刊刻与价值》,《岭南文史》2012年第1期。,他们对该志版本的发现、类型和史料价值都有论述。然综观上述学者们的研究,多止于对《舆地纪胜》显见版本的介绍,而少有对其稀见版本和授受关系的考察,且对相关材料的利用也不够充分,因而搜求各种史料对《舆地纪胜》的版本流传再进行考索仍有意义。
《舆地纪胜》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地理总志,王象之嘉定十四年(1221年)《序》谓此志是“搜括天下地理之书及诸郡《图经》”“参订会稡”而成,“每郡自为一编,以郡之因革见之编首而诸邑次之,郡之风俗又次之,其他如山川之英华、人物之奇杰、吏治之循良、方言之异闻、故老之传记与夫诗章文翰之关于风土者,皆附见焉”,如此“一郡名物,亦庶几开卷而尽得之”(2)〔宋〕 王象之: 《舆地纪胜序》,《舆地纪胜》,清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刊本,第1册,第4—5页,南京图书馆藏。。李埴宝庆三年(1227年)《序》亦称此书“甚巨”,是作者“穷探力究,洞贯本剽”“积日而成”,“使人一读,便如身到其地,其土俗、人才、城郭、民人与夫风景之美丽、名物之繁缛、历代方言之诡异、故老传记之放纷,不出户庭,皆坐而得之”(3)〔宋〕 李埴: 《舆地纪胜序》,《舆地纪胜》,清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刊本,第1册,本序第1、2页。。绍定六年(1233年)(4)李裕民: 《〈舆地纪胜〉辑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期,第185页。曾鸣凤阅此书后也大为赞尚:“舆地万里,如在目前,备见学识之博、收拾之富、考究之精、会稡之勤,不胜叹伏。”(5)〔宋〕 曾鸣凤: 《舆地纪胜札子》,《舆地纪胜》,清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刊本,第1册,第6页。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首先著录此志,言“《舆地纪胜》二百卷,知江宁县金华王象之撰。盖以诸郡《图经》节其要略,而山川、景物、碑刻、诗咏初无所遗,行在、宫阙、官寺实冠其首,关河版图之未复者犹不与焉”(6)〔宋〕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1辑,现代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2页。,揭示出其史料采择的渊薮和体例内容的特征;此志虽然没有记载南宋未收复的疆域,但其史学地位和历史地理方面的价值却历来得到推崇,如钱大昕称该志虽“所载皆南宋疆域,非汴京一统之旧,然史志于南渡事多阙略,此所载宝庆以前沿革,详赡分明,裨益于史事者不少”(7)〔清〕 钱大昕: 《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四,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315页。;张金吾亦云“是书叙述详核,采摭繁富,凡沿革、风俗、形胜、景物、古迹、官吏、人物、仙释、碑记、诗文,分门胪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上可作考证地理之资,下可为登临题咏之助。其所引书,如《国朝会要》《中兴会要》《高宗圣政》《孝宗圣政》《中兴遗史》等书,皆传本久绝,藉此得考见崖略”(8)〔清〕 张金吾: 《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一五,《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9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页。。不但如此,该志的编纂还深受南宋学风的影响,凝聚着地理志书历史发展经验的结晶,所以其编排体例和考据文风深受阮元的赞誉:“南宋人地理之书以王氏仪父象之《舆地纪胜》为最善,全书凡二百卷,备载南渡以后疆域,每府、州、军、监分子目十二门……体例谨严,考证极其该洽。”(9)〔清〕 阮元: 《舆地纪胜序》,《舆地纪胜》,清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刊本,第1册,本序第1页。然而此书“自元以来,传本渐少”、明人“以后,刻本不可复得”(10)〔清〕 阮元: 《舆地纪胜序》,《舆地纪胜》,清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刊本,第1册,本序第1页。;清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时,虽知王象之“著有《舆地纪胜》二百卷”,但也“未见传本”(11)《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37页。。
对《舆地纪胜》成书与刊刻时间的考察,阮元言其《序》是作于“(宁宗)嘉定,全书之成又在理宗时矣”(12)〔清〕 阮元: 《揅经室外集》卷五,《丛书集成新编》第1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71页。;刘毓崧进一步断言,该“书成于(宝庆三年)四五月之间”,所以史事发生于此年“二、三月以前者皆可载入……至六、七月以后则不及载矣”(13)〔清〕 刘毓崧: 《通义堂文集》卷七,《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546册,第432页。。邹逸麟亦认同“该书建制以宝庆三年六月以前为断”(14)邹逸麟: 《〈舆地纪胜〉的流传及其价值》,《古籍整理与研究》第7期,第149—164页。,李德清也认为其成书不早于理宗宝庆三年年末(15)李德清: 《〈舆地纪胜〉的成书年代》,《古籍整理与研究》第7期,第165—168页。。然细考史料,又发现“书中述及(理宗)绍定年号。绍定在宝庆之后而得附载之者,盖因象之过重庆时,与人辨证夏禹之涂山,故备列其考订之语。即其为分宁县宰亦在绍定年间,而陈敏识之祠实其在任时所立,故亦纪其始末,附载于此书。盖以其与己事有关,特续补于成书之后尔”(16)〔清〕 刘毓崧: 《通义堂文集》卷七,《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546册,第432页。,可见《舆地纪胜》宝庆三年成书后又有续补,如上所收绍定三年前后为陈敏识立祠事(17)〔清〕 刘毓崧: 《通义堂文集》卷七,《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546册,第430页。和后来补入的绍定六年曾鸣凤《札子》,且所补史料一直到嘉熙年间,如对“戴挺,嘉熙二年(1238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朝请郎知,四年(1240年)十二月一日满替”(18)李裕民: 《〈舆地纪胜〉辑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期,第184页。知汀州史料的记载,便是明证。可见在宝庆三年后、嘉熙四年前,《舆地纪胜》虽然成书,但仍处于增补状态,尚未刊刻。
再考宋板《舆地纪胜》,发现书内“朗、殷、敬、徵、树、桓、巡、筠,并避宋讳”,最后避的仍是理宗皇帝讳,“盖理宗讳昀,当时以筠字及驯、巡等字俱为嫌名,故此书于筠字则改为均,于驯字、巡字则改为循”(19)〔清〕 刘毓崧: 《通义堂文集》卷七,《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546册,第431页。,可见该志刊刻于理宗时,当在嘉熙四年后的淳祐、景定年间。复考王象之的覆官,宝庆元年他在“官长宁军文学”任上,绍定三年(1230年)前后“为分宁县宰”,也正是在此任上与曾鸣凤书札往来,并由此得到荐举,由望县分宁迁至赤县江宁;“其终于何官,则不可考矣”,不过他在“嘉熙庚子(1240年)”时,“已及悬车之岁,此后即有迁擢,亦未必至显位矣”(20)〔清〕 刘毓崧: 《通义堂文集》卷七,《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546册,第430—431页。。查考在绍定末至淳祐初任江宁县令的有周大昌、惠孔时和王圭,即使到最后在景定元年(1260年)的王镗(21)《景定建康志》卷二七《官守志·诸县令》,《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786—1787页。,也没有王象之知江宁县的记载。刘毓崧认为其任江宁县令的时间是在端平三年(1236年)(22)《景定建康志》卷二七《官守志·诸县令》,《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第1786页。“七月二十九至十月十六日”间(23)〔清〕 刘毓崧: 《通义堂文集》卷七,《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546册,第430页。,可见王象之在江宁县的任职仅数十日;另在当地史志中,也未发现与《纪胜》有明显关联的史料。复考最早著录《舆地纪胜》的《直斋书录解题》,可知“陈氏书中所述南宋年号至嘉熙止,而淳祐以后未尝言及,则其成书似即在嘉熙末年”(24)〔清〕 刘毓崧: 《通义堂文集》卷七,《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546册,第430页。;然续考发现“淳祐五年(1245年)、六年(1246年),《解题》方在撰写之中”“《解题》之作,至淳祐九年(1249年)、十年(1250年)而未已也”,而“直斋盖卒于景定二年(1261年)或三年(1262年)春”(25)陈乐素: 《直斋书录解题作者陈振孙》,〔宋〕 陈振孙著,徐小蛮、顾美华点校: 《直斋书录解题·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97—701页。。可见陈氏《书录解题》著录的书籍至迟是到景定三年,因此《舆地纪胜》刊刻的时间当在嘉熙四年至景定三年间。
一、 宋刻《舆地纪胜》版本知见考
今可考见清代有两部宋刻《舆地纪胜》,一是钱曾述古堂藏本,二是陆漻佳趣堂藏本,然皆下落不明。
(一) 钱曾述古堂藏宋板足本
《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著录:“王象之《舆地纪胜》二百卷,二十本,宋板。”(26)〔清〕 钱曾: 《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卷四,《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920册,第454页。可知钱曾此部宋板《舆地纪胜》共有二十本,且“镂刻精雅、楮墨如新,乃宋本中之佳者”(27)〔清〕 钱曾撰,管庭芬、章钰校证: 《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卷二下,《清人书目题跋丛刊》第4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1页。。在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徐乾学撰就《一统志》进呈之前(28)王钟翰点校: 《清史列传》卷一《大臣画一传档正编七》,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84页。,或有对此书的利用,岑建功言:“今按《一统志》稿本,系昆山徐健庵尚书所辑,顾景范亦与分纂之列。景范与遵王皆常熟人,健庵亦与遵王同郡。其时书局设于洞庭山,所引《纪胜》或即据遵王之完本。”(29)〔清〕 岑建功: 《舆地纪胜补阙序》,《舆地纪胜》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刊本,第49册。顾广圻《校刊舆地碑记目序录》[己卯(1819年)九月]称此本“似仍系完帙”,并慨叹“不审尚在世间否”(30)〔清〕 顾千里: 《思适斋集》卷八,《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91册,第68页。,可见该本在嘉庆朝时已是罕见。
考钱曾之父,字“嗣美、名裔肃”,是钱时俊长子、钱谦益“从孙”,于“万历乙卯(1615年)以《春秋》举顺天”,“亦好聚书,书贾多挟策潜往”,因此家多宋刻孤本;后“卒于丙戌(1646年)之十月,年五十有八”,有“子四人: 长召,亦举于乡。次名,次曾,次鲁,孙男女二十三人。曾,好学能诗,藏书益富”(31)〔清〕 钱谦益: 《牧斋有学集》卷三一,《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91册,第311页。,可见钱曾藏书是在钱裔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后又累得名家典藏,所以章钰言钱曾的藏书渊源是“承父余业”,其后“又侍牧斋左右者有年”,并“累得柳大中佥、陆孟凫铣手写善本”,且与当时众多的“藏弆校订名者”相往来,“左右采获,积有岁年”(32)章钰: 《读书敏求记校证补辑类记》,〔清〕 钱曾撰,管庭芬、章钰校证: 《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清人书目题跋丛刊》第4册,第3页。。就是在此过程中,钱曾收得此本。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著录“《舆地纪胜》二百卷,宋王象之撰。《四库》未收。钱氏述古堂有宋刻足本”(33)〔清〕 邵懿辰撰,〔清〕 邵章续录: 《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82页。,即指此本。
(二) 陆漻佳趣堂藏宋刻本
王士祯《居易录》载:“仁和吴检讨志伊任臣家有《唐会典》《开元因革礼》,长洲陆医其清家有王象之《舆地纪胜》,皆宋刻。”(34)〔清〕 王士祯: 《居易录》卷一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17页。查考“陆医其清”是陆漻,“字其清,吴县人,博闻汲古,家多藏书,手抄几及千卷,有朱存理、钱穀之风,精赏鉴”(35)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七《人物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1册,第868页。。可见在陆漻的鉴藏中,有一部宋刻《舆地纪胜》。杨钟羲也称他“隐于医,善别宋元板书,所居曰听云室”,有“《佳趣堂书目》,置书年月自康熙十四年(1675年)至雍正八年(1730年),盖年八十七矣”(36)杨钟羲: 《雪桥诗话余集》卷三,民国十四年吴兴刘氏求恕斋刊本,第94页,南京图书馆藏。。可见陆漻一方面行医,一方面又置书,终老不息。在《佳趣堂置书述略》中,自言其所藏“典籍内间,有宋元刻本、宋元人钞本、明贤录本、名贤稿本、出自秘阁公卿家者、郡城故族旧所收藏者,皆传流有自……典衣节食,寒暑无间,竭六十余年之心血”蓄积而成(37)〔清〕 陆漻: 《佳趣堂置书述略》,《佳趣堂书目》,《清代私家藏书目录题跋丛刊》第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357页。;虽“足迹不出里巷”,但“名动公卿,实以身系文献之故”(38)〔清〕 叶启勋: 《佳趣堂书目序》,〔清〕 陆漻: 《佳趣堂书目》,《清代私家藏书目录题跋丛刊》第1册,第354页。。如此可见陆漻的生平志趣、置书的勤苦和藏书的成就。然检《佳趣堂书目》却未见此本,该目录收书的日期是止于雍正八年庚戌(39)〔清〕 陆漻: 《佳趣堂书目》,《清代私家藏书目录题跋丛刊》第1册,第351页。,而考王士祯《居易录》是成书于康熙“辛巳(1701年)四月”(40)〔清〕 王士祯: 《居易录》卷三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9册,第754页。,且王氏此书“于辨证古书,言之尤悉”(41)〔清〕 周中孚: 《郑堂读书记》卷五七,《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925册,第65页。,因此其上所载当是可信的,可见陆漻至迟在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前已收得该本;后来编纂目录时或是未记、或是此书已然散出,因而没见著录。
二、 明代《舆地纪胜》版本考
明代《舆地纪胜》的版本,主要有文渊阁藏“三十册”本、“十八册”本和由“三十册”本衍出的杨慎家抄秘阁本。
(一) 文渊阁藏“三十册”本和“十八册”本
《文渊阁书目》著录:“《舆地纪胜》三十册,《舆地纪胜》十八册。”(42)〔明〕 杨士奇: 《文渊阁书目》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5册,第210页。可见,在明初文渊阁内藏有两部《舆地纪胜》。查考文渊阁的藏书渊源,钱谦益云:“自有宋迄今五百余载,馆阁秘书存亡聚散之迹,可按而数也。自金元之破,汲三馆之书载之而北。建炎中兴,书之聚临安者,不减东都;伯颜南下,试朱清、张瑄海运之议,又载而之北。大将军中山王之北伐也,尽收奎章、内府图籍,徙而之南。北平之鼎既定,则又辇而之北。”(43)〔清〕 钱谦益: 《牧斋有学集》卷二六,《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91册,第251页。可见宋元明三代内阁典籍共经历了四次运转,一是北宋亡后金载之北,二是南宋亡后元载之北,三是明灭元后徙之南,四是成祖定鼎北平后复辇之北。倪燦《明史艺文志序》中,亦有类近之言。(44)〔清〕 倪燦: 《明史艺文志序》,《宋史艺文志补》,《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916册,第166页。可见上述四次皇朝内廷图籍的转移,都是发生在朝代兴亡、君权更替之际,是在当时政治、军事实力的操控下实现的,皆与朝代的更替、皇权的确立有关;所转运的典籍也都被贮在朝廷内苑,与明代文渊阁藏书一脉相承。在此时空的流转中,最终由文渊阁“合宋金元之所储而汇于一”(45)〔清〕 朱彝尊: 《曝书亭集》卷四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64页。。在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杨士奇纂成的《文渊阁书目》中,即著录了这两部《舆地纪胜》,表明在南宋之后历经元世至明前期该志仍在流传,也正是如此该志才在被称为“其书仅及元季”的“文渊之目”中得以著录(46)〔清〕 倪燦: 《明史艺文志序》,《宋史艺文志补》,《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916册,第167页。;可见上述二部《舆地纪胜》属于宋元旧本,其册数的差异当是由装帧形式的不同而致。
后来这两部《舆地纪胜》相继亡佚,宣宗“宣德八年(1433年)命少傅杨士奇、杨荣于馆阁中择能书数十人,取五经、四子及《说苑》之类,各录数本,分贮广寒、清暑二殿及琼花岛,以备观览。当是之时,典籍最盛”;“其后,内阁诸书典司者半系赀郎,于四部之旨懵如且秩卑品下。馆阁之臣假阅者,往往不归原帙。值世庙而后,诸主多不好文,不复留意查核。内阁之储,遂缺轶过半”(47)〔清〕 倪燦: 《明史艺文志序》,《宋史艺文志补》,《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916册,第166页。;至宪宗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秘阁藏书中的《舆地纪胜》已仅存“三十册”本,因为在是年(48)〔明〕 钱溥: 《秘阁书目序》,冯惠民、李万健等选编: 《明代书目题跋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39页。由钱溥父子纂定的《秘阁书目》中只著录“《舆地纪胜》,三十”(49)〔明〕 钱溥: 《秘阁书目》,冯惠民、李万健等选编: 《明代书目题跋丛刊》,第693页。,另外一部“十八册”本的《舆地纪胜》则未著录,可见该本当于此前已经佚出。再到神宗“万历间,中书舍人张萱始请于阁臣,躬自编类,更著目录,则视前所录十无二三;所增益者仅近代文集、地志,其他唐宋遗编悉归子虚无有”(50)〔清〕 倪燦: 《明史艺文志序》,《宋史艺文志补》,《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916册,第167页。;复考这部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由孙能传、张萱、秦焜等撰成的《内阁藏书目录》,已全无对《舆地纪胜》的著录(51)〔明〕 孙能传、〔明〕 张萱、〔明〕 秦焜等: 《内阁藏书目录》,《明代书目题跋丛刊》,第603页。,可见文渊阁仅存的“三十册”本《舆地纪胜》在此时也已佚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明自“祖宗以来,藏书在文渊阁,大抵宋版居大半,其地既居邃密……故抽阅甚难,但掌管俱属之典籍。此辈皆赀郎倖进,虽不知书,而盗取以市利者实繁有徒,历朝所去已强半。至正德十年(1515年)乙亥……乃命中书胡熙、典籍刘祎、原管主事李继先查对校理。由是为继先窃取其精者,所亡益多……至于今日,则十失其八”;所以至明万历年间的文渊阁藏书,已是“腐败者十二、盗窃者十五,杨文贞正统间所存文渊书目,徒存其名耳”(52)〔明〕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页、第4页。。可见文渊阁所藏这两部《舆地纪胜》多为宋版书,正是在此过程中逐次佚失的。
(二) 杨慎家抄秘阁本
崇祯三年(1630年)曹学佺《大明舆地名胜志自序》云:“予初得《太平寰宇记》钞本,为宋太平兴国间宜黄乐史所撰。上者,又得建溪祝穆所编《方舆胜览》,盖麻沙书坊板也,常置在案头……既入蜀,作《蜀中广记》当弋材于二书,又得杨用修家所抄秘阁东阳王象之《舆地纪胜》。”(53)〔明〕 曹学佺: 《大明一统名胜志》,明崇祯三年刻本,南京图书馆藏。查考“秘阁”,始设于北宋太宗时,《宋史·艺文志》载:“宋初,有书万余卷。其后削平诸国,收其图籍及下诏遣使购求散亡,三馆之书稍复增益。太宗始于左昇龙门北建崇文院,而徙三馆之书以实之。又分三馆书万余卷,别为书库,目曰秘阁。”(54)《宋史》卷二二《艺文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032页。可见秘阁实是朝廷的藏书库,此处指的是明代文渊阁。再考“曹学佺,字能始,侯官人,弱冠举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授户部主事。中察典,调南京添注大理寺左寺正。居冗散七年,肆力于学。累迁南京户部郎中,四川右参政、按察使”(55)《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400页。。其四川任职是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十一、十二月,溯江往蜀”、三十七年(1609年)“四月初三,入锦城”,至万历四十年(1612年)年“十一月、闰十一月,削两级归”、四十一年(1613年)“二、三月间归家”(56)陈庆元: 《曹学佺年表》,《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所以他入蜀“得杨用修家所抄秘阁”本《舆地纪胜》当是在万历三十七年至四十年间。
复考“杨用修”则是杨慎,《明史》载:“杨慎,字用修,新都人,少师廷和子也。”(57)《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第5081页。杨慎《四川总志序》曰:“先君子在馆阁日,尝取袁说友所著《成都文类》、李光所编《固陵文类》及《成都丙、丁》两记、《舆地纪胜》一书,上下旁搜,左右采获,欲纂为《蜀文献志》而未果也。”(58)〔明〕 杨慎: 《太史升庵全集》卷二,清乾隆六十年养拙山房刻本,第3册,第31页。可见杨慎之父杨廷和在“馆阁”任职期间,曾取阅《舆地纪胜》诸书的秘阁藏本。再考杨廷和,“字介夫,新都人”、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年)”进士、又“改庶吉士”,后“授检讨”;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进修撰。《宪宗实录》成,以预纂修进侍读……修《会典》成,超拜左春坊大学士,充日讲官”;武宗“正德二年(1507年),由詹事入东阁,专典诰敕……进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明年(1508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59)《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第5031页。,自此逐步位极人臣: 正德五年(1510年)“加光禄大夫、柱国,迁改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九月又以“功晋少傅兼太子太傅、谨身殿大学士”;七年(1512年)“十月,以荐陆完功,晋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八年(1513年)四月,为揆首”;十四年(1519年)“加特进”、十五年(1520年)“受顾命”、十六年(1521年)四月辅“世宗即位”(60)杨文才: 《杨慎学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7—51页。,其间总朝政三十七日,“诛大奸、决大策、扶危定倾、功在社稷”(61)《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赞》,第5051页。。世宗即位后又加杨廷和“伯爵”、“太傅”,然多辞;后在“世宗即位之六日……诏议其生父兴献王主礼及尊称、所谓‘议大礼’”(62)杨文才: 《杨慎学谱》,第53页。的过程中,杨氏父子秉义直谏、俱失皇宠,因而在嘉靖三年(1524年)杨廷和致仕、杨慎被谪戍云南永昌卫(63)杨文才: 《杨慎学谱》,第62页。;后至“嘉靖七年(1528年),廷和削籍”(64)杨文才: 《杨慎学谱》,第70页。,并于次年“嘉靖八年(1529年)六月二十一日”离世(65)杨文才: 《杨慎学谱》,第72页。;杨慎则一直受管控于贬所,往来于滇蜀之间,跨三十六年,再也没有回到朝廷,直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六月卒于戍所(66)杨文才: 《杨慎学谱》,第126页。。
由上可见,杨廷和是在正德二年入东阁、进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的,一直到嘉靖三年致仕,共十七年;除去正德十年(1515年)“丁忧”归家至十二年(1517年)“除服,召入阁”的时段(67)杨文才: 《杨慎学谱》,第41、45页。,都是其“在馆阁日”;因此杨廷和即是在此期间拟修蜀地文献志,为搜集资料的方便,将文渊阁藏《舆地纪胜》取读抄录,便形成了曹学佺所说的“杨用修家所抄秘阁”本。又由上可知,在明成化二十二年后文渊阁所藏《舆地纪胜》已仅存“三十册”本,所以杨慎家所抄《舆地纪胜》的秘阁底本应是此本,其性质多属影宋抄本。
嘉靖三年杨廷和致仕,此本亦随之入蜀,曹学佺后在此间任职,所以收得此书。熹宗天启六年(1626年)秋(68)《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第7400页。,曹学佺因在《野史纪略》中“为张差梃击一案”“枚举其颠末甚悉,而附珰诸公遂大切齿”,于是被“严谴,削职为民”;自此“家居二十年”,直至丙戌(1646年)九月清军入福州,自缢殉国;其藏书也由此散佚,此部杨慎家抄秘阁本《舆地纪胜》也随之飘零。(69)〔清〕 曹孟善: 《明殉节荣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雁泽先府君行述》,苏晓君、俞冰主编: 《稀见明史史籍辑存》第11册,线装书局2003年版,第16、21页。
三、 清代《舆地纪胜》版本考
《舆地纪胜》在清代的流传,主要有华希闵藏影宋抄本和何元锡藏影宋抄本以及由何元锡藏本衍出的诸多抄本和刻本。
(一) 华希闵藏影宋抄本
此本今藏于无锡图书馆,共48册,在卷第一百九十二末钤有“华希闵印”“剑光阁勘书记”两方朱印(70)〔宋〕 王象之: 《舆地纪胜》(存一六八卷),影宋抄本,第48册,无锡图书馆藏。,即是华希闵的藏书印。沈德潜《清诗别裁集》载:“华希闵,字豫原,江南无锡人,康熙庚子(1720年)举人,著有《延绿阁集》。”(71)〔清〕 沈德潜编: 《清诗别裁集(下)》卷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964页。嘉庆《大清一统志》也载:“华希闵,无锡人,由举人应博学鸿词科。乾隆十六年(1751年)高宗纯皇帝南巡,希闵献《广事类赋》《逊志录》《经史质疑》各壹帙,恩赏知县。希闵天性纯孝,笃志穷经,平生著述颇多,卒祀乡贤祠。”(72)嘉庆《大清一统志》卷八八,《四部丛刊续编》第32册,中国书店2016年版,第3906页。他担任过泾县教谕(73)〔清〕 王太岳等: 《四库全书考证》卷五七,《丛书集成新编》第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356页。,在“康熙中”刊刻了《元遗山先生集》(74)〔清〕 张穆: 《?傦?斋文集》卷三,《丛书集成续编》第138册,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593页。、“雍正中”重刻了《简端录》(75)〔清〕 周中孚: 《郑堂读书记》卷二,《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924册,第18页。。可见华希闵是一位集藏书、刻书于一身的文化名人,其出生、活动的时代远早于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才出生的何元锡。此本后归民国苏州藏书家许博明,在该本卷首曾鸣凤《札子》始页钤有“许氏珍藏”“怀辛斋珍藏印”;在“宋板舆地纪胜目录”下钤有“吴兴许博明印”“怀辛藏书”;在“舆地纪胜卷第一”下钤有“博明私印”,都是许博明的藏书印。(76)〔宋〕 王象之: 《舆地纪胜》,影宋抄本,第1册,无锡图书馆藏。可见此部影宋钞本在清康熙朝就已存在,后来传至民国许博明,今归无锡图书馆;其行款是每半页十行,行大字二十字,小字双行,行亦二十字,单鱼尾,四周双栏。查考《中国古籍总目》著录《舆地纪胜》有“清钞本,无锡(存卷一至十二、十七至二十八、三十至四十九、五十五至一百三十五、一百四十五至一百六十七、一百七十四至一百九十三)”(77)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编: 《中国古籍总目·史部》第7册,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712页。,即是此本;然与馆藏实物相核,发现此本应是影宋钞本,且卷二十九仍然见存:“卷廿九,抚州,共十四页,全”(78)〔宋〕 王象之: 《舆地纪胜》,影宋抄本,第1册《目录》,无锡图书馆藏。。虽然该本存世较早,但未经发见褒扬,所以声名不大,少有人知;从缺失卷帙判断,其所从抄的底本抑或是一部宋刻残本。
(二) 何元锡藏影宋抄本
嘉庆四年(1799年)前后是钱大昕首先发现了此本(79)〔清〕 钱大昕: 《十驾斋养新录自序》,《十驾斋养新录》,第9页。,《十驾斋养新录》载:“王象之《舆地纪胜》二百卷,予求之四十年未得;近始于钱唐何梦华斋中见影宋钞本,亟假归、读两月而终篇”,并称“此书体裁胜于祝氏《方舆胜览》,而流传绝少,又失三十二卷,想海内不复有完本也。”(80)〔清〕 钱大昕: 《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四,第315页。可见这部《舆地纪胜》影宋抄本是阙失了三十二卷的残本,但自此以后,《舆地纪胜》的传本,无论是抄本还是刻本,多源于此本。
考“何元锡,字梦华,钱唐人,监生,候补主簿”(81)〔清〕 王昶辑: 《湖海诗传》卷四四,《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626册,第402页。,出“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卒于道光九年(1829年),年六十四……客死粤中”(82)郑伟章: 《文献家通考》,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16页。,他不仅热衷诗学,“有《秋神阁诗钞》”,而且也“精于簿录之学,家多旧书善本,嗜古成癖”(83)民国《杭州府志》卷一四六《人物》,《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3册,上海书店2011年版,第489页。。何元锡离世后藏书被其子售出,严可均《铁桥漫稿》载:“梦华弃世,其子贫困,去冬(1833年)以售于秀水令陈振之(84)周季贶星诒云:“陈名征芝,非振之。严氏得之传闻,故音同字误。”参见叶昌炽: 《藏书纪事诗》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12页。。振之,闽人,罢官,本今入闽。”(85)〔清〕 严可均: 《铁桥漫稿》卷八,《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89册,第49页。可见何梦华藏书被其子售予陈征芝,何氏藏书后来随着陈氏罢官返乡而入闽,此部影宋抄本亦在其中。陈征芝《带经堂书目》著录:“《舆地纪胜》二百卷,影宋本,宋王象之撰,前有嘉定辛巳自序,宝庆丁亥李埴序及曾鸣凤札子,缺卷十三至十六、卷五十一至五十四、卷一百三十五至一百四十四、卷一百六十八至一百七十三、卷一百九十三至二百,计三十二卷。”(86)〔清〕 陈树杓: 《带经堂书目》卷二,《风雨楼丛书》,第25页,南京图书馆藏。即是此本。邓实《带经堂书目序》云:“陈氏藏书,大半归之季贶;季贶挂误遣戍,所藏遂归吴中蒋凤藻香生。”(87)〔清〕 邓实: 《带经堂书目序》,〔清〕 陈树杓: 《带经堂书目》,《风雨楼丛书》,南京图书馆藏。可见陈征芝藏书后归周星诒,周星诒藏书后又归蒋凤藻。(88)郑利锋: 《乐史〈太平寰宇记〉版本流传考》,《历史地理》第3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63—379页。查考周星诒《书钞阁行箧书目》著录“《舆地纪胜》,廿三本,影宋钞本”(89)〔清〕 周星诒: 《书钞阁行箧书目》,《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9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82页。,《周氏传忠堂书目》也著录:“《舆地纪胜》二百卷,二十三册。宋王象之撰,宋钞本”(90)〔清〕 周星诒: 《周氏传忠堂书目》,《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9册,第71页。;考蒋凤藻《秦汉十印斋藏书目录》亦著录:“《舆地纪胜》二百卷,宋王象之撰,景宋钞本。”(91)〔清〕 蒋凤藻: 《秦汉十印斋藏书目录》,《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10册,第27页。可见此部影宋抄本《舆地纪胜》即是历经陈征芝、周星诒、蒋凤藻三人递藏的何梦华藏本。蒋凤藻殁后,其藏书多归上海书店翁寿祺。(92)郑利锋: 《〈吴郡志〉版本流传考》,《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2期。
由上可见,在清代存有两部影宋抄本,无论华希闵本还是何梦华藏本都有缺卷,或许其所从抄的宋本亦是残本。华希闵活动的年代早于何梦华,其藏影宋抄本不晚于甚至早于何梦华藏本,然其版本价值却未被发现,因而流传不广。何梦华藏本则历经钱大昕、阮元等人的褒扬,广为人知,并作为底本产生了大量的抄本、刻本,在清中后期广泛传布。下面即对这些抄本和刻本一一考述。首先是清抄本。
1. 阮元内府进呈本和文选楼藏进呈副本
阮元《舆地纪胜序》曰“余昔官浙江,假何氏本影写全部,核以《舆地碑目》,较彼时(明代)(93)阮元《舆地纪胜序》言:“明人所编《舆地碑目》即就《纪胜》中‘碑记’一门钞出别行,所阙者六州一军,盖其时已佚去七卷矣”,加上后少的二十四卷,恰好是三十一卷。参见〔清〕 阮元: 《舆地纪胜》,清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刊本,第1册,本序第1页。所见又少二十四卷,共阙三十一卷”(94)〔清〕 阮元: 《舆地纪胜序》,《舆地纪胜》,清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刊本,第1册,本序第1页。,与钱大昕所言“失三十二卷”略有不同(95)阮元《舆地纪胜序》云:“《养新录》云失三十二卷,顾氏千里云其第一百三十五兴化军,钱少詹未见而云阙三十二卷,钞本有之,故今不在所数焉。今案: 竹汀先生《日记》数《纪胜》阙卷有百三十五至百四十四之语,顾说是也。”见《舆地纪胜》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刊本。而邹逸麟又认为:“按其实数则又为三十二卷,盖将卷五十濠州缺叶误作缺卷所致;今本实缺三十一卷,钱、阮均有疏略。”见《〈舆地纪胜〉的流传及其价值》,《古籍整理与研究》第7期,第153页。;由于此书“自何本之外,更无别本可以参稽,则虽有阙文,弥堪宝贵矣。嗣因《四库总目》未收此书,爰加以装潢,献诸内府,并仿当日馆中提要之式,进呈《提要》一篇。藏副本于文选楼”(96)〔清〕 阮元: 《舆地纪胜序》,《舆地纪胜》,清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刊本,第1册,本序第2页。。可见阮元此次影写何梦华藏本产生了两个抄本,一是“献诸内府”附有《提要》的进呈本,二是藏诸文选楼的进呈副本。考阮元是在嘉庆五年(1800年)正月初七日,奉上谕实授浙江巡抚;在杭期间,与何元锡熟识,“属元和何元锡修《两浙金石志》”,且于嘉庆十年(1805年)编成。阮元文选楼,则是位于扬州阮氏家庙西余地,落成于嘉庆十年(1805年)冬。复考阮元是在嘉庆十二年(1807年)十月初六日入都,二十七日诣宫门谢恩,“奉进恭注《御制味余书室随笔》二册,及《四库》未收经、史、子、集、杂书六十种,蒙赐奖览”(97)〔清〕 张鉴等撰,黄爱平点校: 《阮元年谱》,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2—23、60、64、67页。。综上可见,阮元抄录《舆地纪胜》内府进呈本和进呈副本的时间,当是在嘉庆十年至十二年十月之前。阮元进呈本《提要》云:“今于江南得影宋钞本二百卷,前有象之自序……其卷数全阙者自十三至十六、又自五十至五十四、又自一百三十六至一百四十四、又自一百六十八至一百七十三、又自一百九十三至二百,共阙三十一卷;至其余各卷内之有阙叶,又皆注明于目录卷数之下。”(98)〔清〕 阮元: 《揅经室经进书录》卷二,《清代私家藏书目录题跋丛刊》第2册,第603页。由此可知此本当时的情形。后来岑绍周借抄了阮氏进呈副本,并据以刊刻。
2. 孙星衍藏影宋写本
《孙氏祠堂书目内编》著录:“《舆地纪胜》二百卷,宋王象之撰,影宋写本,内有阙卷。”(99)〔清〕 孙星衍: 《孙氏祠堂书目内编》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92页。《廉石居藏书记内编》言此本是“何文学梦华为予以四十万钱录存,二十四册”(100)〔清〕 孙星衍: 《廉石居藏书记内编》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页。,《平津馆鉴藏记书籍》也著录此书:“《舆地纪胜》二百卷,题东阳王象之编。前有嘉定辛巳王象之自序,宝庆丁亥李埴序。此本从宋板影摹。每叶廿行,行廿字。左右栏线外,俱标卷数篇目,缺……共三十五卷。”(101)〔清〕 孙星衍: 《平津馆鉴藏记书籍》卷一,第110页。可见该本“终一百八十四卷”(102)〔清〕 孙星衍: 《廉石居藏书记内编》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页。,缺卷颇多。此本今藏于上海图书馆,钤有孙星衍的“孙忠愍侯祠堂藏书记”“孙星衍印”“五松书屋”“孙印星衍”“丁未对策上第”藏书印;此外又有“顾千里经眼记”印文和“道光八年(1828年)二月顾千里重校,时年六十三”的题记(103)〔宋〕 王象之: 《舆地纪胜》,清抄本,第1册,第1、3页,上海图书馆藏。,可见顾广圻曾校理过此本;此外还有两方印文,一是“泰峰所藏善本”,二是“茶陵谭氏赐书堂珍藏”(104)〔宋〕 王象之: 《舆地纪胜》,清抄本,第1册,第1页,上海图书馆藏。;查考“泰峰”是郁松年的号,《清朝续文献通考》载:“松年,字万枝,江苏上海人,道光乙巳(1845年)恩贡。”(105)〔清〕 刘锦藻: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六八,第3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0121页。《文献家通考》亦载:“郁松年,字万枝,号泰峰,一作泰丰,上海人。”(106)郑伟章: 《文献家通考》,第821页。可见第一方是郁松年的藏书印,其《宜稼堂书目》著录“《舆地纪胜》,抄,少一本,四匣”(107)〔清〕 郁松年: 《宜稼堂书目》,《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本,第279页。,即是此本。复考“茶陵谭氏”则是清末重臣湖南茶陵州人谭钟麟及其子谭宝箴、谭延闿及其孙谭辅宸一族(108)王钟翰点校: 《清史列传》卷六一《新办大臣传》,第4852、4856页。,可见孙星衍此本后又经郁松年宜稼堂和谭氏赐书堂收藏,再归上海图书馆。
3. 许宗彦鉴止水斋藏本
朱绪曾《开有益斋读书志》著录:“王象之《舆地纪胜》二百卷,余假钞于钱塘许子渌延润,盖周生先生鉴止水斋藏书也。”(109)〔清〕 朱绪曾: 《开有益斋读书志》卷三,《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1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版,第183页。可见朱氏开有益斋此抄本的底本是周生鉴止水斋藏本。查考“周生”是指许宗彦,《畴人传三编》载:“许宗彦,字积卿,又字周生,德清人,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性孝友……无宦情……名所居曰鉴止水斋,杜门以读书为事,垂二十年,卒于杭州,年五十有一。于学无所不通,探赜索隐,识力卓然,发千年儒者所未发,是为通儒。”(110)〔清〕 诸可宝: 《畴人传三编》卷二,《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16册,第540页。《文献家通考》载“子渌、子双,系许氏六子中之两子”(111)郑伟章: 《文献家通考》,第620页。,可见许宗彦有子六人,许子渌是其一,朱绪曾即是通过该子借得周生鉴止水斋藏书的。查考许氏藏书的渊源与亡佚,丁申《武林藏书录》载:“许氏书先得于粤东,又转得于瓶花斋零帙,实多秘笈。自子渌丈官苏、子双丈官粤,其书质于许氏辛泉家。咸丰辛酉(1861年)辛泉家为伪府,克复后为左制军行台,烧残撕毁,益不可问矣。”(112)〔清〕 丁申: 《武林藏书录》卷末,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1页。可见许氏藏书多有秘本,与吴焯瓶花斋颇有渊源;其藏书在1861年的兵乱中散亡,此本亦下落不明。
4. 朱绪曾开有益斋抄本
许宗彦此本,幸有朱绪曾开有益斋抄本。许氏父子是浙江德清人,朱绪曾恰好在此地为官,徐时栋《鄞志寓贤朱绪曾传》载:“朱绪曾,字述之,江苏上元人……道光二年(1822年)举人,历宰浙中,累迁至台州同知、候补知府,治事明决,所至无留牍。省有疑狱,辄委审断而好读书,非公事不掩卷。青鞋布袜,时出坊肆中,每见异书,即手自钞录,钩核同异,辩据明锐。”(113)〔清〕 徐时栋: 《烟屿楼文集》卷八,《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542册,第307页。光绪《嘉兴府志》也载其“尤嗜古书。公余,屏驺从,走书肆,见宋元版本必购归”(114)光绪《嘉兴府志》卷四二《名宦·朱绪曾传》,《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浙江省第53册,据清光绪五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0年版,第1056页。。可见朱绪曾一直有意于收书抄书,因此他借抄许氏鉴止水斋藏书,实是其志趣使然。“咸丰癸丑(1853年),粤寇陷江宁”,朱绪曾“所居秦淮水榭,藏书十数万卷”(115)〔清〕 甘元焕: 《开有益斋读书续志跋》,《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16册,第633页。尽成灰烬,时其“方官浙中,慨收藏之灰烬,因取旅次所存数十箧,日夕关览,掇其大旨,若考证之词,笔之别简,其假自友朋者亦为题记”,撰成了“《读书志》六卷”(116)〔清〕 刘寿曾: 《开有益斋读书志跋》,《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16册,第533页。。此本即著录其间,可见此抄本当借抄于咸丰三年前。朱氏藏书在绪曾“咸丰季年卒”后(117)〔清〕 徐时栋: 《烟屿楼文集》卷八,《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542册,第307页。,由于兵乱其子朱桂模在“咸丰辛酉(1861年)冬,仓皇避地。侨沪渎,僦湫隘屋以居,无过问者”(118)〔清〕 朱桂模: 《开有益斋读书志跋》,《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16册,第539页。,“后不知散于何家”(119)郑伟章: 《文献家通考》,第835页。,此本亦不复闻。
5. 杨文荪藏影抄宋本
杨文荪“字芸士,海宁贡”(120)〔清〕 潘衍桐: 《两浙轩续录》卷一九,《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685册,第489页。,“嘉庆六年(1801年),与顾广圻、臧镛、何元锡等应阮元之聘,同辑《十三经校勘记》”(121)郑伟章: 《文献家通考》,第705页。。可见杨文荪与顾广圻、何元锡交厚,且“亦好藏书”(122)〔清〕 叶昌炽著,王欣夫补正,徐鹏辑: 《藏书纪事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第671页。,“自幼购求书籍,积十年,所藏不下五万卷。凡旧抄及难得之本,无不竭力搜访。闻藏书旧家有秘本,必借抄,或辗转托人抄录”(123)郑伟章: 《文献家通考》,第705页。,杨氏有如此的藏书热情,何元锡又藏有影宋抄本《舆地纪胜》这一难见之书,且二人又同应阮元之聘而共事,其不会不知,所以杨氏此本也当是抄自何梦华藏本,因此伍崇曜言杨氏此影抄宋本与陈其锟藏本“所出无异”(124)〔清〕 伍崇曜: 《舆地纪胜序》,《舆地纪胜》,南海伍氏粤雅堂清咸丰十年刊本,第1册,南京图书馆藏。(见下文)。杨氏此本今藏于国家图书馆,《中国古籍总目》著录的《舆地纪胜》“清钞本,国图(存卷一至十二、十七至四十九、五十五至一百三十五、一百四十五至一百六十七、一百七十四至一百九十三)”(125)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 《中国古籍总目·史部》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712页。,即是此本。在该本“宋板舆地纪胜目录”“卷一”“卷一百九十二”下钤有“海宁杨芸士藏书之印”,即是明证;此外还钤有“树基校书之印”“常熟鲍芳谷过眼”藏书印(126)〔宋〕 王象之: 《舆地纪胜》,清抄本,国家图书馆藏。,可见此本历经鲍振方、杨文荪、陆树基等递藏或勘校,再归今国家图书馆。
6. 吴兰修秘籍本→陈其锟珍藏本
此本是伍崇曜粤雅堂咸丰五年(1855年)刻本和咸丰十年(1860年)重修本的底本(见下文)。吴兰修“字石华,嘉应州人,嘉庆戊辰(1808年)举人,官信宜训导”(127)〔清〕 陈璞: 《尺冈草堂遗集·遗文》卷四,《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547册,第657页。,“为广东知名士,阮相国总制两广时……建立学海堂以课士,首选石华为学长”(128)〔清〕 阮元撰,罗士琳续补: 《畴人传》卷五一,《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16册,第511页。;“兰修枕经葄史,无所不通”,“兼治经解诗赋”,“工诗文”(129)〔清〕 陈璞: 《尺冈草堂遗集·遗文》卷四,《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547册,第657页。,“自榜其门曰经学博士,藏三万卷书”(130)〔清〕 陈璞: 《尺冈草堂遗集·遗文》卷四,《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547册,第657页。,有藏书处书巢、桐华阁、守经堂(131)郑伟章: 《文献家通考》,第639页。,此本即是其所藏“秘籍”之一;后又由陈其锟“珍藏”,伍崇曜言此本是“岭南幸存”的《舆地纪胜》“副本”(132)〔清〕 伍崇矅: 《舆地纪胜序》,《舆地纪胜》,南海伍氏粤雅堂清咸丰五年刊本,第1册,南京图书馆藏。,因而借出作为底本加以刊刻,收入《粤雅堂丛书》。
7. 孙尔准藏嘉庆影宋抄本
冯登府《跋》云:“王仪父《舆地纪胜》二百卷……此本鄞令程侯以佛饼四百购于吴门以赠孙文靖公,为旧钞本,少三十二卷……是书宇内只有数本耳。庚寅(1830年)初夏书于四明轩。”(133)〔清〕 冯登府: 《石经阁文初集》卷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4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30页。可见孙尔准藏有一部《舆地纪胜》旧抄本,是“鄞令程侯”赠送的。查考“程侯”是程璋,同治《鄞县志》卷十八《职官表》“道光”条载:“程璋,字麟章,江苏宜兴人,举人,七年(1827年)七月任,八年(1828年)七月以本省帘差去任……程璋,再见,八年十月回任,十三年(1833年)五月告病。”(134)同治《鄞县志》卷一八《职官表·道光》,清同治七年至十三年修,徐时栋烟屿楼稿本,《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41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158页。可见程璋从道光七年至十三年两任鄞县知县,之间仅隔两月;冯登府此跋作于道光十年(1830年),可见程璋是在道光七年至十年间从吴门购得此本赠给“孙文靖公”的。
复考“孙文靖公”是孙尔准。《清史稿》载:“孙尔准,字平叔,江苏金匮人”,“嘉庆十年(1805年)进士”,在“道光元年(1821年)调广东布政使,擢安徽巡抚;三年(1823年)调福建巡抚;五年(1825年)擢闽浙总督;七年(1827年)入觐,宣宗……赐其子慧翼官主事;十一年(1831年)以病乞休;逾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文靖。”(135)《清史稿》卷三八《孙尔准传》,第38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612页。可见孙尔准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地方大员,且是在其晚年收得此本。再考“冯登府,字柳东,嘉庆戊寅(1818年)顺天举人,庚辰(1820年)进士……教授宁波……生平劬书媚学,著述等身……中年游闽,修《盐法志》《福建通志》,名震海峤间”(136)光绪《嘉兴府志》卷五《列传·冯登府传》,《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1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408页。。可见冯登府是一位醉心于学问著述的人;他中年之所以“游闽”,正是“应孙尔准邀”(137)郑伟章: 《文献家通考》,第706页。,可见二人关系密切。不但如此,冯登府还与李富孙熟识,《清史列传》载他“与同县李富孙交尤密,每著一书,辄与商榷”(138)王钟翰点校: 《清史列传》卷六九《儒林传下》,第5597页。。可见孙尔准将此书交给李富孙校勘,当与冯登府的推介有关。
再考李富孙在“嘉庆六年(1801年)拔贡生”,其“学有所本……肄业诂经精舍,遂湛深经术……著《七经异文释》”,“同里冯登府称其详该奥博,为诂异义者集其大成”(139)王钟翰点校: 《清史列传》卷六九《儒林传下》,第5595页。,可见李富孙经学精湛,学识渊深,所以孙尔准请他校理此本。李富孙《校经庼题跋》云:“宋嘉定间东阳王象之著《舆地纪胜》二百卷,世鲜流传……今仅有写本……近海昌马氏(思赞)购得一本,即从张氏(金吾)传写。庚寅(1830年)冬,制府宫保孙公自闽邮寄是书属富孙雠校,因向马氏乞借,互为校勘,其失去三十二卷,两本皆同……公所藏本较似旧钞,然遇仁宗皇帝庙讳上一字间有缺笔,则亦为嘉庆间所钞……两本皆影宋钞,然互有阙叶及脱落字,似又非从一本钞出,已并为补录。”(140)〔清〕 李富孙: 《校经庼题跋》,《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9册,第587页。可见孙尔准是在道光十年冬将此本寄予李富孙,属其校勘的;李富孙承命后,借得马思赞藏本相校,判定孙氏此本是嘉庆间的“影宋钞本”;而之所以又言孙本与马本不同,则是因为马本在据张金吾藏本传抄后又经过了添改(见下文),三本实则同源于何元锡藏本。
孙尔准有二子: 孙慧惇、孙慧翼,“慧惇,山东利津县知县。慧翼,赏兵部员外郎,升郎中候选道”(141)王钟翰点校: 《清史列传》卷三五《大臣传次编》,第2784页。。此本后由孙慧翼续藏,之后散出,民国时傅增湘收得此本。《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舆地纪胜》二百卷,宋王象之撰……存一百六十八卷,旧写本,十行二十字,注双行同,照宋本传录……钤有‘艳秋阁物’‘研樵藏书之章’‘湛华阁藏书’各印记……此书虽残佚,犹存宋刊面目,亦足珍也。[韩左泉送阅,索二百元,戊辰岁(1928年)收]”(142)傅增湘: 《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80页。可见傅增湘是在民国十七年得见该本;查考“韩左泉”则是“京师琉璃厂书贾”“会文斋何厚甫”之甥,“亦颇识书,唯贪欲过重。尝往来达官大宅,学部侍郎宝丰、练兵大臣凤山等多受其欺”(143)〔清〕 胡思敬: 《国闻备乘》卷三,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9页。;傅增湘喜收书且在“一九二七年十月曾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44)郑伟章: 《文献家通考》,第1408页。,所以韩氏才奔走送阅,傅氏也因此收得此书。
查考上述藏书印,其中“艳秋阁物”“孙印慧翼”和“孙氏家藏”是孙慧翼的藏书印,其常用的有两方,“分别是白文‘孙慧翼印’和朱文‘艳秋阁物’”(145)茅威放: 《华嵒〈松竹绶带轴〉再认识》,《东方博物》2010年第1期。。该本后从孙家散出流入市肆,被“研樵”购得,所以书衣上才有“同治元年(1862年)秋初,购于厂肆之同文堂,研樵识”的题记和“研樵藏书之章”的藏书印。而考“研樵”在清代则有两人,一是“张研樵敦培,吴县人,翟云屏弟子,精鉴藏、工书画。书得衡山翁秀实,画亦如之,名噪吴中”的书画家(146)〔清〕 孙茂炯: 《如画楼诗钞跋》,张培敦: 《如画楼诗钞》,《丛书集成续编》第136册,第914页。,二是“甘肃巩秦阶兵备道董公……文焕,字尧章,研樵则其别署”的朝廷要员;然以能在“同治元年秋”尚在世购书的条件相限,则知此处的“研樵”是董文焕,因其“生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十二日卒秦州新署”(147)〔清〕 翁同龢: 《董文涣墓志铭》,董寿平、李豫主编: 《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董研樵先生年谱长编》第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页。,而张敦培则“生于乾隆辛卯(1771年),历嘉、道两朝,以布衣负盛名”(148)〔清〕 孙茂炯: 《如画楼诗钞跋》,张培敦: 《如画楼诗钞》,《丛书集成续编》第136册,第914页。,在同治朝时已经过世。可见该本《舆地纪胜》从孙慧翼家散出后,辗转于市肆、后在同文堂被董文焕购得。
董文焕此本后又归王懿荣,其上钤有“湛华阁藏书”印,即是明证,“王懿荣,字正孺,山东福山人”,“光绪六年(1880年)成进士”(149)《清史稿》卷四六八《王懿荣传》,第42册,第12778页。,“及官京师,食不兼味,每至厂肆,见宋元旧本及古器物,必尽力购置……其藏书印有‘湛华阁藏书印’‘福山王氏正孺藏书’朱长方等”,“卒后,所藏图籍、金石大半散佚。后人将书抵押于书贾,积久益贫,不能复取”,遂“售之押主”(150)郑伟章: 《文献家通考》,第1152页。。考此“书贾”“押主”是谭笃生,胡思敬《国闻备乘》载清末“京师琉璃厂书贾凡三十余家,唯翰文斋韩氏席先世旧业,善结纳,资本尚充,收藏较他商为富。其能辨古书贵贱者,推正文斋谭笃生、会文斋何厚甫……予初至京,潘祖荫、盛昱,王懿荣皆好蓄书……后数年,祖荫之书归翰文,懿荣之书归正文”(151)〔清〕 胡思敬: 《国闻备乘》卷三,第99页。,可见王懿荣藏书即归谭笃生的正文斋;该藏本也正是由谭笃生之甥韩左泉送阅傅增湘而被傅氏收得的,《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目录》著录此本为“清写本,十行二十字,注双行同,版心记大小字数,左栏外记篇名,标题双钩白文,札子影写手迹,是影写宋刊本。钤有‘湛华阁藏书’等印。存一百六十八卷。余藏”(152)〔清〕 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熹年整理: 《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目录》卷五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页。。
傅增湘此本后归国立北平图书馆,抗战期间暂存于上海租界,后又转寄美国国会图书馆,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著录:“《舆地纪胜》二百卷,六十四册(北图),钞本,宋王象之撰。按是书后出,《四库全书》不载,阮元始进呈。嘉道间学人所见,皆从何梦华处转录,惜诸家不记何本从何来……甘泉岑建功、南海伍崇曜均有翻刻本。余校以伍本,阙卷与此相同,盖诸本皆从一本出故也。此本书衣有题记云:‘同治元年秋初,购于厂肆之同文堂,研樵识。’首页钤‘研樵藏书之章’‘艳秋阁物’两印,余卷有‘湛华阁藏书’‘孙印慧翼’‘孙氏家藏’等印记,疑原为孙氏钞藏,又据扬州马氏本签校者也。”(153)王重民: 《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抗战胜利后,该本被转运至台北,因台北“中央图书馆”条件有限,借用台北“故宫博物院”库房庋藏,可见此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154)《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编委会: 《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出版缘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本序第4页。查考该馆《善本书目》著录:“《舆地纪胜》存一百六十六卷、六十四册,宋王象之撰,旧钞本,黑笔签校,缺……凡三十四卷,北平。”(155)台北“中央图书馆”特藏组: 《台北“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增订二版),台北“中央图书馆”1986年编印,第257页。即是此本。另从上述王重民将此本与“伍本”相校的结果可知,伍崇曜粤雅堂刊本与此本的版系相同,可见伍氏刊本及其底本吴兰修藏本也是出自何氏藏本。
8. 张金吾爱日精庐藏影写宋刊本→瞿镛铁琴铜剑楼藏本
《爱日精庐藏书志》著录:“《舆地纪胜》二百卷,影写宋刊本,从钱唐何氏藏宋刊本影写……共阙三十二卷。”(156)〔清〕 张金吾: 《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一五,《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925册,第361页。可见张氏爱日精庐此本也是从何梦华藏本影写,当然何氏藏本是影宋抄本而非宋刊本。该《藏书志》著录的都是“宋元旧椠及钞本之有关实学而世鲜传本者”(157)〔清〕 张金吾: 《爱日精庐藏书志·例言》,《清人书目题跋丛刊》第4册,第275页。,可见此本在张金吾整个藏书中的地位。张氏晚年经济困顿,“道光六年(1826年)七月二十九日,从子承焕取爱日精庐藏书十万四千卷去,偿债也”(158)〔清〕 张金吾: 《言旧录》,民国二年刻本,南京图书馆藏,第29页。,其藏书由此散去;该本也流出,后归瞿氏铁琴铜剑楼。
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与张氏爱日精庐颇有渊源,瞿绍基就曾收得张金吾的许多藏书。(159)郑利锋: 《〈吴郡志〉版本流传考》,《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2期。《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著录:“《舆地纪胜》二百卷,影钞宋本,题东阳王象之编,有自序、李埴序……是书世鲜传本,近钱唐何梦华得影钞宋本,邑中张氏从之传录。”(160)〔清〕 瞿镛: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926册,第202页。《铁琴铜剑楼藏宋元本书目》也著录此“景钞宋本”,言“是书世鲜传本,近钱唐何梦华得景钞宋本,邑中张氏从之传录”(161)〔清〕 瞿镛: 《铁琴铜剑楼藏宋元本书目》,《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5册,第463页。,可见瞿氏此本即是传自张金吾;铁琴铜剑楼藏书后归国家图书馆前身——北京图书馆,此本亦在其中。《中国古籍总目》著录的《舆地纪胜》“清影宋钞本(存卷一至十二、十七至四十九、五十五至九十五),国图”(162)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 《中国古籍总目·史部》第7册,第3712页。,即是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本;在卷首钱大昕《序》首行的右侧和卷九十五“卷终”的左侧都有“铁琴铜剑楼”“北京图书馆藏”印记(163)〔宋〕 王象之: 《舆地纪胜》,《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84册,第1页。,便是明证。可见此本存卷较前又有减少。
9. 马思赞购藏传写张金吾爱日精庐本
上述藏本张金吾收藏时又产生了新的抄本,李富孙《校经庼题跋》云“近海昌马氏购得一本,即从张氏传写”,可见马氏所购藏的抄本《舆地纪胜》即是从爱日精庐藏本传写的;考“海昌马氏”是马思赞,“字寒中,号南楼,海宁人”,“嗜藏书,家有道古楼,插架宋元旧本,鼎彝秘玩,充牣其中,不减云林(倪瓒)清秘阁”,“为扬州推官麟翔子”(164)〔清〕 阮元辑: 《两浙轩录》卷七,《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683册,第321页。。查考马麟翔,是顺治“十一年(1654年)甲午科”举人、“己亥(1659年)进士”(165)民国《杭州府志》卷一一二《选举》,《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2册,第997页。,也颇致力于收书,可见马氏藏书一脉相承。马思赞此抄本“卷首影写钱詹事手跋、曾巧凤札子有漫灭讹阙字,与张氏刊载藏书记同”,所缺佚的卷数与张本也相同,同“失去三十二卷”;与张本不同的是,此本又经过了加抄改写:“目录内每卷下无行在所临安府、嘉兴府等标目。每阙卷后补碑记,此后人从《舆地碑目》钞附。其所钞当为书贾从彼借录,希图射利,字画极潦草,更多夺落错误,几不可属读。”(166)〔清〕 李富孙: 《校经庼题跋》,《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9册,第587页。马思赞藏书后多归吴骞拜经楼,而考《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却没有著录此本;后“吴氏拜经楼之书亦大都归”马瀛。(167)郑伟章: 《文献家通考》,第889页。查考《马氏吟香馆藏书目》著录:“《舆地纪胜》,八表套”、“《舆地纪胜》,一本。”(168)〔清〕 马瀛: 《马氏吟香馆藏书目》,《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明清卷》第30册,第56、73页。此中或有马思赞所购藏的传写张氏本。
10. 胡树声、胡珽父子的“琳琅秘室”本
《叶氏观古堂藏书目》著录:“《舆地纪胜》二百卷,宋王象之撰,琳琅秘室。”(169)叶德辉: 《叶氏观古堂藏书目》,《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21册,据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叶氏元尚斋稿本(叶德辉校补)影印,第218页。可见叶德辉藏有一部“琳琅秘室”本《舆地纪胜》。查考“琳琅秘室”是胡树声、胡珽父子的藏书处。吕晋昭《胡文学传》言:“胡君树声,字震之,又字雨棠……喜藏书,所购多宋元旧本,不吝值。或更手自缮录,积至千百卷,颜其居曰‘琳琅秘室’,日事校雠,怡然自乐。”(170)〔清〕 吕晋昭: 《胡文学传》,〔清〕 胡珽: 《琳琅秘室丛书》,清咸丰三年活字印本,第1册,南京图书馆藏。卢希晋《元刊草堂雅集跋》亦称:“吴雨棠明经好购异书,一生所积,汗牛充栋。其子珽从余游,颇能继先人之业。”(171)〔清〕 姚觐元: 《咫进斋善本书目》卷四,抄本,第30页,南京图书馆藏。可见胡氏“琳琅秘室”藏书始于胡树声,后由其子胡珽继承。叶廷琯《吹网录》载胡珽是“浙江仁和人,太常寺博士,侨居吴下,好收宋元旧本书,手自校勘,有得即记”(172)〔清〕 叶廷琯: 《吹网录》卷五,《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63册,第78页。,颇有父风。丁丙亦称他“善承先志,与吴郡叶调生廷琯校刊家藏秘本数十种,名曰《琳琅丛书》”(173)〔清〕 丁申: 《杭郡诗三辑》卷五五,清光绪十九年刻本,第9页,南京图书馆藏。,总“四集三十种,宋于庭、徐山民为之序,世甚珍重”(174)〔清〕 叶昌炽撰,王欣夫补正,陈鹏辑: 《藏书纪事诗》,第670页。。可见胡珽不仅勤于收藏而且也热心于校书刊书,善继父业得到公认。然而由于战乱,胡珽于“庚申(1860年)冬,避乱沪城。辛酉(1861年)四月,殁于旅舍”(175)〔清〕 叶廷琯: 《吹网录》卷五,《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63册,第78页。,“劫遗之书,斥卖几尽”(176)〔清〕 丁申: 《杭郡诗三辑》卷五五,清光绪十九年刻本,第9页,南京图书馆藏。,“琳琅秘室”藏书也就此飘零,后此本辗转而归叶氏观古堂。
11. 张穆手校影宋抄本
《华萼堂读书小识》著录:“《舆地纪胜》二百卷,张?傦?斋校钞本。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二百卷,旧钞本……盖从宋本抄出者,旧为张?傦?斋穆收藏。有‘张穆印信’‘?傦?斋藏书’两白文方印及‘穆’字朱文圆印,书面副纸均有?傦?斋题字。”(177)叶启发: 《华萼堂读书小识》,《中国图书馆学史料丛刊》第4册,第275页。可见叶启发此部《舆地纪胜》旧抄本原是张穆旧藏;惜其亦为残本:“原缺第十三至第十六卷、第五十至第五十四卷、第百三十六至第百四十四卷、第百六十八至第百七十三卷、第百九十三至第二百卷,共三十二卷。又……各卷均有脱页,多寡不等。”考“张穆,字石洲,山西平定人,道光十一年(1831年)优贡生……为人豪放,明锐极深,研几于经道”(178)王钟翰点校: 《清史列传》卷七三《文苑传》,第6055页。,“善属文……通训诂、天算、舆地之学”(179)《清史稿》卷四八五《循吏三》,第44册,第13400页。,可见其学养丰厚且精通舆地之学,所以对其所藏的地理志书进行校勘自是应有之义,所以叶启发云:“书中误字,已经硃笔校改;卷一首页右边线外有硃校一行云‘两浙西路’,卷一小注云‘影本’;每页前版边外皆有小字标题,今但记其式于每卷之首;左边线外有硃校一行云‘行在所’,下注云‘影本’,每页后皆有小字标题云;卷三首页外边线外有硃校云‘两浙西路’,卷三左边线外有硃校‘嘉兴府’三字。盖?傦?斋又以影抄宋本重校,依照旧式勾记也。”
叶启发此部“精抄复经张?傦?斋手校”的《舆地纪胜》是“从道州何氏得之”。查考“道州何氏”是指湖南道州的何凌汉、何绍基一脉,为当地的名门望族。第一代何凌汉,是“嘉庆十年(1805年)一甲三名进士”,“道光六年(1826年)授顺天府尹”(180)《清史稿》卷四八六《何绍基传》,第44册,第13436页。,在任期内购得朱筠藏书,家遂“藏书万卷”,所以“其子何绍基东洲草堂藏书,实始于凌汉”(181)郑伟章: 《文献家通考》,第560、648页。。第二代何绍基,为“尚书凌汉子,道光十六年(1836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典福建、贵州、广东乡试”,“咸丰二年(1852年),简四川学政”(182)《清史稿》卷四八六《何绍基传》,第44册,第13436页。,历官各地,家有东洲草堂,“藏书十余万卷……所藏有宋元本、明清钞本稿本及清代禁书”(183)郑伟章: 《文献家通考》,第810页。。第三代无闻。第四代是何绍基之孙何维朴、何维棣。第五代是“何绍基之曾孙、维棣之子”何诒恺,“东洲草堂藏书自何凌汉至诒恺已传五世,然败散于诒恺之手”(184)郑伟章: 《文献家通考》,第1526页。。《华萼堂读书小识》载:“丙寅、丁卯(1926—1927年)之间,太史曾孙诒恺移寓省垣,染阿芙蓉癖甚深,又沉溺醉乡,陆续举其先世所藏者,售金以资所费。余兄弟每于估人手见其家藏旧本,必倾囊金购归。先后所得……元明旧椠、批校稿本,不下五千余卷也。”(185)叶启发: 《华萼堂读书小识》卷二“《古史》六卷”条,叶启勋、叶启发撰,李军整理: 《二叶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18页。可见东洲草堂藏书是被何诒恺售出,何氏五代藏书由此散佚。在此过程中,叶启发多有购获,此部《舆地纪胜》校抄本即是其一。《中国古籍总目》著录:“《舆地纪胜》二百卷,宋王象之撰。湖南(存卷一至十二、十七至四十九、五十六至一百四十三、一百四十五至一百六十七、一百七十四至一百九十二,清张穆校)。”(186)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 《中国古籍总目·史部》第7册,第3712页。即是此本。可见该本后从叶启发华萼堂散出,今归湖南图书馆。
12.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岑建功惧盈斋绿格抄本
阮元《舆地纪胜序》云:“甘泉岑绍周提举建功”,在道光“癸卯(1843年)春……言愿刻《纪胜》全书,请先假归影钞,然后授梓,余欣然许之。未几,余旧居福寿庭第为邻火所焚。凡选楼书籍分藏于彼者悉毁于一炬,而《纪胜》以借钞之故巍然独存”(187)〔清〕 阮元: 《舆地纪胜序》,《舆地纪胜》,清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刊本,第1册,本序第2页。。可见岑建功是于道光二十三年接洽阮元、借录文选楼抄本的;而阮氏此本也正因被岑建功借出誊抄而免毁于火灾。岑建功所抄本即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惧盈斋刻本的底本。后该底本亦散出。值抗战时期,“中央图书馆怵于归安陆氏藏书东渡之前鉴,惧我国宝藏再有流失之虞,乃……以上海为中心,北自燕都、南迄粤港,网罗搜购,不遗余力,南北秘籍,遂集藏于该馆”(188)台北“中央图书馆”: 《台北“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序》,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年印行,本序第1页。,此抄本亦在其中;后迁至台北,今藏于台北“中央图书馆”,查考该馆《善本书目》著录“《舆地纪胜》存一百六十八卷、六十册,宋王象之撰,清道光二十八年扬州岑氏惧盈斋绿格钞本,缺……凡三十二卷”(189)台北“中央图书馆”: 《台北“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甲编卷二,第82页。,即是此本;可见岑建功再钞本是用绿格纸抄写的,完成于道光二十八年。
13. 李盛铎木犀轩藏黑格依宋抄本
《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著录:“《舆地纪胜》二百卷,依宋钞本,原缺三十一卷,二十册、四函。”(190)李盛铎: 《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19册,第41页。可见李盛铎这部“依宋钞本”《舆地纪胜》共有二十册,该志与李氏其他藏书在1939年底由其子李滂一并售出,今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191)郑利锋: 《〈九域志〉版本流传考》,《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1期。查考张玉范《木犀轩藏书书录》即著录此本:“《舆地纪胜》二百卷,宋王象之撰,旧钞本〔清钞本(有朱校,存卷一至一二、卷一七至四九、卷五五至一三五、卷一四五至一六七、卷一七四至一九二)〕,李7476。黑格抄,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当从宋本抄出。内原缺三十二卷。”(192)李盛铎著,张玉范整理: 《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页。查考李氏藏书渊源,叶德辉《观古堂藏书目序》云:“丙戌(1886年)丁亥居会城,县人袁漱六太守卧雪庐藏书大半散出,其中宋元旧椠折阅售之德化李木斋编修。袁书多兰陵孙氏祠堂旧藏。”(193)叶德辉: 《观古堂藏书目序》,《观古堂藏书目》,民国四年长沙叶氏观古堂铅印本,南京图书馆藏。可见李盛铎藏书多得于袁芳瑛卧雪庐,而袁氏卧雪庐所藏又多是孙星衍旧藏;由上可知《孙氏祠堂书目》著录了一部影宋写本《舆地纪胜》,其行款是“每叶廿行,行廿字”,明显与此本“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的版式不同,因此李盛铎此本并非孙星衍藏本,这也可和孙氏祠堂本今藏于上海图书馆相印证。又考李盛铎藏书除了收得袁氏卧雪庐旧藏外,又访购于厂肆,再得“宁波范氏、商丘宋氏、曲阜孔氏、四明卢氏、聊城杨氏、巴陵方氏、意园盛氏”散出之本(194)张玉范: 《李盛铎及其藏书》,《文献》1980年3期。,因而其藏书“量数之丰,部帙之富,门类之赅广,为近来国内藏书家所罕有”(195)傅增湘: 《审阅德化李氏藏书说帖》,《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96页。,此部黑格依宋抄本《舆地纪胜》即是其一。
以上是从何元锡藏本衍出的清抄本,下面再看由其衍出的清刻本。
1. 道光二十九年岑建功惧盈斋刻本
此本即是岑氏以道光二十八年惧盈斋绿格抄本为底本刊刻的,虽然此底本是抄自阮元文选楼副本,但又与之不同,因为“洎影钞既毕,绍周复延仪征刘孟瞻文淇及其子伯山毓崧纂辑《纪胜校勘记》,而自补钞本阙文”(196)〔清〕 阮元: 《舆地纪胜序》,《舆地纪胜》,清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刊本,第1册,本序第3页。,对底本又进行了校勘和补辑。刘文淇《校勘记序》亦云:“文选楼影宋钞本《舆地纪胜》,张氏鉴(阮元弟子)所校颇详。岑君绍周建功重刻此书,延文淇及子毓崧纂辑《校勘记》,成书五十二卷,于张氏之说采录无遗……吴氏兰修所加条记之语,足与张说相辅,则亟为搜罗。车氏持谦、许氏翰所校《碑目》之书,皆与《纪胜》有关,则并为登载。其诸家按语所未及,则核以群书。”(197)〔清〕 刘文淇: 《校勘记序》,《舆地纪胜》,清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刊本,第36册,本序第1页。可见刘氏父子的校勘,吸纳了张鉴、吴兰修、车持谦、许翰四人的校勘成果,在此基础上又有辨析考核,对此底本进行了全面整理。
然在道光“戊寅(1848年)孟夏”,刻工“将次第及于《纪胜》,而绍周遽亡”,“其子秋舲淦及其从子仲陶镕”“咸悼念遗书,引为己责”,并于道光二十九年“先以《纪胜》付诸剞劂,延江都沈戟门棨、凌东笙镛分任校字之事,其《校勘记》与《补阙》亦陆续刊行”,“以成绍周未竟之志”(198)〔清〕 阮元: 《舆地纪胜序》,《舆地纪胜》,清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刊本,第1册,本序第1页。,这即是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刻本。此本是明代之后《舆地纪胜》的第一种刻本,绍周虽逝,其功厥伟。
2. 李韵亭补雕惧盈斋书版本
乔松年《舆地纪胜序》云:“广陵岑氏刻《旧唐书》,又刻此书,并行于世,为学者所珍。自寇盗凭陵江表,军锋四指,居人奔走道路,岑氏书版遂皆放失。乱定后,此版为李君韵亭所得,已阙十之三四。君重王氏纂述之勤且嘉岑氏刊布之力,悼其成之难而毁之易,乃出资补雕,书得复完;印已,持赠知交,得者皆以为快……是书抄传未广,得岑君传之于前,李君传之于后,岂非作书者之大幸。”(199)〔清〕 乔松年: 《舆地纪胜序》,《舆地纪胜》,清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刊本,第1册,本序第1页。可见岑氏惧盈斋《舆地纪胜》书版在兵乱中散亡且已残缺,幸被李韵亭收得;李氏对书版进行了补雕、刷印,于是出现了李氏惧盈斋书版补雕本。《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附录》载:“甘泉岑建功校刻《旧唐书》竟,又假阮氏所藏影宋本《舆地纪胜》付刻,延仪征刘文淇及其子毓崧纂辑《校勘记》五十二卷,建功又自辑《补阙》十卷。兵燹后,岑氏书板散失,《纪胜》板为李韵亭所得,已阙十之二三,遂补雕行世。”(200)〔清〕 邵懿辰撰,邵章续录: 《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即是言此。查考“李韵亭”即李培松,原名抡彦,字韵亭,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太学生,分部行走郎中,钦加三品衔加四级,赏戴花翎,湖北候补道,钦加二品顶戴,覃恩告授荣禄大夫,卒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201)顾一平: 《李氏昆仲》,《扬子晚报》2006年11月25日,第82版。。沈德寿《抱经楼藏书志》亦著录此本:“新刊《舆地纪胜》二百卷,岑氏刊本,宋东阳王象之编,缺三十二卷。王象之序,嘉定辛巳。李埴序,宝庆丁亥。曾鸣凤札子。阮元序,道光己酉。乔松年跋。”(202)〔清〕 沈德寿: 《抱经楼藏书志》,《清人书目题跋丛刊》第5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64页。
3. 伍崇曜粤雅堂咸丰五年刻本
此本即伍氏以陈其锟珍藏的吴兰修旧藏秘籍(203)〔清〕 伍崇矅: 《舆地纪胜序》,《舆地纪胜》,南海伍氏粤雅堂清咸丰五年刊本,第1册,南京图书馆藏。为底本刊刻的。伍崇曜当时所见的此部秘籍已是“原阙”“若干卷”且“纸墨残蚀”过甚,便忧心此部钞本“恐难经久”,于是决意刻印,并请得谭莹襄助;但“当时苦无别本,校雠惟据陈本”,只好“略加厘定”“遂亟授刊”,这即是伍氏粤雅堂咸丰五年刻本,刊印时间是“始甲寅(1854年)迄乙卯(1855年)”(204)〔清〕 伍崇矅: 《舆地纪胜序》,《舆地纪胜》,南海伍氏粤雅堂清咸丰五年刊本,第1册,南京图书馆藏。;行款是半页十二行,行大字二十五、小字双行也二十五字,四周单边,双黑鱼尾,每卷末多有“谭莹玉生覆校”六字。复考谭莹,“号玉生,南海人,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年)举人,官化州学训导,升琼州府教授,加内阁中书衔……凡海内名流游粤,无不慕交”,但“声望虽高,乡场屡黜”,在科场上不甚得意,“然莹澹荣名,计偕后不复北上;爱教职,无事得以肆其搜览,博考粤中文献。凡粤人著述搜罗而尽读之,其罕见者,告其友伍崇曜汇刻之”(205)〔清〕 陈璞: 《尺冈草堂遗集·遗文》卷四,《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547册,第658页。,可见两人是熟友,所以伍氏刊刻此志请他校理底本。
4. 伍崇曜粤雅堂咸丰十年重修本
伍氏后又“购得海宁杨氏(文荪)所藏影钞宋本”,杨本“原阙卷帙与陈本同,知二本所出无异。惟杨本凡遇宋本字画残蚀及宋讳阙笔,皆仍其旧;又每卷标目皆先用墨笔钩出其字,乃以朱笔填之,足证宋本朱书标目尚略见原钞旧观……且纸墨完好,洵善本矣。遂与潘绪卿茂才细校刊本,凡陈本残蚀、初刊无据者,补入若干条、若干字”(206)〔清〕 伍崇矅: 《舆地纪胜序》,《舆地纪胜》,南海伍氏粤雅堂清咸丰十年刊本,第1册,南京图书馆藏。,后又利用新得的李文藻、吴铨旧藏《碑记目》抄本和车持谦勘校《碑记目》刊本为补充,在深入校勘后再次付印,这就是伍氏粤雅堂咸丰十年重刻本。由此可见这部由陈其锟递藏的吴兰修秘藏抄本以及由其衍出的伍氏刊本和杨文荪藏本的版系相同,都是源于何元锡藏本一系。
以上即是对清代华希闵藏影宋抄本、何元锡藏影宋抄本以及由何元锡藏本衍出的18种传本的考述,其中14种是抄本、4种是刻本;虽然有些抄本,如张穆手校影宋抄本、李盛铎藏黑格依宋抄本,没有明言其底本情状,但其所缺佚的卷数与何本一致,可以判定它们的版系相同。
四、 结 语
综上即是通过馆藏实物调查和资料考索对《舆地纪胜》版本的再次考察,可见该志刊刻于南宋理宗嘉熙四年至景定三年间。今可考见其宋刻本有2种,一是钱曾述古堂藏宋板足本,二是陆漻佳趣堂藏宋本,但都下落不明;其在明代的流传,主要有文渊阁藏“三十册”本、“十八册”本和由“三十册”本衍出的杨慎家抄秘阁本;至清代,则有华希闵藏影宋抄本和何元锡藏影宋抄本,其中何元锡藏本经钱大昕、阮元的传扬,影响甚大,迭出抄本和刻本,共有18种之多,包括14种抄本、4种刻本,在清中后期广泛传布。华希闵生活的时代早于何元锡,因而其藏本不晚于甚至早于何氏藏本,是今见《舆地纪胜》最早的版本。今若校理此志,当以精校的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刻本或咸丰十年粤雅堂重刻本为底本,再辅以这部华希闵藏本,并以其他诸本为补充,当庶近最佳本。综观《舆地纪胜》的流传,在清嘉庆朝前不绝如缕,至嘉庆朝及其后则流传广泛、版本众多,授受关系复杂,如此共同形成了其在历史上的版本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