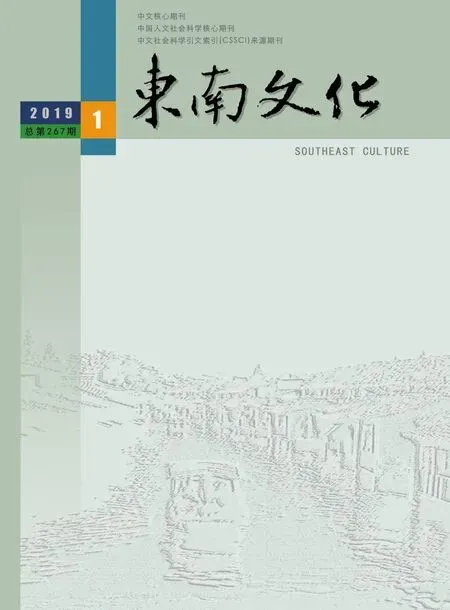从考古遗址到世界文化遗产:良渚古城的价值认定与保护利用
2019-12-15王宁远陈明辉
刘 斌 王宁远 陈明辉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杭州 310014)
内容提要:良渚古城遗址八十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工作充分揭示了遗址的重要价值,证明它是良渚文明的都邑性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是规模庞大的世界级城址,遗址的价值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认可。在各方的配合和努力下,良渚古城遗址的文物保护也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而不断推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2年以来,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工作正式启动,良渚博物院展陈完成更新换代,良渚国家考古公园建设也已大体成型,良渚古城遗址已进入全面展示和利用的新时代。
良渚古城遗址是我国已公布的500余处大遗址中重要的史前时期大遗址。近年来,有关大遗址考古与大遗址保护越来越受到国家文物局和考古界的重视。2005年财政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的《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把“大遗址”定义为“价值突出、规模体量较大、影响深远的遗址,主要包括反映中国古代历史上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重要历史文化信息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及文化景观”。大遗址的产生除了历史上著名的古城址(如汉唐长安城)、古墓葬(如历代帝王陵)外,史前时期大遗址的发现与确立主要依赖于考古工作的积累,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积累过程。良渚古城遗址便是如此。
良渚古城遗址通过八十余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单一遗址的发现,遗址群聚落的确认,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的发现及总体格局的认识。在研究方法、技术手段和研究内容上,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也从以研究器物和遗迹为主,走向多学科合作的关注动植物和气候等自然环境、遗址兴废过程与原因、材料分类与来源等全方位的全息式考古模式。从2007年发现良渚古城开始,逐渐揭示出了一座距今5000年的超大规模的古王国都城,实证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数十年的考古实践证明,长期扎实的考古工作是认识文化遗产、认定文化遗产价值的基础;而考古发现、研究与保护的互动最终能实现遗产价值,让古代遗产成为当今文化的一部分。
一、良渚考古与良渚古城遗址的价值认定
(一)良渚考古八十多年历程
1936年浙江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以下省略敬称)在浙江余杭良渚一带进行调查,发现了十余处以黑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对其中六处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并出版《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1]一书,成为良渚文化和浙江史前考古的发端。在传播论与黄河中心论旧史观的影响下,良渚一带的发现被认为是龙山文化向东南传播的一支。
20世纪50年代,随着基本建设的蓬勃发展,中国的考古事业进入了黄金时代。长江下游地区发掘了十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学界逐步建立起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并认识到其与海岱龙山文化等的差异性,1959年夏鼐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2]。作为良渚文化的命名地,良渚遗址于1961年被公布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浙江省所”)于1981年发掘余杭瓶窑吴家埠遗址[3],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堆积与墓葬,并在当地建立工作站,从此良渚一带开始有了长期稳定的考古工作。随后组织的两次调查又发现不少遗址,1986年在“良渚发现50周年会议”上,王明达提出“良渚遗址群”的概念,并公布“已知的地点多达四五十处”[4]。
1973年,南京博物院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第一次发现随葬玉琮、玉璧等大型玉礼器的良渚文化墓葬[5],良渚文化的玉器从此为学界所知。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考古工作人员先后在江苏吴县张陵山[6]、常州武进寺墩[7],上海青浦福泉山[8]等地发掘随葬玉器的良渚文化大墓。良渚文化的社会发展水平逐渐被认识。
浙江作为良渚文化的命名地,直到1986年才第一次在余杭反山遗址发掘出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墓地。反山遗址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精美玉器,尤其在M12的“玉琮王”和“玉钺王”上发现了完整的神徽形象,这对解读良渚玉器的纹饰内涵和器物造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9]。
1987年,浙江省所在余杭瑶山遗址又发现了12座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墓葬,并且首次发现良渚文化的祭坛遗址[10]。1991年,在余杭瓶窑汇观山遗址又发现了与瑶山遗址十分相似的良渚祭坛和墓地,从而使良渚祭坛的功能和性质得到进一步认识[11]。
1987年及1992—1993年,通过对莫角山遗址的发掘,学界认识到这个面积约30多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10米的大型土台是良渚时期人工堆筑营建的大型宫殿基址[12]。如此规模宏大的建筑遗址,加之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遗址出土的大量精美玉器,反映出此地区应是良渚文化的中心所在。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良渚一带的考古工作几乎没有中断。1998—2002年浙江省所对良渚一带约50平方千米的范围进行了拉网式的详细调查,共确认遗址130多处。
2006年,葡萄畈遗址发现了一段良渚时期的古河道。浙江省所对河岸进行解剖,发现3米多高的河岸下面铺垫一层石头,我们推测葡萄畈村所在的南北向高地可能是良渚时期的苕溪大堤,也可能是围绕着莫角山的城墙。2007年3—11月,经过发掘最终确认了四面城墙。2007年11月,浙江省文物局和杭州市政府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发现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
自2007年之后,在国家文物局和浙江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良渚遗址开始进入长期的、有计划的考古阶段。随着良渚古城的发现,以往的以了解各遗址年代与性状的散点式的考古计划已无法适应新发现的要求,以古城为核心、厘清古城内外功能布局与发展过程,成为良渚古城发现以后的工作目标。因此,浙江省所于2008年在张忠培的指导下,按照“三年计划、十年目标、百年谋略”的方针,制定了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工作规划。十年来,浙江省所按照这一方针,总体勘探,重点发掘,先城外、后城内,逐渐厘清了以古城为核心的约100平方千米范围的遗址分布格局以及古地貌、古环境等情况。
2010年以来,浙江省所通过对城内外10.8平方千米的勘探,摸清了良渚古城遗址的城墙、台地、河道的边界和演变过程;通过勘探和数字高程模型分析,发现了外郭城的城墙及美人地等外郭城范围的遗址分布情况;经过对美人地、扁担山、里山等长条状台地的解剖发掘,确认了外郭城的堆筑形式、使用年代等情况。由于良渚古城西部紧邻瓶窑镇,目前仅确认围绕着良渚古城的北、东、南三面的6.3平方千米的外城。
2009年,余杭彭公一带取土发现了岗公岭水坝,浙江省所随后通过组织开展对其周边区域的调查,在岗公岭以西又发现了老虎岭、周家畈、石坞、秋坞等水坝遗址。2010年初,浙江省所发现岗公岭水坝堆筑的青泥是以草包裹的形式垒筑而成,经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测年确定为良渚时期。2013年,通过遥感分析和钻探,又发现鲤鱼山等另一组较低的水坝遗址,将这些连接两山的水坝与1999年确认的5千米长的塘山水坝相连接,最终我们厘清了由11条水坝构成的庞大的水利工程[13]。2015年,浙江省所分别对鲤鱼山和老虎岭进行考古发掘,并在老虎岭发现了打破坝体堆积的良渚文化晚期的灰沟。11条水坝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为距今5100—4700年。至此我们于2016年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发现中国最早的水利系统。这一发现也使良渚古城遗址的范围扩大到约100平方千米。
无论从宏大的规模,还是从城市体系的复杂性及建筑的巨大工程量等而言,良渚古城都不亚于同时期的古埃及、苏美尔和哈拉帕文明。高等级的墓葬与玉礼器的发现也证实良渚时期甚至已经出现统一的神灵信仰和森严的社会等级分化。如今学术界已普遍公认良渚文化已进入早期国家社会[14]。
(二)多学科全息考古全方位揭示良渚古城遗址的价值
良渚考古工作在大遗址考古理念的指导下开展,科技考古和多学科合作成为极重要的研究手段,取得了显著效果。
1.田野考古测量控制系统极大提高测绘效率
随着良渚古城的确认,我们对良渚遗址的认识完成了遗址点→遗址群→都邑考古的跨越,考古工作的基本着眼点也相应地从对130多个遗址点的分散认识发展到将整个遗址群作为一个特大型都邑遗址来认识。因此,其内部所有的发掘记录和研究必须建立在一个统一的考古测量控制系统之上。为此,浙江省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建立了一个目前全国最大规模的田野考古测量控制系统。此系统实际应用范围为几百平方千米,并可根据需要无限扩大。
这套测量控制系统以良渚古城为中心,涵盖遗址区及周边范围。控制网分“区”“块”“方”三级。其中,每个“区”为边长2500米的正方形,每“区”下分25个边长500米的“块”,“块”下又设2500个边长10米的“方”。“区”依坐标法编号,具有扩展性。控制网内的各个发掘的探方都各自对应唯一的探方编号。随着测量手段的发展,我们又对该系统的测控方式进行了改良。最初设计的控制网,每区都需设置较高密度的固定测控点作测量控制,这种方式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后来我们使用RTK(动态GPS)设备,采用最新的CORS(连续运行参考基站系统)测量方式,实时引用测绘主管部门设置的测量基点的差分数据,不再埋设实体的加密控制点,从而在保证测量精度的前提下,极大地减少了投入,提高了测绘效率。
目前良渚遗址群内的所有考古发掘项目都是基于这套坐标系统进行记录的。
2.地形图和地面影像为遗址分析及遗址规划保护提供基础
遗址区矢量地图是建立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的基本要求。我们对遗址区进行测绘和航拍,并对原有的地图资料进行矢量化处理。目前我们已获得非常完备的的各类地图资料,包括全余杭区1:10000比例、瓶窑和良渚两镇380平方千米的1:2000比例以及古城重点区二十余平方千米的1:500比例的矢量地图。同时,我们也很注重收集历史时期的地图资料,因为早期的地图可能保留原有的信息更丰富、破坏更少。我们收集了清代末期余杭地区的水系图、20世纪30年的杭州地区都图地图、20世纪40年代侵华日军1:50000比例的军用地图等资料。这些资料对很多已被破坏消失的水道等信息都有记录,对现代实测地图具有很好的补充作用。
数字正射影像是基础地理信息的另一种重要载体。我们除获得遗址群范围的GOOGLE公司60厘米分辨率的地面影像外,陕西西安大地测绘及十月科技有限公司还对古城及周边120平方千米范围进行了无人机航拍航测,获得了分辨率高达8厘米的高清数字正射影像图。
在全国各类大型遗址中,良渚地区可能是地图资料最为齐备的地区。这些基础地形信息的获取是GIS工作的前提,为遗址分析及规划保护提供了基础。
3.田野考古数据库系统充分满足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实际需求
田野考古数据库是考古记录系统改进的一项重要工作。浙江省所在2003年即开始以ACCESS方式自行设置田野考古的前端记录系统。随着十多年的改进和实践,我们的记录系统基本上已经可以满足田野工作的需要。与其他一些类似软件相比,田野考古数据库系统因其基于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实际需求而由考古领队自己设计,因此在系统的易用程度、与实际考古工作流程的契合度、与考古工作各类表单的对应关系等诸多关键要素上,更符合实际考古工作的需要。在后期整理中,此系统在查询、统计和纠错等环节的操作和界面简洁明了,通过与WORD软件的整合,各类考古表单的填写和考古报告的编写均能做到一键完成,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目前经过若干个大型遗址考古发掘和整理的实践证明,此系统在维护和开放性等方面要优于其他专业开发的软件,是考古领队真正易于掌握且有效的工具。我们始终认为,一个考古软件系统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考古领队和发掘人员是否愿意使用。而要领队和发掘人员愿意使用,其前提是此软件可使考古记录工作量减少、在易用性和开放性等方面具有优势,且符合考古工作的一般流程。
4.利用GIS技术成功寻找到良渚古城的外围结构
GIS技术在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中获得广泛应用,在良渚古城外围结构的寻找、水利系统的分析、溢洪道等结构的寻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2009年底,我们利用良渚古城区域1:500比例的线划图制作了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结果有惊人的发现:莫角山标准的长方形轮廓,以及其上的大小莫角山和乌龟山这三个高台显示得非常清晰。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明确地发现良渚古城东南部外侧存在着一个长方形结构体,它是分别由美人地、里山—郑村、卞家山构成的北、东、南三面墙体,并与良渚古城的东墙和南墙相接续。经过对美人地等地点的发掘,这里被证实是良渚古城外郭的一部分。
所谓“数字高程模型”,就是把地图上不同高程的范围依照某种色系的变化涂上不同的颜色。即使一道城墙被破坏后呈若干分散的小段,若其基本高程一致,在DEM平面图上就显示为相同的颜色,这样就很容易把它们联系起来观察。DEM反映的是单纯的地表高程变化,所以能从复杂的地表植被和建筑的视觉干扰中,将纯粹的高程信息直观反映出来。因此,DEM是在本地区寻找城墙结构的最有效的方法。
发现水利系统之后,我们又利用DEM分别在高坝东区和西区发现了溢洪道的重要线索。根据水利工程的原理,良渚这种大规模的坝区一定会有溢洪道。水利专家认为,溢洪道无法设置在人工土坝之上,因为过水容易冲垮,推测可能会利用库区内低于坝高1~2米左右的石质山口当作溢洪。但是自然的石质山口通过一般的考古勘探等手段无法判断,因此,我们根据复原的坝顶高将各个库区的数字地图制成DEM。通过设定,将低于坝高0.5、1、1.5、2、2.5的高程点,分别标注为特别的颜色,结果在高坝的东区和西区都发现了符合溢洪要求的山口。其中东区的溢洪道位于坝东侧的一处小山口,高程为28.9米,低于东组30米坝高1.1米。经过实地勘察,此山口为石质基础,后经水利测算,其宽度满足百年一遇降水的泄洪要求,因此起到了溢洪道的作用,这是良渚时期人们有意选择的结果。水库最高水位是由溢洪道高度决定的,因此,在明确了溢洪道高度之后,水利专家利用GIS软件计算出良渚水利系统的库区总面积为13.29平方千米、总库容4635万立方米。
5.运用遥感手段完整揭示出良渚水利系统结构
遥感(Remote Sensing,RS)手段是良渚考古中应用的另一项重要手段。RS技术成本低廉、影像直观,成为良渚大遗址考古中结构性研究中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在发现高坝系统后,我们利用解密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科罗娜(coroana)间谍卫星影像进行观察。2011年初,发现在高坝南面约3千米的鲤鱼山存在一个明显具有人工痕迹的大型坝体,经钻探证实这个近300米长的坝体的确是人工堆筑,同时发现在鲤鱼山的东西两侧共有3段人工坝体。这些坝体连接平原上的孤丘,坝高约10米,形成低坝系统。它不仅增加了坝体的数量,关键在于低坝通过其东面的小山体连接到塘山,又通过西侧绵延的低丘向北连接到高坝,从而揭示出塘山、高坝和低坝共同构成的良渚水利系统的完整结构,意义重大。
同时,RS技术还被应用于良渚古城及塘山长堤的结构研究和功能分析。我们利用corona影像的立体像对古城和塘山进行高程复原,进而找到良渚古城西水门位置,且经过勘探加以证实,同时对塘山长堤结构和功能机理进行了分析。
6.动植物考古和良渚稻作农业调查全面再现良渚时期动植物种类及古气候
通过对良渚遗址群内发掘出土的植物标本的鉴定及地层的孢粉分析,我们对良渚时期的植物种类及古气候有了全面的了解;并且获得了良渚时期的除水稻之外的大量的其他可食用植物标本,如菱角、芡实、桃、李、甜瓜等。通过对遗址中出土的动物标本(其中猪骨占绝大多数)的研究,我们已经鉴定出50多种动物。对动植物标本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良渚时期人们的食谱,同时也显示出良渚时期的生态景象。
对外郭城以内大面积的钻探调查显示古城外郭之内区域现有高地基本为居住地,居住地之间为大面积水域,并无水稻种植。而钟家港等古河道发掘出土的大量陶片以及玉器、石器、漆木器、骨器等的加工废料和胚料,也反映出良渚古城的居住者除统治者外主要是工匠阶层。
另外,在城中宫殿区莫角山两侧及莫角山南面的池中寺遗址发现了总量达20多万公斤的炭化稻废弃堆积,推测为宫殿区粮仓失火后的废弃堆积,说明良渚古城内有大量的粮食储备。我们与日本东京大学合作,对这些炭化稻米进行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这些稻米来源于不同的产地。
7.多学科合作的综合研究丰富了对良渚古城遗址的认识
近十年来,多学科合作研究是良渚考古的重要方面。我们和国内外多家科研单位和高校合作,从“资源与环境”“技术与信仰”“水利与工程”等方面,进行社会考古学角度的全面观察,使得对良渚遗址的认识日益丰富。
在古环境方面,我们对良渚古城出现之前的环境、气候、水文等进行研究,确定了良渚文明出现的环境背景。在本地区良渚堆积之上普遍分布着一层纯净的黄粉土,学界一般认为是洪水堆积层。通过分析,我们获知这层黄粉土的成分主要来自长江口的泥沙,是海相的咸水沉积物,且泥沙颗粒从濒临杭州湾的临平到西侧的良渚一带逐步变细,说明其成因应与钱塘潮有关。这为良渚后期的衰亡提供了一种可信的环境解释。
在地质考古方面,我们拓展了仅对石玉器出土物进行岩性鉴定的传统方法,对良渚整个区域的自然岩石分布进行了全面的勘察,从而在资源与环境的角度获得了很多的新信息。我们计划分三步完成石玉器的研究:第一步,研究作为建筑材料的良渚城墙垫石。岩石学家首先对古城四面城墙解剖点所有暴露的垫石(共10524块)进行岩性、磨圆度、块度的鉴定和统计,发现绝大部分垫石都是散石,很少为人工开采。地质学家对古城周边分水岭以内200平方千米的所有山地进行调查,形成区域岩性分布图,进而与垫石的质地磨圆度等进行对比,获知取石地点多位于山脚和冲沟位置,并利用RS手段和地质及考古勘探资料恢复良渚时期的河道水系。考古学家根据垫石质地和形态对垫石进行分垄计算,推定良渚垫石的运载方式为竹筏运输;并根据河道及采石点位置,还原其可能的运输路径。通过实地的采集搬运和铺装等实验考古,进而计算出整个垫石工程的用工量为8.4万工。
第二步,对整个1000平方千米C形盆地内的良渚文化石器进行全面鉴定,同时将野外岩性调查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区域的山地。目前研究尚在进行中,我们发现良渚时期人们对石器石料的采集有非常明确的选择,并有若干种重要的石料跨流域远距离运输而来。在石器石料的调查过程中,我们还在天目山系发现了玉矿的重要线索,为未来第三步的玉器来源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良渚水利系统研究过程中,我们还与河海大学共同成立“古代水利系统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校地两处设立联合实验室,将专业机构有机引入到良渚水利系统的研究中,使我们对良渚水利系统的功能、结构、性质等的认识获得质的提高,并引起国家水利部门的高度关注。
二、良渚考古与良渚古城遗址的保护
距今约4200年,良渚古城所在的杭州余杭盆地遭遇了持续性的大洪水,良渚古城从此销声匿迹。直到战国时期,这一地区才开始重新出现人类生活痕迹。汉代人口渐多,莫角山宫殿的高地上留下了许多汉、六朝时期墓葬,这虽对良渚的史前遗址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并未伤及遗址的总体格局。南宋时期这一带成为临安城的郊区,我们在遗址边缘也发现了少量这一期的房址和墓葬。因此良渚古城的核心区总体保存完好。
良渚古城遗址的保护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6年到20世纪80年代,遗址区内的村镇处于缓慢发展状态,遗址与城镇化的矛盾并不突出,同时文物市场不发达,盗掘现象罕见。1958年,杭州市民政局组建大观山果园,并兴建了社会福利院和儿童福利院。现知的良渚古城核心区域莫角山、皇坟山、姜家山等高地被划归果园,直到2016年均保持果园状态,客观上使这几处重要遗址避开了城镇化的破坏。1961年良渚遗址被公布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反山、瑶山遗址的发掘加大了遗址的保护力度。此阶段当地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的速度加快,城镇基本建设增加,村民富裕起来,兴起建房热潮,导致村镇建设规模不断扩大、人口密度不断增加。遗址保护与当地村民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遗址的保护问题成为考古和文物保护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工作多为配合基本建设项目,主动性的考古发掘工作极少,但在此过程中,浙江省所始终有着较强的课题意识与保护意识。在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等遗址的发掘过程中,我们决定采用保护性发掘;在发掘完重要遗迹后,我们即采用回填保护,并积极呼吁当地政府参与保护。余杭区政府对于遗址保护向来也高度重视,在反山、瑶山遗址发掘之后随即进行了征地保护,并在1987年成立了专门的保护机构——余杭县良渚文化遗址管理所,负责良渚遗址的日常巡查和保护工作,这一机构的设置对遗址保护起到了关键作用。
1987年,我们在配合老104国道拓宽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莫角山遗址,第一次认识到大观山所在的高地为良渚时期人工堆筑而成。在浙江省文物局和余杭政府的努力下,为了保护遗址,公路部门最后决定将104国道向南改道。1992—1993年为配合长命印刷厂扩建,我们对大观山果园台地的中心部位进行大面积揭露,发现了用一层沙一层泥方式夯筑的建筑基址,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莫角山遗址的重要性。在各方努力下,当地政府决定将长命印刷厂搬迁他处。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进入主动性保护为主的新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学界对良渚遗址的研讨日益深入,其历史价值和地位也愈发彰显。1994年良渚遗址因其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无与伦比的重要价值和保存的完整性,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申报《世界遗产名录》预备名单。1996年国务院批准良渚遗址群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在“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学界普遍认为良渚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甚至已进入文明时代[15]。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地的建设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地处杭州市郊的良渚、安溪、长命、瓶窑一带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迅猛发展,集镇与乡村急速翻新与膨胀。到20世纪90年代末,遗址群北侧的大遮山共出现大小石矿30多家,使良渚遗址每日笼罩在隆隆的炮声和弥漫的粉尘之中。2000—2002年,浙江省政府痛下决心,历经两年时间关停良渚遗址周边的31家石矿,彻底消除了采石经济对遗址环境风貌的破坏。
杭州市与余杭区政府为遗址保护制定了许多政策法规,同时建立和完善了有效的管理机制。1995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良渚遗址群保护规划》,划定了33.8平方千米的保护区,并对遗址群内的建设规模进行了严格限制,从此良渚遗址进入了规划管理阶段。浙江省所专门成立了良渚工作站,负责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并配合审批实地踏查、勘探和出具考古意见。2001年9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面积242平方千米,组建正区(副厅)级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良管委”),原良渚文化遗址管理所划归至良管委,更名杭州良渚遗址管理所。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的设立是良渚遗址保护史上的里程碑,在管理区统一协调遗址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为促进良渚古城遗址的长远保护提供了组织保证。2002年9月,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瑶山派出所成立,专门负责打击针对良渚遗址的违法犯罪活动。2002年,杭州市颁布了《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使良渚遗址保护有了专门的针对性法规,该条例于2013年进行了修订。2002年,浙江省政府成立良渚遗址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委托制定《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该规划最终于2013年获得通过)。为配合保护规划的制定,浙江省所对良渚遗址群进行了进一步调查,制定了《良渚遗址五年考古工作规划》,提出了近期规划与远期目标,从而使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开始走向计划有序的发展阶段。2004年以来,良管委颁布了《良渚遗址保护区文物保护补偿办法》,对保护范围内村、社区的集体经济进行补偿奖励[16],首创了文物保护补偿机制。
第四阶段,21世纪以来,良渚古城遗址的研究与保护走向国际。2006—2007年良渚古城及2009—2015年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确认,使良渚古城遗址的规模位于同时期世界前列。2007年之后,良渚古城开始进行系统的、持续的考古工作,每年持续300天以上,考古工作人员也从原先的几人发展到如今的二十余人,包括十余名研究人员和十余名专业技工。良渚古城的研究方向除传统考古外,还包括数字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地质考古、环境考古、文物保护等;同时还招聘勘探队伍,不间断地对遗址范围进行全覆盖式勘探和系统调查。
2009年6月国家文物局在良渚召开“2009年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暨良渚国家遗址公园启动仪式”;同时,国家文物局和浙江省文物局授牌成立了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实行双重管理,由浙江省所和良管委共同管理。如今我们已经初步建成一个符合世界遗产地要求、符合国际标准的考古与保护研究基地,开启了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的新篇章。良渚遗址考古的实践证明,考古工作站的工作模式是一个地区的考古工作得以长期深入开展的有力保障,是百年大计的大遗址考古工作的内在要求。
三、良渚考古与良渚古城遗址的展示与利用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良渚文化博物馆建立开始,展示和利用便伴随着考古成果和遗址价值的深化而不断推进。1994年,位于荀山南侧的良渚文化博物馆建成开放。2008—2017年是良渚古城考古成果进展最迅速的十年。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深入,原博物馆已经无法容纳新的内涵。2008年的展陈内容已经远远落后于良渚古城的最新认识,为配合良渚古城遗址申遗,2017年8月,良渚博物院闭馆改陈,2018年6月底最终完成并重新开放。复旦大学的策展团队与良渚考古人员通力合作完成了改陈设计,使展陈尽量科学、完整地展示出良渚考古研究的新进展和新认知[17]。建成后的良渚博物院每年吸引四五十万游客前来参观,成为宣传展示良渚文化的重要窗口。
良渚古城遗址展示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遗址公园内的现场展示,包括生态环境展示、遗址本体、遗迹现场模拟展示、数字动画展示等。在遗址公园建设过程中,考古人员以张忠培提出的“遗址定性公园、公园表现遗址、切忌公园化遗址”为原则,积极参与遗址公园的展示设计。
目前,良渚古城的环境整治已经初步完成:古城内外可通视,站在古城的宫殿区,可清楚地看到古城处于三山环抱之中,向东为开阔的平原,周边地形地貌一览无余,视野相当开阔。遗址本体展示已经基本完成:莫角山(包括大小莫角山和乌龟山)、城墙、瑶山、反山、姜家山、池中寺、水坝遗址等均以绿植标识,遗址本体大部分清晰可辨,遗产区的总体框架结构初显。南城墙解剖点、反山剖面、老虎岭水坝剖面采取原真展示。反山王陵墓葬采取复原展示,在墓地原地面覆土加高数十厘米,在原位置放置铜质墓坑,墓坑内按原位摆放仿制的玉器、石器、陶器等随葬品。每座墓均配以图文解读,基本复原了墓葬出土情景。瑶山祭坛、大莫角山F2及小莫角山F17则采取地表模拟展示手段,同样在覆土加高的基础上,通过GRC(玻璃纤维增强混凝土)手段原址展示祭坛、墓坑或基槽、柱坑的形状,大致可模拟发掘出土时的土质、土色。莫角山宫殿区内的其余房屋台基和沙土广场、池中寺炭化稻谷堆积及房屋台基、姜家山和文家山墓地则均在原位置作了标识物展示,如房屋台基以树皮铺装展示、沙土广场以粗砂铺装展示、池中寺的炭化稻谷堆积及房屋台基以绿植标识、姜家山和文家山墓葬以卵石铺装展示等。
四、结语
良渚遗址的考古、发掘、科学研究与保护、展示经历了八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和不断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2013—2017年,我们完成了《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一书的撰写,为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文本的编撰提供了丰富详实的资料。根据最新考古成果,划定了14.3平方千米的包括城址、水利系统和瑶山在内的申遗区;基于城址、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玉器这四个基本价值要素,认为良渚符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标准ⅲ(“能为延续至今或业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和标准ⅳ(“是一种建筑、建筑或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良渚古城遗址的申遗文本已于2018年1月26日正式上报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工作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保护、展示和申遗工作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其中凝结了数代考古人的汗水和心血。历次重要的考古发现均得到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物局以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理解、帮助与奉献。正是这一步步的发现和保护,从点到面,最终才有了今天这样一个保存基本完整的良渚古代王国。当我们站在这高高的五千年的良渚王国的宫殿基址上,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敬畏和感恩!
[1]施昕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浙江省教育厅1938年版。
[2]夏鼐:《长江流域考古问题——1959年12月26日在长办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的发言》,《考古》1960年第2期。
[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余杭吴家埠新石器时代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3年。
[4]王明达:《良渚遗址群田野考古概述》,余杭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5]a.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b.南京博物院:《苏州草鞋山良渚文化墓葬》,《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6]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
[7]南京博物院:《l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
[8]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
[9]a.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b.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2005年。
[1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
[1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与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7期。
[12]a.杨楠、赵晔:《余杭莫角山清理大型建筑基址》,《中国文物报》1993年10月10日第3版;b.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莫角山遗址1992—1993年的发掘》,《文物》2001年第12期。
[13]刘斌、王宁远:《2006—2013年良渚古城考古的主要收获》,《东南文化》2014年第2期。
[14]赵辉:《良渚的国家形态》,《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第3期;Colin Renfrew,Bin Liu.The emergence of complex society in China:the case of Liangzhu.Antiquity,2018,92:975-990.中文版见〔英〕科林·伦福儒、刘斌著,陈明辉、朱叶菲、宋姝、姬翔、连蕙茹译:《中国复杂社会的出现:以良渚为例》,《南方文物》2018年第1期。
[1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
[16]黄莉:《建立补偿机制有效保护遗址——良渚遗址文物保护补偿机制的实践与思考》,《浙江文物》2016年第1期。
[17]高蒙河、宋雨晗:《从“良渚全考古”到“良博全展示”——以良渚博物院2018年改陈策展为例》,《东南文化》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