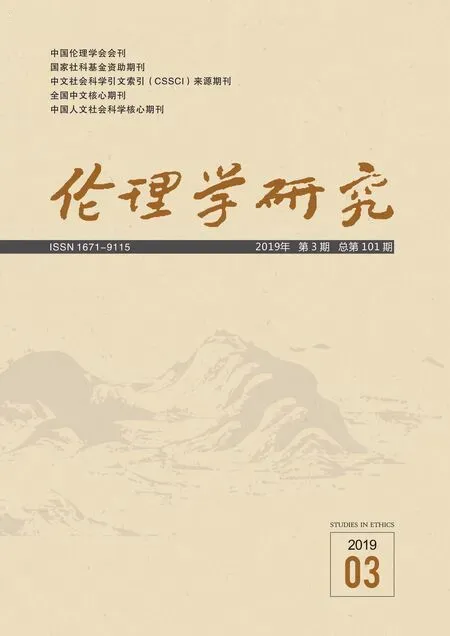医疗纪录片的叙事伦理构建
2019-12-15庞慧敏
庞慧敏
纪录片是记录时代发展变化、反映社会现实状况、呈现社会热点话题的重要传播载体,而医疗是众多民生话题中的核心。近年来,《人间世》《生门》《急诊室故事》等一批高质量的国产医疗纪录片相继出现,客观地反映了当下的医疗现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患者及家属对医生工作的认知与理解,缓和了医患双方的矛盾与分歧,引发了社会公众对医疗改革的反思。
影像画面的连续纪录性,不仅包含丰富信息,还具有故事性,以及对故事的诠释性特征,这意味着影像记录的特定事件往往指涉某种普遍意义。从受众角度来看,纪录片虽然是电子化的、机械的影像集合,但它至少是真实事物的表象,能够触动人们的日常认知与辨识能力,也就使影像实现了自然而然地呈现,完成对事物实然和应然样貌的再现。
但是经由受众感观真实产生的影像,既有溢散效果,也有同化效果。也就是说,影像具有可能造成某种偏见或刻板印象的能力,也有促进认同的能力,特别是对社会道德议题设置与道德标准形成意义重大。这样看来,如何运用影像讲故事对于社会伦理构建具有重要作用,这就是影像叙事的力量。
叙事伦理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从形式上,以伦理的方式构建叙事;二是从内容上,探究叙事所蕴含的伦理意义。医疗纪录片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医院为叙事场景,以医者为叙事主线,其叙事文本具有反映社会问题、传播健康知识、改善医患关系等功能,是健康传播的重要形式。有学者认为,“传播与叙事”之间的关系,不仅强调传播是讯息交换或传递的过程,更是人们通过故事理解彼此日常生活并启迪美好人生的重要途径[1]。因此,通过影像叙事与观众建立意义互动,影响其对故事的认知与重构,能够有效地在道德上触动受众、说服受众。
通过分析影像叙事传播与生命故事的关联性,探究医疗纪录片讲述者如何进行“自我生命再现”,可以实现个人身份与社会关系的构建,唤起受众的集体记忆,产生生命与情感体验,从而完成叙事伦理的建构过程。
一、医疗纪录片叙事的“自我生命再现”
大众传播一向倡导的“信息观”强调客观理性,讲究实证精神,却忽略了传播的主体是关于人的故事。基于此,将“叙事观”引入传播学的研究中,恰可弥补这种不足。这是因为,大众传播是传者与受者共享信息的过程,而叙事是叙事者向叙事对象传达、分享故事的过程,二者之间存在共性。
医疗纪录片以医患之间的故事为主要内容,通过讲述者的自我叙事,借助影像这一文本,向叙事对象(即受众)进行讲述与表达,而纪录片的内容并非只着眼于对现实世界的客观再现,而是从现实世界中选取片段通过符号进行建构与重组的文本,这一过程就是叙事的过程,即“叙事传播”。叙事传播观点认为,人类的传播活动不能脱离于社会环境而存在,传播与交流必须依托表述行为才能进行,因此,人类传播的基本形式即叙事,而叙事的核心是生命故事[2]。
生命故事来源于讲述者的个人生命经历与记忆,换言之,经历即故事,是讲述者选择性地再现与重构记忆过程的结果,而重构之后的故事对于讲述者以及叙事对象来说都具有特殊意义。叙事并非自我的内心独白,而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在与他人建立联系的过程中进行的。讲述者在建构生命故事的过程中会受到社会文化与规则的影响与制约,对过去的自我进行审视、评价,重新认识自我,进而建立身份认同,并寻求他人认同。因此,述说生命故事是人们展示自我、建立联系、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
自我叙事包括自述与他述,讲述关于自己的故事即自述,自我叙事通常以自述为主,自述与个人亲身经历密切相关,个人对于外界的感知促使个人进行自我表达,进而将自我生命记忆与个人经历重新建构、加工并讲述,从而获得生命经验的整合,因此,有他述无可替代的真实感。他述则是转述他人的故事,通常体现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医疗纪录片的影像叙事属于疾病叙事,其中的语言、音乐、画面呈现都是为了叙述病人的生命故事。疾病叙事通常是自述与他述并存,患者对自己的疾病经历、回忆进行整合,之后在镜头前讲述给大众,或是借由他人(与当事人产生社会关系的人)之口,再现与建构其生命故事。疾病叙事的关系性质与回忆录作者和回忆录读者之间存在的联系非常相似,尤其是当回忆录的重点是疾病或上瘾时,这种联系更为显著。在读者看来,回忆录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它代表了作者奋斗与生存的真实生活[3]。医疗纪录片以病患不为常人所知的私人领域生活、自述与他述相交织的叙事方式,提供给病患接近媒介、展示日常生活和生存状态的话语空间,而作为叙事对象的受众通过阅听感知病患的生命故事,可以进行生命与情感体验,因此,医疗纪录片具有情感抚慰、生活引导与质疑社会成规的功能。这种真实生命故事的再现,更容易唤起大众的集体记忆。
这里所说的集体记忆,并非由政治影响力或是特定利益追求引起的,而是通过文化与社会的共同作用,将个人记忆作用于受众,唤起集体记忆。叙事者建构故事的过程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并反作用于社会文化,其个人经验最终将汇入整个社会经验之中,为人们所共享,从而实现教化功能[4](P51-53)。
故事来源于生活而又异于生活。“叙事更加关注故事表达、情感抒发、自我展现、时间空间扮演的特定角色等问题,这在于叙事并非仅是抽象理论,而是‘行动的社区(communities of action)’”[5]。因此,医疗纪录片情感的抒发、自我的表现都会影响受众对于整个故事的接受程度以及情感倾向。具体而言,讲述者的“自我生命再现”方式主要有:
第一,抓取关键记忆。个人故事来源于个人记忆,而个人记忆中只有那些饱含重大情感与重要转折性事件的记忆才能成为关键记忆,才有利于情感抒发与自我展现。McAdams认为5种个人记忆有助于自我定义[6],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三种关键记忆:
转折事件的记忆。这类记忆通常是个人难忘的、严重影响情绪的记忆,比如疾病、生离死别等,常伴随情绪化表达与个人身份的重大重组,对个人的人生际遇与未来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医疗纪录片多是病患展现这类记忆的过程,因患病而导致个人原有身份的丢失与重构,会对个人生命经历造成重大影响。
关联事件的记忆。多是通过此刻的事件回忆起以往的相关事件,将此刻与以往进行整合,建构出新的生命记忆,使个人生命经历得以重构。受众在观看医疗纪录片时会与自己以往的经历进行交换与对比,对故事中人物的生命经历进行情感体验,在此过程中,某些事情的相似性能够唤起自己的相关生命记忆,从而产生同理心与情感依附。
起源事件的记忆。这类记忆通常与不同人生经历的起始阶段,比如求学经历、职业、兴趣、人生目标等有关。在医疗纪录片中,对于患者而言,起源事件是其患病之初的经历,病人在患病尤其是患重大疾病之后,其人生目标、职业、兴趣等生活常态被打破,可能面临失业、遗失兴趣、转变人生目标,转而为治病奔走。
医疗纪录片中的影像叙事通常选择患者或医生的重大情感事件作为叙事主题,比如生育(如《生门》)、罹患重大疾病的经历(如《人间世》)、争分夺秒地抢救(如《急诊室的故事》)、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等,通过这些极具张力与情感的镜头,讲述患者与医生的故事,这种记忆能够使作为观众的患者因经历的相似性产生情感共鸣,同时也会让普通受众产生同理心,通过了解医生与患者的生命故事,进行生命与情感体验。
第二,突出“可能性”与“忠诚性”。尽管叙事不过分强调客观,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随意述说,叙事具有理性,而理性就在于叙事的逻辑性。逻辑性通常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验证,即:叙事可能性与叙事忠实性。叙事可能性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层面是就可能性本身而言的,指故事的连贯性,也就是故事在逻辑上保持一致的能力,包括人物、时间、空间、情感与情节的连贯性,它关系到故事的可信度,这会直接影响受众对于故事的信任,受众只有在认可与接受故事之后才会进行生命与情感体验;第二层面是将其置于医疗纪录片中来解释的,指生命延续的可能性,医疗纪录片叙事中,医生与患者对生命延续的渴望共同建构了这种可能性。叙事忠实性指故事能否说服受众、触动受众,即故事与真实生活经验的相符程度。费希尔认为叙事理论本质上是民主的,任何观众或听众都有能力判断叙事的相对说服力,但是叙事范式理论可以用来检验健康叙事的逻辑,以及健康叙事与实际医疗工作的相符程度[7]。因此,叙事者在进行自我再现时,要关切故事的可信度,突出“可能性”与“忠诚性”,真实可感的故事才利于情感抒发,引发情感共鸣。
医疗纪录片中出现的人物、事件、情节、画面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存在,而且,由于医疗领域的专业性较强,其中展示的业务操作与医学知识都是专业医疗人员的真实呈现,纪录片只是通过影像媒介将其再现,尽管存在后期剪辑,但其基本情况属实,凸显了“忠诚性”。患者与医生真实的生存状态尽数展现在受众面前,其中的情感因其真实性更具感染力与说服力,受众也更容易产生心理共鸣。同时,对于生的渴望贯穿于医疗纪录片的始末,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在为这种延续生命的“可能性”而努力,也正是这种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更容易打动受众。
第三,重构叙事环境。Randall&McKim认为,个人讲述生命故事时,会因叙事环境的变化而选取不同的生命片段,对记忆进行重组与建构,从而实现自我生命的再现[8]。叙事者在进行自我叙事时不是完全按照其生命发展的时间顺序进行的,而是根据不同的时空环境,在不同的情境中选取记忆中的不同片段、不同情节并扮演不同角色,这样看来,不同情景中的话语表达只能反映部分真实。所以,讲述者在自我叙事的过程中根据不同情境选用适当的话语进行表达,更利于抒发情感。
医疗纪录片通过影像文本进行叙事,影像文本建构是对时空元素的再处理过程,因为在屏幕上,时空具有跳跃性与可重组性,是对叙事环境的重构,通常能达到理想的叙事效果。首先,在医疗纪录片中,出现最多的场景是医院,包括急诊室、手术室、重症监护室(ICU)、病房等等,在此叙事环境下,大多选取病人或医生的相关生命片段进行叙事,比如突发心脏病人的抢救(《人间世》第一季第1集)、癌症病人长期的化疗(《人间世》第二季第1集)、连续做了8个小时手术的心外科医生等(《人间世》第一季第1集)等,都与患者或医生的关键生命记忆和经历更为贴近,在特定的叙事空间中,讲述者容易借由场景与物件唤起自己以往的生命体验,真实感更强,也更具压抑感、紧张感。其次,纪录片的影像叙事不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展现的,它的时序会根据故事与情感所需表达发生变化,这体现在纪录片的后期剪辑与安排上,比如《人间世》的每一集选用一个主题,将同类型的病人或同科室的医生放置在一起,产生集聚效应,这样的叙事效果感染力更强,也更能感染受众。
对于普通受众而言,医疗纪录片因其专业性、真实性,以及受众对于医疗行业的未知性,使得其题材本身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加之情感的抒发与生命故事的再现,叙事对象在倾听的过程中接受故事,获得知识,了解自己未曾有过的经历,感悟生命的意义,从而实现情感共鸣,进行生命与情感的体验。对于一些同为患者的受众而言,其影响力更甚。Gro H.Grimsbø等人在进行癌症患者使用交互式健康通信应用的研究中发现[9],一些中高频度使用Web choice的患者(积极的患者)希望通过搜索信息而减少自己对于自身疾病的不确定性,寻求“好转的机会”,获取改善日常生活的建议,增强自己的知识与控制感。受众可以从医疗纪录片中了解到来自专业医生的疾病知识,从而减少自己的不确定性,把医疗纪录片视为“自我帮助的场域”[10],并且通过纪录片体验到与自己相似的生命经历,实则是对自身的一种情感抚慰,其中的正能量会对同为患者的叙事对象产生激励与镇静作用,实现情感共鸣与信息共享。
二、医疗纪录片叙事的个人身份构建与情感依附
医疗影像叙事是借助影像这一文本建构意义的过程,Carlos认为,文本是构成意义的基本单位,但是如果没有叙事与话语,那么文本将毫无意义[3]。因此,文本的叙事具有建构现实的作用,影像即文本。
利科的叙事理论认为,文本与叙事是我们认识和理解自己的媒介,每个人都拥有两重身份:叙事身份和个人身份,个人身份由叙事身份构建,并被叙事身份束缚在伦理领域[3]。因此,叙事是个人认识自我、修正自我、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同时叙事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情境,是在与他人沟通、建立联系中进行的,这种沟通可以同步亦可异步,正是通过与他人的联系,个人可以重构身份,寻求他人认同。可见,叙事活动不再只是单纯地说故事,而是与他人建立关系的表述活动,在此表述过程中,叙事者与叙事对象实现意义的共享与共构,从而达成生命与情感体验。
医疗纪录片通过疾病叙事来构建个人身份:疾病由于其严重性、突发性、长期性迫使患者改变原有身份,这不仅与患者长期忍受疾病带来的生理与心理的双重痛苦有关,也与其思考疾病带来的生命意义的相关问题有关,最终将导致一个人的生活状态、社会关系、期望和目标发生重大重组,以及新的自我认同的重建。重建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可能会贯穿整个疾病轨迹。然而,对于患者来说,关于疾病经历的意义和自我认同通常会在治疗接近完成时出现,此时他们较少关注治疗,而是更多地关注生活。对于患者来说,这是一种更易接受的治疗模式,既是一种医学要求,同时也是一种伦理关怀。
医疗影像叙事是在文本中建构与再现现实生活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并非凭空产生,需要通过“中介媒介系统”[11]才能实现。也就是说,这些建构需要通过中介记忆与现实产生联系。个人故事来源于个人记忆,而记忆并不是自我的内心独白,它会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记忆也不会凭空出现,它需要借助一些特定的事件或人造物品才能勾起以往的回忆,比如照片、影像资料(新闻报道、纪录片等)、日记本或参加一些纪念活动等,这些事件与人造物品大多同记忆存在关联性,因此被称为“中介记忆”。
影像作为传播中介,通过叙述“此刻”实现对以往生命经历的记忆重构。记忆需要依托记录或传播的介质方能唤起,将此刻与以往的生命经历加工与重构,即“社会临场感理论”[12]。叙事对象通过医疗纪录片倾听叙事者讲述故事的同时,唤起自己以往相关经历的记忆,这些记忆经过他人经验共享之后得到补充与加工,从而形成新的生命记忆与生命经验,这种记忆的重构对于叙述者与叙事对象来说都尤为重要,是他们建立社会关系、重新认识自我的重要途径。
媒介故事的内容是转述、再述、构建与再建一般人的生命经验。医学关乎生命与死亡,医疗纪录片通过建构医生与患者的生命故事,向大众展示生命的意义,对于社会大众来说,通过纪录片了解和体验他人的人生故事,可以寻求智慧经验,实现情感依附。
国外研究者召募肺癌患者参与一项实验研究[13],让他们倾听曾经罹患肺癌、目前处于愈疗阶段的肺癌幸存者讲述自己的疾病经历。这一项目通过“直播”“学习”“传递”三个阶段,对肺癌幸存者的个人生活体验,以及成为其他病人的交流者和指导者的经历进行研究,发现肺癌幸存者的经历对于增强其他患者获得知识的能力、创建肺癌社区,以及促进医疗研究和政策实践等问题至关重要。
因此,医疗纪录片的影像叙事其实与上述研究项目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也可以看作是基于“直播”“学习”“传递”三个阶段来建构患者的生命故事,讲述患者的患病经历(包括患者及其家人在身体与心理上的变化)、个人生活经验(包括对抗疾病的经验、对抗疾病的心态、患病之后的生活经验)等,同样利于其他患者从叙事中获取对抗疾病的经验、收获良好的心态、得到更多关于疾病的建议,从而降低对疾病不确定性的恐惧。同时,作为叙事对象的其他患者,因纪录片中故事人物的寻常性以及与自己经历的相似性,更容易产生同理心与共鸣,认为自己并非孤军奋战,而是与其他患者身处同一“社群”,甚至产生叙述自我心路历程的欲望。“这种聆听者即叙述者,因亲身叙事集合在一起,基于同理心而相互启发且彼此聆听的群体,可以称为‘叙事社群’”[16](P12)。在这一社群中,因经历相似而生发的集体身份意识促使叙事者与叙事对象相互回应与支持,产生认同感,彼此因面对共同的疾病困境,又通过分享抵御疾病、积极生活的经验,产生情感关联,这种关乎经验与情感的交流互动,便是一种相互间的情感依附。
另外,在医疗纪录片的叙事过程中呈现大量的医疗知识与专业操作,这些影像对于普通人来说同样是一种经验智慧。人们通过了解纪录片中的医学常识,增加对疾病的认知,获取相关的生命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预防与规避风险。同时,医疗纪录片对医生的生命故事进行大量叙述,再现了医生的日常工作与生活状态,向人们展示了医者仁心、治病救人的医生形象,使受众对于未知的医疗行业有所了解的同时,缓解了对医生工作的误解,从心理上产生情感认同,从道德上被触动,从而实现情感依附。
医疗纪录片通过影像呈现了医疗的救治过程、病人的死亡与痛苦、生死离别的无奈与泪水等,给受众带来更为直观的视觉体验与冲击,因此也更具有感染力,让受众产生同理心的同时也会产生恐惧心理。情感依附理论认为,个人在受到日常生活中的负面经历(此处指体验他人经历,如生病、压力等意外事件)的影响时,会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反应,并寻求安慰,此时,与情感连接的依附需求就会格外突出与迫切,因此,寻求依附的行为也随之出现,对他人的依附是个人消弭无助感的重要方式。通过纪录片,受众体验了故事中人物的生离死别、疾病和痛苦,产生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可能是对自己的也可能是对家人或重要之人的,使受众感受到生命的珍贵与脆弱,对自我进行重新审视与评估,对生命意义产生新的理解,进而进行情感依附,这正是医疗叙事在伦理层面带来的一种警示与教化功能。
三、医疗纪录片伦理叙事的实现
第一,共享“存在感”,实现教育意义。叙事是展现“存在感”的重要途径,通过持续建构与再建构过程达成反思的实现[1]。叙事者在进行自我叙事时,通过对以往生命经历与记忆的再现,建构新的生命故事与生命经验,即建构意义的过程,以此展现自己的“存在感”。叙事对象通过倾听他人的故事、接受叙事者记忆中的经验,能够唤起自己的生命记忆,产生情感共鸣,进而对自己的生命经验进行再建构,此时,叙事对象在再建构的过程中也体会到了“参与感”“存在感”。这种传受双方经验的互动与交流达成一种意义的共享与共构,共享了“存在感”。意义共构的结果势必会造就新的故事生成,新的故事产生新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个人认知自我、认知世界有重要影响。因此,无论是以往经历的故事还是现今重构的故事,都对交流双方具有启发与教育意义。正如教育叙事者Clandinin&Connelly所认为的那样,教育者与研究者都应关切生活、探讨生活,从中发掘生命的经验与真谛[18]。
这种教育叙事的观点对传播学研究有重大启示,将传播学研究引向叙事维度去审视,去关注人本身,发掘传播内容(包括新闻报道)中人的生命意涵与生活经验,将传播视为叙事者与叙事对象交换故事的过程,双方在平等交流、意义互动的空间中分享各自的生命经历,并从对方的故事中选择有价值的经验对自己原有的经验进行补充与重构,进而寻求实现美好人生的途径。正如学者胡绍嘉所言,“我们……必须正视他人的生活世界与生命历史,减少冷漠或讥讽,彼此仔细认真地倾听对方的故事,把对方看成一个独特的、有欲望需求的个体……”[19](P227)在此过程中,双方通过各自的生命述说体验对方的情感与生命经历,回溯记忆以重新认识自我,体会苦难以追求生存真谛,收获经验以享受生活乐趣,这其中的教育意义不言则明。
这种教育意义不仅在于从对方的经验中有所收获,双方共享“存在感”的同时,也感受到被“关怀”、被“关注”,因此,这种叙事是一种出于“关怀”的叙述。诺丁思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任何关系都有两个参与者,一个是“关怀者”,另一个是“被关怀者”[20]。同时,她强调了关怀的三个维度:关注、动机移位和回报。首先,关怀者被动员后,出于自我意愿关心被关怀者,去帮助、支持、接纳被关怀者,并期望其获得幸福。然后,通过动机移位,关怀本身超越了个人利益,通过移情实现对“被关怀者”经历的感同身受。最后,被关怀者对关怀者的关怀行为作出回应。这一关怀与被关怀的过程与叙事者与叙事对象的相互关系如出一辙。在医疗纪录片中,叙事对象作为“关怀者”,倾听“被关怀者”(此处为叙事者)的生命故事,感受他的苦难与经历,通过移情的方式实现生命体验,进而被“被关怀者”所触动,感同身受,实现情感体验,从而对被关怀者流露出支持、接纳、关怀之情,并期盼生命延续的“可能性”;而“被关怀者”通过叙事对象的反应,感受到自己被认同、被接纳、被支持,就更倾向于述说故事,在叙事的过程中不仅能够让“被关怀者”重新认识自我、体悟生命的真谛,也能让广大“关怀者”感激生命、敬畏生命、珍视生命,这就是医疗纪录片带来的伦理意义。
第二,平衡“机构叙事”与“自我叙事”,实现伦理关怀。所谓“机构叙事”,指不同叙事文本的讲述方式因其受各自机构的常规限制而有所不同。在中国,纪录片的拍摄有其遵循的规则,这些规则呈现在影像叙事中便是机构叙事。
纪录片因其客观反映社会真实现状而深受广大受众的青睐,从叙事传播角度来看,叙事传播的核心是故事,好的故事更注重情感的抒发与表达,因此,故事性与客观性之间的矛盾亦是当下国内医疗纪录片的一大隐疾。
从过去“信息观”的角度来看,纪录片的解说词因以第三人的视角叙事更具客观性与真实性,导演、表演成分相对较弱,更容易让受众信服,比如在《人间世》中,叙事者通常以第三者的“他述”(解说词)进行“生命故事的讲述”,而当事人的自述部分较少,这样看似客观,却削减了叙事的故事性。
“说故事”与“说自己的故事”截然不同,讲自己的故事与自我亲身经历密切相关。正如Teresa de Lauretis所言,“人们的主体性总是在叙事、意义和欲望的关系中构成”[18](P206)。叙事是人们通过符号形式依照叙事逻辑进行意义建构的过程,而意义的建构会受说故事者的价值观、社会语境以及其他文本的影响,在这些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下,叙事主体为自己找到一个落脚点,即“自我”,这就是叙事主体重新认识自我、建立身份认同的过程。在叙述者讲述自我生命经历的过程中,对以往的种种经历进行审视与反思,进而体会生命真谛,并渴望寻求更加美好的人生。这一叙事历程不仅对于讲述者自身意义重大,对于叙事对象来说也具有教育性。因此,在影像叙事中,应注重叙事者的自述叙事,尽管医疗纪录片可以通过画面展示叙事者的生存状态与生命经历,然而叙事者在特定的情境中更易抒发情感,通过恰当的自我叙事,达到讲好故事的目的。好的故事不仅会影响叙事对象对于故事的认知与建构,引发情感共鸣,实现生命与情感体验,更容易从道德上触动叙事对象对叙事者的关怀与接纳,尊重生命,体悟美好人生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