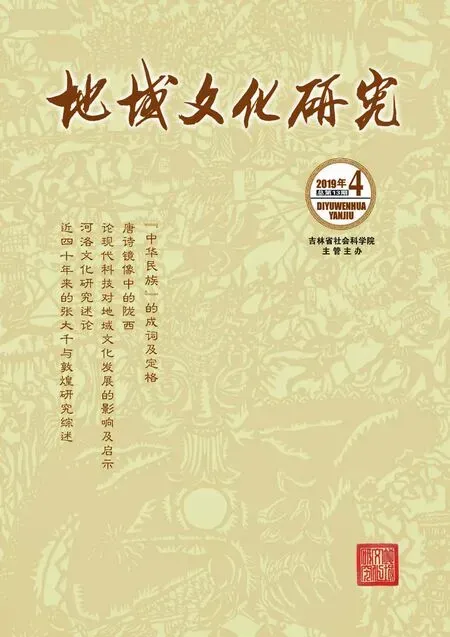近四十年来的张大千与敦煌研究综述
2019-12-14张德明
张德明
1941年至1943年间,张大千为了自己的艺术追求,两次西行敦煌,进驻莫高窟进行绘画临摹,“振千年之颓势,开艺苑之新局,气象雄伟,着色瑰丽,使人物画为之一变”①李永翘:《张大千:飞扬世界》,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542页。,成为其绘画历程的重要转折点,但对于其是否破坏壁画也成为讨论甚多的历史公案。对于张大千与敦煌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前,因其1949年随国民党政权赴台湾地区定居,受历史原因、政治原因等诸多因素影响,在海峡两岸隔阂、对立的局势下,大陆学界几乎没有相关问题的研究论著。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学界开始对张大千与敦煌加以研究关注,并逐渐成为近代敦煌研究中的热点话题。笔者将简单梳理近四十年来,大陆学界对张大千与敦煌研究的代表性论著,从历史、艺术及争论等角度来介绍相关研究,以求对张大千的敦煌之行有所全面认识。
一、关于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历史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张大千的传记较多,都无一例外对他的敦煌之行进行了重点论述。四川省社科院李永翘为专门研究张大千专家,著有《张大千年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国画大师张大千》(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张大千全传》上下册(花城出版社,1998年)及《张大千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等书。其他代表著作还有:杨继仁《张大千传》(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出版,2006年再版)、辛一夫《张大千》(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1994年再版》、白巍《画坛巨匠:张大千》(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①该书在2016年以《一笔贯东西:张大千》为名在陕西人民出版社修订出版。、林彬《一代画王张大千》(安徽文艺出版社,2005年)、王家诚《张大千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刘明山《张大千》(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年)及沙叶新《张大千》(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等书。上述著作都有专章叙述张大千的敦煌之行的缘起、具体活动及贡献,但有些叙述带有文学色彩,缺乏史料支撑。政协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张大千生平和艺术》(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收录了江兆申的《大千话敦煌》、张心智的《张大千敦煌行》、李永翘的《敦煌老人忆大千》三篇当事人关于张大千在敦煌活动的回忆文章。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敦煌当地学者李旭东在团结出版社推出了《张大千与敦煌》一书,分十章系统梳理了张大千在敦煌的活动及其是非功过,如对张大千受李丁陇在成都、重庆的画展影响来敦煌,于右任和张大千在莫高窟的会见,张大千团队在敦煌克服的重重困难及敦煌故旧的张大千情节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为张大千研究提供了许多新见解及新资料。
对于张大千在莫高窟的活动,学者们也进行了客观还原与评价。对于张大千来敦煌临摹的原因,刘进宝分析称:“在当时那种艰苦的条件下,张大千义无反顾地去敦煌,是有多种原因的,除了敦煌作为艺术宝库的吸引外,还有张大千个人要通过敦煌探求中国艺术的源流。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张大千听从叶恭绰的建议,为改变画风去敦煌学习技法。叶恭绰素赏张大千的画,曾力劝张大千弃山水花竹专攻人物,以刷新我国人物画的颓风。”②刘进宝:《丝绸之路:敦煌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79页。对于张大千两次来敦煌的具体过程,陈滞冬指出:“1941年5月,张大千赴敦煌莫高窟调查洞窟情况并编号记录,费时五个月,10月返回兰州,作临摹壁画的准备工作;1942年5月再赴敦煌展开临摹活动,历时十个月。1943年2月以后结束工作,旋即离开莫高窟。”③陈滞冬:《丹青引:中国画研究与欣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3页。对于张大千为莫高窟编号,赵学文指出:“张大千1941年第一次到敦煌,主要是为三百个石窟编号。千佛洞外有一石渠,张大千他们顺着这条石渠,由上而下,从左至右,再顺洞回折向上,花了五个月时间,共给三百零九个洞编了号。这不仅使他们自己工作起来方便,也对后人考查莫高石窟颇为有益。”④赵学文:《张大千外传》,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1页。汪毅提出:“从对敦煌艺术的研究角度讲,张大千不仅为敦煌洞窟科学系统编号,即著名的‘张氏编号’,而且在洞窟中留有相关题记,著有《莫高窟记》,主持编有《已成敦煌目录》《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目次》《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还有在亚太地区博物馆研讨会上宣读的《我与敦煌》论文。至于其艺术表现,即以若干汉唐为主的敦煌壁画为对象,临摹了近300幅作。”⑤汪毅:《张大千与中国文艺复兴》,《成都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李永翘则指出,张大千为了追寻中国绘画的发展源流,曾经不辞艰辛,自费来到敦煌临摹壁画,而其中目的在于,他对破坏严重的壁画进行抢救性的临摹工作,以便能为国家留下一个副本,以后国家有条件时,可用此摹本来作为参照物,用来重修或修缮壁;通过此番临摹,他可以学习和研究敦煌艺术。⑥李永翘:《张大千对敦煌艺术与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一),《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3期。
在临摹壁画方面,学者们论述了张大千团队在此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如有学者称:“这是一项艰苦持久的工作!敦煌夏天闷热,冬天冰封雪冻,石窟高矮各异、空气窒闷,条件十分恶劣,给他们带来了诸多工作上的不便和身体上的不适,然而,他们夙兴夜寐,废寝忘食,克服重重困难,笔耕不辍,因为有伟大的信念支撑着他们。”①清渠编:《民国十大藏家》,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8页。还有学者指出了张大千在经济上的困难,称:“他深入敦煌三年,这么浩大的工程,不但率子侄家人、门人弟子,还需帮手、民工及从青海聘请藏族喇嘛画师帮忙,所需费用是巨大的,总共约有几十万大洋,都是他独自一人承担,为此他变卖所藏古代名家字画,还是债务缠身,以致离开敦煌时债务还高达5,000两(合500根金条),这些债务靠他自己画笔还债,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还清。”②汪毅编:《张大千的世界研究》,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222页。还有学者则称:“张大千临摹的最大幅壁画,达几十平方米之巨,每幅壁画都要记下色彩、尺寸,全部求其原色原大。而千佛洞内,每窟除佛龛佛台之外,空隙之地太小,不能平置画案,而是搭架立起临摹。一手持洋蜡烛,一手拿画笔,有时站在梯上,有时蹲在底下。多数日子是清晨入洞,黄昏出洞,有时则是夜晚开工。”③刘诗平、孟宪实:《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42页。对于张大千带领团队临摹壁画的具体方法,李永翘进行了详细描述称其在临摹中各有分工,又相互配合,“他们临摹壁画的方法是严格按照‘复原临摹法’来进行协摹——即要一丝不苟地按照原始壁画的面积大小临摹下来,色彩也必须要依照古代壁画的颜色,同时更要求摹品的神形皆似,以完全忠实于原作。而对于壁画中那些年代久远、已经变色了的,张大千则首先要在反复调查的基础上考证出它们的原来本色,再在摹本上涂绘出壁画的原色,以恢复壁画刚刚完成时的那种最新鲜和最艳丽的本来面目。”④李永翘:《张大千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第265页。陈滞冬则根据当事人的记录及其他材料,研究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具体时间、摹本幅数及其著作权归属问题,指出:张氏临摹壁画的目的并不是要给敦煌壁画留一个副本,而是借此探讨中国古代绘画的源流。研究古代绘画艺术鼎盛期的技法、制度和格局。张氏的临摹活动改变了他自己一生艺术的取向,为他最后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⑤汪毅编:《张大千的世界研究》,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274页。
对于张大千敦煌之行的贡献,学者们从艺术、学术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学者们认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并对石窟艺术进行了系统研究,撰写了20 余万字的学术专著《莫高窟记》,极大宣传推广了敦煌文化,增强了中国艺术在世界的影响。如山西博物院石金鸣指出:“来到敦煌,张大千不仅怀着敬意对莫高窟等洞窟进行系统编排,发现了壁画之下的画作秘密,更悉心观察、面壁临摹,又将作品进行展览与宣传。实地临摹之举令张大千得以把脉中国传统画,明确其艺术源流与发展脉络,进而画艺精进、笔力健雄;而这些创作于北魏、西魏、隋、唐、五代的壁画经大千之手也更加声名远扬。”⑥山西博物院,四川博物院编著:《大千世界:张大千敦煌临摹作品选》,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致辞。刘再聪则总结其四大贡献称:第一,清除淤泥积沙,科学编排洞窟号码;第二,观察画而色变,大胆追求复原临摹;第三,潜心研究洞窟,积极探索艺术源流;第四,倡议保护国宝,弘扬悠久民族文化。⑦刘再聪:《张大千与敦煌学》,《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2期。罗宗贵、石思茂还强调称:“一方面敦煌之行让张大千梳理了传统人物画尤其宗教画的绘画流程;另一方面让张大千重新研究了从魏晋到五代、宋的宗教画的绘画特点,在中国人物画的研究,尤其敦煌艺术的研究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张大千以其自身的艺术实践在敦煌壁画的临摹中取得显著成果。”①罗宗贵、石思茂:《张大千敦煌壁画研究的意义简析》,《大众文艺》2010年第17期。再如朱介英的《瑰丽的静域一梦:张大千敦煌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一书指出:张大千的敦煌之行,是他绘画生涯的一大转折点,不仅将一段几乎被遗忘的中国美术断代史以临本的形式展现给世人,更使人普遍关注敦煌艺术的文化价值;唤醒沉睡的敦煌,不仅是中国美术的一大福祉,更是中国文化递延的大幸,而张大千确是功不可没的。此外,还有学者关注了张大千于敦煌临摹作品在各地的展览情况。如高万佳称:张大千亦是第一位身体力行认真发掘、整理、考究及有系统地将敦煌艺术介绍于世的中国当代大画家。1941年秋,张大千就将他们在敦煌临摹的首批作品二十余件唐代壁画单身人像,寄到成都,举办《西行纪游画展》,轰动一时。1943年他回川后,出版了他的《敦煌临摹白描画》三集。1944年,他又先后在成都、重庆进行了敦煌画展。②高万佳:《张大千》,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第31页。
对于张大千在敦煌的人际交往,也有学者进行考察。如徐晓卉考察了他与范振绪的关系,指出:1941年夏天,张大千和70 高龄的甘肃著名书画家范振绪从武威一起前往敦煌考察,结成了两位忘年交好友的敦煌情缘。张大千为范振绪作画刻印,范振绪给张大千画题跋,表现了两位艺术家因敦煌而结的深情厚谊。③徐晓卉:《张大千和范振绪的敦煌情缘略论》,《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刘进宝关注了向达与张大千的交往,指出:作为著名历史学家和敦煌学家的向达与著名画家的张大千,由于敦煌而结缘并结怨。1942年,向达因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到达敦煌,此前张大千已率亲友在敦煌临摹壁画。由于对敦煌石窟艺术保护、研究、临摹的不同看法和态度,双方发生了矛盾。向达在1942年12月的《大公报》上发表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对张大千在敦煌的行为作了批评和指责。向与张的矛盾或冲突,首先是是非之争,即张大千在临摹壁画时对敦煌艺术的破坏,作为学者的向达要保护敦煌,反对、制止这种破坏。其次,也有考察期间经济、生活等特殊情况的因素,同时还应该是学术观念之争。他们之间的学术之争,涉及了当时的学术理念、生活状态、学术团体与个人、学界与政界的关系。④刘进宝:《向达与张大千——关于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学术史考察》,《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2期。李永翘则论述了张大千在敦煌与常书鸿、于右任的交往,指出:1941年中秋,于右任来莫高窟看望张大千,张大千则向于右任建议成立专门机构加强对莫高窟的保护,后于右任于1941年12月向国民政府建议尽快建立敦煌艺术学院;张大千在1943年离开敦煌时,将在莫高窟发现的唐朝将军张君义的一支泥塑断手,各种碎经残页及在敦煌所做的调查研究和记录考证等成果,交给了常书鸿。这些资料为常书鸿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后来研究敦煌文物艺术,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借鉴。⑤李永翘:《张大千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民国春秋》2001年第3期。对于他在1943年被迫离开敦煌,陈传席称:正当张大千在敦煌莫高窟得意之时,却被甘肃省主席谷正伦赶走了,其要张大千限期离开敦煌,原因是他损毁和破坏敦煌莫高窟的壁画。而且张大千从敦煌回川时,在路上还受到军统特务对其行李、临摹壁画的多次检查。⑥陈传席:《读书人一声长叹》,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第69页。
二、关于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艺术研究
张大千在敦煌莫高窟临摹了近三百副壁画,学者对其临摹内容也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如郑弌由张大千临摹的一幅敦煌供养人像切入,试图重访西北考察语境下的张大千,指出:“作为艺术家,张大千的敦煌临摹、考察活动多以审美价值彰显,不为学术研究所重。但张大千以其艺术直觉的敏感,重新发掘了归义军时期供养人像作为生者真仪的特殊性。他的临摹使人物画像完全脱离了石窟情境,使得其摹本多为艺术家而非史家所重。”①郑弌:《吾民:再论张大千敦煌考察(上)》,《艺术学界》2018年第1期。马涛则认为张大千敦煌壁画临摹作品为整理研究性的临摹,对壁画残损部分进行了有选择地复原临摹,总结有三大特点,“首先画稿以透明纸从壁画上印描,临本与原壁画同等大小,展现了壁画宏伟气概。其次,对敦煌壁画由于经千百年风化、侵蚀造成色彩褪变的面貌进行恢复,使其金碧辉煌、鲜艳如新。再次,对原壁画存在的瑕疵加以改动,带有再创作的思想和意识,使临本更趋于完美。”②马涛:《张大千敦煌壁画临摹绘画技法探析》,《美术大观》2012年第11期。彭文静则考察了敦煌供养人像与张大千所做的仕女画的关系,指出:仕女图是张大千的作品中自成一体、独具一格的重要部分,尤其是他自敦煌归来后的仕女画作品较之前风格大变,令人叫绝,这与其在敦煌临摹壁画中供养人像有密切联系,特别是在审美、画法上都有许多借鉴。③彭文静:《敦煌供养人像与张大千仕女画——谈大千仕女画风格之变因》,《博物馆研究》2012年第5期。
张大千与敦煌壁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可谓相互成就,学者们也进行了探讨。陈祥明关注了张大千对壁画的研究,称:张大千对有纪年的壁画都一一登记,分门别类,并和中原艺术进行比较研究,考察了不同朝代的人物衣冠装饰、艺术传承、画风递嬗等等,从而得出了莫高窟艺术和中原艺术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自己的而非外来的艺术这一重要结论,并确证“敦煌壁画出自名手而非工匠”。张大千对各个朝代的壁画画风、特点、技艺等均作了深入而详尽的界说。他从规模的宏大、技巧的递嬗、包孕的精神和保存的所得四个方面论述了敦煌壁画的特点。④陈祥明:《大师的风景》,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127页,第134页。对于他与敦煌壁画的关系,徐建融指出:敦煌壁画与中国画的现实创作发生密切的关系,张大千起了重要作用。张大千总结出敦煌壁画的十大亮点,其本人亦受益于敦煌壁画而创作出了伟大的作品。⑤徐建融:《张大千与敦煌壁画》,《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7期。王炜民则认为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为莫高窟作了科学系统的编号;其二,对敦煌壁画作了系统研究,并将这一艺术珍宝向社会作了生动感人的宣传;其三,揭示了敦煌石窟画下藏画的奥秘;其四,推动了敦煌艺术保护与研究事业的发展。”⑥王炜民:《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研究的贡献》,《阴山学刊》1996年第2期。有学者则强调称:“张大千在敦煌研究和临摹古代壁画,对隋唐至北魏的人物、山水及佛教画都有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从而对中国传统绘画有了系统和完整的认识。敦煌之行刷新了张大千人物画的面貌,佛教艺术中天上人问的人物形象、敦煌的历代供养人和经变佛教故事中的世俗生活形象,使他从传统画稿程式化的人物造型中解放出来,不仅超出了他原有的人物画技法水平,而且开创了古装人物面向现实、反映时代风貌的新画风。”①刘建一、刘邦一:《世界画坛百年:20世纪杰出画家生活与创作》,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第340页。还有学者称:“在敦煌临摹的两年中,张大千致力于隋唐、五代的人物、山石、花卉等的临摹,风格大有转变,与之前可谓判若两人。正所谓当他临摹了大量壁画之后,他自己的人物画风,已完全舍去了原有的格调。他后期的人物画格,完全由敦煌而来。而对于中国古代传统绘画,大千也有了新的认识,在各个时代画风问题上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②20世纪中国艺术史文集编委会编:《艺术的历史与事实:20世纪中国艺术史的若干课题研究(1900-1949)》,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87页。
对于张大千临摹壁画的意义,学者也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如马涛指出:“张大千潜心临摹敦煌壁画,深入研究敦煌艺术,绘画理论和技法进一步升华,并且实现了自身的超越,奠定了张大千一代绘画大师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张大千挖掘了敦煌壁画的价值与意义,向世人宣传、展示敦煌艺术,首次为莫高窟作了科学、系统的编号,保护历史文化宝藏并大力弘扬这一艺术瑰宝,推动并促进了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③马涛:《张大千敦煌壁画女性形象研究》,《艺术百家》2015年增刊。李莉的硕士论文《试析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意义》(山西大学,2013年),分析了张大千不辞辛苦来临摹敦煌壁画这个历史事件,探讨了其临摹壁画的动机及艰辛历程,并探索了张大千临画的方法及个人画风的变化,认为其无论是否破坏壁画,都对民国美术及画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徐大纬的文章结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最新诠释》(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3年),对张大千临摹的壁画进行了系统研究,如对张大千首创的复原临摹法,所作《观无量寿经变》版本、临摹腰鼓舞伎和天宫乐舞、被遗忘的敦煌临摹壁画等细节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见解。赵声良则对张大千的临摹敦煌壁画的影响指出:“一方面,对于敦煌艺术研究来说,其临摹敦煌壁画在四川等地大规模展出,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学者们关注敦煌,研究敦煌艺术,从而促进了敦煌学研究的发展,也使更多的人开始重视以敦煌石窟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艺术。另一方面,对于张大千个人来说,对敦煌壁画的临摹是他绘画艺术发展的重要阶段。经过敦煌艺术的熏陶,张大千在人物画方面形成了新的风格。”④赵声良:《敦煌石窟艺术总论》,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57页。王家达则称:“敦煌之行是张大千艺术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经过千年古迹的洗礼,他的艺术水平有了质的飞跃,精神气韵升华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从此,他的视野更加开阔,底气更加饱满,技巧更加纯熟,手法更加多样,创造出一种独立于世的气势恢宏、瑰丽雄奇的艺术风格。”⑤王家达:《莫高窟的精灵:一千年的敦煌梦》,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3页。
对于张大千此次临摹敦煌壁画的艺术地位,学者多有讨论,肯定了其复原临摹法的创造性及其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巨大贡献。如张重岗提出张大千敦煌之行对中国文艺复兴的推动,称:“对敦煌壁画的临摹和研习,使得张大千对中国的文人画传统作了反省。张大千自设的使命是在绘画上重新激发民族的活力。在他心目中,敦煌壁画不仅仅是单纯的画艺而已,实则具有在绘画史上补偏救弊的重大意义。”⑥张重岗:《张大千敦煌之行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化研究》2014年第3期。叶浅予则对其画法解释称:“大千临画的方法,是透过现象,恢复原状为目的。凡现状有变色或破损处,尽可能推测其本来面貌,行笔着色虽有所损益,仍忠实于原画的精神。他临画的目的,在于学习古人的造型设色和用笔的方法,为自己的创作所用。”①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张大千》,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76页。巴东还称:“张大千绘画艺术与敦煌石窟艺术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张大千赴敦煌苦修三年,掌握了敦煌石窟艺术最重要的创作特质——‘法相庄严’的独特视觉装饰效果。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临摹及摹本展览对于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其于古迹国宝之维护与宣扬功不可没。”②巴东:《论张大千绘画艺术与敦煌石窟艺术的内在联系》,《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李永翘的《论抗战时期张大千对于敦煌艺术的贡献》(《抗战文艺研究》1984年第2期)及其发表的《张大千对敦煌艺术与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3期、第4期)等文章,则是从总体上论述张大千对研究、宣传及保护敦煌艺术的贡献。
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目前集中收藏于四川省博物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近四十年来,国内推出诸多关于张大千临摹壁画结集的画册,如《张大千临橅敦煌壁画》(四川美术出版社,1985年)、《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第一、二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张大千临橅敦煌壁画白描稿》(四川省博物馆,第一至四辑,1988年)、《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四川美术出版社,1997年)、《大千世界——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作品展》(云南省博物馆,2010年)、《大千世界——张大千敦煌临摹作品选》(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大千与敦煌:四川博物院藏张大千绘画精品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年)等。但是这些画册多是简单结集出版,缺乏对作品的深入介绍与研究。
三、关于张大千是否破坏敦煌壁画的争论
张大千是否破坏了敦煌壁画,这是一个争论颇久的历史公案。早在20世纪40年代即有很多学者质疑张大千破坏敦煌莫高窟壁画,在向达等人的呼吁下,张大千迫于压力于1943年离开了敦煌。关于此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即引起了讨论。《旅游天府》1981年第2 期发表了署名石湍(刘忠贵)的文章《张大千并未破坏敦煌壁画》,作者曾在莫高窟工作,以当事人回忆称张大千并没有破坏敦煌壁画,反而是用力恢复和整理了壁画。同年,曾与张大千一起到敦煌的谢稚柳在香港讲学期间也认可了此种说法,称他没亲眼看见张大千把两幅败壁打掉,并认为既然外层剥落严重,在确定里面有壁画情况下,可以把外层揭掉。③李永翘:《文物界中的一桩大冤案——记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来龙去脉》,《中国文物报》1988年1月8日,第1版。四川省社科院李永翘则在1988年1月8日的《中国文物报》发表《文物界中的一桩大冤案——记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来龙去脉》一文④此文经作者修订后,还发表于《敦煌文史资料选辑》1995年第3辑。,梳理考证得出张大千没有破坏壁画,其所引用的证据除了上述两位当事人在内的多人回忆,并称是县府随行人员损毁敦煌壁画,该文最关键证据为:1948年7、8月间,部分议员在甘肃省参议会上要求省政府调查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一事,予以严惩。经过调查,1949年甘肃省府函复称:“查此案先后呈奉教育部及函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电复:张大千在千佛洞并无毁损壁画情事。”他在《丝绸之路》1997年第2期发表了《还张大千一个清白——关于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案的调查报告》,继续为张大千鸣冤,结论仍是张大千并没有破坏敦煌壁画,与上文观点类似。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当时甘肃省府的调查不足为凭,缺乏客观性与说服力,坚持认为张大千损坏了壁画。
此事到21世纪又起波澜,缘起在2000年8月22日,《新民晚报》记者杨展业发文《张大千在莫高窟留下的问题——揭开敦煌宝库一历史谜团》,后被《人民日报》海外版摘选,引起海内外极大反响。该报道指出,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罗庆华在回答该报记者询问称:“张大千剥损的壁画总共约有30 余处。张大千在敦煌期间,雇用了几名当地的喇嘛和农民为他打杂,而这些人亲眼目睹了他剥损莫高窟壁画的行为。但凡是被张大千剥掉的壁画,都成了废土,从此就毁灭了。”①杨展业:《张大千在莫高窟留下的问题——揭开敦煌宝库一历史谜团》,《新民晚报》2000年8月22日。该文发表后,郑重随后在2000年8月31日的上海《文汇报》发表《张大千破坏了敦煌壁画吗?》,介绍了关于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三种说法,他则认为是因为张大千并未破坏敦煌壁画,而是被人诬陷,并且还认为张大千使之“恢复旧观”的唐代壁画,对研究敦煌壁画艺术史的断代起了决定作用。②艾绍强:《永远的敦煌》,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第136页。杨展业的文章曾被很多报纸转载,如同年9月1日《宁夏日报》以题为《国画大师张大千为何要破坏敦煌壁画》转载,曾陪同张大千赴敦煌的其子张心智看到后,为鸣不平,在11月22日的《中国文物报》发表《张大千不曾破坏过壁画》一文,指责该文严重失实,引用了李永翘之前文章的证据给予否认,并称自己当时亲眼所见,张大千并未破坏任何壁画。同年12月22日《上海劳动报》上刊登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对此事看法,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张大千破坏壁画,并称:“正是张大千在四川展出临摹的敦煌壁画后,敦煌文化才震惊了世界。”“张大千对敦煌壁画进行了准确、细致的‘断代’,同样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③剑华:《敦煌研究院院长昨认为,张大千盗壁画无证据》,《上海劳动报》2000年12月22日。
争论发生后,李永翘在《东方艺术》2000年第6 期发文《张大千没有破坏敦煌壁画》,在《阳关》2001年第1期发表《张大千没有破坏敦煌壁画》,在《寻根》2001年第2 期发表《张大千从未毁损过敦煌壁画》,在《西部》2001年第11 期发表《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真相揭秘》等文章,梳理了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传言产生的过程,并继续坚持提出张大千从未破坏过敦煌壁画。还有学者对张大千揭剥第130 窟的壁画称:“他并不认为这是对壁画的损坏,因为里面的是更为精美的壁画,揭剥表层为的是让更美的艺术重见天日。然而当时的条件和揭剥技术,不仅会让外层壁画荡然无存,也必然会损伤里层壁画。更何况,精美的壁画是艺术史的珍品,表层的壁画同样也是艺术史唯一性的证据。张大千为艺术的激情所鼓动,但却忘记了保存历史原貌的意义,结果当然是他的这种发现越多,对敦煌壁画的破坏越大。”④刘诗平、孟宪实:《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45页。随后贺世哲在《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发表《对张大千“不曾破坏敦煌壁画”之质疑》,经过考证指出:第130 窟主室东壁北侧大面积的表层壁画也是张大千剥掉的,认为他步伯希和的后尘,用同样的手法破坏了第130 窟甬道南北壁的表层宋代壁画,并且他带走了在莫高窟发掘的文物。彭金章在2007年的《敦煌考古大揭秘》一书中也指出,张大千在莫高窟临摹壁画期间,曾指使当时居住在上寺的徐喇嘛(汉卿)和马步青派来为张大千担任保卫的“枪兵”,对北区洞窟进行了乱挖乱掘,给莫高窟的考古学研究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并且他还将挖掘的文物带走,作为私人财产秘密收藏。⑤彭金章:《敦煌考古大揭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2-56页。但亦有学者却为其进行解释称:张大千当时果断地“破壁”,是对研究敦煌壁画艺术史的断代问题有所贡献,此“破坏”非彼“破坏”,是去伪存真,应该算张大千的一番功绩。张大千当时所收藏的宝物,最后都捐献给国家,并不能简单地将其行为认定是为个人私利盗取古物,据为己有。①汪锋编:《名人密码:张大千的传奇与风流》,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95页。沙武田则指出:“客观而论,张大千对敦煌艺术的弘扬功不可没;但他也的确有为了求得早期的绘画而剥离表面壁画的破坏文物之失;加上他临摹壁画多是直接帖在壁画表面,多有破坏壁画之事;又经他之手使部分敦煌文物流散出去,均造成永远不可挽回的损失。”②沙武田:《敦煌壁画故事与历史传说》,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9页。
近年来,学界对此事又加以关注。如2017年2月,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在讲座中回答该问题时,则提出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张大千在敦煌的活动,回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评价张大千。他认为当时的技术、经济条件有限,张大千从艺术家的眼光,剥掉表层壁画,露出更早的壁画,是可以理解的。③李超:《敦煌“掌门人”:将推动跨国敦煌数据库构建》,《兰州日报》2017年2月23日,R13版。2018年2月,曹鹏则撰文指出,张大千热爱艺术,本意仍是保护敦煌文物,并且经他的建议才有了以后政府对莫高窟的保护,可以说他是敦煌的功臣,在临摹壁画过程中不妥之处乃是无心之过。④曹鹏:《如何看待张大千的敦煌壁画临摹(上)》,《江阴日报》2018年2月23日,第A04版。同年,李旭东在其《张大千与敦煌》专著中也梳理了此公案,他认为:“以张大千本人的价值观和道德操守来看,故意大规模砍伐破坏敦煌壁画的可能性不大,只能说客观上他的确对敦煌壁画有一点很小的破坏。虽然剥离残破壁画应该向有关部门报告请示,但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情况,法制体系也不健全,保护条例也没有,张大千真想打剥离壁画的报告,未必找得到人接收,所以这件事还应该酌情考虑。”综上所述,虽然许多当事人出于各种考虑不承认张大千损坏壁画,但包括敦煌研究院人员在内的多数学者对张大千剥掉壁画或多或少已经承认,但又肯定了其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纵观近四十年以来的张大千与敦煌的研究,可谓是颇为活跃的研究话题,众多学者的论著从历史、艺术的不同视角推进深化了此问题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张大千敦煌之行对推广宣传敦煌艺术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是其个人绘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但是关于张大千是否破坏莫高窟的壁画的历史公案,仍然没有定论。笔者认为,张大千临摹壁画的艺术成就及发扬介绍敦煌文化的贡献无可否认,至于其是否破坏壁画,还是应抛弃个人感情,一切从史料出发,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具体情况下进行考证,并对这些史料及当事人的说法进行真伪辨析,既不能神化张大千,也不能丑化他,才得出公正结论。而且对于张大千敦煌之行的研究,中国学界的综合考察较多,但是仍有许多细节需要考证清楚,有必要进一步整理相关档案、报刊及与其同往敦煌亲历者的资料供学者参考,并还应充分吸收借鉴海外学界关于张大千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于张大千临摹的近三百幅壁画作品,在综合分析其艺术价值基础上,也有必要加强这些个案的艺术研究。总之,有关张大千与敦煌这个富有争议且丰富的研究问题,未来仍须学者进一步深挖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