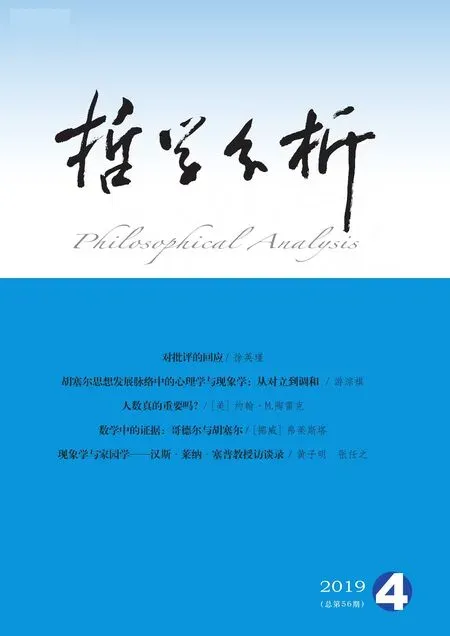人数真的重要吗?① 据John M. Taurek, “Should the Numbers Count?”,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6, No. 4, 1977, pp.293—316译出。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陶雷克仅发表过这一篇文章,《人数真的重要吗?》对当代英美伦理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2019-12-14约翰陶雷克文王薛时
[美]约翰·M.陶雷克/文王薛时/译
我们拥有一些资源可用来分配利益或者避免伤害,但资源的支配却受诸多限制,例如,由于太多的人的存在,我们无力使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救助,此为一种限制。还有另外一种经常会遇到的限制,我们必须在使一些人受益(或避免使这些人受到伤害)和使另外一些人受益(或避免使另外一些人受到伤害)之间作出选择,而无法兼顾双方。这篇论文要讨论的一般性的问题是:就行动决策而言,在权衡案例(trade-off situations)中我们是否应该把互竞双方的人数看作本身具有重要性的东西。②我关注的权衡案例具有相对简单的结构。这些案例给出了三个选项:(1)我们可以救助特定的一个人(或者一组人);(2)我们可以救助完全不同的一组人;(3)我们不做任何事情去救助任何人。(我暂不考虑第三个选项,即便我并不认为不救助任何一个人在道德上是不被允许的。)罗伯特·施华兹(Robert Schwartz)使我对某些与简单权衡案例相似的例子有所警觉,这些设计相似的例子涉及不同的但相互重叠的成员。举个例子,假设第一个选项是救助A而非B或C中的任何一人;第二个选项是救助A和B而非C;而第三个选项则是救助C而非A或B中的任何一人。稍后便知,那些持有我在简单权衡案例中所提观点的人并不能轻松应对这个或者比这个更为复杂的例子。除了提出这些让我不安的例子之外,施华兹也想出了解决这些决策问题的办法,这个办法和我对于简单权衡案例的看法是相容的。不过,我担心讨论这些复杂的问题会扰乱我的主要论证,故而舍去。我的结论是否定性的,人数并不真的重要。我对这个一般性问题的讨论集中在某个特定的虚构案例上,在这个虚拟构建的例子中我们身处一个特定的位置,我们能够保护一个人免遭一个特定的伤害,或者保护其他五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免遭一个相同的伤害,却无法保护全部六个人免遭伤害。
论文所考虑的案例是:我有一些救命药物。①这个例子由菲利帕·福特在其论文“Abortion and the Doctrine of Double Effect”中提出,参见Moral Problems,edited by James Rachels, New York:Harpercollins College Div, 1971。有六个人需要这种药物治疗,如果没有得到恰当的救治,他们都会死去。然而,其中的一个人需要全部的药物才能存活,其他五个人每一个人只需要五分之一的药物。试问,我应该怎么做?
对于面对此般情形的很多人来说,暂不考虑特殊的情况,一种很自然的选择是大多数人应该得到救助。我拒绝接受这种观点。我认为赞同这种观点的人们中间至少有一部分未能认识到一个特定的困难,即他们在这个案例中持有的观点不能与他们持有的其他更为根深蒂固的观点相调和一致。首先,我想描述某些刚才提到的困难。以此为参考,我希望其他人能够更具批判精神地省察支撑这种观点背后的直觉。其后,我会提出一个至少对我来说是恰当的、有吸引力的处理类似权衡案例的办 法。
那些认为我应该把药物切分成五等份然后分给五个人的人,对于自己的立场毫不含糊。他们坚持认为:“其他事项保持不变,或者不考虑特殊情况,多数一方应该得到救助。”他们所说的特殊情况究竟是什么呢?“其他事项保持不变”这个附加条款让我们不再考虑何种情况?
我认为他们所考虑的特殊情况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关于某个人的特殊说明会让他的死比其他情况下这个人的死更为糟糕(worse)。例如,他就快要发明出一种特效药,或即将为世界常年动乱地区赢得永久和平。这里的意思是,一个人的存活会以某种重要的方式对相当多的人们的福利产生影响。在这些人看来,这种特殊情况会让他的死成为一件更为糟糕的事情。当然,他们所想的还有一种可能性,关于五个人的特殊情况会使得他们的死并不算太糟糕。他们五个人或许是连路都不太能走的老人或是弱智的婴儿,没有人会在意他们是生是死。在这种情况下,救助一个健全的人而不是其他五个人在道德上是被允许的,在某些人看来这甚至是道德上负有义务去做的事情。所以,当人们说“其他事项保持不变,多数一方应该得到救助”,他们已经排除了上述考虑的特殊情况。他们的想法是,暂不考虑特殊情况,五个无辜的人的死要比一个无辜的人的死更为糟糕,相较于一个人的死,五个人的死是一件更为有害的(greater evil)、产生更大损失(greater loss)的事情。鉴于我只有能力避免两个糟糕事情中的其中一个发生,道德要求我去避免更为糟糕的事情发生。
这个推论对于很多人来说颇具吸引力。不过,让我不解的是它如何与这些人广泛分享的其他信念相协调一致,对于这一点我甚至难以想象。考虑一个例子,这个人叫大卫,大卫是一个我认识并且喜欢的人,而其他五个人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人。我很有可能会把自己的药物给大卫。我倾向于认为:假如这么做,我并没有做出不道德的事情。我推测大多数人都会持有和我一样的看法。
当然,有些人确实会认为我的做法与道德的要求背道而驰。他们认为,因为认识并且喜欢大卫我就把药物给他而让其他五个人死去是错误的。尽管他们认为大卫是我的朋友这一点让我的行动变得情有可原,但它并不会让我的行动成为正确的。
就目前而言,我的观点主要针对那些分享我的观点的人——把我的药物分配给一个我认识并且喜欢的人并不是错误的,即便这些人认同的是上述提到的一般性立场。他们一定会否认,原初主张以及其背后的思想会迫使他们接受我应该救助五个陌生人这个观点。他们或许会反驳,当例子引入大卫这个我认识并且喜欢的人的时候,我已经引入了另外一个特殊情况,而“其他事项保持不变”这个条款正是为了消除特殊类型的考虑。但是,如果这是一种有意被消除的特殊情况,它也不同于前文提到的特殊情况。后者是一些关于五个人的特殊情况,以使得他们的死并没有那么糟糕,或者是一些关于大卫的特殊情况,让他的死要比一个其他普通人的死更为糟糕。这些特殊情况对我应该如何行事产生影响,这是因为这些特殊事实的存在会让一个人的死要比五个人的死更为糟 糕。
但是,我并不认为大卫——与其他五个人相比较——恰好是我认识并且喜欢的人这一事实会让他的死比在我并不认识他或认识他而并不喜欢他的情况下他的死更为糟糕。所以,我并不太明白这一事实如何对这种情况下道德要求我去做的事情产生影响。我也不太清楚的是,这一事实如何对那些相信我有道德义务——这个义务来源于下述事实,其他事项保持不变,五个无辜的人的死要比一个无辜的人的死更为糟糕——去救助五个人的人的观点有所改变。
或许,这些特殊情况与前文提到的特殊情况存在很大的不同。假设一个人提前与我签订了契约,规定在特定的时候我必须把额定数量的药物给他。有的人也许会认为,这种通过签订契约所产生的针对某一方的特殊义务(special obligation)优先于把药物分配给五个人避免了更为糟糕的事情发生。契约或者承诺并非是这种特殊义务的唯一来源。父母可能被认为对孩子负有特殊的义务,或子女对父母负有特殊的义务;医生可能对病人负有特殊的义务;人们也许会认为个人对捐助者负有特殊的义务,等等。人们可以合理地认为这种针对特定人群的特殊义务的存在也是“其他事项保持不变”有意排除的对象。但是,对于那些想要在把药物给朋友我并没有做错事这种直觉和固守原处立场之间作出调和的人们来说,诉诸特殊义务究竟有多大用处呢?
这似乎并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回应。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作出的假设是什么?难道是因为某个人是我认识并且喜欢的人我便负有优先义务(overriding obligation)去救助这个人?这个假设似乎无法说明我对相关案例的思考。我之所以去救助大卫——一个我认识并且喜欢的人——是因为我对他的福祉(well-being)的关心要强于对其他五个人的福祉的关心,而并不是因为我意识到对他负有的优先义务。设想一个例子,这里只涉及大卫和另外一个陌生人。在这个陌生人缺少权利主张的情况下,我会救助大卫。如果被问及解释或者辩护我的选择,我并不会答复说——由于我认识并且喜欢大卫这个事实——我在道德上被要求把药物分配给他。大卫是我的朋友这一事实相当自然地解释了我偏向于救助他而不是其他五个人。正是缺少救助另外任何一个人而不是大卫的义务,才使得我的选择在道德上是被允许的。无论正确与否,在当下所讨论的例子中我对自身行为就是这么设想。对我而言,救助大卫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偏好。在缺少救助其他人而不是大卫的义务的情况下,我的做法在道德上是被允许的。
然而,对大卫负有特殊义务的说法似乎太过强硬了,这种义务并非来源于我们之间的承诺,契约或者准契约关系,而是来源于我认识并且喜欢他这一简单的事实。这是因为这种观点并不仅仅说的是救助大卫是被允许的,而是我在道德上负有义务去救助他而不是其他五个人。可是,这并不是那些认为救助大卫并非是错误的人的想
法。按照当下讨论的观点,人们在道德上被要求——其他事项保持不变——去救助五个人而不是一个人,这是因为—其他事项保持不变——五个无辜的人的死要比一个无辜的人的死更为糟糕。然而,如果这个事实构成了分配药物给五个人而不是一个人这一道德义务的有力根据话,那么我十分怀疑它的道德效力(moral force)。这里的问题是,如何解释——特别向那五个人——为何仅仅因为我认识并且喜欢大卫而与他们五个人没有交集就能使我逃脱救助他们的道德要求呢,况且这个道德要求是其他在我这个位置上的人大多会承担的。这里唯一相关的考虑便是我恰好喜欢大卫胜过喜欢其他任何人。想象一下我对他们说:“说实话,如果不是我对他的生死有所偏好,相关的事实让我在道德上负有义务把药物分配给你们。”这里所说的事实必定非常脆弱,竟能被一个同样脆弱的诉求击败。
让我们把当下考虑的案例与另外一些案例相比,在后者所描述的情形中,我们愿意承认分配药物给五个人这一道德要求的理由。举个例子,假设这五个人事先和我有契约,规定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我要把药物分配给他们。任何人似乎都不太可能会认为我偏爱把药物分配给某个人这个事实会以任何方式对我负有的道德义务有所改变。当然,从心理学角度讲,它可能会让我履行义务变得更为困难。再设想一个例子,这五个人是美国军人而我是军队的医生,并且只有少量的药物可以使用。让我们再设想这另外一个人是我认识并且喜欢的一个人,但他是其他国家的公民。有任何人会认为我偏好用药物救助这个人这一事实能够以某种方式废除或者搁置我负有的分配药物给五个军人的义务吗?
其中的要点如下。一般而言,当相关事实让任何一个不偏不倚的人接受像分配药物给五个人之类的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的义务时,诉诸这个人恰好对某些人的利益怀有偏心并不能推翻道德义务。这正是这样一些人的看法,他们坚持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不偏不倚的人在道德上被要求把药物切分为五等份分配给五个人。但是,因为我个人偏好于把药物给其他人,故而道德允许我这么做。①想要调和这些观点着实不易。这里我无法面面俱到评述这些观点。我主要的兴趣在于凸显出任何想要调和这些立场的尝试都会面对严重的困难。面对这些困难,我的想法是,那些坚持原初观点的人们也许会被激励以开放的心态去重新思考必须救助多数一方的道德要求的根据,特别是在行动者对所有相关的人都持有不偏不倚的态度的情况下。
我的想法是,我们要么赞同在这个案例中我救助大卫是错误的,要么承认救助五个人而不是大卫的道德要求是没有根据的。如前文所言,让我们现在考虑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在这个案例中我偏好于救助大卫是错误的。他们会觉得目前的讨论只是在证明这一点。因此,我打算回应他们的观点,以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行动者去救助一个朋友而不是五个陌生人在道德上是被允许 的。
假设这个药物属于你的朋友大卫。这是他的药物,他需要服用额定的药量。其他五个人无论对你还是大卫来说都是陌生人。你会试图劝说大卫把他的药物分给其他五个人吗?你认为你应该这么做吗?假设你尝试劝说大卫,你会怎么开始?你要求他放弃自己的生命而让其他五个陌生人继续存活吗?
设想你试图和大卫讲理,就像如果药物属于你,你和自己讲理一样。“大卫,可以确定的是你的死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确实非常糟糕。但是难道你没有发现五个人的死是一件更为糟糕的事情吗?现在,你有能力避免任何一个糟糕的事情发生。可惜的是,你没有办法避免它们都发生。因此,你应该确保更为糟糕的事情不会发生。”
难道你没有想过大卫会抱怨吗?难道他不会问道:“对谁而言更糟糕?”大卫以下述方式提出的辩护也许是非常自然的而且也是相关的:“对于我而言,我死他们生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我也不否认,对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而言,他们死我生要比我死他们生更为糟糕。凭心而论,我不会要求(也不期望)他们放弃自己的生命以使得我这个陌生人能够继续存活。但是,为什么你或者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想让我放弃自己的生命,以使得他们每一个人都能继续存活?”我认为大卫的问题确实切中了要害。那五个陌生人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可以促使大卫认为值得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保全他人。惯用的功利主义的说理方式即使不是令人恼火的,也一定是滑稽可笑的。设想五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请求大卫说道:“喂!大卫。我不过是一个人。如果你愿意把你的药物的五分之一给我,我就会活下去。我可以肯定的是,从长期看来我会获得更大的‘快乐—痛苦’和‘幸福—不幸’的净余额。诚然,如果这就是你的死可以实现的全部东西,我并不期望你会放弃自己的生命。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继续活下去,你也可以合理地认为会实现至少一样多的快乐余额。但你没有看到吗,这还有第二个人。如果他继续活下去,他一样会得到一个不错的‘快乐—痛苦’的净余额。而且,这还有第三个、第四个和第五个人。我们现在并不是叫你去死以使得我们五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能够实现自己快乐余额。因为你也可以认为自己能够在生命中实现同样的东西。然而,认为你自己在生命中可以实现我们五个人加总在一起的令人愉悦的净余额将是多么的不合理。”
这种由置身事外一方做出的冷淡推理即便不是令人憎恶的,也不免被人诟病为愚蠢。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了向大卫兜售下述主意的荒唐,即通过比较性地关注五个人的幸福加总得出的更大的总额让他认识到五个人的死要比一个人的死更为糟糕,那么什么样的推理听上去会稍微不那么荒唐呢?暂时把关于他们幸福的考虑放在一边,让他关注五个人所承载的内在价值的总额会不会不那么荒唐,尤其是和自己所承载的内在价值相比。
我想不出来我能给大卫何种理由以说明为什么他应该认为五个陌生人的存活要比他一个人的存活更好。可以理解的是,用他自己的药物保全自己的生命,大卫所成全的是对他而言极为重要的东西。他看重自己的生命胜过看重其他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当然,这并不是说他认为他“显然地”比其他任何一个人或五个人加总在一起更为重要。(不管显然这个词作何理解)另外,我想强调的是,当拒绝把药物给其他五个人时他并没有错误地对待任何一个人。在这个情况下,五个人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对大卫的药物提出合理的主张(claim),因此五个人加总在一起也不会有这样的主张。如果他们攻击大卫抢夺药物,他们就是谋杀犯。你和大卫两个人完全有权利抵抗这种抢夺药物的行为。
这就是我倡导的观点。我希望大多数人能够赞同我。然而,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大卫在道德上被允许把药物留给自己,那么为什么道德就不允许我做同样的事情了呢?这是我的药物。对我而言,大卫的存活要比其他五个人的存活更为重要。我看重他的生命胜过看重其他人的生命。在这个情况下,五个人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对我的药物提出任何特别的主张,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要求我把药物给他而不是大卫。因此,五个人加在一起也没有这种特别的主张。若是我用自己的药物救助大卫的生命,我并没有错误地对待任何一个人。假设这五个人意识到我准备救助大卫而故意抢夺药物,我抵抗他们的行为可以得到完全的辩护。
至目前为止,我已经说明清楚了,鉴于道德允许,大卫使用自己的药物救助自己而不是其他五个人,因而,假设药物是我个人所有,并且我对五个人中任何一个人没有特殊义务,道德也允许我使用自己的药物救助大卫而不是其他五个人。一些人可能会觉得我所论证的观点太过于违反直觉了。按照我的观点,如果一方A必须决定要免除另外一方B所承受的损失或者伤害H,还是要免除第三方C所承受的损失或者伤害H’,除非B——不考虑对立的特殊义务的情况下——负有义务免除C的伤害H’,哪怕以牺牲自己的义务为代价,否则A—不考虑特殊义务的情况下——没有道德上的义务免除C的伤害H’。换言之,我的想法是:如果道德允许B选择免除自己受到损失H, 而不是选择免除C受到损失H’,那么在权衡的情形下,其他人——在不受制于任何对立的特殊义务的情况下——一定会被允许采取B的视角,选择做对B而不是对C最为有利的事情。
下面是一个可能会被提出的反例。许多人(估计大多数)或许会赞同,如果B身处在特定的位置上以至于他能够保全C的生命或者保全自己的一条胳膊,但没有办法兼顾两者,那么道德——不考虑特殊义务——并不要求他选择一定要保全C的生命。一个会被提出的问题是:“但如果作出选择的人是你呢?你要么保全C的生命要么保全B的一条胳膊。难道你不认为自己——不受制于特殊的义务——有义务去保全C的生命吗?你选择保全B而让C死去难道不是错的吗?”
我并不认为在这个情况下道德并不允许我去保全B的胳膊。这个道德要求的根据究竟何在?我所面对的选择是两个可能的结果中哪一个能得到实现:一个结果是B的胳膊得以保全而C则会死去;另外一个结果是B会失去他的胳膊但C的生命得以保全。如果这个选择是B作出的,那么他被允许选择第一个结果。但是,我就不被允许作出同样的选择。为什么会这样?根据假设,在这个情况下我不受制于相关的特殊义务。所以,B和我之间存在何种差异以使得我在道德上被要求确保一个对C有利的结果,尽管道德并没有对B作出这样的要求?除非出于某种理由行动者在道德上不被允许把另外一个人的福利看作自己的福利来对待,那么我一定被允许——在不受制于特殊义务的情况下——选择对B有利的结果。当然,如果对我而言B的福利比C的福利更为重要,那么确保C的福利就是我会做的事情。
然而,B要失去的东西和C要失去的东西之间的差异可能会达到一定的程度,以至于我会选择保护C不受侵害。但是,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下,我倾向于认为即便选择由B作出,他也应该偏好C的利益得以保全。对某些人而言,在B要失去胳膊和C要失去生命这个例子中过大的悬殊程度已经达到了。就这个例子而言,人们的态度可能存在根本性的差异,我不知道如何判定孰对孰错。我个人并不认为任何人——不受制于特殊义务的情况下——应当保全我的生命而不是保全他们自己的胳膊。其他人也许并不这么想。
我怀疑那些认为这个所谓的反例能够对我的观点形成有力威胁的人大多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多半认为自己确实应该准备好牺牲自己的胳膊以保全我的生命。然而,如果选择真的出现,他们会怀疑自己是否还会这样做。切身感知到这一点,他们就不会把这种要求施加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然而,当他们把自己设想为第三方角色的时候,对于保全C的生命他们不再有所犹豫,第三方角色对B的福利并没有特别的关心。毕竟,失去胳膊的人并不是他们。但如果这就是他们的想法,那么他们对我倡导的观点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威胁。
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权衡案例展开进一步的分析。我的看法是,如果药物是大卫的,他——不受制于特殊义务——使用药物救助自己的生命而不是放弃药物给其他五个人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出于同样的理由,我认为——暂不考虑特殊义务——假设药物是我的而大卫是某个我认识并且喜欢的人,我把药物给他而不是其他五个人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因此,我必须否认任何第三方——暂不考虑特殊义务——在道德上被要求去救助五个人而让大卫死去。那么,在缺少对任何相关的一方特别的关心的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让我谈一下在类似的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做。在我眼前有六个人,对他们中每一个人的福利我都感同身受。我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人死去,但是我又没有办法救助所有人。为什么不给每一个人以平等的活下去的机会呢?例如,我可以抛一枚硬币。如果正面朝上,药物归五个人,如果反面朝上,药物归一个人。这种方式给每一个人以50%的活下去的机会。每当我遇到类似的情况,抛硬币似乎是最能体现出我对每一个人平等的关心和尊重(equal concern and respect)的方式。有任何人能够抱怨我做错事了吗?基于何种理由呢?①这篇完成之后,我注意到多年以前安斯康姆小姐对这个最早由福特女士提出的案例的评论。这个案例给她的感觉是,行动者把药物给一个人,五个人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抱怨他受到了错误的对待。关于她的评论请详见“Who is Wronged?” , The Oxford Review, No. 5, 1967。
行动者应该救助多数一方而不是少数一方这个主张依赖于另外一个主张,即五个人的死——其他事项保持不变——要比一个人的死更为糟糕。我不能接受这个评价性的判断。我不愿意接受下述说法,即“五人死,大卫生”要比或将要比“大卫死,五人生”更为糟糕。我不愿意接受这种说法,除非事先限定清楚对谁而言,或相对于谁,或相对于何种目的而言,它是或者将是一个更为糟糕的事情。
我承认,对于五个人中的每一个人而言,大卫生他们死要比大卫死他们生更为糟糕。但是,若是从大卫的视角出发,情况就不同了。对于大卫而言,他死是一件更为糟糕的事情。从我的视角出发,我的境况不会因任何一个结果而改善或者变得更糟糕,但其他人无疑会受到所发生的事情的影响。对于那些喜欢或需要大卫的人来说,其他五个人死比较好。但对于那些与五个人有亲密或者依附关系的人来说,大卫死而五个人生比较好。
对于这种判断的意义,我无法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这种判断和那些针对特定的人和团体抑或是特定目标和目的的相对价值的判断存在重要的区别。面对两个可能的结果,当我作出判断对于这个人或者这个团体而言一个结果会更坏(或更糟糕),我并没有在两个结果之间表达出一种偏好。一般地说,我并没有受到压力去承认我或者任何一个人应该偏好一个结果而不是另外一个结果。但是,当我从一个客观的视角评价结果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说从道德的视角),事情就变得极为不同了。当我判断这个发生要比那个发生明显更为糟糕的时候,一般而言,我确实在两个结果之间表达出了一种偏好。另外,我至少感受到了某种压力去承认我应该持有这样一种偏好,即使实际上我并没有持有这样一种偏好。未能做到偏好本身被认为是好的事情而非本身是坏的事情在道德上是一种缺陷。
因此,我不能把这种非切身的评价性判断当作决定把药物给五个人而不是一个人的理由。我没有办法对这个人说出下面的话:“我之所以把药物给五个人而让你死去是因为他们死比你死要更为糟糕,难道你没有看到这一点吗?”我并不期望大卫或者任何在他这个位置上的人应该认为他死而五个人活要比他活五个人死更好。我并不认为,仅仅因为他偏好他活五个人死这个结果,而不是他死五个人活这个结果,他便在道德上有缺陷。
在大卫是我的朋友而其他人是陌生人的情况下,我确实偏好于某个结果而不是另外一个结果,对我而言这样的偏好相当自然,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鉴于我并不期望每一个人都分享这个偏好,我并不打算把它表达为一个普遍性的具有约束力的评价。我并不是要对五个人说,我之所以把药物给大卫是因为他的存活本身要比五个人的存活更好。我不认为这种说法是可取的。毋宁说,我只是解释说大卫是我的朋友。他的存活对我而言要比其他人的存活更为重要。我希望他们能够理解这一点,假设他们是我所接受的道德共同体中的成员的话,就像我们的角色相互调换时我会做的那样。另外,确保大卫得到救助我并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利。我的行为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辩护,就像在药物属于大卫的情况下没有进一步的辩护需要被提出一样。他不需要,或者说根本不应该,把他的存活本身就比其他人的存活更好这个判断当作决定把药物留给自己救命的理由。谁能够期望他们中的任何人接受这一点?他只需要指出,就像这真的需要说明一样,对于他而言他的存活要比其他人的存活更为重要。而且,在保全自己生命的时候他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利。难道还有别的需要说吗?
对我而言,在当前考虑的权衡案例中所有六个人都是陌生人,我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特殊的情感,不曾对某个人比对其他任何一个人有更大的关心。另外,根据假设,我的境况不会因为任何一个结果而变得更好或者更坏。因此,如果我的偏好不是武断的,则需要理由作为支撑。当然,这正是一个非切身的评价性判断需要满足的要求。如果我偏向于把药物给五个人,那背后一定有理由支持我的偏好。我不能赞同对于这些结果的评价性判断。因此,在这个情况下我确实没有理由偏好五个人而不是一个人,同样地,也没有理由偏好一个人而不是五个人。故而,我倾向于给每一个人以平等地得到救助的机会从而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
尽管如此,我能想象有人可能还是会说,“但人数肯定还是重要的”。有的人会充满疑虑地问道:“在救助五十个人和救助一个人之间你还会抛硬币决定吗?在互竞双方的人数悬殊过大的情况下,你必须承认行动者必须救助多数一方而不是少数一 方。”
暂不考虑特殊情况,在这个情况下我仍然会选择抛硬币。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单是人数的增加就能对决策有所改变。在我看来,在当前讨论的案例中那些主张我把相对人数自身看作重要的人就是让我以衡量物品价值的方式来对待人。如果六个物品受到火灾的威胁,我只能救出在一个房间中的五个物品,或者在另外一个房间的一个物品,而无法使六个物品都得到保全。在这个情况下我作出决定的方式和人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作出决定的方式并无二致。在我看来,每个物品都有特定的价值。如果六个物品的价值相同,我自然会保护多数一方的物品而不是少数一方。为什么?这是因为五个物品的价值加总在一起是一个物品的价值的五 倍。
但是,在刚才描述的例子中,当我去救助人不受伤害的时候,我并不是以对待物品的方式来对待人。我对他们的遭遇有着深刻的同情。我对他们遭遇的关心主要在于我意识到他们每一个人都极其关心自己的遭遇,就像我在他的位置上会关心自己的遭遇一样。我不会把他们看作具有一定的客观价值的东西,像对待物品的客观价值那样来决定人的客观价值,然后计算出五个人的价值的总和,随后再与一个人的价值相比较。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对象是和我一样的生物——对于他们而言所要发生的事情极其重要,我不会这么在意他们是生是死。如果仅仅是完整无缺的物品,我不会这么看重它们,它们和路边的毒蘑菇一样常见。Pietà失去一条胳膊对我而言非常重要,但这不是因为Pietà会想念它。像我一样的生物失去一条胳膊对我而言非常重要,这仅仅是因为我知道他会想念它,就像我会想念自己的胳膊一样。我所关注的是对于某个人而言的损失(the loss to this person)。他失去胳膊不会影响我看重的东西。但是,如果我真的关心他,我应当希望他不要遭受损失。
如果我把药物给五个人而让大卫死去,我不确定的是我因此保护了任何一个人免于承受一个比大卫所承受的损失更大的损失。而且,相似地,如果我把药物给大卫而让其他五个人死去,我看不出来我让任何一个人承受了一个比大卫避免承受的损失更大的损失。每一个人潜在的损失对我而言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这里的损失是对于某一个人而言的损失。因为根据假设我对每一个相关的人都有相同的关心,我给每一个人以平等的免于遭受损失的机会。
我对于这些权衡案例的思考方式是,仔细考虑如果我不介入这个人会失去或者承受什么,然后把失去或承受的东西对于他而言的重要性,与其他任何一个人在我不介入的情况下会失去或者承受的东西相比较。这反映了对下述加总概念的一种拒斥,即在相关的情形中把两个各自独立的人的损失加总计算。对我而言,这实际上是对人们在相似的权衡案例中的思考方式的一种自然的扩展,这种案例中所涉及的相关的人的损失并不相同,甚至那些认为我处理迄今所讨论的案例的方式荒谬的人也是这么认为。或许,作为最后一项劝说他们的努力,考虑下面这种权衡案例是十分有益 的。
假设我知道,如果作为陌生人的你同意承受某种较大强度的痛苦,我便能免除承受一个较小的痛苦,我不清楚有什么原因能够让你自愿作出这样的牺牲。要求你作出这样的牺牲只能说明我的懦弱。现在加上第二个人,对你而言仍然是陌生人。再一次地,我们被告知,如果你自愿承受较大的痛苦,我们两个人都能免除承受较小的痛苦。如果在这个情况下我要求你作出牺牲,我丝毫不觉得自己不再受人鄙视了。你没有理由为了我能免除痛苦而让自己遭受苦难。对此我能说的大概只有这么多
了。
现在增加更多的成员——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承受如你一般的痛苦——到我这一方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它不应该改变我这一方的任何事实。如果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给你一个好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你情愿经受巨大的痛苦以使得他免遭较小的痛苦,那么你就干脆没有理由承受痛苦以使更多的人可以免遭更小的痛苦。承受痛苦不是以这种方式加总的。多数一方每一个人经受的较轻的头疼所带来的不适并不能加总为任何一个人经受的偏头痛。在这种权衡案例中,你的痛苦或者损失所比较的对象不是我们集体的或者加总后的痛苦——无论如何理解加总后的痛苦,而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个人所承受的痛苦或者损失。
或许可以理解的行为是,一个只有你自愿承受相对较小的痛苦才不会承受很大痛苦或者巨大损失的陌生人会要求你认真地考虑他的处境,让你同情他将要经历的痛苦。但是我认为,要求你认真考虑承受痛苦,对我们之中任何人而言只能是一种令人鄙视的行为,“当然,不是我自己将要承受痛苦。没有人只会考虑自己。然而,请关注我们作为一个集体会承受的痛苦。想一想经过抵消之后的痛苦的总和。我们这一方显然承受了更多的痛苦啊。”按照最好的理解,这种说法是令人费解的。按照一般的理解,我认为它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然而,在之前描述的例子中这种想法却被一些人继承,他们根据互竞双方的相对人数来决定如何行事。如果对所涉及的当事人来说人数并不重要,那么为什么对任何其他人来说就重要了呢?假设我能解除你的痛苦或者解除多数一方的人们较小的痛苦,却无法兼顾双方。如果没有当事人可以把人数看作是重要的,为什么我就可以这样做呢?我不能理解为何我应当加总他们各自的痛苦继而附加上重要性,这么做对当事人来说是不妥当的。如果让你承受痛苦,我看不出我因此为任何一个人解除了更大的痛苦,甚至是程度相当的痛苦。我不明白为什么关注人数就更能让我解除多数一方而不是你的痛苦,相比于当你没有理由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作出牺牲的时候,关注人数能让你牺牲自己以成全多数一方。
我的目的并不是争论,在这个情况下仅仅因为你的痛苦比其他任何一人的痛苦更大,我就应该解除你而不是多数一方的人的痛苦。毋宁说,我想澄清的是,在这个案例中,为达成一个决定而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你和多数一方任何一个人在没有我的介入的情况下会承受的痛苦之间的比较,这是非常自然的做法。我想强调的是,在这个案例中加总多数一方人们的痛苦并不是自然的做法。我想挑战的是某些人们持有的一种明显的思想倾向,即他们对五十个人中每一个人承受的某种强度上的痛苦的回应,和他们对某些人承受大量或者五十倍强度的痛苦的回应,两者是完全一样的。我认为这种倾向正是那些在权衡案例中认为人数重要的人们的思想中活跃的部
分。在最开始的虚拟案例中,我们必须在救助大卫的生命和救助五个人的生命之间作出选择。在作出决定的时候,我并没有把他的损失和五个人集体的或加总的损失相比较,而无论对这种集体或加总的损失如何理解。毋宁说,我应当比较的是,在我不介入的情况下,大卫的损失或苦难和任何其他一个人的损失或苦难。如果大卫没有理由为任何一个人牺牲自己的生命,相比专注于人数会让大卫为了多数一方的存活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使我专注于人数不会更加让我救助多数一方,而不是大卫,对我而言,人数本身并不重要。我认为人数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应该在行动决策中算作重要的因 素。
我猜想有些人会认为下面这个充满荒唐性的案例对我的观点造成难以应付的困境。假设火山喷发让许多人的生命处于危难之中,多数一方聚集在一个岛屿的北端,少数一方聚集在岛屿的南端,双方都在等待救援。附近仅有的救援力量海岸护卫救援船的船长发现自己恰好处在这两拨人中间的位置。船长应该先救谁?他被我的论证说服,面对船员和同事、官僚的惊讶,政府的愕然以及随后媒体的狂轰滥炸,他抛出了硬币,最后去了小岛的南端救人。
究实而言,对于我们道德文化中的许多人来说,直接把船驶向岛屿北端救人显然是船长的义务所在,根本无需通过抛硬币决定应该救谁。然而,我并不打算否认这确实是船长的义务。但是,我们需要询问的是,船长负有义务的来源究竟何在?如果船长负有救助多数一方而不是少数一方的义务是因为,其他事项不变,多数人死少数人生要比少数人死多数人生更糟糕的话,那么我不能接受这一点。但是,我怀疑这就是大多数人快速和确信的判断之背后的思想方式,面对这个案例,他们声称诉诸抛硬币来决策哪一方得到救助,船长违反了他负有的义务。
这个案例和我之前一直讨论的案例在许多重要的方面存在不同。在这个案例中,船长所能控制的资源并不是他个人所有的,至少不是他个人专有的东西。尽管在对这个案例的描述中这一点并没有直接交代清楚,我认为,很多作出快速判断的人已经预设了,每一个可能会受到伤害的人对于资源的使用或从资源中受益持有平等的主张(equal claim)。因为这些理由,海岸护卫救援船的船长在这个情况下被认为是受制于义务的(duty-bound),受制于按照相关的资源使用政策来行动的义务,这种政策能够被资源的所有者承认。因此,这里考虑的相关问题,和某个普通公民决定如何行使船只,或者分配药品,或者伸出援助之手,存在很大的不同,后者并不受制于特定的道德限制,仅仅受制于那些每一个人都服从的限制。
对于这些不同的觉察显然会对那些面对这个案例的人的判断产生影响。例如,将大多数人判断海岸护卫救援船长的行为方式与他们对于一个普通公民的行为的判断相比较。如果这个普通公民先去岛屿南端救人,是因为少数一方中有一些是他亲近的人,而多数一方都是陌生人,人们大多不会提出抗议。尽管有些人会说,这个人来岛屿北端救助多数一方会是一件更好的事情,但是他们不太可能会认为,这个人的行为违反了他负有的相关的义务。然而悲剧的是,即便海岸护卫救援船长有朋友在岛屿南端,如果他先去救助自己的朋友而不先去救助全都是陌生人的多数一方,那么他违反了自己所承担的义务。人们便会认为,船长的行为违反了那些能够对相关资源提出合理主张的人们的权利。海岸护卫救援船长如何辩护先去岛屿南端救援的决定?他怎么向岛屿北端的人们辩护他的行为?对于多数一方而言,船长亏欠他们一个辩护。个人的偏好不会起到辩护作用。这是因为在岛屿北端的人们对相关的资源具有平等的主张。
所以这个例子和之前讨论的例子存在很大的不同。有的人可能会强调说,关键之处在于人们认为船长被要求首先去救助多数一方的人。抛硬币决定哪一方应该得到救助对他而言是错误的。难道这个案例不就是一个反例吗?作为一种辩护,除了下述说法以外我们还能对那些留在岛屿南端的人们说些什么呢,“岛屿北端多数一方的人们的死要比你们少数一方的人们的死更为糟糕”。
我认为,在这个案例中对于船长的行动而言还有一种可能的辩护,这个辩护不需要诉诸任何这类的主张。它是一个更有吸引力的辩护。我猜测它更接近于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可能错误地)认为的事实。我认为我们可以这样来思考眼前的案例。一群人联合起来投资一项资源,其主要目的在于保障投资人的利益。每一个人是否投入了一份绝对平等的份额,以及每个人的投资是否可以细化到与其匹配的资源,则不是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至少从理论上说,每一个人的投资(或者地位)可以被看作赋予他享有一份平等份额的权利,对于资源的使用或者从资源中受益享有平等的主张。在类似于当前的权衡案例的情景中,一项关于资源如何使用的政策必须被采用。而且,这项政策必须提前被所有相关的人赞同,这项政策被看作能够平等地服务于他们的利益。那么,船长的义务——不管其内容是什么——就被看作来源于这份协议。因此,为了向那些没有得到救助的人辩护船长的行动,我们只需要援引他们和其他人一起事先达成的这项政策即 可。
就这样一个协议或者政策的形成而言,我并不反对以下这种考虑人数的方式:把未来可能发生的权衡情景中的相对人数看作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种方式让我免于作出非切身性的比较性的结果评价,而之前提到的对船长行为的辩护诉诸这种结果评价。所有的人可以提前达成一项协议,假设一个权衡情景发生,资源要被用来救助最大多数的具有平等主张的人们。这是因为,我可以假定,在资源以集体名义被认购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权衡情景中他会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不知道是在多数一方还是在少数一方。因此,这样一项政策可能会被所有的人接受,其理由在于它能够最大化每一个人从资源中获利的机会。
根据这样一个预设的协议,船长负有的直接救助多数一方的义务就能够得到辩护。这种观点和我所坚持的关于数字并不重要的观点是相容的。因为这种辩护没有诉诸下述观点:少数一方的死要比多数一方的死本身是(或将是)一件更好的事情。这样一个辩护并不要求一个人从某种非切身的、客观的(道德的?)视角出发,承认他的生命要比两个人或三个人抑或是三百个人的生命具有更少的价值。
我相信很多人会偏向认为,这种辩护在类似于当前所讨论案例的大多数情景中是行得通的。但是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事实可能是,当并非所有人都能受益的时候,某个关于使用资源以使更多人受益的政策,无法通过诉诸每一个主张者渴望得到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机会而得到辩护——当然,此处说的是平等的机会被分配给每一个主张者。举个例子,设想在这个岛屿上多数人生活在岛屿的北端,南端只有少部分人居住。现在有人提议岛上的每一个居民投资一艘救援船。使用救援船救助多数一方的政策无法——基于它给每一个人提供了平等并且是最大化的存活的机会——兜售给那些居住在岛屿南端的人们。他们非常清楚的是,根据这项政策,一份平等的投资并不能享受到和岛屿北端的人们一样的利益。不过,他们仍然可能会被说服而进行平等的投资。鉴于他们的处境,这也许是他们能为自己作出的最好的选择。但是,他们并不会把这项政策看作每一个准股东的利益都获得了平等重要
性。如果少数一方的谈判地位比较有利,我相信岛屿南端的人会为一个更加公平的政策而坚持不懈,为了能够真正平等地从相关的资源中受益,或是为了降低他们的投资费用,抑或是为了从别处得到一些补偿。现在我们能够想象岛屿北端的人们在诉诸道德时会怎么说吗?“听我说,你们都是体面的人。一言以蔽之,难道你没有看到,生活在岛屿北端多数一方的人们生而你们少数一方死,要比你们少数一方生我们多数一方死更好。所以,请你们明智地、实心实意地看待真实的道德原则,让我们赞同假设某个权衡的情景发生,救援船要去救助多数一方的人们。”谁会在这种诡辩上浪费时间?还不如强迫少数一方赞同这个政策来得简单一些,这至少不会让人觉得那么伪善。①诚然,事情可能会比这里所设想的更为复杂。或许这个救援船投资只是岛上全体民众通过中央政府以经常援引的“公共利益”之名做的许多投资中的一个。岛屿南端的人也许会听到下面这种说法,尽管这次提议的有关救援船使用的政策并没有授予他们以平等的得到利益的主张,但是他们不应该抱怨。在过去的“社会行为”的实践中,他们也以北方人为代价享受了一些好处,并且借助立法政策的力量期待在未来获取更大的好处。或许有人可能会争论说,从长期看它能够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某些版本的“多数决定原则”对政策制定而言可作为参考。我非常想找出一个清晰的论证思路突破迷雾。但是,如果问题的背景是如此复杂,那么对于船长直接救助多数一方的义务辩护的探讨,就会回到一个关于一般性问题的讨论上来,即政府及其职能的道德根基的相关问题。而这些问题并非是本文要处理的议题,即便它们并非毫无关系。
截至目前,我一直讨论的案例是居住在岛屿上的居民拥有(或提议投资)一艘救援船。每一个人都把自己视为对相关的资源拥有平等的主张,不管其背后的理由是他被要求进行投资活动,或者是他作为岛屿居民的地位。因为资源十分有限,它无法满足所有人需求的情况可能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存在很多可能的关于资源如何配置的政策。然而,并非每一个政策都能确保每一个人对相关的资源持有平等的主张这种自我认知。例如,设想医疗研究者、高层管理人员以及智商超过120的人被给予优先的资格,不管采纳这种政策的理由是什么,它显然没有平等地对待岛屿上的每一个人。它并没有显示出对每一个人的生死的平等关心。因此,如果平等的关心是居民认为他们有资格得到的东西,他们会拒斥这种政策。
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会拒绝在权衡情景下救助多数一方的有关救援船如何使用的政策。生活在岛屿南端的少数一方无法理解这样一个政策如何授予了每一个居民以平等使用集体资源的主张。设想生活在南端的人们知道岛屿北端人们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救援船所能容纳的承载量。在这个情况下,有人提议说救援船应该去救助多数一方。你不太可能期望南端的人们会被你说服——这个政策体现了对岛屿上每一个居民生死的真正的平等关心,它给予了每一个人以平等地使用资源的主张。你或许也会试图说服智商在100以下的人们,让他们相信给研究者、管理者以及高智商以优先资格的政策来体现对每个人生死的关心。
当要判断一个与其利益相关的资源如何使用的政策的时候,我认为这就是大多数人如何思考这些案例的方式。但是,当遇到利用他们自己的资源去救助别人的情况下,这些人对于资源应如何配置的想法就有所不同了。举个例子,假设这个岛屿的居民购买了一艘救援船。在邻近的一个岛屿上居住着另外一些人,他们也受到火山的威胁,但是因为贫穷,他们无力购置救援设备。拥有救援船的人愿意帮助其他岛屿上的居民。关于救援政策的问题仍然会出现。当然,他们可以按照其他岛屿上人们的智商或是社会重要性的次序来布置救援工作,这么做并没有违反任何人的权利。但是,他们或许想要一个能够平等地对待所有人的政策,真正体现他们对每一个人的生死一眼就可觉察出的平等的关心。继而,他们便会拒斥那个偏好救助高智商人群和具有光耀的社会地位的人们的救助政策。这种政策和他们渴望对每一个人的生死表达出平等的关心存在不相协调之处。然而,如果大多数居民居住在岛屿的北端,而只有少数居民在岛屿南端,我们岛屿的居民——如果他们和我们的情况大致相同——决定派遣救援船救助岛屿北端的人们。诚然,那些生活在岛屿南端的居民不能抱怨我们的行动违反了他们对于这个救援船持有的财产权利。但是,对于岛屿北端的居民和南端的居民来说,这个案例中的救援政策能被认为比之前案例中的救援政策更好地体现了对每一个人生死的平等的关心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