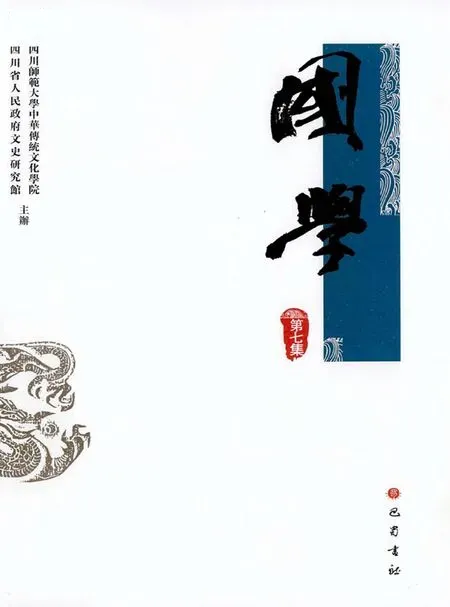文勢與義理:論朱熹的韓文校勘
2019-12-13趙聃
趙 聃
錢穆先生認為:“朱子平生從事校勘最大之成績,實開出後來校勘學上無窮法門,堪稱超前絶後。”①錢穆:《朱子新學案》,成都:巴蜀書社,1986年,第1740 頁。這裏所説的“校勘學上無窮法門”指的就是朱熹在《韓文考異》中所採用的校勘方法與原則。據朱熹《韓文考異》,可知朱熹校勘的原則與方法是“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他書之可驗者決之”②[宋]朱熹:《書〈韓文考異〉 前》,《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朱子全書》第24 册,第3682 頁。亦見於《昌黎先生集考異》,《朱子全書》第19 册,第367 頁。“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它書之可證驗者決之。”二處文字有區别。以下《昌黎先生集考異》皆簡稱為《韓文考異》。。朱熹的這一方法與原則實際上是在方崧卿所作之《韓文舉正》的基礎上而提出的。具體而言,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韓文考異》的校勘體例
朱熹所作《韓文考異》一書的體例是在對《韓文舉正》體例的批評中確立起來的。據《跋方季申所校韓文》載:
余自少喜讀韓文,常病世無善本,每欲精校一通,以廣流布而未暇也。今觀方季申此本,讎正精密,辨訂詳博,其用力勤矣。但《舉正》之篇所立四例,頗有自相矛盾者,又不盡著諸本同異,為未盡善。蓋此等書,前人為之,已有成例,若大書本文於上,而用颜監《漢書》法,悉注衆本之同異於其下,因考其是非,以見定從今本之意,則讀者有以曉然知衆本之得失,而益信吾書之取捨不誣矣。萬一考訂或有未盡,取捨不無小差,亦得尚存他本别字,不遂泯没,以待後之君子,尤久遠之慮也①[宋]朱熹:《跋方季申所校韓文》,《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三,《朱子全書》第24 册,第3905 頁。。
朱熹雖然認為方崧卿所著之《舉正》有“讎正精密,辨訂詳博”的優點,但也存在所立體例自相矛盾,諸本異同不盡著的缺點。朱熹這裏所説的“所立四例頗有自相矛盾者”,據《韓文舉正·序》可知,是“此書字之當刊正者以白字識之;當删削者以圈毀之;當增者,位而入之;當已者,乙而倒之”②[宋]方崧卿:《韓文舉正》,《四庫珍本初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1/2B)。。朱熹在《書〈韓文考異〉 前》一文中對方氏所確定的這四例亦進行了批評,他説:“例多而詞寡,覽者或頗不能曉知。”③[宋]朱熹:《書〈韓文考異〉 前》,《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朱子全書》第24 册,第3682 頁。亦見於《昌黎先生集考異》,《朱子全書》第19 册,第367 頁。《韓文舉正》四例用符號表示分别是:“字(陰文):誤字當删;○:衍字當削;□:脱逸當增;乙:殽次當乙。”然而在具體文本中以文字或符號標識出來,必然會引起混淆錯亂的現象④參劉真倫:《韓愈集宋元傳本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102—105 頁。。朱熹正是在認識到《舉正》存在不足的基礎上,纔確定了自己著《韓文考異》的體例。他在《修韓文舉正例》一文中説:
的同大書本文定本上下文無同者,即衹出一字;有同字者,即並同上一字;疑似多者,即出全句。字有差互,即注云:“某本作某,某本作某”,二字及全句下即注首加本字,後仿此。“今按云云,當從某本。”本同者即前云‘某某本’,後云“某等本”,後仿此。字有多少,即注云“某本有,某本無”。字有顛倒,即注云“某某字某本作某某”,“今按”以下並同⑤[宋]朱熹:《修韓文舉正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朱子全書》第24 册,第3581—3582 頁。。
朱熹詳細地説明了《韓文考異》的體例。即在認為《舉正》存在“例多而詞寡”的不足時,精簡了這四種體例符號,並用相應的文字進行説明。另外,朱熹在《與方伯謨》文中也進一步對注釋異文的體例如何用文字進行描述做了説明。他説:
《韓文考異》大字以國子監版本為主,而注其同異,如云“某本某作某”。辨其是非,如云“今按云云”。斷其取捨,從監本者已定,則云“某本非是”;諸别本各異,則云“皆非是”。未定,則各加“疑”字。别本者已定則云“定當從某本”,未定,則云“且當從某本”。或監本、别本皆可疑,則云“當闕”或云“未詳”。其不足辨者略注而已,不必辨而斷也①[宋]朱熹:《與方伯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四,《朱子全書》第22 册,第2020 頁。。
朱熹亦確定了注釋異文與校勘時的體例,即用“某本某作某”的方法注釋不同版本的“同異”,並對於這些文字的是非,用“今按云云”進行説明。對於他本所載有異文且能確定異文有誤者,則用“某本非是”説明;對於諸别本各異,則云“皆非是”;對有疑問處則以“疑”字標出。朱熹認為他的這一做法有效地避免了方崧卿校勘體例中不注各本異同而産生的問題,並説“ 《考異》須如此方有條理”。
二、“悉考衆本之同異”
在朱熹所著《韓文考異》中,朱熹徵引衆多版本來校勘韓文。莫礪鋒認為:“朱熹校勘韓文時所掌握的本子雖然僅僅稍多於方氏,但是由於方崧卿盲目信從閣本等少數幾種本子,又片面地認為古本、石本一定可靠,所以方氏的校勘成績遠遠不如朱熹,衹有《韓文考異》纔真正做到了博採衆本之長。”②莫礪鋒:《朱熹文學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08 頁。對此亦有學者認為:“前人常常推崇《韓文考異》旁稽博證,而事實上《考異》文字校理的文獻來源大多是第二手資料。”③劉真倫:《朱熹韓集校理文獻來源考實(一)》,《天中學刊》2005年第1 期。這是很有道理的。雖然朱熹在材料的引用上不如方崧卿,但《韓文考異》之所以能在學術界産生如此大的影響,亦有其原因。據《韓文考異序》載:
南安《韓文》出莆田方氏,近世號為佳本。予讀之信然,然猶恨其不盡載諸本同異,而多折衷於三本也。原三本之見信,杭、蜀以舊,閣以官,其信之也則宜。然如歐陽公之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識誤,多為校讎者妄改。亦謂如《羅池碑》改“步”為“涉”,《田氏廟》改“天明”為“王明”之類耳。觀其自言,為兒童時得蜀本《韓文》於隨州李氏,計其歲月當在天禧中年,且其書已故弊脱略,則其摹印之日,與祥符杭本蓋未知其孰先孰後,而嘉祐蜀本又其子孫明矣。然而猶曰“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則固本未嘗必以舊本為是而悉從之也。至於秘閣官書,則亦民間所獻,掌故令史所抄,而一時館職所校耳。其所傳者,豈真作者之手稿,而是正之者,豈盡劉嚮、揚雄之倫哉? 讀者正當擇其文理意義之善者而從之,不當但以地望形勢為重輕也①[宋]朱熹:《韓文考異序》,《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朱子全書》第24 册,第3681 頁。亦見於《韓文考異》,《朱子全書》第19 册,第365—366 頁。。
在朱熹看來,從時間上來説杭本、蜀本因是舊本,距離原作時間較近,流傳的環節相對較少,從而可以避免在傳播中産生一些新的錯誤,因而有可能優於後世校本。但正如歐陽修所説,由於存在校讎者妄改《韓文》的情況,所以“ 《韓文》印本,初未必識誤”。閣本由於出自官方,有一定的可信性,但是閣本底本源於民間,並經過館閣之臣抄録過,因此方氏手中所得之閣本或不是作者所作之手稿。這裏朱熹對於方氏所信任之杭本、蜀本、閣本一一進行了辯駁,並舉出了不可偏信之例證。正是在杭本、蜀本、閣本存在不足的前提下,朱熹纔確定了自己選取版本、材料和校勘的原則。那就是“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不偏信古本。對於方崧卿以杭本、蜀本、閣本為尊的情況,朱熹在《韓文考異》一書中,亦多次指出其不足。他説:
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刊方氏校定本號為精善,别有《舉正》十卷,論其所以去取之意,又他本之所無也。然其去取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館閣本為定。而尤尊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他本雖善,亦棄不録。至於《舉正》,則又例多而辭寡,覽者或頗不能曉知。故今輒因其書更為校定。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他書之可驗者決之。苟是矣,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其所以然者,以為《考異》十卷,庶幾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而筆削焉②[宋]朱熹《書〈韓文考異〉 前》,《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朱子全書》第24 册,第3682 頁,亦見於《昌黎先生集考異》,《朱子全書》第19 册,第367 頁。。
朱熹作《韓文考異》時是針對方崧卿《舉正》所存在的問題而確定了自己的校勘體例、方法與原則。方氏之不足主要表現在,就校勘的底本而言,方崧卿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館閣本為主要的參校本,甚至偏信這三個版本,因而在文字的校勘之中出現了這三個版本即使存在謬誤也往往曲從,其他版本雖善,亦棄之不録的毛病。對此朱熹則確定了“悉考衆本之同異”的方法,既不偏信閣本、古本、石本等方氏認為好的可靠的版本,同時也不忽視民間所發現的版本,而是在廣泛收録各種版本的基礎上,對各本所載之不同進行詳細認真的考證。
三、“以文勢義理”校勘韓文
《韓文考異》不僅是校勘學上的典範之作,也是“朱熹平生文學活動中極為重要的一項工作,他不但值得後代的校勘工作者進行藉鑒,而且應在文學批評史上佔有一席之地”①莫礪鋒:《朱熹文學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36 頁。。其實在《韓文考異》中,朱熹將自己的校勘學思想與文學思想很好地結合在了一起,這也是《韓文考異》所具有的獨特學術價值。正如朱熹自己所説:“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他書之可驗者決之。”這裏考衆本之同異,即是校勘學的方法,而最終判定異文,則是以“文勢、義理”這一文學的方法來實現。對於朱熹在校勘中用文勢義理的方法,有學者認為:“朱熹批評《舉正》的理由是‘泥於古本,牽於旁證,而不尋其文理’。而朱熹所謂‘文理’ 是屬於詩歌藝術表現、修辭技巧。以有無‘神采’、‘意象’ 為判斷異文正誤的準則,其實是校勘變成鑒賞,不合校勘原則的。”②倪其心:《校勘學大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40 頁。當然僅從文字校勘本身來説,這一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方氏採用的是本校的方法,這一方法在保存文本真實面貌上有其重要的價值與作用。而朱熹運用文勢、義理等文學的方法來對韓文文字進行改動的做法,甚至是不足取的,但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韓文考異》在文學史上所具有的意義。
通過統計,朱熹在《韓文考異》中明確標明用“文理”來校勘的有42 處之多③注吴長庚統計為“約十四五見”。見吴長庚:《朱熹文學思想論》,合肥:黄山書社,1994年,第209 頁。,文理不僅僅運用於韓詩的校勘中,更多的是運用於韓文的校勘。朱熹這裏所説的文理並不僅僅衹屬於詩歌藝術表現、修辭技巧,它還應該包括文章。此外,朱熹在校勘中,不僅運用了“文理”,還運用“文勢”“語勢”等方法來校定韓文。我們將對此一一進行討論,試圖探討朱熹以文學方法來校勘的基本情況。
(一) 文勢與校勘
“文勢”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劉勰認為:“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勢者,乘利而為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④[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529—530 頁。這裏劉勰認為,勢是根據情感,選取體制後形成的。即:“根據不同的思想情感内容表達的需要,選定合適的體制和相應的風格。”①吴長庚:《朱熹文學思想論》,第212 頁。朱熹在校勘中多衹言文勢,而不言何為文勢。雖然朱熹對文勢一詞没有給出明確的定義,如《守戒》“為有”下,朱熹按:“今詳文勢,疑為字衍。”②[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卷四,《朱子全書》第19 册,第457 頁。《守戒》“莫大於不足為”下,朱熹按:“今詳文勢,疑足字衍,下句不足為者仿此。”③同上。《與崔群》“百千輩”下,朱熹按:“諸本及詳文勢皆當有此三字,但不知指何人而言耳。”④[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卷五,《朱子全書》第19 册,第488 頁。等等,但我們可以通過這些具體的實例,去探討朱熹所説“文勢”的含義。
吴長庚認為朱熹的文勢論,指的是“所校原稿内容之形式諸方面,是文間語意脈絡發展的邏輯趨勢。它與作者的創作個性,表現手法,修辭技巧密切相關,在文章中,則體現為結構形式,藝術風格等等,是文章學研究的範圍”⑤吴長庚:《朱熹文學思想論》,第208 頁。。通過統計,我們可以發現《韓文考異》一書中,“文勢”一詞共出現14 次。朱熹不僅將“文勢”運用於文章的校勘中,也將“文勢”用於詩歌的校勘中。因此,朱熹這裏所説的“文勢”不僅是文章學的研究範圍,亦是詩歌研究中的一個内容。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層面的含義。
第一,文勢指的是在上下文的聯繫中所體現出的一種語意的連貫與發展的邏輯。朱熹在校勘韓文中就多次將文勢放在上下文的聯繫中來進行討論。如在《復志賦》:“誰無施而有獲”下,朱熹説:“今按:此名本用《楚辭》‘孰無施而有報,孰不殖而有獲’ 之語,詞意既有自來,又與上下文勢相應,故嘉祐杭本與諸本多如此,乃是韓公本文相傳已久,非陳以意定也。閣本之謬如此,而方信之,反以善本為誤,今不得而不辯也。”⑥[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卷一,《朱子全書》第19 册,第370 頁。又如《論淮西事宜狀》“據行”下:“或無行字。今按上下文勢,合有行字,行下更合有營字,其理甚明,今輒補足。”⑦[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卷九,《朱子全書》第19 册,第585 頁。又如,朱熹在對《鄆州溪堂詩》“四鄰望之”句進行校理時説:“閣、杭、蜀及諸本中居之下皆有此四字,方從古本删去。今按文勢及當時事實,皆當有此句。若其無之,則下文所謂恃以無恐者,為誰恃之邪? 大凡為人作文,而身或在遠,無由親視摹刻,既有脱誤,又以毀之重勞,遂不能改。若此者蓋親見之,亦非獨古為然也。方氏最信閣、杭、蜀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今此三本幸皆不誤,而反為石本脱句所奪,甚可笑也。”⑧[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卷五,《朱子全書》第19 册,第470 頁。這裏朱熹根據“下文所謂恃以無恐者”,而認為應有“四鄰望之”四字,此乃根據上下文文勢的聯繫進行校勘的又一實例。可見,文勢是一種在上下文的聯繫中所形成的語意發展的内在邏輯性。這種内在的邏輯性,即上下文的語意與所抒發的情感連貫性。正如朱熹在校勘《南山詩》中“衆皺”一詞時所説:
朱熹在這裏對“衆皺”一詞進行校勘時,就運用了文勢的方法。朱熹是從文章上下文的聯繫中來校勘的,他這裏所説的“況此句衆皺為下文諸或之綱領,而諸或乃衆皺之條目,共語意接連,文勢開闔,有不可以毫厘差者”,指的是“衆皺”一詞屬於文章的綱領,對以下文章的寫作起到了一個提綱挈領的作用,衹有校定成“衆皺”,《南山詩》之語意纔會接連,形成開闔的文勢。也就是“衆皺”是總起下文的,與下文對於各種皺樣景物的描寫形成總分的關係。另外,朱熹在與門人的交流中,也提到了“文勢”對理解《論語》的作用。據《朱子語類》載:
問:“為人謀有二意:一是為人謀那事;一是這件事為己謀則如此,為人謀則如彼。”曰:“衹是一個為人謀,那裏有兩個? 文勢衹説為人謀,何須更將為己來合插此項看。為人謀不忠,如何便有罪過?……②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二十一,《朱子全書》第14 册,第720—721 頁。
朱熹運用文勢的方法對門人錯誤地理解《論語·學而》“為人謀而不忠乎”③[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學而》,第2457 頁。進行了辨析。根據《學而》的文勢來看,此句“衹説為人謀”,而門人卻“拗轉枝蔓”,不遵文勢,將其理解為“為己謀”,這顯然就是不恰當的。因此,朱熹要求人們在讀《論語》時,應該從“文章語意脈絡運行的主體趨嚮”④吴長庚:《朱熹文學思想論》,第214 頁。來理解文義,從而纔能“自然通透”,玩味出聖人意思。又如:
但就本文看,説“命矣夫”較深。聖人本意衹是惜其死,嘆之曰命也,若曰無可奈何而安之命爾。方將問人之疾,情意悽愴,何暇問其盡道與否也? 況下文以為“斯人”“有斯疾”則以為不當有此疾也。豈有上文稱其盡道而死,下文復嘆其不當疾而疾? 文勢亦不相聯屬①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三十一,《朱子全書》第15 册,第1124 頁。。
朱熹根據文勢是否相聯屬對《後牛有疾章》進行了解讀。作者在上文中説了“盡道而死”,而在下文中再次感嘆“人之疾”,顯然就文章語意連貫上來説,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朱熹這裏所説的文勢指的是相聯屬對,是上下文的聯繫中所形成的一種語意發展的内在邏輯性,是“文章語意脈絡運行的主體趨嚮”②吴長庚:《朱熹文學思想論》,第214 頁。。
第二,文勢亦指文章語言結構所體現出的“緩急”“抑揚”之勢。根據朱熹在《韓文考異》中對文勢的運用,我們可以進一步明確文勢也指文章結構所體現出來的氣勢。正如劉勰在《文心雕龍·定勢》中所説:
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為乏,辭反正為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③[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531 頁。。
劉勰指出,辭人的創作可以通過“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等“訛勢”手段達到“反正為奇”的效果。雖然劉勰對辭人好奇的創作傾嚮進行了批評,但是他卻揭示出了文勢論的另一個内涵,即文章結構。朱熹在這一理論的影響下,對韓文進行了校勘。如對《送區册》一文中對“陶然以樂”的校理時,朱熹説:
方無以字。今按:欣然喜、陶然樂,當為一例,故諸本皆有以字,而方本皆無。然竊詳其文勢之緩急,恐上句應無而下句應有也,故定從此本云④[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卷六,《朱子全書》第19 册,第509 頁。。
方崧卿認為此句無“以”字,為“陶然樂”。朱熹根據此文文勢的緩急將該句校勘為:“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説,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這裏的“急”,相對於“欣然以喜”而言,“欣然喜”由於少了虚詞“以”,從而讓語勢變得相對急促,這更有利於突出在聞仁義之説後的欣喜;“緩”指的“陶然樂”而言,“陶然以樂”由於多了虚詞“以”,語勢從而變得緩慢,這樣更有利於突出投竿垂釣時悠然自樂的心境。同樣,通過對於語言結構的變化與用詞的選擇,亦可以體現出“文勢抑揚”①[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卷九,《朱子全書》第19 册,第593 頁。。如在《論變鹽法事宜狀》“之時糴鹽”下,朱熹認為:“糴上,或有來字。今按文勢,恐來字上更有從字,今亦補足。”②同上,第586 頁。從以上例子中,我們可以發現朱熹特别注意虚詞對於文勢緩急快慢的影響。
不僅如此,朱熹同樣認識到了實詞在韓文校理中的作用。如對《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事備”一句的校勘,朱熹説:“備下,或有悉字,或有複出事字。今按文勢,疑當有悉字在備字上。”③[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卷八,《朱子全書》第19 册,第565 頁。在這裏朱熹根據文勢的特點,認為此處“疑當有悉字在備字上”,就是其重視實詞在校勘中作用的體現。又如,在《論淮西事宜狀》一文中對“據行”一句的校勘,他説:“或無行字。今按上下文勢,合有行字,行下更合有營字,其理甚明,今輒補足。”④[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卷九,《朱子全書》第19 册,第585 頁。這裏朱熹根據上下文語意的連貫與邏輯,從下文“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一句,認為原文應該是“據行營所追人額”。可見,這是朱熹運用文勢的理論來校勘實詞的一個例證。
綜上所述,朱熹用於校勘韓文的文勢,不僅是指在上下文的聯繫中所形成的一種語意發展的内在邏輯性,也是文章語言結構所體現出的“緩急”“抑揚”之勢。朱熹充分運用了文勢的這些特點來對韓文進行校勘,體現了朱熹將文學方法運用在校勘之中的特點,這是其區别於方崧卿校勘的一個典型性特點。
(二) 語勢與校勘
朱熹在《韓文考異》中亦運用語勢來校勘。語勢一詞,在《韓文考異》中共出現13次,與文勢一樣,朱熹並没有在《韓文考異》中對語勢一詞進行詳細解釋,但是我們可以從具體的實例中去探討朱熹校勘中所用語勢的大致含義。
首先,語勢“指一定文章體裁所要求的”“文章體裁與語言文字之勢的關係”,因此“不同的文學作品體制,在語言文字的長短、聲律的安排、排行的樣式等上起碼的規定,這就構成了不同的語體。這種不同的語體實際上因長短、對偶、聲律等不同,自然而然地會形成不同的語勢”①童慶炳:《〈文心雕龍〉 “循體成勢”説》,《文化與詩學》2008年第1 期。。這一點,可以從朱熹校勘韓文時,針對不同文體用語勢進行校勘的實例來説明。在對古文《原性》的校勘中,朱熹就運用了語勢。如對“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的校勘,朱熹説:
與,諸本多做歟,善惡下又有歟字。今按:二與字,皆當讀如字而為句首,猶言及也。作歟而為句絶者皆非。《左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語勢亦相似②[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卷四,《朱子全書》第19 册,第451 頁。。
這裏朱熹認為將“與”作“歟”的做法是不正確的,並舉同為散文的《左傳》中的實例“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來證明,其原因在於同為散文的這兩句語勢是相似的。同樣,在對詩歌《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的“日薄”下,亦運用語勢來進行校勘,他説:
薄,或作落。方云:薄,迫也。《國語》:“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今詳語勢,但如白樂天所謂“旌旗無光日色薄”耳,方説非是③[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卷三《朱子全書》第19 册,第419 頁。。
在這裏方崧卿認為:“薄,迫也。”並引用《國語》“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進行了説明。雖然方説有理有據,但《國語》乃史書,使用的是散文的語言,因此,朱熹從詩歌的語勢出發來討論,認為方説不可取,並舉白居易詩句“旌旗無光日色薄”來進行説明。顯然這裏方、朱二人都是引用他書來校勘,從引用的材料來看,朱説引詩歌來證詩歌更具説服力。這裏要指出的是,朱熹總共在三首詩歌中用語勢四次,分别是《北極》《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驛途中見寄》《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就詩歌體制來看,這三首詩歌分别收入《韓集》第二卷、第四卷、第七卷,屬於古詩。朱熹在對這三首詩用語勢進行校勘時,則指出不必要拘泥於“古韻”“古人語”。這似乎與古詩所要求的體制有所衝突,其實不然,這又涉及了語勢的另一個層面的意思。
其次,語勢還包括“個人的語體之語勢,作家在創作中發揮自己的創作個性而形成的不同的語體之語勢”④童慶炳:《〈文心雕龍〉 “循體成勢”説》,《文化與詩學》2008年第1 期。。這也就是説雖然每種文體都有自己固定的語勢,但是由於作為創作主體的個體具有差異性,因此在具體的創作中作品亦體現了作者自己的個性,從而形成不同的語體之語勢。朱熹在校勘韓文中就充分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將文體所固有的語勢與韓愈之個人語勢相結合來校理韓文。如對古詩的校勘,在《北極》詩“平茫茫”“風狂”下就運用了“古韻”,他説:
平茫茫
方作茫茫平,云用古韻。今按:此詩固用古韻,然皆因其語勢之自然,未嘗作意捨此而用彼也。諸本衹作陂澤平茫茫,韻諧語協,本無不可,若作陂澤茫茫平,卻覺不響,不應以欲用古韻之故牽挽而强就之也。又按:别本平或作路,而或作何者,語意尤勝,讀者詳之①[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卷一,《朱子全書》第19 册,第380 頁。。
風狂
方作狂風。今按:方亦强用古韻之過,不如衹作風狂,語勢尤健②同上。。
這裏我們可以發現,朱熹認識到了《北極》詩“諸本衹作陂澤平茫茫,韻諧語協,本無不可”的文章體裁所要求的語勢。同樣,他認為“若作陂澤茫茫平,卻覺不響”則不合韓愈個人之語勢。因此,《北極》詩“固用古韻”,但是我們“不應以欲用古韻之故牽挽而强就之也”,在考慮文章語勢時,也要尊重韓愈個人“語勢之自然”的特點。同樣,朱熹認為方崧卿在對“風狂”進行校勘時,也因强用古韻而導致失誤,朱熹認為“作風狂,語勢尤健”亦應從韓愈個體語勢出發來進行校勘。這一點在朱熹校勘《柳州羅池廟》“秋鶴與飛”一句時就有體現。
或作秋與鶴飛。今按:歐公以此句為石本之誤,沈存中云:非也,倒用鶴與兩字,則語勢愈健,如《楚辭》云“吉日辰良”也。但此石本團團字,初誤刻作團圓,後鐫改之,今尚可見,則亦石本不能無誤之一證也③[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卷八,《朱子全書》第19 册,第559 頁。。
這裏朱熹校勘的依據就在於“倒用鶴與兩字,則語勢愈健”,這不僅在《楚辭》中有文獻依據,也與韓愈的文章特點相符。對於這一看法,朱熹在《楚辭集注·東皇太一》“吉日兮良辰”下引洪興祖《補注》進行了更加詳細的説明:“沈括存中云:‘吉日兮辰良’ 蓋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韓退之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 用此體也。”①[宋]朱熹:《楚辭集注》卷二,《朱子全書》第19 册,第47 頁。可知,朱熹認為倒用鶴與二字相錯成文的做法,讓語勢更加矯健。
綜上,我們可以知道,朱熹所説的語勢是文學作品本身的語言文字特點所決定,不同的文體有不同的語勢,由於作家的個體差異性,對於同一文體的創作也會呈現出不同的語勢。朱熹在校勘韓文中,不僅注意到了古文與詩歌所具有的不同的語勢特點,而且將其運用到不同文體的校勘中。不僅如此,朱熹亦從韓愈的個性特點出發,注意到了韓愈語勢的“自然”與“健”,進而在校勘時注意到了韓詩所具有的不同的語勢,將文體所固有的語勢與韓愈之個人語勢相結合來校理韓文,這體現了朱熹校勘韓文的特點。
(三) 義理、文理與校勘
朱熹在校勘時還用到了“義理”,他説:“而一以文勢義理及它書可驗者決之。”②[宋]朱熹:《書〈韓文考異〉 前》,《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朱子全書》第24 册,第3682 頁。可見,校勘時“義理”與“文勢”一樣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朱熹在《韓文考異》一書中“義理”一詞僅出現了兩次。一次是在《月蝕詩效玉川子作》“森森萬木夜僵立”一句的注解中,朱熹説:“森森,方作臨臨,殊無義理。”③[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卷二,《朱子全書》第19 册,第408 頁。一次是在《與孟尚書》中所説的:“異端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自勝。”④[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卷五,《朱子全書》第19 册,第494 頁。顯然,《與孟尚書》中所出現的“義理”與校勘韓文無關。因此,“義理”一詞在《韓文考異》校勘中僅出現了一次。從僅有的一次中,我們可以發現,朱熹所説的“義理”指的是文章内容的合理性,吴長庚認為是“内容發展的必然之理”⑤吴長庚:《朱熹文學思想論》,第207 頁。。一般來説,校勘考察的往往是文字的正誤,而文字又是構成語意的基本組成部分。因此,朱熹在這裏所説的文章義理,也就是文章的語意與内容。顯然,這在校勘中不可或缺。其實,朱熹在校勘時,往往用“文理”這一與“義理”同意的詞語來代替,它們都指文章内容。
朱熹在《韓文考異》中運用文理來校勘達42 處之多,文理不僅僅運用於韓詩校勘,亦運用於韓文校勘。朱熹這裏所説的文理指的是文章的内容,也就是所校文本的思想内容發展的必然之理。因此,朱熹在用文理對異文校勘時,是從内容發展的連貫性與語意發展的趨勢來判斷的。如對《古意》詩“青壁無路難夤緣”的校勘,據《韓文考異》載:
方從唐本作五月壁路難攀緣,云:《鮑溶集》有陪公登華山詩,蓋五月也。夤,或作攀。今按:公此詩本以古意名篇,非登山紀事之詩也。且泰華之險,千古屹立,所謂削成五千仞者,豈獨五月然後難攀緣哉? 若以句法言之,則五月壁路之與青壁無路,意象工拙又大不侔,亦不待識者而知其得失矣。方氏泥於古本,牽於旁證,而不尋其文理,乃去此而取彼,共亦誤矣。原其所以,蓋緣五月本是青字,唐本誤分為二,而讀者不曉,因復削去無字,遂成此謬,今以諸本為正①[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卷一,《朱子全書》第19 册,第389 頁。。
這裏方崧卿根據《鮑溶集》所載陪韓愈登華山詩認為《古意》一詩作於五月,朱熹則從此詩題為《古意》出發,認為是以古意名篇,並不是登山紀事之詩,方氏拘泥於唐本,牽於《鮑溶集》中所載之旁證,而不從《古意》一詩所要表達的文理出發,即不從詩中所描寫的内容與要表達的情感出發,進而導致錯誤。另外,朱熹在這裏亦從“句法”的角度來進一步做了説明,認為“青壁無路”意象更工。
朱熹用文理來校勘,在韓文中更加普遍,有36 處之多。如在《伯夷頌》中,“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萬年一人而已耳”句下載:
方從杭、《粹》及范文正公寫本,無力行二字,千下有五字,云:自周初至唐貞元末幾二千年,公言千五百年,舉其成也。今按:此篇自一家一國以至舉世非之而不惑者,泛説有此三等人,而伯夷之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又别是上一等人,不可以此三者論也。前三等人皆非有所指名,故舉世非之而不顧者,亦難以年數之實論其有無,而且以千百年言之,蓋其大約如此耳。今方氏以伯夷當之,已失全篇之大指,至於計其年數,則又捨其幾二千年全數之多,而反促就千五百年奇數之少,其誤益甚矣。方説不通文理大率類此,不可以不辨②[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卷四,《朱子全書》第19 册,第460—461 頁。。
這裏朱熹認為方崧卿之所以校勘有誤在於不通《伯夷頌》之文理。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以伯夷當千百萬之人;一是不應該用年數之實來討論,時間衹是取其大約之數而已。鑒於此,朱熹從《伯夷頌》的具體内容出發,取幾近二千年之全數定為“千百萬年一人而已耳”。又如,對《送孟東野》一文中“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的校勘,朱熹先後兩次用到文理。對於“又其精也”,方從“閣、杭、蜀本,去又字,而取下句尤字足成一句”定為“尤其精也”。朱熹認為這是“不成文理”的③[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卷六,《朱子全書》第19 册,第499 頁。。他在“尤擇”條下對此進行了詳細説明。他説:
上文已再言“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矣”,則此又言人聲之精者為言,而文詞又其精者,故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是關鍵血脈首尾相應處。方以三本之誤,遂去又字,而以尤字屬上句,不唯此句不成文理,又使此篇語無次第,其誤尤甚,今悉正之①[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卷六,《朱子全書》第19 册,第499 頁。。
在這裏“又”“尤”二字,朱熹認為是關鍵,這是因為上文已經説了“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矣”,接下來又要説“人聲之精者為言”,下句有“尤”字不僅能避免與前文的重複,亦表遞進關係,更加突出善假之鳴的重要性,這樣文章血脈首尾相應,文章所要表達的思想内容也更加符合文理。
綜上所述,朱熹在對韓文校勘時不僅確立了體例,並多採衆本之同異,運用了文勢、語勢、文理等方法來校勘韓文。這體現了朱熹韓文校勘“義理、文章、考據相容並包”②錢穆:《朱子新學案》,第1775 頁。的特點。客觀來説,雖然朱熹建立了一套自己校勘韓文的方法,但從校勘學的角度來看,朱熹對於方氏的批評確實存在不確的地方,並且“朱熹所謂‘文理’ 是屬於詩歌藝術表現、修辭技巧。以有無‘神采’ ‘意象’ 為判斷異文正誤的準則,其實是校勘變成鑒賞,不合校勘原則的”③倪其心:《校勘學大綱》,第40 頁。。但正如朱熹所説:“大氐今人於公之文,知其力去陳言之為工,而不知其文從字順之為貴,故其好怪失常,類多如此。”④[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卷一,《朱子全書》第19 册,第376 頁。朱熹不僅僅强調“韓詩平易”與“文從字順”的一面,也注意到了“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⑤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一三九,《朱子全書》第18 册,第4295 頁。,這對於全面認識韓文的藝術特點是多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