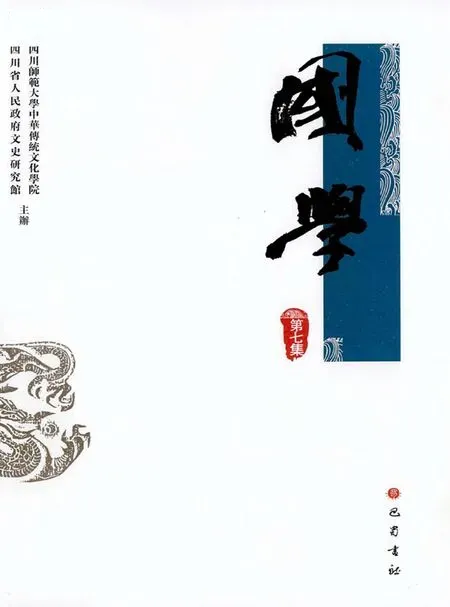關於陶淵明的組詩《飲酒》
2019-12-13顧農
顧 農
《飲酒》二十首是陶淵明(365—427) 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其詩前有小序云:
余闻居寡歡,兼秋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娱,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
可知這一批總題為《飲酒》的詩並非精心結撰的組詩,而是在擁有“名酒”的某一年秋天,偶然陸續隨意寫出的,後來由他的朋友抄寫編次為一組,略加編輯而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當年編就並由故人書之的這一組詩,本來大約到不了二十首,後來在陶集流傳過程中被加進了若干,纔形成我們現在看到的情形。選本和類書中的某些資訊證明了這一點:《文選》(卷三十) 録入今本《飲酒》中的詩二首(其五,其七),而題作《雜詩》;《藝文類聚》(卷六十五“園”部) 節選了這兩首,也題作《雜詩》。但該書(卷七十二“酒”部) 又録入《飲酒》中的另一首:“有客常同止,趣舍邈異景。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此詩在今本陶集中列為《飲酒》詩其十三,《藝文類聚》節選了其中六句,仍然題作《飲酒》,而且還引用了幾句詩序:“既醉之後,輒以數句自娱。紙墨遂多,别辭無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談笑也。”(詩序的文字與今本稍異,可為校勘之資)。這一首應在《飲酒》原編本之内。
可見在較早的抄本陶集中,雖然確有一組帶序的《飲酒》詩,但可以肯定其總數不到二十首;换言之,現在的《飲酒》詩二十首中某些篇章原來不在這一組中,而另題為《雜詩》或别的什麽題目,衹是因為其中也寫到了酒,後來就有人也把它們一併收編到《飲酒》這一組裏來了,加起來一共達到二十首。這種增補的操刀者及其動手的時間,現在都無從知道。
關於《飲酒》的寫作時間,因為其十九有“拂衣歸田里”“亭亭復一紀”之句,於是有學者即據以指出這一組詩當作於陶淵明抛棄彭澤令(義熙元年,405) 的一紀(十二年)之後,也就是晉安帝義熙十二、十三年(416—417)①前賢多有持此説者,如湯漢注《陶靖節先生詩》卷三、温汝能《陶詩彙評》卷三、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四等等;時賢亦多有類似之看法者,不具引。。這樣來推算自然是有根據的,還可以為此説補充一個證據,《飲酒》其九寫一“田父”勸陶淵明與體制認同,而詩人回答説“吾駕不可回”——他忽然來談自己的生活方嚮不能改變,應有比較具體的背景,不是一個田父忽然就能提出並直接拉動的。按《宋書·隱逸傳·陶淵明傳》載:“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南史·隱逸傳·陶淵明傳》也有同樣的記載。所以其九這一首應作於義熙十三年丁巳(417),纔是合乎邏輯、可以理解的事情。其九與其十九形成一種互相支持的關係,表明《飲酒》中有一部分作於義熙十二三年(416—417) 間。還有些作品可能寫得更晚,甚至在晉、宋易代之後。這次易代比較自然,陶淵明的心態也相當平静。
但《飲酒》中另外一些作品大約寫得相當早,如其十六,其中提到“行行嚮不惑”,則此詩當作於陶淵明四十歲之前不久,例如三十九歲(亦即晉安帝元興二年癸卯,403年)左右。
《飲酒》組詩中另外較多的篇章則當作於義熙元年(405) 十一月詩人徹底歸隱之後,但大體難以確指其寫作的具體年代。如其四(“棲棲失群鳥”) 一首欣慰於自己明智地退出了官場,也流露了一點孤獨之感,似應作於陶淵明歸隱之初。又如《飲酒》其五中有“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以及“心遠地自偏”等句,當不可能作於他歸隱之初住在“園田居”之時,其時心與地全都偏遠,看其《歸園田居》其一中有“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之句就可以知道。其五這一首應作於義熙四年戊申(408) “園田居”住房毀於一場火災、後遂移居於近郊的南村之後。這時他的住地離城較近,不像過去那樣偏遠,纔會説這樣的話。
總起來看,《飲酒》詩二十首本來就來路不一,寫作時間也前前後後多有差距,但可以説大抵是歸隱之後的作品。
飲酒是陶淵明的最愛。前人説陶淵明詩篇篇有酒,略見誇張,但他喜歡喝酒並一嚮在詩裏大談其酒也確是事實。從酒談起,各種内容都可以掛靠上去。陶淵明有一首《連雨獨飲》,大談他飲酒之心得,談得最為集中而且透徹: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間? 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自我抱兹獨,僶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
陶淵明曾經寫過一篇《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其中説起他本人的外祖父孟嘉同桓温的一番對話:
(桓) 温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耳。”
孟嘉實際上是笑而未答。飲酒之趣這個問題,現在由《連雨獨飲》一詩來具體回答。
陶淵明説,有一種意見(以贈酒給陶淵明的故老為代表) 説飲酒可以成仙。陶淵明認為這不可能,人總是要死的,從古到今没有例外(“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赤松子、王子喬一類仙人,不過説説而已。喝酒喝醉了,可以暫時同平時的自我告别,抛棄舊有的感情(“試酌百情遠”),忘記身外的一切(“重觴忽忘天”)。儘管那一切仍然存在,客觀世界没有變化(“天豈去此哉”),但暫時的告别仍然是有意義的——這時可以神遊八極,無遠弗届(“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使自己得以擺脱肉體的束縛,而僅僅留下自由的心靈(“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這樣的自由多麽可貴!
陶淵明像他的外祖父孟嘉一樣,頗得酒中之趣。飲酒不能成仙,也不能改變客觀狀況,衹是藉此獲得陶醉,讓身心暫得休息,進入自由王國。這個看法放之古今而皆準。
在那些陰雨連綿下個不停的沉悶日子裏,陶淵明獨自飲酒,思考人之自由的問題,寫下這首詩,為他的外祖父孟嘉補交了一份具體的答卷。看來詩人並没有真醉。明朝人黄文焕引述沃儀中評論此詩的高見道:“他作談生死,猶是彭殤齊化之達觀,獨此云忘天任真,形化心在,誠有不隨生存、不隨死亡者。一生本領,逗洩殆盡。”(《陶詩析義》卷二) 這首詩不是運用莊子的相對主義去齊一生死,而是拿一種暫時自由的心靈去對抗以至於化解實際生活中的人生無奈——這確實是陶淵明的一大本領,反映出他的人生哲學,也是他的詩一嚮頗得人心之所在。這一首《連雨獨飲》如果早先被編進《飲酒》組詩裏去,這一組詩就變成二十一首,要再多幾首也不是什麽難事。
讀《飲酒》二十首最宜採取通達的態度,不必認定某一年作,或以為衹談某一具體主題。這裏總的話題是人生哲學,而其中涉及許多方面。
以下分别簡述之。
其 一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兹。
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此首雖然列為《飲酒》二十首的第一首,但並非序詩。這些詩的順序本來就是非常隨意的,“辭無詮次”,没有什麽邏輯上或情緒上的前後。前人或以為這第一首是“二十首總冒”(吴瞻泰《陶詩彙注》卷三引汪洪度語);又有人認為這一組詩有“大章法”,“藏詮次於若無詮次之中”(黄文焕《陶詩析義》卷三),皆求之過深,牽强無據,也講不清楚。
此詩中用了秦漢之際前東陵侯邵生種瓜的典故①《史記·蕭相國世家》:“召(邵) 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表明富貴榮華不可能長期保持,且很容易發生變化,在東晉末期至劉宋初年這樣動亂的時代就更是如此。“彼此共更之”乃是人間的規律(“人道”),對此能够充分認識的纔是“達人”。人生的意義即在於順應世事的變化——那麽不如還是來喝酒吧。
其實認識人世的規律同飲酒之間並没有什麽必然的聯繫,但喜歡飲酒的人可以隨便找到一個什麽理由,世事無常自然是一個方便的理由,用這個題目喝酒可以提升其意義,顯得很有必要的樣子。這正如老烟槍之大抽其烟,可以説藉此休息,又可以説幫助動腦筋,既可以抽支烟涼快涼快,也可以抽支烟暖和暖和。嗜好在任何情況下總不缺少它充足的理由。
其 二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 九十行帶索,饑寒況當年。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飲酒》其二這一首批評因果報應論。像伯夷叔齊這樣的了不起的好人,卻没有什麽好報,最後竟然餓死。“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原是中國傳統思想中固有的觀念,後來佛教更大講因果,陶淵明完全不相信這種説教,他説過:“夷投老以長饑,回早夭而又貧。傷請車以備槨,悲茹薇而隕身。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 疑報德之若兹,懼斯言之虚陳。”《感士不遇賦》已經舉伯夷以及短命的颜回為例,這裏又以“夷叔在西山”來證明世界上不存在什麽善有善報。陶淵明相信天命決定論,不贊成因果報應論。
詩的後四句寫榮啓期(其事迹詳見《列子·天瑞》)。其人安貧樂道,是“君子固窮”的典範。可知詩人不相信因果報應之論,而仍然高度重視為人的操守和境界,這並不是要得善報,而是理應如此。
其 三
道喪嚮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本詩的主旨在於嘆息人生苦短,空名無用,不如飲酒。《列子》裏大講享樂有理,晉朝人多有這種思想。張翰(字季鷹) 早就説過:“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及時一杯酒!”畢卓(字茂世) 説:“一手持蟹鼇,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均見《世説新語·任誕》) 陶淵明也反覆申述虚名之毫無意義,與其追求什麽身後之名,不如生前來痛快地飲酒—— “道喪”容易使人産生諸如此類的想法。
其 四
棲棲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斂翮遥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開頭的“失群鳥”應當是陶淵明的自喻,他在脱離了官僚階層以後衹好“獨飛”,必須找到一個“托身”之所來安身立命。他很榮幸地找到了,這就是歸隱,於是下決心在故鄉的田園裏堅持下去,千載而不相違。
所謂“孤生松”可以是拿局部指稱全體,代指他的鄉間别墅,也就是《歸園田居》五首其一裏提到的那一處住所:“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從“曖曖”兩句看去,這裏離本地老百姓的村莊有相當的距離——這就是所謂“孤松”了。陶淵明在這裏離群索居。《歸去來兮辭》中也曾經提到“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以盤桓”。這裏的“孤松”固然可能是他家庭院中實有的東西,更可能衹是一種象徵,詩人因孤立而感到光榮與高傲。
陶詩中寫到鳥特别是歸鳥這一類意象的句子甚多,還有一首專門的《歸鳥》。《飲酒》其四則一上來就逕寫“棲棲失群鳥”,以表達自己的孤獨寂寞之感。他脱離了官場,脱離了他曾經非常熟悉的上流社會,不免有一種難以擺脱的“失群”之感。面對落差很大的生活方式的轉軌,一時總有一點不大適應,儘管這一斷然的轉軌完全出於他自己的選擇。中國古代的士大夫在本階層的群體裏待慣了,他們所信奉的儒家思想所關注的也完全是如何在體制之内的人際關係網裏安身立命——而這軟硬兩個方面現在在陶淵明的生活中忽然統統失落了,他在心理上難以承受,因此必須在詩文中提出强有力的解説讓自己得到解脱。
有一座别墅,就硬件而言可以説“托身已得所”,更上一層則還要有合適的軟環境,做到“托心”亦復“得所”。《歸去來兮辭》寫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絶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 悦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造成自己“失群”狀態的責任並不在自己而在“世”,是“世與我而相違”。於是他衹好轉而在親情中找慰藉,在琴書中找寄托。
前人或將此詩與晉宋易代聯繫起來考慮,其實此時離易代尚遠。政治上失意或絶望之後轉而從親情中尋找安慰和寄托,乃是古代文人的慣例。例如率先模仿陶淵明的劉宋詩人鮑照有句云:“棄置罷官去,還家自休息。朝出與親辭,暮還在親側。弄兒床前戲,看婦機中織。自古聖賢皆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擬行路難》其六) 鮑照此詩即與改朝换代完全無關①參見顧農:《鮑照美文 殊以動俗》,《中華讀書報》2017年1月4日第15 版《國學》。。
離群索居到底是痛苦的,於是陶淵明便入鄉隨俗地多與農民交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歸園田居》其二),但他始終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融入農民的群體之中,歸隱之初他把自家的住處安排在遠離村莊的地方就是一個明顯的標志;他後來主要與一批農村知識分子、地方官員交往,“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移居》其二),在一起喝酒談天以消除寂寞。當然,陶淵明同那些遁入深山老林的老派隱士不同,他具有某種程度的世俗化的品格,因而也就具有某種可推廣性,終於成了“古今隱逸詩人之宗”(《詩品·中》)。
陶淵明歸隱之初的一批詩文乃是為他本人的心理調適而寫的,所以其中有許多對自己行為的解釋和自我安慰。這與他在另外若干作品中流露出來的得以歸隱的欣喜之情正可以互相生發,互為補充。
其 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這首《飲酒》其五是陶淵明最著名的詩篇之一。按説“結廬”當然是“在人境”,這有什麽好説的呢? 但不能忘了在陶淵明之前,許多隱居之士往往躲入深山老林或其他人迹罕至之處,離群索居,以奇特的生活方式表示他們對政治對社會的厭惡和疏離——即使在21世紀的今天,也還有人跑到終南山深處去隱居。
所以隱居也叫“隱遁”——從人間逃亡出去,不理會人間的種種;而陶淵明實行的卻是“歸隱”,退出官場,回到自己的老家,過農村知識分子很普通的生活:讀書、飲酒、訪友、談天,高起興來的時候也幹一點農活,外觀上一點也不像過去的隱士那樣奇奇怪怪的。他仍然在人間,完全過世俗的生活,卻已經獲得老派隱士們代價甚高的自由。“結廬在人境”相當於宣佈自己是實行一種新型的隱居方式,帶有革易前型的重大意義。
老派隱士之所以要遁入山林,一大原因是要遠離人世的渾濁和喧囂,防止污染,取消麻煩,遺世獨立。現在陶淵明竟然在故鄉就地隱居,用傳統的眼光看起來,“結廬在人境”根本缺少隱居的基礎性條件,人間必有種種世俗的干擾,“車馬喧”就是這種干擾的形象化的説法。“問君何能爾?”詩人要回答這樣的質疑,這樣就有了下面的詩句。
説“心遠”就“地自偏”也大有意味。一般來説“地”偏不偏要看它具體的地理位置,買房子首先要挑地段。但“心”的作用也很大。觀察評估同一個物件,不同的人主觀感受可以很不同。語云“情人眼裏出西施”,而在跟她不相干的人看去,她就未必是絶代佳人,甚至根本算不上漂亮。住處是否偏遠安静,同樣與“心”大有關係。
“心遠”的人心胸開闊,思虑深遠,擁有一種哲理意義上的瀟灑,毫不拘執於眼前的瑣屑。這一點陶淵明没有作正面的解説,衹是用形象的描繪予以暗示:“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人在自家宅院的東籬下採菊,眼卻望着南山,又轉而去看飛鳥,這就是所謂“心遠”了。
“望”字一作“見”,許多陶集本子裏大抵採用“見”字。按“望”與“見”各有其來歷,而一字之差,意味很不同。蘇軾説:“因採菊而見山,境與意會,此句最有妙處。近歲俗本皆作‘望南山’,則此一篇神氣都索然矣。”(《東坡題跋》卷二《題淵明飲酒詩後》) 蘇軾的弟子晁補之説得更為充分:“東坡云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採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既採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藴矣,非淵明意也。‘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採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閑而累遠。此未可於文字精粗間求之。”(《雞肋集》卷三十三《題陶淵明詩後》) 原來他們不是從原作的感情和邏輯出發,而是將這兩句從原詩中割裂出來,用宋代士大夫的閑適情趣加以改塑,自説自話。事實上“望”字在版本上更有根據,蘇軾之所謂“俗本”和今日所能看到的陶集古本善本均作“望”,《文選》亦作“望”(其編者蕭統乃是最早為陶淵明編集子的人)——則自當作“望”;“見”字則出於宋人的妄改,並没有什麽堅强的依據。
採菊與“望南山”之間有着内在的聯繫。晉朝的流行觀念是相信傳服食菊可以延年益壽,陶淵明採菊就是為了服食,他喜歡用菊花泡酒喝。“南山”就是廬山(當時或稱南嶽),也可以指《詩經》裏説過的“如南山之壽”。這裏古典與今典字面上恰好合而為一。
陶淵明遊廬山的次數應當極多,但未見他有專門寫此山勝景的詩篇,而大抵取來作為敘事抒情的背景。深於《易》者不言《易》。
服食菊花是為長壽,但能不能真的令人長壽,陶淵明也不是很計較,他奉行當時“心無”派思想家之所謂“於物上不執心”(元康《肇論疏》)——反正酒是要喝的,於是就大喝其菊花泡酒,能有助於長壽最好,如果效果不明顯或完全無效也没有什麽。所以他“悠然望南山”,態度瀟灑得很。我們現在吃一點滋補品,也不能指望立竿見影就有神效。在争取達到某一目的的時候而能没有志在必得的意思,人的精神就可以放鬆下來了。
“悠然”是一種不大容易達到的境界,須忘懷得失甚至看破人生纔行。馮友蘭先生説過:“若做事常計較個人的利害,計較其事的可能底成敗,即是有所為而為。有所為而為者,於其所為未得到之時,常恐怕其得不到,恐怕是痛苦底。於其所為決定不能得到之時,他感覺失望,失望是痛苦底。於其所為既得到之後,他又常憂慮其失去,憂慮亦是痛苦底。所謂患得患失,正是説這種痛苦。但對於事無所為而為者,則可免去這種痛苦。”①《新世訓》,引自馮友蘭:《三松堂小品》,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317 頁。説的正是這一層意思。
無所為而為乃是所謂“心遠”的一大要領。所以我們現在有時還勸那些急功近利以至於氣急敗壞的朋友“悠着點兒”。一點“悠然”的意思都没有,那就活得很累了。
陶淵明厭倦了官場的折腰應酬,抛棄了青年時代“大濟於蒼生”(《感士不遇賦》) 的書生意氣,毅然歸隱,回歸於自然,回歸於自我,這時他已經把人世參透了,因此縱有車馬喧騰,有種種世俗干擾,他也一概不去理會,衹顧自己採集菊花,享受生活。他有一股很强烈的生命意識和對於自由的嚮往。
詩中最後提到“真意”,但没有明説究竟是什麽意思。從全詩看去,陶淵明固然希望長壽,但並不執著,態度悠然,可知他更看重的乃是自由自在的生存狀態,希望有一個自由而和諧的精神家園把自己安頓下來。於是詩人由望山而及山之氣象,“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大自然生生不息,自有佳趣,飛鳥自由自在,日落歸林,這一極常見的傍晚景象給陶淵明極深的啓示,他由此體認到,這纔是人生理想狀態的象徵,所以接下來説:“此中有真意”,“此中”即指“採菊東籬下”到“飛鳥相與還”這四句所描寫的意象之中,此中藴含的“真意”,包含着對於生命和自由的愛戀與嚮往。
陶淵明逃禄歸耕的原因,舊説一般歸結為政局惡劣,所以他要及早抽身,還有説他痛恨官場,不願為五斗米折腰因此掛冠而去,如此等等。這些都有些道理,但陶淵明最為關心的,其實尤其在於擺脱束縛,回歸自然。《歸去來兮辭》序説起他到彭澤去當縣令,“及少日,眷然有懷歸之情。何則? 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一有“矯厲”即不自由,也就是“違己”,而歸隱的好處即在於恢復本性,自由自在。看清這一點我們纔能理解他在《歸園田居》詩裏何以那樣高興地説起“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其一),以及“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其三) 等等意思。想給豆苗鋤草就去鋤草,衣裳沾濕了也不足惜;想採菊便去東籬下採菊,吃下去能否長壽,也没有什麽大關係。總之陶淵明希望在無拘無束中享受人生,名利等等身外之物皆可忽略不計,物質生活水準如何也不重要,最要緊的是不違背自己的意願,不喪失本性。“使願無違”可以説是陶淵明人生哲學的核心。這些意思詩人都没有直截了當地説出,衹是含糊其詞地説“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有些複雜精微與傳統觀念格格不入的意思,確實不是幾句話就能説明白的,從來言不盡意,全在個人體悟。
其 六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 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 三季多此事,達士似不爾。咄咄俗中惡,且當從黄綺。
這首詩説是非難分,毀譽也就難定,“達士”(亦即其一首詩中説起過的“達人”) 總是超越世俗的是非毀譽,例如秦末漢初的商山四皓就躲進深山,不管世俗的雷同一響。
清人方東樹説此詩要旨在於“言心不遠者,但見是非紛紜而不能已於言”(《昭昧詹言》卷四);而陶淵明卻高出許多,在歸隱生活中自得其樂,不欲與俗人去囉嗦計較。
其 七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陶淵明喜歡喝菊花酒,當時的人們普遍相信服食菊花非常有助於養生長壽。長期大量喝酒對身體顯然没有好處,所以陶淵明也曾考慮過戒酒,還寫過一首題為《止酒》的詩,但他根本没有戒成。在酒中泡進菊花,這酒就是有益無害的了。“酒能祛百慮,菊解制頹齡”(《九日閑居》),喝菊花酒既可以過酒癮又達到了養生長壽的目的,豈非一舉兩得?
中國古人服食菊花起源甚早,《離騷》中已有“夕餐秋菊之落英”之句。晉朝人一般都相信服食菊花有助於保健長壽,例如傅玄在《菊賦》(《全晉文》卷四十五) 中明確指出“服之者長壽,食之者通神”,孫楚在《菊花賦》(《全晉文》卷六十) 中稱讚菊花“超庶類而神奇”,而著名博物學家嵇含在《菊花銘》(《全晉文》卷六十五) 中更説“詵詵仙徒,食其落英。尊親是禦,永祚億齡”。
用菊花泡酒當年似乎頗為流行,潘尼《秋菊賦》(《全晉文》卷九十四) 有句云:“泛流英於清澧,似浮萍之流波”,這正是陶詩之所謂“泛此忘憂物”了。陶淵明的愛菊是最有名的,而在背後起作用的是晉代流行的觀念和常識。
此後食菊花之風歷久不衰,宋人謝翱《楚辭芳草譜》釋菊云:“觀崔實、費長房九日採菊語,則茹菊延齡,自古已然”,可見此風一脈未斷。又宋人范成大《菊譜·序》云:“山林好事者或以菊比君子…… 《神農書》以菊為養性上藥,能輕身延年。南陽人飲其潭水,皆壽百歲……故名勝之士,未有不愛菊者。至陶淵明則尤甚愛之,而菊名益重。”至今人們還在服食菊花,最簡便易行的辦法是用杭菊花泡茶,據説有降火明目等特效。
除了菊花酒以外,陶淵明還神往於上古巫書中説起的“丹木”和“玉膏”。《讀山海經》十三首其四云:“丹木生何許? 乃在密山陽。黄花復朱實,食之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見重我軒黄。”丹木、玉膏均見於《山海經·西山經》,乃是傳説中黄帝軒轅氏享用的東西。據説丹木“員葉而赤莖,黄華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饑”,白玉則是玉膏的凝固狀態,“其原沸沸湯湯,黄帝是食是餉”,“君子服之,以禦不祥”。陶淵明對這一類神仙的專用品也大有興趣,看來他並不滿足於效果未必特别明顯的菊花酒,還有着更高的追求,衹不過就他而言最切實可行的養生之道還衹有喝這種土法自製的菊花酒。
其 八
青松在東園,衆草没奇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提壺掛寒柯,遠望時復為。吾生夢幻間,何事絏塵羈。
“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原是一種常見的情形,而其中確含哲理,是陶淵明率先提出來的,遂成絶妙的警句。先前的玄言詩也大談哲理,但没有幾句給人留下印象,那是因為其中的哲理乃是從書上抄來的,衹見其引用前人,全然没有自己的新發現和新體悟。
卓然的孤松是陶淵明一再寫到的意象,見之於《歸去來兮辭》(“撫孤松以盤桓”) 和《飲酒》其四(“因值孤生松,斂翮遥來歸”)。陶淵明一嚮以此為人生的依托、精神的安慰。在《飲酒》其八這首詩中,他寫自己把酒壺掛在青松的寒枝上,嚮遠處眺望——這樣的畫面似乎可以作為陶淵明的標準像①有關陶淵明的畫像甚多,袁行霈先生在《陶淵明影像——文學史與繪畫史的交叉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一書中有深入的分析,敬請參看。。
“心遠”與飲酒是陶淵明安頓人生的兩手,他這兩手都很硬。
其 九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 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襤縷茅簷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這首詩主要由一番對話構成,用的是樂府詩裏常見的手法。“田父”帶着酒來看望詩人,勸他放棄高隱,依從於體制,也就是重新出來當官。詩人則回答説自己的本性就是不與“一世”認同,不能違背自己的本心,“吾駕不可回”! 我們不談這些,還是來高高興興地喝酒吧。
這樣的場景可能真的發生過,也可能出於詩人的虚擬,而表達的意思都是一樣的,不願意東山再起。
這樣的情形當有一番具體的背景。《宋書·隱逸傳》載:“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義熙是東晉的年號,凡十四年(405—418)。陶淵明是義熙元年(405) 歸隱的,一晃十幾年過去,朝廷竟然想起陶淵明,要請他出山了。陶淵明雖然當官多次,但從未在朝廷任過職,這一次的徵辟,不知道有什麽具體的背景,總之詩人的文名已經上達朝廷了。但是陶淵明不幹。不過受到過朝廷徵辟也是一種榮譽,一個身份,所以等到他去世以後,颜延之作《陶徵士誄》(《文選》卷五十八),就特别强調他的這一身份。誄文寫道:“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嶽之幽居者也”,又道“有詔徵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於尋陽縣之某里”。這裏説是朝廷以“著作郎”一職虚席以待,比《宋書》本傳所説的“著作佐郎”更高一檔。李延壽《南史·隱逸傳》之陶淵明部分説:“義熙末,徵為著作佐郎,不就。”與《宋書·隱逸傳》全同——大約確實是準備請他當著作佐郎。陶淵明不肯出山。
後來劉宋王朝又曾請他出山。蕭統《陶淵明傳》載:“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這一次陶淵明似乎傾嚮於接受徵辟,但因為健康原因,已經來不及到任了。到晚年他的態度何以會有這樣的變化,現在看不到什麽明確的記載,但我們知道他晚年在同劉宋官員颜延之的談話中説過:“獨正者危,至方則閡。哲人卷舒,布在前載。”這些話自然是他對年輕朋友的教誨,同時應當也表明他晚年的人生態度有所變化,由“吾駕不可回”一變而為吾駕亦未嘗不可以回了。這一輪見面在劉宋永初三年(422),陶淵明時年五十八。
如果不是那樣匆匆地去世,陶淵明的形象也許會發生令人刮目相看的新變化吧。
其 十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塗。此行誰使然,似為饑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
本詩提到的“遠遊”並非一般的旅遊或如唐人之所謂“壯游”,應是出仕的委婉説法,實指陶淵明的初仕。陶淵明二十歲時開始仕於江州刺史桓伊。
所以此詩無非是回憶往事,説自己那時為了生計出去當小官,四處奔走,經歷過許多風波(“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塗。此行誰使然,似為饑所驅”),十分辛苦,那原是不得已而為之啊。
陶淵明不止一次説起自己二十歲時的往事,如《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天道悠且遠,鬼神茫昧然。結髮念善事,黽勉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録至,收斂不盈廛。夏日常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在己何怨天,離憂悽目前。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為賢。
詩中所謂“弱冠逢世阻”,以及《有會而作》一詩開頭所説的“弱年逢家乏”,都與《飲酒》其十的“此行誰使然,似為饑所驅”相呼應。二十歲時陶淵明深感必須謀取一個職務纔能養活自己並資助家庭,但當時這個差事與他的遠大理想不盡相合,幹了一段時間就回家去了——這就是陶淵明的初仕與初隱①詳見顧農:《陶淵明的初仕與初隱》,《書品》2016年第4 輯。。本詩中之所謂“息駕歸閑居”正是説起他的初隱。
到太元十八年(393) 他二十九歲時,再次出山,仕於其時的江州刺史王凝之,但幹的時間卻要短得多。陶淵明一生的仕途折騰甚多,他始終不大願意接受官場的拘束。
前人因為不甚瞭解陶淵明的初仕與初隱,此詩遂不能獲得正解。例如有人説:“此直賦其辭彭澤而歸來之本意”(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其實此時離他任彭澤令又掛冠而去還相當遠,具體的情緒也有許多不同。當然,陶淵明反覆出仕、反覆退隱確有一對基本的矛盾:一想獲得官俸以改善生活,二欲閑居於故園以享受自由,而二者不可得兼。
其十一
颜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饑至於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
其十一這首的主旨也在於强調現實生活最為重要,身後的空名没有什麽意義。
陶淵明主張一要生存(最好長壽),二要滋潤(不能枯槁),三要稱心(不要違己)。人應當好好活着,死了就是死了,到那時一切財富都將没有意義。嵇康講“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否定現行政治體制中的用來教化的“名”而回歸自己的本性。陶淵明更進一步,把誘導人們認同現行體制的身後之名也一道抛棄了。
“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被認為是陶淵明最要緊的警句之一。“保千金之軀者,亦終歸於盡,則裸葬亦未可非也。”(湯漢注《陶靖節先生詩》卷三)
有人説:“陶公一生志節如是,其顧惜身名為何如耶! 篇中言身世不足惜,不過世人之見,反言之以自寫其一時達趣云爾。不然,飲酒之餘,身名不惜,何以為靖節哉。”(温汝能《陶集彙評》卷三) 把陶淵明正面宣揚的思想當作他不以為然的思想,目的無非怕影響陶淵明的正面形象,其實卻完全歪曲了陶淵明,抽空了陶淵明,把他改塑為傳統的正人君子——這種做法正如把他改塑為東晉王朝的遺老一樣,在陶淵明研究中曾經産生過很大的影響,並且至今仍在起作用。不把這些外加的東西去掉,將無從認清陶淵明的真相。
應當承認,先前陶淵明也同一般的士人一樣,是相信名教,看重“身後名”的,也曾經在作品中説過“病奇名之不立”(《感士不遇賦》),感慨過“四十無聞,斯不足畏”(《榮木》);但後來終於認識到衹有抛棄名,包括“身後名”,纔能真正獲得自由。
魯迅先生也是不要身後之名的,他在遺囑中説:“趕快收殮,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忘記我,管自己生活”①《且介亭雜文末編·死》,《魯迅全集》第6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612 頁。。
魯迅和陶淵明由此獲得了最充分的心靈自由,但後人卻没有忘記他們。
其十二
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辭。仲理歸大澤,高風始在兹。一往便當已,何為復狐疑? 去去當奚道,世俗久相欺。擺落悠悠談,請從餘所之。
詩中提到的兩位古人和他們的事迹都大有言外之意。這首詩的寫法略近於詠史,又完全没有涉及飲酒,有可能是後來加進《飲酒》組詩裏來的,另外還有幾首也是如此——可惜此事現在都無從證明或證偽。當然,起初在不在《飲酒》組詩裏關係並不大,反正都是陶淵明的詩。
漢朝人張長公曾經先仕後隱,但衹是一次性的,没有任何反覆②《史記·張釋之列傳》:“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這同陶淵明本人在仕與隱之間多次折騰頗異其趣。唯其如此,他對張長公其人非常仰慕,多次在作品裏提到,有時還就此作自我批評。例如:“遠哉長公,蕭然何事? 世路多端,皆為我異。斂轡朅來,獨養其志。寢迹窮年,誰知斯意。”(《讀史述九章》) “張生一仕,曾以事還。顧我不能,高謝人間。”(《扇上畫贊》) 至於那個“歸大澤”的仲理即漢朝的儒師楊倫,則在仕與隱之間有所反覆①《後漢書·儒林列傳》:“楊倫,字仲理。為郡文學掾,志乖於時,去職,講授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後特徵博士,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絶人事。”,雖然不失其高風,終不免落入第二義。陶淵明批評他“一往便當已,何為復狐疑?”這其實也正是陶淵明的自我批評。
陶淵明忽然在詩中歌詠這兩位漢朝名人並有所議論,大約是以朝廷徵辟他出任著作郎或著作佐郎為背景,他也未嘗没有動過心,而這時他想到了張摯和楊倫,想到自己的過去和現在,終於得到一個明確的結論:“吾駕不可回。”把這首詩與其九聯繫起來讀,可以看出他的内心世界是何等生動。
其十三
有客常同止,趣捨邈異境。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寄言酣中客,日没燭當炳。
這裏寫到很不相同的兩個人或兩類人,一是“長獨醉”的,一是“終年醒”的,他們之間没有什麽共同的語言,説話自然不能投機。陶淵明以醉人自居,甚至主張夜以繼日地飲酒,點起燭光來。
先前屈原形容自己説衆人皆醉我獨醒,現在陶淵明説,不要去管那些清醒的人,繼續沉醉吧。説起來似乎截然相反,其實乃是殊途同歸:我行我素,走自己的路。别人説什麽不必理會,反正説不到一塊兒去(“發言各不領”)。
在陶淵明的熟人中必有不贊成他一味歸隱的,有勸他東山再起的,陶淵明認為他們都太清醒太積極了,自己寧可醉得頹然而自適,這纔是當今需要的聰明(“兀傲差若穎”)。
宋朝人湯漢解釋本詩説:“醒者與世討分曉,而醉者頹然聽之而已。淵明蓋沉冥之逃者,故以醒為愚,以兀傲為穎耳。”(湯漢注《陶靖節先生詩》卷三) 古語説大智若愚,又説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都是剥進一層的見道之言;而清朝大畫家、詩人鄭板橋的名言“難得糊塗”,則亦猶此意也。
其十四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本詩寫詩人同他的好友一起很開心地共飲,鋪點草木坐在地上,也不講究什麽禮儀,就那麽隨意喝酒,雜亂閑談,大家都進入了物我兩忘的境界。陶淵明寫飲酒之趣,似以這一首為最舒適。
其十五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迹。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
本首轉折甚多,“灌木荒宅以下,是貧居景象,宇宙句放筆嚮空中接”(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四);以下念宇宙之無窮,嘆雙鬢之已白,感慨人壽幾何,深知必須達觀委命,保持自己一貫的思想和風格。
人上了年紀之後,往往會發生若干變化,其常見的消極的方面有固執吝嗇,所以孔子早就説過“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論語·季氏》)。老年人心理上不能老,要保持過去的“素抱”,勿使半途而廢。
其十六
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行行嚮不惑,淹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弊廬交悲風,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孟公不在兹,終以翳吾情。
既然説“行行嚮不惑”,可見這首《飲酒》其十六作於四十歲前不久,似可繫於元興二年癸卯(403) 詩人三十九歲之時。
本年陶淵明又作有《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最宜互相參看:
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絶。顧眄莫誰知,荆扉晝常閉。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結。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悦。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平津苟不由,棲遲詎為拙。寄意一言外,兹契誰能别?
《飲酒》其十六中提到弊廬和荒草,而這裏也説到空宇蕭索,二詩的情緒也都比較低沉,其寫作時間應當相當靠近。此時陶淵明正因為母喪在家守制。
陶淵明在他四十一歲(義熙元年,405) 之前隱居過三段時間:一是他在二十歲(太元九年甲申,384) 初次出仕後,幹了一段時間就回老家閑居;二是從他二十九歲那年即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 “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宋書·隱逸傳》) 以後到他三十五歲即安帝隆安三年(399) 出山在桓玄手下任職以前的那五六年;三是從隆安五年(401) 冬陶淵明因母喪退出官場離開桓玄起到安帝元興三年(404) 再度出山到劉裕手下任職之前,這三年時間,陶淵明固然是遵守當時的禮制回家守孝,同時也可以視為他的又一度隱居。在此後不長的時間裏,陶淵明先後當過鎮軍將軍劉裕的參軍、建威將軍劉敬宣的參軍和一個小小的地方官彭澤令。這三次為官時間都很短,一共不足兩年,終於在義熙元年(405) 十一月徹底歸隱。
陶淵明義熙元年(405) 歸隱後也曾經有人勸他東山再起,他没有同意,説是“吾駕不可回”(《飲酒》其九)。為什麽先前他的隱士大駕可回,而到這時就如此決絶呢?
在這以前他還年輕,可以選擇的道路比較多,以後便定局了。在寫作《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一詩時,他也還没有完全找準自己的人生定位,詩中明顯地流露出彷徨和動摇。《飲酒》其十六也是如此。
陶淵明的出仕,大而言之是要有所作為,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小而言之是尋找生活出路,弄點收入養家糊口。這兩層意思在他詩文中都曾經説起過,前者以《感士不遇賦》之所謂“大濟於蒼生”説得最為簡明,後者則他在《歸去來兮辭》的小序中明確説過“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這些都是真心話。而如果退出官場,過隱居的生活,一則大志無從實現,二則生活水準必然下降。後者尤為立竿見影且必有切膚之痛。《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一詩前半用了許多筆墨寫自己在衡門之下饑寒交迫的苦況,甚至説雖然外面是很好的雪景—— “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結”,這兩句,前人評價極高,被稱為“千古詠雪之式”(《古詩源》卷八),“後來者莫能加也”(《鶴林玉露》卷五),而自己卻完全無心欣賞:人太窮了就顧不上審美。
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而固守其窮決非易事。陶淵明説自己是“謬得固窮節”,這表明他本來並不想走這樣一條路,現在衹是不得已而為之。那時在陶淵明面前有兩條路:一是在官場裏不斷運作和升遷,那是陽關大道(“平津”);另一條是退守田園,棲遲於衡門之下,這是獨木小橋。陶淵明説,既然前一條路走不成,那麽衹好走後一條,這也不算是“拙”。
這麽説話總有點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味道,有自我安慰的意思。這時的陶淵明認為固守其窮乃是“拙”,算不得“高操”。可知他本心深處並不打算“拙”,衹是被逼至此,無可奈何罷了,這與他後來下決心“守拙歸園田”(《歸園田居》其一),心情是很兩樣的。
《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結穴處的“寄意一言外,兹契誰能别”兩句頗有玄言的色彩。這裏的“一言”指一個字,就是上句之末的那個“拙”字①按:此“一言”或謂指“固窮”,或謂指“棲遲詎為拙”,皆不合適,那樣就不止一個字了。。“拙”字在陶詩中出現過多次。陶淵明後來往往在褒義上使用此字,除了他的名句“守拙歸園田”以外,還有“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為陶一觴”(《雜詩》其八)、“介然安其業,所樂非窮通。人事固已拙,聊得長相從”(《詠貧士》其六)、“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乞食》)。在這些詩句裏“拙”字的含義已經由貶而褒。而先前的“棲遲詎為拙”這一句是為“棲遲”亦即隱居辯護的。他説這樣活着還不能説是“拙”,這裏“拙”字明顯是貶義的。當然,陶淵明立即又説,“拙”字在它的一般義之外還有言外之意,這就含有要替“拙”字推陳出新的意思了。詩中末句忽然發問道,誰能够對此作出分析研究呢? 他大約是寄希望於他的從弟陶敬遠罷,但也没有明言,此時詩人自己陷入了深沉的反思。
陶敬遠生平事迹不詳,據陶淵明的《祭從弟敬遠文》可知,其人逝世於義熙七年辛亥(411),年紀不過三十剛出頭(“年甫過立”)。他比陶淵明大約要小十五六歲,當元興二年(403) 陶淵明寫《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送他的時候,這位從弟也就二十幾歲,陶淵明希望他能够明白自己的深意,亦不便作過高的要求。祭文寫道:
……感平生之遊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湣湣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攜手,置彼衆議。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共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静月澄高,温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離世!
寫這篇祭文的時候,陶淵明已經徹底歸隱好幾年了,他這時回想起八年前同敬遠在一起的那些日子,不禁感慨萬千。關於他本人十年前回家暫隱的緣故,這裏説成是“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策歸來”,似乎是對政局另有所見,並基於某種人生哲理主動退回故鄉的,可是我們知道這分明與事實不合,實際上應當是他遭遇母喪,非回家不可。回憶中總不免用較近之時的想法取代當年的事實和思路。寫《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一詩時桓玄的事業正方興未艾,所以在陶淵明眼中還有一條“平津”大道;而到現在,桓玄早已徹底垮臺,政治局面同先前大不相同了,於是他的措辭就發生了不小的變化。
自從孔夫子提出“君子固窮”(《論語·衛靈公》) 這一原則,對待“窮”——政治上失意,生活上貧困——的態度,一直是士人十分關注的問題,能固守其窮而不改變節操,乃是一種極其重要的品格和素養。陶淵明是能够“君子固窮”的,所以他放棄彭澤令而歸隱,為了心靈自由寧可抛棄當官的高收入,而且一直堅持到底,再也没有復出。這是很不容易的。
陶淵明過去還做不到固守其窮,所以往往隱居了一段時間就又出來當官。他曾經反覆出仕,反覆歸隱,折騰過多次,到他最後一次出山也還是想弄一點錢來作為“三徑之資”(《宋書·隱逸傳》)。後來實在是覺得“違己交病”(《歸去來兮辭·序》),無法忍受,這纔最後下定決心退回老家。而即使是在離開彭澤歸隱之後,在他内心深處也還有兩種思想傾嚮的鬥争,在兩種生活模式之間猶豫動摇,這就是他詩中所説的“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颜”(《詠貧士》其五)。毫無内心衝突而固守其窮,那是遠於人情的。
陶淵明的偉大之處不僅在於他終於戰勝了自己的情欲而心甘情願地固守其節操,還在於他一嚮説真話,敢於暴露其真實思想,這可能比固守其窮還要難。
固守其窮的人也還希望得到别人的理解。在《飲酒》其十六這首詩中,陶淵明除了感慨隱居生活的辛苦之外,還於無意間流露了一點自己内心深處的矛盾,這就是詩的最後兩句:“孟公不在兹,終以翳吾情。”如果孟公在兹則如何? 詩人很可能就要嚮他訴苦,希望得到其人的理解和同情。“孟公”指東漢人劉龔,“龔字孟公,長安人。善議論,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後漢書·蘇竟傳》);又,皇甫謐《高士傳》載:“張仲蔚者,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没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固守其窮的張仲蔚雖然閉門自守,也還有一個知音劉龔劉孟公,而自己則没有這樣的幸運,陶淵明很有些寂寞的悲哀。他在另外一首詩中又曾寫到張仲蔚與劉孟公:“仲蔚愛窮居,繞宅生蒿蓬。翳然絶交遊,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音,衹有一劉龔。”(《詠貧士》其六)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陶淵明卻缺少這樣一個知己。饑寒交迫長夜難眠固然痛苦,無人理解孤獨寂寞則更加痛苦。《飲酒》其十六最深刻的悲哀在此,其動人之處也正在這裏。由此可知陶淵明在“行行嚮不惑”之時還没有堅强到不怕孤獨的水準,總要到若干年後,他纔鍛煉成為不懼嚴寒孤獨的青松。
其十七
幽蘭生前庭,含熏待清風。清風脱然至,見别蕭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鳥盡廢良弓。
“高鳥盡,良弓藏”曾經是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常態,本詩詠嘆此事,似屬老生常談,而陶淵明本人其實並没有這樣的遭遇。有人以陶淵明的抛棄彭澤令為良弓被廢,恐怕没有根據;即使委婉一點,説成是“鳥盡弓藏,蓋藉昔人去國之語,喻己歸田之志”(湯漢注《陶靖節先生詩》卷三),也大感難通,陶淵明立言不當如此牽强。
清人温汝能《陶詩匯評》(卷三) 説:“此詩衹是藉幽蘭以自喻,似無别意。唯末句所指不甚明晰。”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此詩傳世本或已有殘缺,而由後人拉雜編入《飲酒》組詩中。
其十八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觴來為之盡,是諮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
兩漢之交的大學者、大作家揚雄(字子雲) 是個窮人,喝不起酒,要靠朋友門生資助①詳見《漢書·揚雄傳》。。幾杯酒下肚來了精神,這時談起學問來,什麽困難問題都能解決,而碰到敏感的政治問題,他就不肯多説什麽了。什麽東西該講,什麽東西應當沉默,揚雄從不失去應有的原則和分寸。
“仁者”自有自己的底綫。陶淵明是喜歡喝酒的,他寫這首詩大約是要表示,自己並没有喝昏了頭,也自有其原則和分寸。
其十九
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嚮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
本詩是考證《飲酒》寫作時間的重要文證。這裏説到自己先前的出仕(“去學仕”) 和歸隱(“歸田里”),而至今又是十二年過去了。由此可知,原本《飲酒》的一組詩當作於義熙末年(416—417)。由於後來又被加進了一些其他作品,今本《飲酒》中各首的寫作時間就比較複雜,不能下簡單化的結論了。
詩裏説,自從歸隱以後自己就大喝其酒,經濟情況不甚佳,不可能像漢朝退休的高官疏廣、疏受那樣大把地花錢喝酒②《漢書·疏廣傳》記載前太子太傅疏廣退休時曾獲皇家大量賞賜,回鄉後經常請老鄉喝酒,準備花光,不欲留給子孫。西晉詩人張協有詠二疏的《詠史》詩云:“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娱。藹藹東門外,群公祖二疏。朱軒曜京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行人為隕涕,賢哉此丈夫! 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座賓,多財為累愚。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參見顧農《陶詩二首解讀·〈詠二疏〉》,《古典文學知識》2005年第5 期。,但也還能有點低端的濁酒喝喝,這也就不錯了。陶淵明要求不高,一嚮自得其樂。
其二十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如何絶世下,六籍無一親! 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本詩中“汲汲魯中叟”指孔夫子,他的工作是為了再使風俗淳;“區區諸老翁”指漢初諸老儒,他們在秦火的浩劫之後努力地恢復儒家的經典,立下了很大的功勞。
可惜如今儒家學派再次衰落了,六經簡直没有人讀,衹知道在名利場中奔走馳騁。現實的狀態如此,我能有什麽辦法,衹好喝酒取醉,酒後發些狂言,還要請大家原諒纔好!
陶淵明始終没有完全離開儒家。
但陶淵明又絶非所謂純儒,他接受的前代思想遺産相當豐富駁雜,除了儒家思想以外,道家有一點,《列子》書的思想有一點,佛教的東西也有那麽一點點。他都没有隱瞞,而一一坦然道之。陶淵明是個有思想的人,但恐怕也還算不上思想家。
各種思想都有一點,那麽還能够指出一種主導的東西嗎? 如果勉為其難,也許可以説,陶淵明還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在他心目中,孔子和漢儒是一些偉大的標杆,衹是自己生不逢辰,無從完全追隨其後,衹好逃離上層社會,躲在鄉下,喝點小酒,自得其樂,不去同流合污也就是了。《飲酒》組詩正是他這種思想風貌的集中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