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头
2019-12-11郑宏章
郑宏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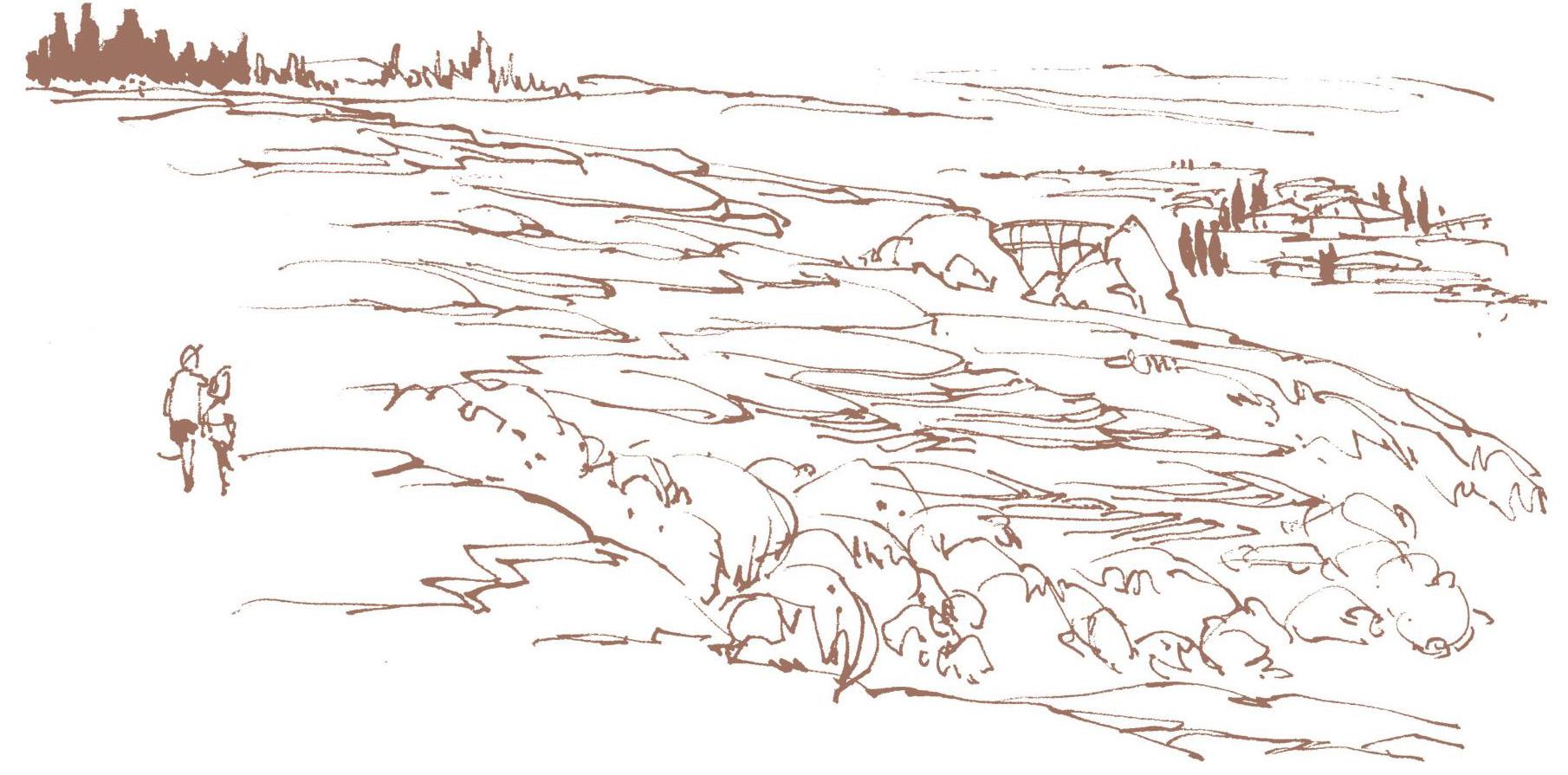
小 时候我有个同学,名字很特别,叫做笼 头,大我两岁,见人就咧着嘴笑。我俩虽不同村,但常黏乎在一块,上树掏鸟蛋,下河逮鱼虾,形影不离。他村上有一口古井,井水清凉带甜,夏天暑热,远近村子的人,没有不喜欢去打了喝的。我想喝了,就跑去找他,管我喝饱,还外带一瓦罐回来。
土改时候,笼头家分得一头驴。这驴拉石磨时,常会偷吃磨盘上的粮食。他爸就用竹子编个笼头套住驴嘴,不让它吃,任驴子打着响鼻,只能乖乖地围着磨盘转圈子。他小时候逗人喜爱,爸妈特金贵他,就给他取个小名叫笼头,意思是他像套驴嘴一样被套牢了。那时候有人逗乐,问他属什么,他就指指驴,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笼头爸上过几年私塾,记忆力好,嘴皮子利索,擅长说书,我特喜欢听他爸说《包公传》。那时乡村一到农闲,晚上除了上床就没事干,大家就说:“请老程头来说书。”老程头就是他爸。听到精彩处,大家就笑,笼头也跟着嘿嘿地笑。
笼头很像他爸,不仅面相酷似,嘴皮子也利索。放了学就跟着他爸干农活,播种收割都干得像模像样。大包干那时候,他家的责任田施行套种,整得像个花园一般。他肯卖力气,上小学三年级时,他就挑着两只笆斗到乡粮站缴公粮,俨然小大人。
后来他娘跌断了腿,他爸跟着得了痨病,他为此请假回家帮忙,耽误了不少课,但他学习也更刻苦。初二下学期的一天,他爸病得不行了,他就回家奔丧。那个周末临回学校时,他捎口信来,说不念书了。初三未上就退了学,他在家不吃不喝睡了一天,哭得很伤心。后来我上了高中,就很少见到他,再后来我去外地上大学,毕业后进了城,分配到法院工作,我和他见面就更少了。
后来村里人纷纷外出打工,他却迟迟不肯挪窝。我打电话问他:“你咋死守那一亩三分地呢?”他说:“我就只会种地呀。”我放下电话,感叹道,真是一条庄稼汉子啊!他的心和土地连在了一起。
再后来,年近半百的他拗不过村里人的鼓动,终于带上老婆孩子,去外地“打工”,租地种了十年大白菜。
十年后,我俩好不容易相见了。一见面,他就把我抱起来转了几圈,就像小时候在麦场上比试摔跤。他看着我的法官服,说:“你是俺村老枣树最红的一颗枣子!嘿嘿。”我说:“当年你若不退学,上大学是三个指头捏田螺——稳拿!”“认命认命。”他苦笑了一下。
虽然皱纹爬上了他的脸庞,原本稀薄的头发也更加稀少了,但他说起话来声音洪亮,吐字利索。他告诉我,刚去打工,他看到那里有大片被征用了的土地抛荒,就提出由他来承种这些地。获得同意后,老两口起早摸黑一锹一镐地开垦出70亩地,全都种上大白菜。刨坑、栽苗、浇水、施肥、除草、治虫、收菜、卖菜,从春忙到秋,上缴的费用从不拖欠,累是累点,却增加了收入。去年忙得红火时,镇里贴出了告示,要收回他的菜地,那时大白菜还在地里长着,再过半个月,就要收获了。一天晚上,一下子开来了几台铲车,众人拽住老两口,碾的碾,铲的铲,不一会儿,大白菜全给毁了,仅留下一地的残根碎叶。老两口大半年的希望也跟着破灭了。翌早,老两口抱着被铲烂的大白菜,到镇政府说理,理没讲成,双双被送到派出所关了一夜。于是老俩口聘了律师,正儿八经地同镇政府打起了官司。那地种不下去了,他带着全家又回了老家,一边在家门口的田里为自己打工,一边惦记着未了的官司。
讲到这儿,他叹了口气,像又回到了那个恶梦般的晚上。他掉泪了。我的眼睛却喷着火,明白这帮人伤害的不仅仅是大白菜,更是农民对土地执着的心!笼头心里没底,咨询我:“人家说我是民告官,我能告赢吗?”我回答说:“能,一定能!”并叮嘱他,“最要紧的是不能丧失信心。”他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眉头舒展开来,笑着说了一句:“借你吉言。”便兴冲冲回去了。
没多久,他儿子从老家打来电话,哽咽地告诉我,他爸走了!“怎么了?”我脑袋嗡了一下。“他起夜时跌倒,没抢救过来。他本来说等法院的判决下来再去看你的。”
等我赶回老家那天,他的骨灰已经下葬。也是那天,法院的判决书送达他家,官司勝诉,十多万的大白菜补偿款判给了他。
他是农民,也许他不能离开土地,抑或土地也离不开他,好在他最终与土地融在一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