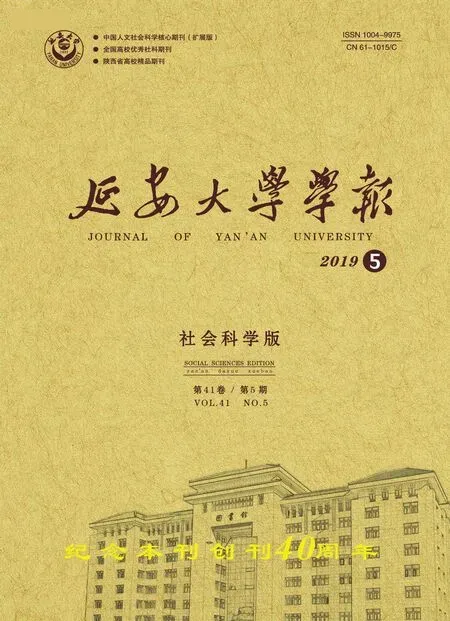画像石中的汉代陕北社会
2019-12-08刘蓉
刘 蓉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1920年前后,陕北出土的“故雁门阴馆丞西河圜阳郭仲理之椁”和“圜阳郭季妃”画像石首次在《艺林月刊》披露,这是陕北发现画像石的最早记录,但是没有明确的发现地和出土墓葬。1949年后榆林地区陆续发现了一批画像石墓,分布在榆阳、靖边、神木、米脂、绥德、子洲、吴堡、清涧等8县区,这些墓葬出土的画像石,加上历年收集所得,目前总数已超过一千块,使得陕北成为画像石富集的几个主要地区之一。其中有纪年画像石集中于东汉和帝永元二年(90年)至顺帝永和五年(140年)之间。有赖于各种发掘简报和调查报告资料的发布,(1)发掘简报类如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米脂官庄画像石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收集著录类如陕西省博物馆:《陕北东汉画像石刻选集》,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李林等主编:《陕北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李贵龙:《绥德文库·汉画像石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等。有关陕北汉画像石的研究一直为学界所关注,研究成果丰硕。(2)汉画像石综合研究情况可参见沈颂金:《汉画像石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期,巫鸿:《国外百年汉画像石研究之回顾》,《中原文物》1994年第1期,刘太祥:《汉代画像石研究综述》,《南都学坛》2002年第3期,杨爱国:《五十年来的汉画像石研究》,《东南文化》2005年第4期。代表性研究可参见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李发林:《汉画考释和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蒋英炬、杨爱国:《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等。关于陕北汉画像石综合研究,可参见何正璜:《陕北东汉画像石概述》,《陕北东汉画像石刻选集》,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信立祥:《陕西、山西画像石综述》,中国画像石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陕西、山西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康兰英:《陕北东汉画像石综述》,《中国汉画研究》(第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李林:《陕北汉代画像石述论》,《人文杂志》1999年第4期;张欣:《规制与变异—陕北汉代画像石综述》,《中国汉画研究》(第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相关专题研究可参见李贵龙、康兰英、李林、李凇、吴镇烽等众位学者的论著。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画像石,使我们得以对汉代进行更细致的了解。本文就画像石所展示的汉代陕北社会状况进行一些探讨,祈请方家指正。
一、上郡、西河与汉代陕北行政区划建置沿革
西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年)前,今陕北地区属上郡,系承秦郡而来。战国魏有上郡,魏惠文王十年(前328年),“魏纳上郡十五县”[1]《秦本纪》206,魏襄王六年(前313年),“魏尽入上郡于秦”[1]《魏世家》1848。秦昭王时,始置秦上郡。(3)《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85页)称:“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宣太后杀义渠王一事,《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4页)载:“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周赧王四十三年,为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年)。《水经·河水注》则记载:“奢延水又东,径肤施县南。秦昭王三年置,上郡治。”辛德勇《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与边境解析》(《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采上郡及其郡治肤施始置于秦昭王三年(前304年)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上郡为秦三十六郡之一。
元朔四年,汉武帝以上郡东部及代国西部诸王子侯国为主开置西河郡。(4)《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18页)“西河郡”注曰:“武帝元朔四年置。南部都尉治塞外翁龙、埤是。莽曰归新。属并州。”《汉书》卷15上《王子侯表上》(第453-455页)载元朔三年正月壬戌日武帝封代共王子九人为侯。自此,今陕北地区属上郡、西河两郡,所辖县当以《汉志》所载上郡地与西河郡黄河以西属地为准。(5)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79、149页)指出“元朔三年以前上郡当为《汉志》上郡与西河郡河水以西地之和”,可以信从。但认为“元朔三年时,西河郡未置,故代王子侯国必别属上郡”则可商榷。武帝元朔二年颁布推恩令,为的是削减诸侯王势力,因此分封代王九子的侯国,必在代王所王太原郡境内,而不可能挤占上郡之地。因此上郡所辖元朔四年前应以西河为界,与代国太原郡相望。《汉书·地理志下》:
上郡,户十万三千六百八十三,口六十万六千六百五十八。县二十三:肤施,独乐,阳周,木禾,平都,浅水,京室,洛都,白土,襄洛,原都,漆垣,奢延,雕阴,推邪,桢林,高望,雕阴道,龟兹,定阳,高奴,望松,宜都。[2]《地理志下》1617
西河郡,户十三万六千三百九十,口六十九万八千八百三十六。县三十六:富昌,驺虞,鹄泽,平定,美稷,中阳,乐街,徒经,皋狼,大成,广田,圜阴,益阑,平周,鸿门,蔺,宣武,千章,增山,圜阳,广衍,武车,虎猛,离石,谷罗,饶,方利,隰成,临水,土军,西都,平陆,阴山,觬氏,博陵,盐官。[2]《地理志下》1618
《汉志》所记为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数据,经过一百多年变迁,到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上郡、西河所辖县城及户口数都有了很大变化。《后汉书·郡国志五》:
上郡,十城,户五千一百六十九,口二万八千五百九十九。肤施,白土,漆垣,奢延,雕阴,桢林,定阳,高奴,龟兹属国,候官。[3]《郡国志五》3524
西河郡,十三城,户五千六百九十八,口二万八百三十八。离石,平定,美稷,乐街,中阳,皋狼,平周,平陆,益阑,圜阴,蔺,圜阳,广衍。[3]《郡国志五》3524
从以上两组数据对比来看,上郡省并减少了十四个县城,增置了一个侯官。西河郡省并减少了二十三城且并无增置,两郡政府控制的属地和户口数都急剧下降。到东汉依然存在的二十多个县城中,学界对其城址所在,一直颇有争议,很多都只能笼统大概言之。不过得益于陕北汉画像石题记与出土地的相互印证,我们的认识现在能更清晰更具体一些。比如平周,以前学者多认为在河东,(6)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18页)认为平周属河东八县之一,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王子今《西河郡建置与汉代山陕交通》(《晋阳学刊》1990年第6期)均沿用此说未改。但是1978年出土于陕西米脂县城郊官庄村四号墓的牛季平画像石题记以及2005年官庄二号墓出土的木孟山夫人画像石题记,却有不同的记载,这些题记分别刻于各自墓室前室北壁的中柱石上。
其一称西河平周寿贵里牛季平[4]205
另一称平周寿贵里木君孟山[5]80
两块画像石出土地为陕西米脂,题记明确墓主籍贯为“西河平周寿贵里”,郡县里俱全。更为难得的是,牛季平画像石还有纪年,为永和四年(公元139年),距离《续汉书·郡国志》所采永和五年数据只差一年,足以证明西河郡的平周是在黄河以西。(7)参见吴镇烽:《秦晋两省东汉画像石题记集释——兼论汉代圜阳、平周等县的地理位置》,《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1期。
另外可以确定的就是西河郡的圜阳。陕北出土画像石中,明确提到西河圜阳的有:
田鲂画像石(92年):西河太守都集掾圜阳富里公乘田鲂万岁神室[4]203。
郭稚文画像石(103年):永元十五年三月十九日造作居圜阳西乡榆里郭稚文万岁室宅[4]204。
张文卿画像石(104年):西河圜阳张文卿以永元十六年十月造万岁堂张公寿堂[4]204。
田文成画像石(106年):西河太守掾圜阳榆里田文成万年室延平元年十月十七日葬[4]205。
这四块画像石出土地均在陕西绥德县,田鲂墓在四十铺镇前街,郭稚文墓在张家砭乡五里店,张文卿墓在中角乡白家山村,田文成墓在四十铺前街。也就是说,西河郡的圜阳就在今天的绥德无定河以北以东。随着圜阳确定,圜水也就不需再争论了,可以肯定汉代无定河称圜水。由此,则圜阴也可以重新推定,或许绥德城西的黄家塔即是其址。(8)民国《米脂县志》的修纂者高照初等以圜阴为横山县之响水堡,吴镇烽认为在今横山县党岔乡西杨口则附近。这两处均在今横山县境无定河南,符合“圜阴”在圜水之阴的条件,但距圜阳较远,中间还隔着位于米脂的平周县,且无定河在横山县境和绥德县境流向不同,似乎不宜用来作为阴阳的参照。我认为,圜阴和圜阳应隔大致同一流向的某段圜水相望,两地相距不会太远,绥德黄家塔正符合这个条件。
二、汉代陕北的官吏及其生活
从上郡西河的户口数来看,西汉时的陕北人丁兴旺,由此各类人才也不断涌现。汉代上郡、西河郡人仕宦为吏者,见于文献、石刻资料等记载有:
1.陕令上郡奢延郭硕升公
2.元氏左尉上郡白土樊玮字子义
3.渔阳郡守上郡王氏
4.朔方太守上郡仇氏
5.良乡长西河圜阳田植君长
6.故雁门阴馆丞西河圜阳郭仲理
7.大高平令郭君
8.徐无令乐君
9.使者持节护乌桓校尉王君威
10.辽东太守
11.河内山阳尉西河平周寿贵里牛季平
12.故大将军掾并州从事属国都尉府丞平周寿贵里木君孟山
13.西河太守都集掾圜阳富里公乘田鲂
14.西河太守行长史事离石守长杨君孟元
15.永元十二年西河府史郭元通
16.西河太守掾任孝孙
17.西河太守掾圜阳榆里田文成
18.西河太守盐官掾贾孝卿(9)参见刘蓉:《陕北东汉画像石来源问题再探讨》,《榆林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李贵龙:《石头上的历史—陕北汉画像石考察》,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5页中的附表《陕北已发现有题刻和纪年文字的汉代画像石墓统计表》。
这些籍贯为上郡、西河的官吏,大多为掾史、令长、丞尉,位高者至郡守、使持节护乌桓校尉。郡守、护乌桓校尉、属国都尉、长史等,在地方上都是颇为显赫的。而最能直观展现汉代陕北官吏官场及生活状态的,莫过于木孟山夫人墓室的画像。
该画像石墓位于米脂县境内无定河西岸官庄村,2005年发掘。墓门横楣石下栏中,八位官吏头戴进贤冠,内衬黑介帻,身着宽袍大袖,端坐于枰上。两侧及中间各蹲踞两位小吏。前室南壁横楣石左右两端有榜题“诸郡太守待见传”,表明了画像的名称和主题。横楣石整个画面分为三部分,两端分别刻画一庭院,院中有高瓴大屋,每屋内分别刻待见的四位郡守形象,人物上方的屋檐上用隶书阴刻两行八字并涂红彩,标明太守所在郡及本人籍贯姓氏,左屋内左二人上方可见“太原太守扶风法君”“雁门太守颍川□君”,右二人上方刻字无法辨识,右端屋内四人上方刻字也无法辨别。横楣石中间部分刻画八位太守的车马,均为二马牵驾的轺车,各轺车上方阴刻二行六字,标注车马主人,尚可辨识者有“五原太守车马”“朔方太守车马”“上郡太守车马”“定襄太守车马”。前室北壁横楣石为车马出行图,中柱石阴刻铭文“故大将军掾并州从事属国都尉府丞平周寿贵里木君孟山夫人德行之宅”。(10)参见《米脂官庄画像石墓》发掘报告,第45-93页。
榜题所见的太原太守扶风法君,应该就是见于史籍的东汉法度。安帝延光三年(124年)“以太原太守法度代为(度辽)将军……冬,法度卒”[3]《南匈奴列传》2959。此外,史籍中未见其他法姓太原太守,而扶风则确为法姓郡望。如“法雄,字文强,扶风郿人也,齐襄王法章之后。秦灭齐,子孙不敢称田姓,故以法为氏。宣帝时,徙三辅,世为二千石”[3]《法雄传》1276,其子法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寿终”[3]《逸民列传》2774,法真之孙即刘备重臣法正。法雄永初三年(109年)被征为青州刺史,迁南郡太守,元初中卒于官,则法雄之死在公元114至119年之间。法真卒于中平五年,当生于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太原太守法度卒于延光三年时法真24岁,可知法度比法真为早,或为法雄同辈。
法度延光三年以太原太守代为度辽将军,其年冬卒于度辽将军任上,则其参加木孟山夫人葬礼一事必在此年之前。而榜题雁门太守颍川□君字样,又为我们确定该墓葬的时间上限提供了重要线索。史籍所见东汉雁门太守有三。光武帝时有郭凉,时间较早可不论;皇甫嵩的父亲皇甫节也曾任雁门太守,但皇甫氏为安定人,也可排除;另一位雁门太守庞奋,籍贯不详,永元七年(95年)“以雁门太守庞奋行度辽将军”[3]《南匈奴列传》2956。庞奋永元七年便已改为行度辽将军,与法度任太原太守的最后一年延光三年相距时间过长,所以庞奋也不可能是木孟山夫人墓画像石中所提及的雁门太守。
另据《武清东汉鲜于璜墓简报》披露,还有一位雁门太守鲜于璜。鲜于璜永初元年(107年)拜雁门太守,“到官视事,七年有余”,并于延光四年卒,享年八十一岁。那么,鲜于璜离任时应在元初元年(114年)左右。鲜于璜晚法度一年而卒,生前一为太原太守、一为雁门太守,原本最有可能是那位汉画像石中所图画的雁门太守,不过张传玺已考释鲜于璜为渔阳郡人,[6]那么这个推论也不能成立。但是法度与鲜于璜的信息,已经为我们缩小了推论范围,若再考虑大将军邓骘建光元年(121年)以罪死,则木孟山夫人之死可进一步确定在元初元年至建光元年(114-121年)之间。(11)《米脂官庄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整理者认为大将军可能是邓骘,可以信从。邓骘任大将军约在永初二年(108年)十一月至永初四年(110年)十月间。参见该报告第84页。
综上,八位太守齐聚西河平周,时间约在东汉安帝在位的114-121年期间。八位太守,可确定的有太原太守扶风法度、雁门太守颍川某君以及五原、朔方、上郡、定襄四位太守。这六郡均为并州诸郡,而并州下辖上党、太原、上郡、西河、五原、云中、定襄、雁门、朔方九郡,根据榜题“诸郡太守待见图”和木孟山“大将军掾”“并州从事”的头衔,可知剩下的两位必在上党、云中、西河太守之中。西河郡是木孟山籍贯所在,西河郡守与木孟山理应有君臣之分,因此“待见”太守中不应有西河郡太守,那么其余那两位就只能是上党太守和云中太守,而云中太守极有可能就是继耿夔任云中太守的成严。(12)《后汉书》卷19《耿夔传》(第719页)载耿夔永初三年(109)“左转云中太守”、卷89《南匈奴列传》(第2958页)载永初五年(111年)“以云中太守耿夔行度辽将军”,则109-111年耿夔为云中太守;《后汉书》卷5《孝安帝纪》(第233页)建光元年“鲜卑寇居庸关,九月,云中太守成严击之,战殁”、卷90《鲜卑列传》(第2987页)“建光元年秋,其至鞬复畔,寇居庸,云中太守成严击之,兵败,功曹杨穆以身捍严,与俱战殁”。耿夔之后若再无他人继任,则111-121年成严为云中太守。并州辖下的八位太守齐集西河,为木孟山夫人之丧致祭,可见木孟山的威势或影响力极大,人缘也极好。
当然,能让八郡太守前来吊丧,也可见汉代缘边诸郡官场的生态。从东汉初年开始,因为北边匈奴、乌桓、鲜卑以及羌人的威胁不断加大,这些边郡不仅面对战争时同生死共进退,而且职务变动也往往互相接替交换,因此形成了较为密切的官方和私人关系。如建武六年“芳将军贾览将胡骑击杀代郡太守刘兴。芳后以事诛其五原太守李兴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飒、云中太守桥扈恐惧,叛芳,举郡降”[3]《卢芳列传》507。永平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骑入于五原塞,遂寇云中至原阳,南单于击却之,西河长史马襄赴救,虏乃引去”[3]《南匈奴列传》2948。章和二年南单于将并北庭,上言“臣素愚浅,又兵众单少,不足以防内外。愿遣执金吾耿秉、度辽将军邓鸿及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3]《南匈奴列传》2952。总之,利害相关,荣辱与共,促成了相互之间较为密切的合作与往来。
木孟山为夫人营葬,就把八太守前来致祭的这一盛事刻画在墓中,而在最显著的墓门横楣石上,刻画八位太守连同其侍从端坐正中,以此炫耀死者的哀荣及其家门的显赫。与之大致相似的还有和林格尔壁画墓,该墓主曾先后出任“西河长史”“行上郡属国都尉”“使持节护乌桓校尉”,据榜题“西河长史所治离石城府舍”,其任西河长史时已在永和五年西河郡治迁至离石后。(13)参见黄盛璋:《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与历史地理问题》,《文物》1974年第1期,第38-46页。壁画将墓主一生仕宦经历图画出来,浩浩荡荡的车马出行队伍充分显示了其生前的赫赫威仪,用意与木孟山夫人墓中的八郡太守待见图一样,夸耀的意味极明显。这种喜欢炫耀、矜夸的性情也正是陕北人的性格特点之一,那些具有浓郁写实风格的浩荡车马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排场,也是陕北人更重视现世生活的真实写照。(14)巫鸿《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汉代丧葬艺术中的“柩车”与“魂车”》(见《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第260-273页),认为苍山墓中送葬行列的图像具有象征意义,这些车马行列象征了死后旅程的两个阶段,其转换则是通过车马方向从面向墓内到面向墓外的变化而完成的。但是,我们考察陕北汉画像中众多的车马出行图,扑面而来的都是浓浓的生活气息,很难看出其中有什么“象征意义”。陕北汉画像总体风格是写实的,这与山东汉画像的情形大异其趣。
参加木孟山夫人葬礼的那位上郡太守姓名无考。不过见于史籍者尚有几位,如西汉名将李广[2]《李广传》2439、冯奉世之子冯野王、冯立兄弟。野王兄弟深得吏民爱戴,史称“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为太守,歌之曰:‘大冯君,小冯君,兄弟继踵相因循,聪明贤知惠吏民,政如鲁、卫德化钧,周公、康叔犹二君。’”[2]《冯奉世传》3305西汉末王遵父[3]《隗嚣列传》528、东汉末王旻[3]《皇甫规列传》2136也都曾为上郡太守。西河太守有常惠[2]《霍去病传》2487、杜延年[2]《杜周传附延年》2666、宗育[3]《邓禹列传》603、宋汉[3]《宋弘列传》905、崔钧[3]《崔骃列传》1732、邢纪[3]《孝灵帝纪》355等。
郡守、长史之外,上郡、西河还有一些特别的官职,如上郡武库令。上郡地当北边之中,因此秦以来即设有武库,储存武器装备以供边防军需,因其重要,可能只有宗室或亲信才能任库令,如西汉河间王刘良就曾任上郡库令。(15)《汉书·成帝纪》“立故河间王弟上郡库令良为王”注引如淳曰:“《汉官》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第303页。再如属国都尉,汉武帝元狩二年为安置降汉的匈奴昆邪王及其四万余众,始置五属国[2]《武帝纪》176》,“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张守节正义“五郡谓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并是故塞外,又在北海西南”“以降来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国之俗而属於汉,故言属国也”。[1]《骠骑列传》2934宣帝神爵二年“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2]《宣帝纪》262,五凤三年“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2]《宣帝纪》267,东汉和帝永元二年“复置西河、上郡属国都尉官”,李贤注“西河郡美稷县、上郡龟兹县并有属国都尉,其秩比二千石。《十三州志》曰:‘典属国,武帝置,掌纳匈奴降者也。哀帝省并大鸿胪。’故今复置之”[3]《孝和帝纪》170》。属国都尉“主蛮夷降者……稍有分县,治民比郡”[3]《百官志五》3621》(16)《后汉书》志28《百官志五》:“属国,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每属国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丞一人……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第3619-3621页。。哀帝时,班固祖父班稚[2]《叙传》4203、王莽弟成都侯王邑[2]《何武传》3487都曾出任西河属国都尉,木孟山的职务之一就是属国都尉丞,其显赫也是很自然的。此外,上郡还有北部都尉、匈归都尉,西河有南部、北部、西部都尉等。
三、陕北居民及其日常生活
西汉时的上郡西河,农牧并举。元朔四年开置西河郡,“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2]《武帝纪》178,“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2]《沟洫志》1684,政府为管理农业生产,还设置了农令、农都尉等农官。到东汉初年,邓禹已称“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3]《邓禹列传》603,可见农牧业之兴盛。汉代陕北农业发达、畜牧业昌盛,可在画像石中得到直观感受,如涉及农业生产题材的牛耕、翻地、播种、拾粪、锄草、收割等图像不仅数量多,还细致逼真,尤其是牛耕图,既有二牛抬杠、一人扶犁,也有一牛挽犁、一人扶犁的形式,反映了陕北耕作技术的成熟和不断进步,同时大量畜牧狩猎图也显示了陕北当时畜牧业的发达状况。(17)参见李贵龙:《历史踪迹留贞石——绥德汉画像石题材鉴赏》,见《绥德文库·汉画像石卷》。汉画像上生动的图像让我们更容易理解虞诩《复三郡疏》中对汉代陕北的描述:
《禹贡》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又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阸据险。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3]《西羌传》2893
上郡、西河的居民构成较为复杂。春秋战国以来,这里即是白狄所居。战国末、秦汉时,有楼烦、白羊。西汉收复河南地后,迁徙关东平民数十万口居于此。东羌也是这里的古老居民。上郡、西河的属国有大量降汉的匈奴,元帝时曾有“上郡属国降胡万余人亡入匈奴”[2]《元帝纪》280。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郡龟兹属国,北魏郦道元称“县因处龟兹降胡著称”,而龟兹原本是西域北道大国,武帝时经营西域,龟兹始为汉所知。宣帝时,先有龟兹王携公主入朝,后有郑吉征发渠黎、龟兹诸国五万人迎降匈奴日逐王至河曲一事,[2]《郑吉传》3005龟兹属国的设置或在此时,用以安置内附或俘获的龟兹等西域降胡。龟兹人既以农牧为主,又擅长歌舞伎乐,有独特的文化信仰,他们的加入,为陕北社会生活注入了鲜活特色。(18)参见刘蓉:《陕北汉画像石中所见东汉民间信仰》,《榆林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地理气候的适宜,加上居民的五方杂厝,汉代上郡、西河的生活方式便呈现出多元性。从汉画像看,既有汉族、羌族甚至龟兹人的春种秋收、积粪耕耘的农业活动,又有匈奴、鲜卑、乌桓等民族放牛养马、拦羊喂鸡的畜牧业活动,既有炊米煮饭,也有烧烤肉串,孩子们在草地上玩着“抓子”(19)陕北绥米叫“吃鳖”,把猪羊腿关节上的骨头简单处理后用作玩具,玩时先将一子抛起,在其落下之前将撒在地上的余子,按照正、背、竖等顺序,依次摆放一遍,最后将所有“子”全部抓入手中,期间上抛的子不能落地,没接住就算“坏了”,换对方来玩。东汉画像石上的这一玩法,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陕北依然很流行,女孩子们能玩到把手指都磨破了,仍乐此不疲。的游戏,显示出丰富生动、充满活力的生活状态,而其畜牧射猎尤为特色鲜明。司马迁称“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1]《货殖列传》3262,班固称“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2]《地理志下》1644。政府在上郡设苑养马,上郡骑士及二郡属国胡骑名震当时。(20)《汉书》卷27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第1424页)载景帝时“匈奴入上郡取苑马”,卷69《赵充国传》(第2977页)载“上已发三辅、太常徒弛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汉代以所谓“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2]《地理志下》1644,而上郡、西河名列其中。(21)《后汉书·百官志二》:“羽林郎……掌宿卫侍从。常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补。”第3576页。甚至相马术在陕北也颇有传承,名将马援铸作铜马、为《铜马相法》,自述师承曰“近世有西河子舆,亦明相法。子舆传西河仪长孺,长孺传茂陵丁君都,君都传成纪杨子阿,臣援尝师事子阿,受相马骨法”[3]《马援列传》840。
此外,与其他地方一样,汉代陕北也逐渐开始形成大姓著族。上引画像石中如上郡奢延郭硕升、西河圜阳郭仲理、郭季妃、郭秩文、大高平令郭君、西河府史郭元通均为郭姓。见于史籍者则有列名游侠的西河郭翁中,班固誉其“虽为侠而恂恂有退让君子之风”[2]《游侠传》3705。灵帝末尚有黄巾余党郭太,“起于西河白波谷,寇太原、河东”[3]《孝灵帝纪》355。可见,两汉郭氏应为陕北大姓望族,其他如西河圜阳田氏,平周牛氏、木氏也应当盛极一时。
汉代陕北人的形象也值得关注。画像石中官吏、贵族等上层人士一般戴冠,或巾帻,交领长袍宽袖,妇女衣裙曳地,门吏侍从或拥彗,或持戟,或佩剑,或捧物,或捧笏簪笔,武官冠插鶡尾。下层民众多短衣著裤,或槌髻,或散发,或巾帻,比较随意,要以便捷为原则。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妇女的发型。陕北画像石所见妇女发型,一种以田鲂墓墓门侧石所刻画的发型为代表,头上是三个高耸的发髻,呈“山”字形,该女子从其着装及有女侍者侍立的情况看,应是一位贵族妇女,发型相当讲究,似乎梳理起来也不容易,或有假发帮助定型;另一种以延家岔汉墓横楣石正中女性发型为代表,头发向后挽一个发髻垂在颈脖处,这种发型应该是一种较为休闲的风格,便于打理;出现最多、最普遍的发型则是垂髾髻。垂髾髻就是发髻之后下垂一绺头发,西汉洛阳卜千秋墓壁画妇女已有垂髾髻发式。沈从文先生认为“这个垂髾式样,较早出现西汉时,东汉却少见,而魏晋之际在东北、西北墓画中又经常出现,成为这一时期下层妇女发式特征”[7]169(22)可参见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沈先生在分析《女史箴图》临镜化妆部分时,指出图中梳头宫女发式,于云髻峨峨后下垂一髾,这在西汉墓壁画即经常出现过,传世宋摹《列女仁智图》中也反复出现。先生所举例子,除晋《女史箴图》外,还有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壁画妇女垂髾发式、嘉峪关魏晋间墓彩绘画像砖妇女的垂髾髻以及辽阳三道壕汉墓壁画中婢女的垂髾髻。图见该书第201、203、168页。。现在根据陕北汉画像中妇女普遍梳垂髾髻的实际情况,得以对沈先生的看法做些补充。首先,垂髾髻东汉时仍在陕北普遍流行,说明这种起于西汉的妇女发式,并非东汉少见,而是一直为两汉妇女所钟爱,至少包括陕北在内的北方妇女应该一直较为青睐这种发型,甚至西王母、女娲有时也被刻画妆饰成垂髾髻(23)参见王圣序墓竖石上的西王母、大坬梁汉墓中伏羲女娲残石等。均见《绥德文库·汉画像石卷》,第141、287页。;其次,魏晋间东北西北各地重又出现这种垂髾髻,说明这种发式在北方一直流行到魏晋时期,中原地区这种发式趋于消失,则与战乱有极大关系,也有南方等地流行式样的影响;第三,从梳这种垂髾髻妇女的形象来看,并非只在下层妇女间流行,而是也包括上层妇女,正如巾帻,上至王公,下及士庶,都可以使用。
最后补充一点关于帽子的情况。陕北汉画像石中男士除了梁冠、巾帻较为普遍外,还有一种尖顶帽也非常显眼。绥德田鲂墓门左竖石就有一戴尖顶帽男子形象,绥德刘家湾一号墓、延家岔汉墓、黄家塔汉墓、王得元墓,神木大保当一号墓、二十三号墓等,也都可以看到另一种戴尖顶帽的男性人物形象,其中尤其以刘家湾一号墓前室南壁画像石的形象最为典型。其他几处图像含义不太明显,研究者有不同释读,如神木大保当一号墓,报告者认为该图是说唱图,说此人“服襜褕,戴进贤冠,手执一物作说唱状”(24)参见《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第38页。,黄家塔画像石中戴尖顶帽者,说者认为是主人在迎迓宾客,故伸手作延请状。(25)参见《绥德文库·汉画像石卷》,第279-280页。不过,刘家湾一号墓前室南壁横额显示的画面形象,与其他几处极为不同。横额右端,一戴尖顶帽者拥袖端坐,与另一位戴冠或著帻者相对而坐,两人身后各有侍者服侍左右,可见这两人身份都较高,不可能是说唱艺伎之类。该墓左竖框上格,亦是戴尖顶帽者袍服拥袖端坐,左侧有立侍者。(26)参见绥德县博物馆编:《陕西绥德汉画像石精品选集》(该选集未正式出版),第47页。据此综合分析,戴尖顶帽者应当是羌胡豪贵,这种不同于汉人冠帻的尖顶帽,应该是其民族传统服饰。尖顶帽与宽袖袍服自然地穿戴在一个人身上,为我们展示了汉代陕北因不同民族杂居共处而形成的文化融合。
汉代上郡、西河生活的官吏和民众,应当来自众多民族。尤其是羌人,在所谓的“羌乱”之前,原本就是汉朝北境的编户齐民,很多人即是所谓的六郡良家子,承担着汉朝的兵役徭役,战乱时,则被征发组成羌骑。作为汉朝的边境,陕北一直担当着“缓冲地带”的功能,这里既是政府安置内附匈奴、乌桓、鲜卑等族民众的理想地区,又是徙内郡民众实边的目的地。因此无论对内亚游牧各族来说,还是对中原农耕民众来讲,这一地区都有特殊意义,它的开放、多元因而成为了鲜明特色。观察汉晋以来的历史变迁,这一地带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