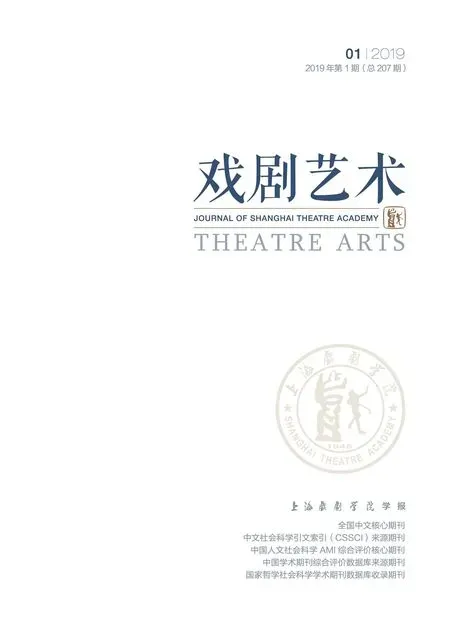从创作模式看梅兰芳与斯坦尼、布莱希特的“戏剧体系”*
2019-12-08
引 言
在中文语境中,一般来说,“戏剧创作”主要指编剧的工作;导演和演员的艺术当然也是创作,但人们往往在前面加上“二度”两个字,也就是说,第一位的还是剧本创作。这个习惯不但存在于历来以戏剧文学为基础的话剧界,现在戏曲界的人也习惯这么说了,因为我们似乎已经不再有梅兰芳那样的表演大师,可以启动并主导戏剧的“一度”创作了。
梅兰芳和话剧导表演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都是非凡的优秀演员,也都极其重视剧本的作用,他们二人代表的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戏剧创作模式。梅兰芳从演员的要求出发,组织他熟悉的编剧以他为绝对主角来打造本子——既有改编也有原创;斯坦尼则总是寻找、选择他看中的业已完成的优秀剧本——大多是角色众多的话剧,从来不突出他自己的角色——他演的也未必都是主角,有时候他干脆只导不演。
在梅兰芳始于演员的模式和斯坦尼始于剧本的模式之间,布莱希特代表了又一种模式——剧本始于编、导合一的创意,再由编剧亲自导演,成为有详细排练记录(model book)的“范本”演出。可惜这一模式并未能通过足够的排演实践来发展、落实。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时值创作力最盛时期的布莱希特失去了实践基地,被迫辗转各国避难,在美国的九年最长,但也一直没有自己的剧团来实践他的导表演理念,只能写下剧本存着。他1949年回国,名义上有了柏林剧团,但事实上又等了五年,直到他人生的最后两年,才得以在健全的剧团里把剧本搬上舞台,给后人留下了好几个他称为“范本”的演出。不过他独特的表演理论并没能在其中充分体现出来,留下的反而是无数对其表演理论的问号。因此,布莱希特理想的以导演为中心的模式总体上还是落入了斯坦尼那样的从剧本出发的西方主流模式。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斯坦尼对世界戏剧及影视的最大贡献是,通过40年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总结,开发出了最科学、最实用,因而影响最大的表演方法和相应的演员训练方法,这是在他和聂米洛维奇-丹钦柯1898年那个著名的18小时会面以后正式开始的。那次会谈决定了两件具体的事:合作成立莫斯科艺术剧院,排演契诃夫的剧作《海鸥》;从长远看,那次会谈还预示了斯坦尼表演体系的开端,因为斯氏体系就是以《海鸥》那样的优秀文学剧本为基础的。会谈时斯坦尼对《海鸥》还不是十分熟悉,只知道它不久前刚在圣彼得堡皇家剧院首演失败,但他坚信好的表演必须建立在好剧本、好角色的基础上,而且他相信丹钦柯的文学眼光和对《海鸥》的大力推荐,相信契诃夫塑造的人物一定能立在舞台上。可是会谈后读了剧本他却为难了,剧中人物缺乏传统戏剧中必需的明显的行动——难怪皇家剧院的职业演员演出失败了。这个戏要排好,必须找到新的排练方法——关键不在演员技能的高低,而在对剧本的深刻理解。他想出了一个奇特的方法,自己当“案头导演”,关起门来仔细研读剧本,把所有导演指示写成笔记画成图,让专用“快递”每天来回穿梭,交给排练场上的丹钦柯,由他对演员执行这些导演指示。这恐怕是导演史上空前绝后的案例。一般认为丹钦柯长于文学而非表演,身为演员的斯坦尼当然最懂表演,但他们的第一次合作却刻意颠倒了角色。斯坦尼下决心弄懂他本来不很熟悉的契诃夫剧本,绝不用以前驾轻就熟的表演套路来绕过剧本中的难题——圣彼得堡演员的失败已证明这条“捷径”走不通;他也决定要排除排练中演员的问题和疑虑可能对他产生的干扰,干脆把自己和演员隔绝开来。[注]见David Richard Jones: Great Directors at Work: Stanislavsky, Brecht, Kazan, Brook(第一章).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海鸥》演出的巨大成功证明,他这个集中精力研读剧本的方法成功了,他也对自己解读艰深剧本的能力有了自信,以后没再采用这样的极端方法,但总是根据剧本的需要来决定导演措施。1902年下半年他导演高尔基的《底层》,事先做了很多功课,请丹钦科分析剧本的内容,也请高尔基告诉他“剧本是怎样写出来的,以什么人做模特儿,他谈到自己的流浪生活,自己的遭遇,也谈到剧中人的原型,特别是沙金一角。”[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第一卷·我的艺术生活》,司徒敏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第301页。但演员不熟悉剧中的底层人物,心里还是没底。“这些分析式的讨论还不够,他(斯坦尼)需要活的模特儿来激发他的想象力。8月22号晚上,他带着剧组走访了希特罗夫市场。那里聚集的流浪汉和惯偷们见到艺术家大喜过望。”[注]Jean Benedetti: Stanislavski, a Bi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1990. P. 122.几杯酒下肚,流浪汉们说出很多故事,斯坦尼也找到了他要演的沙金的模特儿——一个因赌博而败光了家产的前禁卫军军官,虽然衣衫褴褛,却保持着完美的仪态。斯坦尼让舞美设计西莫夫当场画了很多速写,让大家回去后对着这些形象反复练习。
同年斯坦尼还导演了托尔斯泰的《黑暗的势力》,“为了研究农村生活,我们特地跑到剧情发生的地点——都拉省去。我们在那里住了住了整整两个星期,访问了附近的一些村庄。……我们还带回来一个老农夫和一个老农妇,作为‘蓝本’。”老农妇很快记熟了台词,在一个演员生病时代她参加排练。“这位农村老婆婆的即兴表演简直引起了一场轰动。是她第一次在舞台上表现了真正的农村,表现了真正的精神上的黑暗和它的势力……我们不禁毛骨悚然。” 托尔斯泰的儿子看了建议就请她来演,斯坦尼试了一下,但最后没让她演,因为她会“丢开托尔斯泰的台词,自己编一套,里面充满了极其难听的粗话”[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第一卷·我的艺术生活》,司徒敏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第306-307页。,反而背离了剧本。
斯坦尼根据剧本要求带领演员“下生活”,主要是在演员的外部形象上下功夫;而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些剧本的启发下,第一次发现了话剧演员十分需要但多半不懂、不会的本领——找到角色的台词下面深藏不露的内部行动。契诃夫和高尔基的剧本大多缺乏明确的外部行动。焦菊隐说在契诃夫的剧作里,“有些人物只说了半句话,便不肯再说下去;有些人物絮絮叨叨地发着大段的议论,可又没有一句碰着边际的,……我们假如实地观察一下看自己生活的周围,就能发现同样的现象。……唯有契诃夫第一个把这个重大的现象指给我们,我们才在他的剧本中,发现那些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地方”[注]焦菊隐: 《〈樱桃园〉译后记》,《戏剧艺术》,1980年第3期。。 小说里这样的人物不少,19世纪俄国小说中尤其多,但舞台上还是第一次大量出现;所以契诃夫在《海鸥》首演失败后怀疑自己并不适合写剧本,已经准备不再写。以前的戏剧中很少看到这样的人物,这并不是偶然的;一般演员不知道怎么演缺乏明显外部行动的角色,或者演了观众也不要看——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全看导演能不能读懂剧本,再教演员方法,让他在舞台上“活”起来。斯坦尼被契诃夫反常的剧本逼得下苦功反复细读,终于在剧本平静的表面底下找到了隐藏的内部行动。例如,《海鸥》男主角特里勃烈夫似乎只会怨天尤人一事无成,但事实上他写剧本请妮娜演出,就是在积极地向身为演员的母亲证明自己的才能,他那些仿佛消极的牢骚也恰恰说明他心里多么想要取悦母亲。演员必须抓住这样的心理动机,才能演好契诃夫那些表面上缺乏行动的“多余的人”。
斯坦尼在“絮絮叨叨不着边际”的角色中发现了潜在的内心动作,这个本领比众所周知的“从自我出发进入角色”更难得,注意到他这一成就的人也少得多。梅兰芳说:“我在舞台上一生所体会的,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也是相通的”[注]《梅兰芳戏剧散论》,第204页。,他们的“相通”仿佛就是在演员要像角色一样“走心”,这只是个比较常见的共同点;从另一角度看,这两位大师各有一个独特的表演方法,其背后的思路更是出奇地相像。斯坦尼在看似消极被动的角色心中找到强烈的内部行动,这跟梅兰芳把看似只是优美舞姿的“卧鱼”程式解释为屈身下腰去“闻花”异曲同工,都是用合理的心理逻辑来解释一般人眼里空洞的舞台形象,使其变得丰富起来,让演员能内心充实地演绎好这些形象。梅兰芳在谈《贵妃醉酒》中闻花的“卧鱼”时说:“要点是在当时我的心中、目中都有那朵花(其实台上空无一物),这样才会给观众一种真实的感觉。”[注]《梅兰芳戏剧散论》,第36页。而斯坦尼也强调,要点是演员心中要明确角色每句话、每个动作的内在目的。
除此之外,斯坦尼还发明了情绪记忆、感官记忆等话剧、影视演员需要掌握的体验角色并体现出来的方法,这也都是他在仔细分析了许多剧本的规定情境以后,为了帮助演员真实地塑造剧中人物而发明的。斯坦尼认为导演要为演员当好“媒人”,也就是帮助演员和剧中人融为一体。在聚焦于演员塑造人物的内部技巧并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以后,后期他又把注意力转向“形体行动分析方法”,其实也是一系列为演员和剧本角色牵线搭桥的技巧:导演引导着演员和角色初次见面,不断磨合,包括在形体动作中分析角色,用即兴小品来走进角色的内心等等,最后使二者融合,形成舞台形象。
布莱希特
布莱希特的创作生涯也是始于剧本。他年轻时最早写的是表现主义的剧本如《巴尔》《半夜鼓声》《城市丛林》等,在导演方面有些特殊的要求,但那时候他还只是初露头角的编剧和戏剧顾问(dramaturge),还没能独立当导演。1929年他发明了篇幅短小、技术要求也简单得多的“教育性短剧”(Lehrstucke, didactic pieces),成了编导合一的全才戏剧家。由于剧本的故事内容简明扼要,戏的特色主要体现在独特的、辩证的导演构思上。《措施》(The Measures Taken)就是这样一部最具布莱希特特色的“教育性短剧”,它的序幕是:一个五人小组被共产国际从莫斯科派去中国帮助革命,回来后向组织报告情况,组织要他们用动作呈现出他们在中国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来个“戏中戏”。这里的难题是,五个人只回来了四个,那没回来的人竟是被这四人处死的。为什么处死那位“年轻同志”就成了这四个人要用行动来解释的关键。谁来演这个已经不在的“年轻同志”呢?这是导演的最大难点,也是最大的亮点。剧作家布莱希特在舞台指示中已经为导演设计好了“措施”:由四个人轮流在闪回式的片段中扮演那被他们处死的第五个人——每人只需换一个简单的符号化服饰就瞬间变成那个“年轻同志”。这个戏在1930年的柏林首演被特地处理成了一个音乐会版,四个演员唱着歌跳进跳出——好像中国的曲艺表演,或者以戏曲清唱为主的堂会表演。
布莱希特理想的表演需要制造Verfremdung Effekt,也就是陌生化效果,这个词更多人译为“间离效果”,但更容易有歧义。他这个理论挑战了2500年来人们普遍接受了的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和“真实”观,也和绝大多数话剧演员的感性经验相悖,很少有演员主动接受的,更多的人则因为概念解释不清而造成困惑。布莱希特在莫斯科看了梅兰芳的表演后写了《中国戏曲中的“陌生化效果”》一文,其实误读了梅兰芳的表演;中国表演艺术中真正接近布莱希特理想的是跳进跳出的曲艺,可惜他从未见过。但是布莱希特有一篇很好的文章解释他想要的“陌生化表演”,题目叫《街景》,文中他以街上常看到的交通事故及其后的争执为例:出事的人事后向警察和路人演示刚刚发生事故的场景,这样的表演是不会投入感情的,相反必须理性地从他自己的角度对刚才的“街景”做出图解,目的是要让警察看了接受他的再现和解释。《措施》里设计的“戏中戏”是体现“街景”式表演的最好例证,那四位刚杀死“年轻同志”的报告者绝不能把他演得令人同情——因为那就会证明他们杀错了;相反他们要理性地演出被杀者的错误,要演出他的不顾大局,要演出他的情绪冲动如何危害了集体,让组织看了产生“陌生化效果”,批评那位已经死去的同志,追认他们四个人已然执行了的措施——处死他。
《措施》的剧本极有特色,也完全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新奇的导演手法才写出来的;如果从评价传统剧本的角度来看,它的主题、情节、人物、语言都并不特别出色(至今中国大陆还没有中译本),但却是最能代表布莱希特导表演风格的戏——没有之一。他还有其他一些充满辩证精神的教育性短剧,如《说是的人·说不的人》也是这样。可惜的是,那些戏的剧本过于简单了些,在对他的导表演风格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的情况下,翻译过来好像也没有太大意义,因此布莱希特的这些最有特色的戏在中国还没有多少影响。关键是他自己也没能继续把教育性短剧进一步发展成更为成熟的戏剧品种。
二战期间他被迫流亡出国,没了自己的剧团和演员,就没法再做导表演方面的实验。他夫人海伦·魏格尔是位优秀的演员,1933到1948年整整15年里没演过一个专业的戏;好在布莱希特是作家,一个人也可以写诗写剧本。后来成为布氏经典的一系列大戏如《伽利略》《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阑记》等就是那些年里写的。这当然也是国际剧坛的幸事,但与此同时,布莱希特本来已经开始探索的以导演构思为出发点的戏剧创作模式就中断了。他1949年回到东德,政府专门给他建立了由魏格尔负责的柏林剧团,但因为战后百废待兴,剧团头几年还未能正常运作,直到1954年才出现柏林剧团推出的正式演出。[注]根据John Willet的The Theatre of Bertolt Brecht,我原以为布莱希特1949年一回国就在柏林剧团排戏了。2018年10月17日,国际戏剧协会演艺高校联盟在上海开研讨会,来自柏林的国际剧协“世界戏剧培训学院”课程主任Christine Schmalor告诉我,布莱希特去世前只有一两年时间排演他的戏。此说显然与John Willet的书有矛盾。五天后我在北京参加梅兰芳纪念馆主办的“东方与西方——梅兰芳、斯坦尼与布莱希特国际学术研讨会”,求教于布莱希特专家、中央戏剧学院前副院长丁扬忠教授,他告诉我他1950年代中期在东德留学时了解的上述情况。他在人生的最后两年里日以继夜,抓紧把以前攒下的大型剧本在舞台上竖起来,还要助手把主要剧目的排练过程都详细记录下来,称之为“范本书”(model book)。他一直健康不佳,很可能意识到时日无多,必须及时留下遗产;他还多次带团出国演出,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然而这些声誉更多地还是来自严谨的剧本和导演,而不是他年轻时那种真正在观众中创造了“陌生化效果”的最有特色的布氏戏剧。那两年高强度的经典打造和国际推介也透支了他的精力,1956年他才58岁就英年早逝,留下了一系列“博物馆”式的剧目。1986年在名为“布莱希特:30年之后”的多伦多研讨会上,我看到柏林剧团带去的《高加索灰阑记》,就是这样保留下来的四平八稳的高台经典,已很难看到当年的“教育性短剧”中充溢的质疑世界、变革世界的锐气。后来又看过不少这部戏的不同演出,我自己也导演过两次,发现这个戏表达主题的方式已经与《措施》的辩证法南辕北辙,成了简单说教式的——干脆让说书人直截了当说出主题:“一切应该归善待他的人。”而女主人公格鲁莎则是一个传统的可以催人泪下的“好女人”——事实上我的两次导演经历都让我确信,在多数情况下,布莱希特打破第四堵墙的所谓“间离效果”其实是角色向观众交心的“连接效果”。[注]孙惠柱:《从“间离效果”到“连接效果”:布莱希特理论与中国戏曲的跨文化实验》,《戏剧艺术》,2010年第6期。
布莱希特后期的经典大戏中唯一真正实现了他“非亚里士多德式”理想的例外是《四川好人》(写于1939年,早于《高加索灰阑记》)。该剧是辩证剧《措施》的“大戏版”,舞台指示规定,演到最后演员要走向观众,坦承不满意戏的结局,但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只好请大家帮忙出主意。这是个刺激观众采取行动的极妙的编剧、导演相结合的方法,只是由于剧中提出的好人坏人、生财散财的人生哲理问题太深刻、太难回答,从1940年代首演至今,还没听说有哪个演出的观众当场提出过什么修改结局的好建议。纵观布莱希特的整个职业生涯,他自己并没能实现要刺激观众看戏以后站起来质疑、挑战世界的理想,这个任务只能留给巴西的导演兼社会活动家奥古斯托·伯奥(1931-2009)来完成了。伯奥发明的论坛戏剧继承但又发展了布莱希特的理念,跟布氏早期的教育性短剧有点相似,也只做短剧;他的短剧还回避了《措施》和《四川好人》中那样太深的哲理问题,只提出特定社群的具体问题,力图在演出和“观演者”参与的过程中当场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这就使得论坛戏剧不再是作为艺术的戏剧,而更像一种社会或政治活动,不大可能留下任何经典剧本。相比之下,布莱希特毕竟还是个艺术家,他留下的主要还是剧本和诗歌——在米切尔·霍夫曼编选的《二十世纪德语诗选》中,入选最多的就是他的诗,多达15首。[注]王家新:《重新发现布莱希特的诗》,《文学报》,2018年9月27日。有这么多诗和剧作传世,布莱希特不愧为一位大作家,但他的戏剧创作最终还是没能真正突破导演斯坦尼从剧本出发的西方传统模式——也就是他自己在理论上坚决反对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剧本戏剧模式。
梅兰芳
梅兰芳所代表的体系就完全不一样了,他理想的创作模式不是从剧本出发,而是从他自己作为演员的视界(vision)和需要出发的。因此,在他声名远扬的20世纪前期,中国的现代文学家对他大多持尖锐批评的态度。鲁迅的抨击也许是最著名的,但还不是最激烈的,文学史家郑振铎写了分贝更高得多的《打倒旦角的代表人物梅兰芳》,开宗明义便宣称:
我们要提倡真正的艺术便不得不对于虚伪的艺术下攻击,虚伪的艺术不消灭,真正的艺术是不会有成功的可能的。……中国舞台技术的如何幼稚,剧本的如何不合理,化装与脸谱的如何无根可笑,锣鼓喧天的如何震撼人耳脑。演武戏时,强迫童伶表演激烈动作的如何非人道,卖艺者与演戏者联合的如何荒唐,件件事都足耐我们的仔细讨论与反对。然而最使我们引起恶感的却是所谓男扮的旦角——一种残酷的非人的矫揉做作的最卑下的把戏。[注]西源:《打倒旦角的代表人物梅兰芳》,《文学周报》(第8卷),1929年,第62-63页。
欣赏、褒扬梅兰芳的有完全不一样的两拨人——国内的国粹派和外国的梅粉丝,但与批评者相同的是,他们也都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在表演上——外国人还特别喜欢梅兰芳的男扮女装。他们对剧本的特点都没有太关心——或者是默认剧本不怎么样,或者认为剧本就是不好也与他这个演员无关。前一种看法确实不容易辩驳,如果和斯坦尼演绎的契诃夫、易卜生、莎士比亚等人的剧本以及布莱希特自编自导的剧本相比,梅兰芳演的大多数剧本确实要弱很多;他那些文字篇幅很短、全剧角色很少、以歌舞为主的折子戏,也许根本就不应该跟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的西方戏剧文学经典放在一起去比。不过,第二个看法就大可商榷了,因为梅兰芳与他演的剧本不但有很大的关系,而且是一种西方人难以想象的决定性的关系。相比较而言,斯坦尼与剧本的关系体现在他选剧本来导演和表演——都是别人已经写好的剧本;布莱希特倒是简单,自己写剧本,还亲自导演,但他自己从来不演,也不能阻止别人导他的剧本,因此他并不能完全控制他的戏最后的舞台形象;梅兰芳自己一般不写剧本(只与人合写过一个《邓霞姑》),他有一群“御用”的“梅党”成员帮他写、帮他改、帮他一起排,而他的戏的舞台形象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全面掌控的。
很难说梅兰芳演的每个剧本都体现了他的审美理想,在他尚未成名、尚未有梅党相助的时候,只能用现成的未必理想的剧本稍加修改进行舞台演绎。一旦找到了在戏剧观上投缘的合作伙伴群,他就开始了全新的戏剧创作模式。和他合作最多的齐如山在其回忆录中有《编戏》一章:“说到我帮梅兰芳的忙这一层,虽然不敢说全国皆知,但知道的人确是很多。……实实在在我也帮了他二十多年……所以帮他忙之动机,则确是为的编戏。”[注]《齐如山回忆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04页。在给梅兰芳打本子之前,齐如山还只是个编剧新手,在欧洲看了不少戏,想给国人编点新戏,但在遇到合适的演员之前,他编的几个戏都没能演出。他这才明白:“一个脚色想排一出新戏,则该脚必须是该班的主脚,否则便不易排。”[注]同上,第105页。后来他发现了新星梅兰芳,但并没有一开始就给他写剧本,“因为从前编了戏找人排吃过碰,所以以后不肯轻易提到编戏,而且也不知道他排新戏的能力如何”。[注]同上,第114页。他通过写评论其表演的长信来与他沟通,梅兰芳也虚心地接受了他的修改意见,无形中把他当成了一个“案头导演”。他们通了两年信,发现艺术理念十分接近,这才见面;又交往一年后,才谈到编戏之事。其实梅兰芳急切地需要新戏,因为他的竞争对手排出了新戏,“戏虽没有什么价值,但北京人没见过,大受欢迎;兰芳之班大受影响,叫座之力不及人家。兰芳此时已知,不排新戏,不能与人竞争,”[注]同上,第115页。因此他对齐如山是求贤若渴。齐如山还是很谨慎,一开始并没有给梅兰芳编他在欧洲看戏时就开始酝酿的新派“神话戏及清高的言情戏”,而是先编一出旧式的戏《牢狱鸳鸯》试试;尽管编得很平常,演出后却是人山人海。这说明对当时的京剧观众来说,剧本最重要的是,在故事基本合理、主题符合常理、又有一定新意的基础上,给主角演员提供充分发挥其表演才能的机会。
那以后,为了在中秋节的档期用新戏胜过竞争对手,齐如山实现了他多年的梦想,为梅兰芳编了神话剧《嫦娥奔月》,“大受欢迎,大家都叹为得未曾有,连演了四天,天天满座……把第一舞台之《天香庆节》打了个稀溜花拉。”[注]同上,第118页。齐如山在回忆录里对自己的成就多少有些夸张,其实为梅兰芳编剧的并不只他一个人,他主要是出构思写提纲,身边还有一批梅党合作者,包括擅写台词唱词的李释戡等,都是些既有学问又熟悉戏曲表演的文化人,他们分工合作,把戏曲史、舞蹈史、文学史的知识都用到剧本、服装设计、动作编排中去,为众多既留恋传统国粹的程式歌舞、又渴望舞台上有点新形象的艺人和观众竭诚服务。他们很快又为梅兰芳编了《洛神》《天女散花》《太真外传》等剧本,这一系列戏突出了梅兰芳擅长的舞蹈才能,奠定了他的超级明星地位,还把京剧历来以听老生唱为主的“卖点”转到了载歌载舞上来。也正是这些神话戏引起了鲁迅、郑振铎等新文化人的不满。鲁迅这样写道:
梅兰芳……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注]鲁迅:《花边文学》,《鲁迅全集》(第五卷),台北:谷风出版社,1989年,第 596-597页。
鲁迅对梅兰芳崇“雅”的批评其实并不准确。梅兰芳的拥趸中固然有不少文人士大夫,但平民观众也是不少的。他不可能只在士大夫的堂会演出,一定要去戏院,而戏院不可能只出售座好价贵的票子,梅兰芳的戏便宜票也很热门。刘祯在一篇关于欧洲人看梅兰芳的文章里综合了外国人和中国人对戏院的描述:
格里格具有西方人的幽默感,却看到了中国剧场文化的特征。“一颗白色的彗星突然从我们头顶上呼啸飞过”的,是一块看客所需要的毛巾,描写的何其生动,又何其诙谐!这成为中国剧场的一景,当时就曾有许多外国人评价“中国戏不但舞台上的伶人能演,就连满园里茶役们也都能打出手呢”。喝茶、嗑瓜子、抽烟、扔毛巾、小买小卖、喧闹、杂乱等,在格里格的笔下,被描写的“彗星呼啸飞过”,徐慕云曾批评这种剧场现象是“楼上楼下满园手巾把子飞舞的怪状”,历来遭到知识精英的诟病,但同时他们却也忽略了它与中国戏曲演出与生俱来的源生性,以及剧场演出的生态文化,民众对其文化的认知、选择与参与。[注]刘祯:《格里格——“北欧的斯诺”及其眼里的梅兰芳与中国戏曲》,《艺术百家》,2017第6期。
可见,梅兰芳演戏的地方并不见得就是鲁迅所批评的“紫檀架子上”的“玻璃罩”,甚至比现在有些“大排档”还要“接地气”,梅兰芳是一位广受大众欢迎、雅俗共赏的京剧演员。但上面鲁迅引文中间的那两句话却是极其精准和关键的:“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这就是梅兰芳体系不同于斯坦尼、布莱希特的最大特点。梅兰芳纪念馆的俞丽伟博士专门研究了梅兰芳演出剧本的创作由来,她总结道:
由梅党担任编剧的古装新戏为13部。分别为《嫦娥奔月》《天女散花》《麻姑献寿》《上元夫人》(前、后部)、《霸王别姬》《西施》《洛神》《廉锦枫》《太真外传》(一、二、三、四本)、《春灯谜》、红楼戏《黛玉葬花》《千金一笑》《俊袭人》。其中《嫦娥奔月》是由李释戡提议七月七应节戏选题,齐如山根据《淮南子》《搜神记》打提纲,李释戡编写剧本,其他人斟酌修改。《天女散花》的创意来自梅兰芳观摩友人的仕女画《散花图》,由齐如山起草提纲,填词是李释戡、王又默,梅兰芳表叔陈嘉梁制谱并整理工尺。……梅党集体编剧的古装新戏多取材于小说、传奇、汉赋,也有如《天女散花》发源于绘画,偏向于神话女性人物、妃子、红楼女性题材的古装歌舞剧。梅党编写的古装新戏在梅兰芳新戏剧目中占有较高比重,也是剧本选材视角、文学性、戏剧性整体质量较高的剧目类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剧本提升了民国时期京剧文学的内涵,是文人参与京剧剧本创作的有益探索。
由梅党改编的老剧目新戏为3部。分别为《凤还巢》《抗金兵》《生死恨》。……《抗金兵》是梅兰芳拟创作抗敌主题戏,由叶玉甫提议梁红玉故事,梅兰芳受启发借鉴传统剧《娘子军》“梁红玉擂鼓战金山”,戏名由叶玉甫定为《抗金兵》,并由叶搜集资料,在梅党集体编写原则下完成初稿。[注]俞丽伟尚未发表的中国传媒大学2018年博士论文:《梅兰芳演出剧目的生成与递嬗》,特此致谢。
从这三位大师和剧本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在斯坦尼、布莱希特和梅兰芳代表的三个体系中,严格地说,只有梅兰芳的才是完整的“戏剧体系”,因为只有他才主导了从最初的构思编剧一直到最终的舞台呈现的全部创作过程。相比之下,斯坦尼代表的是一个伟大的导演、表演体系——对之前的剧本创作产生不了影响;而布莱希特的则主要是一个编剧、导演的体系——他的表演理念更多地是呈现在纸上而不是舞台上,并没能在他主导剧团排戏的最后两年里全面付诸实践。只有梅兰芳的体系才是涵盖了编剧、导演、表演整个创作过程的全面的“戏剧体系”。梅兰芳为人低调谦逊——仿佛和齐如山刚好相反,梅兰芳在描述他的剧本创作流程时,还特意淡化了他自己的作用:
我排新戏的步骤,向来先由几位爱好戏剧的外界朋友,随时留意把比较有点意义,可以编制剧本的材料,收集好了。再由一位担任起草,分场打提纲,先大略的写了出来,然后大家再来共同商讨。有的对于音韵方面是擅长的,有的熟悉戏里的关子和穿插,能在新戏里善于采用老戏的优点的,有的对于服装的设计,颜色的配合,道具的式样这几方面,都能推陈出新,长于变化的;我们是用集体编制的方法来完成这一个试探性的工作的。我们那时在一个新剧本起草以后,讨论的情形,倒有点像现在的座谈会。在座的都可以发表意见,而且常常会很不客气的激辩起来,有时还会争论得面红耳赤。可是他们没有丝毫成见,都是为了想要找出一个最后的真理来搞好这出新的剧本。经过这样几次的修改,应该加的也添上了,应该减的也勾掉了。这才算是我初次演出以前的一个暂时的定本。演出以后,陆续还要修改。同时我们也约请许多为本界有经验的老前辈来参加讨论,得着他们不少宝贵的意见。[注]梅兰芳口述,许姬传、许源来、朱家溍整理:《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回忆录》(上),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236-237页。
大家都知道,这个“集体编制”的核心绝对就是梅兰芳,所有关于剧本的“讨论”“激辩”都是围绕着如何让他做出最好的舞台呈现。这样的编、导、演一体化有什么好处呢?梅兰芳说:“剧本从执笔者在辛勤伏案的构思中写好后,由登场演员在观众面前表演出来,经过不断演出,不断修改,有的得到观众拥护,成为保留剧目,有的因为不受欢迎就束之高阁,无人问津。这里的甘苦得失,只有身历其境的‘案头人与场上人’才说得清楚。”[注]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第425页。比起编剧和导演,演员每次演出必须身临现场,用心的演员最能亲身体会观众的各种反应。在梅兰芳成名的年代,没有任何政府或基金会的赞助,戏剧人必须悉心体察买票观众的心理,但又不能降低身份媚俗讨好——那会开罪品位高雅的人士,还很可能被政府以“有伤风化”为名禁掉。在社会上还存在大量文盲的年代里,中国的民众一向还有到戏院长点知识、接受点高台教化的习惯和期待,戏剧人必须把握好教化和娱乐之间极为微妙的度;因此,由梅兰芳这样悟性极高的一线演员来策划主导戏剧创作的全过程,很可能是那个时期大众戏剧发展的最佳道路。
由演员主导策划创作剧本,是不是会产生郑振铎所说的“剧本不合理”的问题呢?这个问题确实大量存在,但主要是由于多数剧班的当家演员不像梅兰芳,他们找不到齐如山、李释戡那样的好编剧,剧本只能凑合,就容易出各种问题。如果说即便是梅兰芳、齐如山、李释戡的文学水平还是比契诃夫和布莱希特差远了,那就有点脱离艺术家的文化语境了。当然,演员梅兰芳年轻时学养水平确实还有限,他对剧本内容的要求很朴素:“有人说小说里的故事,都是作者杜撰的、不可考的,这一点我觉得倒没有多大关系。只要故事生动,合乎情理,能对群众起教育作用,或者虽然没有积极的教育意义,却也并无毒素,又能给观众欣赏上的满足的,这些都可以拿出来上演。”[注]梅兰芳口述,许姬传、许源来、朱家溍整理,《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回忆录》(上),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266-267页。这标准显然并不怎么高,然而,他的剧本比起当时大部分戏曲剧本,已经有了明显的高度。就拿鲁迅批评的《嫦娥奔月》来看,本来这只是一出为中秋节而编的应景戏,故事的依据只有《淮南子·览冥篇》里的一行字:“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但在梅兰芳演的剧中,“嫦娥当作后羿的妻子,偷吃了她丈夫的灵药,等后羿向她索讨葫芦里的仙丹,她拿不出来,后羿发怒要打她,她就逃入月宫”,[注]同上,第258页。这样她就成了一个因被丈夫欺负而逃离家庭的女性——简直有点像一个神话版的“娜拉”,只是她逃上了月亮以后不免又感到了孤寂——这也十分真实可信。
梅兰芳的《贵妃醉酒》也经过了类似的脱胎换骨的改造,他把杨贵妃重新刻画成了一个受压迫的女性:
《醉酒》既然重在做工表情,一般演员,就在贵妃的酒话醉态上面,做过了头。不免走上淫荡的路子,把一出暴露宫廷里被压迫的女性的内心感情的舞蹈好戏,变成了黄色的了。这实在是大大的一个损失。……我历年演唱《醉酒》就对这一方面,陆续加以冲淡,可是还不够理想。前年我在北京费了几夜工夫,把唱词念白彻底改正过来。又跟萧长华、姜妙香二位,细细研究了贵妃醉酒之后,对高、裴二卿所作的几个姿态,从原来不正常的情况下改为合理的发展。京津沪三处的观众看了我这样表演,似乎都很满意。……凭着我自己这一点粗浅的理解,不敢说把它完全改好了。应该写出来让大家更深切地来研究,才能做到尽善尽美的境界。[注]同上,第228页。
梅兰芳的文学理念日渐成熟后,却因迁居上海而与合作了20年的齐如山分手了,再以后是抗战期间的“蓄须明志”。尽管如此,他一生中最后的大戏《穆桂英挂帅》(1959年)还是可以看作他主导创作的文学性较高的成功之作。虽然那是从豫剧移植过来的,并非原创剧本;但西方的希腊悲剧和莎剧以及梅兰芳自己早期的改编早已证明,是否“原创故事”绝不应是评判经典的标准。那时梅兰芳已经65岁高龄,因戏曲行当所限并不能像话剧影视演员那样改演老旦角色,因此最好是演一个年纪长了几岁的原有行当角色——例如一个年长的穆桂英。但当时京剧中并没有那样的戏,而梅兰芳在豫剧里看到了,于是就组织班子,根据京剧特点移植剧本,推上舞台,为梅兰芳的晚年艺术生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梅兰芳戏剧体系代表的是中国戏曲文化中极为出色的一套创作方法,像这样由名角演员策划主导剧本创作、然后自己担纲主演的案例在其他名演员当家的剧团里也很常见。一个突出的好例就是程砚秋请翁偶虹写《锁麟囊》。他俩见面之前程砚秋已看过几个翁的剧本的演出,但他约翁写的第一个剧本《瓮头春》并没上演,因为他的朋友们觉得剧本虽好,但他悲剧演太多了,最好换一下风格,演个喜剧。他请翁到家来,本来说是谈《瓮头春》的演出计划,不料二人缄默地对坐了约十余分钟,程砚秋才不好意思地开口:“……能不能排一出适合我演出的喜剧?您说好吗?”翁偶虹有点担心“只怕材料不太现成”,程砚秋立刻取出一本焦循的《剧说》,翻开夹着书签的一页给翁看,他说看到书里《只麈谭》的“赠囊”故事,觉得可以编成戏。翁在回忆中写道:“文字极短,瞬即看完,我未加思索,答以可为。程先生似乎更兴奋地拱手一揖,含笑相视。这时,恰巧又有客人来访,我即告辞,在回家的途中就开始回味这个素材,考虑如何将它写成一出适合程派排演的喜剧。”[注]翁偶虹:《为程砚秋先生写〈锁麟囊〉》,《文汇报》,2018年9月6日。《剧说》里的素材只是个故事轮廓,连具体人名都没有;翁偶虹做了大量功课,融入山东民俗,取名《锁麟囊》。程砚秋读了剧本初稿后,提出不少修改意见。“程先生的建议,不仅生动地说明了场上的表演,更大可升华剧本,深化人物,我欣然接受,遵意照办。”这样互动多次以后,《锁麟囊》1940年4月成功首演。
以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在当今的戏曲演员中,最接近我想象中梅兰芳那辈大师水平的是张火丁——我生已晚,未能亲眼欣赏老一辈大师的表演;看到张火丁,一下明白了为什么当年会有那么多人迷梅兰芳、程砚秋。很难用理性的文字来描述她的表演究竟高明在何处,但就是耐看耐听,魅力无穷。而最能让张火丁展现魅力的剧目,就是当年程砚秋在编剧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命题作文”激出来的《锁麟囊》。现在众多指导剧本创作的领导和专家们如果能有演员程砚秋那样的策划和约稿水平,我们的戏剧想来可以繁荣很多。
结 语
梅兰芳体系的特色并不仅仅体现在其表演技巧和表演美学方面的博大精深,同样值得深入研究的是,梅兰芳和他的同侪们从表演出发进行编剧策划以及反复排演修改的总体戏剧创作模式——说不定这是一个世界上唯一有据可证的真正全方位的戏剧体系。纵览创作所涵盖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梅兰芳超过了与他同时代的那两位欧洲戏剧大师,因为他们分别只专注于导演、表演和编剧、导演。斯坦尼的导表演只能是编剧完成以后的“二度创作”,布莱希特虽然身兼编剧、导演二职,但他对表演的出格要求在他自己的大部分戏里也难以真正实现,更不用说大量的布氏剧本是别人导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梅兰芳的理论著作过于朴实、略显单薄,就觉得要在两位西方大师的“导表演体系”和“编导体系”面前自惭形秽,以致都不敢将梅兰芳的全套遗产称为“体系”。
有人说,“体系”一词只能是斯坦尼独享的概念,别人都够不上;因为国际上极少见到其他戏剧大师的遗产被冠以“体系”之名,就连汗牛充栋的布莱希特研究中也很难找到“体系”的说法。此话不假。但是,这背后的原因却跟三位大师的成就高低没有关系,而主要是由于不同的语言文化习惯造成的问题。“体系”本来也不是中文里常见的名词,是1950年代全国学苏联、学俄文时才热起来的。苏联人喜欢宏大的概念,斯坦尼的那套方法和理念就是“斯坦尼体系”;而主导了英语世界话语权的美国人不太喜欢这样的大概念,虽然他们通过好莱坞电影无形中向全世界介绍了斯坦尼这套最实用的表演方法,但总觉得“体系”(system)这个词跟“制度”一样,带了点强迫的意思,于是宁可换用一个低调的词“方法”,只不过在前面加个冠词,再用上大写,叫the Method,以区别于其他各种各样的方法。所以,在英文世界的戏剧话语中,别说梅兰芳和布莱希特,就连最早被尊为拥有体系的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被剥夺了“体系”的地位。难道我们也一定要去学美国人,认为谁都不配有体系吗?
其实重要的不是辩论应该给这几位戏剧家贴上什么“级别”的标签——是“体系”还是“方法”还是“流派”;重要的是对他们艺术创作的总体特点进行仔细深入的研究。三位大师都有相当长的艺术生涯。其中布莱希特受战乱影响最大,寿也最短,58岁就去世了,但他还是留下了大量的剧本、论文和好几个“范本”演出;最高寿的斯坦尼享年75岁,如果不算以前的业余演剧,就从他1898年排《海鸥》起到1938年逝世,他用了整整40年探索、记录他的体系;梅兰芳写有两本《舞台生活四十年》,其实从他1904年首次登台演戏到1961年67岁逝世前两个多月的最后一次演出(《穆桂英挂帅》),足有50多年舞台生涯,也留下了大量的剧目和文字,还有很多录音和录像。要比较他们三个人整体戏剧创作模式的异同,这篇文章的研究只是刚刚开了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