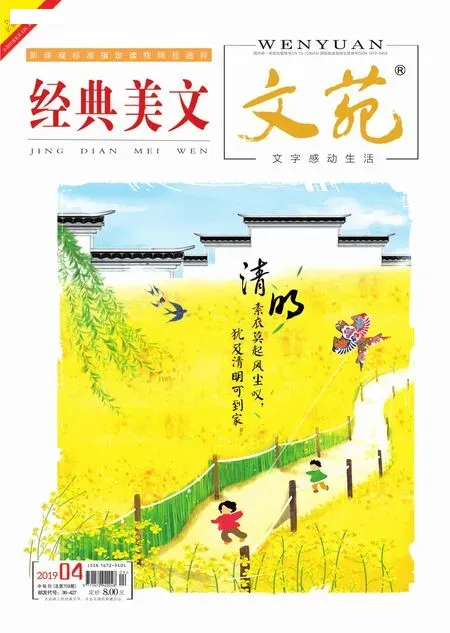我与梅花有旧盟
2019-11-21王金声
文/王金声
家藏一幅陆小曼画的山水,大约是她自己满意的作品,曾在1941年的个展上展出,画的右下角钤了方压角章,印文为“我与梅花有旧盟”。我纳闷,画上无一处梅花影子,干吗盖这章,想必另有隐情。后来才明白小曼的母亲吴曼华是位画家,又名梅寿,而小曼的小名叫小梅,画画也受其母的影响,应该算与梅花有因缘旧盟吧,再说翁瑞午有个影梅书屋,也很难脱得了干系。
先父爱梅,爱的是纸上梅花,案头除了工具书外便是这本印刷的陈叔通《百梅集》。儿时记得墙上挂了幅梅花,乡前辈房毅所绘,梅干倾下而疏萼几点凌寒独妍,配着先父所书主席诗联,诸如“梅花喜欢漫天雪”“玉宇澄清万里埃”,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挂到了八十年代。不料,先父某天上班回家一言不发,沉默半晌又独自喝起闷酒来,酒酣之际起身一把扯下墙上的梅花,撕个稀烂,全家人面面相觑,不知所以然。不日母亲才告知我这件憾事,父亲原有出国考察的机会,填报审批文件时在有无海外亲属与关系一栏填写了“无”,听说被人检举后查实,因隐瞒组织取消了资格,出国成了泡影。那天我问父亲干吗迁怒于这张梅花图,父亲苦笑说:“你不觉得画上梅枝全倒了?我倒了大霉啊!”真是无语,倒霉事竟然与梅花的形态扯上了关系,父亲毕竟是斯文扫地年代过来的“知识分子”,面对伤害也不敢回应,心存对宿命的敬畏,却用偏激的手段毁了那张倒梅画,以宣泄心中的惆怅,从此不见老父再有爱梅的情结,性情也大不如前。
我的忘年交郑逸梅曾说过一个掌故。某岁仲夏,逸老去梅景书屋看望同学吴湖帆,吴见逸老手中持扇,打开一看,是章太炎的书法,见另一面空白,自告奋勇要补空,忽然表情严肃地问:“给你画个折枝梅花忌讳吗?”逸老笑逐颜开:“弗碍!弗碍!”原来折枝梅花一般不给年长者画,怕有折寿的附会,故吴怕逸老误解,先问清楚才敢画。
记得中学读过一篇《病梅馆记》,那个一肚皮不合时宜的龚定庵,对于文人画士崇尚以曲欹、疏影为美的梅桩盆景,统统斥之病梅,准备辟个病梅馆来誓疗之,还要用毕生精力收集那些病梅,解开绳之以梅的棕缚,还其原生状态。这些耐人寻味的话语又何尝不是龚定庵想要表达反对束缚人才、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
我与先父大约也有几分精神遗存,不变的仍是爱梅天性,也不分倒枝直杆,而且爱得饱满。曾驱车徽州购回一株朱砂红梅老桩,置于阳台辟圃以栽,倒也数度花开,大约没几年竟成了枯枝朽木。基于自己的偏好,大老远带回都市,本身已改变了它生存的环境,加之平时呵护不力,备受旱涝煎熬,只在冬季问问梅花消息,对自然法则而言,“意外”必定如期而至。梅花咱养不活,不必苛求,还是回到纸上吧,文窗无俚,重新收拾老父存玩的梅花旧笺以开襟抱。从清代至近代真是琳琅满目,洋洋数百张,最可流连者为八张一组的“梅花喜神”笺,图案取自吴湖帆家藏宋刻《梅花喜神谱》,为吴妻潘静淑的嫁妆,以致吴把自己斋号也改为“梅景书屋”,谱按梅花从蓓蕾至烂漫的百种姿态,以极简风格呈现,叹为观止。
冬夜玩笺,暗香缥缈若浮纸上,惜乎今人都是低头一族,尚有几人恋此美笺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