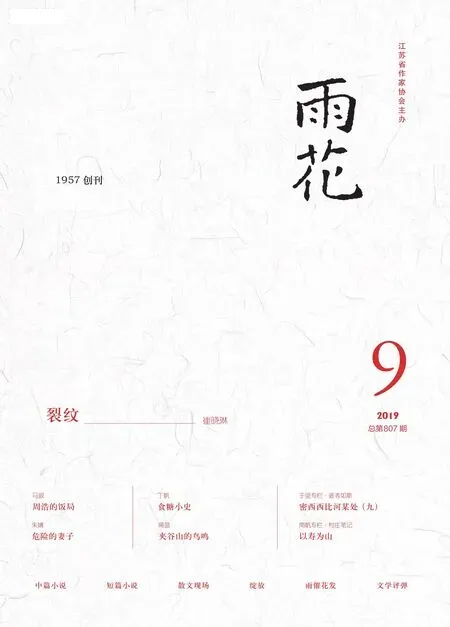夹谷山的鸟鸣
2019-11-20蒋蓝
蒋 蓝
夹谷山如吞云吐雾的一匹花豹
在人们的印象里,山势的巍峨,一是取决于其自然而然的高耸,二是着眼于山势人文积淀所形成的伟岸。但往往是第二种山,成为了丈量历史海拔的一大基点。比如,孔子曾经登临农山,他发出了“登高望下,使人心悲!”的千古浩叹。钱钟书把这种悲愁如大云的慈悲情怀称之为“农山心境”;再比如,位于春秋时期齐鲁交界的夹谷山,更藏匿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夹谷山以山顶为界,分属山东临沭县和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西南距临沭城17.5公里,东南25公里处便是赣榆区青口镇,史籍中多称此为“赣邑夹谷”。
在赣榆人的发音里,俗音“盖于”,暗示了此地与齐鲁的悠久渊源。春秋战国时期,此地有纪障之城和莒子逃亡至海的点滴记载,暗示赣榆乃是鲁国最后的陆地边界。赣榆夹谷山早有齐鲁对峙期间在此会盟的传说。对于赣榆这样一个鲁国东界之县,发生这样的历史事件丝毫不奇怪。如今连云港市北部还有孔望山、端木晒书台等景点,从地名学知识打望,这些地缘均暗示了,孔子肩负重大使命的东行并非虚构。
2019年初夏时节,我和十几位作家寻阶而上,到此踏访。夏日阳光透过茂密的丛林,在石头上溅起一层白光。当地人告诉我,夹谷山林木茂密,更有他山皆无、此地独有的植物特征,那就是遍及沟壑的野生葡萄和野葫芦。仔细一看,果然,葡萄或挂于树枝,或藏于草丛,绿如历史深处的翡翠,凝聚在葡萄上的露水被阳光照亮,更像猫科动物那双疑惑、觊觎之眼。朵朵雪白的葫芦小花迎风乱抖,却未见一只葫芦。当地传说是,夹谷山的葫芦三千年只结一只,这只被上苍选定的葫芦,经三千个春秋而成熟,就像王母娘娘的蟠桃。铁拐李来此吃了葡萄成仙,临走时又摘了那只未满三千年的葫芦,从此夹谷山的葫芦秧就只会开花,再也不结果了。
在我看来,这应该是由于此地风大、地瘠,造成主蔓上雌花稀少,挂果甚难。在这只充满寓言的葫芦上,其实已经暗示了历史在此峰回路转的艰难。
夹谷山并不险峻,十几分钟即登临山巅,迎面便是“一望众山小”的古碑。夹谷山脊背隆起于拱卫的山峦之中,周围大小山头沉默而蛰伏,似在聆听夹谷山的风声、雨声,抑或山的独语。花树与云朵互嵌,山势如吞云吐雾的一匹花豹,蹲伏在黄谷峪盆地的东部边缘,豹身逶迤而斑斓,将东西两侧的村庄分隔,由此构成了特殊的自然景观:太阳刚露面时,东麓的村庄、山峦一片金红,西麓则因山影笼罩,仍处于昏暗之中;太阳刚刚没入地平线,西麓正是一片金黄,东麓已拉开了夜幕。据此“日出而红,日落而黄”的现象,先民们将东麓的村庄命名为“红出村”(后演变成“洪双村”),西麓的叫“黄谷峪村”,旧有“八大黄谷峪,十二个小红出”之说。(见《夹谷山史话》,载《临沭县文史资料选集》。)
夹谷山之南,紧靠小地名“马山”,两山之间是一道弯曲的纵切山谷,俗称“鹰愁涧”。这些地名无一例外都在烘云托月。涧之北即夹谷山南坡,顺山势东西各分布有一道山梁,中间山坡平缓,杂树横斜,像一个硕大的宝座。这里就是春秋战国时代“齐鲁会盟”之地。
当地文管所管理员讲,他们在30年前接到村民发现古石碑的消息,很快寻到了埋于地下的一块花岗岩石碑。碑高约3 米,宽约1 米,镌刻有“孔子相鲁会齐侯处”,为明万历丙子年立。字体丰硕饱满,洒脱而骨力十足。此处另有一碑为清光绪七年所立,文曰“赣邑西境夹谷山,圣人相鲁会齐故址,旧有夫子庙,岁久倾圮……”细细察看,碑身上斑斑驳驳地覆盖有淡淡的青苔,碑文落款处有几个方块字样的浅浅凹窝,给人古朴苍拙和世移人远之感。
历史上,齐鲁举行过多次议和会议,“礼仪之邦”显然必须在繁文缛节的客套之间,在举卮与作揖之外,渐次展开智谋的倒刺。为何单单这次相会显得特别重要?我以为不仅仅在于有孔子作为鲁国国相出席,更关键在于,曹沫劫持齐国国君的阴影在前,这是一次熄雷霆为祥云、化干戈为玉帛的大会。暴力循环的定数,在此得到了一次富有深意的中断。
一把横飞的短刀
学者李零撰文指出:“曹刿就是曹沫,这是没有问题的。至于此人是否当过刺客,我只能说,这是古人的成说,而且从《孙子兵法》看,还很有根据。它不仅见于战国秦汉的古书,也被《史记》采用。司马迁讲曹沫,特意记载的就是他劫齐桓公的壮举,不但《刺客列传》讲,还载之《年表》与《齐世家》《鲁世家》,反于论战之事不置一词,可见这种说法在汉代影响非常大。学者怀疑,可以,但如果不是别有所见,我们还是应该尊重古人,至少是留有余地。”(《花间一壶酒》)其实,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初版当中,《曹沫》篇就自注“或作曹刿”的字样,可见学术上早有使两人“和二为一”的趋势。
在我的阅读印象里,这两个人好像是完全无关的类型。曹沫血勇尚力、大胆莽撞,是刺客出身,为鲁庄公所用,在齐鲁乾时之战之前,就已经成为了鲁国大将,在乾时之战中又曾经吃过败仗,另外有学者认为曹沫当时并没有指挥军队;曹刿则是一派儒雅风度,是一位足智多谋、重礼知义的军事家,在长勺之战前夕,自荐进入鲁国军政界,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但李零先生令人信服的考证,我是大体同意的。
所以,曹沫即曹刿,一作曹翙。生卒年不详,后出任春秋时鲁国大夫。鲁庄公十年(前684年),齐桓公不顾主政大夫管仲的竭力劝阻,派鲍叔牙率大军伐鲁。此前,齐鲁几次交战,鲁国都被打败。听到齐国大军压境的消息,鲁庄公和群臣惊慌失措。曹刿此人在史书里并没有详细刻画和记载,按照他在与人聊天时称别人为“肉食者”来分析,他大体是来自鲁国民间的平民,但又不是普通人——应该算是胸有韬略、蛰伏民间的隐士。隐士一亮身,让他的身形投射在国家权力的强光下,他似乎就是卧龙式的大人物。曹刿坦然求见庄公,主动提出一系列抵抗齐军的方案。这就是著名的“曹刿论战”——“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左传·庄公十年》)果然,后来鲁国大败齐军,让曹刿赢得了军事家的名声。
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写道:曹沫是鲁国人,因为勇猛有力被恰好喜欢角力的鲁庄公赞赏,并且做了鲁国的将军。春秋时期,国家军事训练的主要形式是“田猎”和“武舞”。田猎的目的,是训练对各种武器的使用及驭马、驾车之术,是集身体、技能、战术的训练为一体的综合军训。据《礼记·月令》载:“天子易教于田猎,以习五戎。”五戎即弓矢、殳、矛、戈、戟五种兵器。田猎活动也包括“空手以搏”和“手格猛兽”的搏斗技能。利用田猎进行军事训练,不仅商代如此,直到西周春秋也是如此。只是商代比较简单,到西周时才逐渐制度化。由此可知,曹沫的搏斗技能相当出众。
毕竟徒手搏斗不同于大规模阵地战。鲁庄公又喜好攻城略地,曹沫为鲁国的大将,同齐国作战,三次都以鲁国大败而告终。国君庄公已经杯弓蛇影,只好向齐国提出讲和条件,并忍痛割让了遂邑等土地,但仍然以曹沫为大将。
齐国答应了鲁国提出的讲和条件。公元前681年,两国便在柯邑(位于今山东阳谷县境内,即后来传说的武松打虎之地。)举行盟誓仪式。齐桓公同鲁庄公在盟坛上,体现出来的礼仪就是一国之尊,上香入案,手捧玉盂,两国国君热烈拥抱,同志加兄弟,目送飞鸿,目光流转,彼此深谙唇亡齿寒之理。他们正准备歃盟,曹沫突然飞身冲到坛上,亮出了藏在怀里的匕首,大鹰一般扑向齐桓公。匕首逼颈,把毫无防备的齐桓公制伏。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但谁也不敢妄动,否则电光火石之间,就可能使齐桓公身首异处。齐桓公身经百战,反应过来了,这是劫持!他镇定地问道:“你想干什么?”曹沫答道:“你们齐国欺人太甚,逼鲁国割让土地。你们自己说该怎么办?”曹沫用一个锋利的反问句,回答了对方的问题。即使在这样的场合,曹沫也没有直截了当地亮出底牌,但他的意图显然是要求齐国归还土地。
齐桓公回过神来了,他马上答应:“我同意退还鲁国割让给齐国的土地。”齐桓公的语音一落,曹沫即刻扔掉了匕首,缓步走下盟坛,像变了个人似的,真乃循循书生,恭恭敬敬地回到群臣的行列中站立,礼仪周到,面色不变,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这样的变化颇为戏剧,齐桓公感到一出胜利者的正剧被一个昔日的手下败将,活生生地导演成了闹剧,自己成了小丑,不禁恼羞成怒,决定收回刚才的诺言,但锦心绣口的管仲劝止了他:“你不能变卦。贪小利而失大信,以后诸侯谁会相信呢?”
齐桓公猛然醒悟。他秣马厉兵,素有称霸诸侯的雄心,管仲一语切中要害。为了取信于天下,齐桓公不得不忍痛兑现诺言,将曹沫几次打仗所丢失的鲁国土地,全部归还鲁国。
我推测,曹沫此举,表面上是为了国家,但有没有因为自己在战场上连续失利而积累的怨恨呢?冒死劫持,鱼死网破,但事情竟然兵不血刃,一蹴而成!用军事智慧没能取得的胜利,反而以一己之力,就挽回了自己的面子和一国尊严。
我们可以认定,曹沫开创了古代刺客的理想主义典范,所谓“单匕寸言索国土”是也。执着、果敢、决绝、从容,这得到了司马迁的由衷夸赞:“奋三尺剑,一军不能当”,并推为《刺客列传》的首位,实在是很值得玩味。
在司马迁的价值观中,刺客与侠客有着天然的难以割舍的联系。曹沫此举透出侠气,意料之外的人做意料之外的事,却表现了维护国家的正义之情,又在意料之中。
由此也可见古人是如何“守信”的。桓公与管仲不背柯之盟,桓公守约纯粹为了信用。因此时曹沫已经丢下武器,离开桓公。放弃唯一的武器,其实也在赌桓公会守约。总体来说,此次守约对桓公而言应该是变不利为有利。一般人会如是推想:桓公在别人用违反道义的方式胁迫下答应的约定都可以遵守,何况其他!桓公以往所建立的信用,使得齐鲁可以用成本很低的方式达成交易,否则,桓公甚至可能会被掳回鲁国,后果将是难以估量的。
绑架,也称之为劫持。古代有两种说法,一种叫“持质”,另一种叫“劫质”。“持”是用暴力挟制,“劫”是用暴力胁迫。曹沫劫持齐桓公,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并且获得成功的一次暴力劫持人质行动。曹沫又是春秋时代唯一一个成功之后得以全身而退的大侠。与刺杀相比,劫持更有头脑(商人头脑),它比刺杀更老练,有更多的权谋在其中。所以,顺此先河,春秋及战国时代数百年间,这种冒险行动一再被后来者仿效。李零在《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里分析说:“汉代劫官员,有些也是出于政治目的,但上面说的例子,地位还不够高。汉代末年,贼人特多,大家就连天子、公卿都敢劫。比如,读《三国演义》,大家都知道,张让、赵忠等宦者,李维、郭汜等军人,他们劫持的就是天子、公卿(见《后汉书》的《董卓传》和《宦者列传》)。那时的时髦话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挟天子’也是劫持活动。很多人都以为,只有白脸曹操这么干,其实这是那时的流行思想。”(《花间一壶酒》)
口舌的锋利胜过了刀剑
鲁国阳虎之乱被平定以后,孔丘由中都宰升任大司寇,主管刑法和外交往来之职。孔丘辅国兴礼乐、重教化,鲁国得以兴盛。齐国自然惧怕这样的教化之力,长此以往,鲁国崛起,怎么得了!齐景公采纳大臣黎弥的建议,表示愿与鲁国“修好”,相约两国举行“乘车好会”。于是,在距离曹沫举刀完成劫持齐国国君事件184年之后,公元前500年的夏季,齐景公和鲁定公决定在赣榆夹谷山会晤,具体商谈议和事宜。
由于早有前车之鉴,齐鲁双方皆作武备,具官以从。齐景公下榻祝其城,翠微华盖,车马千乘,浩浩荡荡西赴夹谷。他们在城内外及山峦沟壑间埋伏重兵,一旦结盟不成,立即刀兵相加,孔老夫子和鲁定公定然难逃此劫。
当然了,鲁国绝不会甘做俎上之鱼。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所以鲁国早准备了一支较强的卫队,埋伏在夹谷山周边。
在我上山的一路上,还看到很多大块大块的岩石上钻有一尺多深的圆孔,据说是用来插旗杆所用。足以见得夹谷山会盟旌旗猎猎下蛰伏的危机。
齐国可谓万事俱备,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们没有估计到的是,真正谈判的对手,是孔子。
彼此准备工作做得扎实,齐国一味注重硬实力,忽略了谋略,腰力十足,所以会盟一开始就显示剑拔弩张的态势。齐国企图用消灭莱国时所俘虏的莱兵赤膊上阵,劫持鲁定公,迫其归顺。而孔子立即用周礼、周法退之。他指出,齐国、鲁国都是周王室的诸侯,所以边夷不能扰乱华夏之正统,而俘虏更不能干涉会盟,不能用武力逼迫修好。
真正的问题在于,孔子如何知道齐国的密谋呢?合理推测是,鲁国的侦查人员深入敌营,显然提前把这一重大情报予以了通报。
齐国觉得用武力不行,就接着演奏“四方之乐”“宫廷之乐”,以此羞辱和荧惑鲁定公。美其名曰“四方之乐”,实际就是“夷狄之乐”,这时齐景公命令众将士拿着弓弩、戈戟、宝剑聚于阶下,兵器闪烁起一大片冷光,赤裸裸的威胁。孔子知道这是“文攻武卫”之术,他长身而起,登坛严厉斥责对方,认为两国和好,不能用夷狄之徒登坛演奏,更不能用优倡侏儒演戏于前,这样是缺乏礼仪的,应该诛杀这些戏子。
从这一点上,展示出孔子临危不乱、据理力争的沛然之气。有理、有仪之人,似乎总是真理的情人,他们总是双飞双宿,联袂而起。
齐国安排的A、B 计划都没有得逞。显然齐国没有吸取历史教训,过于依仗武力,明显缺乏一波三折的回环智谋,更缺乏处置危机公关的能人。与群臣面面相觑之余,齐景公仰天浩叹,那天阳光刺眼,晃得他睁不开眼睛,只好在盟书上签字。
为了最后的颜面,齐国又提出一个联合协议:如果齐国今后有军事行动,鲁国必须派三百甲车随从。有理的人物一直是稳操胜券的,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孔子让兹作揖回答:“如果你们不归还我们鲁国汶水北岸的土地,却要让我们供给齐国的所需,也要按盟约进行惩罚。”
谈到这个程度,面子越绷越薄,几乎就要撕破脸了。于是,齐景公准备设享礼款待鲁定公,喝了酒,再谈,也可以谈不成,甚至就希望谈崩。孔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酒,还是不喝为上。
他为齐国的梁丘据上了一堂深奥的礼仪课:“齐国和鲁国从前的典礼制度,您怎么可能没听说过?!盟会的事已经结束了,而又没有设享礼款待,这是让办事人受累了。再说,牺尊和象尊从不出国门,钟磬也不能野外合奏,设享礼必须全部具备牺磬,不然就是抛弃了礼仪;如果这些东西不备齐,那就像用秕稗来款待贵宾,分明是国君的耻辱;抛弃礼仪则名声不好。您为什么不好好考虑一下呢?享礼是用来发扬光大德行的。不能发扬光大,还不如不举行。”
在孔子这一番宏论之下,礼仪峭拔如东岳泰山,礼仪滔滔如天象钟际大河,齐国群臣简直无法抵挡。就是说,连一顿酒都喝不成了。齐景公讨了个没趣,他的确缺乏理由来举行享礼了。
我们很难想象,腰力十足的齐景公,是如何离开夹谷山返回齐国的。那种愤怒与懊恼,估计比丢失了土地还要令人沮丧。土地丢失了还可以夺回来,但在孔子铺排的礼仪语境当中,曲径通幽,花明柳暗绕天愁,陷阱之下还有陷阱,自己就是永远的输家。
值得一说的是,当年冬天,齐国向鲁国归还了郓邑、瓘邑和龟阴邑的土地。真可谓输得彻彻底底。
在我看来,孔子的锋利口舌明显胜过了刀剑,明显胜过了曹沫横飞的匕首,真是摧枯拉朽。从不口言计谋、阴谋、阳谋的孔子,似乎仅仅以礼仪之光,就让对手在照妖镜之下露出了原形。一言以蔽之,鲁国取得了外交上的重大胜利。
取得这次胜利之后,也就在齐鲁夹谷会盟后的第四年,鲁定公打破了周王室诸侯任近亲为上卿的旧例,任用长袖善舞的孔丘为大司寇执掌相事,共同治理国家,这也成为孔子入仕的高音部。
《春秋大事年表》(前770年—前403年)记载,历史上的春秋会盟有450次之多,足见会盟、会晤、会谈、会见一直是国粹;草签协议就是伟大成果。春秋会盟谱系当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夹谷会盟。正是由于孔子的文韬武略,礼仪的正义叙事胜过了暴力劫持,成为了影响最大、传史最久的春秋大事。
我在会盟处的四周徘徊,右侧见到众多历代文人碑刻,为近年当地文化部门翻刻。唐代咸通年间,进士不第的诗人胡曾在一个春天畅游夹谷山,慷慨怀古,赋《咏史诗·夹谷》一首:
夹谷莺啼三月天,
野花芳草整相鲜。
来时不见侏儒死,
空笑齐人失措年。
诗人站在鲁国立场上,对于孔子操排的这一场历史大剧,予以了高度颂扬。
明万历年间纂修本地方志,夹谷被文人们列为“赣榆八景”之一。赣榆籍人、曾经官居明朝大理寺正卿的裴天祐某天登夹谷山,感于历史的畸变,赋诗云:
翠微西近祝其城,齐鲁当年此会盟。
幽洞云深人已去,左坛松老月还明。
劫兵余焰遗空谷,罢享流风动废营。
我欲东临寻胜迹,并尊东麓听啼莺。
这两位诗人均来过成都,再到赣榆夹谷山,于我似有前定。“废营”,指齐鲁两国与盟人员驻地旧址。“并尊”谓举杯饮酒。白云苍狗,但往事不会湮灭,犹如急射的鸟影,总在天空留下了一串墨汁。而一轮明月之下,往事其实并未湮灭,往事历历如绘。诗歌最后两句,极富深意,深得孔子三味。
诗歌里提到的“啼莺”,来自当地的传闻:夹谷一线山谷深邃,劲风吹石洞,滚滚松涛中能听到清越娇婉的莺啼声。千回百折,山鸣谷应,若即若离,这就是明清赣榆八景之一的“夹谷莺啼”。其实,“啼不必莺,风微石罅莺声也”,这是山风啸过石洞或岩隙而发出的阵阵鸣响,酷似黄莺啼啭,这神韵独具的无莺自啼,曾让多少游人访客为之神魂颠倒,流连忘返。
恕我耳背,我竖起耳朵了听了半天,没有听到这著名的拟鸟风声,倒是听到了树叶飘洒落地的声声嘤咛。齐与鲁的此消彼长,就像一片树叶的两面,并无媸妍之别啊!
孔子身为鲁国国相,鲁国如虎添翼,让齐国深感不安,他们决定无论如何要煞一下鲁国的气焰。某日,齐王向著名的晏子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心病:“边邻国家有圣人,这就是敌对国家的忧患。现在孔子当了鲁国的宰相,如何是好?”
晏子的回答,可以看成是“智者”对“礼”的攻击:“君主你用不着忧愁。鲁国的国君是一个昏庸软弱的君主,而孔子是德行才能出众的宰相。国君,你不如暗地里表示钦慕孔子的才能,假说许他做齐国的宰相。孔子努力劝谏而鲁君不听从,孔子一定会认为鲁君骄横刚愎自用,会放弃他而来到齐国。假若孔子真的来了,国君你也不要接纳他。这样,他将自绝于鲁国,又不能任用于齐国,孔子就窘迫了。”
“折辱之计”,实际上实现了。
过了一年,孔子离开鲁国到齐国游历,原本以为齐景公会“礼贤上士”,隆重接待自己,甚至委以高官。他万万没想到的是,齐景公根本不接纳他。因此孔子一度被困于陈、蔡两国之间,连一顿肉都吃不上,甚感屈辱……
我再上山顶,站在那块镌刻有“尼山分秀”的巨石边,我猜,当年的孔子在离开夹谷山时,一定不是踌躇满志的。孔子唱的自然不是空城计,他胸怀汹涌礼仪,足以抵挡百万兵。可惜的是,礼仪从来没有像树木那样,在大地上成为森林。
有人大喊了一声:“快看,海市蜃楼!”我循声而望,崮顶的西面,隐约显出一片亭台楼阁,云雾缭绕,下面竟是波光粼粼的水面。当地文管所研究员解释说,山的西面因为有一个大型水库,所以远远望去就如海市蜃楼一般。就在我抬头之际,只见东面的峭壁上,竟有一幅天然形成的人像,似孔子;但也有人说,更像齐景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