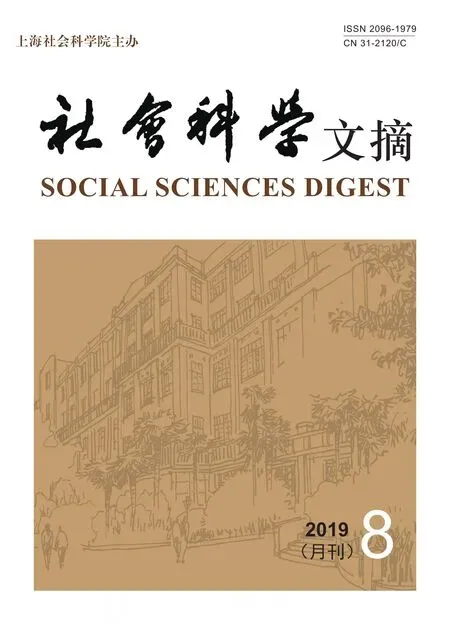新“生存伦理”陷阱:连片贫困区农民家庭转型困境的一种解释
2019-11-19刘景琦
文/刘景琦
改革开放以来,深刻的社会经济变迁重新刻画了中国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形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很多农民卷入其中,在城乡之间流动。家庭转型压力下,改变家庭生产方式,达到家庭劳动力的最优配置,以实现家庭经济收入最大化,是中西部农民家庭的普遍选择。在此情况下,全年外出务工成为理性选择,中途极少回家,这成为普遍性现象。由于经济条件更为落后,家庭转型压力更为巨大,连片贫困区的农民家庭劳动力优化配置程度可能更高,在打工时间与打工强度上也可能更高。但在贵州连片贫困区调研时发现,这里的农民工回家的频次较高,且在家时间比较长,来回奔波在家乡与打工地之间,形成了当地人所谓的“来来回回”的钟摆式打工样态。这种打工样态减弱了农民参与市场获得收入的潜力,整个家庭的财富积累能力较差,在全国性婚姻市场下,形成了“光棍成窝,离婚成堆”的现象,家庭再生产面临威胁。这构成了认识与经验之间的悖论,也形成了本文的问题意识,如何理解与解释这种现象,是本文关心的问题。
文献综述
经济伦理与经济行为是研究农民家庭非常重要的切入点。由于处在生存线的边缘,农民家庭行为仍是建立在斯科特所谓的“生存伦理”的基础上的,农民所追求的不是经济收入的最大化,而是较低分配风险和较高的生存保障之间的平衡。“过密化”的小农经济成为家庭主要生计模式。农业生产陷入“没有发展的增长”当中,农民家庭陷入了“生存伦理”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将农民卷入城乡间的地域流动、工农间的产业流动。农民生计模式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农民作为“能动的主体”,充分利用外地市场和本地社区资源,家庭再生产的顺利实现依托于“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半工”结构带来的非农收入,是家庭城市化与家庭发展的重要资源,“半耕”结构带来的社区生活与农业收入,是家庭劳动力失业或“退养”的保障。二者之间相辅相成,亦可能会此消彼长,甚者可能会相互掣肘,故半工与半耕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与伦理意义调适上应该保持一种内向的平衡。
城市化、工业化催生出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由内而外抑制了长期以来的农业“过密化”。小农家庭逐步转变为发展型小农家庭,家庭的“发展伦理”逐步凸显并替代“生存伦理”,成为农民家庭赖以转型的主导性经济伦理。
从过密化农业境况下以农业生产为家庭资源主要投向的小农经济到工业化境遇催发的普遍稳定的“半工半耕”家庭生计模式,可见在家庭经济伦理和家庭生计模式之间必然存在一种调适和匹配过程,因此要理解农民家庭转型就要理顺这一过程内的关系变化。相关学者主要强调了“半工”结构的重要性,认为“半工”结构带来的家庭劳动力的充分利用与家庭收入的增长增强了“发展伦理”在家庭生计中的地位。然其背后隐含这一假设——半耕结构能够维持传统小农意义上的生计、适应社区内伦理性消费,不会对半工结构生成的发展空间造成掣肘。
但是,当“半耕”结构不能在家庭留守劳动力手中得以维系的时候,其原本承担的家庭劳动力失业或“退养”保障功能必然弱化甚至崩溃,进而对半工结构形成硬性牵制,引致家庭再生产层面上的结构性危机,倒逼农户在劳动力配置、生产性投入、消费性支出等生计策略方面适时做出微调。
通过对连片贫困区生计模式的考察指出,弱半耕结构使得农村家庭“生存伦理”凸显。农民家庭为了维系“弱半耕结构”,保障家庭的底线生存,实施以“钟摆”式打工为主的打工策略。这种打工策略使得家庭面临着新的挑战,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家庭没有办法完成社会继替,最终陷入了新的“生存伦理”陷阱。
弱半耕结构下“生存伦理”的凸显
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有赖于农业提供就业空间和农村提供生活空间。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下,老年人作为辅助劳动力,在村从事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维系乡村人情往来,并以此作为退养的保障。但是,在贫困山区,由于交通不便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市场发育程度也比较低,在从事基本的农业生产、完成家庭抚育/赡养责任、家庭人情往来时,单独依靠老人不能实现家庭功能的有效运转,老人不足以成为“半耕”结构的担纲者。
连片贫困地区的糊口农业,自然禀赋差,主要从业者——老人不能像平原地区农业型村庄的老人可得益于生产全过程的机械化作业与社会化服务,必须通过烦琐沉重的体力劳动才能维持农业生产。面对需要“在场”的人情往来与人力帮工,经济水平与体力衰减使他们力不从心。可以说,直到现在,这里的老人依然是真正的老人,很早就丧失了劳动力和参与社区生活的能力。除此之外,随着老人体力的衰退,老年人赡养和子女抚育也随之出现问题。由于山高人稀,居住分散,且交通不便,老年人很难独立完成砍柴、割猪草、赶集、看病等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事务。老人文化程度低,且思想观念落后等,也使得家庭没有办法通过隔代抚育的方式完成对下一代的照料。
对将村庄社会作为退养保障的家庭而言,弱“半耕”结构显然是不利于家庭正常运转的,这种弱“半耕”结构也使得家庭无法在社区内立足。在这种情形下,家庭“生存伦理”的逻辑就凸显出来。
“钟摆”式打工策略的生成
弱“半耕”结构倒逼农民家庭对既有生计模式做出微调,以保证家庭再生产的顺利完成。一般情况下,农民家庭将一部分主要劳动力从“半工”结构中拉出来,重新纳入到“半耕”结构中,替代老年人,成为家庭“半耕”结构的主要担纲者。
将主要劳动力从“半工”结构中拉回来,一种情况是完全从“半工”结构中退出,返回到村庄社会当中,成为“半耕”结构的担纲者;另一种情况便是“钟摆”式打工策略,既不完全从“半工”结构中退出,也不完全进入“半耕”结构,二者兼顾,平衡家庭内部的工农生产、城乡关系。村庄中有一部分村民采取的是完全从“半工”结构中退出,但比较罕见,主要在于家庭主要劳动力数量较少,但家庭功能的维系需要主要劳动力长期在家留守,长期留守的前提也在于能够在乡村本地获得体面劳动和足够收入。另有一种情况是留一个青壮劳动力留守村庄,一般是让男性留守,妇女出去打工。男性留守的策略性选择受制于以下因素,首先是农业生产仍属重体力活,男性具有优势,其次是本地市场发育不足,农闲时只有适合男性的建筑零工市场,而女性可以在全国性劳动市场中找到工作,且女性一般比较节省,有更多节余寄回家补贴家用。
不过,由于本地劳动力市场发育不足,就业机会少,为获得更多收入,大部分劳动力采取“钟摆”式打工策略。采取该策略,主要是为了实现家庭抚育、赡养功能的正常运转。“钟摆”式打工策略的成形,需要劳动力与农时结构、家庭需求、社区人情往来的规律相匹配。一般情况下,在农忙时节和春节等重要节日,主要劳动力都会选择在村庄中,参与农业生产和村庄社会人情往来。在劳动力市场从事就业灵活、危险系数高、日薪高的工作,以实现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以获得更多的现金收入。
新“生存伦理”陷阱的生成
(一)“钟摆”式打工策略与基本“生存伦理”维系
在“钟摆”式打工策略下,通过将主要劳动力从“半工”结构中拉回来的方式,补充“半耕”结构的不足,从而满足了家庭退养的保障。这种打工策略重塑了家庭生计模式与劳动力配置方式,改变了家庭收支结构,家庭收入水平在下降,而家庭支出水平却随之增多。
与“半工半耕”结构形成的长年外出打工相比,在“钟摆”式打工策略下,农民家庭收入是减少的。首先,农民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不足;其次,农民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状态不稳定;此外,这种钟摆状态增加了农民进入市场的时间成本,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减少了工作日。
但与此相对应的是,农民家庭的支出并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首先,钟摆式打工策略增加了农民打工的成本。其次,青壮年劳动力在返回家中完成家庭抚育与赡养责任的同时,还要参与人情往来。赶人情成为家庭重要的开支,一般农户一年的人情开支费用就有2万元左右,但为了维持家庭在村庄社会中的社会地位与社会交往,这又是村民不得不承担的花费。
通过“钟摆”式打工策略,家庭调整了劳动力配置方向,补充了“半耕”结构的不足,虽然能够满足家庭在村庄社会中的生存,但对“半耕”结构来看,只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它只是满足了家庭社区性生存的需要和农民的底线保障。这种底线保障指满足家庭在村庄社会内能够较为体面的参与生产生活以及人情往来,免除失去村庄社会内的社会地位的风险。通过“钟摆”式打工策略,农民家庭免除了社区性死亡,实现了基本的“生存伦理”。
(二)家庭继替危机与新“生存伦理”陷阱
农民家庭免除了“生存伦理”的威胁,但又面临着家庭发展能力不足的困境。从整个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这些农民家庭仍然需要面对“发展伦理”的挑战,家庭仍然需要面对城市化竞争和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在当前,社会继替是社会转型的基础,家庭想要完成再生产,首先需要保证儿女能够完婚。在男女性别比失衡、全国性婚姻市场形成的背景下,婚姻成本全面货币化且逐年快速上涨,以房子、彩礼、三金为代表的婚姻要价也逐渐成为“标配”。但“钟摆”式打工策略减弱了农民参与市场获得收入的潜力,整个家庭的财富积累能力较差。这就使得很多家庭缺乏足够的资金,供自己的孩子在婚姻市场上寻找到合适的婚恋对象,或者是保持稳定的婚姻状态。
在没有办法完成“发展伦理”的要求时,家庭也就没有办法完成社会继替的要求。这些家庭在以后会自然消亡,而不再有发展性和社会继替性。这时候,家庭面临的威胁就不再是“社区性死亡”的问题了,而是通过社会继替的中断导致的社会性的死亡。
可以说,家庭通过调整打工策略,从短时间来看,能够避免家庭“生存伦理”的威胁,也可以避免家庭的社区性死亡;但长时段来看,家庭仍然需要面对“发展伦理”的挑战,“钟摆”式打工策略进一步降低了农民家庭的财富积累能力,使得一部分家庭没有发展能力来应付社会继替的需要,最终导致这些家庭的自然消亡,也就是社会性死亡,家庭仍然避免不了“生存伦理”的威胁。家庭对“生存伦理”的反应难以规避“生存伦理”对家庭生计转型升级的禁锢,新“生存伦理”陷阱由此生成。
(三)新“生存伦理”陷阱的特点
采取“钟摆”式策略的农民家庭,与传统小农经济下的农民家庭相比,所面对的“生存伦理”陷阱是不一样的,可以称之为新“生存伦理”陷阱。新“生存伦理”陷阱主要指的是家庭陷入了社会继替的风险,从而造成的社会性死亡。新“生存伦理”陷阱与旧的“生存伦理”陷阱相比,有以下几方面的区别。首先,农民家庭面对的结构环境不一样,传统小农经济“是在缺乏土地、资本和外地就业机会的背景下进行的”。而当下的农民家庭,面对的是保护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可以有比较充分的外地就业机会。其次,农民家庭的期望并不一样,传统小农家庭追求的是“安全第一”,而现在的农民家庭对家庭发展非常看重,但是“生存伦理”是底线。再次,解决“生存伦理”陷阱的路径不一样,传统小农采取的是“过密化”路径,想要通过“没有发展的增长”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没有根本解决;现代的农民家庭想要通过增强“半耕”结构的方式缓解“生存伦理”带来的危机,但是却带来了更大的危机。
不过,相同的是,农民家庭的生活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生活都有一个防御圈,在过去,安全第一确实意味着,围绕着日常的生存问题,有一个防御圈;在防御圈内,要避免的是潜伏着大灾难的风险;在圈外,盛行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计算。而现在,防御圈内要避免的是“生存伦理”的风险;在圈外,要实现家庭的“发展伦理”。可惜的是,现在的防御圈已经不再长期有效,只要坠入防御圈内,家庭就会长期堕入“生存伦理”的陷阱当中。
总结与讨论
面对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以及比较充分的就业机会,贵州连片贫困区的农民家庭,并未像普通中西部农村家庭,通过全年外出务工方式,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以满足家庭发展的需要,而是采取“来来回回”这种钟摆式打工方式来应对。这是基于难以发展的糊口农业和农民家庭的社区羁绊,单纯依靠老人无法实现家庭在社区的底线保障和退养需求,这种弱“半耕”结构使得家庭“生存伦理”凸显。家庭优化劳动力配置的方向不是将劳动力从半耕结构中转移出来,而是采取将劳动力从“半工”结构中拉回来的策略,最终保持了“半耕”结构的稳固和家庭在村庄社会的维持。但采取这一打工策略并没有真正解决家庭“生存伦理”的危机,家庭面临发展能力不足的危险,随之而来的是发展能力不足带来的家庭继替的风险,“光棍成窝,离婚成堆”是其表现形式。短时间内的“生存伦理”危机的解决,却没有使家庭真正跳出“生存伦理”陷阱,从长时段来看,通过自然死亡导致的自然消亡成为家庭难以摆脱的命运。
由此我们也可以对人口迁移中的推拉理论做出反思,受到农民“生存伦理”的影响,推和拉都发生了变形,由于农民家庭面临城市化失败的风险,“生存伦理”就凸显出来,弱半耕结构以及退养保障的需求使得贫困的农村由向前的推力变成了往后的拉力,特别是对连片贫困区而言,农民家庭普遍的弱半耕结构成为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的结构性障碍。
同时可以对当前的反贫困政策做出反思,“弱半耕”结构会阻碍“半工”结构的充分发展与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对连片贫困区而言,单纯通过产业扶贫政策,没有办法解决农民家庭的后顾之忧,农民虽然能够享受产业扶贫红利,但受制于家庭羁绊,参与市场的动力与时间仍然不足,就业仍不充分,新“生存伦理”陷阱仍然没法跨越。
最后是对农村定位的反思,中国农村是劳动力的蓄水池和社会的稳定器,是中国现代化、城市化、农民家庭的大后方。如果大后方不稳定,特别是农民家庭面临弱半耕结构带来的“生存伦理”危险,那么整个农民家庭就会陷入新“生存伦理”陷阱,整个城市化进程会受到阻滞,中国现代化进程就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