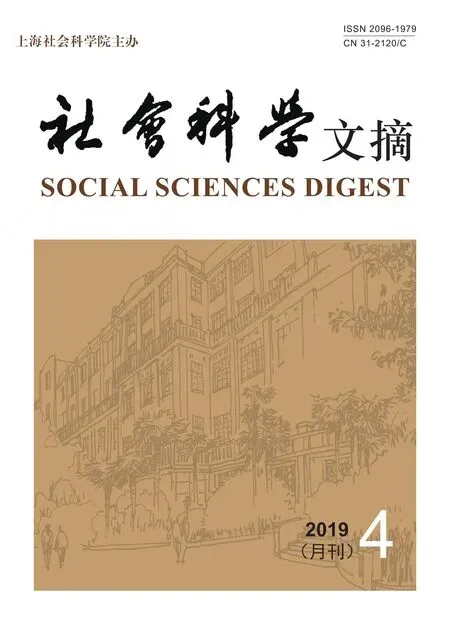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是一个特别的目的地吗?
2019-11-17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就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而言,中国是否是一个特别的投资目的地?进一步地,在中国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却看似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促使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的有四个背景性的因素。首先,在中国大陆的外资中,来自美国的资本并不突出。在2011—2015年的这五年里,来自美国的投资额平均为29亿美元,占前十大投资来源地对中国大陆投资的比重平均为2.7%。其次,在美国对外投资中,中国所处的地位也不突出。依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提供的信息,在2011—2015年的这五年里,按存量数据统计,中国位居第14位~第17位,所占的比重平均为1.4%。再次,如果美国对中国的投资看重的是市场,但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增速却滞后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也落后于整个外资流入的增速。在2011—2015年的这五年里,中国GDP的增速平均达到7.9%,人均GDP的增速平均达到7.3%,而美国对华投资的增速平均为-7.6%。最后,中国最近再度关注外资的重要性并频密地调整外资政策,外资利用面临新的机遇。美国是世界上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与此不相称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却显得相对不足。
在这些背景之下,本文通过跨国面板数据考察美国对外投资的动机,并跟踪中国作为一个投资目的地,是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对上面提到的事实给出一些回应和解释。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针对2002—2012年156个国家的跨国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样本覆盖面和时间跨度来说,这对已有文献是一个改进。其二,跟踪了中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特殊性,并挖掘了使得它有别于其他目的地的具体因素,包括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开放度,以及治理水平等。其三,进一步聚焦制造业,以初步把握美国对外投资的驱动因素在行业之间的差异性。我们在利用联合国贸发会(UNCTAD)的FDI数据的基础上,还利用了BEA的FDI数据。其四,我们在研究中关注了中国和印度,以考察两个具有可比性的发展中国家在吸收来自美国的投资方面的异同。
文献回顾
结合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我们对文献进行了回顾。
从东道国社会和经济环境考察影响FDI流入的因素的实证文献有很多。例如Nunes等(2006)以15个拉丁美洲国家1991—1998年的宏观数据为样本,发现市场规模、基础设施、经济开放度对FDI流入具有促进作用,而通货膨胀、工资水平会抑制FDI的流入,自然资源和私有化对于拉美国家吸收FDI没有显著影响。研究多个国家FDI流入的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多,而研究单一国家对多个目的地投资的影响因素的文献则相对较少,文献相对集中在美国这个FDI最大的输出国上。Biglaiser和Staats(2010)利用微观调查数据研究过去20年拉丁美洲的民主化进程对于来自美国的FDI的影响,结果发现产权保护、法律有效性以及高效的法律系统是美国公司在投资时最看重的。
有关美国对华投资的影响因素,也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徐康宁和王剑(2002)利用1983—2000年全国整体数据分析美国对华投资,他们发现主要因素是市场规模、政府的开放政策、跨国公司的前期资本存量和汇率。Du等(2008)利用1993—2001年6288家美国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数据,特别关注了制度因素的影响,结果发现知识产权保护良好、政府对商业活动干预少、政府腐败程度低,以及合同执行力强的地方,可以吸收更多的来自美国的投资。
关于美国对华投资不足的因素,有学者发现,美国对华FDI投资总量偏少的外表下存在着结构性问题。蒋殿春和张庆昌(2011)基于美国跨国公司全球经营规模数据构建了行业面板,他们发现在控制了东道国市场规模、人均收入水平和贸易成本等因素之后,美国对华投资显著低于模型的预测水平,但在制造业内,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却高于应有水平,也就是说美国对华投资的主要阻碍在于服务业。Holmes等(2015)则把主要原因归结于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认为该政策抑制了投资意愿。作为一篇理论文章,该研究把重心更多地放在如何将“以市场换技术”政策引入到模型中,对于其他可能影响到FDI流入的因素的讨论不够充分,而这是本文想要完善的。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基于现有文献,本文利用地理距离、自然资源、基础设施、通货膨胀、贸易开放度、GDP、人均GDP、经济增长率、治理水平、文化差异、人力资本等变量对经济状况、治理能力、禀赋条件这三方面因素进行控制。总体FDI净流入数据来自UNCTAD,而制造业FDI净流入数据和美国跨国公司经营数据则来自美国BEA。由于缺少服务业整体的FDI信息,在行业层面,我们聚焦制造业进行分析,并间接地对服务业做些讨论。地理距离数据来自CEPII。治理水平的原始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数据库,文化差异的原始数据来自“霍夫斯泰德国家文化(Geert Hofstede National Culture)”数据库。其余变量均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结合文献,我们预计自然资源、基础设施、贸易开放度、市场规模、人均GDP和经济增长对FDI的流入有促进作用,地理距离、治理水平差异、文化差异和通货膨胀率对于FDI的流入有着抑制作用。
本文使用的是非平衡的短面板数据,使用混合横截面回归方法。在实证检验中,还引入了一系列虚拟变量:Developed(目的国是发达国家时,该变量取1,否则取0)、Taxhaven(对于避税天堂,该变量取1,否则取0)、FC(2008年及之后的年份该变量取1,否则取0)、China(投资目的地是中国时,该变量取1,否则取0)、India(投资目的地是印度时,该变量取1,否则取0)。
基准估计
我们首先针对总体样本展开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聚焦制造业样本展开相应的实证研究。
(一)总体样本
针对全样本的估计,比较稳定的结论如下:市场规模、人均GDP、开放度和自然资源等四个变量,与美国投资显著正相关;地理距离和治理水平差异等两个变量,与美国投资显著负相关。在哑变量中,金融危机和避税天堂的系数分别显著为负和显著为正。在控制了这些因素之后,我们发现:与其他投资目的地相比,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并没有明显偏离应有水平,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大体上是现有变量可以解释的;而与其他投资目的地相比,在控制了现有变量之后,美国对印度的投资有高于应有水平的部分证据。此外,美国与目的国的文化差异抑制了前者对后者的投资。
(二)制造业样本
针对制造业样本的估计,比较稳定的结论如下:市场规模和开放度等两个变量,与美国制造业投资显著正相关;地理距离、自然资源和治理水平差异等三个变量,与美国制造业投资显著负相关。Developed、FC和Taxhaven等三个哑变量多不显著。在控制了这些因素之后,我们发现:与其他投资目的地相比,美国对中国的制造业投资有高于应有水平的倾向;而与其他投资目的地相比,美国对印度的制造业投资没有偏离应有水平。此外,与目的国的文化差异抑制了制造业投资,人力资本与投资显著正相关。
从对总体和制造业样本的估计结果可知,就美国对外投资而言:推动性因素包括市场规模、人均GDP水平、开放度等;制约性因素包括地理距离、治理水平差异、文化差异等。与其他投资目的地相比,从总量看,中国并不是特别的投资目的地。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并没有明显偏离应有水平,现有变量大体上可以解释美国对中国的投资。
拓展性分析
我们聚焦美资的重要影响因素,进一步考察中国作为投资目的国的特殊性。考虑到数据可得性,这里主要关注市场规模、人均GDP、经济增长、开放度、治理水平差异等因素。
(一)总体样本
对于全样本,在模型设定中分别引入市场规模、人均GDP、经济增长、开放度与China的交互项,四个交互项的估计系数都为正但均不显著。进一步引入治理水平差异与China的交互项,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单从交互项的符号看,似乎暗示:与其他投资目的地相比,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开放度对于中国吸引美资而言更为有力;而治理水平差异则可能是一个制约性的因素。
(二)制造业样本
对于制造业样本进行同样的估计,我们发现,市场规模、人均GDP、经济增长、开放度与China的交互项均正相关,只有治理水平差异与China的交互项负相关。这意味着,与其他投资目的地相比: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开放度对于制造业领域中国吸引美国的投资更为有力;而治理水平差异则相对地是一个制约性的因素。
结合两组针对制造业回归的结果可以知晓,在制造业领域,美国对中国投资高于应有水平的迹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和贸易开放度等的特殊吸引力。与此同时,治理水平差异则相对地是一个制约性的因素,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除了注意到中国在吸引美资方面的优势之外,也要看到一些制约性因素的影响。
稳健性检验
具体包括:一是对FDI采用不同的度量办法;二是对制造业进行细分。
(一)使用跨国公司经营数据代理美国对外投资
蒋殿春和张庆昌(2011)使用美国跨国公司1999-2007年在44个经济体的总资产和总销售额近似地代表美国对外投资的规模。我们效仿这一思路,用2002—2008年美国跨国公司总资产和总销售额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总体样本中,当被解释变量为总资产时,相近的解释变量的结果是接近的,如市场规模、人均GDP、经济增长、开放度;China的系数在他们的文章中为负且显著,在这里,绝大多数也为负,虽然多但不显著。当被解释变量为总销售额时,估计结果与蒋殿春和张庆昌(2011)的结果对比:除人均GDP之外,相近的解释变量的结果是接近的;最重要的是,China在他们的文章中,均为负且显著,在这里,它也均为负且绝大多数显著。
针对制造业样本的回归表明,在控制了相关变量之后,China的系数绝大多数为负但不显著。这说明,如果用总资产和总销售额代理美国对外投资,美国对华制造业投资没有低于应有的水平。对比用总销售额代理美国对外投资的总体和制造业样本结果,说明如果美国对华投资偏低,原因很可能是服务业的美资相对不足所致。这一论断与蒋殿春和张庆昌(2011)是相似的。
我们也同样关注了印度的情况。在总体样本,India的系数绝大多数为负,且在总销售额为被解释变量时绝大多数显著。在制造业样本中,India的系数均为负,且绝大多数显著。对比全样本和制造业样本的结果,可以知道如果用总资产和总销售额代表美国对外投资,美国对印度的投资整体偏低,而这基本上是由于美国对印度制造业投资偏低造成的。这一结果与中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细分制造业
将制造业具有代表性的子行业作为样本,进一步考察结果的稳健性。具体地,筛选出五个在投资存量中占比较大的制造业子行业,包括电脑和电子产品、食品加工、化学工业、机械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可以发现,在这五个子行业中,China的系数始终显著为正,说明美国在这些制造业子行业的对华投资高于“应有”水平。
针对稳健性分析,我们有两点小结:第一,使用跨国公司经营数据作为美资的代理变量,结果显示,美国对华制造业投资并不低于应有水平,但对华服务业投资则相对不足,这与前面的结论和现有文献的发现是一致的;第二,在中国,电脑和电子产品、食品加工业、化学工业、机械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等五个代表性制造业的美资,高于应有水平,这为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吸收美资所具有的优势地位提供了更微观的证据。
结论与政策含义
针对美国对华FDI看似偏低的现象,本文利用2002—2012年美国对156个国家的投资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基准估计和拓展分析,我们得到以下结论:其一,总体上看,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美国对华投资并没有偏离应有水平,大体上是现有变量可以解释的;其二,如果局限于制造业,美国对华投资甚至有高于应有水平的部分证据;其三,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率、开放度等因素对于美资的促进作用,在中国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是制造业吸引美资表现突出的微观基础。与此同时,治理水平的差异则相对地是一个制约性的因素;其四,与制造业吸引美资的成效不同,服务业在吸引美资方面的潜力可能还未充分释放出来,这与印度的情况形成了对照。在稳健性检验中,通过对制造业进行细分,再次获得在制造业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并不低于应有水平的一些证据。以企业经营数据作为美资的另一种代理,我们得到了与蒋殿春和张庆春(2011)近似的结论,即如果美国对华投资不足,那应该是在服务业。
结合上述结论,就美国对华投资看似偏低的现象,我们有两点解释:一方面,人们可能只看到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和开放度等引力因素,而忽略地理距离、治理水平和文化差异等制约性因素,形成美资流入偏低的“错觉”;另一方面,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利用美资的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对整体的美资利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通过本研究,我们有三点政策建议:第一,继续深化改革,挖掘经济潜力,通过扩张市场规模、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经济增长率,以及扩大对外开放,维持和强化中国整体特别是制造业对美资的吸引力;第二,继续改善营商环境,强化问责制,保持政治稳定,提升政府效率,提高监管质量和法治水平,充分展现吸引美资的“软实力”;第三,继续优化投资环境和政策设计,在维持制造业对美资的吸引力之外,加大服务业的开放,促使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在结构上更为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