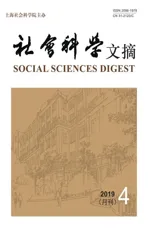新民主国家的再分配理论:欧洲新民主国家的收入差距
2019-11-17
民主能否减少收入差距?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研究认为,民主要对大多数人负责,民主应该带来更大的收入平等。弱势群体在民主国家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因为他们可以将数量的多数变成政治优势,从而要求实现再分配。现有的研究还发现,从专制政体过渡到民主政体后社会支出会显著增加。这些增加了的社会支出主要流向了多数人那里(主要是穷人)。因为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需要建立比专制统治者更强大的联盟来获胜,所以,他们选择用公共政策来换取赢得选举的筹码。
尽管有这样的理论预期,本文的研究却表明,新民主国家在转型之后并不具有显著的减少收入不平等的能力。实践观察结果也表明,欧洲大多数新民主国家都保持着原先的不平等水平,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平等水平还有所增加。为什么一些新民主国家没有实现收入平等的理论预期?本文在新民主国家存在没有改善穷人生活、减少不平等、兑现其经济承诺的现象后,再试图去分析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民主并不能减少不平等,主要在于,穷人在选举过程中的低参与度和新民主国家政党的弱制度化。两者使得执政党在进行国内资源分配过程中牺牲了穷人的利益。工会、商会等这些有着很强组织能力的团体,自专制政权时期起,他们就与新民主国家的执政者之间关系密切。在建立民主政权后,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刺激政府,使得政府推行有利于他们的社会政策。一方面,穷人由于缺乏公民社会所需的各种能力而导致政治参与不足;另一方面,政党对这些高投票率的社会团体的依赖程度又进一步增强。这就使得分化的社会政策日益有利于富人阶层,从而导致收入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
本文研究的意义有三点。首先,它有助于我们理解民主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文章对现有文献中关于选民投票率和稳定的政党制度化的理论假设进行了重新考虑,提出了中间可能选民理论(Median Likely Voter Theory)来修正中间选民理论(Median Voter Theory)。其次,文章强调并分析了新民主国家政党制度波动的影响,说明了高度波动是如何导致更多经济不平等的定向性政策产生。最后,文章在综合了民主化、社会政策、收入不平等和政党体系制度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解释了为什么向民主过渡会导致更大的不平等。
民主与不平等
再分配是政党追求最大化选举机会时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它通过税收和社会政策的形式把资源从高收入群体向低收入群体转移。为了赢得选举,作为执政者和选票追求者的政党作出了选举承诺,并进一步导致了他们提出倾向于中间选民(median voter)的政策主张。平均收入(mean income)和中间收入(median income)之间的差异决定了再分配水平。如果中间选民的情况相对较差,那么,政党则倾向于分配更多资源给中间选民,以缩小差距。唐斯(Downs)以中间选民的均衡为基础,运用他的再分配理论来解释民主政权和专制政权在分配和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差异。其论点的前提有两点。首先,专制领导人需要精英阶层的支持,他们需要满足精英的利益以维持权力。这使得他们不太关心穷人的福祉。其次,与专制政权不同的是,民主国家坚持多数主义。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在议会中占多数以实现掌权。因此,民主国家的执政党将收入低于平均收入的中间选民作为目标,并为之争取更多的再分配资源。这样就会促使政党实施更多旨在缩小中间收入(median income)和平均收入(mean income)之间差距的再分配政策。向富人征更多的税,以重新分配给穷人。由于这种再分配政策,民主国家才可能产生减少不平等的预期。
然而,本文对31个民主国家基尼系数进行了对比,对比的结果却发现新民主国家中不平等的增长情况非常严重。在1975年到2005年间,与已建立的民主国家相比,新民主国家的不平等分值增加了一倍以上。这明显违背了民主应该减少不平等的传统预期。本文需要对这些差异进行解释。
中间选民理论与中间可能选民理论
中间选民理论是解释新民主国家政党运作的重要框架,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首先假设的是所有人都投票的状态,从而认为重新分配有利于中下阶层。在所有人投票的假设下,政党将制定社会政策,以回应处于中间收入水平的选民的再分配要求。
然而,与中间选民理论中的假设相反,民主国家的调查表明,穷人在选举中投票的可能性远小于中产阶级,穷人对执政精英施加的压力相对较小。贝拉门迪(Beramendi)和安德森(Anderson)在对经合组织国家的研究中表明,中等收入以下的选民选举弃权率非常高。很多学者也持类似观点:选民投票率不成比例的下降来自穷人的退场,而资源分配率的下降又进一步削弱了穷人的组织和动员能力。
穷人的低投票率是这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还没有关于新民主国家穷人投票率的经验数据。本文使用了2002年至2006年间进行的三次欧洲社会调查(ESS)的所有数据来分析这些国家的穷人和富人在投票率上是否存在差别。
在使用所有“欧洲社会调查”(2002 ~ 2006年)的数据后,本文发现:不论是新民主国家还是长期存在的民主国家,都存在穷人不同程度的弃权现象。除了英国、土耳其和捷克共和国,无论是新民主国家还是长期存在的民主国家,穷人都占不投票人数的很大部分。如果我们考虑收入群体的投票概率,可能选民(Likely voters)的相关人数将会更加充裕。因为考虑到了穷人和拥有较强组织能力的群体的投票水平的差异,新中间选民理论在社会支出分配方面相对现实。中间(可能)选民的政策偏好更有利于富人选民,而不是穷人选民。因为富人对政党有着强大影响力,他们除了投票选举和游说等活动之外,作为有组织力量的群体也不断对政府施加影响力。而穷人不积极投票也不热心于通过组织的力量去影响政府。这样就减少了收入再分配的可能。
其次,中间选民理论假定执政党对重新分配给有组织的公民社会团体没有偏好。这一假设忽略了政党和工会、专业团体、小企业主等这些公民社会组织团体之间的先前关系。在专制时代,执政精英通过团结不同的组织团体来巩固政权,而亲民主联盟则通过与各种组织团体的结盟来挑战专制政权。所以,掌权后的政党会通过偏向这些组织团体的社会政策,以获得他们的继续支持。最近的研究也表明,公民社会的强势群体利用与政党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对政府政策施加更大的影响力。
最后,中间选民理论假定政党存在并运作在一个稳定的政党制度之中。对于长期存在的民主国家而言,选民可以收集有关政党政策立场的信息,反对党也有相对稳定的选民基础。但大多数新民主国家的政党都是在高度动荡的选举环境中运转,这就增加了政党为了选举利用社会政策的可能性。发达国家现有的政党体系具有低度波动性。这些政党建立在深刻的社会分裂之上,是具有稳定性的选举组织。他们成立一党执政的政府或长期联盟的政府,已经磨合了几十年。新民主国家政党在政府和议会中的存活率很低,执政党更替频繁,很难预测哪一政党将组建政府。在1945年到1995年期间,欧洲长期存在的民主国家有48%的政党获得连选连任,而拉丁美洲只有32%的政党在此期间获得连选连任。后共产主义国家中在1991年至2006年期间只有16%的政党实现了连选连任。新民主国家政党的竞争非常激烈,即使是执政者也同样面临着生存挑战。
波动对社会支出和不平等的影响
社会政策的高度波动性会产生一些影响。
首先,波动性给执政党带来了选举的不确定。为了在动荡不安的政党制度中生存下去,政治家们很可能借助政策工具来实现选举机会的最大化。在大多数情况下,用社会政策来获得自己党派选民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政党还需把那些并非其权力基础、但组织良好的选民群体作为争取对象,为这些关心社会政策并且投票可能性很高的选民群体制定政策,以获得他们的选票支持。
其次,学者鲍恩(Bawn)和罗森布卢特(Rosenbluth)认为,“长期”联盟组成的单一党派政府和“短期”联盟组成的多党派政府具有不同的选举问责机制。与一党政府相比,多党派政府的公共支出更高,即使这两个政府都代表同一个群体。与长期存在的民主国家相比,新民主国家的政府和(或)政党更替率更高,社会政策寿命相对短暂。他们在制定社会政策时,优先考虑历来投票率高的群体的利益。如果是联合政府,那么其存活时间可能更短,政党有着更大的压力将公共资源分配给联盟伙伴的主要支持者。总而言之,随着政党制度的波动加剧,政党更可能偏离惠及穷人的纲领性政策,并倾向于其自身的基础选民和具有较高组织能力、有可能帮他们赢得选举的群体的利益。
穷人选民的低投票率和政党制度的高波动性,两者影响了社会支出的使用,使社会受益比例相对较小。投票率越低、波动越大会导致更多的定向支出。政党需要向支持他的组织群体转移资源,以维持并巩固其选民基础。如前所述,穷人的低投票率、政党制度的不成熟、现有政党和选举结果之间的高度不确定性,使得穷人在分配国内资源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教育和卫生等非定向支出资源被削减或针对穷人的定向支出被削减,这些群体的社会流动将日益困难。政府倾向于忽视穷人,他们的政策有利于那些组织良好的投票群体。随着定向支出水平的提高,再分配的低效率将进一步加剧新民主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
数据方法和结果
(一)数据方法
我们把欧洲作为研究对象,构建的数据模型包括定向支出和不平等两个变量,但定向支出也是不平等模型中的一个关键自变量。两个主要自变量是投票率和选举波动性。主要的因变量是基于基尼系数中可支配收入来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研究的数据结构是时间序列的横截面。由于缺乏数据可用性,数据范围限于从1980年到2003年31个国家的数据。
(二)数据结果
1. 收入不平等对定向支出的影响
对新民主国家而言,选举波动、政府意识形态对定性支出具有积极的影响效应;而投票率、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则对定性支出具有消极的抑制作用。对于长期存在的民主国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促进了政府定性支出,而随着选民年龄的增长,会对定性支出起到消极影响。因此,投票率上升,这意味着以前低动员的群体(如穷人)将参加选举,迫使当事方转向扶贫的立场,选民投票率的水平会缓和波动对定向支出的影响。
2. 定性支出对不平等的影响
总体来说,模型结果支持定向支出对平等有不利影响的结论。定向支出在统计上显示了不平等的滞后影响。定向支出的直接影响是积极的,但统计上不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时,定向支出的增长会增加不平等。定向支出增长了1个百分点,不平等将增加0.09个百分点。如果增长了12%,那么不平等的变化就是1%。
调查结果还显示,纳入(滞后的)定向支出对这些工业化民主国家的不平等没有统计意义。这可能是因为劳动力市场覆盖率高,公共资金支出通过养老金、失业和其他福利覆盖大部分人口。这些国家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水平都很高,这表明每个人都受益于定向支出。总体而言,这些结果支持了本文的观点,即对新兴民主国家不平等的研究必须考虑定向支出的增加。
对于长期存在的民主国家来说,只有落后的不平等会对不平等水平产生持续的显著影响,其他变量影响不大。另外,通货膨胀和城市化会加剧了不平等,经济增长则可以减少不平等。经济表现的改善,对新兴民主国家的收入分配可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根据库兹涅茨曲线,新民主国家经济发展对不平等的影响呈曲线状。
结论
本文采用大样本跨国分析的方法,试图阐明欧洲第三波新民主国家在向民主过渡之后经济持续不平等的原因和方式,并进一步解释了欧洲新民主国家无法产生收入平等的原因。对学界而言,有以下几点贡献。
首先,理论和实证结果挑战了民主会减少不平等的传统观点。中间选民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穷人在选举过程中会有更多的发言权,迫使执政者重新分配资源给他们,直到实现中间收入向平均收入靠拢。然而,这一理论仍无法解释新兴民主国家的再分配政治。中间选民理论需要被完善修正。实证研究结果否定了以下观点:即从专制政权向民主政权过渡,由于增加了选举权和获胜联盟,将导致更高水平的公共产品。本文也反对布瓦(Boix)的观点:作为对大众公共产品和政策的需求回应,民主带来了更多的公共预算。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公共部门更关心为富人制定和执行政策。穷人政治的低参与度扭曲了新民主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然而,如果穷人动员起来并参与其中,情况可能有所不同。这样一来,即使在极端不稳定的选举环境下,也可能实现对穷人公共政策再分配的转移。
其次,本文修正了梅尔策(Meltzer)和理查德(Richard)提出的中间选民理论,提出了中间可能选民理论。中间选民理论忽略了历史、意识形态和公民社会组织化的利益团体与政党之间的组织联系,而中间可能选民理论看到了穷人低投票率、政治制度高度波动性的事实。它为认识新民主国家的再分配政治提供了一个更现实的图景。
第三,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由基弗(Keefer)等人发起的讨论,认为新民主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的信誉是一个重要问题,这将促使公共政策处于从属被利用的地位。各大政党在选举中缺乏有特色的政党纲领,社会政策处于从属地位,往往被用作争取另一党派选民的重要工具。政党选民基础日益趋同,这对公民福利和民主质量有一定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认为,政党选民基础的趋同减少了选民的福利,而分歧可以增加福利。但政党选民基础的趋同,增加的是有组织的公民社会团体的福利和政党核心支持者的福利,对穷人来说却并不如此。
总之,本文研究揭示了新民主国家出现了不平等这一令人费解的现象,并提出新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本文分析仅限于欧洲,本文的理论,特别是组织化的公民社会团体与政党、选举波动之间的关系,可能也适用于其他新民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