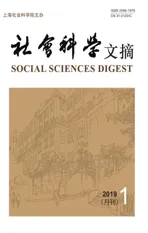清华简《厚父》与中国古代“民主”说
2019-11-17
清华简《厚父》公布后,因涉及《孟子》引《书》等内容,而备受学者关注。关于其思想主旨,更是引起热烈讨论。有学者认为《厚父》主要反映了古代的民本说,并将民本的产生推到夏商时期。其实,《厚父》所表达的并非民本说,而是作为三代意识形态的“民主”说,即“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本文拟通过对《厚父》的解读,对三代“民主”说的发展,以及春秋以后“民主”说的演变做出探讨,指出“民主”说才是中国古代思想哲学的母题,政治哲学研究需从民本范式转向“民主”范式。
一
“民主”一词在现有文献中虽出现于周初,但其反映的观念则渊源甚早,应该是随中央王权的出现而出现的。我们知道,夏代以前中国是邦国联盟时代,到了夏商周才出现统一的中央王权。随着中央王权的确立,“天命王权”、“王权神授”的观念随之出现,以说明王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所谓“民主”说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不过,“民主”说虽贯彻于夏商周的政治实践,被其统治者普遍接受,但在对于天、君、民及其相互关系上,不同时代又可能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据《礼记·表记》,殷人、周人在宗教信仰、政治治理上存在一系列的差异。在宗教上,“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而“周人尊礼尚施”,在祭神的形式下突出了伦理的内涵。在政治上,殷人“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突出权威意识,强化等级观念。周人与之不同,更重视亲亲,把亲亲置于尊尊之上,“亲而不尊”,讲究人情而待人忠厚。
殷、周宗教观念上的差异,前人多有讨论,而《表记》认为在政治观念上,殷人强化王权、重视刑罚,与周人有所不同,也是基本符合事实的。据《尚书·洪范》,殷臣箕子向武王进献的“洪范九筹”,其核心是“皇极”一项,而皇极就是要“惟皇作极”,一切以君王的意志为最高准则。而君王的准则,也就是上帝的准则(“于帝其训”),具有绝对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与强化“民主”的地位相应,在君民关系上,箕子则强调君王要做民之主,要绝对支配民,而不可听从于民。如果将殷人“从民所欲,则致国乱”的观念,与周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国语》引《尚书·泰誓》)的信念做一比较,不难发现二者的差异甚至是对立。
当然这样讲,并不意味着殷人没有保民、养民的观念,任何国家都是君与民组成的,所谓“民主”首先是民之主,没有民也就无所谓主。虽然古代的“民主”说一开始主要关注的是做民之主,是君对民的统治、管理和民对君的依附、服从,但随着对民之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就不能不涉及为民做主以及保民、养民的内容。清华简《尹诰》中商汤称:“非民无与守邑”,“吾何作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商书》中也有“施实德于民”(《盘庚上》),“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盘庚中》)。这只是统治者重民、爱民的一些说法,并未达到“以民为本”的地步,其在殷人思想中只居于从属地位。
与殷人不同,周人的“民主”说一是突出德,二是重视民,而不论是德,还是民,都为天所喜好和关注,故敬德保民方可得天命,为“民主”。在统治方式上,周人主张“明德慎罚”,慎罚并不是不要刑罚,西周政治理念之主流就是“软硬兼施”、“宽猛并济”,“德”、“刑”是维系政治秩序两种不同的方式,形成所谓“德、刑二元主义”。所以周人的“民主”说同样包括了保民、养民与治民、教民两个方面,既强调要为民做主,也重视为民之主,只不过由于周人突出了民与德,主张明德慎罚,其“民主”说较之殷人,更强调保民、养民和为民做主一面而已。明确了这一点,再来看《厚父》的思想,就容易把握和理解了。
二
《厚父》记载某王与夏人后裔厚父的对话,这位王即周武王。《尚书·召公》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监于有殷”,武王访箕子,《洪范》是也;“监于有夏”,武王问厚父,本篇是也。故《厚父》与《洪范》一样,应属于《周书》,而非学者所认为的《商书》或《夏书》,是周人对夏朝政治理念的记录和总结。不过由于殷革夏命后,夏人长期生活在商人的统治之下,故厚父的观念中也包含了商人的思想,受到后者的影响,实际融合了夏人、殷人的思想。《厚父》云:
惟□□祀,王监嘉绩,问前文人之恭明德。王若曰:“厚父!朕闻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启惟后,帝亦弗恐启之经德少,命皋繇下为之卿事,兹咸有神,能格于上,知天之威哉,问民之若否(注:犹善恶),惟天乃永保夏邑。……”
武王想借鉴夏人建立的功绩,了解其先王的恭敬显明之德,于是询问厚父。由于夏朝的第一位先王禹是通过治水获得天命,成为“民主”,故武王首先问禹治水事。由于禹治水有功,上天便赐给他民众,建立了夏邦。不过禹虽是夏朝的建立者,但按照当时的禅让传统,并不能传子,而是将王位传授给益。《孟子》记载此事:“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万章上》)这是从民本解释启之得位,认为启得民心因而得天下。
在孟子眼里,启是以德而得天下,而《厚父》则说:“帝亦弗恐启之经德少。”上帝虽然不满启的德行,但并不否认其天子地位,而是派皋陶为启的卿士,负责司法,协助其治理天下。而不论是启还是皋陶,都有神力(“兹咸有神”),能达于上天(“能格于上”),能知天之威严(“知天之威哉”),能察民之善恶(“问民之若否”),因而上天长久保佑夏邦。要是后来在位的夏王,如夏桀之流,不忘祭祀禹、启、孔甲“三后”,遵从他们制定的法度,就会“永叙在服”。武王问厚父他的看法如何呢?
厚父拜稽首,曰:“都鲁(注:叹词),天子!古天降下民,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之(注:至)慝王乃遏佚其命,弗用先哲王孔甲之典刑,颠覆厥德,沉湎于非彝,天乃弗若(注:赦),乃墜厥命,亡厥邦。惟是下民,庸(注:均)帝之子,咸天之臣民,乃弗慎厥德、用(注:以)叙在服。”
对于武王的疑问,厚父以天设立君、师的职责和目的作答。由于这段文字与《孟子》引《书》内容相近,颇受学者的关注。然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厚父》与《孟子》引《书》文字虽然近似,但内容并不相同。《孟子》引《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梁惠王下》)虽然《厚父》与《孟子》所引《书》都主张君权神授,认为“天降下民,作之君”,属于古代的“民主”说,但在思想倾向上又存在明显差异,前者突出治民、教民,后者强调保民、养民。从《厚父》到《孟子》引《书》,正反映了“民主”说内部的发展和变化。
有学者注意到,在后人的记述中孔甲乃是一“淫乱德衰者”。但在《厚父》中,孔甲被称作“先哲王”。出现这种情况,显然与“民主”观念的变化有关。虽然都是谈“民主”,但夏人、殷人强调做民之主,重在树立权威,加强对民众的统治,所以突出刑罚的作用。而周人则主张为民做主,提倡“敬德保民”、“明德慎罚”,试图以德来协调部族间的关系,增加其归附和向心力。
综上所论,《厚父》是武王访于夏人后裔厚父的记载,性质类似于《洪范》,只不过前者是“监于有夏”,后者是“监于有殷”。由于厚父长期生活在殷人的统治之下,其思想也可能包含了殷人的观念。武王访厚父,目的是了解其“前文人之恭明德”,以夏为鉴,敬德保民,治国安邦。但厚父对孔甲之典刑的推崇,对夏桀亡国的总结,与周人观念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厚父所言,对于武王可能只具有反面的借鉴意义,而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晁福林先生曾分析指出,箕子所陈《洪范》九筹并没有为周人所接受。类似的情况同样也存在于《厚父》这里。《厚父》虽然在政治实践中没有发挥作用、产生影响,但就思想史研究而言,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难得的了解古代“民主”思想的珍贵文献。
三
周人具有了民本的萌芽和观念,但还不具有完整、独立的民本学说。周人的政治理念依然是“民主”说,而“民主”从根本上讲是君本,周人的民本的价值理念与君本的实际追求混杂在一起,共同构成“民主”说的基本内容。
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国人地位的提高,并在政治领域开始发挥一定的影响和作用,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左传·桓公六年》记随大夫季梁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夫民,神之主也”是“夫君,神之主”的反命题。“夫君,神之主”是以天命、神意的形式肯定了君本。而季梁“夫民,神之主”的命题则扭转了传统的认识,认为民才是真正的主祭祀者,故是以天命、神意的形式肯定了民本。
又《左传·文公十三年》记邾文公就迁都于绎一事进行占卜,结果出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的情况。当时邾文公已在位51年,年事已高,经不起迁都之劳。“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当国君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邾文公依然选择了后者,认为国君的利益是从属于民众利益的,民众既然得利,君主自然也有利,这当然是一种民本思想,是对周人保民、养民说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
不过春秋时期,虽然民本思想得到一定发展,但在现实中依然是以君为本,故当时更多的思想家是试图将民本与君本协调、统一。《左传·襄公十四年》记师旷对晋悼公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师旷认为“天生民而立之君”,职责是“司牧之”,不同于邾文公的“以利之”,所强调的是教民、治民,而不是保民、养民,主要继承的是《厚父》的思想,是对后者的进一步发展。不过师旷生活于民本思想得到发展的春秋时代,不能不受其影响,不能不考虑约束君权的问题,这样他又试图立足于民本来限制君本。
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虽然有所发展,并与君本思想产生紧张、对立,但思想界的情况是复杂的,有人试图从民本突破君本,也有人试图调和民本与君本。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民本是孕育于“民主”说之中,是从后者发展出来的,故往往与君本纠缠在一起。很多人是在治道而不是政道上谈论民本,是在君本的前提下倡导民本,民本无法上升为国家最高的价值、政治原则,即使有一些闪光的民本思想和举措,也无法突破现实中的以君为本。这样实际上是二本,政道上是君本,治道上是民本,而无法真正做到一本——以民为本。
要想突破“民主”的束缚,真正做到以民为本,就需要从权力私有走向权力公有,从“君权神授”走向“君权民授”。战国时的儒者某种程度上已认识到这一点,《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天下为公”指权力公有。而要实现权力公有,就需要“选贤与能”,把最有才能的人选拔出来,替民众管理天下,此乃理想之大同之世。大同社会虽有君、有民,但其关系不同于权力私有的小康之世。
《礼运》之后,孟子、荀子两位大儒均接受“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但在对民本与君本关系的理解上又有所偏重。孟子曾以尧舜禅让为例,说明天下非天子的私有物,而是属于天下民众的。舜的天子之位既来自天,也是民众的授予。而在孟子这里,天是形式,民众的意志、意愿才是最高目的。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民为贵”不仅是价值原则,也是政治原则,不仅认为民众的生命、财产与君主、社稷相比,更为贵重、重要,同时也强调,国君的职责、义务在于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否则便不具有合法性,可以“革命”、“易位”。
不过在经历了燕王哙让国失败之后,孟子对“选贤与能”、实行禅让持保留态度,认为“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万章上》),表明他不再看重禅让与世袭的差别,不再强调对于天子、国君选贤与能的必要。孟子放弃禅让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抉择,具有某种无奈甚至必然,但对其民本思想则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使其无法突破君本的束缚和限制。孟子的思想或许可以概括为政道上的民本,治道上的君本,至于政道与治道如何统一,则是其没有解决的问题。
如果说孟子主要继承了周人“民主”说中的保民、养民说,以及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而向前做进一步发展的话,那么荀子则更多地吸收了古代“民主”说中的治民、教民说,同时与保民、养民说相调和,因而其与《厚父》的内容多有相近之处。
从荀子的论述来看,其所谓的“以为民也”,实际包括治民与养民两个方面,是对《厚父》以及周人思想的折中与调和。在荀子看来,君之为民,首先是制定礼义,确立法度,使民众摆脱“偏险悖乱”的困境,以达到“正理平治”的结局。所以治民与养民是统一的,只有治民,才能养民;只有建立起礼义秩序,才能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和物质利益。荀子的“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实际是指治民以养民,它虽然具有民本的性质,但也强化了君主的地位和权力。与孟子不同的是,荀子并不强调君主的权力需要经过民众的授予,这就使其权力公有的观念大打折扣。
荀子的君民思想,似可概括为政道上的君本、民本混合,治道上地地道道的君本,实际是对古代“民主”说中教民、治民说与保民、养民说的折中与调和,但同时又做了进一步发展。从这一点看,真正与《厚父》思想相近甚至可能受其影响的应该是荀子,而不是孟子。
综上所论,三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乃“民主”说,包含了做民之主和为民做主两个方面,并呈现出从强调教民、治民到重视保民、养民的变化。春秋以降,“民主”的发展演变实际存在三条思想线索:一是突出古代“民主”说中蕴含的民本思想,由“民主”而民本,以春秋时期的邾文公、战国时期的《礼运》、孟子为代表,并经明末清初黄宗羲,下接近代的民主,构成了“民主”——民本——民主的思想线索。第二条线索是将“民主”说中的君本、民本相融合,既强调做民之主,又要求为民做主;既肯定君主治民、教民的合理性,又要求其保民、养民,照顾到民众的利益。这条路线以春秋的师旷、战国的荀子为代表,秦汉以后更是大行天下,成为两千年帝制的主导思想。第三条线索则是继承“民主”说中的君本说,发展为尊君卑臣、崇君弱民的思想,所谓“天主圣明,臣罪当诛”,其在法家思想以及后世的政治实践中不绝如缕,发挥着作用。以上三种思想都源自古代“民主”说,是从后者发展分化出来的,“民主”说才是古代政治思想的母题,搞清“民主”说的具体内涵和发展演变,才能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做出全面、准确的把握,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需要从民本范式转向“民主”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