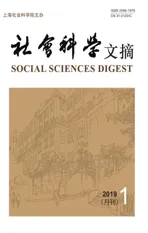行刑鸿沟:实然、根据与坚守
——兼及我国行政犯理论争议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2019-11-17
行政犯是一个兼具立法论与司法论性质的问题。行政犯自被纳入刑法的视野以来,已然成为了一个难解甚至无解的课题。行政犯问题的核心在于行刑关系,解决问题的关键当是定位与处理好行刑关系,以提出有效解决二者关系的可行方案。由刑法的独立性所决定,刑法在选择处置行刑关系的原则时,涉及四种基本类型:极端从属性、完全从属性、相对从属性、相对独立性。基于行政关系认识混乱所导致的罪责刑的“貌合神离”,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则突出表现为罪不当罚与罚不当罪两种类型。近年来,在刑事司法学界引起广泛争论的典型之案例,进一步诱发了对行刑关系处置原则的争论,并通过无罪而罚的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轻罪重罚的闫啸天非法猎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有罪不罚的常州毒地案,重罪轻罚的长春生物疫苗等案件,而达至激化的状态。凡此问题,均涉及行政犯的理论困境与解决路径之问题。
行刑冲突解决机制探寻:“行刑鸿沟”的提出与论证
(一)行刑鸿沟之意义
行刑关系并不是零和关系,二者之间更非一条简单的分界线,尽管存在着出乎于行(行政不法)而入于刑(刑法不法)的基本观念,但是,如此简单地将行刑关系理解为一“线”之隔,则是大为错误的。跳出行刑关系属于“线”性关系的思维,转而认为行刑之间存在有宽度的“鸿沟”,那么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合理解决。“行刑鸿沟”就是在坚持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是法系统中两种独立评价的前提下,根据犯罪化的一般标准,就行政不法向刑事不法的转化条件所设定的应然区间。行刑鸿沟意味着,刑法会对一定行政不法加以容忍,刑法并非是将所有溢出行政不法的行为均纳入其评价的范围。据此,行政犯的成立公式可表达为:“行政不法+鸿沟要素=刑事不法”。
(二)行刑鸿沟之实质
行政犯的正当性,并非是任何由法律规定的“恶”而就自然地具有了刑法所要求的、等同于自然犯的“自体恶”性质,这是由刑法的犯罪化根据所决定的。当一项行为违反了行政法的规则秩序,就满足了行政法上“恶”的要求,但是,只有在此违法行为有造成刑法所保护的核心价值与利益体系的积极减少时,才能认为有搭建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沟通桥梁的必要,此时才可能具有刑法“恶”的性质,行为对造成核心价值体系减少的程度,则决定了刑法“恶”的程度。因而,行政不法能够被认定为犯罪的起点,必须是该行为造成了核心价值与利益体系的积极减少。
(三)行刑鸿沟之根据
1. 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有何差别?
行政不法的量只关注行为对相关规范的违反程度,而选择性忽视其他问题。刑事不法的“质”是由法益是否被侵害所决定,法益被侵害的程度则决定着刑事不法的量。因而刑法关注的范围更广,其不仅关注造成损害的行为,而且关注损害的结果,即只要存在核心价值体系(法益)的积极减少,都属于刑法关注的范围。
2. 行政不法能否仅因量的增加而转变为刑事不法?
应当认为,质的差别,不能以量来填补。原因在于,秩序与其代表的法益都是抽象的概念,对秩序的侵害,只有规范是否被违反可以确定,而对秩序的侵害程度则不可计量,只能通过行为的恶劣程度或者结果的严重程度来虚拟出秩序的侵害程度。因而行政不法的质是由规范是否被违反来确定的,行政不法的量是借助“少增加”的幅度来确定的,当涨幅为零时,行政不法的量达到极值,所对应的表现为该行政领域的秩序瘫痪。
“行刑鸿沟”的跨越:行刑关系转化实质要件的论证
(一)“基础型”行政犯行刑关系转化要件:行政不法+主要价值减损
1. 主要价值是指核心价值体系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而具体确定核心价值的最简易方法可以参照刑法分则的章节规定。对于核心价值的认定,可以大体参照刑法分则的章节进行,但是需要进行一定的修正,因为刑法分则的章节并非全部是依照某项犯罪所侵犯的主要法益来归类的,也可能会因为行为外观的相似性和前置法的统一性而被归为一类。主要价值是指原始价值与其衍生价值。原始价值是指自人类社会存在以来就最为重视的价值——人身价值与财产价值;衍生价值就是随着社会进入发展状态之后而在原始价值的基础上进阶的价值。衍生价值与原始价值是高低位阶的关系,二者各自独立,又水乳交融。
2. 价值减损是认定结果无价值的关键,对于人类核心价值的侵害,可以较为直观与具体。对于衍生价值的侵害,则较难直观判定,尽管可以通过将之还原为核心价值后再进行判断,但是,其实该价值已经先于核心价值而受到了侵害,并且已经能够体现为核心价值的侵害,所以为防止法益保护的过度滞后,通常需要对侵害行为进行预先的设定。而这种预设的前提与标准,就是需要对能够造成核心价值的通常性侵害的行为进行抽象与类型化。因为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都是定性与定量的统一,因而行为对核心价值侵害的抽象危险,要认定为是对派生价值的实害,就需要辅助一定的情节来进行认定。
(二)“补充型”行政犯行刑关系转化要件:行政不法+主观恶性+次要价值减损
1. 次要价值与主要价值的界限并非十分明确。首先是因为价值的抽象性与其抽象程度不同,会导致价值概念在逻辑层面的交叉。其次是不同价值之间难以比较,如同田忌赛马一样,次要价值的高损害与主要价值的低损害难分伯仲。最后是行为的复合性,会造成价值侵害的事实层面交叉。因而在认定一项犯罪是侵犯何种价值时,应当根据其主要侵犯的价值进行判定,而不能根据价值的重要程度直接认定。而对于认定次要价值依然应当从刑法分则的章节确定的价值中进行筛选,标准是无法将主要部分直接还原为人身、财产价值的,应当认定为次要价值。
2. 次要价值的缓和性,使得价值侵害处于极度分散的状态。价值减损无法被直接估量,同样只能借助于人身、财产的损害来间接衡量,而此时的损害结果早已经发生,因而,对次要价值的保护同样应当提前于人身、财产价值的保护。如果在次要价值的损害能够体现在人身、财产之上时,则意味着刑法保护过于滞后,同时,因行为对此类价值的侵害较为缓和,且次要价值在核心价值体系中处于第二等级,所以应当以人身、财产价值出现具体危险时来认定。通过一定客观化的结果来实际确定主观恶性的大小是妥当的,而具有主观恶性的行为,其入罪的最低标准需要参照前置法中的保护规范。因为一般违反前置法中调整规范的行为,能够被前置法中保护规范处罚的,就应该属于是不满足刑法的刑事不法要求的行为。但如果行为人在反复被前置法处罚后再次实施同类行为,而被刑法认为具有刑事不法性的,那么就应当认为是行为的主观恶性较大,满足了造成人身或者财产价值的具体危险,进而能够被认为是造成次要法益的减损。因为是通过具体的行政处罚次数来认定主观恶性,就应当认为多次实施便是最低程度的客观化结果。因而当主观恶性已经能够通过一定客观化的结果表现出来时,就应认定该行为造成了次要价值的减损,而应当构成相应的行政犯。
(三)“特殊型”行政犯行刑关系转化要件:行政不法+不履行义务+特定价值减损
1. 真正不作为:违反命令规范+价值减损失控
对于真正不作为的行政犯,尽管刑法已经明确了各项标准,没有太大争议,但是,应当认为,行政犯中的真正不作为犯,其刑事不法性应当由是否会造成价值减损的失控状态来衡量。如果仅在校区里游行示威,被责令解散而没有解散的,因为价值减损并不会呈现失控状态,因而不应认为相关人员构成犯罪。
2. 不真正不作为:行政不法+危险前行为+实害结果
就行政犯而言,其存在两种不真正不作为的类型。(1)当特定价值有减损的风险时,负有行政法赋予义务的主体应当履行义务而不履行,导致价值减损的,应当认为是不作为犯罪。(2)当主动违反前置法的行为,创设了特定价值减损的风险,应当排除或者控制风险而未排除或者控制,导致特定价值减损的,应当认为是不作为犯罪。前者的义务来源于法律义务,后者的义务来源于先行行为。另外需要认定的是,价值减损的含义。因为前置法并不关注行为的主观,违反前置法的行为在是否追求价值减损上,也即追求刑事不法上,表现的罪过形态更为模糊,故刑法中的不真正不作为的行政犯并不能从行为无价值上进行判断,行为等价性理论也无法适用。
“行刑鸿沟”价值功能的实际验证
(一)无罪不罚的正反验证
1. 正向验证:赵春华案
从理论逻辑上看,持有行为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状态,具体说应当是占有状态,但是占有状态从形式上判断并不是典型性、类型化的行为,因而需要实质判断“持有”这种特殊行为能否具有类型化行为的特点,因此就需要观察“持有”能否创设出对人身或者财产价值的抽象危险。从事实上看,本案中的持有枪支行为,即使处于辅助状态,甚至是属于吸收犯中的从行为,也不会造成对人身或者财产价值的任何实害,因而本案中的持有,并不会创设人身或者财产价值的抽象危险,也即不会造成公共安全价值的减损。并且,借助对人身或者财产价值的抽象危险来确定公共安全价值的侵害,仍需要一定的情节作为填充行刑鸿沟的条件。在本案中,并不存在这种能被视为公共安全价值减损的情节,所以本案中的持有枪支的行为并不符合第一项要件。因主要价值重要性高于次要价值,所以需要再对比第二项要件,按照上文的逻辑,本案中的持有行为即使有后续行为,例如持枪杀人,也只能认为是不能犯,不会对人身或者财产价值造成任何伤害,所以持有行为就不会存在任何的危险,无论是抽象危险还是具体危险。同样,借助人身或者财产价值的具体危险来确定次要价值的减损,也需要存在一定的客观结果。本案中,并不可能存在这类结果,故本案中的行为,也不符合第二项要件。如果将持有视为不作为,那么就需要看第三项要件,非法持有杀伤力的枪支,确实可能会有价值侵害失控的概率,但是,本案中,不作为的行为并不会使得特定价值出现减损的风险,更不会因不履行作为义务而造成特定价值减损。当“持有”完全不会创设人身或者财产价值的抽象危险,那就意味着不会造成公共安全价值的侵害。所以,本案的行为,自始即不符合刑事不法的标准与要求,更无须在刑法视域内讨论其出罪的问题。
2. 反向验证:富乐假药案
已经被行政处罚的生产假药行为的行政不法性不言自明。而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尽管是规定在以经济价值为主的刑法分则的章节之内,但是,该行为对公共安全价值造成的侵害必然大于对经济价值的侵害,应当认为生产、销售假药罪侵犯的主要法益为公共安全,而无论是经济价值还是公共安全价值都是主要价值,所以应当看行为是否符合第一项要件。对于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在形式上看,其实是一种欺骗行为,认为其符合类型化的行为是合理的。再从实质上看,银杏酸是一致公认的潜在过敏物质,是自然界中最强烈的接触性过敏源中的成分之一。所以不合格的银杏提取物是具有人身危险性的,生产该类假药的行为,已经能够造成人身损害的抽象危险,而且从处罚的情况来看,用于表征的情节已经十分严重,所以认为该公司的行为满足第一项要件,认定具有刑事不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借助行政处罚来规避刑罚,使得行政处罚成为犯罪的“保护伞”,是完全与现代化法治相背离的。因而必须通过“行刑鸿沟”明确入刑标准,明晰行刑关系,让犯罪无空可钻。
(二)有罪当罚的正反验证
1. 反向验证:深圳鹦鹉案
非法出售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是行政违法行为,具有行政不法性。珍稀野生动植物属于核心价值体系中的环境价值,而环境价值其主要部分并不能够直接还原为人身或者财产价值。尽管环境与人身或者财产愈发休戚相关,但是,从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环境价值是人类伦理道德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衍生价值。从目前来看,将环境价值理解为次要价值是较为合理的结论。所以,直接从第二项要件进行考察,先从形式上看,行为的主观恶性尽管说有直接客观化的结果可以表征,但是,非法出售自己繁殖的珍贵动物的主观恶性,并不等同于在禁猎区、保护区的猎捕野生动物后出售的主观恶性,所以仍需要从实质上考察,即,行为是否会造成环境价值的减损。如果说猎捕野生动物后出售,确实会对社会的财产价值产生侵害的危险,但是自己孵化、培育的野生动物,其实是在增加相应的价值,即使是自己培育后又杀死,也只能认为损害了“虚增”的环境价值,而并非是造成实际价值的减损。所以应认为出售自己繁殖的珍贵动物,并不是刑事不法行为,应当认为只是行政不法行为,或者最大限度地被认为是仍处于行刑鸿沟中的行为,并不存在成立刑法不法的条件。
2. 正向验证:常州毒地案
基于上文分析,目前的环境价值是次要价值,故带入第二项要件中加以观察。从形式上看,化工厂的主观恶性在客观化的结果上表现为对土质和水资源污染的严重程度。尽管没有全面的数据,但是从已知情况看,该地块地下水和土壤中的氯苯浓度分别超标达94799倍和78899倍,所以认为该客观化的结果可以表征主观恶性已足够充足,造成数百人不同程度中毒这样的侵害结果,也足以认为化工厂污染环境行为已经造成环境价值严重损害。所以应当认为该行为能够满足行刑鸿沟的跨越条件。即,该行为是污染环境犯罪,应当根据污染的严重程度确定刑罚的适用。
结语
虽然将具有行政不法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视域之内,再实质讨论其出罪与入罪的问题,同样能够取得类似的效果,但是有罪推定的思路实不可取。必须置身于刑法之外,立足于行刑鸿沟之中,来实质审查行政犯的存在与否。明确三项实质转化要件,不仅可以取得实质出罪的功效,更能够提供实质入罪的基本路径,这一环节恰恰是司法实践最亟待解决行刑矛盾的钥匙。徒法不足以自行,行刑鸿沟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正是在于,为理论与实践创造了协同的契合点,行刑关系的明晰与实质要件的确立,已然开始推动司法实践由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迈进。但是,“罪与罚”只是实质正义的最低要求,“罪刑均衡”才是实质正义的核心追求,因而,希望行刑鸿沟理论能够作为追求“罪与刑”的敲门砖,开启追寻实质正义之路。现行行政犯入刑标准的终点也是行刑鸿沟理论的新起点,对现行司法层面的协调,尚无法应对新生立法层面的挑战,所以,行刑鸿沟理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