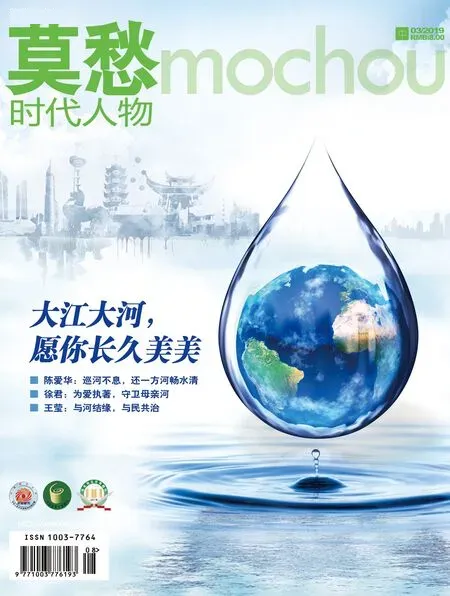马春苓与一战百年
2019-11-14徐旸
文徐旸
在法国巴黎市中心有一块华工纪念碑,上面用中文与法文刻着:“公元1916-1918年,14万华工曾在法国参加盟军抗战工作,有近万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是历史的见证,14万中国劳工用血与汗铸就的丰碑。
不出深井,不知天地偌大
1913年,有一位名叫马春苓的年轻人顺利考入山东临朐县一所师范学校,他自幼聪敏,喜读经籍,16岁便能写八股文。毕业之后,马春苓进入了当地一所小学,担任教员。
之前,在马春苓考入师范学校一年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全面爆发。几年时间内,便席卷了整个欧洲。而在远东的中国,虽未直接加入战局,但是也受到了波及。在这种情势下,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开始关注起那片遥远的西方土地,好奇中亦满含着隐忧。
彼时的中国,新兴思想已经进入。整个社会在新旧交替间,逐渐出现了多种思潮。这场看似遥远的战争将社会的安定表象撕开了一个缺口,除却看见了现代工业带来的坚船利炮,也看见了血色之中的熹微曙光。马春苓觉得自己一直以来就像是一只井底之蛙,可透过这几年间的种种新闻,却从四周的混沌中看见了一线天光。于是他一边传道授业,一边关注欧洲战局。等到1917年,英法求援北洋政府,请求外派一部分中国劳工支援欧洲战场时,马春苓奋然陈词:“今日之举,既能增军事之新学识,又得偿游历之夙志愿,时哉弗可失矣!”于是马春苓放弃教职,义无反顾地成为了中国劳工中的一员。
大义所趋,死生何惧
1917年10月22日,马春苓辞别了娇妻弱子,与3430名同伴坐上了前往欧洲的轮船,沿途,他第一次直面了真正的战争。为了躲避德国潜艇的堵截与攻击,他们不得不绕道日本,取道美国与加拿大,辗转前往欧洲。数月的水路奔波,每个人都疲惫不堪。当轮船漂浮在浩浩荡荡的太平洋上时,那个曾经想象过无数次远方的马春苓,在日记中写道:“惟见碧浪滔天,弥望无际,岛屿不见,飞鸟绝迹,彤云密布,朔风砭肌,直令人惕然而惊,亦惨然而凄。惟伏处仓中,欹枕长卧而已。”但即使风浪滔天,孤独、恐惧与晕船不停地侵袭着他,他却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此行是去支援正义的战争,因此他觉得,大义所趋,死生一之,又何惧乎!
经过两个月航行,1917年12月,马春苓一行人抵达了驻扎营地。
刚刚到法国的时候,马春苓被派到加莱西北部的工厂,虽然不需要冒着枪林弹雨,但夜间时常会遇上飞机空袭。有一次炸弹就在离他数百米的地方爆炸,白日里一起工作的工友,可能第二天便已经生死相隔。对死亡的恐惧徘徊在劳工们的心底,马春苓在那里提心吊胆呆了七八个月,最初的激动与好奇逐渐被现实炸得粉碎。由于晚上经常遇袭,有时一晚上要换好几个避难所,因此没有一日可以解衣而寝。加上英法对劳工的严格看守,更令马春苓感到压抑。这个时候,他萌生了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记录下来的念头,这便有了后来的《游欧杂志》。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战火与汗水,渐次汇聚于马春苓的笔下,正如滴水入海一般,他将自己这段时日以来的感触,都写进了集子里,从最初的好奇憧憬,到路途中的忐忑不安,再到而今的艰难困苦。每当累倒在异国他乡,听远方传来依稀的枪炮声时,他总会怀念起万里之外,那一盏故乡的明月光。眼前耳畔,异国的风景与语言冲击着观感,而心间笔下,那些流淌的文字,却满怀着恋乡的情愫。
除了书写一路所见之外,马春苓还重点考察了沿途的风俗物产,并以冷静而睿智的笔触,分析了世界在一战前后的格局与趋势。书中有叙述,有议论,有时还有诗歌:“荒野蓬蒿千宅绿,颓楼牖户万家通。昔年黎庶堂前燕,遁入战壕铁屋中。”(《吊比国街市》)蓬蒿丛生,哀鸿遍野,满目疮痍,当中式的意境被植入比利时当时的情景之中,马春苓在心有戚戚之余,愈发坚定了自己当初的誓言:“大义所趋,死生一之,又何惧乎!”
两载春秋,志士来归
1918年11月,历时四年多的的一战终于结束。次年8月22日,马春苓终于等来了可以回国的消息。一时间,狂喜与激动梗在了心头,他在《游欧杂志》中写道,听闻可以回国之后,“阖队欢欣异常,白叟拍掌而相庆,黄童舞蹈以欢呼!歌声笑语,彻夜不休。”那些劳工们,在去国怀乡经年之后,终于可以回到故土,怎能不喜?有近万人,已经长眠在了异乡冰冷的泥土之下,暴烈无情的炮火之中。能够活下来的,都是战争的幸存者。
同年12月28日,马春苓终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临朐县。
那时,离他作为劳工奔赴欧洲,已经过去两年时间。到乡之后,他才发现已然恍如隔世:田地早不耕种,老母双目失明,临行前抱着父亲不愿离开的四个孩子,看向他的眼神里也多了几分陌生。甚至那个意气风发、曾立志要劈开眼前帘翳、游历求知的自己,也已华发早生。两年间,他经历过太多波折磨难,见过太多死别生离,看到过漫天战火下的残酷与温柔,也领略到异国的“水陆山原之异势,飞潜动植之殊态”,这些经历不仅拓宽了他的视野,也丰富着他人生的厚度。
穿越百年岁月的《游欧杂志》依然在马春苓的后人手中代代相传着。记忆不会风化,历史闪烁在字里行间,让后来者知道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可贵,知道先辈们曾为此付出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