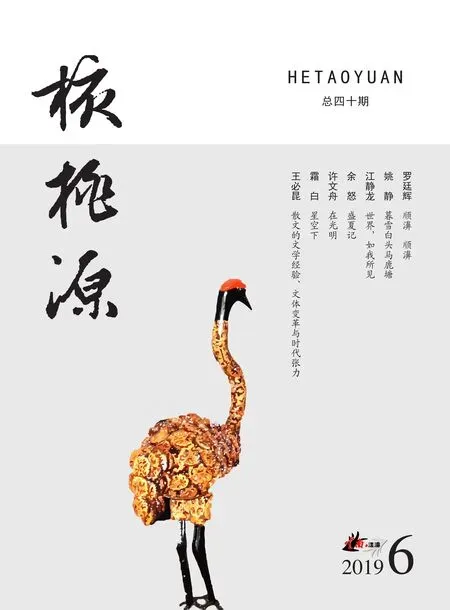父亲的犁牛
2019-11-14
父亲一生养过三架犁牛。
第一架是从爷爷手里接过的尖国(角)与阿崅。那年,父亲18岁,犁牛14岁。“尖国”无疑是从他那对大角得名,可“阿崅”除了贴合它那对壮、状如芭蕉,还有着与芭蕉一样老裂痕的大角外,跟它的年龄也刚好相符。似乎幼牛叫阿崅就不好听了。就像“果果”多可爱的宝贝,可当他40岁时,若不冠上张、李、陈姓,叫着别扭。又或许,这个名字在彝语牛文化里的确存在着迷一样的色彩,遗憾我一直未打开这个惑口。
牛是一架熟牛,可18岁的父亲是新犁手,他往往不知道该在这道坎边打个小转,以致留下个小毛埂或是让牛空拖一趟犁。也不知道地边绍到哪里最恰合。还老是唱错牛诀,只是他唱错,牛却不走错,那是它们走了半辈子的老路,爷爷带它们从岁月深处走来,它们带父亲往春光明媚走去。子承父业的路总要好走一些。
父亲29岁时,已然成为了驭牛娴熟的老犁手,可一架“老者”已拖不动犁尖穿透那粘绵的黄胶泥。爷爷说:“卖了吧”。留下尖国做掌杆牛,阿崅被人牵走了。不敢看它那大得藏不稳忧伤的眼睛,更不敢想象它低头走前时没有割舍这个家。三次回稍,都是顶着月色而来,当父亲拉开木大门时,一对芭蕉角已顶在眼前,父亲也哭了。
那时,家里牛、羊多。不仅犁牛有名字,闲牛也有,红胖,白香……小时候只喊小牛,稍稍大些就给叫上名字。羊却没有,给领头羊叫上查国(角)、青母羊什么的就行。一村子的牛、羊撒在大荒地,一村子的娃娃在地上抓石子、捏泥人。煽牛高叫对阵,牯牛低吼,牯牛的峰堆在害怕煽牛的压抑中一天天堆高。有些煽牛虽然卖了,但它拗过国(角)根的那道土坎还留下印迹,得好几年才能长上青草。
真是计划不如变化,预留做掌杆牛带生牯子的尖国却在春耕前摔断了腿。父亲只好拴起一架生牯子,惊鸿和曼团——父亲的第二架犁牛。
曼团体型粗圆,芋头角,一身毛色红润,两扇屁股间呈滑溜溜的沟状。惊鸿是头健杆牛,角不大,也似芋头状。无论如绸缎般红亮的毛色还是拉地的本事,都不负“惊鸿”的盛名。到中年些,坐实了膘,倒与曼团成了一架外型很搭的老搭档。
选一块平滩地教生牛。一架生牯子怎么甘愿被一根牛皮脖索拴在牛杆上,用不撞倒南墙不回头的粗脖子往两处拉扯。牵筋往回拉拽倒也没把牛杆拽翻过那两坨小山包似的峰堆。爷爷挥着柱棍东哟西指,母亲背着娃儿牵着套在惊鸿两角上的麻索。牛旋着打个转,绳头不是踩进牛的蹄夹子里,就是绕进了犁与牛绞成的乱圈中。一家人在黄灰四起中也治服不了这架生牯子。父亲哪怕喊破喉咙,它们除了听不明白牛诀,根本也不会听凭父亲指挥。
父亲对爷爷和母亲说:“你们让开,横拌直拌我一个人拌”。父亲卸了犁,左手拿麻绳牵着惊鸿的头,右手用鞭子围着曼团屁股。赶到那边地头,又围转这边地头,中间也有牛执拗跑偏,还是被哄回原路。无数次往返,牛渐渐明白了,即使有再大的雄心壮志,它们需要做的不过是从田边走到地头。知道了只需做一件事,就能把这件事做好,甚至往与返都要在父亲的一声“喔列”中才得以转换。套上犁时,已渐渐能画出一些整齐的线。惊鸿首先明白了这一点,在一次曼团硬挤向它欲强脱轨时,它转头给对方一角。在父亲的“刻子挖啥(太能干了)”一声大赞中,惊鸿荐升为掌杆牛。
“骡靠驮板,牛靠犁板”,从教生牛的那天起,牛和父亲都没有歇过。如曲腿的犁弯,似卧躺的犁底,通过像足麻花的小扣(以致我们称麻花为小扣糖)连接牵筋与牛扯上关系。牛杆中间有三道印,牵筋拴在中间一道叫平杆,左移则给左牛背一杆,需要多使力,右移也一样。犁尖探进湿热的土里,掀起的土块在犁板上往两边分开。坡地,上分的土少,往下的土,若粘性好的,可以拉过尺把长的土把子,上面铁磨留下的呈亮,经太阳一晒,会变得如铁般坚硬。以致忙种时节,在清朗的月色下,也能听见锄头敲碎土把子的闷闷一声声“砰……”。
农村里一直沿袭换工做活,互帮互助。犁地的时候,从下至上,每人犁一搭地,新翻的一溜看得见潮色,未犁的干着,整片地的下半部分便呈现出干潮相衔的条纹,牛架在各自的衔口上缓缓移动。犁完一搭,上翻一页,整个部分又在地的上半部分重复。
越近黄昏,牛诀唱得越悠长。不管是习以一辈子只需做一件事的安然,还是苦于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的叹息,都只用伸长脖子到地头来表达。看阳光退出大地的模样,看阳光在牛毛上弹起,再看牛毛深吸暮色,寒来暑往皆在犁沟间重复。
解牛了,牛在通向炊烟的阡陌上缓缓行走,父亲扛着犁在后跟着。有时,犁尖的宽平处会站着一个小孩,越过父亲的肩头向后看着手茧打磨光滑的犁把手,仿佛星光、月色落到上面也会迸散四溅。
惊鸿与曼团也老了,卖了。那年父亲56岁,又有了第三架犁牛,花脸与草白。
花脸与草白来不及变老,就赶上了犁行的大变革,犁地机代替了犁牛。年纪轻轻的闲在圈里,拴在田边地角,或是荒地里晒过冬天。偶尔去犁犁坡地,也因不常锻炼,不好犁。再后来,核桃绿了坡地,它们就更闲着了,又闲了两、三年便卖了。
那年,父亲67岁。往后再没养过犁牛。
邻家螺子
大乌嘴是邻家的骡子,全身灰黑毛色。若以貌取之,并不被待见,缎子黑、枣红骡比比皆是。因嘴筒处毛色深些而得名。鬃毛也不似我家海流马鬃般雄帚的立着,特别靠前那一撮,像极了黄毛歪分的二流子,我这样回忆着。可当时,我是怕极了它的,怕它的嚣张跋扈,稍有不耐,就背着耳朵歪抬起头,欲先侵犯,嘴里还带着啍啍的威胁。
要说起驮驮子,大乌嘴可是一流,吃重、又会掌驮,左右稍有点不平衡,它也能把驮子安然驮回家。有遇到别家骡子驮不了剩点东西,润喜叔总是说:“拿来,加在大乌嘴上。”有老人或小孩也总让骑在大乌嘴上—安全。就像船遇到水能乘风破浪,担起责任它是虔诚的信徒。
它的跋扈也是让村里人受够了的。只要闲拴在田边地角,它总能想办法脱疆,铁扎嘴拴得住别家骡马,唯独套不牢它的乌嘴。飞扬四蹄奔跑在村路上,高昂着头颅,不见一丝奴性,反倒是海阔天空任它行。把上村的村围、稻坵、鸡飞狗跳以及围追它的凌乱、高喊的队伍甩在蹄后,又横行向下村的村围、稻坵、稍后的鸡飞狗跳以及前来堵截的凌乱、高喊的阵营。见人甩头扬蹄恐吓,遇猪鸡则横行越过。
水塘靠近箐边,中间有一小段林荫秘道。左边塘埂,右面树荫,只有站在前后,才看得见路上的情形。那天,也是一场围追堵截的混乱,而我险些在那场混乱中丧生。大乌嘴极熟悉村中的路径,要想到下坝荒田里撒蹄,必须经过那段林荫秘道,而夏日炎炎,那里也是我准备“搭窝过日子”的小家呀。大乌嘴钉着马盏的铁蹄从我脑瓜上跃过,父亲却以为我肯定不会幸免。当他扑到我身上看着我完整的脑瓜子,半道上窜出的那股怒火竟化成了热泪。那急匆匆的几秒里,父亲是这样想的:“一定要端出老火枪,一枪崩了大乌嘴”。此时,电影中俊马四蹄紧收的俊美模样跃入脑海。可嘴上对大乌嘴的憎恶是不会少了,“这匹劣骡,翻主子紧了”。润喜叔撵上骡子拴在我家门前黄梨树上,与父亲“哈哈……”闲唠。
没踢坏我的脑瓜,也没踩死过一只鸡,大乌嘴也没被翻主子。不变的日升日落、四季更宕,不变的隔三差五的围追堵截,变了的是一林场安营、二林场扎寨,满江飘流扎成筏下放到江桥街的橼子,大乌嘴们驮去的方木、过梁、沉重摆断街,整齐的圆木、横料,压低了蓝色解放牌满身补丁车箱下的四个橡胶轮。如此,些些木白一点点抽取山中亘古积淀的黛色,这场混乱竟持续了大乌嘴的整整一生,要论大乌嘴这一辈骡马的功与过,无非就是它们受人指使的奴性,一驮驮搬空了家乡的山。
那个年代,有男人的家庭都买匹骡、马驮料子。有些牲口因耐不住重,不掌驮闪着腰,成了闲放的磨腰骡。骡子背上背几个鲜红的压疮那是很常见的。那年因润喜爷伤了腰,由他的大女儿阿香牵着大乌嘴去驮料子(确切地说,是大乌嘴带着阿香去驮)。去往林场的路上,大伙儿都不舍得点手电筒,都骑在自家骡子上。一伙、一路的从散集山间的村子于天擦黑涌向林场。一群大男人(也掺杂少数女人)唱着山歌,在渐次燃起哄闹氛围中,越唱越露骨。就着夜掩月明,女人也回应几调,而且也越回越显大胆,氛围还燃,骑影攒动,心潮涌动。阿香只会偷笑,她便不敢回应那调情的笑唱。
返程,歌声寂了,手电筒光密集起来。人们都忙于招呼自家牲口背上那根生湿的尺把过心的柱头或是过梁,驮独龙是最难驮的,赶马人要帮着掌驮。阿香哪会掌驮,打着那支两筒电,能防好大乌嘴转弯拐时别让过梁的后尾甩着自己就不错了。一路相跟着到家,休息两个小时,倒出两节旧电池,换个新的在前面,再放上两个旧的,接上一节手电管,变成三筒电。揣上母亲备好的粑粑,又上路了,这次要驮到江桥街换成钱。
大乌嘴将近暮年时,时代悄悄改变,大乌嘴的使命也在渐渐改变,已不用整夜整夜驮料子。
那天,由阿香的小妹阿花牵着去赶鸡街,六月三伏,去时晨光明媚,回时却被飘泼大雨、河洪涛天阻隔。到众人等雨小点,河水缓些决定渡河时,天已黑尽。以大乌嘴的本事,驮着十二岁娇小的阿花,把它(她)们围在中间过河不成问题,可变故往往始料未及,大乌嘴滑倒了。洪浪的巨响来到阿花脑边,没有水流把她浮起,只有大大小小的石头把她击沉,泥沙从她耳、鼻、眼中灌进脑子,让她的意识也在洪水泥沙中沉沦。只知道不远处就是一条江,那是一条不归路。突然,她的肩膀被一只熟悉的前蹄扒拉了一下、两下,她拽着那只碗大铁蹄离开了洪流。
它(她)们不敢动,等所有的呐喊、焦急、手电筒光聚积到它(她)们身上。它(她)们依然站在那个狭小的境地,侧边是它(她)们在其间挣扎了几十米的鸡街河洪,前面是更宽、更满、更响彻天的漾濞江。等着亲人把它(她)们弄出移一步就再次踏进死亡的境地。
说让大乌嘴空身吧(不驮驮子),可此时阿花与大乌嘴谁也离不开谁的温暖,于是,父亲脱下母亲备给的蓝雨衣裹在阿花身上,叔叔解下那床温厚的塑料布披在大乌嘴鞍上,继续赶路。雨还在下,却变得绵绵密密。阿花和大乌嘴裹在叔伯暖暖的电筒光中,在叔伯“终于没把润喜兄幺姑娘弄丢”的安心中。又把自己和大乌嘴裹在密密的雨帘里、蓝雨衣下、雨衣滴水滴在厚塑料布上的“吧—哒”声中。阿花的右腿斜插在大乌嘴前肢左侧的攀胸中,她使劲把自己的脚面与腿侧紧贴着大乌嘴,汲取大乌嘴的暖,也把自己的暖使劲给予大乌嘴。在这温暖中,她(它)们通过那条腿紧紧依偎、拥抱。
当他们翻过习村领岗,已是凌晨五点多,已经有一点曙色。熟悉的村围就在对门,上村和下村由模糊的大地坎子隔开。温暖近前,他们赶路更快了。远方天边出现半圆亮,那是某个畜积着无限力量的点或球投射出的光与希望,快速的投射并铺陈。
前方更亮也更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