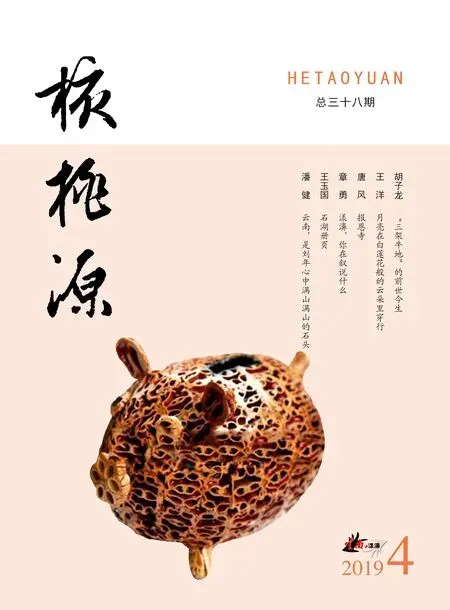夜 声
2019-11-13李新立
李新立
办公楼就像空旷的办公桌上立着的一口茶杯,孤独得单调。
我所拥有的一个空间,就装在茶杯里。
空间,是相对于另一空间而言的,互相封闭,却又给它们的存在互作印证。夜幕降临,白天所有的纷繁潮水一样退去,我合上窗帘的瞬间,冷寂必至。而小屋灯光点亮的同时,也为白天所忽视的事物打开了通道,另一空间的声与光,必然就窜了进来。
我有时觉得自己十分可笑,最惧怕周围没有一丝声音的那种沉静,像是陷入黑暗幽深的无底洞一样令人心神不宁。有时却对轻微的声响具有高度的警惕,比如那种非日常和平素没有接触过的。据说这是病症的表现。完全有可能的,一个需要安全生存的人,强迫自己屈从或者接受某些东西,内心的焦虑和反抗经常会表现在行为的细枝末节上。
这个声音,已经在多个深夜出现。以我的经验,完全可以排除老鼠蠢蠢欲动。“丝——”它那么不易察觉,却真实存在。我屏住呼吸,侧耳静听,判断声音方位。我到东边,它好像在西边,我去了西边,它却又似乎在北边,在室内,又在室外,游走无踪,难以捕捉。我把它当作一个游戏所发出的挑战,多年沉睡在内心的倔强被唤醒。必须弄清是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响动,于是,我开门,怕惊动了声响,蹑手蹑脚地慢慢前行,仔细倾听。楼道的光,是安全通道标志牌的绿光,铺在脚下,我被映衬成贼一样的影子,投射在粉白墙上,变形,模糊,忽隐忽现。顺着楼道,左拐右转,到达偌大的门庭,才知道四处都有这种坚持不懈地声音。然后,我踩着台阶上楼,将身体靠近每一个房间的门窗,甚至每一堵墙壁,哦,依然听得见它时而细若游丝,时而风一样急速奔走的躁动声。
令人不安的声音是必然存在的。我原路返回经过分层供电柜时,突然想,是不是电流的声音?一转眼又否定了这个想法,电流声是不应该四处游走的。就在这时,“哒——”,仿佛从高空坠落,敲打到充满空气的球体上,尔后被弹了起来,不像针一样尖锐,却在空旷的楼道里显得惊心动魄。扭头,马上判断出这个声音的来源与方位:洗手间突然掉落的一滴水。
水!我随即想到了水,我镇静得似乎胜券在握。像抓住现行一样,迅速进入洗手间,把耳朵贴近自来水管,“哧——”,是自来水发出放气一样的声响。取得重大胜利般回到房间,我不再为它而困扰,将身体放倒在床上。细想,我曾经受水的惊吓过深,对它的敏感自然有加。七年前,原谋生二十多年的企业即将关闭,那是几百人无望之后的挣扎与慌乱,各种形式的破坏、明目张胆的盗窃、无缘无故的殴打、言语攻击上的伤害、乱无目的的上访数日不断。我被安排值守在空荡荡的楼内,深更半夜,看着值班室破碎了的玻璃、踢踏坏了的房门、被击打后掉在一边的挂图,对安全的渴望大过为数不多的关闭补偿,担心一个提着钢管的暴力者悄悄靠近值班室。这时,一滴水的声响,不亚于一根利箭嘶鸣着从暗处射了过来。
旧事,给予伤害和经验,也给予了不安和警惕。
难以成眠时,又突然想到,平地而的高楼在成长过程中,自来水管作为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被植入大楼的体内,这就像一个人的成长,遍布有大大小小的血管一样。我便确信,这钢筋与水泥的合成品,因为有水流动,也是活着的。
活着的,才会有声音,生命的声音。
我的小空间在一楼,对面是长长的走道,因为昏暗,人行通道的指示标识牌才显得更加光亮。在白天,它们的作用几乎不大,巴掌大的一块绿光反而使昏暗的走道更加昏暗。这正是白天与黑夜对比出的效果。走道靠近房间处,放了一张几年没有挪动一下的长条桌,腿脚有些松动,积满了空气抖落的灰尘。我的房间温度不高,但潮湿得厉害,担心食物发霉变质,我正好可以把买回来的蔬菜、馒头、米面,搁在一个快递公司用于包装物品的纸箱里,置放于长条桌上。最近又放置了一箱朋友送我的苹果。我老家是适宜苹果种植的地方,并且近年已在全国很有名气。有了这箱苹果,我就能闻得到果香,能想像到春天开花的样子,着实内心充满欣喜和热情。
有天我听见走道里有动静,出去一看,是有人在摆放鼠粘、鼠夹和颜色好看的鼠药,说是怕一些重要设备被老鼠咬坏。我就担心我的蔬菜、馒头、米面是否已经被它们染爪。经过仔细检查,确定目前还没有被它们祸害,终于放心了下来。第二天,第三天,我循着别人摆放的陷阱查看,也没有发现有老鼠中了圈套,就认为他们纯属大惊小怪,这么封闭严密的大楼,怎么会有老鼠!如果有,那也应该在堆放着美食的五楼食堂才对。
是夜,我睡下后又听见外面小有动静,悉悉索索的,与水声是有极大区别的,也不像人在轻步慢移。就把耳朵挨在门缝上听着。门很不严实,张开的缝子有如合不拢的嘴巴,能伸进指头,平时会有好多陌生或熟悉的声音传进来。我听见了梦一样的诡异对话,很是奇怪。一个说:“有久违了的果香啊。”另一个说:“也闻到了。真香,比清油香多了。”又一个说:“咱们去找一找,好解解馋。”一个说:“慢!你们真没经验。你们看看,走道里给咱们设置了多少陷阱。”另一个说:“还是你有经验。人类现在很坏,比传说中的猫还坏呀。”
梦一样声音消失了。从轻得几乎难以察觉的声音上判定,说话者已经离开了我的苹果。但我于心不安,久久淹没于似睡非睡中。我怎么也想不通,那些陷阱并不是我布置的,怎么能随便说我属于坏人呢?我考虑怎样才能扳回人类的脸面,并且证明我不是坏人。第二天下午,我决定将两只苹果奉送它们。怎么送呢?我将苹果从箱子里取出来,取了发泡网,特意摆在了阴暗的角落处。按理,这位置应当是它们光明正大经常行走的地方。
之后我便出差去了,回来大概是一周后。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两只奉送的苹果,其实我在出差途中一直牵挂着这两只苹果。如果猜的不错,苹果肯定只剩下果核和一些碎屑。想必它们大快朵颐时,一定欣喜若狂,一定没有给我差评。我慢慢靠近放置苹果的角落,让我失望的是,苹果还那么放着,没有一点儿动过的痕迹。
旧的生活经验让人和动物都处于成长状态。比如早前年正月某日晚上,有个不相识的人在酒肉狂欢之后,路上与我不期而遇,他怀揣莫名燃烧的怒火,在我毫无防备情况的下,竟然朝我头上以混荒之力开了一砖。起初,我悲愤难抑,想弄清原因,第二天,当得知势不均力不敌时,我便携带着伤疤自动选择离开了让我失望的小城。当我以另一种状态投入到另一种打工生活中时,我就像选择离开的老鼠一样,为当时的逃离而庆幸。
万物皆有灵。离开,的确,有时实在是一种智慧。
灵性,灵魂,灵动。我就喜欢起“灵”这个字了。
大楼是一个空间,我房间的后窗外,也是一个空间。这里,傍晚的风扯着几缕霞光,给我山村般的美好,也给我像陷入黑暗一样陷入怀念和流离的忧伤。我一直怀疑,窗外的微光,是有声音的,它快速地奔跑过来,一部分被物体挡住后,而又坚决不会退却,与物体不分你我一样纠缠在一起,甚至融为一体。没有被挡住的,将窗帘扒开一条细小的缝隙,愉快地降落在我的桌上、床上、盆花上,甚至栖息在我的脸上、衣服上,它必然会感受到我(物体)的存在,我也会体味到它游走的快乐与忧伤。这些光是太阳的余晖,极多的是升腾而起的星光,喧闹得凄凉。
当然,在深夜,室外飘忽不定的光斑洒在窗帘上时,恍恍惚惚,总觉得有几双眼睛窥视。这种体验让人很难成眠。许多事物还是热爱黑暗的,除了光,比如风,就喜欢在深夜游走。乡村生活的经历和老辈们分享的故事,给这样的夜晚增添了浓重的趣味,当然也有恐惧。后窗风起时,有可能就是风牵着精灵的手在奔跑。我们一般都认为精灵是蓝色的,要不是白色的,颜色纯正,具于无形。它们互相打闹嬉戏,踢起地上一只易拉罐,看着易拉罐“叮叮铛铛”移动时,惊讶得躲在墙角,继而吹起纸张,坐在上面在半空冲撞。当撞到坚实的水泥墙面上时,会发出反弹回去的叫嚷。如果不幸钻进塑料袋,塑料袋膨胀、变形,挂到树枝上、电线上时,它们就会发出求救一般的“呜——呜——”声。
有时,我会不由自主地认为,肯定有一个两个淘气的家伙,趴在外窗上朝里张望,他们的母亲牵着他们离开,他们又会偷偷地溜回来,否则,窗户也就不会发出“吱吱”声。这不奇怪,对人世的深入了解比躲避更为重要些,更何况,大多精灵由人间而去,眷恋是一种共态,一种常态,所谓“阴阳两隔”,是一个生死概念,并不是自然的状态。
我做梦了。好几次梦见了父亲、老家的旧宅,父亲和以前一样在院子里走动,抽着烟,歪着头,认真东打量西打量的。那年,我正好下岗失业了,没有来得及告诉他,他就去世了,是春天。这些年,按照风俗,都给他烧点纸钱、送些衣物,可他还是以前那一身蓝色中山装。我就不解了。而正好,他去世当天我看了他一眼,刚刚离开了父亲,不安地走在打工的路上时,老家的一个电话又把我追了回去。
我的窗帘不错,透视的效果差,如果关了灯,与空屋无异。这狭小的空间就这样封闭。我迷迷糊糊睡着了,外窗的说话声惊扰了我。首先我得悄无声息地起来,然后屏声敛气静听,不能有任何惊扰外面的举动,更不能开灯。有说话声,千真万确,是人声,是人在说话。准确地判断给了我安慰。现在,轮到我偷窥了。透过窗帘,我看到一团光亮,光亮照亮了对方的脸,那是一位稚气却显沧桑的男子的脸,不,是少年。那一团光亮,是手机屏幕光。
后窗的不远处,仍然坚持在夜间在施工,几栋高楼正待崛起。少年来自于工地,口音与我的老家没有两样,就多了些亲切。我稍加判断,明白他和一个女子在微信视频。好像他对她说,他很想念她,寄的衣物收到了吗?今年腊月咱们结婚吧。我还明白,他在蹭我房间的无线网络。有人互相牵挂,在深夜,多么幸福和快乐。
我便不知不觉地牵挂起了他。有那么几天,他没有来后窗了,我就有些担心,心里生出许多不好的推理。终于,一天雨夜,他来了,急匆匆地先和未婚妻视频,然后给父母打了个电话。他说,他现在当班长了,收入不错,工地安全,老板和气,能很早结束工作休息。听他这么说,窗户里面的我就替他的父母着急:假话,假话。大凡儿女,有几个不在父母前说自己现在很好呢?!我在黑暗中朝远处施工的大楼看去,窗外影影绰绰的光亮使远处愈显旷远,工地模糊一团。
我莫名地担心我会在晨曦微露时错过了什么美好的事物。便不能入睡,一直坐等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