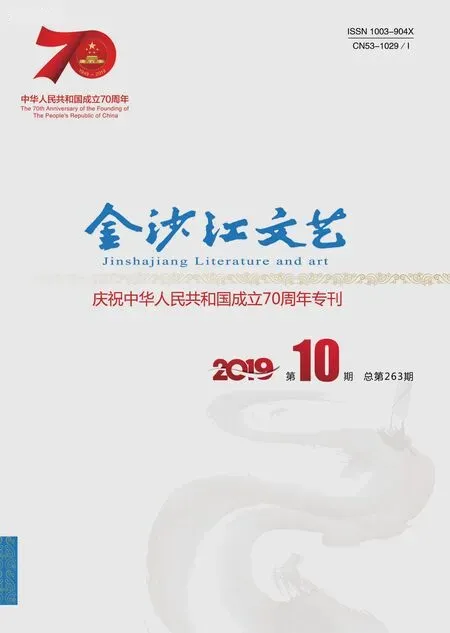童 年 (外一篇)
2019-11-13
瓦黑井的天空瓦蓝瓦蓝。
学校东边有棵虬根盘结,高大无比的桉树。
喜欢安静独处的我,时常抬眼瞧桉树果从天而降,掉落在树根间和泥地上,看小帽与身子分开。捡起中间凸起尖尖角的果帽,用左手拇指和食指指尖捏住旋出,飞到硬泥上继续转动,像个小陀螺,极好玩。
抑或夜晚站在桉树根上,看东边一串串闪烁的珍珠,仿佛在天上。听妈妈说,那是南华城的灯。这幅天上街市的景象镌刻进我幼小的想往之所。
童年对路刻骨铭心。
第二天清晨,外公、小舅、母亲和我从瓦黑井起身,沿崎岖的山道抵达新铺。时常,大理开往昆明的班车经停此地,可以搭车到县城。等良久不见踪影,我们只好顺公路行进。
从新铺走到沙桥,进入沙桥街,青石板路面古朴且精致。听过沙桥童谣:沙桥街子两头低,一边豆腐一边鸡。街天,南来北往赶集人到这里或交易或购物,街子两旁的铺台出售货物,市场极盛。镇子旁长长的湖水,唤名毛板桥水库。
我实在走不动。外公放慢脚步,给我点干粮,指着前面的山对我说,翻过东边这座山,你就能看见梅花鹿。这一招灵,有望梅止渴之效。说起梅花鹿,心就跳得欢。我忽让母亲牵手,忽拽住外公的羊皮褂,抑或干脆爬到小舅背上载我一小程。紧跟大人的步伐,我没有停留,只为梅花鹿。
傍晚时分,来到县城西街。此时,梅花鹿的念想全无,双脚不听使唤,我只想睡。县城到老家还有十余公里,我已忘记何时到的家。
令人窒息的徒步,终生难忘。
读小学进入天申堂中学,开始住校。从瓦黑井到天申堂,约10余里,要穿过滇缅公路最高点——天子庙坡,过乱坟冈,经套狼阱,林密,路不远却寂静,行人极少。
母亲每周日都要送我到套狼阱,嘱咐我拿根小木棍,这样走路不会害怕。等见不到我了,她才朝相反的方向回瓦黑井完小。兄妹四人,我排行老大,父母都在瓦黑井完小教书。天申堂中学的学生要自己做饭,因路途遥远不能往返,每周的口粮和蔬菜要带够。
大学专业的选择将有可能决定你一生的航向,假如能全面放开转专业可行,人生是否可以开启第二次、第三次启航呢?本项目的选题意义就在于:
上山捡菌子是童年的乐事,母亲能准确记住菌子的生长地,俗称 “菌子塘”,好似去自家菜园子里拿菜,非常神奇。把吃不完的菌子切成片,用根细竹条串成圈晾晒干出售,补贴家用。母亲是民办教师,课余需参加学校毗邻生产队的劳动。母亲有自己的菜园子,在自己筑的垛木小屋圈养肥猪。
母亲在病痛折磨中离开我们,对母亲而言是解脱,于我是悲戚。那么多美好的事物只能凭记忆收藏。
母亲留给我的记忆只有 “勤”字。忙碌是她生活的缩影,走不完的山路,守护挚爱的丈夫和子女。
现如今,童年的梦,珍珠般闪亮的县城已成居所。有了自家的小汽车和房子。童年的山成了路。还有像梦一样的高铁,驶过家门口只是瞬间。
父亲的档案
家里有两样物件珍藏至今,都是解放后分到的胜利果实。旧式手提皮箱,灰黑色,镶铜扣子,方便上锁,跟随父亲。青铜底座绘花鸟的白瓷瓶,可以插花,留在老宅。
父亲的档案,写着解放前家人是蟠龙寺和尚的佃农,耪和尚田,每年收入被人家收去一半。三间瓦房和三条水牛土改后保留,靠分的田地维生,合作化、公社化时入了社,生活逐年改变。
父亲的出生地叫代家村。祖父担任过四个月保长,这是解放前的事。更远的只能在墓碑上找到。
祖父置一副木制对联于正堂,上书“忠厚传家久、读书继世长”。父亲童年,与同龄人相较,是幸运儿。除了放牛,便读私塾。稍长一岁,便到大智阁、双河完小念高小。16岁那年,走进楚雄中学教师短训班,毕业后由政府分配,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17岁那年,时值秋天,父亲像往常,从执教的铺冲小学担柴回代家村。翻山过箐,因森林茂密不敢停留。在山腰与一只花豹相遇,双方谁也不敢动,对视几秒钟,花豹窜入树林中,这是一次危险的奇遇。
父亲读镇南师范是五十年代中期的事。由杨中正、杨嘉林两位同志作为介绍人,父亲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镇南师范从南华迁至楚雄更名楚雄师范学校。
在瓦黑井完小教学中,我的父亲认识后来成为妻子的罗秀芬,学生变成妻子,一同执教,成为一段佳话。
收音机在六十年代是时尚品,父亲几年攒下170元购得上海出产的红旗牌半导体收音机一台,既拓宽个人知识面,又丰富校园文化。
瓦黑井背靠龙箐梁子,站在这座古人称雄岭的山巅,群山绵延起伏,总让人心旷神怡。父亲在七十年代中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瓦黑井大队党支部书记罗有富和瓦黑井小队队长鲁国珍是他的介绍人,宣誓选在天申堂学区。
有些荣誉,值得铭记。1981年元宵节刚过,作为教育战线基层一名党员代表,父亲参加中国共产党南华县第四次代表大会。
教书育人与山乡结缘,和一长串地名相连。平桥、田心、云台山、铺冲、石桥河、瓦黑井、阿咪期苴、古路苴、岔河、大谷堆、碾子房、蟠龙,这十三所小学都留下父亲的足印。还有一事,记上一笔,父亲担任过文笔学区岔河完小校长。
时常回父亲退休后的老家,与老人促膝叙谈。经年的过往,平素已经淡忘的记忆又一幅幅浮现。我年幼时体弱,时常让父亲或背或骑在肩膀之上,学区开会、夜晚看露天电影都这样。
写下 《父亲如兰》这首诗时,父亲刚走不久。时有夏日的凉雨不期而至。
曾带父亲回学校看看,父亲流露少有的笑容。此时的他,靠拐杖挪动细碎的脚步。
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
只是眼前不再是旧时的模样。山绿、水清,群起的新式民居,焕然一新的校园,蜿蜒无尽头的水泥路。
脑海里的记忆渐行渐远,被全新的风景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