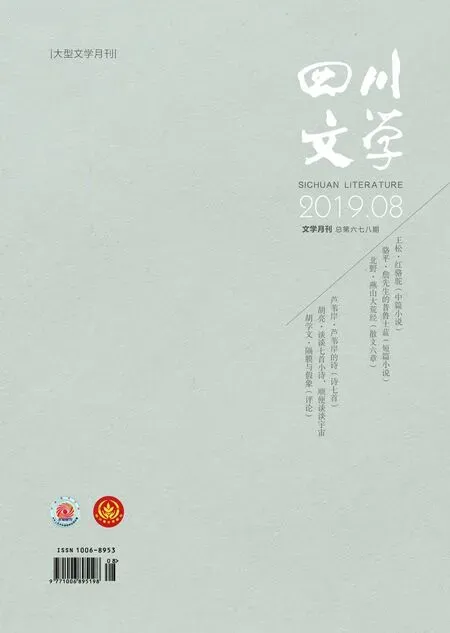正声起微茫 平原眺晨曦
——抗战时华西坝的诗人群体
2019-11-13岱峻
□文/岱峻
“江流呜咽水迢迢,惆怅栏前万里桥。今夜鸡鸣应有梦,晓风残月白门潮。”这是作家张恨水应本埠新闻界同人邀宴,题赠“枕江楼”的一首七绝。枕江楼位于南门大桥西侧,是一家江南酒楼,为文人墨客雅集常去之所。
1942年暮秋,临江吊脚楼高朋盈座。新履职的金陵大学中文系讲师孙望做东,宴请五大学的文学教席庞俊(石帚)、萧中仑、陈孝章(志宪)、萧印唐、高文(石斋)、刘君惠(道龢)、沈祖棻(子苾)等。“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老杜曾歌咏这一带风光。然而此刻,大半个中国沦陷,东吴船进不来夔门,下江人归期渺茫。凭栏远眺,但见山寒水冷。把酒临风,徒生离愁别恨。座中,高石斋放言,刘君惠悲泣。日中开宴,薄暮始散。众人相约,以《高阳台》为题,各自填词。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次日,沈祖棻率先完稿,她写道,“余近值流离,早伤哀乐,饱经忧患,转类冥顽,既感二君悲喜不能自已之情,因成此阕。”词曰:
酿泪成欢,埋愁入梦,尊前歌哭都难。恩怨寻常,赋情空费吟笺。断蓬长逐惊烽转,算而今、易遣华年。但伤心,无限斜阳,有限江山!殊乡渐忘飘零苦,奈秋灯夜雨,春月啼鹃。纵数归期,旧游是处堪怜。酒杯争得狂重理,伴茶烟、付与闲眠。怕黄昏,风急高楼,更听哀弦。
华大学生刘彦邦后来回忆:
此词传观后,参与当日宴集的庞石帚、萧中仑、陈孝章、萧印唐诸先生以及高石斋、刘君惠两师都用同调和作,各抒胸怀,每首都有惊心动魄的警句。如庞石帚词中的“高楼别有斯文感,早登丘无女,临水闻鹃。灯畔吟声,男儿虫是堪怜。家乡作客君知否。梦幽单,惯得孤眠”;高石斋词中的“角声又送残阳去,叹青冥飞辙,容易回车。咫尺长安,如今水隔云遮”;刘君惠词中的“夕阳红到销魂处,甚欺人,锦瑟华年。更相逢,如此楼台,如此江山”,都脍炙人口,传诵一时。
《高阳台》词七阕,正是刊登在正声诗词社主办的《正声》诗刊创刊号上。所谓“正声”,取自李白“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一)。
1942年秋,沈祖棻随程千帆到成都金陵大学任教,开设《词选》课,又在金陵大学和华大讲诗。“不久,她就发现班上有几位可造之才,但他们居处分散,下课后从不在一起交流学习心得。……便去同系主任高石斋师商量如何使成绩好的学生能多有机会互相研讨,共同提高。”于是,倡议成立“正声诗词社”,沈祖棻与丈夫程千帆担任顾问,聘请金陵大学教师高文、陈孝章、刘君惠作导师。时任金陵大学中文系学生会正副会长的四年级学生邹枫枰、邱祖武,三年级学生卢兆显三人牵头,吸收国文专修科的杨国权、池锡胤以及农艺系崔致学等,为正声诗词社首批社员。此后,又有四川大学中文系的宋元谊、金陵大学的萧定梁、陈荣纬、刘彦邦等学生相继加盟。
杨国权以《论近人研治诗词之弊》一文代发刊词,阐述正声社的宗旨:紧随时代,“其咏一草一木,每抒身世家国之感,悲愤激烈之怀”;坚守格律,“倚声之家,但有恪守成规,平仄声韵,悉依前制,未曾稍忽”;守雅正之风,反对新奇怪异之理论与创作;提倡创作与欣赏、研究相结合。
《正声》诗词月刊一期、二期分别于1944年一、二月正式出版,刊登社员及名家诗词,每期印数500本,200本分赠文化部门及亲友,300本交各大书店代售。“由于注重内容质量,特别是刊布当代名家的作品(主要由本社导师提供),刊物极快售完。”当年夏,邹枫枰、杨国权、池锡胤即将毕业,自费编印“正声丛书”《风雨同声集》,汇辑杨国权《苾新词》30首、池锡胤《镂香词》36首、崔致学《寻梦词》31首、卢兆显《风雨楼词》36首。沈祖棻在《风雨同声集》序言中写道:
壬申、甲午间,余来成都,以词授金陵大学诸生。病近世佻言傀说之盛,欲少进之于清明之域,乃本夙所闻于本师汪寄庵、吴霜厓两先生者,标雅正沈郁之旨为宗,纤巧妥溜之藩,所弗敢涉也。及门既信受余说,则时出所作,用相切劘,颇有可观省者。……盖在昔南宋群贤,觏逢多故,陆沉天醉之悲,一寄诸词,斯道以之益尊。今者,岛夷乱华,舟覆栋倾,函夏衣冠,沦胥是恫,是戋戋者,乌足以攀跻曩哲。然其缅怀家国,兴于微言,感激相召,亦庶万一合乎温柔敦厚之教,世之君子傥有取焉,而不以徒工藻绘相嘲让邪?
诗集出版后引起关注,章士钊《论近代诗家绝句》有云“沈祖棻为程氏妇,其门人已刊《风雨同声集》词稿”。吴宓称赞沈祖棻“行道救世、保存国粹”。
沈祖棻,字子苾,1909年生在苏州。祖籍江苏海盐,曾祖父沈炳垣是清咸丰内阁大学士,是咸丰皇帝老师。祖父沈守谦精于书法,与画家吴昌硕、词人朱孝藏同为诗书画三友。沈祖棻少即能文,中学就读上海,后考上海商学院,次年转至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受业师胡小石、汪东(寄庵)、吴梅(霜厓)等先生影响很深。
其间,沈祖棻爱上了小自己四岁的中文系本科生程千帆。据程述:“当时三四年级的学生成绩好的,可以听研究班的课。这样,我就有机会同她接触。后来打仗了,我们从南京逃到屯溪,就在那里结了婚。”流浪途中,“楚辞共向灯前读,不诵湘君诵国殇”,不到半载,日寇进逼,“仓皇临间道,茅店愁昏晓”,沈祖棻先行入蜀。1939秋,这对新婚夫妻在重庆巴县团聚,也与金陵恩师汪东、汪国垣及同学章伯璠、尉素秋、杭淑娟、赵淑楠等欣忻重逢。沈祖棻填词《喜迁莺》:
重逢何世?剩深夜,秉烛翻疑梦寐。掩扇歌残,吹香酒酽,无奈旧狂难理。听尽杜鹃秋雨,忍问乡关归计。曲阑外,甚斜阳依旧,江山如此。扶醉。凝望久,寸水千岑,尽是伤心地。画毂追春,繁花酝梦,京国古欢犹记。更愁谢堂双燕,忘了天涯芳字。正凄黯,又寒烟催暝,暮笳声起。
狼烟起,笳声疾,旋逃离。战时惊鸿,时聚时散。1940年暮春,沈祖棻在成都四圣祠医院查出腹有肿瘤,住院治疗。某日午夜,丈夫未在身边,医院突然失火,沈祖棻以羸弱之躯与惊惧的人流“奔命濒危”。沈祖棻以《宴清都》叙其事:“迷离梦回珠馆,谁扶病骨,愁认归路”。当程千帆从旅舍惊慌不定赶到医院,夫妻“相见持泣,经达似梦”。
程千帆回忆:
我和沈祖棻就在1942年8月一起到成都的金陵大学任教。我们都是副教授,不过沈祖棻是研究班毕业的,工资还比我高一些。我在武大时编了《文论要诠》的讲义,就是那十篇文章,没有编完,到金陵大学就继续编。后来金陵大学自己出钱,就把这教材印了出来,线装本,书名是《文学发凡》……
在金陵大学我教目录学、教骈文,用的是《六朝文絜》,也教《文心雕龙》。因为那个时候诗歌是高文先生在教,过去的习惯就是,如果一个朋友教的课和你重复,就应该让开……这样我就到四川大学教书,兼教金陵大学的课。
1944年秋,因不满校方对经济问题的处理,奋起抗争,两夫妇被解聘。程千帆前往成都中学任教,沈祖棻改聘华大文学院,教授“诗词曲选”。
此时,正声社前期社员大都毕业,又有学生陆续加入,如华大中文系王文才、刘国武,四川大学中文系周世英、王淡芳,和武汉大学中文系高眉生等。此后约两年间,每两月选一节假日,在少城公园的茶馆或南门外枕江茶馆聚会。“开会不拘形式,人人皆可畅所欲言,但当导师讲话,社员们总会先静听,后质疑。导师之间有时对诗或词有所辩论,我们在一旁听了真感如坐春风,深受启发。”
王淡芳回忆,当时程千帆要求学生学诗、论诗,必先自己学会作诗。从自己作诗中领会诗作者的甘苦,揣摩其立意敷词之旨意,始能进而学其诗,论其诗。不然将是囫囵吞枣,一知半解,甚至会妄自评说,厚诬古人。
刘国武写道:
沈先生为人和蔼可亲,讲课细致深刻,诲人循循善诱,特别是对我们后学,在学习上稍有进境,即给予热情的勉励。记得当时学作《玉楼春》词,曾有“阑干四面合成愁,春水一篱都是泪”之句,甚得先生赞赏。先生并曾亲手楷书《鹧鸪天》词“尽日疏帘不上钩”四首及“青鸟蓬山渺信音”四首命余和作……
在选读《诗选》课时,沈先生多次出模拟题目,要求学生习作。如讲李商隐七言绝句,使学生效李义山体写咏柳诗。我当时拟作二首,至今尚能记忆。其一云:“白门残照总堪怜,曾逐西风噪暮蝉。似雪何如春日好?纷飞乱舞一溪烟。”其二云:“红紫丛中绿自绕,细开嫩叶软垂条。东风莫谓无才思,斗罢纤眉又舞腰。”
“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蓬蓬勃勃,传统文化花果飘零,旧体诗词日渐式微,但古典诗词是一种寄予高尚情感的高贵技艺。沈祖棻夫妇与正声社师友、门生,坚持旧体诗词创作孜孜不倦,逆风而行,恰似折不断的芦苇,在月明星稀夜,吹奏出天籁之音。
“诗歌是中国人的宗教”(林语堂),在教会大学宗教气氛日益弱化的同时,坝上自由的诗风和暖轻飏,空气中有一种甜丝丝冷津津的微醺。
1942年至1945年间,以成都地区各大学为主体的青年诗人成立了一个文艺组织——“平原诗社”。其产生,须追溯到先期成立的“华西文艺社”。抗战初期,为宣传抗日救亡,成都各大中学青年诗人,定期集会,讨论抗战文艺问题,先后编辑出版《华西文艺》月刊五期,成为一份在巴蜀地区有影响的文艺刊物。1939年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打压各种社团活动,“华西文艺社”因组织松散,思想倾向不一,于1940年底自然解体。但火烧芭蕉不死心,他们随时准备东山再起。“这样,以原来华西文艺社的一些骨干成员为核心,两年之后重新组织了一个新的文艺团体,这便是平原诗社。”
华西文艺社骨干杜谷于1940年8月考入乐山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很快放弃学业,到了重庆,经诗人常任侠介绍,进入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任职。工作之余,在力扬、常任侠、艾青等人鼓励下,在《新蜀报》蜀道副刊、《国民公报》文群副刊和《抗战文艺》等刊物发表诗作。1942年春,他到北碚复旦大学拜访邹荻帆、姚奔、绿原等诗友。看到他们所办《诗垦地》丛刊所产生的影响,“回来以后,我兴奋不已,连夜写信给芦甸、蔡月牧、白堤,建议华西文艺社的老朋友中有志于写诗的,应该像《诗垦地》一样组织起来……”一石投水起涟漪——
1942年8月,芦甸、白堤、蔡月牧纷纷给我来信,告诉我平原诗社成立的盛况:参加的不仅有原华西文艺杜的旧友寒笳、左琴岚、葛珍、许伽、若嘉、张孟恢、任耕,还有蔡月牧介绍的缪恒苏、覃锡之(诗人覃子豪的弟弟,笔名黎茹、羊翚),左琴岚介绍的范方羊,葛珍介绍的穷发以及白堤介绍的青年女诗人杨哲、榛虹和青述林……刚来投考四川大学的诗人孙跃冬,也被邀请入社,并且请了“五四”时代的老诗人周无(周太玄)担任名誉社长。大概当时成都的青年诗人都包容了,真可谓极一时之盛。
1943年7月9日,相关审查单位公示了“平原诗社”登记程序,拟出版《平原》季刊,发行人周太玄,编辑张续清、刘振声、段惟庸,社址在成都祠堂街。考查结果:“尚合规定”。
请周太玄出山基于以下考虑:他原本就是五四时代的诗人,在赴法留学的海船上,曾以“周无”为笔名写过一首影响很大的诗《过印度洋》:“圆天盖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也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哪里是非洲?哪里是欧洲?/我美丽亲爱的故乡却在脑后!/怕回头,怕回头,/一阵大风,雪浪上船头,/飕飕,吹散一天云雾一天愁。”后来他致力于生物科学,没再写诗,但仍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四川分会会员。四川大学教授周太玄也明知一个思想激进的青年诗社,可能给自己带来烦恼,但他热爱青年,热爱诗,就像热爱春天,于是心安理得地为他们撑起保护伞。
平原诗社就像一列开动的列车,人员时有上下,先后参加者有芦甸(刘振声)、杜谷(刘锡荣)、岳军(蔡月牧)、左琴岚、葛珍(段惟庸)、寒笳(徐德明)、任耕、任谷(张孟恢)、若嘉、方然(朱声)、方羊(范志成)、穷发(刘以桑)、许伽(徐季华)、白堤(周志宁)、羊翚(覃锡之)、孙跃冬、青述林、缪恒苏等。具体负责人是芦甸和杜谷、蔡月牧等。当时芦甸在北较场中央军校成都分校一个学生中队任指导员,诗社常以他居住的纯化街53号寓所为聚集地。社员多是在校大学生,也有一些外地成员如蔡月牧、寒笳、杜谷等。聚会较为频密的,是交通近捷的坝上五大学学生,如燕京大学羊翚,金陵大学方然、白堤、白永达,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许伽等。
燕京大学历史系学生羊翚,四川广汉人,本名覃锡之,是平原诗社最年轻的一位,被大家戏称为“十八岁的西班牙少年”。其时,他就读的燕京大学,校址在陕西街,寝室在文庙街,与纯化街近在咫尺。他晚年回忆:
那时,我们都很年轻。年轻人对于诗歌有着初恋般的感情……
有天,芦甸笑嘻嘻地说:“诗垦地的曾卓来了!”于是大家就在53号聚会。用不着多介绍,诗歌是最好的“通行证”!当时曾卓已经写了好些为青年传诵的诗篇了。见面后,大家谈到《新华日报》关于时局的评述和来自解放区的消息,令人兴奋!芦甸提出要在成都办诗刊,向他约稿。曾卓慨然答应,挥一挥手走了……
不久,曾卓由重庆寄来一组诗:《生活》。还约来一批诗稿,给我们带来喜悦。在抗战进入艰苦年代,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候,曾卓写道:“我们都是涉滩的纤手!”代表了当时青年代的心情。芦甸高兴地说:“我们相携如兄弟!”于是“平原诗丛”第一辑便以“涉滩”命名。
平原诗友有的已经在诗坛上崭露头角:
诗人杜谷细腻的艺术感觉,鲜明的诗歌形象,为常任侠和胡风所称道。1941年编成的诗集《泥土的梦》,列入“七月诗丛”。由于国民党图书审查机关的阻挠,可能未出版。方然豪情洋溢,正处于写作的“盛期”;蔡月牧进入了他的“垦殖季”;孙跃冬和左琴岚以不同的风格令人瞩目;白堤因《小土屋》而知名;而芦甸,不仅是诗人,又是出色的组织者……
1942年秋末,平原诗社第一期诗刊《涉滩》出版发行,载有蔡月牧、杜谷、芦甸、范方羊、许伽、若嘉、任耕、白堤、左琴岚、葛珍、青述林等社员的诗作,有张孟恢用“无以”的笔名翻译的《莱蒙托夫诗选》及方然的诗论;还有重庆“诗垦地”成员邹荻帆、曾卓、绿原、冀汸、SM等人的诗作,及老诗人李广田的诗论《树的比喻》。
1944年冬,平原诗社出版第二期诗刊《五个人的夜会》。开篇就是羊翚(黎茹)的长诗《五个人的夜会》。诗中,他写了五个社会底层陌生人:一个渔夫、一个马夫和三个铁匠,偶然地,在“灯火错落的夜街”小酒馆里相遇,“他们争着打开自己的钱袋,/同时也敞开了心和口,/嬉笑而且怒骂,/成了亲密的朋友”。他们叙说漂泊的生活,以及对美好日子的期待——
这个老渔夫,/想望着有只船——/一只漂洋过海的大木船。/然后,让他的儿子摇桨,摇桨,/摇到他想去的地方……
三个铁匠,/则希望有一片合伙的店,/而里面是自己的产品。/他们不再愿打造杀人的刀子。/他们要每天打造镰刀、锄头,以及/摩天大楼上的钉子,/让每样东西都能产生最大的价值!
最后,马夫喝完了酒,/道出了他们的希冀,最简单的希冀——/他说:连畜生也不喜欢鞭子。/他祝愿他的马永远壮健,/不论过山过水过平原,/不扬一扬鞭子,/一切都称心如意!……
五个人“敞开了心和口”,倾诉“最简单的希冀”,也是诗人对不平人生的呼喊:“而明天——/在不同的地方。同另一些人,/他们又将举杯,重复地向世界诉说着:/他们的诅咒和希冀……”如果说《桃花源记》是诗人陶渊明描写的古代乌托邦,羊翚的诗则是一种仿现代乌托邦的叙事长调,流淌着五色杂陈的梦幻。
金陵大学国文系学生朱声,笔名方然,1919年出生于安庆怀宁县一个官宦之家,早年失怙,靠在南京国防部作高参的伯父朱镜鋆养大。1938年,朱声高中毕业,投奔延安读延安公学。数月后离开陕北来到成都,1940年考进金陵大学。据说他离开延安的原因,是对延安文艺界的领导看不惯。方然在课余时,开始翻译《斯大林论语言》。但他最为钟情的还是诗歌女神缪斯。他在诗作《安慰》中写道:“我怎样安慰你呢?/你哭瞎了眼睛的母亲呵!/我的肩上放着你颤抖的手,/我听着你手杖触地的声音。”母子间凄婉的情感传递,化为呼唤光明的声音。
1943年1月2日,23岁的方然完成长篇叙事诗《哀歌》。同寝室的金陵大学农经系学生谢道炉(即后来的思想家谢韬),对年长自己两岁的方然崇拜不已。他在日记中写道:“四三年元月三日晨全部抄完。我将扬声地宣称,这与世界任何伟大的诗篇比,是会毫无羞愧的!五年来广大的诗坛中,这是第一流最伟大的作品!我没有多的话,诗全抄在这里了!”方然在《哀歌》里写道:
春三月/江南的母亲们/都想起/她的青春……/河水绿了,河水香,/月亮照着河水,/白石上一个姑娘/洗她的褪色的衣裳。/她凝望着自己的影子,/一只翡翠鸟呀,/也在河边柳树上/出神凝望。/她的辫子垂到水里,/河水流走她的衣裳……
那些/“经理”呀,“老爷”呀,/是怎样左手/握着银钱与喷香的手帕,/右手是怎样,/拧姑娘的小腮,/解开姑娘的衣裳……
一个姑娘/是怎样几个月/缩在屋角落里,/哭泣着,/终于在一个夜里,/生出了那个/罪恶的,羞辱的,/“挨错了门槛”的“小鬼”呵……
而后,清明,/她又是怎样偷偷地/在“小儿”的坟头上/烧几片纸钱,/呵,那纸灰,/果然笔直地飞上天/她抚着坟头上的青草/像摸着孩子底头发哟……
一个吹箫人/叫我听他在月夜里/低低吹着箫/他说:/“听呀,/落水的水鬼们/在那池边柳树下/呜呜地哭了,/为着找到的替身,/又是自己的亲人!”
孰料,这首《哀歌》中,对不堪凌辱、投水自尽的“母亲”的哀鸣,竟是对自己命运的预设。
关于《哀歌》的创作动机,方然在给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钱瑛的信里谈道,“在阴冷而抑郁的家庭里,我长大,到如今二十三年了。我是第一次看着自己点起了火,是自己的灵魂这样炽烈的燃烧着。”他是要烧毁自家老宅院连同那个旧世界。青春的力比多,除了革命,还有恋爱。此时,朱声开始疯狂地追求钱瑛。他的情书中有这样滚烫的句子:“如果生命只是浪费,/爱情只是陶醉,/那算得了什么?∥我以爱情光荣我的生命,/我以生命证实我的爱情。”
狂热的爱情像烈焰,很快就会燃尽。几十年后,钱瑛这样总结:“我生命中最璀璨的青春期是和方然一起度过的,他给过我狂热的爱情。但方然毕竟是一个诗人,当爱情的激情在平凡的生活中逐渐转变为亲情时,我们的悲剧也就开始了。他是一个‘以爱情光荣生命,以生命证实爱情’的诗人,他一生追求的是狂热的爱情,他无法从诗的梦幻中走向现实。我会宽容他的,特别是每当我想到他跳进西湖的那一刻,我的心总是刺痛得厉害。好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金陵大学经济系的白堤(曾用笔名杨华、白玲等),本名周志宁,祖籍四川宜宾,1920年生于广西南宁。青少年时代,他随父母住广东、澳门,后到浙江杭州。因喜爱白堤,故以之为笔名。抗战爆发后,他随家于1937年底迁回成都,1941年秋,考入金陵大学经济系。
在此前后,为白堤创作的“井喷期”。诗作《乡村酒店》《啜盲者》《早安呵,锦江》《拉纤夫》等,辛辣地鞭挞黑暗势力,对光明的未来充满希望。诗作《小土屋》在重庆《诗垦地》丛刊第二期“枷锁与剑”上一发表,即被诗人常任侠、孙望选入《现代中国诗选》,并被誉为“中国诗坛十朵绚丽的鲜花”之一。白堤将生活细节和丰富的想象融为一体,刻画了一座乡村“黄色的小土屋,/温暖而黑暗的小土屋”:
我喜欢我的小土屋,/但更喜欢那扇小小的窗子,/因为早晨的太阳,/是从那里进来的。/因为我从窗子里/可以看到天空的云彩和星星,/田野的树林和茅屋。/而且,/我还可以看到田野/农民们的操作……
而在夜晚,/我点起了菜油灯,/一边听田野水磨的歌,/一边工作/现在田野是寂寞的,/我的小土屋也是寂寞的,/但不久春天就要来了,/田野会有菜籽花的芳香/和布谷鸟的歌,/而我的小土屋,/也不会再寂寞了/因为在那时节/我的邻居/土蜂要回来了,/那将要为度蜜月而来的,/蔷薇花也红着脸回来了。
《小土屋》是青春朦胧的诗人,带着童稚般的幻想,向未来发出的一次眺望,属于现代浪漫主义诗人惯用的“异方想象”。
1942年发表在桂林《半月文艺》第二十四、二十五期合刊上的《早安呵,锦江》一诗,模仿郭沫若当年立足日本海边写出的《晨安》,白堤在晨光中,向着锦江上的纤夫、渔夫、洗衣妇……向整个世界一一道声“早安”——
早晨,从那鹅卵石的江边走过,/我看见闪耀着太阳的江水在笑……∥早安,/明媚的明媚的锦江,/我们的静静的顿河呵!/早安!∥早安!/静静的在呼吸的/我们的顿河的流水,/——我们的英雄是从你这里去的呵!∥你,鹅卵石,/我们静静的顿河两岸的/顽强的客人呵!/早安!∥
你停泊在岸边的/疲乏的船呵!/载着粮食和军火/航行于江上的船呵!/早安!∥早安!/你,我们的顿河上的/原始的水车轮呵!/绿色的树林呵!/暴风雨所剥蚀的石桥呵!/堆积在岸边的木材呵!/徘徊在江上的,/从江岸的砖瓦厂底烟囱里/喷出来的,/从江岸的兵工厂底烟囱里/喷出来的,/乌贼鱼放射的墨汁般的/煤烟呵!/早安!∥
早安!/每天早上消失在煤烟里的/小小的渔船呵!/船上的捕鱼鸟呵!∥从站立在我们的顿河两岸的,/长足的鸽子笼样的木房里/肩挑篾扁担出来的,/滨河而居的搬运夫呵!/早安!∥早安呵!/你长年漂流在外面的/“靠水吃水”的/船夫呵!/拉纤夫呵!/——比无期徒刑还要痛苦的/终生被绳索所桎梏的/悲苦的生命呵!/早安!∥从钉着“杀敌光荣”的木牌的,/低矮而阴暗的/草房里走出来的,/为了胜利/忍受着饥饿寒冷的痛苦/在我们的静静的顿河两岸/洗着衣裳的,/晒着衣裳的,/纺着纱的,/织着布的,/我们的出征的英雄的眷属呵!/你们,/早安!
诗人借助抑扬顿挫的节奏,繁密的修饰比喻,使意象丰满,质感坚实,营造出沉郁辽阔的意境;诗人颇具匠心地将眼前锦江的寻常之景,与正在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苏联顿河相联系,试图赋予成都以庄重的时代气息与严肃的历史感。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文系的许伽(另有笔名徐慢、禾草、石池、柳池等),本名徐季华,1923年生于四川灌县(现都江堰市)。父亲徐步青是当地士绅,曾任新繁、汉源、崇宁等县教育局局长、民政科长,还担任过灌县参议员、水利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39年春,16岁的徐季华坚持到成都上南薰中学,开始了新诗创作,参加过《战时学生》旬刊社、华西文艺社、现实文学社等进步团体活动。1942年考入成都金陵女大,成为平原社骨干成员。
作为“本土诗人”,许伽对成都的态度如同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对故乡故土,对生长的旧式大家庭,爱恨交加。出于青春期的叛逆激情,她把目光投向社会阴暗面而发出激越的批判之声:《弃婴》写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就被冷冷地抛弃在街头;《擦皮鞋的孩子》,本该坐在学校念书的孩子,却被生活赶到“在风雨飘摇的街头”;《路》,“我们在城市的一角,/议论。探讨,/流泪,争吵:/这人生之路在哪里?”1941年,她在《古城,我爱你》诗中写道:
古城,/我爱你!∥古城,/我爱你,/虽然你的硬石板上/移动着许多软脚。∥古城,/我爱你,/虽然那些被饥饿烧得发狂的眼睛,/要拼命夺去行人手中的一块小饼。∥古城,我爱你,/虽然这长街上,/只有/寂寞和阴暗的风景。∥古城,我爱你,/你使我开始知道生活。
终于到了向爱恨告别的那一天,她在《告别》一诗中写道:
再见!/又爱又恨的古城,/我终于要向你告别!/我早已经发誓要离开你,/可偷出牛市口回望时,/又恋恋不舍故乡月。∥像一个学游泳的孩子,/深深浅浅乱扑腾,/心上竟有那么多伤痕!/小鸟不能老待在巢里,/要飞出去,/哪怕被暴雨雷电轰毁!∥让我抹去告别的泪水,/趁深夜,/去追寻前行的脚印!
渴望冲出封闭、落后的盆地,走向战斗的“北方平原”,许伽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懑,是要挣脱和告别的理由;但真要就此了断,远走高飞,古城连同家乡和亲人,又变成生命中难以割舍的记忆。许伽“成都书写”的文字与情绪,就像从两扇石头磨盘间流出的浆汁。
平原诗人是自由的歌者,无视诗歌韵脚与平仄,追求诗歌的无拘束、散文化,有的诗恣意表现纯美的个人情趣。如金陵大学农经系白永达的《七月的田野》:
“七月的田野,/一阵阵菜花的清香。/那黄金的一片片/和粉红密集的荞麦花,/华贵地装饰大地。/而无数的蜜蜂/便从寨子墙上的洞里飞出来了。”若嘉的《怀乡曲》:“我仰望着天边,/待着一只带来家书的雁;/却飞过群群铁鸟,/撒下这遍野的荒烟!/我彳亍在溪头,/溪中的流水悠悠,/一阵秋风惊破了水面,/半个影儿也不给我带走!/我幻想到故土,/遥隔万重关山,/我不能归去了么,/敌骑暴加横阻。/我怀念着家乡,/不禁在深夜唱出一只哀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平原社青年诗人的创作,受到左翼作家的关注与批评。1942年底,齐鲁流亡成都的老报人、《新新新闻》编辑王冰洋以龚莺为笔名,在一篇诗歌评论中,肯定了这群青年诗人艺术上的诚挚,也指出有些诗未跳出个人小天地,色调显得苍白,主观追求与客观现实之间还存在差距。
“山那边,好地方”,到了1945年夏,在犍为女中教书的杜谷、芦甸和在燕京大学读书的羊翚,和在广汉的缪恒苏相邀一起去中原解放区。平原诗社由于主要骨干相继离散,也就无形解体。“船是水手的家,水是船的家,战斗的友谊,是我们的家。”当年,蔡月牧以一首《送别》诗,表达对岁月与战友的怀念。
新诗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诗界的反传统观念,并非仅仅出自精神或艺术上的考虑,而是针对中国社会现实,发出“铁屋子的呐喊”。汉娜·阿伦特说过,“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平原社的诗人是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死的一群人。旧时代的黎明鸟或也是新时代的猫头鹰,其后的命运不言而喻。更为可悲的,有时,诗人生命的结束,甚至是以诗的方式。
羊翚本名覃锡之,他有一个哥哥,是台湾著名诗人覃子豪。当20世纪90年代《覃子豪诗选》《没有消逝的号声》和《覃子豪诗粹》在大陆出版,洛阳纸贵时,羊翚写了一首《诗魂》。他写道:
诗人死了。诗的精灵还活着:/这不安的灵魂,仍然在世界上漫游。/二十年前,你在台湾诗人们的悼歌中长眠,太早了一些;/死后二十年后,我给你招魂,又太晚了一些……/我常常在梦里听到你的歌声,却不知道你的所在。/我们是兄弟,就像天上的星星,互相追逐,期待相会。/你来了,昨夜走进我的梦:我们都返回了童年,围绕在母亲的膝前嬉戏。当我还在玩积木的时候,你已经学会了唱歌;/用歌声讨得母亲的欢喜——/“妈妈,让我再给你唱支歌!……”/呵,这个梦真是太好了!
“儿不嫌母丑”,这或许是弟弟覃锡之此时要表达的。他与平原社同人,多是些“用歌声讨得母亲的欢喜”的孩子。几十年后,他们还有另一个比喻,叫“重放的鲜花”。所谓鲜花,不过是夹在发黄发脆书页里已枯萎的生物学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