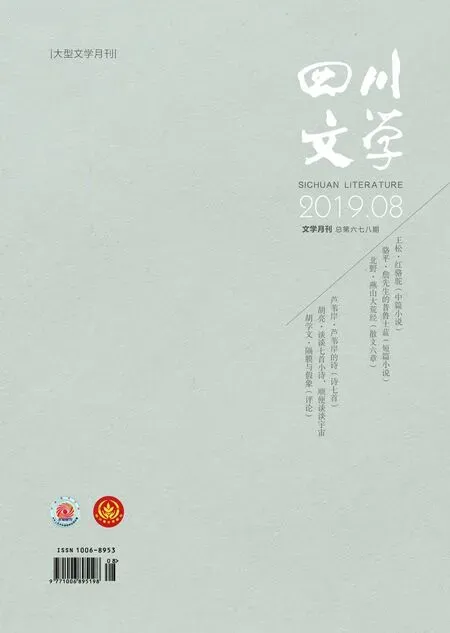燕山大荒经(散文六章)
2019-11-13北野
□文/北野
1.草木经
我在地皮上说:“我,我们,要被淹死于夏天的花朵和灌木。”我把枯枝立在树顶上,点着香烛;我把花瓣串起来,用于祭献;我把自己用作掩面啼哭的那个人,然后,在旷野上,高一声低一声地喊:“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夜幕下,蹲在河边洗脸的人,是三年前那场大火,烧死的老榆树转世,它满脸的烫疤像丑陋的奥登。现在,他只能用树皮掩盖自己的真容;而那些烧灼的伤痕,已经被印在肉里,谁能把它们洗去?即使你用整条河的水,洗它三天三夜也没用。
我攥着一把灰在山里奔走。我的身体里跳跃着一万个树冠,我的皮肤里翻滚着一百里的树根,它们像石头一样被驱赶、轰鸣,无数座森林的影子在撞击我沉默的颅骨和头皮;我伸开双臂——我只能如此,但它们并不顺从我宏大的怀抱和山谷,它们在飞,像黑暗中的沙尘一样飞,像苍黄的薄暮一样飞,像北方绝望的初春一样飞……此时,我对自己毫无信心,我只能抓住其中一粒,像抓住天空的袍袖上一块破碎的补丁。
木楔插进身体,它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疼痛,它喜悦于其中的迅速躲避;这样的景象,也许可以证明:整座森林并不缺少敏锐的反应,少许的麻木,也许恰好控制了它的腐烂和陈旧。树顶上尖叫的人,舞蹈中跌落的人,棺椁中嬉笑的人,以灵芝身份重生的人,在朽木上一下一下雕刻自己的人……或者,都另有自己的目的?
我不是那个疯狂奔跑与你迎面相撞的人。在你面前,我有时疾走,有时漫步,像用黎明或黄昏考验耐力和体力的那些老人,即使行将就木,我仍不愿做鲁莽的棒槌,一下就敲破了今天的鼓皮;我在楼头上种树,种悬铃木、银杏、车梁木、鹅掌楸、白蜡、合欢、黄连木、糖槭、黑榆、鸡桑……它们给我的荫翳,广大而虚无,像一场空荡荡的梦,虽无望,但听着风声也是好的——我这样安慰自己。
如果我今天能在影子里得到安慰,我希望世上的森林都冒出烟雾,让我们欢叫,追着它四处飞扬的灰。
2.伐木者
我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斧头,这样的因果,证明我曾是一棵树,或是一片森林,而现在,我要砍向谁?我被崩出豁口的身体如同一把失去弹力的锯,在夕阳下,它拖着大地上的倒影。树干里的流水,已经开始变得缓慢,它们就要断流了,这些并不明确自己归宿的小溪,通过山谷里的烟岚,记住了远处的响声;通过枯枝,翻开了绿荫下湿漉漉的泥土。
我在纸上画斧头,画冰雪上的马车,狐皮帽子包住脸的人,舔树干冻僵舌头的人,黝黑的烧炭者,翻下山岗摔成碎片的人,摇摇欲坠的悬崖,还有月光里用风的脚步到处乱走的影子……我还要在纸上画出有限的石头,让它们拥挤在树林里,偶尔向前滚动一下。
我把斧头挂在森林中间,整个大地都跟着发出震动!像秋千一样晃荡的斧头,像钟摆一样摇曳的斧头,明晃晃的,我带领的这些人,都不能躲开它的锋刃!我看见的这些树木,都要被它劈开,露出白色的牙齿。
它们被劈开就对了,因为它们什么都不需要,它们只要不脱离一片宏大的旷野,不脱离自己的绿荫就行了;而我们不行,我们需要薪火相传,需要缓慢的真理和轮回。我们太苦,我们没有办法在春风中再次获得复活的机会,所以我们要在身体里设置一场无休止的战争,哪怕是对自己的一次袭击,然后杀伐,然后获胜,然后像沉寂的坟场一样在夜幕下冒出蓝光。
这能让我变得更加锋利吗?当我用尽力气,向一座森林砍去,“当”的一声,斧头落地,我呆住了,我看见:每一个树干里,都有一个睡眠的人,他们像婴儿一样甜蜜地蜷缩着,他们无声无息。
3.一个秘密的人
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存在?一个比影子还虚无的人,真的那么诡异?他通过谁来到我的面前?他通过什么方式,把我洗劫一空?
我行走时,他用翅膀拍打我的头顶;我睡眠时,他用梦境运走我的身体;我抬头仰望,他用巨大的空白修改了我的眼睛和大脑,使一场有意义的远眺变成了装腔作势的假寐;当我进入沉思,身体里一群庄重的哲学辩论者突然变得轻浮无状、嬉皮笑脸……当我死去——假设这是最后的一次仪式:四只蚂蚁用高高的触角举起的葬礼,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个人尊严的界限和重量,突然一泡狗尿凌空而下,哦,我今生最后的一趟差役,也变成了一股湿淋淋的烟雾……
如果这一切,是受制于一双手,那么,我需要向谁诉说我的委屈?而谁才是那个一生躲藏在我的身边、从来不露出面孔的隐秘的聆听者?月光在我的身影里洒满了银子,但这并不能让我对生活产生记忆——“忆旧等于耻辱”!想想这句话,我骨头都疼得难受。
那些白瓷土无法被浇成城堞,只能被烧成酒瓮,放在山顶。一个鼓盆而歌的人坐在云中。他大口喝酒,然后用透明的拇指擦洗那些移动的阁楼,然后他像一只老猴子那样长啸、流泪,绝望得如同一面黑色的悬崖……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存在。我在旷野上寻找,但我始终不能得到他的踪迹。
他不属于人群里应有的那种,他也不是隐士,他是一个被时间藏起来的人。任何一种贪恋空间的行为都会被他讥笑,即使是针尖上的一个空位,对于他,也是道德的坟墓。一节快要崩断的钢丝上,他站着。或者是钢丝本身的断裂?我常常在他面前悲伤得像一道空旷的峡谷,弯曲的,黑暗的,不知底细的,没有结局的恐惧……
4.草原上那座腐烂的房子
如果不是在星空的背面,我找到你的时候,你怎么能匆匆腐烂?
时光迟缓得像穷人身体中的肺病,气喘吁吁的影子里,蝴蝶披着白花、红花和说不清颜色的野花在其中飞;流云迷幻,仿佛一场盛大的欢聚,在无人的山岗上,放射出耀眼的金光银光,又翻卷着挪出空旷的头顶。
那座腐烂的房子,站立在阳光下,它的阴影仅够盖住它自己。
鞑靼人在敖包下沉睡。他梦见一个壮汉在往悬崖上抹胆汁,而天空倾斜,像一匹停止了飞舞的丝绸;骑着鹰脊的少女,额角烫着天狼的族徽;被向日葵篡改了的大地疯狂舞动,它们混淆了一群热血沸腾的武士和烈女,混淆了油菜花里流连忘返的游人;而他们那些衣着鲜亮的后世子孙,此时正在滦河桥头出租鞍鞯和马群,他们牵着马,驯顺地走在草地上,用媚笑和小伎俩赚取花花绿绿的钱币。
山岗上沉睡的人突然翻身坐起,狠狠地骂了一句。我猜他在梦中肯定是遇见了一些粗暴的人。天空下,一个在草原上竖直梯子的人,像在大地上整理那些纷乱的烟尘,他是在想爬上头顶的白云,还是在想爬上远处的星辰?秋风浩荡,吹拂他长发中月亮一样的脸庞,像寒露吹散胡草中白色的冰凌。
一个分食獐狍野鹿和牛羊的欢欣部落,一群马头上挂着剑戟和阴影的莽汉主义信徒,有时是箭镞下被追赶的兔子,有时就是飞翔的箭镞本身;他们既沉溺于杀戮,也沉溺于消逝;草地上流出的蜜汁,喂养了太多的英雄、土匪和盗贼,也喂养了无数粗手大脚的绝世女子和她们身体里充满柔情蜜意的爱情。
荒岗上那些石头,像时光在默默堆积,它们偶尔被鹰抓起,塞进胃里,磨碎了另一些沉睡的人;我从不轻易在草原上捡起它们,也不会把它们放进书房,我担心它们会在纸上发生一场暴动,而一场文字的动荡会暴露出多少前世的秘密?这也许是今天的幸福生活永远不能诠释的秘密?
在草地上使劲摁车铃的游客,突然飞起来摔进草丛。他爬起来的时候,开始用一种异域口音喋喋不休地倾诉,好像一个逝去多年的人曾经蒙受过不可思议的耻辱;他今天突然清醒,是用谁的手拨开了自己的迷雾?
那座腐烂的房子,草原上那些寂寞灵魂的最后堡垒,在一粒一粒地掉着土屑,而它们是无声的,如同一具千年前美丽的木乃伊,她内衣里的小乳房已经停止了发育……
5.从森林里来的船
这漏风的木头,这腐烂的岁月,这四处弥漫无法收拢的颓废的心;风穿过去,风的喉咙在叫喊,它的骨骼锈蚀在木屑之中,它被黑暗所羁押、所引诱。大海和堤岸成为幻觉。时间是卡在它骨缝里的盐,它荒凉的身子瘫痪了下来,散发出药味,散发出远处一片蔚蓝的腐朽的波澜——那永不停歇的谜一样的远处,在夕阳里弓起脊背。
如果要我原谅你:这木棉的花,这森林的花,这阴影和百兽跳跃的虚幻之花。这失败的诺言和流走的迷途;这暗中的黑色,内心掉着一片片木屑,但它破碎的四肢仍然在迎风招展。离乡的床铺被异乡所抛弃,被冒死的斧头所砍伤,被铁器所离间——一座巨大的森林如果也被动摇了,天空将像一张纸,而我也要被掀翻一次,像一条小溪屈服于一道波澜。
我不拒绝河畔的滩涂,我也不拒绝自己的衰落和浪漫;秋天退尽盛装,露出发呆的礁石。涛声必须献给大地和坚硬的天空,献给寂寞的心灵。而在远处,溪水冲出内陆河,冲出心中的堤坝,把田野上的四季淹没;泛滥的岁月,像颤抖的音乐,抚摸着头颅中倾斜的木塔和耀眼的山坡,抚摸着高过城市钟楼的墓床;编钟里流出的紫黑色液体,是时间的颜料再次复活。而我迎头碰上的夜晚,却沉默着,有一种辽阔的绝望之美。
今夜,暴雨如注。大地的命运缩紧。我的小命令人担忧。我现在才知道,我多么脆弱,我像一枚枯叶,小心翼翼隐身在雷电的缝隙之中,消耗着最后的能量和困惑。今夜我多么微不足道,我用四肢抓住大地,用呼吸贴紧树梢上的波涛,这使我想起草原,想起可以用很多方式,接近的毡房以及那些寂寞的仓廪外腐烂的马厩所散发的时间的味道。今夜,我只有大声呼喊,才能止住内心的悲伤和失落。
6.在草原上远行
土獾在草皮下,羞涩、拘谨,心中偶尔一震,额头顶着眩晕的轻霜。它眼睛看着我,像盯着恍惚的童年,它还不知道,草甸子上一个一个掀翻的沙塔,正在沉入夜晚,而日出的结果,就是把另一座沙塔,重新竖起在它的头顶。
此时,谁跑在最后,谁将被饥饿所击溃,这都需要计划。隐约往返的根系,在它的胃里,开始泛起花草苦涩的阴影。那些干净的少年,都用小鹿的身体,围绕着湖泊和毡房,围绕着跪在地上的羔羊,看它用红色的双唇,慢慢挨近母亲的乳房。而卧在夜色中的牛群,所咀嚼的干草,此时正在天边的牧场上,像烟雾一样摇荡……
在象牙上雕出一片丛林的小匠人,突然暴跳如雷,像火焰中扇着耳朵的大象——他扇着自己的脸庞,似乎十分追悔自己人生中那些无法挽回的错误。我庆幸它们的骨子里还保有警觉,我也庆幸它们的心中,仍然装着一轮爱情的暖阳。
它们扶老携幼,奔走在夜幕之中,靠的就是身体里那些衰落的光亮。
而斧凿和猎枪,并不能最终敲碎它们。它们的长牙上藏着的刀子,仍然闪着月亮的银辉。
半夜起身,对着远处尖叫。我用岩石里聚集的海豚,我用风中沉默的冤魂;直到我自己,突然喉咙沙哑,身体出现一道裂缝;直到你从中探出头来,看着我信心全无,萎靡不振,一下子从自己的肉体里跳出,离开了我无形的身影……
而在半夜出来一个打铃人,气喘,咳嗽,像风中的老校舍,像碾坊里抖动的风车。此时三星已偏西,树梢上冰霜纷落。而锈铁已经把月光的话,传到了野外。此时隔墙似乎有耳,窃窃私语杳如消失,一波追不上一波了。
此时猎户座周围的流星雨,正在我梦中穿行……
人类如果衰弱于万物,我们的脸,在星辰之间雪花一样闪耀。但黑暗一直是隐秘的,雷霆掘出的沟渠,盛满了玻璃的碎片和白骨的声音。这时,我熟悉了月光照亮的田野,也熟悉了山岗上薄纱包裹的峰峦——它们又熬过了这一夜。而我们像平常一样醒来,洗漱、外出。
不管尘埃是否永生,我们只管苟活,像大街上轻佻的花店,在陶醉中推开门,把屈辱的身体插上花束,让它的今天,像一支透明的瓶子那样鲜艳夺目。
而末日如同一场强拆,我们始终无法阻挡它失败的车轮快速滑向深渊,如同我们无法阻挡自己,在春风中把青春的容颜修改了一次又一次。
我在玻璃器皿中卖血为生。你在枯枝里,秘藏了颓废的岁月。而我们的苦衷,都是一样的。这其中的快乐仅是一束光,溃败是另一束弯曲的光,只有麻木的身体,才能获得最后的解脱。
但这要走过几十年,或者更漫长的时间,才能到达。即使是闪电,即使是命运里埋伏的刀锋,也不能再次击穿它仅剩的肌肤——因为,那是一层薄纸一样仅有的自尊。
在时间的高处,我找到了一匹马的伤心之地。我喃喃自语:草原。陷落的天空。弯曲的穹顶。比秋风还冷漠的荒岗。顺着大地奔跑的黑泥……我要如何才能扶住她巨大的身影?
白天是不需要一盏灯的。一盏灯又有什么用?我心中纷飞的雪光,已经使八月开始了寒冷。断肠草、大芦荔、山楸树、血蘑菇、乌拉草、还魂笕、鬼打墙、旱魃子、云盘花、蛇灵芝、雾萌子、婆婆丁、益母草、降龙木、苍术、金莲花、石竹子、干枝梅……这是我天天带在身边的秘籍和药罐子,我把它们的汁液喝下去,驱寒回暖,以毒攻毒。
我把它们的茎叶编成花环,献给门前经过的少女,她马上换了一副笑脸说:“我爱你,包括你的美德、病毒、热情和忧伤,包括你微弱的呼吸和狭窄的胸膛,包括那些危险的小命和命中的芬芳……”我喃喃自语:草原,草原,我陷落的梦境和女王呵……在时间的高处,我百病缠身,苦挨着幸福的寂寞时光。我的身体上,盖着灰暗的天空。
鼹鼠在黑夜里钻出巢穴,它的丑陋,有安静之美。它磨牙的声音带着血腥,让我感到草原的辽阔和残暴。经过短暂的呼吸,或者眺望,只是一瞬,它就转身逃走了,像一位神秘的观众。它看见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
如果是一种游戏,它的出现扮演了谁的角色?城市慌乱的灯光是它要躲避的?鸡飞狗跳的乡村,让它预感到突然而至的祸端?牧场深处的雷声,摇动了它心中惊恐的宫廷。它扛在背上的粮仓过于庞大,压制了它逃跑的速度。但它的尖叫已经被我听见,它还要告诉我什么呢?
这盛大的风景中,安眠着你和我的居所,而草原和海水,仍然在昏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