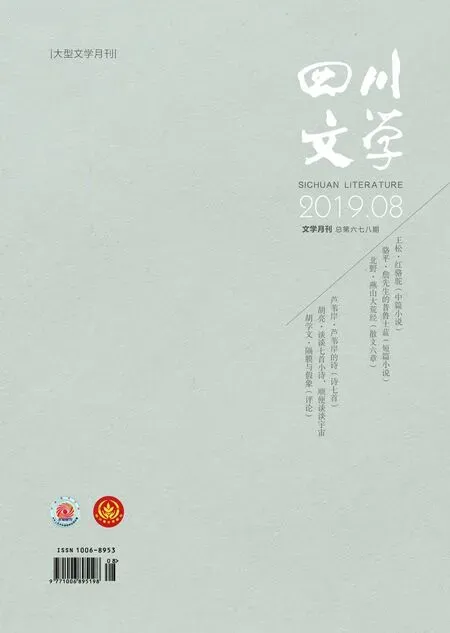赫二海的糟心事
2019-11-13刘宝凤
□文/刘宝凤
1
赫二海躺在床上睡不着,翻来覆去地咒骂着工头肥仔,狗日的都六个多月没发工资了,是准备把人熬到啥时候呢?今天和老婆通电话,老婆对几个月没往家寄钱生了疑心,还诈赫二海说,有熟人看见他搂着个花枝招展的女人打街上过,赫二海当下赌咒发誓说绝没有这回事。老婆才扑哧一声笑了,说逗他呢,就他那逑样子,谁眼瞎了才看得上。说完老婆好像觉出这话不对,又补充到,她是牛屎糊到眼睛上了。
干啥呢干啥呢,下铺的松朋把床板踢得咚咚响,床上是有你老婆哩?滚过来滚过去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赫二海被惊了一下,才觉出自己不光脑子在翻,身子也没停地翻转着呢。赫二海不敢再有响动,静静的,像个木乃伊一样,躺得平平的。
木乃伊是老婆常骂赫二海的话,因为他人傻嘴笨,用老婆的话说就是根本没长脑子,只会像个木乃伊一样,走哪儿挺哪儿,还不会挣钱,十足的窝囊货。没办法,赫二海念书少,除了一身蛮力就没别的本事,除了民工能干啥呢。虽然说这活饿不着但也吃不饱,就混个日子。赫二海盘算着他已经出来八个多月了,也不知道老婆给儿子把对象踏摸得咋样了,今天被老婆那么一乍胡,紧张得忘了问。想到儿子,赫二海才有点笑模样,不管他赫二海咋样,总算养出个好儿子。儿子念书不行,好在脑瓜子够用,技校毕业就开始在酒店当厨师,一个月没少挣钱呢,比他这个老子强得不是一点半点。
当然不能全靠儿子挣钱,老子总是差儿子一房媳妇的,所以赫二海才愿意跟着“大部队”来这离家几千公里的地方干活。他们之前在山城那边修公路,修完公路了,工头又说固城这边有活,问谁愿意跟着走。大家都跟着来了,原因很简单,没有工地愿意用当地的民工,为啥?这你就不懂了吧,当地民工离家近事情多,今天这个请假回去给谁帮忙结婚,明天那个村又有老人下世了要回去抬埋……一天到晚都有人请假,哪个工头泼烦死了才会搞些本地人。
这工地只有做饭的马头是本地人,他并不姓马,只因为长得人高马大,就被大家伙叫成马头了。第一次看见马头赫二海差点把他认成了大老板,一个人长得高大就是气派。哪像赫二海,才一米七出头的个子,瘦得麻秆一样,在哪里找工作都要被挑拣半天。好在亲戚给搭的线,才跟着肥仔混饭吃。其实在来这工地之前,老婆说家门口有个盖房的事需要民工,就是时间短,可能两个月就做完了,赫二海怕到时候活续不上,又得闲半年几个月的。不管咋样,他跟肥仔也混熟了,听肥仔说这边的活没个两三年是完不了工的。
只是要再不寄钱回去,老婆又该骂他把钱塞哪个女人那儿了。赫二海想老婆的嘴,真他妈毒。可是再毒也还是自己老婆,回去了热被窝一钻,也还是有些滋味的。
一想到这里赫二海又烦上了,除了刚来那两个月发了工资,后来的工资肥仔总是一脸笑地说马上发马上发,他的这个马得是要到蒙古骑回来呢。当然赫二海见了工头可不敢叫肥仔,得老老实实低头哈腰地叫人家王经理呢。背地里大家都说工头吃得肥头大耳快流油了,说工头有好几个小老婆,每一个都嫩得能掐出水来,还说肥仔把力气都用来扑小老婆了,当然没空去找大老板要钱。说这些话的时候松朋笑得最欢实,好像冷不丁摸了肥仔的小老婆一把似的。
说归说骂归骂,活儿还得照样干,那钱不发是给自己攒着呢,要不干活立马就得滚蛋,宿舍都别想住了。这次干活的地方在一个废弃的厂子,厂子倒闭后把大门口临近马路那两幢办公楼租给了外面的人,靠里面的厂房都是要拆掉的。据说这块地皮翻整好以后,要盖个什么温泉小区,还说要加入什么新科技,总之说这些赫二海不懂也不管,他只盼着按时发工钱,想到老婆一下子拿到五六个月攒下的工钱,肯定笑得满脸褶子。尤其是这次出来管吃管住,不用掏一个子儿,赫二海又自豪上了,回家一定得好好给老婆讲讲。
周围的高楼早都林立起来了,据肥仔说这个旧厂子规模大底盘也硬,没人能拿下这块地,就耽误到了现在。站在厂子里,头一抬,四面都是高楼,不用想都知道那是个热闹非凡的世界,可一进厂子就完全成了两个天地。老旧的食堂,带着高大烟囱的生产车间,还有几长溜库房,两层楼的宿舍,宽敞的水泥路,从哪儿都能看出来这厂子以前规模够大,也够气派。但也能感受到这样的厂子矗立在繁华的城市中央,实在有些大煞风景,就好像吃得正香的猪肉熬菜,却从里面拣出了一根头发,倒胃口呗。所以说该拆,不拆不建像赫二海这样的民工又到哪儿找活干呢。只能说这么大的厂子倒闭了,可惜喽。
赫二海他们是从厂子最里面的板房往外拆,靠近大门南边有一院原来的宿舍最后动,就让工人住了,用肥仔的话说就是紧跟时代要求,关心民工的住宿问题。一间宿舍有三张架子床,上下铺那种,铺盖一收拾就住进来了。赫二海他们几个都是从大西北来的,就挤到了同一间宿舍里。这间宿舍啥都好,就是老旧的木头窗户上,有几块玻璃不见了,大家就想让肥仔给装上。肥仔把手里的鳄鱼皮包一下抡到离得最近的松朋脑门子上,张口就骂,当你几个是闺阁里的小姐呢,还要啥玻璃,就你们这驴样子,摆到那儿都没人看。肥仔不肯装玻璃,指望他们几个就更不可能了,谁也不愿意花这冤枉钱,所以离窗户最近的铺位就没人去了,四个人宁愿挤在靠门这边的上下铺上。
赫二海他们几个的宿舍门口就是水池子,一条管子上装了七八个水管,就这人多的时候还得错换着用。夏天的时候,他们就脱了上衣在这水管下面冲凉水澡,不是爱干净,是怕热。这地方夏天热得人要脱层皮,哪有老家凉快。赫二海每次汗流浃背的时候就骂,狗日的天气也欺负外地人啊。厕所离这儿有点远,在宿舍背后再远一点的角落里,用简易的钢塑板搭起来的,两个茅坑的门上不知是谁还用黑笔煞有介事地分别写上了男和女。几个人就笑,就咱干活这地方,除了母蚊子就没见过个母的。
大家笑归笑,这好赖也管吃管住了,尽管大灶夫马头只会做水煮萝卜、白菜跟洋芋,里面连个油星星都没有,那也总比修公路风餐露宿的强,吃住的钱省下了还不是自个儿的。
不发钱赫二海倒还扛得住,他花钱节省又不抽烟,除了偶尔买点日用品,基本上没有额外开支。可松朋那伙人肯定是扛不住的,他们一到周末不上工都往那个环城公园的舞厅跑。赫二海从来都不去,他不是那种有歪心思的人,再说他儿子都快要娶老婆了,他可不能在这种事情上给儿子丢脸。工友们就都笑赫二海假正经,在外面老婆看不见管不着的,把自己憋得火大,舌疮都上来了。赫二海就说,才不是,那是不小心咬到了嘴唇,工友们更乐了,说那还不是缺肉吃。
所以松朋气赫二海翻腾不光是因为打扰了他睡觉,更是因为他好长时间都没钱去舞厅了,心里怄得慌。松朋要比赫二海年轻四五岁,看他一副烧心挠肺的样子在床上使性子,赫二海往下瞅了眼没敢笑出声。都他妈没钱闹的,松朋又使劲蹬着上铺的床板骂道。松朋没瞌睡,手往褥子底下一摸,拿出几张舞厅的门票在鼻子跟前闻着,好像那就是个白白嫩嫩的大姑娘。赫二海仔细瞧了下,门票上面画着一个大大的变了形的“舞”字,旁边还有一个搔首弄姿的女人仰着头,露出半截长白的脖子。赫二海就在心里骂,就你这逑样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
同样睡不着的冯柱子从床上一咕噜翻起来叫道,妈的,你们说,这肥仔啥时候能发工资啊,老子穷得天天喝米汤,这裤带都往脚下溜呢。
葛老三的声音也从床铺上面传了过来,你这哪儿是穷得往下溜,你那是骚得往下溜,见了谁都想解裤带吧。
你个狗日的,咋老说大实话。冯柱子在地上转了几圈,转到赫二海的床前,他站着刚好能看到赫二海平躺着的脸,哎,二海哥,我说把你的钱给兄弟借上一点么?
赫二海猛地捏紧了被子下的口袋,我没有钱,早花完了。
骗谁呢,你一天到黑捏着个包,谁不知道就你还有家底。给兄弟们匀一点呗,发了工资就还你了,再说了,你也不忍心看着弟兄们渴死吧,葛老三也说道。
就是就是,其他几个人也附和道。眼看着几个人都朝赫二海的床铺来了。赫二海见识过这几个人的生冷,以前有个工友不“合群”,被他们三两下扒得光光净给关到了门外面。赫二海嘴上说没有,还是怕大家真的上手,他可丢不起那人,只好说,你们这么多人,我没,没那么多钱。不用太多,一人二十就成,发了工资就还。葛老三一说二十,其他几个人笑得心照不宣。
破财消灾吧,赫二海只好从口袋里摸索出钱沓子,认认真真地给每个人抽了两张。赫二海有个习惯,喜欢把钱换成十块的,这样每次花钱不能超过一张,也算是个约束。抽完了六张,他心里一阵抽痛,只好叮嘱几个人尽快还钱。
赫二海想这个周六晚上过得真是憋屈。
第二天,宿舍的几个人早早都起来出去了,连灶上的水煮白菜都没吃,这帮人臭德性,赫二海一边嚼着蒸馍,一边对马头说,那几个人出去逛了,把他们的菜给我舀上吧。马头翻了个白眼又给赫二海的碗里添了半勺汤水。赫二海没敢再争取了,他知道马头的脾气,有一次新来的民工嫌菜少,结果马头把他的碗端起来,菜全倒回了盆里,任那个人叫骂了一下午也没再给他盛菜。从那以后没人敢跟马头说三道四,饭菜多也好少也罢,都安心地吃着。好的是虽然给的菜不多,但馍、面或者米饭是管饱的,就在打饭窗口外面放着。也就是说,只要你能吃下去,你随便盛去吧。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马头的活不好干,菜打多打少不是他说了算,是肥仔给的钱多少说了算,这么百十号人,手不敢松,一松钱就搂不住了,马头总不能自己往里面添钱吧。
马头说,你宿舍那几个货还真是活宝,全工地也就这几个人骚包,也不看看自己啥德性,还往黑舞厅跑,小心哪天叫局子的人给收拾了。赫二海没敢说是借他的钱,嘴里打着哈哈。你咋不去呢?赫二海连忙摆手,说咱不弄那事情。马头又说黑舞厅下午才开门,这会儿就是去了也只能在环城公司溜达。不过去得早了有挑头,去得晚了只能拾掇剩下的。
马头是本地人,知道的信息肯定比他多,赫二海就问马头,那真是弄那事儿的地方?马头呛他一句,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赫二海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似的,赶紧收拾碗走了。
下午没啥事,赫二海想着不如出去转转,他来这么久,还没见识过固城的繁华呢。赫二海不想花钱坐车,就借了马头平时买菜骑的自行车。这自行车破得,简直是除了铃不响,其他哪儿都响。
正是初秋,天还没完全凉,骑个车子吹着微风还真是舒服,总算把那个苦哈哈的夏天熬过去了,赫二海想。他琢磨着去城墙看看,这是固城的标志,来固城没去看过城墙,就跟没来一个味儿。赫二海转完城墙时间也不早了,他忽然想起松朋提过他们去的舞厅就在这附近。赫二海不知道哪根筋抽着了,就想去看一眼,不进去就在门口看一眼。也可能是因为几个工友借自己的钱来这里显摆,让赫二海心里不忿,以此来发泄自己的不满。也可能是别的原因,他说不清。本来想着看一眼就走,却愣是挪不动步子了,他看着门口夸张扭动着的“舞”字,心想就是这个地方?他把眼睛投向舞厅里走出来的人,还有点不相信这是松朋他们说的那回事,就盯着一个出来的人看,看得人家怪不好意思的,掩着脸赶紧小跑着走了。
赫二海又仰头看着舞厅门头上的四个大字“人间天上”,这不是那啥电视剧里的名字么,他正奇怪时,松朋几个人出来了,看到赫二海,揉了揉眼睛才跑过来拍他肩膀。几个人都露出贱贱的表情,一定要让赫二海进里面看看。赫二海嘴上说不去,身子却被他们几个架着,终于在跨进门的那一刻,赫二海找了个机会挣脱了,他跑出去老远,才想起自行车来,又赶紧回去找自行车。
等赫二海回到宿舍,其他人早已经回来了,没有了昨晚上的烦躁和暴戾,都一副满面春风的样子,像当了新郎官似的。赫二海低着头赶紧爬上了自己的床铺。松朋却不放过他,从下铺伸出个脑袋,问赫二海,啥滋味?是不是比家里老婆滋味好?赫二海没听出来啥意思,但在松朋不怀好意的笑声里,赫二海明白了他说的不是好话,就骂松朋神经病,赶紧钻进了自己的被窝,好像真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似的。
松朋却不放过他,把几张舞厅的门票塞到了赫二海的褥子下面,说,喏,这个送给你解馋啊。
2
赫二海在工地上发现了肥仔的身影,正从油光锃亮的新奥迪车里往外钻,赫二海记得之前肥仔来开的还不是这车,是一辆灰不溜秋的面包车,总之没有这个看着气派。赫二海放下手中的推车,悄声叫着松朋和葛老三几个。大家都眼露兴奋的光芒,这肥仔有些日子没来工地了,这次来说不定是来发工资的呢。
肥仔没有像往常那样背着手,悠闲地在工地上指手画脚一番,而是喊离得最近的人去招呼所有民工都过来开会。大伙觉得有戏,比平时聚涌得更快一些。
咳咳,肥仔清了清嗓子,说现在省上市上到处都在调查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情,如果上面有人来检查,让大家伙长个眼色,一定要说他们从来不拖欠工资,都是按时发放的。
大家一听这话有些懵,他妈的不发钱不说,还要叫人撒谎。
要是谁说错了话,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肥仔说这话的时候,眼里杀气毕露,看得赫二海脖子一缩,好像他告密被抓了个现形。肥仔再三强调,看着面生的人,或者穿着西装的人都有可能是来暗访的,让大家提高警惕,宁愿不说,也不能说错。谁要是说错了,欠的工钱就全被扣了。
大家都在底下嘀嘀咕咕地交头接耳,但当肥仔大喝一声,听到了没有时,大伙齐刷刷地喊知道了。肥仔这才卸下一脸的严肃,朝背后那个倚在车边的波浪大卷女人走去。那个女人穿着一身艳红色的短款连衣裙,两条白皙的腿在外面晃荡着。赫二海傻不愣登地瞅着女人想,我都穿上秋裤了,这女人光着腿冷不冷啊。这时葛老三软着声音叫了一声,王经理。大伙都向他投去赞赏的目光,因为这个时候敢开口说话的人,还真是胆儿肥。
王经理,葛老三舔了舔嘴唇,好像十天没喝水似的,说出来的话也干涸得冒烟,音调都低了下去,王经理,到底啥时候能发工资呢?大家也纷纷点头表示都想知道。我们都断粮了,老婆孩子也都等着用钱呢,一双双渴求的眼睛恨不得长出钩子来把肥仔的口袋打开看看。肥仔不耐烦地挥挥手,像驱赶一群苍蝇,该发的时候自然就发了,要是让我知道谁的嘴不老实,别怪我不客气。
说完,肥仔快步上了豪华新车,那个媚眼如丝的女人也轻蔑地瞟了葛老三一眼,像是看一株不起眼的白菜,不屑至极。
车屁股冒着白烟走了,恶狠狠的样子。
妈的,这亏先人的肥仔,有本事包工程,没本事给大家发工钱……骂人的话在工地上四处响起,可除了骂上几句解气,谁还有啥办法呢,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追问得急了,肥仔顶多一句话,就这活你干就干,不干了滚蛋,谁离了你这伙胡屠夫,还不吃带毛的猪了?!
都没发钱,又不是一个人没发钱,按理赫二海不该这么心慌,可糟糕的是,宿舍几个人都把目光瞄到他这儿了,都知道他口袋里还有几个钱,过个两三周就觍个脸来借二三十的。但就是再有钱,也抵不住这三四个人轮流借啊。而且一直没发工资,松朋他们拿什么还?他们只会说发了钱马上还你,马上你奶个脚后跟,这意思不发钱就得跟老子赖账是吧。
赫二海有些悔恨自己那天晚上的软弱了,因为那一次心软,给自己挖下了一个填不满的坑。要说前几次都给大家伙借钱了,后面不借就得罪人。他们还更绝,一副你这次不借,前面借的就不还了的赖皮样,把赫二海气得够呛。
那几天,果真有陌生的面孔来工地转悠,碰到个农民工就问东问西。赫二海真想走过去说肥仔已经六个多月没给我们发工资了,可他不敢,只能站在一边生闷气。被问到的农民工也一样,明明一脸愁相,还偏偏得给人家说在这里干活好着呢,工钱不少,发得也及时,一脸谄媚的样子活像一只哈巴狗。赫二海就小声骂被问话的工友真傻,那又不是肥仔怕啥呢,挺直了腰杆跟他说话啊。可真要有陌生人向赫二海的方向来,他保准儿跑得比兔子还快。
所以一到晚上,宿舍里此起彼伏的骂声更稠密了。
松朋几个聊着聊着就把话题转向了肥仔带来的那个漂亮女人身上,狗日的要是让我摸几把,我就不把他欠咱们工钱的事情说出来。冯柱子更是把自己当成肥仔,幻想他跟那个波浪卷女人各种不入流的事情。赫二海说我老婆那么丑的女人脾气都那么大,那漂亮女人的脾气肯定更大吧。赫二海你就是个傻老冒,想还不往美了想,只有你个窝囊货才会三句话不离老婆,你是还准备窝在你老婆怀里吃奶呢,瞧你那点儿出息。葛老三一句话把赫二海噎得不知道回啥好。
那几天,来暗访的人走了一波又来一波,肥仔开始还没太在意,接到大老板电话后就不敢再大意了,生怕谁走漏了风声就得停工写检查。肥仔在沿街面的大楼南侧拾掇了一间办公室待着,从窗户能看到工地里面,说是方便盯着农民工,却有事没事就跟那个波浪卷女人在办公室调情,从窗户下路过的松朋亲眼看见了,说两个人在办公室里就亲嘴来着。
从肥仔的办公室往南,能看到一座雕花亭子,也是要拆的对象。亭子高,而且是木质结构,得人工一下下拆除,不如里面能用机器推倒的厂房好拆,所以这个活一直扔着。松朋偏自告奋勇地跑过来了,还叫上了赫二海和葛老三几个。松朋人在这边干活,却不时朝北边那个窗户瞅一眼,运气好还能看到波浪卷女人。松朋还真逮着了跟波浪卷女人说话的机会,她问松朋厕所在哪儿,香艳的气息从发嗲的声音里往外散。大楼里是有厕所的,但松朋偏偏指了指他们平时去的那个,舌头打结地连说带比画地指向了门上写着男女的那间简易厕所。
松朋瞅着女人朝那个方向走去,不知怎的就露出了一副得意的表情,好像刚从女厕所偷窥回来似的。正好赫二海过来推废弃的木料,松朋便鬼使神差地给赫二海说,刚肥仔去那边上厕所,让人给他送手纸。赫二海是个老实人,可怜巴巴地回宿舍扯了半卷卫生纸,就往厕所那边去。
结果赫二海一敲男厕所的门没人,他就敲女厕所的门,波浪卷女人在里面哇哇乱叫,吓得赫二海纸一扔,撒腿就跑。回到了亭子这边,赫二海就骂松朋不是个东西,葛老三一看赫二海的紧张样子便笑得前俯后仰。
晚上松朋和葛老三一个劲儿地缠着赫二海,让他讲讲都看见啥了,波浪卷女人白不白,身上香不香……赫二海说他啥也没看见,听见女人的声音腿都软了。不对,冯柱子说你腿软了怎么跑回来的?冯柱子不仅不相信,还开始信马由缰地胡诌起来。遇上松朋这几个不要脸的牛皮糖,赫二海只有认输的份。赫二海知道松朋几个是计较让还钱的事情呢,可借钱还钱,天经地义啊,赫二海又开始在心里问候起几个人的祖宗八代。
这事儿本来就这么过去了,谁知道松朋就是个搅屎棍,硬把一个玩笑发酵得有鼻子有眼,在工地里越传越离谱,说有人去厕所偷看波浪卷女人,连屁股上的痣都看清楚了。赫二海听了一肚子气,想去争辩又觉得没意义,便端了吃饭的碗躲到了食堂外面。没想到肥仔居然也到灶上来了,说是下雨了懒得出去,就跟大伙一块儿同甘共苦。话是这么说,估计也是想把大家伙看紧一些。
谁都没注意到肥仔的到来,头抵着头依然说得起劲,好像自己亲眼看见了波浪卷女人一样。本就是胡猜瞎蒙的,偏又碰了巧,波浪卷女人臀部真有一颗痣,肥仔也就信了真,他一把打翻了盛菜的盆子,热闹的食堂顿时噤了声。
这下事情闹大了。
3
肥仔把赫二海叫去了办公室,咣一声关上门,便开始声色俱厉地逼问赫二海到底都看见啥了。赫二海一肚子委屈,真的啥都没看见。怎么可能,肥仔背着手来回转着,手里的烟都顾不上抽了,眼看着要烧到指头上了,赫二海结结巴巴地说,你的烟完了。肥仔瞪了赫二海一眼,这个关键时候赫二海还有心思关心烟头,让他很生气。肥仔把烟屁股塞到一次性纸杯里使劲按了按,搞得赫二海脖子一缩,好像自己就是那个倒霉的烟屁股。
无论赫二海怎么讲原委,肥仔始终一副“你在说谎”的表情,还试图引导着赫二海说出波浪卷女人的痣在左边还是右边。赫二海头都快炸了,只好蔫蔫地求肥仔高抬贵手,放他一马。赫二海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痛恨自己只长了一根舌头,不知道咋样给自己辩解,如果是冯柱子那滑头,肯定是有办法的。
可赫二海越是这样,肥仔越是笃定他看见了,而且看得很真切,因为肥仔去厕所那边“侦察”过了,女厕所的门上有个不宽的缝隙,把眼睛贴上去怎么可能看不见里面。赫二海心想那破烂厕所,里面连个灯都没有,关上门都可能踩到茅坑里,就算想看也看不见的。
赫二海被翻过来倒过去地问,就这么扛着不让走,从中午到下午,眼看着天都蒙蒙黑了。赫二海急了,这肥仔要一直不放自己出去,明天还有可能耽误出工,这按天计的工资可经不起这么折腾。赫二海把心一横,脖子一扭说出来的话青筋毕露:“你不就是想听我去看了你的女人么,就是,就是偷看了,这么说行了吧!你赶紧放我走吧,明天我还要上工呢!”
肥仔前面的怒骂好像就是为了得到这个答案,一听到赫二海这样说反而踏实了,说明他的疑心不是空穴来风。可接下来干啥呢,肥仔想了想便踢了赫二海几脚,说也就是你,换了其他人我早把他的皮扒了。肥仔没跟赫二海过多计较,说是看在亲戚的面子上,他可能也知道赫二海这种老实疙瘩做不出那样下作的事情,但赫二海脸上还是臊臊的。
过了几天,赫二海的儿子打电话说要到固城给酒店采买一些厨房用品,正好来看看他。被肥仔一顿收拾的赫二海还没缓过劲来,任谁被冤枉了估计也跟他一样沉闷吧。他想不明白的是,明明他说的是真话,肥仔却死活不相信,难道肥仔喜欢听假话?还是假话听多了就成真话了?赫二海想,他活了五十多岁了,咋越来越活不明白,也看不懂这世道,到底啥是真的,啥是假的?难道他记错了,他真的偷看了波浪卷女人?
因为这件事,赫二海有好长时间都不理松朋,可松朋依然没皮没脸地往他跟前凑。这次他又要借钱,赫二海一口回绝,并让他赶紧把前面的钱还了。赫二海很少发火,松朋也自知没趣,悻悻地算了。
一想到儿子要来,赫二海被肥仔冤枉的难受劲也散了一半。他就知道儿子准有大出息,这采买东西在过去那就叫大总管,儿子都当上酒店的大总管了,比他这当爹的出息了不止一点半点。以后儿子混好了,他就再也不出来打工了,就在家当一个悠闲的阿公公,等着给儿子看孩子。不用像现在这样,走哪儿都要受欺负,肥仔、松朋,没一个好东西。
赫二海一转身又有些犯难了,平时他都是在灶上吃饭,儿子来了,总不能跟他一样在灶上吃吧,就那水煮白菜自己吃得都反胃,更别说在酒店做大厨的儿子了。想来想去,赫二海决定在外面请儿子吃顿饭。
晚上,赫二海说了儿子要来的事情,葛老三几个人都说好事情,娃能来看你说明有孝心。可当赫二海说要请儿子吃饭让大家还钱时,松朋马上就说,你儿子没事上咱这儿来干啥,就咱住的这烂地方,干的这些下苦活,叫你儿子看见多寒碜,其他几个人也附和着。赫二海虽然知道他们是没钱还他才这么说的,但他一想到自己的工作环境,也还真不适合叫儿子过来。
冯柱子脑瓜活,说,二海哥,你再别瞎操心了,你儿子那么有出息,指不定还要请你去他住的酒店吃好的呢,你就别在这儿费心思了。
葛老三也说,对哦对哦,咋没想到这点呢。肯定的,你还不如把自己收拾整齐,也上人家那大酒店逛上一回,要能住一晚上才美哩。
几个人三说两说,把赫二海那些积攒在心里的不快散去了,他觉得大家说得有道理,自己是该准备一番。他看了看身上的衣服,万一儿子带自己去酒店,穿成这样的确太寒酸了。他把包打开,拿出了最好的一身衣服,这衣服他从来都不舍得在工地穿,只有离开家或者回家的时候才穿上,就是想让老婆和儿子知道自己在外面过得好呢。对,就穿这一身。
把衣服收拾妥当,赫二海就给儿子打电话说,既然酒店给他报销食宿,就别上工地来了,这地方又脏又乱,来了也没地方插脚。儿子却偏不,甚至开玩笑说他妈交代的,让他到工地好好地考察一下赫二海。哪怕赫二海一再提出两人可以在外面见面吃饭,儿子还是执意要来。
儿子要来,赫二海就让大伙好赖把宿舍收拾一下。其他人还好,把自己的床铺简单收拾了,乍一看,倒也过得去。只有松朋一百个不情愿,赫二海不给他借钱,他的火没处发,只好把被子胡乱揉成一团表达不满。赫二海有些生气,松朋平时咋样不说了,这自己的儿子要来,怎么着也得给个面子吧,被子弄成这样子,实在太不像话了。赫二海就想帮松朋把被子重新叠整齐,没承想,他手刚把被子抖开,一件女人的内衣豁然出现在眼前。妈呀,这狗日的,成天偷着弄啥呢,这几根线的衣裳咋穿呢,赫二海像捏到了烫手的洋芋。
爸,爸你在没?儿子的声音突然传来,赫二海吓了一跳,胡乱把内衣塞进了自己的口袋,又赶紧把松朋的被子叠起来。还没收拾利索,西装革履的儿子已经进来了,一脸帅气,赫二海觉得宿舍都顿时变得明亮了。
赫二海只记得给儿子说过厂子的大概位置,没说过宿舍在哪儿。儿子好像看出了他的疑惑,说在门口碰见几个农民工,人家给他指的方位,他就自己进来了。
今天刚好都在上工,只有赫二海请假在宿舍,所以给他爷俩腾出了说话的地方。儿子顺势坐在了松朋的床铺上,赫二海说这不是我的铺,我的铺在上边,儿子看了看说,上去不方便,咱就坐这儿说会儿话就行。
赫二海的新衣服成功引起了儿子的注意,儿子说,爸你在工地咋还穿得这么讲究。赫二海只是笑,他的那点小心思自然不能说出来。
接着,儿子说,别人给介绍的对象,谈得差不多了,妈说是到年跟前了就先定下来,把礼钱啥的说好了,明年五一估计就能结婚。赫二海高兴得连说了几个好字,两只手交叉着搓了又搓,好像迫不及待准备要见准儿媳妇了。儿子又对赫二海说,妈问他工资发了没,这就要准备订婚结婚了得不少钱呢。赫二海嘴上说没问题,心里却虚到了底,再两三个月就过年了,到底能不能拿到钱还两说呢。可他不想让儿子失望,硬是憋着一口气坚定地说过几天就把钱给家里打回去。
儿子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接着说他自己倒是攒了点钱,但现在都兴买房子,他的钱要用来买个一居室的房子,结婚后够他们小两口住就行。赫二海心里酸涩得恨不得把手里的苹果扔出去,儿子心里丝毫没有他这个当爹的,这是要跟他们分家另过啊。但赫二海没那么做,还把好不容易削了皮的苹果硬塞进了儿子手里。
看儿子一口口啃着苹果,赫二海才想起来一早上忙着收拾卫生,都忘记打水了,该给儿子泡杯茶的,他便拎着水壶出去了。儿子便站起来上下打量着宿舍,比想象中的要整齐一些,但依然很寒酸,除了被褥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是平时用的小东西。儿子叹一口气想摸摸赫二海的褥子薄厚,他听说固城的冬天特别冷。儿子的手刚往褥子下一塞,便发现有一叠硬纸有点硌手,顺手拿起来看了看,是舞厅的门票。
赫二海本想着和儿子好好吃顿饭,儿子说什么都不肯,更别提带赫二海去酒店看看了,只说让他早点把钱寄回去,省得他妈操心。赫二海强压着内心的失望,说你难得来一趟,连饭都不吃,有点说不过去。他就是这种臭讲究的人,哪怕口袋没钱出去借,也不能让上门的客人饿着肚子回。更何况来的是他的儿子,他一辈子的寄托和希望。他觉得有些伤感,便把上午专门去买的苹果、香蕉一股脑儿连袋子塞给儿子。儿子说什么都不要,说他还要到处跑采购,拿这些东西不方便。
赫二海便想着给儿子塞点钱,像小时候那样,给了钱会让他这个爹当得心里瓷实,才没白让比自己还高的小伙子叫他一声爹。赫二海要给,儿子不要,硬是把一叠好好的钱推让得皱巴巴的。儿子郑重地把钱塞回赫二海的口袋里,说,爸,这点小钱我还是有的。赫二海明白了,儿子想要的是大钱,就这么一晃神,儿子把他口袋里的内衣带出来了,儿子蓦然脸色大变。赫二海只好说这……这是给你妈买的……心里却暗骂,这狗日的松朋,净给自己添乱。赫二海越想赶快把内衣塞回口袋,那交错的细带子越不听话,弄了好几下,才塞回了口袋。那叫我给妈捎回去?儿子试探地问。不,不,我回头给你妈寄回去,赫二海只能硬着头皮圆谎。这衣服要真寄给老婆了,他就得脱层皮。
儿子没多说话,走了。留赫二海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宿舍里,像收完庄稼漏掉的那一株玉米,孤零零没有依靠。他大脑空白了许久,才记起那件内衣,一把扔回了松朋的床上,呸了一声。
4
隔了几天,赫二海打电话问儿子回去没,在固城办事顺利不?儿子没有回答,只说固城的报纸有点意思,让赫二海看看。赫二海哪有心思看报纸,嘴里却应了。儿子又问给他妈买的衣服寄回去了没有?赫二海奇怪,啥衣服?我啥时候给你妈买过衣服?儿子说工地上的人都说你不正经,我还不相信,看来是真的了。儿子啪一声挂了电话。赫二海想肥仔都不信的事情,是哪个嚼舌根的说给儿子听的?
紧接着老婆的电话来了,本来说好一个月只通一次电话的,这么急的打来是要干啥?老婆的电话简单明了,就一句话,赫二海,好你个狗日的,我要跟你离婚。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老婆根本不给赫二海说话的机会,把他骂了个鬼吹火:你挣钱全用到骚女人身上,你心里就没有我跟儿子,我在家一把把屎尿地拉扯儿子,好不容易儿子该娶媳妇了,你倒生了花花肠子……
赫二海把手机拿远了,还能感觉到老婆的唾沫星子在往自己脸上喷。老婆终于骂累了,坚定地说让赫二海赶紧回去离婚,还让赫二海滚得越远越好。
赫二海不知道到底该听哪一句,是赶紧回去离婚,还是滚得越远越好。他茫然地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羞辱,这种感觉还是在他十来岁的时候有过,邻居家丢了鸡蛋,非说是他拿的,他再怎么争辩都没用,只觉得羞辱,这种不信任让他非常难过和自卑。从那以后他就保持沉默,能不说话的时候绝不会多说一个字。所以老婆总骂他木乃伊是对的,他就是长了嘴,却不会说话的木头。
赫二海想打电话再问问儿子,想问清楚老婆到底是犯了哪门子病了?结果儿子的电话没有人接听,等他过会儿再打的时候提示关机。
葛老三回宿舍的时候,说又有穿着西装革履的人向他打听发工资的事情,他估摸着又是暗访的人,只好硬着头皮说发钱了。冯柱子也说前几天有个年轻小伙也在工地打听发工资的事情呢。
接着松朋没完没了地说,暗访的人跟肥仔是一路货色,要不然咋不一直待在工地上看看到底有没有给大家发工资,这些人光做些表面文章,可怜他们这些农民工拿不到钱还一肚子委屈。
有个念头一闪而过,赫二海没抓住。只觉得老婆发神经,儿子也奇怪,好像都不对劲,他却不明白到底是哪里不对劲。但他并不是那种喜欢刨根问底的人,他想还是好好干活吧,到年底带着钱回去,看老婆还有什么话说。
那天松朋和葛老三几个人,又趁着周末出去了,赫二海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又借着钱了,几个人春风得意的样子,还背着自己挤眉弄眼,是怕他追着要钱吧。赫二海现在心烦得连催要钱的劲都没有了,他只在心里嘀咕老婆到底是犯啥病了,就像葛老三说的那样,他心里来回只有老婆,是没出息,可小日子谁不是这样过的呢。
下午葛老三几个回来就很不对劲,好像眉眼间有掩不住的庆幸,又好像还略有遗憾,从他们遮遮掩掩的话里,赫二海断定他们这次去没办成好事,好像是那个舞厅出啥事了。赫二海懒得去问,他现在非常烦,除非老婆打电话来说不离婚了。赫二海特别了解老婆,那是个说一不二的女人,年轻那会儿要跟自己结婚,也是撕破脸皮跟娘家哥嫂闹了好久。后来结婚有了儿子,老婆非要去弄个卖猪肉的摊子,赫二海见着那些血腥的东西就害怕,说啥都不同意。结果呢老婆的肉摊支起来了,为了避开卖肉切肉的血腥,赫二海只能到外面打工。所以对老婆说要离婚的事情,赫二海一点都不怀疑,老婆是个说得出做得到的人。
赫二海只盼着赶紧到年底,发了钱好回家过年。
谁知道年底还没到,一个重磅消息却来了,肥仔跑了,说是前面承包的公路用不合格水泥出事了。欠下了农民工一河滩的钱,人跑没影了,这怎么能行,赫二海心慌气短地跟着大伙儿一块儿去找大老板。大老板却说上面检查时,他把一年的工钱都提前给肥仔了,上次追问肥仔也说工资发到大家手上了,他还问了几个农民工的。
完了,这下全完了。
妈的,被肥仔耍了。一群男人围在一起有了哭泣声,没钱可怎么回去过年啊。干了一年等于白干了,当下就有人不活了,喊着要跳楼。
赫二海是怎么硬着头皮回家的,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年底了儿子要订婚,有没有钱他都得回去看看。
站在熟悉的楼栋门前,赫二海心里五味杂陈,他想知道老婆为啥要跟他离婚,但又怕知道。所以他站了好久,心里设想了无数个可能,才终于鼓足了勇气。他拿钥匙的手颤抖着,不敢把钥匙插到孔上,他干了一年活,除了人回来了,其他一无所获,根本就没办法给老婆交代。两件事夹在一起,让他明明渴望回家,却不敢推开家门。
谁承想,门自己开了,老婆拎着一袋垃圾,看见他非但没有一年没见的激动,反而身手敏捷地把垃圾准确无误地扔在了他身上。
老婆一边劈头盖脸地挠他,一边骂他不要脸,在外面找女人。老婆身材高大,常年干粗活劲也大,赫二海推不开她,几下就把他抓得不成人样。老婆还在那里大骂,赫二海本就矮小的身材在她面前又矮下去了半截。
赫二海试图解释,老婆就问你说你没找骚女人,那好,钱呢?你干了一年活,钱都跑哪儿去了?!
赫二海自然拿不出来。老婆便继续打骂他,叫你骗我!叫你骗我!你狗日的还不承认!上次儿子去你们工地,打听得清清楚楚呢,工资从来都没拖欠。你还在这儿扯谎,眼看都要当阿公的人了,也不臊得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还给那骚女人买什么一根线的内衣,说出来我都觉着恶心……
儿子也走出来,扔给他一张报纸和几张舞厅门票,让他看清楚,这是在他褥子下面拿的。赫二海知道这门票是松朋经常拿着看的那种,就捡起了报纸。说是记者去“人间天上”暗访,中途舞厅的灯灭了四十分钟后,满地都是用过的避孕套。哦!怪不得那天葛老三和松朋一脸庆幸的样子……
赫二海总算是明白了,这一系列的事情串联起来,可不就让儿子跟老婆误会了么,难怪儿子跟他说话时一脸恶心想吐的表情。
在老婆的打骂声中,赫二海硬是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讲了一遍,可磨破了嘴皮子也没人相信他,老婆不信,儿子理都不愿意理他,还让妈快点离婚,省得他娶媳妇的时候人家说他有个这样的爸。赫二海疼得心都拧成麻花了,可他的解释却显得那么苍白。他一使劲就推开了老婆,原来他是可以推开老婆的,这么些年来,他一直以为老婆比他力气大,所以心甘情愿受老婆欺负,原来并不是老婆力气大,而是他不舍得用劲推她。
扑整了一下衣服,赫二海转身就往外走。老婆愣了一下,但还是拦住了他,问他干啥去?他想说去找松朋或者葛老三来给自己作证,可满腹委屈让他不由地赌气大声说道,找骚女人去!如果说刚才老婆的抠抓挠都是表面功夫,那这次痛到心里的掐和咬就货真价实了。就你这逑样子,还找骚女人!我让你找让你找!离婚,马上离婚!这日子过不成了!
真他妈的糟心,为啥说真话没人信,说假话偏偏就都信了呢,肥仔是这样,大老板是这样,连老婆也是这样。赫二海不懂,他越活越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