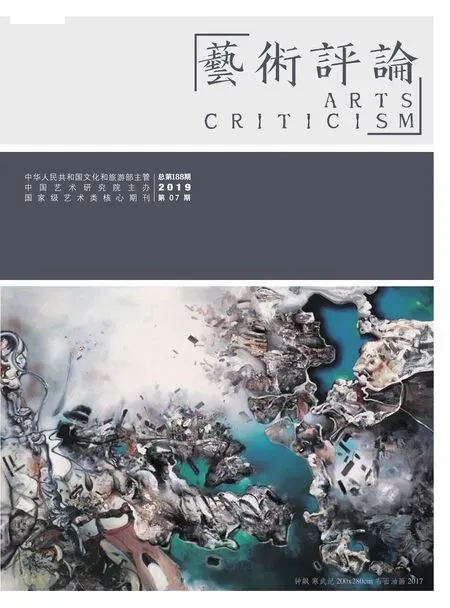中西比较视域下的电影伦理溯源
——兼谈关于中国电影学派理论建构的思考
2019-11-13
[内容提要]舶自西方的电影形式在中国落地生根以后便一直浸润在中华伦理文化之中,无论是电影创作形态,还是电影理论与批评体系,一定程度上都受中华民族伦理取向和价值判断的影响,与西方电影发展呈现出不同的路径和特色。因此,在中西比较视域中进行电影伦理溯源,认识中西电影创作实践与学术研究差异,并从传统文化,特别是伦理文化的角度分析其成因,可以更好地认识我国电影发展的独有优势和薄弱环节,从而在充分了解西方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参考借鉴,为中国电影学派建设提供学理支撑。
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式,电影深受民族文化滋养。了解一个国家、民族电影的独有特色,需从其传统文化中求本溯源,且在与异域文化的比照中辨识该民族电影文化的特质。相较于西方文化而言,中国文化具有鲜明的伦理特征。中华民族的历代先贤崇德重礼,将修身养性、社会教化同国家治理相结合,形成德治思想和伦理文化。舶自西方的电影形式在中国落地生根以后便一直浸润在伦理文化之中,无论其创作、批评还是理论建构,一定程度上都受中华民族独特价值判断与伦理取向的影响,与西方电影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路径和特色。
因此,在中西比较视域中认识中西电影创作实践与学术研究差异,并从传统文化,特别是伦理文化的角度分析其成因,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电影发展的独有优势和薄弱环节,从而在充分了解西方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借鉴,为中国电影学派建设提供学理支撑。
一、电影创作体现伦理差异:注重人伦与探求法理
中西方伦理的不同取向和特质往往潜移默化地体现在电影创作之中,构成不同的电影文化和创作传统,且往往能够从主流电影类型发展中呈现出来。其中,就伦理取向而言,中华文化注重人伦教化,强调内求于心,西方推崇科学理性,倾向外求于世,这种伦理诉求与思维方式不但是电影研究方法论的主要出发点,也体现在电影创作之中。其中,在影片类型表现上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家庭伦理片与科幻电影在中西方的不同地位与发展面貌,以及中西动作片中对于英雄形象刻画的不同伦理指向。
(一)注重人伦之宜的家庭伦理片
中国传统文化受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儒家思想以家庭为本位、伦理为中心、等级为基础,社会治理以“礼治”“德治”为主,法治为辅,主张圣贤决定礼法,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主要通过道德原则、伦理规范和宣传教化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依靠德性权威维护社会秩序,即“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 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从“父慈子孝”推至“忠君爱臣”,将家庭的血亲伦理关系外推为国家的伦理法则,家国同构成为主要特征,这种注重修身存养、人伦之宜的伦理文化、道德思维不但渗透在中国的政治生态、社会生活和艺术审美之中,也在中国电影艺术发展中明显体现出来,形成以人伦教化和社会责任为重的电影观,构成中国电影类型发展的独特形态。
譬如,中国第一部故事短片《难夫难妻》(1913)和促成“国产电影运动”的《孤儿救祖记》(1923)都是通过家庭伦理题材体现现实批判意识。此后,家庭伦理电影在中国一直雄踞主流地位,从蔡楚生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费穆的《小城之春》,谢晋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张艺谋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我的父亲母亲》,黄健中的《良家妇女》,颜学恕的《野山》,到近年来的《钢的琴》《相爱相亲》《失孤》等,这一系列家庭伦理电影都从表现家庭亲情、伦常关系出发探讨社会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表述传统。
中国的家庭伦理电影往往承载着中华传统伦常观念,张扬中国伦理文化所崇尚的乐“群”贵“和”原则,彰显“仁爱孝悌”“笃实宽厚”“谦和好礼”等中华传统美德,在表现家庭悲欢、天伦之乐时给观众以情感抚慰,在描述社会人生、世态炎凉的同时渲染浓浓亲情,不但能够净化心灵、呼唤责任,而且可以播扬中华民族主流文化意识,巩固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形成稳定的道德规范系统。
然而,西方电影虽然不乏家庭伦理内容,但并未发展成为主流电影类型,因为从文化性质和社会制度来看,与中国文化偏重“伦理”,注重“礼治”不同,西方文化更加倾向于“法理”,以法治为主,德治为辅,通过法律与制度维护社会秩序。而且,西方强调个体独立性和自由的人格,以个人取向为主,忽视家族或宗族纽带,更加关注个人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家庭伦理关系在向社会、国家过渡时逐渐弱化。在黑格尔看来,家庭生活和国家生活分别遵循不同的规律,前者基于血缘关系,后者基于国家法律,即其在《精神现象学》所称的“神的规律”和“人的规律”,两者之间往往存在着原则上的冲突和对立。所以,中西不同的伦理观决定了中西主流类型片不同的走向。
(二)彰显科学探索精神的科幻片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透视中国,指出,“我们文明的显著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中国文明的长处则在于对人生归宿的合理理解”,这是因为西方“主客二分”的“认知型”思维方式更加崇尚“科学理性”,即将宇宙作为外在的客体进行研究和探索。在伦理选择中,西方主张把科学知识作为通向道德最高境界的方法与手段。譬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总结的“四德”为智慧、勇敢、公正和节制,智慧位列其首;苏格拉底也明确指出“美德就是知识”,将知识或理性作为道德的前提。可见,西方崇尚科学探索精神,不但自然科学发达,其对科学知识的渴求和对自然界的探求精神也熔铸于电影创作之中,使科幻电影在电影发明不久便应运而生。
1902年,法国导演乔治·梅里爱拍摄了《月球旅行记》,1927年德国摄制了《大都会》,美国也陆续推出《科学怪人》(1910)、《化身博士》(1913)、《海底两万里》(1916)等科幻电影,好莱坞科幻片的产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渐成熟,五六十年代首度繁荣,90年代以后更是借助电脑特效等高新科技达到全面繁盛。
十年来,好莱坞科幻片大举进入中国电影市场。自2009年《2012》获得中国票房冠军之后,好莱坞科幻片在中国进口片票房前十名中经常独拥四五席,且一直占据大部分电影市场份额。然而,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多年来,国产科幻电影数量稀缺。据统计,20 世纪中国大陆仅出品了14部科幻电影;21 世纪头十年仅有11部,此后科幻电影数量有所增加,但主要为网络大电影,进入院线且引起反响的影片稀少。这一定程度上源于我国资金和技术方面的弱势,但也因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欠缺崇尚科学的伦理基础,即与西方偏重向外探究宇宙、控制自然的伦理取向不同,中华民族更加看重修养内心。王安石在《礼乐论》中便说“圣人内求, 世人外求”,道家把“为学”(知识) 与“为道 ”(道德) 对立,指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认为“求仁”高于“求智”,注重伦理之功、道德之用,忽略科学之真,认为道德品质比科学知识更重要。这一观念不但导致我国近代以来科学精神匮乏,自然科学发展缓慢,而且使科幻片在我国的发展先天不足,缺乏有利的文化土壤。
(三)中西动作片中不同的英雄观
“英雄观”反映出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所持的道德理念和理想追求。中国传统上崇尚“舍生取义”“舍小家,为大家”“精忠报国”等家国情怀和集体主义精神,西方则强调人的主体性,重视个体价值的自我实现。中西不同的英雄观体现在各自典型的动作片类型之中,折射出中西方对于德与法、家与国等伦理价值的不同侧重。
武侠动作电影类型独具中国特色,倡导源于中国春秋时期的侠义精神。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说,“春秋以后,游士日多”,而士之中,“文者为儒,武者为侠”,文儒与武侠同出一源,且“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电影进入中国之后,自然吸纳武侠小说与武侠戏剧的叙事内核与传统。1925年,我国推出第一部中国武侠电影《女侠李飞飞》,但真正获得成功的是1928年明星电影公司出品的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连续拍了18集,创下中国电影史上续集最多的单片电影记录。此后,武侠片作为中国独特的电影类型载入史册。从张彻的《独臂刀》《刺马》,李小龙的《精武门》《龙争虎斗》,成龙的《蛇形刁手》《醉拳》,胡金铨的《侠女》《忠烈图》,到李安的《卧虎藏龙》(2000)和徐克导演的黄飞鸿系列片,武侠片不但展示了中华武术,还张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气节,在银幕内外传扬仁义、诚信、谦让的游侠之德,标示着中华民族的道德取向和情义伦理,即对舍己为人、扶危济困的侠义精神的推崇,故以其独特神韵获得观众青睐,成为中华文化的标志之一。
然而,由于中西文化传统及人们的伦理观、人生观、价值观有所不同,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国际观众乃至电影学者在观看中国武侠电影时存在认知上的差异,对武侠片体现的价值取向、信仰体系、社会制度和行为模式产生不同理解,即因文化结构差异而出现“文化折扣”现象。譬如,美国著名电影学者大卫·波德威尔在《香港电影的秘密》中提到,中国的侠义传奇缔造了一个人们心目中的国度,那里虽有稳固的传统,但既不属于法律,也不属于政府,而是关乎光明磊落的个人操守。在此,波德威尔把中国武侠片与美国西部片加以比较。西部片是美国的古老片种之一,在电影技术传入美国不久的1903年,埃德温·鲍特拍摄了《火车大劫案》,奠定了西部片在美国电影史上的地位。作为美国电影的特殊类型,西部片并非注重再现美国西部大开发的真实历史,而是着重营造理想的道德规范,体现美国民族性格和精神指向。在西部片中,作为英雄的警长或牛仔代表了执法者、探险者和征服者,为保护白人移民而除暴安良,反映了美国人对秩序、和平、公正和法律的向往。波德威尔指出,在美国西部片中,英雄人物若非搬出文明社会的公义,便无法将坏人绳之以法,但武侠片中缺少超越个人的法律传统,英雄必须行侠仗义,暴力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这种男儿的荣辱观似属儿戏,但别具感染力。
可见,不同伦理取向的文化语境衍生出的电影创作形态各具特色,构成了民族电影风格的独特底蕴,也作为电影研究的基础,使中西电影理论与批评体系建设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二、电影批评伦理基点差异:教化求善与探索求真
中西方伦理观对于真、善、美的强调各有侧重。中国注重善美统一,认为“求善”高于“求真”,倾向于从道德情感中寻求美感体验;西方以真为美,强调的“真”主要指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和客观发展规律。上述倾向也体现在电影批评实践之中,即中国电影批评注重伦理文化、道德思维下的社会责任和教化功能,而对西方电影研究者而言,一种能够模糊现实与虚构之间界限的媒介自然引发伦理问题,故多在“虚构/现实”关系的配置中研究电影应如何通过虚构的结构为观众呈现真实的现实。
(一)美善结合的教化功能
中国古典美学偏于伦理学和心理学,强调美善结合,此处的“善”指的是具有实用性、功利性和道德伦理的善,即认为善以合目的性为美,把理想的善看作是最高的美和真。譬如,孔子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提出“尽善尽美”理想,认为诗可以“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把诗乐与家庭伦理、国家政治联系起来。中国古人也往往将伦理的“善”和认知的“真”相提并论,认为通过加强自我道德修养,达到“善”的境界,即可获得“真”,这也是中国古人着重内修的原因,从而使艺术作品注重伦理道德的教化功能。
在中国电影批评演进过程中,重伦理教化功能和社会实践价值的“实践理性”使中国电影人始终怀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危机感,推动电影实践呼应时代脉搏。譬如,侯曜在《影戏剧本作法》(1926)中对“影戏”的探讨先从社会功能入手,强调电影的社会性和教化性;李昌鉴在《提倡平民化电影》(1931)中提出,应提倡平民化电影,起到感化作用,从而有益于社会;席耐芳在《电影罪言》(1933)中呼吁拍摄暴露性电影作品,“将现实的矛盾、不合理赤裸裸地摆在观众面前,使他们深刻感觉到社会变革的必要”;徐公美在《电影艺术论》(1938)中指出,电影应忠实传达国家和阶级意识,成为思想斗争的武器。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程度不断加深,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高涨,左翼“影评人小组”和“软性电影”论者之间的论战主要围绕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与娱乐审美功能的取舍、影片题材内容与形式技巧的权衡等问题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电影批评强调电影的政治宣传功能。新时期以来,电影学术界一定程度上转向电影本体研究,但电影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取向仍是学界与创作界关注的焦点。
(二)以真为美的认知功能
西方强调人与自然的“物我两分”“二元对立”,人为主体,自然是客体,人与自然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西方伦理主张“爱智,求真”,强调合规律性、现实性和真实性,努力揭示现实的本质、时代的特征以及未来的走向。西方古典艺术也偏于再现,强调“美真统一”,把美同对客体、自然的科学认识联系起来。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了重摹仿、再现,重美、真统一的基本原则,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说艺术“必须切近真实”,法国文学批评家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把“理性”奉为诗的准则,认为“只有真才美,只有真可爱,真应统治一切”,能否真实反映现实成为西方电影伦理判断的重要基点。
所以,西方学者认为电影的审美问题也是艺术如何表现历史和现实的问题。这一以求真为取向的媒介伦理认识基础可以追溯至1922年美国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中的“拟态环境”概念,借此说明媒介引发伦理问题的原因。李普曼认为,人们关于真实世界图景的认识很大一部分需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间接获得,媒介构造出来的符号环境构成了信息环境,即“楔入在任何环境之间的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人们对“客观真实”的认识往往基于大众传媒所呈现的“符号真实”,进而形成人们的主观认识,即经过“符号真实”的中介,已成为与“客观真实”有所不同的“主观真实”。现代社会中“虚拟环境”的比重越来越大,且主要由大众传媒所造成,李普曼因此就大众传媒可能“歪曲环境”的负面功能提出警示。宏观来看,大众传播是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即具有“促进顺从某种既定秩序或行为模式的系统性倾向。其主要效果是通过意识形态和‘意识工业’来支持既存权威的合法性”,故而通过其呈现的“拟态环境”建构社会,影响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发展。微观而言,媒介可以影响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电影作品无疑或明或暗地反映了作者的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观众在欣赏和接受过程中也有意无意地受其影响,形成自身对意义的阐释。
在西方电影理论发展早期,法国电影批评家安德烈·巴赞提倡的“纪实美学”便认为蒙太奇手段会剥夺观众的自由选择权和独立思考能力,故提出电影影像本体论、电影的心理学起源和电影的进化观,强调电影应该重视社会现实,将不干涉主义的审美宣布为“道德”,反对向观众提供已被解释和重新组合的生活,体现出独特的电影伦理态度。
1978年,美国摄影师约翰·沙科夫斯基(John Szarkowski)区分了“窗户”摄影和“镜子”摄影。按照他的观点,“窗户”摄影应当客观再现现实,不受镜头或摄影师倾向性的影响;“镜子”摄影则通过操纵光线、比例、背景乃至拍摄对象,主观地重塑世界。当反映摄影师倾向性的“镜子”摄影被冒充成再现现实的“窗户”摄影并提供给观众时,观众便受到欺骗。
21世纪以来,数字技术统领了电影制作领域。惠勒·温斯顿·迪克森便在《合成电影:21世纪的主流电影》中指出,随着传统电影被数字影像取代,图像处理获得无尽可能性,电脑特效构成的电影世界正在朝不真实方向转变,漫画电影、宇宙电影、超级英雄电影不再提供对人类实际生存状况的反思,这对电影的未来不利。
三、电影理论本体认识差异:内容之道与形式之道
教育家蔡元培曾在《中国伦理学史》中指出,我国以儒家为伦理学之大宗,“一切精神界科学悉以伦理为范围”,在美学方面同样如此,即“评定诗古文辞,恒以载道述德、眷怀君父为优点,是美学亦范围于伦理也”。可见,在中国美学的评价体系中,与伦理密切相关的“道”具有决定性意义,且在艺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强调“文以载道”,认为技术与形式是工具性载体,注重艺术作品题材内容及其体现的思想内涵。在西方,贺拉斯根据诗学理论提出了“合理”与“合式”之说,其中“合理”是合乎人情事理,合乎理性,“合式”是在表现形式上要做到尽善尽美,给人美感。但与中国古典美学偏重内容的伦理功能不同,西方更加关注艺术的形式表现,甚至将形式奉为艺术的本体。毋庸置疑,对于道与文、内容与形式的认识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艺术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的逻辑起点之一,反映在电影研究上,形成了中西电影理论与批评的不同范式。
(一)重道轻器的研究视角
中国“泛道德”的“伦理型”文化反映在艺术理论归纳上,表现为“文以载道”的伦理向度和“知行合一”的实践原则,要求理论具有实际效用,体现了社会、经验和实用三位一体的“实践理性”。自古以来,荀子要求“文以明道”,韩愈强调“文以贯道”,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认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指出“文者,贯道之器也”,都强调“文”的作用是要阐明“道”。在“道”与“文”的关系上,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清代思想家黄宗羲提出“文之美恶,视道合离”,都认为有效“载道”的“文”才是好“文”,将“文”当作“道”的载体,而“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将文学艺术创作的目的定位为宣扬儒家的纲常伦理,或是为政治教化服务,较少探讨文辞或形式自身的伦理意义。
中国电影诞生以来,学术批评界虽然也就电影本体审美潜能和哲学意义进行探讨,但更多关注的是电影题材内容的社会功能,即探寻电影内容之“道”,认为技术和形式是中立的载体,本身并无伦理取向,伦理问题产生于技术和形式如何被应用,形式上的技法主要用以辅佐内容表达,表现伦理观念,较少对媒介本身的伦理特质进行研究。追本溯源,这可以说是“文以载道”“重道轻器”观念在理论见解中一定程度的体现。
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电影界对电影艺术的形式也有所探索,《电影导演论》(孙瑜)、《编剧二十八问》(洪深)、《创造中的声片表现样式》(思白)、《“倒叙法”与“悬想”作用》(费穆)、《略谈“空气”》(费穆)、《再论演技》(郑君里)等理论性著述虽涉及了电影艺术的本质属性、本体特征、审美价值等问题,但主要以感性认识和经验总结为主,重归纳、轻演绎,重直接的感悟、轻严密的论证,强调电影形式为内容服务,侧重电影技术与形式的实践意义,即如何利于电影作品表述内容和表达伦理。譬如,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防电影”“抗战电影”走“电影救国”路线,强调抗日宣传功能,形式以浅显易懂为宜。凤吾在《论中国电影文化运动》(1933)中强调,技术越好,对于内容的宣传力量越大;形式上应明快展开,多动作、少对白,不要运用倒叙、回忆等只有知识分子或是看惯电影的人才懂的手法,就连暗示也应以看得懂为限。尘无提倡采用纪录片、拍摄短片和进行露天电影的放映,认为这些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电影深入大众的必要条件。这种对形式的相对弱化虽然与巴赞所称“语言希望被忽略是电影语言进化的必然现象”相似,但巴赞提出“电影是现实社会的渐近线”的目的是保持现实的多义性,其理论支点和论证依据是实现电影形式完整呈现现实的功能,而非保证宣传内容的单一性和易解性。
20世纪70年代末,张暖忻、李陀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重点反思了当时电影存在的弊端与面临的困境,指出我国传统伦理观念下电影观的偏颇与痼疾,点明了我国电影理论探索的某些特征与不足,并认为这将阻碍我国电影理论形成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
(二)形式主义的伦理开掘
西方伦理崇尚科学理性和逻辑思辨,构成以“纯粹理性”为特征的实证主义和形式逻辑。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开始,西方形式美学的判断一定程度上从自然存在转向了人类本身和内在精神,概念也从“数理”转向人伦,开辟了形式美学研究的新领域。20世纪以后,俄国形式主义将“形式”确立为艺术的本体性存在,结构主义形式美学也强调对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研究,西方的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研究也都与形式美学有所融合,多元发展。西方这种科学理性和形式逻辑在电影艺术理论中体现为对技术与形式自身伦理意义的探讨,即探究技术与形式本身的“道”。
我国艺术研究者一般认为伦理选择存在于技术使用者的意图,而非技术或形式本身,但西方理论界往往认为任何技术和形式都隐含价值观。法国技术哲学家雅克·埃吕尔(Acquis Ellul)明确提出,技术的核心是价值体系,不理解隐含于技术之中的价值可能会导致意外的后果。所以,西方学术界往往把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结构进行形式分析,关注电影形式自身的伦理意义,或是研究电影机制与观看主体、社会机制的关系,并基于既有的人文社科理论体系,就媒介技术及形式本身探寻电影媒介的伦理价值乃至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
譬如,苏联蒙太奇学派把蒙太奇这一技术手段作为形成隐喻、象征的媒介,使之超越传达意义的“能指”功能,成为有意义的“所指”,表达对现实的哲学理解和伦理认识。其中,“电影眼睛派”创建者吉加·维尔托夫主张在保持镜头内容真实的条件下,应运用镜头剪辑技巧发挥电影分析、概括现实的作用,将蒙太奇发展成为意识形态工具;爱森斯坦深受俄国形式主义影响,认为形式可以创造内容,并强调形式自身便具意识形态意义和党性。
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思想,认为产生“效果”的不仅是传播内容(讯息),还有媒介形式本身,即媒介变革改变了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促使其行为发生变化,并进而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变革。所以,技术本身决定了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成为一切效果的根源。美国媒介学者尼尔·波兹曼则认为媒介是“隐喻”,其强大的暗示力能够定义现实世界。他指出,媒介的隐喻力量表现在为某个时代培养出普遍的认识论。影视等电子传播媒介将电子革命和图像革命结合起来,对语言和文字产生强大攻击力,把原来的理念世界改造成为影像世界。影像要求人们诉诸情感而非理性,它让人们去感觉,而非思考,这使人们不再停留在一个主题上进行深入开掘。因此,包括电影、电视在内的电子媒介削弱了人们的理性能力,摧毁了文化的价值,造成了整个社会文化智力的下降,从而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也揭示了大众传媒与文化危机之间的关系。他提到,以电影、电视为代表的视觉媒介强调形象而非词语,诉诸戏剧化而非概念化。在他看来,视觉媒介的传播效果并非来自内容,而是形式。譬如,电影利用蒙太奇手法调节情感,通过刻意选择形象、变更视觉角度、控制镜头长度和构图等技术手段组织审美反映,追求新奇、轰动、冲击等效果,这瓦解了文化的聚合力,使文化意义更快枯竭。
可见,西方电影伦理研究有其独特的哲学视角和价值观念,跳出单纯针对电影题材内容进行文学式评析的窠臼,注重从电影的形式与机制出发探讨电影等电子媒介对理性认知、行为方式、社会控制、人类文明的影响,与我国传统美学思维中偏重内容的社会性、否定形式的自足性观念不同,更倾向于对媒介形式本身特质的开掘与研究。
四、对中国电影学派理论建构的启示
中国电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标识之一,承载民族文化基因,因此不能仅以技术水平、票房收入等物质层面的提升作为首要目标,而需在扩大产业规模的同时,担负起精神表达的历史重任,这使建立体现国家品格的中国电影学派势在必行。建设中国电影学派,需要在紧密结合我国本土经验与国际视野的基础上,着眼于我国电影创作、电影批评、电影产业以及电影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未来发展,建构独特的电影理论体系,才能为中国电影事业的持续繁荣提供智力支撑。
(一)努力发扬我国既有优势与特质
中国电影学派并非朝夕之间确立,其学术传统自中国电影出现之初便已开始点滴累积,获得国内外的认可也并非仅仅瞩望未来的创新,还需梳理提炼我国既有创作与理论成就,依据我国传统哲学观、价值观、伦理观与艺术观,发掘其中体现出来的民族特色,使“中国电影学派”从历史的尘封中逐渐显现出来,利用我国电影研究的既有资源为中国电影学派的学术建设打下扎实基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有效地开掘中华文化传统精髓,在丰富中国电影学派学术体系的基础上,努力发挥学术研究对于电影创作的指导与借鉴作用,创作承载中华民族精神、展现中国国家品格、体现中国伦理取向和价值判断的优质影片,并不断将之推向世界,打造中国电影学派这一国家电影品牌,向世界观众讲述中国故事,使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得更为广泛的传播。
(二)借鉴科学理性与逻辑思辨传统
我国的电影研究虽然也有近百年的悠久历史,但一直没有出现具有规模效应的电影学术流派,缺乏自己的标志性理论话语,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传统思维模式的拘囿和伦理取向的限制。蔡元培在其《中国伦理学史》中指出,中国伦理学在先秦便已极盛,与西洋学说之滥觞无异,然而自汉以后,虽思想家辈出,但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围,且所得“乃止于此”,这主要因为:一是无自然科学以为之基础;二是无论理学以为思想言论之规则;三是政治宗教学问之结合;四是无异国之学说以相比较,“此其所以自汉以来,历二千年,而学说之进步仅仅也”。可以说,蔡元培指出的不仅是我国伦理学的发展问题,也切中我国包括电影学在内的各学科领域理论体系建设的软肋,即缺乏西方伦理所崇尚的科学理性、逻辑思辨传统,较少运用抽象思维及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故而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很难形成系统而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范式。
总体而言,我国电影思维主要以电影的社会功能、政治意义为伦理取向和价值诉求,重“德性之智”,轻“闻见之智”,虽然在整个电影发展进程中也不乏对电影本性的研究,但大多重灵感、轻逻辑,重体验、轻思辨,重直觉、轻论证,其成果主要基于感性经验和直觉感悟,在“实践理性”思维方式主导下侧重总结电影技法的实践操作意义,且一定程度上存在重道轻器、忽视主体意识问题,较少有意识地开掘电影艺术形式本身的伦理或文化蕴含,对电影本性的研究大多通过区分电影与其他艺术形式来获得零散的感性认识,很少从理论视角对电影本体进行形式探究,从而束缚了电影理论研究的深度、广度和多元性,很少形成体系完备的理论学说和学科范畴,这也是我国未被世界以“中国电影学派”冠名的原因之一。
因此,加强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建设,需要吸收借鉴国外电影研究的逻辑思维方式和理论建构的科学方法,在充分开掘本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寻求理论创新的多元视角,开掘新的研究路径与方法,有意识地依托中华民族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原则,实现伦理与科学、功用与本体、实践理性与纯粹理性的有机统一,使内容探讨与形式研究并重,感性体悟与理性论证结合,从而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理论体系建构打下坚实基础。
(三)打破学科界限丰富电影学体系
西方伦理崇尚的科学主义和形式逻辑反映在学术研究上,往往体现为对知识纯粹性和学科独立性的追求。在电影诞生之前,西方已经建立了各种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体系,研究者往往从这些相对成熟的学科领域出发,将电影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诠释和剖析,进而构成电影本身的概念体系和学科范畴,形成了诸如电影心理学、电影符号学、电影叙事学、电影精神分析学、意识形态电影批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等西方电影理论与批评体系。诚然,西方的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局部分析、轻整体归纳的问题,从而使其理论探索有时只专注于某个部分或层次,忽略整体面貌,从而失之片面。然而,我们需要借鉴西方把20世纪以来的人文社科学术成果最大限度地运用于电影理论研究的做法,努力开拓电影理论与批评的新路径,明确电影的艺术价值和学术地位,丰富电影的学科体系。
(四)求同存异中拓展电影发展空间
任何伦理观念都是人们对世界与自身的认识和总结,虽然脱胎于不同的文化土壤与思维方式,但都是人类智慧的凝聚,且具有相通共融之处。多元文化追求中的共同价值取向可以成为求同存异、消除隔膜的良好基础。在理论建设上,我们需要充分了解西方的民族文化心理和伦理道德诉求,找到中西相近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倾向,将之应用于电影创作实践之中,这样才能加强彼此之间的心灵沟通,争取对话的权利与空间。因此,中国电影学派的建设需要采取更加开放的姿态,研究西方影人的创作思路和西方观众的审美习惯;在理论上加以总结和归纳,支持电影创作界制作出探讨人类发展的共同问题与困境、反映人类共同愿望与诉求、既能为国际观众所理解和认同、又能体现中华民族价值取向与伦理判断的优质电影作品;推动中国电影参与全球交流与对话,以此消除不同文化之间的疏离状态或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意识形态屏障,拓宽我国电影创作的国际空间,激发更加充沛的电影创新活力。
可见,中国电影学派的学术建设不仅需要深入研究电影艺术本身的内在规律,还要打破中西文化及电影与其他人文社科领域之间的界限,努力对电影进行国际性、跨学科研究,通过引入新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以及理论体系,为中国电影研究提供新的增长点,同时吸纳多元领域的学术力量,壮大中国电影学派队伍,丰富电影理论的学术维度与研究路径,努力构建独立、完整、科学、规范的中国电影理论体系,并在与国外电影研究与创作的对接过程中找到中国电影学派的独特定位,从而建构中国电影思想体系、美学体系、工业体系“三位一体”的宏伟大厦,提升中国电影在国际艺术领域的声誉与影响,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影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注释:
[1]孔子.论语·子路//诸子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2006:286.
[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7.
[3]〔英〕伯特兰·罗素.中国问题[M].秦悦译,北京:学林出版社,1996:39.
[4]老子.道德经//诸子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2006:29.
[5]〔美〕大卫·波德威尔.香港电影的秘密[M].何慧玲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238—239.
[6] 孔子.论语·阳货//诸子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2006:374.
[7]李昌鉴.提倡平民化电影[J].影戏生活,1931(1):16.
[8]席耐芳.电影罪言[J].明星,1933(1):1.
[9]徐公美.电影艺术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44.
[10]〔古希腊〕亚理斯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M].罗念生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55.
[11]周来祥.文艺美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169.
[12]〔美〕沃尔特·李普曼.公共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1.
[13]〔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崔保国、李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363.
[14][24]〔美〕菲利普·帕特森.媒介伦理学//问题与案例[M].李青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195,52—53.
[15] Wheeler Winston Dixon.Synthetic
Cinema
:Mainstream
Movies
in
the
21st
Century
.Quarterly Review of Film & Video,7 Jul 2017,pp.1-15.[16][26]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8,180.
[17]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4.
[18]马其昶.昌黎先生文集校注集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77.
[19]朱熹.朱子语类·论文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139.
[20]黄宗羲.李呆堂墓志铭[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10):401.
[21]孔颖达.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3.
[22]凤吾.论中国电影文化运动[J].明星,1933(1):1.
[23]张暖忻、李陀.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J].电影艺术,1979(3).
[25]〔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