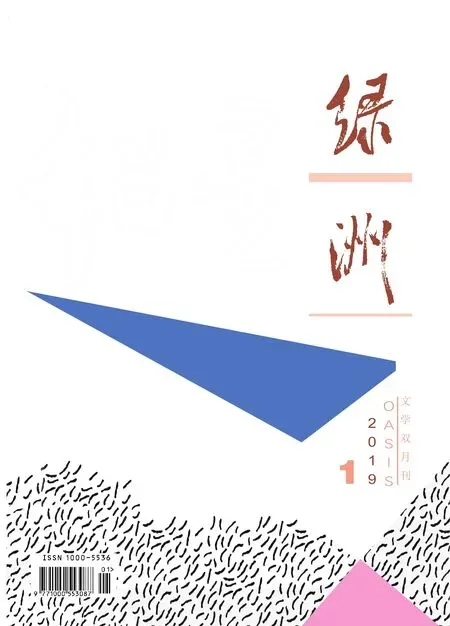天空并不遥远
2019-11-13梁积林
梁积林
扎斯停了车,拉起了手刹。他把车载播放器里的音乐调到了歌曲《鸿雁》上。他摇下车窗,又往大里开了开音量。他趴在车窗,向天空仰望,一只鹰盘旋着,突然一个俯冲,落在了对面山腰的一根石柱上。他拿上副驾驶位上的相机下了车。他又一个腿子跨上车,把播放器的音量开到了最大。随着被音乐震颤了的车身,他的身子也颤栗了一下。他倚着车边停了停,闭上眼睛,随音乐哼了几声。他觉得释放了点什么,或者还有别的。他舒了口气,下了车,但没有关车门,这样音乐传出的声音大,在整个峡谷里回荡,对他是一种陪伴,也是激越。
他打开了相机盖,向着石柱上的鹰对好了焦距。他迷眼按下快门,石柱和鹰定格在了镜框里,像一幅岩画。
《鸿雁》依然唱着,已近尾声。一股水一样的东西在他的身体里漫过了某个节点。
云层很低,一些声音像是峡谷里的风与云层摩擦出来的。要下雨吗?他看了看鹰,鹰在振翅。他吼了一声,鹰腾空而起。鹰在他的头顶盘旋了几圈后,折身翻过了东山梁去。
他又用特制相机上的望远镜对准了石柱和石柱后面的岩壁,拉近了焦距,没有发现什么,但他还是从车的后备箱里拿了本子,去石柱那儿看看。
扎斯走下路基,过了沙河,爬上了对岸的沙坡。石丛中,他鞠着身子,在每一块黑岩石上寻找着他所需要的东西。然后,他站在了石柱前,挓挲起双臂,做了个飞翔的姿势。他走到石柱侧,向石柱后的夹缝里看了一阵。他放下相机和本子,从很窄的夹缝里穿过去,到了石柱的后面。他看到了奇迹。石柱后背上是一幅很大的岩画。画面左上方有两个呈仰卧颠倒状交媾的人形,右侧是四只似乎受惊吓而奔跑的北山羊;右上方,有几个圆圈连缀在一起的纺锤体图案,仿佛一个变形了的葵花头;但他细细一琢磨,发现那个图案更像一个女人的阴部。他明白了,这是古人渴望繁衍生息的图腾。扎斯兴奋不已,这和他在龙首山中找到的岩画都不同,那些不是北山羊,就是驼队,更多的是射猎图。而这幅独具匠心且很有意味。
扎斯从夹缝里钻了出去,取了相机和本子。他把本子从夹缝里扔了进去,右手提着相机,侧身又从夹缝里钻了进去。石柱后面的空间稍大些,但也艰难,他几乎扭曲着身子,睡倒了,才拍了几张岩画的照片。他又在本子上把那幅岩画临摹了下来,在图下写道:龙首山岩画33号。他思谋了一阵,给画起名为:交媾图。他又依依不舍地端详了一会儿岩画,并用右手食指沿画迹游走了一遍。他抬头,从窄缝里看了眼云层厚重得几乎要坠下来的天空,那只鹰又掠过了头顶。他把本子扔出了夹缝,才像先前一样的姿势,提着相机,从夹缝里钻出。
他回到了车里,放好相机。音乐已响到了别处,是一首他也很喜欢的摇滚《招招手》,正唱到:你不嫌我丑,见面招招手,山高呀路远就一样地走;我不嫌你黑,黑的像个鬼,举起杯呀还就嘴对嘴,喝它个前腿碰后腿。他长得黑,长年累月跋山越岭,餐风宿露晒黑的。DD喜欢他的黑,总是在他面前唱这首歌里的这几句。DD,他想。他从副驾驶座上,拿起了一本影集。他翻开影集,DD依然向他笑着。“我不嫌你黑,”DD在他的耳边唱着,贴近他的耳朵说了句什么,只有他们能明白的一句话,让他身子抽搐了一下,心猛地刺疼。不对,是他的左小腿的腿肚上被什么扎了一下的锥疼。他下意识地抬起了左腿,同时带起了一些什么,很笨重。他佝下头,伸下右手去。他看到一条蛇吸附在他的腿上。他一把捏住了蛇的七寸,一甩手,把蛇扔出了车外。
他感到身体上突然开了一道风门,冷风直往里面灌。毒性在侵袭,不能怠慢。他卷起裤腿,小腿已红肿起来,伤处开始变的黑紫。他咬紧牙关,用双手挤压伤处,但没有挤出什么来。他知道,得用嘴吸,可自己又够不着。他挪下车,从后备箱里找出了一截搭帐篷用的绳子。他脱了裤子,用绳子狠劲地在大腿根扎了一道箍儿。
他看到后备箱里折叠好的篷布,搭帐篷休息?他想了想,但他立马摇摇头。不行,得尽快把蛇毒吸出来,或者其他治疗,不然会毁了他的腿子,他想到了截肢,或者更严重的后果,那他就再也不能到山里探秘岩画了。要是DD在,DD,DD,DD随同他进过几次山,后来退缩了。
扎斯关好后备箱,进到了车里。他拿出手机,拨号呼救,但是没有信号。自救的办法只能是前行,山里有牧民,说不定不远的某处就有一顶牧人的帐篷。他的左腿已经疼得踩不动离合器,他把全身的重量都放在了左腿上,才踩下了离合。他打着车,慢慢起了步。
播放器里的音乐又返回到了《鸿雁》,他没有关,也没有调小音量。他开着车,DD就坐在副驾驶座上,一路给他唱着《鸿雁》。DD唱完《鸿雁》唱《招招手》……
路很窄,扎斯得忍疼小心驾驶。天黑下来了,加上疼痛的分心,路有些漫漶,他开了车灯。
一股冷风,从车窗刮进了几滴雨星。他停了车,把手伸出窗外,天的确下雨了。一道闪电划过,像是谁挥着鞭子,急急赶着雨来了。紧接着,一声滚石般的雷鸣,雨像开了闸门般地,泼开了。扎斯狠狠地按了几下喇叭,停了停,他又用双手压得紧紧地按了一声长号。
他停了下来,侧耳聆听着,闭了会眼睛。
他挂上了档,继续前行。
只走了一截,他又停了下来。车在打滑。在这条只能通过一辆车那么宽的路上,稍不留意,就会翻下沟去,何况打滑,何况他的身子在一阵阵地发冷打颤。
他拉起手刹,熄了车,开了车内灯。
扎斯拿出了手机。他翻了几下,按出的是DD的号,无法接通,是他的手机依然没有信号。而那边呢?DD,他想。
这次进山,DD说有事没有送他。他进山的第三天,DD给他打电话,说她换手机了,还换了别的,然后就挂断了。他反打过去,那边的手机已关机。
“换了别的。别的什么?”扎斯嗫嚅了一句,抽了抽脸上的肌肉,把手机装进了上衣口袋里。他拿起影集,看了看DD的笑脸,“鸿雁,北归还,带上我的思念……天空有多遥远。”他的心被什么咬啮了一下,滑身哆嗦了起来。左腿的疼又一次向全身蔓延。
又一声雷鸣。一道闪电延伸到了车前头的石崖上,接通了他和天空的距离。
天空并不遥远。
他不能这样等下去,这样等,就等于等死。
扎斯点着左脚,掂量着下了车。他试着向前挪了挪,尽管疼,但能走。他吃力地走了几步,又返回了车上。他开了车前灯,可以用来照明。他看了看本子上的岩画图,又拿起影集,摸了摸DD的脸,再次下了车。
路很滑,扎斯只能扶着路内侧的岩壁才能前行。他每抬一次左脚都很吃力,满脸都是雨水混杂着汗水,几乎把眼睛都迷住了。他停了下来,一只手搬着一块凸出的石头,用另一只手抹了一把脸。眼里涩涩的,他挤了几下眼皮,才能睁开眼睛。
先一段,路面上有石子,还可将就行走。接下来,是一段光溜溜的土路,一挪脚,就向外滑。车灯已很远了,显得模模糊糊。他蹲下身子,脱了鞋。他站起身,扶着岩壁,用脚尖抠着地面,一寸一寸往前移。
但他还是跌倒了,紧接着,滑下了路面。他攥住了路边上的一墩马莲,坠在了石壁上。他双手攥紧马莲,镇定了一下自己。他长年累月在野外跋山涉水,身体里蓄有力气。他鼓住气,一努劲,做了个引体向上。他趴在了路边上。但是再往上爬时,路面上没有可抓的东西,吃不上劲,他上不去。他一只手死死握紧马莲,用另一只手在路面上摸着。他摸到了露出地面的一个石尖。他用指头在石尖四周抠着。他已挖出了一个能扳住石尖的小坑,但还不能握得太紧。
他想到随身带的腰刀,拔了出来。他用刀子几下就在石尖四周剁了一圈深坑。他把刀子狠狠地扎进地面。他左手握着刀柄,吃住劲,让右手从马莲上腾了出来,扳住了石尖。他双臂一用力,猛一纵身,上到了路面。
扎斯索性没有站起,而是直接爬着前行,反而快点。只是左腿已经麻木,吃不上力,像是身后拖着个重物,在匍匐。
雨小了。不知走了多远,早没了车灯的照耀。满山谷都是他的喘息声。
扎斯扶着石壁,坐了起来。
休息并没有给他带来好处。疲惫使他的身子一下松弛了下来,一会儿,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了。
他咬了咬嘴唇,又狠狠地咬了几下牙,像是嚼了嚼了黑夜的硬度。
他趴下身子,不是先前的屈俯前行,他已没了那么多能力,而是平展展地趴在地面上,一下一下地蠕动。
他没有意识到前面是个急弯。他摸到了几株灌木和一些草,以为出了峡谷,到了草地上。他抓住灌木,猛一挺身子,猝不及防,一头栽下了路去。
DD在喊他,推了他一把。一声惊雷。紧接着的瓢泼大雨,像一个人在他的脸上泼了一盆水,使他一个激灵。他惊慌失措,不知身在何处。他揉了揉眼睛,动着麻木了的腿。左腿动不了,他才回过神来,他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扎斯额头很疼。他摸了摸疼处,有一道伤口。他想找什么贴上。但是口袋里只有一叠卫生纸,已被水浸成了泥团。他往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液,据说能消炎,抹在了上面。
他挪了挪身子,想继续前行。但衣服上满是泥水,像是背着多重的东西,根本就动不了身。他把衣服全脱光了,只留下背心和裤头。
好在,他坐着的地方真的是一片草地,而不是沙河,那样的话,他光着身子怎么爬行。他趴了下来,向前挪了一截。他借着微弱的光气,看到了模模糊糊的山形。前面很开阔,他出峡谷了。
虽然是草地,但是是上坡,一爬一滑,也很费劲。
雨小了,只有零零星星的雨滴偶尔落在脸上。他停了下来,听着山谷的寂静,他听到了一些更显寂静的声音。他屏住了呼吸,听得更真切了,是狗叫声,忽高忽低。
他急急爬行,越往前爬,狗叫声越清晰。有节奏的吠声,鼓点一样,像是给他鼓劲、督行。
扎斯的肚皮上肯定被什么划伤了,钻心的疼,但他一努劲,就把这些小疼给忽略了。他终于爬上了坡顶。他看到了远处的一星光亮。
狗叫的更厉害了,可以说是凶猛,还有牛的喷鼻声。他只在坡顶上稍喘了口气,就向下滑开了。在半坡里,他坠着一墩灌木坐了起来。他看到一柱手电光向他照了过来,还听到了一声吆喝。他赶紧呼应了一声,但因为自身的疲乏和饥饿,声音很微弱,那边未必能听到。
他开始用屁股滑行。随着手电光的晃动,他看到一个身影向他移了过来。他看到了坡下面有一群牛,牛的眼睛像小火苗一样,扑腾着。
扎斯滑到坡底时,那个身影也离他不远了。
“谁?”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干啥的?”
“我。”扎斯拼出了所有的力气。“救命。”扎斯猛地站了起来。但他忽地又跌倒了。他的左腿麻木,一点知觉都没有,失去了支撑力。由于暴发的太猛,近乎挥霍,一下掏空了身体里所有的能量。
那人掐疼了他的人中,他的生命气息又回来了。他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咋了?”那女的手电光照在他身上,又挪开了,“咋成这样了?”
他张张眼皮,又疲惫地闭上了。
“遇到啥了?”那女人说,声音迟疑。但她马上往起里扶他。
“蛇。”他说,“被蛇咬了。”
扎斯顺着女人的搀扶站了起来。
女的从腋窝里挟住他,拉过他的左手搭在了她的肩上,用右手裹着他向帐篷走去。
那女的把他放在了地铺上,他看到他的左腿肿得像水里浸泡过的椽子。一个女孩从被窝里探过头来。“谁?阿妈?”女孩怯生生地问。
“别管,好好睡觉。”女人说。女孩向后缩了缩,但眼睛一直向他瞅着。女人抬起他的左腿,找见了伤口。
伤口在腿肚子上,在下面。女人扳着身子,让他趴在了地铺上。女人拿了一只鞋,用袖口擦了擦鞋底,在伤处猛拍了几下,他疼得直出声。
“男人!”女人语气很重地说。他感觉到了她的轻蔑。他咬住了枕头的一角,堵住了嘴。女人在用嘴吸他的伤处,他像是又被蛇咬了一下似的,抽了抽身子。
女人“噗”地吐了一口:“别动。”
“别!”他说。他想翻起身来。
女人在他的屁股上拍了一把:“别动。”
女人又连续在他的伤处吸了几次。
“时间太长了。”女人叹息着说。“得找医生。”女人说。“你一定很饿了吧。”女人把他扶着坐了起来,背后垫了一床被子。
他看清了女人的脸,虽然皮肤黑,但眉清目秀,像吉克隽逸。
女人捅了捅火炉,在上面搭了把茶壶。接着,女人又折身从墙角的木桌上拿过一只碗。女人提起茶壶,向碗里倒了些什么。
“饿坏了吧。”女人说,把碗递给了他。“先喝些凉的,压压饥。”
是奶茶。他几乎没换气,就喝完了多半碗奶茶,肚子里像空山回音,很重地响了一声。女孩“扑哧”笑出了声。
“我叫乌云。”女人说。女孩叫哈斯,乌云说。
乌云等着奶壶滚了后,给他做了几个糌粑,又倒了一碗热奶茶放在了他的旁边。在这当儿,他给乌云讲了他的工作,和他遇险的经过。乌云一直皱着眉头听着。有一阵子,扎斯看到乌云的眼里在神往什么,更像是迷惘。
“怎么?”扎斯说。他不知道他这句话的来由,他不明白要说什么。他望望乌云,又看了看眼神专注的哈斯。
“没什么。”乌云说。她随手套上了一件衣服。“你把这些都吃了。”她说,“我得去找医生。”
“这么迟了?”扎斯说,“再说,我觉得好多了。”
“不行,”乌云摇摇头,“毒还没有完全排掉。”出门时,乌云又回过头来说:“难受了难受,腿上的绳箍先不要解开。”
“阿妈?”哈斯坐了起来。
“待着。”乌云说。
一会儿,听着一阵马蹄声急速地驰过了帐篷门口。狗叫声像河水一样,一直在不停地潺潺流淌。
“那是你妈妈?”扎斯问哈斯。
哈斯点点头。
“爸爸呢?”
哈斯摇摇头。
扎斯吃完后,疲惫,使他不一会就迷糊了过去。
医生在扎斯的伤处,用一个吸附器,狠吸了几次。医生又给他打了一针,解开了绳箍。扎斯觉得轻松了许多。
医生放下了一些针剂和一个针管。“一天打上两针,把这些针都打完,应该就好了。”医生说。“这段时间不要走动太多。”医生给扎斯说,望着乌云,更像是给乌云安顿。
医生在扎斯的头上包扎了几圈绷带。“好了,我该回去了。”
医生出门时,扎斯觉得应该给医生就诊费的。“稍等。”他说。医生回过头来。可他一摸身上,几乎是裸体。“我的东西都在车上。”他说,“我好了后,去给你。”他说。“医药费。”他说。“还有,太谢谢你,你们了。”
“别管这些了。”乌云说,眼里是责怪的体慰,“好好养伤吧。”
“听乌云的,”医生说,“好好养伤。朋友,真是万幸……”医生停了下,望着乌云,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
“这,”乌云像是被什么卡了一下,咳了一声,才又流畅了。“等会,我立马就做好了,吃过早饭了再回。很快,不耽误你多少时间。”
“不了,我回去刚好赶上上班。”医生说,出帐篷门。扎斯看到天光已大亮。
送走医生,乌云返回帐篷。“我去挤奶,挤完奶,把牛放到山坡上,就回来做饭。”乌云说,提了奶桶,走了出去。哈斯已穿好了衣服,随阿妈走了。
扎斯也想挣扎着起来,可坐起身,才明白自己是裸体,怎么示人,又躺了下来,偎进了被子里。
扎斯闭上了眼睛,DD给他喂饭。他感冒了,DD一口一口地给他喂着,直到他睡着。
扎斯太累了。乌云把饭做好,才叫醒了他。
“手抓羊肉,羊汤。多吃上些,养身子。”乌云说。
看着扎斯吃开了,乌云急急地吃了些,就站起了身。
“钥匙?”乌云说,把手伸向扎斯。
“什么?”扎斯说。
“车钥匙。”
扎斯恍惚了一下说:“就在车上。”
乌云一笑。“我也是糊涂了,你光着身子来,那来钥匙。”乌云揶揄了一句。“即使不在车上也早丢路上了。”乌云揉了下鼻子说,“你吃过了,睡着,缓着。我给你往回弄车去。”
“你?”扎斯说。
“是啊。”乌云说。
扎斯还是不放心。“那条路,又窄又滑,不好开。”他怀疑地问,“你会开车?”
“原来有过一辆,后来卖了。”乌云说,眼神里有一些很抽象的东西一闪而过,像是大草坡上,一只老鹰的掠影,倏忽就不见了。“那条路我能不知道,常来常往的。”乌云说,“再说了,天早晴了。天一晴就把路面晾干了。”
扎斯想说,给我找件衣服吧,我和你一起去。一想,一个女人家,看得出来家里没有男人,哪里给他找男人衣服去。但他还是试探着说了。“有男人衣服吗?给我找件穿上。我和你一起去。”
“有。”乌云说,转过身,从一个木箱子里翻出了一套衣服,犹豫一下,很规整地递给了扎斯。“穿上吧。”乌云声音很轻地说,带有暧昧,似乎还有别的情绪。“但你不能去,去了伤着,反而累赘。”
乌云取下挂在墙上的马鞭。“哈斯,你好好陪着叔叔待着。我去去就来。”乌云搭起门帘,一股强光猛地涌进了帐篷。
吃过后,扎斯穿上了那套衣服,几乎是崭新的,也挺合身。扎斯站起身,试了几下,但不能走,左腿使不上劲。他向帐篷里各处瞅了瞅,没个可拄的东西。“哈斯,来让叔叔扶着你。”他示意哈斯走到了他的左边。
他把手搭在了小哈斯的肩上,趁了点力,向前走了几步,又扶着帐篷边,出了帐篷。天晴得万里无云。草地上,湿气蒸腾,整个河沟像是一个大蒸锅。空气中弥漫着牛粪的味道。扎斯放开帐篷边,想继续前走,但没走两步,就趔趔趄趄的,几乎跌倒。他前倾身子,扶住了扯帐篷的杆子,才把自己稳住。
哈斯很懂事地,从帐篷里搬出了两个小凳子,让扎斯坐下。她并排坐在了旁边。
“哈斯,你爸爸呢?”扎斯又想到了那个疑问。
哈斯还是摇摇头。
“你几岁了?”
“六岁。”
牛场边的狗突然很狂地叫起来。
“妈妈。”哈斯兴奋地喊了一声。
扎斯朝着哈斯出声的方向一看,一匹马从草坡上飞奔了下来。
“妈妈。”哈斯站了起来。扎斯也站了起来。
乌云在帐篷前吁住了马,跳下马,从马上抱下一堆湿衣服。
“你的。”她说,把衣服堆在了扎斯面前。“赶紧掏掏口袋里,有什么东西都掏净了,我给你洗去。”她又从怀里拿出个什么递向扎斯。“这个,是你的吧?”
扎斯接过去。是他的手表。表链断了,啥时候丢的,他都不知道。是DD给他买的。扎斯望向乌云,想说句什么感激的话。但乌云望向了别处。狗不叫了,一块洁白的云挂在对面的山尖上,一飘一飘的。
乌云从帐篷里拿出了一个脸盆,把扎斯的衣服盛在里面,去了牛场那边的河边。
“车呢?”扎斯想。但他没问。他觉得这是一种不信任。
乌云端着一脸盆洗好的衣服回到帐篷前,把衣服挂在了晾衣绳上。
“我得去趟旗上。”乌云说,“车没电了。”
扎斯醒悟过来,车灯着了一晚上,能有电吗?咋能开回来?他咋早没想到。
扎斯拿起掏在地上的手机,抡着胳膊甩了几下,飞出了好多水珠,直到手机没水了才停下来。他试着开机,按了几次开机键,都没有动静。是烧坏了?还是没电了?
应该充上电试试。扎斯在手机上比划着,问旁边的哈斯,可以充电吗?哈斯明白:“行呢,能行。阿妈的手机也经常充电。”她知道充电的地方。“帐篷里有插座。”哈斯很情愿地要接过手机。可是,还需要东西呀。扎斯想到了,充电器在车上,他做了个无奈的动作。
“没有充电器。”扎斯说。收回了手机。
哈斯第一次在陌生人面前笑了,伸了伸舌头。一只鸟落在了面前,她用手去抓,小鸟飞了起来。她一停下,小鸟又落下来,面对她“唧唧”地叫着,像是向她示威。她又追了过去,一直追到了老远。
“不要跑远了。”扎斯喊。
哈斯应了一声,蹲下了身子。
这时,他听到一只小鸟在他身后的什么地方“唧唧戛,唧唧戛”,很欢实地叫着。是刚才哈斯追了的那只吗?他磨转身子四处寻找。帐篷南面的太阳能极板上,有一只彩色的鸟儿。旁边是一个电视接收器。是它,是它高昂着头在那儿抑扬顿挫呢。就像DD在给他有模有样地唱着《鸿雁》。他注目着,鸟儿没有飞走的意思。他想叫过哈斯来看。可是先前蹲了的地方没有哈斯。四处也没有。他急了,硬挣着站起来。
“哈斯,哈斯。”他喊。
哈斯没应声,狗却叫了起来。
他站不久,左腿吃不上力,人在摇晃。他拿起凳子,前挪了几步,又坐了下来。
“哈斯,哈斯。”
哈斯却从哪儿转回来,站在了他身后。她用手蒙上了他的眼睛,“咯咯咯”地笑呢。笑完了,很快地窜到他前面。“看。”她说,“好看吗?”扎斯看到哈斯的头上插着两朵马莲花,努着嘴,做着怪像。他也笑了,说:“好看,漂亮。”看来哈斯在他这个陌生人面前终于放开了,不再拘谨。他又想起了那个问题。
“哈斯,给我说说你爸爸。你爸爸呢?去哪了?”
哈斯还是摇摇头。脸上换成了疑惑的表情,好像那个词与她没任何相干,或者说她就不懂那个词是什么意思。
“你没见过爸爸吗?哈斯。”
哈斯还是摇头。
“你妈妈也没说过爸爸?”扎斯说。
“没有。”哈斯说,摇着头,似乎更疑惑了。
“像我,”扎斯说,“像我一样的男人。爸爸。”
哈斯头一弯,思考着。然后她拧紧了眉头,又放松下来,像是一下子豁然开朗了。哈斯突然捏住扎斯的鼻子。“那你就是爸爸。”她说,取下头上的马莲花,插在了扎斯的头上。
兴许是活动得久了,扎斯觉得左腿胀疼,阳光也更强了,晒得他直淌虚汗。他有些支撑不住了。他一只手按住凳子,趁上劲,站了起来。他示意哈斯,让他扶着她去帐篷。但哈斯拽着他的手和衣角,又把他拉住坐了下来。“等等。”哈斯说,向帐篷后面跑去。一会儿,哈斯拿来一根木棍,递给了扎斯。扎斯明白了哈斯的意思,小丫头挺机灵的,得刮目相看。他接过木棍,抚了抚哈斯的头,把自己早已取下来,握在手中的马莲花插在了哈斯头上。
有拐杖方便多了。哈斯走在前面,倒行着,笑盈盈地看看扎斯一拐一拐地进了帐篷。
扎斯上了地铺,拿出了手机捣鼓着。没啥结果,他长叹了一声,放下手机。
哈斯好像很理解扎斯的那一声叹息,忙打开了电视,并把遥控器递给了扎斯。
扎斯接过后,哈斯笑了一下,向帐篷外跑了。
扎斯拿着遥控器翻了一遍,台很少,没有他想看的考古频道。内蒙古频道倒是有,但这个时段没有他想看的,是个娱乐节目。又向下翻了几个频道,他停住了。画面上是一片荒原,这引起了他的兴趣;接着,画面转到了一座山峰上,顶上是一块巨大的岩石,很圆;然后镜头拉向了一辆自行车,确切地说,是一辆非常漂亮的山地车;画面急转直下,落到了一个山体的裂缝里;镜头突然停在了一个点上:是一个人和一块石头,在裂缝的半截处。他明白了,这个他看过,是美国电影《172小时》。此刻,拉斯顿正在用一块石头,往断里砸他的手臂。他的手臂被一块石头夹在了山缝里,他想了许多办法,他坚持了很久了,绝望中,他必须以这种方式才能逃离灾难。“哐哐哐”的砸击声,像砸在扎斯的身上。
如果没有碰到乌云,他想,时间久了,他的左腿就会坏死,就会蔓延到整个身体。他咬紧了牙。他想,如果真是那样,他有没有决心弄断自己的左腿……
一阵车的轰鸣,越来越响,到了帐篷前,戛然停了。几个人下了车,嚷嚷着向帐篷门走来。扎斯往起里坐了坐身子,注视着门口。
先进来的是哈斯,跟着是两个男人,乌云在后面谦让着。
是他们帮了他的忙,扎斯知道,是他们把他的车弄回来的。两个男人进门后和他打招呼,他赶紧点头致谢。哈斯看着电视上那个致残自己的人,抖了一下身子,像是受了惊吓,急忙跑到了妈妈身边;乌云用手一拨她,她抽身到了扎斯旁,贴在了他的身上。
乌云在忙着往地中央摆桌子,然后端过了一盘早晨做下的手抓羊肉。乌云又在炉子上搭上了奶茶壶。那两个男人围着桌子坐定后,乌云又盛了一盘羊肉,放在了扎斯旁。
“吃吧,都不要客气了。”乌云说,“大中午的,都饿了。”
其中一个男人拿起一块羊肉,对着扎斯举了举,说:“吃。一起。”
乌云在桌子上摆好酒杯,用一只锡壶往酒杯里倒酒。倒完后,乌云站起身,走到扎斯旁,也给他递了一杯酒。
“给你介绍一下,扎斯。他俩是旗上汽车维修部的师傅。是他俩开车拉上电瓶,到你车那儿,才把你的车打着,开到这来的。”乌云说。
扎斯忙说:“太谢谢了!”
男人说:“不要客气。万幸,万幸。谁都会有难处。你脱险才是最应该敬的。来,互敬互敬。”一起举杯喝了。
乌云给那两个男人添上了酒,又过来给扎斯倒。扎斯把酒杯往怀里一收,说,“我有伤,不能多喝吧。”
那个男人“哈哈”一笑。“酒能消毒,多喝有好处,喝吧,兄弟。”
乌云也笑脸认同。
“喝吧,兄弟,喝上几杯了,我们马上要回旗上去。”那两个男人说。
扎斯把酒杯伸向了乌云。
“边吃边喝。”乌云说。她也端起了酒杯。“敬你们。”
哈斯已经不吃了,洗了手在听他们说话。他们不说话的时候,她拿起了扎斯的手机翻来复去地看。她像是突然想起了先前的事情,想起了给手机充电的事。
她说:“妈妈,给手机充电。”她指了指扎斯说:“爸爸的。”
乌云先是一愣:“什么爸爸。”接着,她就反应过来了,脸一红:“胡说呢。哪有爸爸。那是叔叔。”
“爸爸。”哈斯执意地说。
那两个人也明白过来,“哈哈哈”地笑个不停。
扎斯拽拽哈斯说:“哈斯,我说的爸爸是……是问你的爸爸呢,可是……”他觉得一时也解释不清,就不再说了。他转向乌云说:“我的手机充电器在车里的包里。”
乌云起身去拿。
“给,车钥匙。一个男人说。又说,“怎么忘了,把车给熄了。你顺便把车打着,让多着会儿,把电充起来。电跑光了,不充的话,过阵子又打不着了,还得我们再来。”
乌云把那两个修理工送走后,又给扎斯打了一针。扎斯让她从插座上拿过他的手机。扎斯按着开机键,手机仍旧没有反应。扎斯很沮丧地把手机扔到了一边。“看来,是彻底坏了,”他说,呆呆地坐在了那儿,看乌云收拾屋子。他突然抹了一把脸,又有了表情。
“你的。”他说,“乌云,你的。”
“什么?”
“你的手机。”扎斯说。
乌云停下了手中的活,从长袍的怀里掏出了手机,在手上掂了掂。扎斯看到乌云的手机是那种简单功能的超长待机款。“怎么?”乌云说,把手机扔在了扎斯偎着的被子上。
“用你的手机打个电话。能打出去吗?”扎斯说,拿起了手机,琢磨着。“我是说这儿有信号吗?”他说。
“可以的。”乌云说,“但得上到后面的山顶上。”她佝着身子,把桌子上的骨头往一个盘子里捡。“这里没信号,得上那儿才行。”乌云说,端着盛满骨头的盘子出了帐篷门。
“非得打吗?”乌云拿着空盘回到帐篷后,望着扎斯说。
“得打。”说这话时,扎斯没有什么深刻的语调,只是淡淡的,他怕带上过于强制的意味。但他心里是急的。
“那行。”乌云抹完了桌子,“那现在就去。”
尽管乌云没再问更多的话,好像一切都是应该的。但扎斯不那么想,他觉得这是一种为难。
“要不就算了。”他说,“腿子这样,怎么上山?”
“有事就不要推托。”乌云说。“有我呢。”乌云又说。
扎斯犹疑了一下。“也没什么要紧事。”停了下来,他又说,“就是,昨天一直在山谷里,没信号,没有打通过电话。得给单位说行踪,这是每次出来时,单位的要求。另外,家里只有阿爸一个人,我每天都得给他报个平安,不然他会担心的。”扎斯长出了一口气。
“这还不要紧?”说完,乌云连忙脱了长袍,套了一件运动衫。“走吧。”她说,过去扶扎斯。
扎斯做了个要强的动作,说:“我能行。”但乌云已从胳膊上牵起了他。她牵着扎斯一直出了门。哈斯在后面喊了一声:“爸爸。”两人回过头去,看到哈斯手里拿着那根木棍。两个人都笑了。哈斯也笑。乌云说,“这丫丫能了。”接过了木棍。很明显,她在“爸爸”那个词上有过异样的表情,想说什么,但她立马就放过了。倒是扎斯有些脸红,像先前在帐篷里时那样,不知道怎么解释,也放弃了。他拿住乌云手里的木棍。“这个挺好的。”他说,拄着木棍前走了两步,“我能行。”他说。说这话时,他的心劲在上升。
没走几步,他就觉得费劲了。走在旁边的乌云看出来了,上前,扔了扎斯手中的木棍,把肩膀顶在了他的腋窝里,几乎是掮着她,向前走去。哈斯在另一边,手里拿着捡起的木棍。
走到半山腰里,单靠右脚着地的扎斯,腿太酸了,脸上已是大汗淋淋。他都这样了,支撑他半个身子的乌云肯定也够呛。
“缓缓吧。”他说。
“这儿。”哈斯跑向前面,指着一块石头说。
乌云搀着扎斯坐在了石头上。望望山脚,又看了看山顶,似乎在测着剩下的距离。哈斯蹲在地上喘了几口气,起身去捉一只“吱吱”响的蚂蚱。
“扎斯。”乌云说了一句,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停了下来。
扎斯等着,望着乌云。他低下了头,又抬起头来。“乌云,你怎么知道我叫扎斯。我记得我一直没给你说过我的名字。”他说。
乌云身子颤了一下。是颤了一下,扎斯看到了那个变化。乌云捋了一下头发,没说什么,带着一种神往的表情看向了远处。
一只旱獭停在了他们前面,抬起前腿,“呱呱呱”地叫了几声窜上了山顶。
“走吧。”乌云说,转过身,拽住扎斯的双臂,把他背了起来。
“这咋行?”扎斯挣扎着说。
“行呢——”乌云说,往上掂了掂扎斯。“这样快些。”她说。她换了手,抓紧了扎斯的双腿。扎斯不能乱动了,不然让乌云更吃力,他双手抱在了乌云的脖子上,很轻地。但一会儿,他不得不用上点力气。
中途,扎斯要乌云把他放下来,他自己再走会儿。乌云没停,她一口气把他背上了山顶。
三个人并排坐在了山顶。哈斯把那根棍子递到了扎斯手里。
“这代价也太大了,打一个电话。”扎斯沉闷了一阵说,“不打了。”他有些气恼。
乌云像是没有听明白,直愣愣地望着扎斯。
“这算什么?”她说。她也气恼了。她把手机塞到了扎斯的手里。“打。”她狠劲地说。
扎斯看了眼乌云。她的脸上有一种不可违拗的东西。扎斯按上了一个电话号码,但不通,什么反应都没有。他摇了摇头。“不通。”他说。他先按上的是阿爸的号码。
乌云说:“不急,这个地方信号也不太强,时有时无。你多打几下兴许就通了。会有那么一次的。”她站了起来,看着扎斯按上了重拨。
但还是没有反应。扎斯连按了几次都一样,没一丝动静。“不行。”他说。
“我试试。”乌云躬下身,接过了手机。“得走着试,不定哪个点上就通了。”她说。她重拨上号码,来回在山顶上走着。哈斯也站了起来,跟在妈妈后面来来回回地走。乌云反复拨着那个号。一直向北,走到山沿上时,手机通了。但她能听到那边说话,那边却听不到她说话,她使劲说着,那边却总是说你说话呀。她赶紧挂断,又重新打过去,又不通了。其间,那边往回拨过来,通了一次,乌云慌忙接上。那边“喂”了一声,她也“喂”了一声。“你是DD呀。”那边说。她说什么,犹疑了一下,她刚说,“我是……”她喊道,“扎斯,通了。”手机“吱吱”地响起了怪声,然后就断了。再按,就一直不通了。扎斯已拄着棍子站在了她旁边。
乌云看着他,无奈地耸耸肩,发愁地皱了下鼻子。“这个地方有时信号好,有时干脆就没有,这个,说不来。”她说,把手机给了扎斯,让他再打。她看着扎斯打过了几次依然不通。她停了停,像是在思索。她说,“那个山尖上倒是信号非常好,我打过几次都通,清晰的很。可是,”她指了指北面的一个山顶,“远着呢,走上去,得一个多小时。”她停下来,像是在决断,她接上说,“要不我开上车,拉你到旗上打去。”
“那怎么行。”扎斯连忙说,否定地摆了摆手。“就这够折腾你了。”他说,“我明天一早就出山。”
“那可不行,你得把伤养好了的。”她说,“医生说那些针打完你才能好。我得听医生的。医生说,你腿没好,绝对不能让你走长路,即使坐车也不行。刚才我说的去旗上,都是不可能的。那也是我急了随口一说。”听那架式,要继续说下去,但她突然停了。她接上又兴奋地说了一句。“还有个办法。”她说。
“什么办法?”扎斯说。
“发短信。”她说。
“连电话都打不通,短信能发出去吗?”扎斯不相信地笑了笑。
“你等等。”乌云说;又对哈斯说,“哈斯,你和——”她笑了笑说,“你们在这等会,我一会就来。我用过。”
她说着向山下跑去。
哈斯喊了一声:“妈妈。”但没有回音,又转向扎斯说:“爸爸。”
扎斯无可奈何地笑笑,说,“你的爸爸。”
哈斯像学生跟着老师念生字似的说:“你的爸爸。”
这是一种无法辩驳的执拗。扎斯抚了抚哈斯的头,两个人同时笑开了。
一会儿,乌云肩上扛着件皮袄上来了。她没有停下休息,还在大口地喘气,就选了个地方,把皮袄拉展铺开。她“呼哧呼哧”地说,“你写短信,把短信写好,我们就开始发。”她一屁股坐在了皮袄上。
“写好了。”扎斯捏着手机说。“发送了。”
手机“嘟噜”了一声,显示“发送失败。”
“不对,”乌云说,“你写好了给我。”乌云站了起来。“你得给我。”她说。“你那样可不行。”她笑得不行。
扎斯把手机递给了乌云。乌云接过手机,止住了笑,按了重复发送,猛地把手机向空中扔去。三个人眼巴巴瞅着手机在空中回旋了一下,落在了皮袄上。乌云拿起来,一看,还是发送失败。她重复发送了一次,又向空中抛去,这次抛得更高。手机再次落地皮袄上时,乌云已迫不及待了。她拿起一看,一下跳了老高。“成功了。”她说。她兴奋地说:“发送成功了。”
“真的?”扎斯说。
哈斯也跟上说,“真的?”
乌云把手机给了扎斯。“你看。”她说。“还有给谁发的,你写上。”
“你太神了。”扎斯说,“怎么想出这么个办法?”他说,又写好了下一个。
乌云照旧扔了几次,把另一个短信也发成功了。
扎斯看着手机。
他拿着手机鼓捣了好一会儿,才迟疑地说:“还有一个,不知道发不发。”
“发呀,怎么不发?”乌云说,“有需要发的就发,不要让人家为你着急。”
其实他早写好了短信,只是在那儿纠结着。他把手机给了乌云。乌云只掷了一次,就发送成功了。
乌云坐在了皮袄上。扎斯和哈斯也跟着坐了下来。
“等着收回信。”乌云说。
“不收了。”扎斯说。
“他们回吗?”乌云问。
“收到的话,肯定会回。”扎斯说。
“那就收呀,怎么不收?”乌云说,“收到了你心里也踏实。”她说,“稍等会。”
乌云站起身,向空中抛了几次手机。她把手机给了扎斯。
“都收到了。”她说。“手机响了三次短信音,收到了三个短信。你发出的三个短信都回信了。”她说,“你看。”
扎斯前两个是发给阿爸和一个同事的,后一个是发给DD的。他打开收到的回信一看,一个是阿爸的,一个是同事的,另一个是天气预报。
“下山吧。”乌云说,挥了一下,“得揽牛去了。”
扎斯向乌云笑了笑,也许是自己苦笑了一下。“下山。”他说。他看到夕阳像一块烧红的铁,钻进了云里。
四天过去了,扎斯已经能不拄“拐杖”行走了。其间的几天里,他们每天下午上到山顶上发一次短信。
第五天早晨,乌云挤过牛奶,把牛群吆到山坳。回帐篷做上饭吃过,乌云忙出忙进忙完后,给哈斯换上了崭新的衣服,也让扎斯换上了自己的那套行装。这几天,扎斯一直穿着乌云给他的那套男人的衣服。乌云把那套男人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进了木箱里。她也换上了一件新长袍。
乌云又包好一包酥油和一包牛肉干,装进了一个袋子里,又把袋子装进了一个背包里。乌云出了帐篷,把背包放进了车里,打着车,返身进了帐篷。
“走,上旗上去。”她说。
“有事吗?”扎斯问。扎斯另有打算。他犹疑了一下说:“我还想,今天可以回了。”他甩了甩自己的左腿:“你看,好好的了。”
“不行,这可不行。”乌云被这话给提醒了,光忙了准备去旗上的事,扎斯还有一天的针没打呢。“得把针打完。”她说。取了针给扎斯打了。
“给你散散心,顺便看看他们。”乌云说。
“看谁?”扎斯问,“你的父母亲?”他说,“我去不合适吧。”扎斯想到了别处,想到关键时候,哈斯叫他“爸爸”。
乌云低了头,做了个祈祷的动作。“不是,他们在几年前就相继去世了。”她说,脸上出现了另一个意思。“去看看铁彬他们。对了,就是那两个维修工。你也知道,当时你给他们付钱,他们不要。说是又没有修什么,只是帮了个忙。”她说。“给他们带了些东西。”乌云说。
“就那些。”扎斯说。
乌云点了点头。
乌云牵了一把他:“上车吧。那边去,我开车。”
“我能开。”扎斯想从乌云手里拿钥匙。
“不行,今天你还是病号。”乌云说着先上了驾驶位。
哈斯在他们说话时,早上了车,在副驾驶位上坐着。扎斯拉开车门,一看,想到后面坐去。但他看到哈斯向他伸着手,又改变了主意。他上车抱起了哈斯。哈斯往他身上紧紧一贴。“爸爸”哈斯说。车子震颤了一下,起步了。
到了旗上,把车停好后,乌云让扎斯和哈斯在停车场旁边的一排椅子上坐着,让他们稍等,她去去就来。
一会儿,乌云手里拿着一个白盒子从一个拐角处走了过来。
“给我。”乌云说,站在扎斯面前伸出手。
“什么?”扎斯说。
“你的手机呀。”扎斯看到乌云的另一只手里拿着个手机包装盒。他算是明白了。“怎么能让你——”但他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了自己的手机。“我还打算抽个空子修修去呢。”他说。
乌云已经拆开了包装盒,拿出了新手机。乌云接过了扎斯手里的手机,取出卡,安进了新手机里。“算了,不修了,用这个吧。”乌云说,递给了他。
“这?”扎斯说。
“别说了。”乌云说,“快给家里打电话吧。”她说,“老用我的,他们会把我当成谁了。”乌云说。
还真让乌云给说着了。正说着,乌云的手机响了。乌云接了起来。“是DD吗?”乌云知道是扎斯的阿爸,她“哦”了一声,赶紧挂了。她说,“是你阿爸。”他向扎斯说,“用你的手机打过去。”
扎斯给阿爸回了电话,又给单位打了一个。停了停,他按上了DD的号,但那个号永远是空号了。扎斯捏了捏手机,装进了口袋。他像摆脱什么似的向空中甩了一下手。“哈斯。”他说。他把那块旧手机递给了哈斯,让她当玩具玩去。去年他同时买了这样的两部手机,一黑一白,白的DD拿着。
扎斯看着乌云走到了车前,取出她的背包,把手机包装盒装进了包里,同时掏出了装酥油和牛肉干的袋子。
一进修理铺,乌云就喊:“师傅,师傅。”但没人应。扎斯向四面瞅着也没人。“咋没人?”乌云说,大声喊了一声,“铁彬。”听到什么地方有响动。一会儿,从一辆车底下钻出个人来。正是铁彬。“来了呀,乌云,你们。”他拍了拍身上的土,“哈斯。”他说。他转向站在不远处的扎斯说,“伤好了吗?扎斯兄弟。”
“好了,好了。”扎斯说,“非常非常感谢你们。”
“谢什么呀。”他说,抽出了一根烟给扎斯递。
扎斯摆了摆手。
“这个。”乌云掂了掂手里的袋子,“放哪?”
“什么?”铁彬说。
“没什么,你说放哪?”乌云往上提了提袋子。
“别,别放,好像送礼似的,真没劲。”铁彬说,瞪了乌云一眼。
“谁给你送礼,想得美。自家做的酥油。”乌云也还了一眼说。“拿着。”乌云直接把袋子杵到了铁彬的怀里,他不得不接。
“还是不行。”铁彬抱着袋子,换了一下手,提在了手里。“要是吃上瘾咋办?”铁彬嘻哈着说,没了刚才的严肃劲儿。
“好啊,自己来取呀。”乌云就势说。
“只怕有人不愿意。”他把目光扎在了扎斯身上。
“谁?”乌云挑了挑眼睑。“谁?”她笑着说。
铁彬又看了看扎斯,肯定是想起了那天在帐篷里的情景。他摸着哈斯的头,“这是谁呀?”他问哈斯,他指的是扎斯。
“爸爸。”哈斯很快地说。
铁彬目地性地笑着。
扎斯脸黑红黑红地敲了敲了旁边一辆车的引擎盖。“这车不错,越野性能好。”他说,像是没听见刚才铁彬的用意和哈斯说的。
“怎么就你一个人,别的人呢。”乌云趁机转了话题。
铁彬不笑了。“出外勤了。”他说。“红寺湖那段的公路上出了事故,到那修车去了。”铁彬说,又说,“进办公室,我给你们泡茶喝。”
“不了,我们到别处转转去。”乌云说。
“好吧,转会儿再过来也行,下午他们来了,请你们一起吃烧烤。”铁彬说。
“再说吧。”乌云说,“看时间。”
他们先去了一个超市,给哈斯买了些零食。然后,乌云领着他们转过几个小巷子,停在了一个叫“红·其其格”的精品店门前。
原来,那家店的主人就叫红·其其格。店里没别人,一进门,乌云冲着正在串一副手链的女店主喊了一声“红,红姐”。那个女人抬头一看,就叫开了:“乌云呀,总算想起姐来了。”说着,两个人又是牵手又是拥抱的,亲热的不行,把扎斯和孩子都忘在一边了。
扎斯看到她们兴奋的样子,脸上也溢出了莫名的微笑。他想说什么,动了动嘴唇,但收回了原想的调侃。他不想打扰她们的那股诉说劲儿。他牵着哈斯的手,坐在了柜台外的一个圆凳上,透过玻璃看那些五光十色的手链和挂件,并一一指给哈斯看。
“这个,像个蝴蝶。”哈斯指着一个挂件说。
这时,红像是才注意到他们。
“哈斯呀。”过来抱起了哈斯,“几天没见长这么大了。哈斯真好。”她说,又对乌云说,“怕是一个多月没见了,上次还是旗庆的时候,你们来的。”
“就是。”乌云说,“一个多月了。”
“自己瞅,瞅上哪个,阿姨送给你。”红说。“这个吗?”红指着那个蝴蝶挂件说。
红把哈斯放在了扎斯的腿上,取了那个挂件,要给哈斯戴,让乌云挡住了。“不用,不用,不能太惯孩子,再这样,我可就不来看你这个姐姐了。”乌云说,“上次给的,都还没正经戴过,一直在她的小包里放着。孩子还小,大了你咋给了给去。你就是置嫁妆我也乐意。”乌云说,笑了起来,她被自己说的话给惹笑了。
“那还用说。”红说,“早就说好的,哈斯是我的孩子,那嫁妆肯定得我给置办。”说着,红愣怔了一下。“这位是?”她说,望着扎斯,又望向乌云。
“忘了给你介绍,过路的。”乌云说。“找岩画的,受伤了,在我们那住了几天。”乌云说,觉得没说明白,又说,“养伤呢。”
红拍了一把乌云。“你就胡诌吧。”红说。
乌云有些急了。“真的,咋能哄姐姐。”乌云说,“可不能胡说,让人家听了多不好意思。还以为——”乌云说,觑了一眼扎斯。
红没有让乌云说完,就截住了。“好了,好了,不胡说了。”
乌云忙打岔儿:“姐姐最近生意好吧。”
红从里间屋子里拿出三瓶饮料,一一打开,让他们喝。但她又接上说:“说真的,乌云,你不打算再找吗?”压低了声音,“上次见的那个,怎么样?我给你介绍的。就是左旗的那个巴特尔。”
“咋又转到这个话上了。”乌云红着脸说,像是恼了。
“好,好,好,不说这个了。”红说。
停了一会儿,她们又说起了别的。
扎斯趴在柜台上看着,一直听着她们说的话。几次,他都想说,但他没说。那些话牵扯到了他,他怕添进去更乱了。他把注意力转向了柜台里饰品,一件一件地打量。
“爸爸。”哈斯突然指着靠墙的货架上的一个玩具,拽了拽扎斯的胳膊。“小牛。”哈斯说。
红的耳尖,猛地就笑开了。“你看这人。哈斯都叫上了还装。叫的啥,你听见了吧?还瞒你红姐。”
“哪里?”乌云忙解释,但又觉得解释不清,只好作罢。“孩子那是胡叫呢。”
这时,进来了一个买货的,趁机,乌云说还到别处转转,告辞出来。
出了店,乌云并没有显出生气,抱起哈斯说,“这丫头,你咋总是胡叫?”望了望扎斯。但哈斯没改她的认定,又叫了声:“爸爸。”
扎斯接过了哈斯,抱在了怀里。“没事,孩子嘛,咋叫了叫吧,只要她高兴。回吧,乌云。”
“还早呢,要不我们找个饭馆,吃了再回。”乌云说。乌云又说,“找个火锅店吃去,哈斯最爱吃火锅了。”
扎斯想了想,拿定了一个主意。他说,“去超市,把菜和料买上,回去了我们自己做上吃,我做。几天了都是你伺候着,让你们也尝尝我的手艺。不比火锅店里的差。”
“你?”乌云说,“你行吗?”乌云好奇地说。
“没问题。”扎斯说。接着用做广告的口气说:“保管你吃了还想吃。”
他们在附近一家超市买好了东西,提着去停车场。
把东西放到车上后,扎斯上了车,又要下车。
“你们在车上稍等会儿。我有个小事。”他说。
“你有什么事?”乌云说,“这个地方你又不认识人。”
“刚才路过看到一把腰刀挺好,我想买上。”扎斯说。
“你有腰刀呀。丢在草里,我给你找到了。”乌云说,“你以为没有找见?”她跳下车,从后备箱里拿了出来。
“这个?”扎斯看着刀,眼里有异样的东西,感激,或者什么。但他停了停说,“这把旧了,我想买把新的。”
“那我和你去。”乌云说。
“哈斯一个人咋行。你陪着她。孩子溜了一天够累的了,不能再跟上去。你陪着他休息一会儿。”扎斯从后备箱背上背包走了。
扎斯不到半小时就来了。
“这把刀还真不错。”乌云看了看,递回给了扎斯,打着了车。
半路上,铁彬打来电话。乌云说他们已经回了。
扎斯忙着做火锅。哈斯在地铺上入迷地玩着一只小牛的玩具。
乌云把牛吆到圈摊后,回到了帐篷,天已黑透了。没有月亮,只有狗叫声,在远处,一下一下地闪烁。
乌云看到哈斯手里的东西,问是哪来的。哈斯头都没抬,说:“爸爸。”
“你——”乌云看了一眼扎斯,没再说什么。她洗了手,往地桌上摆起碗盏。
“我知道孩子喜欢那个。”扎斯悄悄说。
“你就娇惯吧。”乌云说。
扎斯没有接茬口。扎斯说,“开饭了。哈斯,过来吃火锅了。”
哈斯抱着小牛玩具,吃饭时,也不放下。连妈妈往过里接,她都不给。她是抱着那只玩具小牛睡着的。
吃过收拾停当后,乌云没有把地桌搬走。她拿过了两个酒杯和一锡壶酒。她倒好了酒,给坐在桌子对面的扎斯递了一杯,自己也端了一杯。
“你明天就要走了。”她说,碰了碰扎斯的酒杯,一饮而尽。
他接过酒壶,又斟满了个两只杯子。
“是啊,”他说,“如果不是遇见你——”他说。他没有碰杯,一口喝干了自己的,看着乌云。
“别说那个。”乌云说,也干了自己的。“说说你。”她说。
“我,”他说,“我有什么好说的,不就在这儿嘛。”
乌云动了动身子。“DD是谁?”她说。她说,“你阿爸在电话里说的。”
“这个,还是不说了吧。”扎斯像是在挣脱什么撕扯,往上挺了挺身子。
乌云不再追问。但扎斯却说了起来。
“一个过往。”他说,“她也是我们肃南人,我是在QQ上认识她的。她叫当然,她的网名是DD。她主动加的我。她说她知道我是搞岩画的,他喜欢我长在野外的生活。后来,我们就见面了。我进山找岩画,她每次都陪着。两个人方便了许多。后来,她突然不跟我进山了,她说太累,她还要在家里干些别的。对了,她是写网络小说的。但不是那样。”他端起酒杯,呷了一口,又猛地喝尽,长出了一口气。“不是那样,”他说,“后来,我发现她和一个文化传媒公司的老板来往密切。但我没有干涉,我觉得她有她的生活,我得尊重她的生活。起先,她也坦诚,那个老板给她买的镯子,她戴在手上,也给我说。那个老板知道她喜欢看书,就投其所好,拼命给她买书,她也拿给我看。她常到我们家去,她和我的阿爸也熟。我都三十几了,阿爸催促我们结婚,她也同意,把日子定在了今年十一。后来,阿爸再催,她总是敷衍。再后来,她很少去我们家了,就连我从山里回去,她也推托有事,不和我见面,最多闪个面就走了。我忍着,装做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一直等着她的回归。”他不说了。
他一个不抽烟的人,却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盒。他抽出一支点着,又给乌云递了一支。乌云摆摆手,但马上又接了过去。她让扎斯给她点上,吸了一口。她说,“后来呢?”
“后来,”他说,“就这次了。我刚进山时,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换了手机,是别人给买的,还换了别的。然后,她的那个手机号就不通了。她的手机和我的,是我同时买的两个,一白一黑,她拿白的,我拿黑的,号都是连着的。”扎斯又接上了一支烟。“可是,”他自嘲了一下,“没有可是了。”他说,“后来的,你都知道。”
“也许……”乌云说。
扎斯轻轻摇摇头。
乌云站起来,走出了帐篷。扎斯看着乌云走出帐篷,又走了进来。他看到有一种东西在她的身体里突然强烈起来。
“你真的认不出我来了吗?扎斯?”她说。“扎斯。”她说。
扎斯愣怔着,看乌云脸上的表情。
“我是其其格,乌云·其其格。”乌云说,“那时,你们不叫我乌云,大家都叫我其其格,叫我格格。”她坐了下来,喝了一口酒,又平静了下来。
“格格,你是格格。”扎斯在记忆深处搜寻着,又盯着乌云的脸看。“格格。”他说。
乌云又站了起来。她在那个盛衣服的木箱里,翻着什么。她找到了。她拿出一个很厚的本子,放在了桌上。
扎斯刚要拿起,乌云把手按在了上面。“先别。”她说,“等说完了再看。”她看着扎斯。“记得蒙合吗?布仁蒙合?”她说。
“记得,怎么能不记得?”扎斯说,“我们是大学同学。我们挺要好的。”扎斯停了停,像在踅摸什么,眼睛一闪一闪的。“可是,他大学毕业后,考上了公务员。我们通过几次电话。后来,他的手机换号了,或者怎么,反正打不通了,就再没联系。也许他给我打过电话,但不会通的,因为,我也换号了,单位统一换的。”
“是的,”乌云说,“我知道你们挺要好的。还记得吗?”乌云说。
“啥?”扎斯说。
“你们上大学时,有次野外实习,到我们这儿来,一班同学分散在各个牧区。你们几个就住在我们家里。”乌云说,“那时,我阿爸阿妈都还健在。你们是四个人:扎斯、蒙合、达隆还有辛巴。”
扎斯重重地点着头。“对,格格,就是那个人人喜欢的格格。”扎斯在乌云的脸上找到了过去的那个格格。他笑了:“没变,就是黑多了。”
乌云也笑。“你不是也从一个白面书生变成了一个又黑又壮的黑熊。”说完了又觉得不贴切。“不对,这像是在损人。应该是……”她屏住声息;她在想个好词。
“像啥都行,别纠正了。”扎斯也笑。
但乌云不笑了。“只要你不生气就行,反正我也想不出个更好的说法。”乌云说。她严肃了起来,或者神往。
“你们在我家待了有半个月,对吧?”乌云说。
扎斯说:“是半个月。白天我们出去勘察,晚上就在你们家住。你们家给我们四人单独扎了顶帐篷。可是,我们总是在你们帐篷里待得很迟了,才回去睡。听你阿爸讲了许多东西,还喝酒。记得你阿爸还让我们把离的近的同学招集来,给我们开了一次篝火晚会。那次,差不多都醉了。”
“你记得很清呀。”乌云被触动了,她说,“就是那次,”她停住了。“就是那次,布仁偷偷亲了我。”她接上说。“这个布仁。”像是布仁就在旁边,她嗔了他一下。
“这小子够贼的呀。”扎斯说,“我们可没发现,他也从来没说过。”
“问题在后面。”乌云说。
“怎么?”扎斯很吃惊,他怀疑到了别处,比如他让她怀上了孩子。他想到了哈斯,可是,不对,显然时间和哈斯的年龄相差很大。“那么?”他说。
“你们回校后,没几天,他就又偷偷来了一次。”乌云说。
“这,他可一点都没透露过。”扎斯说。
“那天阿爸阿妈都不在,去旗上购物去了。我正在看他走时给我留下的一本书。我初中毕业就不再上学了,受你们的启发,我想多学些东西。我在帐篷外的草地上坐着,他突然就走到了我的跟前。他抱住了我,把我都吓着了。他说他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回来告诉我,他要娶我,让我等着他。他让我向他保证,在他娶我之前不要嫁给别人。他说他爱我,除了我,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他说我要不保证的话,他就不回学校去了,留下来和我一起放牧。我答应了他,我和他跪在太阳下发了誓。”乌云说着,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扎斯点着头,又在各自的杯里倒上了酒。他端起来喝了。乌云也端了起来。她喝了一半,又把酒杯放在了桌上。
“他是左旗人。”乌云说。
“这个我知道。”扎斯说。
“但他考的是我们右旗的公务员。他毕业回来就给我说了,考到右旗的目的是离我近些。他考上了,分到了税务局。但那不是他想要的。和你一样,他喜欢的专业是勘察岩画。我鼓励他先把班上着,还有别的可能,想办法,兴许有调到博物馆什么单位的可能。就是你现在上班的那种地方。”
扎斯点着头,没有说话。他又给自己倒了点酒。
“调工作,你知道的。他这人不会去求人,更不会走动什么的。但他工作认真,领导看中了他,不久就提拔他当了副局长。”
“这小子,官运亨通呀。”扎斯咧咧嘴,“好事嘛。”
“可是,让你当,你当吗?不是你的专业。”乌云说。
“这个,”扎斯吭了吭,“这个恐怕不行。”他说。
“所以嘛,他就急了,回来和我商量。那时,我们已结婚了。他说他不干了,回来和我放骆驼,正好安心勘察岩画。他说他宁可放弃别的,也不能放弃他的专业。我们家那时有骆驼群有牛群。现在骆驼群还在,是哥哥嫂子在曼德拉山中放着。”乌云说。“另一个山,离这儿很远。”
“你们结婚后,他没想把你搬到旗上去吗?”扎斯不解地问。
“有过,但我不愿意。我喜欢放牧。”乌云说。“我当时一听,觉得还真委屈了他。我真的很疼爱他,更支持他的事业,这一点,与你们实习时,给我种下的印象有很大的关系。于是,我就说,回来就回来吧,这么大的牧场还养活不了一个你。他就打了报告,辞了工作回来了。后来,阿爸去世时,把驼群分给了哥哥,把牛群分给了我们。嫂子是曼德拉的人,说那里更适应养骆驼,就搬迁上去了那儿。”
“壮举啊。”扎斯说,把酒杯拿在手里,捏了好一会儿,猛地喝了。他明白了一切。“可是,”他说,“他人呢?”他说,“他人呢,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
乌云没有回答他。她继续接上说:
“他每天把牛吆到山坡上后,就到山里面去找岩画。他拿着个本子,在上面写写画画,到晚上,讲给我看。他还在每幅岩画后面配上了诗。”乌云说。“就这个。”乌云把本子推给了扎斯。
“我们结婚后好几年了没有孩子,后来才有了哈斯。可是,哈斯生下来不久,他就出事了。”乌云声音哽咽,停了下来。
扎斯翻着本子,好多地方都被水洇坏了。
乌云接过了扎斯手里的本子,翻到了后面。
“就是这幅。”她说。乌云指着最后一幅画说,“就是这幅岩画,让他出的事。”她说。
扎斯吃了一惊,那幅画正是他刚刚发现的“交媾图”。画得细致,配有说明文字,还配有一首小诗。他起的名字是:“图腾”。
“这幅画在一个石柱的夹缝里,他就是在研究这幅画时,天突然下起了暴雨,突然的洪水,把他堵在了夹缝里。”乌云说,“找到他时,他在那个夹缝里趴着,这个本子在怀里的衣服里紧紧裹着。”她咳了一声,捂了下嘴。“我们的圈摊原来并不在这儿,在另一个沟里。他是在这里出的事,不知道为啥,我就搬到了这里,扎了摊子。”
“哦,是这样啊。”扎斯说。他想叹息,又觉得轻浮。他闭上眼睛沉默着。
“这个,我一直没给哈斯说过,所以,”乌云又说,“哈斯并不知道爸爸是什么。从小就不知道爸爸这个概念,直到你给她说了。”
扎斯抚着本子,抚着那幅画。他想说什么,又说不出什么。但他还是说了。“这个,我能带上看吗?”里面有许多他没有发现的岩画,他要带着他复查。他说,“我会还回来的。”
“对你有用,你就用吧。”乌云说,“还不还的,对我有啥。”
扎斯一页页翻着画册,许多他没有发现的岩画,让他震惊。每一幅画都配有一首诗。每一首都配得那么精准,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一种创举。
他坐不住了。他满满地喝了一口酒,走出了帐篷。乌云也跟了出去。
“爸爸。”是哈斯。是哈斯在梦中叫了一声。
他转过了身,猛地就抱住了乌云。他说格格。他还说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