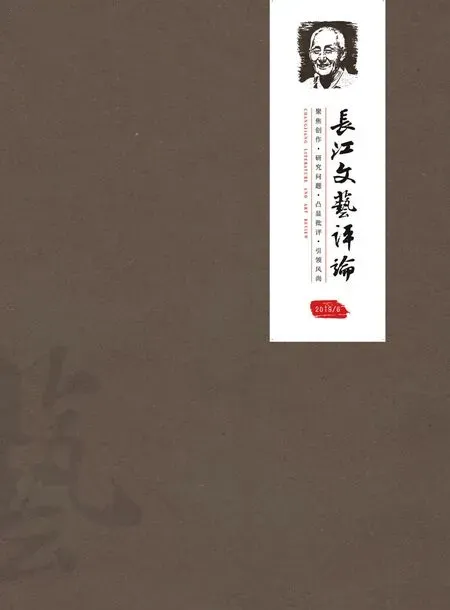传统戏曲的现代性难题及其隐喻
——关于陈彦的《主角》
2019-11-12◆徐勇
◆徐 勇
陈彦的《主角》毫无疑问是近年来现实主义的巨大收获,其语言的鲜活、形象的生动、结构的缜密、故事的曲折和内容的厚重,都令人印象深刻。作为编剧,陈彦不同于一般的作家的地方在于,他会让故事在一波三折和跌宕起伏中展开,他的小说读起来妙趣横生,特别能抓人。而这里想探讨的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与上述特征息息相关。比如说人物生动活泼,但也缺少内心活动的深度,小说几无内心活动的表现,它是通过动作表现人物的内心。比如说情节转换较快,几无静态的风景或氛围的烘托渲染,也少有对出场人物来龙去脉的介绍,甚至人物的对话也都是倾向于在行动的框架中展开,一切都在动态的情态中呈现。可以说,正是这一“动”和“静”的对照关系,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奇特风景。
一
他是从“动”的角度展开叙事。小说凸显的是动,而不是静。但这“动”却毋宁是被动。小说的主人公们都是一群“好动”的人,却也是被动的“好动”,他们甚少与时代互动或对时代深入思考,他们与时代之间构成的是一种被动的对应关系。因而时代的转折,在小说中也常常以背景的方式存在。时代只是作为草蛇灰线般,若隐若现。但事实上,时代在情节结构中却不可或缺,它既决定着主人公的命运,也决定着秦腔的命运,对于理解这部小说也是关键所在。比如说秦腔,它的每一次命运的起伏都与时代有关。忽然间老戏解放了,可以演了,其对应着的是“文革”的结束;突然之间,秦腔就没有人看了,其指向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转型;突然之间,秦腔又遍地开花重新热起来了,其反映着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所带来的传统文化的复归;再比如说剧团的工资只能发一半了,或者剧团的改制,等等,也都可以从时代的变迁中找到或直接或间接的因由。
主人公秦腔名角忆秦娥将近半个世纪的人生历程,其人生命运的变化,都与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她作为一个普通农民家的孩子,既没有家学渊源,又无背景,其之所以能考入剧团,除了她舅舅胡三元的帮助之外,主要归功于毛泽东时代对文艺宣传功能的极大推崇。某一天,忆秦娥——当时她还叫易青娥——在山上放羊,被母亲喊回家,说是县剧团敲鼓的舅舅来了,要带她去考县剧团。这还是在“文革”期间。在当时,农民进城不外乎招工、当兵或读书,读书的路径对于很多农民而言,几乎行不通,就只剩下招工和当兵。忆秦娥却走出了第四条路,即报考剧团。应该看到,这是特定时代给她提供了机会走出山外。忆秦娥同她的养女宋雨,虽然有相似的经历,都是烧火丫头出身,都很能吃苦,都具有秦腔表演的天赋。但她们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忆秦娥始终是被动的,一旦遇到困难动辄表现出动摇、逃避和退缩,而不像宋雨,她却是主动坚决要学秦腔,可谓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前者是无意,后者是有心。后者表现出历史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前者却是被时代所推动。而恰恰是这种差异,使得小说格外具有症候性。
决定忆秦娥的命运变化的,主要有几种力量。一是时代,二是天赋,三是宿命。时代的作用前面说过,再看天赋。忆秦娥的大半生都是在身边伯乐们的推动下,一步步走向秦腔的舞台,成为主角的。这些人围绕在她身边,粉墨登场,然后黯然退场。先是为了帮助她立足舞台,而后是为了秦腔艺术的复兴。他们就像行星一样围绕在她周围,这些人有舅舅胡三元、胡彩香、米兰、厨房大厨宋师、封潇潇、古存孝、周存仁、苟存忠、裘存义、县剧团朱团长、秦八娃、封导、省秦单团长、刘红兵、省秦薛团长、石怀玉、派出所乔所长等。此外还有她的陪衬,比如说楚嘉禾、周玉枝、龚丽丽等。之所以围绕忆秦娥,皆因她有着秦腔表演的某种天赋,而这种天赋,却并不是任何人都具有的,纵使勤奋和费尽心机(就像楚嘉禾那样),也仍是不开窍、全枉然。不难看出,这是一种典型的神秘天才观的体现。这就使得她身边的人(除了她舅舅胡三元)对她如众星拱月般,纵容她、惯她,并不是因为她个人的魅力大小,而是因为她所承载的复兴秦腔的伟业。但也是因为这秦腔表演需要天赋,所以一旦有新的具有天赋的人物,比如说她的养女宋雨出现,他们便又纷纷弃她而去。这就是历史的残酷,也是忆秦娥的宿命之所在,她只具有历史的符号的象征意义。即使这时她对秦腔舞台有了主动性和自觉意识,也仍然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
这种历史的宿命和残酷,是通过争夺舞台的主角而展开的。这里之所以要以忆秦娥为核心组织情节,其意在聚焦舞台主角的争夺这一点上。小说采用的是虚实相生的聚焦法,围绕忆秦娥人生际遇的变化来组织情节和安排人物,其他都是作为背景的“虚”,以作为忆秦娥的光芒的映照或陪衬。大凡与忆秦娥无关的人物,都可以舍弃;大凡需要的时候,又都可以把他们随时召回。比如说米兰,她的消失和再度出现,都是为忆秦娥服务的:她不嫁给物资局一个比她大12岁的男人,然后出国,就不会有时隔二十多年后忆秦娥率领省秦到美国百老汇演出这一情节,因而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轰动世界,是米兰在为忆秦娥和她的秦腔艺术走向世界铺路搭桥。
可见,这是围绕、聚焦忆秦娥来表现主角争夺的宿命。这里面有胡彩香和米兰的争夺,这是忆秦娥的师长辈;有忆秦娥同龚丽丽的争夺,有忆秦娥同楚嘉禾的争夺,这是忆秦娥同辈间的争夺;还有忆秦娥同养女宋雨的争夺,这是上辈同晚辈间的争夺。从这三代人之间前后相继地围绕主角的争夺,不难看出其背后的象征意义:困扰戏剧舞台的不可挣脱的宿命的象征。扩而广之,如果戏剧舞台只是人生舞台的集中呈现的话,他们之间围绕主角的争夺,其实可以看成是人生舞台和历史舞台之主角地位的争夺的象征了。这或许就是忆秦娥挣脱不了的宿命。岂止是忆秦娥,对每一个努力奋斗和不甘沉沦的人来说,难道不也是如此吗?只要他们一直奋斗和不甘,他们就难逃这一挣脱不了的宿命。
因此换一个角度看,这其实又是女性的命运之书。忆秦娥这么优秀、纯粹和美丽的女子,她一生的幸福何在?她虽然有定力,有眼光,不为金钱所惑,坚决拒绝了煤老板刘四团,而且,跟她有感情纠葛的男人都是那么的痴情且优秀,但结果呢?不是疯掉了(封潇潇),就是残废(刘红兵),或者最后自杀(石怀玉)。她的每一段感情,都很真实、真挚且真心,但都不能善终。这难道真的像古语所说红颜祸水,抑或命硬克夫?陈彦通过忆秦娥的感情经历,其实是写出了现代杰出女性的命运悲剧。她们的人生,如果像周玉枝那样,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庸庸碌碌,嫁个平凡男人,反而过上幸福安宁的家庭生活。
忆秦娥的问题可能就在于,光芒太盛和气场太强,以至于她身边的男人都成了陪衬。而她又心高气傲,固执己见,不解风情,不善(不去)经营。夫妻间的矛盾,当然无法协调。倒是胡彩香和米兰,她们的生活虽然各异,但其实家庭生活都很和谐。胡彩香曾经为了演戏,同胡三元勾搭一起,但她最终并未选择胡三元,她分得清艺术和日常生活的区别之所在。对从事艺术的人而言,其人生幸福与否与他们能不能有效地区分艺术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胡三元分不清,所以他的情感很是不顺,终其一生单身;米兰看得清楚,所以她嫁给了比她大12岁的男人,虽彼此谈不上心心相印,但却得到足够充分的关心爱护。这种感情虽然庸俗,却让她(们)足够意笃心定。相比之下,忆秦娥的每一段感情生活,都不日常、非平常,一个是天涯咫尺的割舍不断,一个是沉浸于对舞台的痴迷,一个是追求返回山野的浪漫。这样的感情都很执着和浓烈,但终究不是日常,不能落地,因而也就不能善终。
从这个角度看,陈彦之所以选择女性作为秦腔舞台的主角和小说的主人公,其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从女性与主角的关系入手更能彰显命运的主题。这不仅是女性的命运,更是人的命运的象征。一个人,太过纠缠于主角的荣光和舞台的聚光,失落的可能就是人生。从陈彦的另一部作品《装台》看出:对于主角,身在其中的人,可能有盲视。旁观者(装台者)则可能更能参透,而且这种旁观者,又不是那种毫无关系的旁观者,如观众;也不是关系过密的旁观者,如忆秦娥的亲人;而是像刁顺子(《装台》)那样的,既在其中又在其外的角色,只有这样,才可能看得更清、看得更透。
二
关于《主角》,不能不提起贾平凹的《秦腔》。这里之所以要把《秦腔》和《主角》放在一起比较,是因为两部小说都在思考秦腔在当代的境遇这一命题。虽然两部小说都可以视为现实主义的作品,但在贾平凹那里,秦腔并未以正面的形象示人,它只是背景,以隐喻和象征的形式出现。贾平凹向来擅长以实写虚,秦腔在其中是虚。相反,《主角》中,秦腔则是实。《主角》是以秦腔演员忆秦娥作为线索来写秦腔在“文革”结束后的兴衰替继。对于两部小说而言,它们的背景是相似的,都是在“文革”结束前后的背景中展开。但《主角》写的半个世纪的故事,《秦腔》则是截取新世纪初这一时段。立足点不同,两部小说的内涵截然不同。
对秦腔的当代境遇命题,两部作品有不同的表现。贾平凹的《秦腔》是在八九十年代的转折的背景下展开,《秦腔》可以看成是《主角》下部的前半部分。这是秦腔在经历了八十年代的短暂恢复和复兴后,遭遇市场经济冲击下的困境期。《秦腔》因而具有挽歌的意味,可谓“秦腔一曲动地哀”(张颐武语)。《主角》则是从近百年的时间框架下思考秦腔的兴衰成败及其可能的命运。这样一种不同,决定了两部小说的不同风格。《秦腔》虽侧重清风镇的现实日常书写,其中有各式各样的人物群像,但其主人公却是“秦腔”。他虽始终没有正面写秦腔,但秦腔却是其贯穿始终的主题和主人公。《主角》没有固定在一个时空地点,其空间是流动性的,由九岩沟到宁州县再到北山地区,而后省城西安,再就是北京、上海,乃至欧美。《主角》是把秦腔的当代困境和忆秦娥的宿命放在一个流动的空间中展开,空间的流动性并不能改变或带来秦腔的命运的根本改观,也不能带来忆秦娥宿命的破解。
虽然说《秦腔》的时空相对固定(空间是清风镇,时间是新世纪初),贾平凹对秦腔困境的思考却并不是封闭的,他是把秦腔放在传统的现代境遇的问题域中展开,他从一个特定时空的表现角度表达他对秦腔的困境的思考,他的思考因而更多是隐喻性的。而不像陈彦,陈彦的思考更多带有操作性。这里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从封子导演和薛桂生团长的身上得到体现。他们最开始都试图通过现代技巧和传统艺术的结合,以尝试完成传统戏曲的创新,但最后都告失败。陈彦以他们试错性的失败让我们明白一点:传统戏曲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程式,稍有改动,就不称其为传统戏曲了。按照秦八娃的话说就是:“戏曲的本色,说到底就是看演员的唱念做打。舞台一旦不能为演员提供这个服务,那就是本末倒置了。再好看的布景,再炫目的灯光,看上几眼,也都会不新鲜的。唯有演员的表演,通过表演传递出的精神情感与思想,能带来无尽的美感与想象空间。”所以才会有之后的忆秦娥遍访老艺人,向传统学习,肚子里终于存了几十部老戏。另一个方面,是通过外国人的接受错位得以呈现。秦腔顺利走出国门本是中国文化影响力的体现,但外国观众接受秦腔的角度与我们不同。“欧洲观众看中国戏曲,更多的还是在欣赏‘绝活’。”比如说打斗场面,而忽略了演员的表演和故事内容。这种情况下,是要迎合他们呢,还是坚持传统,小说作者显然更倾向于后者。
虽然说陈彦在前面提到的两个方面都有自己的思考,但终究没有提供更多有创见的想法,而把问题的解决交给偶然因素。比如说宁州县剧团顺利上演老戏,是因为团长黄大正被调走。比如说欧美人对秦腔本来面目而不仅仅是其“绝活”的接受,是因为财大气粗的米兰的周密安排。更多时候,他则是把困境和机遇交给了时代的转折:困境是在九十年代的市场转型和现代歌舞的涌入所带来的对秦腔的冲击。机遇则是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前后(从煤老板刘四团的兴衰可以大致判断出)。“突然一天,怎么西京城里就有了秦腔茶社。并且不是一家,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开业了好几十家。”秦腔又可以走出国门,走向港澳台了。诚然,秦腔的命运与时代的转变或递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这里,秦腔的命运并不是被决定的,而应该有自己的内在轨迹,有秦腔同人的努力,但作者却只是把这种转机放在了秦腔艺人的被动等待上,他们在这种困境中甚至停止了思考。小说中秦腔灵魂人物秦八娃在胡三元敲断别人门牙被判入狱后来到西安见忆秦娥时说过如下一段话:“新鲜刺激的东西,也该玩够了。世事就是这样,都经见一下也好,经见完了,刺激够了,回过头来会发现,自己这点玩意儿还是耐看的。”“你等着瞧吧。好好看养着你的那身唱戏功夫就是了。几个轮回过来,你可能还是最好的。”他相信,等待再等待,总会有转机的。与之相比,《秦腔》中虽看不出转机,但他把秦腔的命运凸显出来,让人不可或不能回避。贾平凹的《秦腔》虽然也把秦腔的衰败置于转折时期,但他写出了秦腔艺人或知识分子的痛苦、思考、挣扎,及其深深的无奈,具有挽歌意味。他把这种挽歌置于时代转折的背景下展开,这一挽歌是与市场经济的勃兴相伴随的,因而也就格外触动人心和让人深思。
三
诚然,《主角》把问题聚焦主角能很好地表现主人公的命运变迁,但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秦腔的当代困境的思考并不能有真正突破性的进展。在这种情境下,个人的主体性、主动性体现在哪里?秦腔艺术的创造性体现在哪里?以忆秦娥一己之力或个人的努力能否代表或决定秦腔的命运?忆秦娥的秦腔表演虽然获得巨大的成功,获得各种奖项和美誉,并得到欧美观众的认可,这看似是传统戏曲的胜利,但其蕴含的问题,比如说传统戏曲与现代技术的关系问题,传统戏曲人才的培养模式,传统戏曲的价值等等这些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它们只是被时代的转折带来秦腔命运的突变所遮蔽。
如果传统戏曲的现代出路仍旧是以其回归为前途,传统戏曲的困境及其悲剧性命运将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传统戏曲与现代商业之间的关系,也仍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作者通过忆秦娥大半生历程的叙述道出了传统戏曲的“生死疲劳”的重复性:这里面既有围绕戏曲舞台的反复争夺,也有忆秦娥对秦腔演戏之苦的厌倦、拒绝和无奈。她的大半生都是被“逼”上舞台,成为主角,但当她因为年龄而被迫退出历史舞台时,她才真正发现作为主角的荣光和诱惑之所在。在这之前,她被舞台、掌声和赞美所包围、所塑造,她身在其中而不自觉,但当她真正具有自觉意识时,却是退出舞台主角之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悖论和吊诡之处。忆秦娥的形象塑造背后,体现了历史的深深无奈:传统戏曲的异化力量、程式背后的非人格化和个人命运的盛极而衰。作者写出了其中的无奈,但把这种无奈置于个人为争主角的矛盾中展开。是主角的光芒,使得她们飞蛾扑火,前赴后继,忆秦娥也不能免俗和例外,她曾经表达过抗争,表示出不满,但她仍旧陷入了历史的怪圈。作者突出了人事,而忽略了历史和社会的因素。就忆秦娥而言,其症结在于她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个体之自我。她既没有明显的自我身份认同,也以一种宿命的方式表达她的抗拒,但这种抗拒最终仍旧落入了争夺主角的循环之中。这都因为她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人,不是现代意义的个体。这或许才是真正的悲剧之所在。
就现实而言,主角的争夺可能是传统戏曲表演中面临的难题。这确实是传统戏曲在当代面临的问题或困境:因为毕竟传统戏曲只有在现行文化体制的框架内才能发展。传统戏曲的现代困境决定了其命运,但把矛盾聚焦于主角的争夺上,则又似乎是对其他问题的回避。陈彦的《主角》试图回答秦腔的当代命运问题,但他提供的解决之道并不显得有多高妙超拔;他把问题的解决推给了外力——即时代和命运,因而只能以被动的或偶然性的方式展现。回到与贾平凹《秦腔》的比较,《主角》的全部秘密可能还在于以实写实的倾向和直面现实问题时“罕见的诚挚和诚恳”上。从《主角》和《装台》的叙事风格看,陈彦并不是一个刻意凸显文人情调或趣味的作家,他追求的是对传统戏曲及其关联下的生活的“诚挚和诚恳”的感受、观察和表现。而这也表明如下一点:传统戏曲在中国古代更多是与市民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即是说,现实生活本身的坚实、丰富和绵密构成了《主角》的底色与风格,这也意味着对这一作品能否形成切中肯綮的把握,与能不能看到这一点不无关联。
注释:
[1]但也是这种个体性的不足或“个人化的生活经验”的被超越,恰恰是“民族共同体建构”或“大家庭”伦理观念建设所必须的。参见吴义勤:《作为民族精神与美学的现实主义——论陈彦长篇小说〈主角〉》,《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1期。
[2]关于此,可参照李敬泽在谈到《装台》时说的一段话:“作为沉浸于传统戏曲和传统文化的戏剧家,陈彦也许在这个问题上并未深思,而是提起笔来,本能地就这么写下去。”《修行在人间——陈彦〈装台〉》,《西部大开发》,2016年第8期。
[3]李敬泽:《修行在人间——陈彦〈装台〉》,《西部大开发》,201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