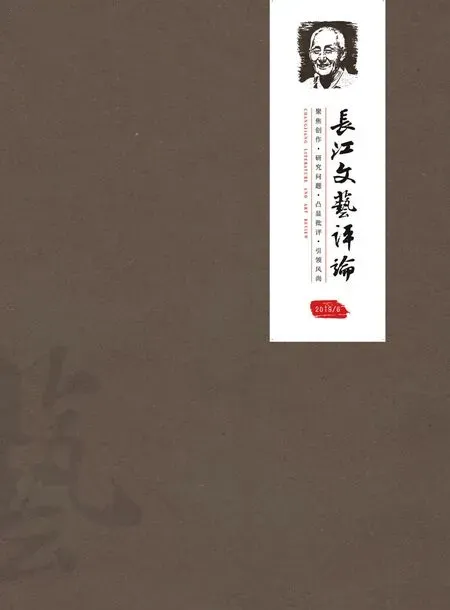新世纪湖北工人写作的思考
2019-11-12刘天琪
◆刘天琪
进入新世纪,随着经济基础、人民素质与传播媒介等要素的日趋成熟,人民群众在时代的大变革中获得了物质和精神上更多的自由。通过文学,通过个人书写,群众逐渐探索和形成了自我意识和集体意识,有了认识和想象中国、反映自己生活的诉求,群众自发性写作悄然而生。
区别于当代文学史上的“新民歌”和“三史”写作,新世纪自发兴起的群众写作热潮“是一种真正自由的文学精神,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群众写作。”如何发现与把握群众写作的内质与新变,如何在满足普通群众表达诉求这一环的基础上发掘和建构文学的社会意义,如何让其写作在商业时代“坚守初心”,这个问题变得迫切。而近年来,工人写作的发展与沉淀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鲜活的中国经验。
对“生活殖民”的反抗
与建国初期国企体制内工人及其集体写作不同,现在的工人在身份上更加丰富,多数是打工者,以“新工人”的身份存在。他们拥有更加丰富的打工经历,今天是流水线工人,明天是外卖送餐员,后天可能做起了销售,这些经历让他们更能体验城市的繁华与生活的艰辛。当他们完成了一天的奔波后,迫切期望寻找一个精神上的出口和共鸣,却发现城市打工者的情感体验在新的公共性写作中无处安放。在“底层写作”的潮流里,知识精英们写出的是同一种物质匮乏兼夹着精神麻木的底层生活;在“新都市文学”旗号下,读到的可能是大同小异的奢靡生活和一地鸡毛的家庭故事;编造相同类型的官场内幕或商场沉浮的写作者,更是不在少数。
这种对当代城市生活的简化和改写,如果用哈贝马斯的话说,是把丰富的生活世界变成了新的“生活殖民地”。“这种殖民,不是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的殖民,而是一种生活对另一种生活的殖民。……假如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去写这种奢华生活,而对另一种生活,集体保持沉默,这种写作潮流背后,其实是隐藏着暴力的——它把另一种生活变成了奢华生活的殖民地。”如果保持对城市生活单一的写作模式和视角,若干年后,读者或者研究者再来读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也许会形成一种错觉,认为这个时期的城市生活只有光鲜的写字楼,奢华的住宅跑车,而城市底层人民只有蜗居和贫苦,没有诗和远方。
而工人写作的出现,正是对这种新的生活殖民的反抗。湖北籍打工诗人郭金牛是这种反抗精神的积极践行者。郭金牛是浠水人,“60后”,自1993年到深圳龙华打工,他摆过地摊,做过建筑工、搬运工、工厂普工、仓管等。2012年他凭一首《纸上还乡》受邀参加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而名声大噪,诗歌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传播到国外。当人们认为这又是一个“打工诗人”靠文学改变命运的圆满结局时,他只是淡淡地说:“写诗和我吃饭、喝水、撒尿一样,是种需要。”与他个人对浮躁生活的反抗一致的是他的诗歌对底层叙事的多元化的探索。郭金牛说,难道打工者的困境仅仅是生存的困境吗?如果我们不钻透打工的另一个困境,也就是人的精神困境,文学就将流于祥林嫂式的“苦难和伤痛的诉说”。他将打工诗与古典元素相结合,告诉读者打工诗歌也可以有意境之美。“月亮离开了蒹葭/月亮离开了白露/月亮离开了湖北省/它走了一千多公里/唉,镜中的许白露/画中的许蒹葭/没有生下湖北人的后代。”(《虚构中的许》)“南宋以南/经罗租村/经街道,经卡点,经迷彩服/经查暂住证/经捉人”(《罗租村往事》)。郭金牛也并不回避打工诗歌书写工伤、死亡,城乡区隔与身份迷失,流水线上个体异化的一面。“我经历了90年代在深圳的打工生活,如果我作为经历者都不写,谁来写?打工者不能被遗忘,他们不是工业的数字,是埋在城市底下的血肉啊。”所以便有了成名作《纸上还乡》:“少年,某个凌晨,从一楼数到十三楼/数完就到了楼顶/……这是半年之中的第十三跳。之前,那十二个名字/微尘,刚刚落下/……”正如诗歌的名字《纸上还乡》,郭金牛带着湖北的个性、乡音、味觉在他乡沉淀,其诗歌的真实与坦然在现代主义趣味诗学泛滥的诗歌现场中是一种新奇别扭却极具分量的存在,也让以后的历史建构者们不敢随意地将这段历史乔装打扮。
如果不是一篇《我是范雨素》的网络文章,“很多外国人对中国农妇的印象停留在《红高粱》的九儿,停留在《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主人公上。我为自己所做所为,改变了外国人对中国农妇的形象而欢欣,觉得自己也能为国争光了。这一年,算是没白活一回。”范雨素在文中对自己生活的表达,对底层群体生存状态的观察,对城市社会的描述,打破了主流社会对底层视角的垄断,打破了固化的阶层叙述所形成的盲区,从而让人们看到一个自以为熟悉却很陌生的生存世界。对生活的再发现与再表达是新工人作家们有意无意的写作动机,同时也是人民群众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觉醒的显现。
乡土之梦的破碎
与沈从文、汪曾祺、贾平凹等“农裔城籍”的具有乡土情结的现当代作家一样,初入城市的打工者的写作,其观照对象自然少不了“此在”的城市与“远方”的乡村。进城后,一方面由于远离家乡的不安全感与“被抛于”城市的痛感而生出对于“此在”的批判意识;另一方面,在空间位移和距离美感的作用下,“远方”的乡村自然而然被乌托邦化。如此,不少新工人作家在城乡二元对立的情感态度的催化下,也选择了“乡村美、城市恶”的典型叙述模式。然而,随着乡村城市化的推进,城市与乡村的差异性在缩小,传统“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形象变成了一种美丽的符号只存在于想象中。因而作者笔下这种对乡村的情感依恋和夸炫,是创作者在感性状态下短暂的精神返乡和故里梦回,一旦回归理性,笔下便会出现别样的乡村图景。
从梦回到梦醒,从“商州世界”的美好到《秦腔》的乡土批判,贾平凹等被打上“精英知识分子”写作烙印的作家如此,进城务工的王十月亦如此。生于湖北石首的新工人作家王十月,初中毕业即来到广东务工,如他在不少小说中写到的打工者一样,拖着一条“蛇皮袋”,离开了薄雾鸡鸣的村庄,从此把自己抛入了命运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最初的“抚慰自身”的写作动力的驱动下,他提到自己“受沈从文先生和汪曾祺先生的文学观影响,要写一种优美而自然的生活方式”,因而有了其笔下的“湖乡纪事”系列小说,既是故乡的精神眷恋,也暗含着对传统乡土叙事的模仿与传承。“这里的人,受了水的滋养,男人俊美,女人漂亮,这是不必说的,人却都顶顶聪明,生活总有着自己的智慧。”烟村是他记忆中的净土,但那乡土只是想象中的,与现代化进程的乡土有着太多的隔膜,作家笔下刻舟求剑式的乡土叙事,不仅无法克隆出那种自耕农式的田园风光和审美情趣,甚至越唱越像一首乡土挽歌。正印证着王十月所说:“故乡在我心里已经远去。我为此有强烈的焦虑,在这焦虑感驱使下,我试图建立一个心灵的故乡。”
小说《开冲床的人》便是对此的清醒认识和隐喻,失聪的乡村少年李想,最大的梦想就是用打工开冲床的收入买一个人工耳蜗,重温梦中才能听见的童年的鸟啼和虫鸣。然而,当他戴上人工耳蜗,听力恢复的他听到的不是象征着“田园牧歌式乡土”的鸟鸣,而是代表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床的巨大轰鸣。在失聪的寂静中所维系的,少年与冲床的和谐关系被打破,巨大的噪声干扰中,冲床夺走了他的手掌。作者有意在工业文明中探寻精神返乡的方式,却发现一旦现有的和谐关系被打破,带来的是巨大的焦虑与不适。
回归理性后,以王十月为代表的新工人作家们,既无法直视乡土中人性的痼疾在现代文明的裹挟下被放大,又不能融入都市文明,夹缝中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让他们难以自洽。因此,一方面,不少新工人作家借由笔下人物传递着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寻找并正视其痛苦根源并不主要来自于物质生活的窘迫,更多来自身份歧视和物质压迫。他们跟笔下的人物一样,都渴望成为强者,渴望过上受人尊敬不被欺辱的体面生活。如王十月的小说《文身》中的少年,把纹一条龙看成强者的符号和象征,可又事与愿违地给自己招致了不少麻烦。作者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意象性的细节,具有象征意味。另一方面,新工人作家借由笔下人物转移着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并积极探索解决之道。在近年来王十月构建的文学空间中,他不再执着于城市与乡村的对立而是并立,共同成为观照人性与现代文明的场域,通过城乡双重视域的复合叙事来揭示出更为复杂的人性本质。他所反思的并不仅仅在于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渗透和替代,也无意于褒贬任何一种文明,而更注重二者的复杂联系以及彼此的影响。因而,在《米岛》等典型的返乡叙事中,王十月抛弃了淳朴、空灵而美好的想象中的乡村世界,大胆地暴露了乡土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在深刻的人性表现和历史与现实的参照中隐藏着强烈的社会批判和深层的未来忧虑。新工人作家离乡土与城市底层最近,有着专业作家无法言述的生命体验和感受,他们自发性的艺术实践以其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现实主义精神,给“主流”文坛带来了生机和活力,甚至无法替代和置换。
与时代的交织
除在外务工的新工人作家外,不少来自大型国企或合资企业的传统产业工人延续了前30年工农兵作家的传统,自发地加入群众写作的队伍中,他们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写作既是对时代、企业变化的感知与记录,也彰显了产业工人参与现实的主体意识和精神面貌。湖北作为中部地区的工业大省,拥有众多产业工人,以湖北为代表的工人写作活动,充分显现了我国产业工人的人文关怀与社会价值。
如果说新工人作家群体的兴起离不开新媒体的发掘与支持,那么产业工人的写作也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扶持和培养,这是我国产业工人写作的一大特色。新世纪以来,湖北省作家协会延续了当代工人作家培养体制,高度重视对基层作家包括农民作家、草根诗人、产业工人的扶持与引导,组织编撰出版了不少相关丛书。2016年11月出版的“湖北工人作家丛书”便是对产业工人生活和写作的全面呈现。
值得关注的是,丛书中的十个选题并非官方所设定,而是从全省生产一线的工人作家自发申报的79个创作选题中评选产生的。让工人作家自己确定选题,充分尊重工人作家的主体性和对生活的感受与体验,一方面体现了新时期党和政府对工业题材的重视和工人生活多元化的尊重,另一方面释放了工人以流水线螺丝钉的身份用文学的方式关注社会、参与现实的情绪。所以我们看到了:新时代底层夜班工人生活(殷铁梅《夜班工人》)、知青一代的爱情与时代变迁(陈智胜《与卓斯娅跳一曲华尔兹》)、湖北宜昌地址勘探往事(王国良《大峪口》)、“50后”企业家命运史(付汉勇《五十年代生》)、装卸工人在时代大潮的浮沉(梁小琳《沸腾的生命》)、国有建筑企业走出去的沧桑(李文红《坦克吊上的向日葵》)、毛纺厂女工的悲欢(陆明祥《深秋厂花开》)、大别山地区工厂工人的蜕变史(谭冰《乌桕树下》)、湖北支援新疆的采棉工人生活(柳晓春《白棉花》)、武钢第一代检修工人的奋斗(贾勇《检修班长》)等具有强烈现实感与工业气息的选题。
而在这些最终呈现的选题背后,反映的是产业工人自发性写作的精神源头:对时代巨变的感知与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砖瓦贡献之间的某种心灵联系。与新工人群体每日奔波生计,接触缤纷的社会不同,产业工人往往拿着并不富裕的固定工资,待在某条流水线的某个工位做着重复的工作,并且这些产业往往足够大,大到决定国家经济命脉(钢铁、石油、水利、铁道、矿藏、纺织),大到可容纳几代产业工人的生命长河,大到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后勤都可在产业园区完成。如此,我们看到的产业工人的创作生态:在生活环境上,产业工人的全部世界(朋友、亲人、日常生活)都与产业本身息息相关;在价值实现上,产业工人生产出的产品影响着国家和世界的发展,而在个人价值感知上,重复的工作内容不断提醒着产业工人只是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般的存在。因而,当个人的“小我”与影响社会、国家发展的“大我”产生激烈碰撞时,部分敏感的产业工人拿起了手中的笔,将碰撞产生的情绪通到写作的方式抒发出来。
在他们自发的写作中,选题上必然离不开产业与时代发展变迁等宏大主题;叙事形式上多数是展现产业的大历史风貌;角度切入上必然是以小见大,从被产业元素填满的个人生活中窥见产业与时代的风云。以此种种来倾泻个人对生产、对生活、对产业生命与国家社会生命的热爱与尊崇。因此,这种写作天生具备了旺盛的生命力、强烈的思想冲击力与朴素的艺术感染力,而作家本身也在这一创作过程中,得到了意志的磨练和思想的升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产业工人的写作从建国初的政策鼓励到新时代的自发而作,其生命的延续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也必将在与社会发展、时代交织中得到绵延。
总结特点与经验固然重要,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从对生活殖民的反抗出发至意识到乡土之梦破碎后的理性回归,再到在时代的交织中发现个人的写作价值,从郭金牛、范雨素、王十月再到“湖北工人作家丛书”的十位工人作家,以及更多的本文无法提及的工人作家、农民作家们,他们的写作本质上源于对生活的发现与思考,而不是外界附加的价值观。更应该意识到的是,无论是新工人写作还是传统产业工人写作,无论是湖北还是全国,无论作为工人还是作为农民,于写作而言,重要的也许不仅仅在于我们对生活要有所发现,也在于我们怎样以及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这种发现。
注释:
[1]於可训:《说群众写作》,《长江文艺》,2012年第8期。
[2]谢有顺:《追问诗歌的精神来历——从诗歌集〈出生地〉说起》,《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
[3]何晶:《打工诗人郭金牛,从居无定所到走上国际诗坛》,https://cul.qq.com/a/20141215/025153.htm。
[4]刘珍妮:《打工诗人郭金牛——知天命的年纪,把拳头换成了诗》,《新京报》,2017年8月4日第A12版。
[5]韩逸:《我还是范雨素》,http://www.sohu.com/a/214905940_99948639。
[6]王十月:《国家订单》,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
[7]王十月:《米岛》,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4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