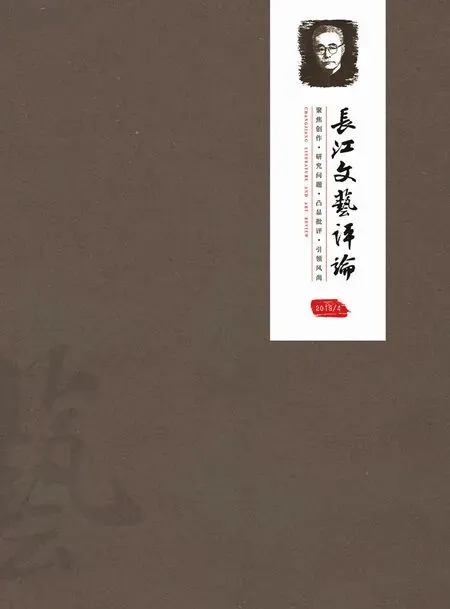身份转换的悲喜剧
——读中篇小说《飞扬的灰》
2019-11-12聂运伟
◆聂运伟
胡述武的中篇小说《飞扬的灰》所描述的生活场景、人物故事、情感样式,对于今天六十岁以下的读者,多少会有一些陌生感。
《飞扬的灰》可归为非虚构小说。在作者纪实性的叙述中,一群年轻人的花样年华在泛黄的历史氛围里,伴着已逝的青春旋律,绽放出一种欲说还休的生命追忆。当“知识青年”“招工”成为历史档案里的抽象名词时,我们的孩子是很难从教科书里看到他们父辈曾经鲜活的历史的。近些年异军突起的非虚构小说,力反惯常粉饰性历史写作,以拒绝遗忘的姿态,叩问过往岁月的奥秘,让芸芸众生突破重重有形或无形的遮蔽,获得生命真实的存在感。所以,许多非职业的热爱文学写作的普通人,暮年时,纷纷拿起笔来,钟情于纪实性的文学书写。我想,这样一种写作的动向,不必用文学理论的高头讲章,匆忙评判其文学价值的高低。这种书写的全新意义在于,它为未来更真实的历史书写、文学书写,留下了一代人人生踪迹和情感颤动的宝贵自述。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没有对生活的热爱,没有对历史的反思,没有长期用文字思考、叙述人生的能力,是很难做到的。《飞扬的灰》的作者胡述武,出生于1952年,历经知青下乡、招工进厂、机关提干、下海经商,现为独立写作人、环保从业者、高级经济师、公司董事长。与频繁变动的职业角色不同的是,他是一个永远坚持文学书写的人。
随历史波动而波动不定的人生,其中有多少期盼和无奈?以文字展现自我生命意义的写作历程,其中有多少憧憬和痛苦?我们此般人生是否有一个扬帆起航的开端?我们有那么多的身不由己,我们又万般不甘地寻寻觅觅,这一切的一切,在《飞扬的灰》中,化为一个具象的叙述起点:从下乡知青到工人——我们这代人身份转换的喜剧与悲剧。
1970年的7月,一群下乡一年多的知青,从江汉平原的乡村招工回到了故乡武汉,尽管武汉只是梦里的故乡,他们的目的地是距武汉一百多公里的黄石。一句朴实的描写:“脸上憋不住稚嫩的兴奋”,已然消退了起源于1968年的下乡热潮的“神圣”。“虽然没能回武汉,第一批招工进厂,已经让人感到无比光荣激动不已。那个夜晚,一直在为身份而焦虑的你和我——我们,踩着趸船与石阶之间的跳板,揺揺晃晃地登上码头。眼里的沿江大道,既熟悉又陌生,路灯闪闪烁烁,灰暗生涩……”
1952年出生的作者,是 1966、1967、1968 三届初高中毕业生(俗称“老三届”)里年纪最小的,1968年开始下乡时,他才十六岁。许多人还没有萌生出任何人生的梦想,就被时代的大潮裹挟到陌生的他乡,心理上无定的漂泊感也就自然成为他们人生体验浓郁的底色。
知青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但这个群体并不是一样的。上山下乡与支边支疆的不一样,北方和南方的知青体验程度、内心的感悟等也完全不一样。起码我知道,我们这批知青大多在农村只呆了一两年,生活还没有适应落定,就又在漂移挪身了。知青——漂泊在外,身无定所,希望自己归属于先进的革命的阶层,加入某个感觉好的集体,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从而获得安全感。而这些,工厂里都有。
小说中的这段议论,凝聚了作者多年后回首当年的历史认知。在庞大的知青群体里,他们算得上是幸运儿,十八岁就告别了插队经历,有了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他们没有去边疆兵团的知青们理想幻灭后的迷茫,没有去云南插队的知青们种下的“孽债”,也没有在乡村苦熬到知青大返城卖大碗茶的苦涩……坐落在黄石市的一个小小的红旗水泥厂,无论多么寒碜,多么没有现代工业的气派,却成为一群年轻人转换身份、改变命运的福地,因为“1968年12月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发表时,已经提前得到信息的军队干部子女,一个一个悄无声息地跑到军营里去了。上山下乡,实际上只是红五类中的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们也有过犹豫、不情愿,有过不甘心、想不通和无奈,但还是响应号召。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才有出路,在我们的思想中占据了主流”。所以,“在当年,未能被这个集体接纳,就会陷入惶恐孤独甚至觉得无路可走”。作者以几个真实的细节告诉读者,那种“惶恐”与“孤独”是多么令人心悸:
一个女生“背上行李在码头苦等三天,最后点名却没有了她的名字”,眼看着大家都上了船,她焦急地喊起来:“还有我呢!还有我没点名!”周围的同学也帮着喊。招工的师傅挤到她面前,低声说:“你的母亲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我们不能带你走,你的招工表退给县招办了。”这几句话音量不重,对她来说却是劈天的炸雷,让她好长时间回不过神。在一些知青点,招工“名单公布后,无论走的还是留下的,心情都很复杂。走的人,不知是高兴还是庆幸,但又顾及没有走的,说不出来的感觉”。留下的知青“一连数天没有人笑,说不上几句话,然后就是沉默。吃饭的劲头明显减少,屋里死气沉沉,也不想出工了,有的赶快给家里发电报,到处打听消息。那些日子,比农村的苦累、孤单更让人煎熬的,是内心的冲突、失落、迷茫”。
从武汉前往黄石,今天走武黄高速公路,只有一个小时的行程。可是:
当年的绿皮车很慢很慢。武汉到黄石只有100多公里,站站停靠。为了和水泥厂见面,我们耐着性情坐了四个多小时。沿途的景物在车窗外一一闪过,山丘、流水、房屋、树林,还有开阔的天空,都没有兴致去看。巴心巴肝我们只想见你,心情就像初恋时的头一场约会。
带着“初恋”的心情奔赴转变身份的工厂,尽管内心潜藏着“这一切不知道是幸运呢,还是无奈”的喟叹,但是:
在红旗厂当工人,政治上已属于“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尽管上班时穿着沾满油腻和灰尘的工作服,但是我们都有一种自豪感——国家“主人公”,端的是铁饭碗。工人阶级的质地,身份的不一样凝聚了人心。我们将工厂视为家园,虽然这个家灰尘仆仆,倔头倔脑,仍然怀揣憧憬,想充分地展示自己。这应了美国的一位心理学家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他认为,“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人的重要心理需要,只有满足了这一需要,人们才有可能“自我实现”。
作者的议论很有趣,一半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本土话语,一半是八十年代后泊来的西式话语,两者奇妙的混合无形屏蔽了内心的“无奈”,为后面充满喜剧色彩的叙述确定了一个敞亮、欢快的情感基调,带着青春的激情,尽情放大“我们”对“幸运”的认知:
我们还保留着上山下乡的思维,明明是苦难,非要罩上无比幸福的外衣,甚至以“不怕脏、不怕灰”为荣。当时的懵懂青年,多处在混沌状态,真的是不知道自己能够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但又都想施展一下拳腿。
“我们”在一个县团级的小厂里掀起了一场又一场青春的风暴:“我们”把路边的石头墙“修饰成黑板报墙”,“高三米、长二三十米”,“油漆黑亮”,“自然得到头头脑脑们的力赞”;“我们”赶上大革文化命的“新生事物”,“摇身一变成了占领上层建筑的工宣队员”;“我们”组建了桥牌队、宣传队、篮球队;“我们”办起了“抗大”小学,让厂里适龄儿童都能在家门口上学;吹拉弹唱,排演样板戏;那个年代把战争挂在嘴边,民兵训练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我们”时不时进行防空演习,“训练的内容主要是队列、刺杀、投弹、射击和三防(防空袭、防原子、防化学)等军事技术,训练以民兵排为单位,每星期一次,几乎风雨无阻”;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1971年“9·13事件”后,“我们”“单纯的心地受到刺激”,不再热衷于政治宣传,而是“土法上马”,积极投入“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的生产活动……
这里的“我们”,在作者充满温情的记述里,不管是工作场景,还是业余娱乐,似乎都是一个乐观的群体存在,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显示自身的才华,如同一棵小树,拼命地吸收一切养分,渴望成长。但在作者刻意渲染的“我们”的背后,或许有一个被遮蔽的“他者”,隐藏在“我们”中的每一个个体的“内心深处”:
当年由知青转身,以武汉伢为主的青工,表面上或许与本地的工人没有太大区别,可唯有我们自己知道,在内心深处,藏着什么样的记忆,影响什么样的人生!
这个“他者”是什么?在作者的叙述里,并无清晰的界定,但它又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不时撕裂了集体认同感的表象,把“幸运”背后的“无奈”或隐或显地透视出来。于是,我们在作者喜剧色彩的叙述里,又看到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悲剧色彩的叙述。在悲剧色彩的叙述里,有着那个时代激情的“我们”,悄然置换为不无悲情的“我”。这一置换无形解构了“我们”的群体同一性,如“有次团支部讨论我的入团问题,我本人也在场,对我提意见的是一起招进厂的武汉青工,在厂里表现特别革命的几人”。
但是我对他们的生活态度并不欣赏:汗渍、灰土和油污结成壳的工作服穿在身上,腰间系上一根绳子,有时就是一把草绳捆住,衣扣有意丢三落四,显出玩世不恭……
其实他们批评我也不冤枉:人虽然在工厂,心里边崇尚的还是小资的一套,冬天里喜欢穿一件咖啡色丝棉中式袄。那是我母亲做给我父亲的,父亲舍不得穿又给了我。
那个时候胸前别一支钢笔基本上是有文化的,我的口袋里插上笔,不是一支而是两三支,以显出自己清高。
“我”有自己的生活理想,“我”希望用知识和写作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那时候,我和许多文学青年,似乎也能够从恶劣的环境里,滋生出一种莫名的浪漫主义情结。把困苦精神化,把耐受理想化。其实,亦是为了逃出困境,抖落身上的灰。”一句话,“我”不甘心被淹没在那个伪饰的“我们”之中。
1970年代的后期,“跌宕起伏的折腾,山雨欲来的气氛,翻天覆地的动荡,影响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我们在工厂里也异常沉闷,笼罩在一种莫名的茫然中……更大的失败和幻灭感来自我们内心。面对残酷的现实,承受精神偶像被打碎和信仰遭受挫折的痛苦。我们的痛苦来自真诚,那是一种心灵遭到伤害的铭心刻骨的绝望,就像纯洁少女被骗失身。是为自己心灵被玷污而痛苦。还有什么比最神圣的信仰被欺骗更绝望的事情呢!”作者对时代记忆的准确描述,实为小说里“我们”的解体和“我”的出逃的历史背景和心理动机:“在红旗厂,头几年我们还有很重的学生气,渐渐地发现自己已经长大,没有半点技能,成了底层人,对个人和国家的未来持着悲观态度,以及对恶劣环境的不满情绪日积月累。”
“出逃”红旗水泥厂,回到故乡,成了“我们”共同的心愿。只是为了实现这个心愿,每个人都会用绝对利己的方式,动用各种社会资源和关系,甚至不惜相互伤害,把自己从那个曾经温情脉脉的“我们”中剥离出来。几年前因身份转换,从知青到工人,从农村到工厂的幸运感如今已被无奈的现实消磨殆尽,随着喜剧的落幕,悲剧也就登场了。小说中头绪纷繁的故事演绎,其实都是围绕身份转换而展开的,作者不仅用大量细节让读者感受到“我们”因身份转换而经历的悲喜剧,而且敏锐地感知到“我们”年轻时的一次身份转换,其心理上的影响竟然会陪伴“我们”的一生。在作者的笔下,读者可以看到,以不同方式离开红旗水泥厂的伙伴,在日后更宽阔的人生舞台上,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但是,“我和我们,不知道跟红旗厂之间,究竟是怎么样的关系。我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这样的记忆牵着走……”
为什么?沉浸在过往岁月中的作者没有回答。我想,这也不是今天能够回答的问题。因为作家的困惑本来就是一个时代的困惑:
在这部非虚构文字的写作中,如何谈论出走红旗厂的问题,多日来总在困扰着我的思绪。就说我自己,一方面在努力赞美宣传所在的工厂,一方面急急忙忙抖落身上的灰。现今当然好解释,当年却是曾经困惑、曾经矛盾,让我十分纠结的问题。
其实,作家的本事就是真实地再现生活中的困惑和人生的无奈,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解释,因为是有了追求和梦想,才有困惑;有了选择和行动,才有无奈。作为当年知青群体中的一员,我从作家的叙述里发现:“我们”有着现代人难以理解的复杂的过去,“我们”是历史的产物;但“我们”又有着与现代人脉息相通的明快的情感,“我们”同样渴望突破历史的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