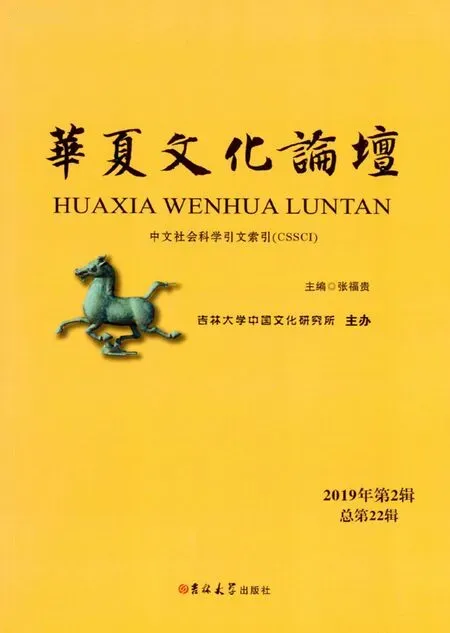明代浙东文统的发掘与地方文学书写
——以明前期浙东文派为考察中心
2019-11-12朱光明
朱光明
【内容提要】明清时期文学书写的地域意识明显增强,出现大量地方文学流派,影响着文学的发展和走向。浙东地区是明清时期文学的重要中心之一,引领着文学发展的潮流。明前期浙东文派通过发掘浙东文统,强化地域文学书写,塑造地域文学景观。该派梳理浙东文统的方式有:编纂地方性的文学总集;编纂人物记、方志或给方志作序;刊刻乡贤文集与纂修宗谱;给浙东文人别集或总集作序等。通过浙东文统的梳理,并以诗文的形式书写浙东风物,如八景书写,建构具有浙东地域特色的文学景观。同时,浙东文派的地方文学书写对江右派等其他地域文人的地方书写产生一定影响,具有不容轻忽的文化意义。
自南宋以来,浙东地区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学术与文学的重要中心之一。浙东文派成员在谈及乡邦之际,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以具有小邹鲁美誉的金华为例,无论异时吾婺文献视他郡为独盛,还是异时东南文献之懿,惟婺为最盛,以及畴昔吾婺称小邹鲁,他郡莫敢望而拟焉,均是上述心态的反映。类似的说法在浙东其他地区也有体现,如王廷用即将赴桐庐担任训导,姚夔在写给他的赠序中谈到吾严人才自昔甲于两浙,而吾桐庐亦不出他邑左。作为严州府桐庐县人,姚夔谈到家乡,深具自豪之情。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心态的背后折射出对地方文统的发掘,并催生地方文学书写的兴起。这便涉及到一个话题,即明代地方文学书写究竟如何兴起的?地方文人发掘文统有哪些方式以及对地方文学书写的影响。这些均是值得探讨的研究课题。本文以明前期浙东文派为考察中心,探讨浙东文统的发掘方式及其文学书写情况,以见明代地方文学书写兴起之一斑。
一、浙东文统的发掘与审视
浙东文士对文统高度重视,早在南宋便有专门论述文统的文章。先后师从陈耆卿、叶适的吴子良,便对汉代以来的文统进行梳理,强调“文有统绪,有气脉”,并对汉、唐、宋的文章统绪进行较为具体的论述。不但有对整个中国文统的梳理与此同时,而且对浙东文统的建构也代不乏人,不断强化地域认同感。戴良在《送胡主簿诗序》中对金华地区的学统和文统进行简单梳理,称“以道学著者则有东莱、大愚二吕氏、北山何氏、鲁斋王氏、仁山金氏,以文章家名者则有香溪范氏、所性时氏、香山喻氏……是数氏者皆相望百载之内、相去百里之间,彬彬乎郁郁乎,其鸾凤之岐阳、骅骝之冀北欤”。卢演、翁明英《方正学先生年谱》“洪武二十四年”条记载“在缑城,《大易枝辞》《文统》成”。方孝孺的《文统》虽已不存,我们也难以得知其到底探讨哪些内容,但至少可以表明他对文统是重视的,并亲自撰写文章畅谈自己的思考。谢铎在《读怀麓堂稿》中直接把浙东文派成员纳入中国古代文统中,视其为文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古之人所谓不朽者言以德立,而其功与天地并。孔孟而下,若周、程、张、朱数君子不可尚已。其次焉者则汉之司马迁、唐之韩昌黎、宋之欧阳氏、苏、曾氏,以至于我国初若刘中丞、宋承旨、方正学诸公亦皆后先相望,足以自立于不朽之地”。浙东文派成员重视对浙东文统的梳理,主要如下:
第一,编纂地方性的文学总集。谢铎、黄孔昭编纂台州的诗歌总集是一个富有代表性的例子。宋人林表民曾辑《赤城集》,不传。谢铎在京师期间重新辑录,其《书赤城集后》谈到是集亦成化乙未中录之秘阁者也。集之所载碑、铭、序、记等虽不必尽出于台之人,而实有关于台之事。是故足以备志之缺遗而不可无者。除此之外,谢铎、黄孔昭还效仿林表民而辑《赤城诗集》等。李东阳《赤城诗集序》梳理了浙东文士对本地文统的梳理,初,宋理宗时,有林咏道者,尝辑为《天台集》,今刻本不传。天顺初,国子学录张存粹辑《黄岩英气集》,而不及旁县。至是始粹然成编,予得而观之,其音多慷慨激烈而不失乎正。谢、黄二人辑《赤城诗集》有明确的塑造乡邦文学传统的意识,李东阳序言中所引用二人的对话此吾乡文献之马懿,其不可以废足以说明这一点。
在金华地区,有《金华文统》《婺贤文轨》等总集的编纂,以文学选本的形式呈现金华文人的创作情况。《金华文统》是金华知府赵鹤所编的一部金华历代文人的文章选本,从宋建炎至明成化,历时约三百年,选宗泽、梅执礼、潘良贵、郑刚中、范浚、陈亮、柳贯、吴师道、黄溍、吴莱、宋濂、苏伯衡、胡翰、戴良、吴沉、王绅、章懋等人的文章,共十三卷一百三十五篇。此书所选文章皆是“正而粹”,目的是启迪后学。此书具有明确梳理金华文统的意识,在《金华文统引》中,赵鹤纵论金华文章发展情况,认为金华之文有三变:自梁刘孝标到唐骆宾王、舒元舆,金华之文“未脱骈偶”,为一变;自宋建炎以来,范浚、吕祖谦、陈亮等人的文章,其文法密气昌,“足以追轶两汉而上”,为再变;自咸淳以来,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宋濂、王袆、苏伯衡、胡翰等人,“文之变至是极矣”,为三变。此篇序不啻为一篇简明的金华古文史,金华文统于此一目了然。
赵鹤虽非金华人,但《金华文统》的编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刺激着金华本地学者编纂文章选本的决心。金华本地文士戚雄编选的《婺贤文轨》,选取乡贤潘良贵、范浚、吕祖谦、陈亮、唐仲友、夏明诚、何恪、时少章、何基、王柏、柳贯、金履祥、许谦、吴师道、胡助、黄溍、吴莱、宋濂、王袆、苏伯衡、胡翰、戴良、冯宿、陈樵二十四人的文章,共五卷(其中冯宿、陈樵在“拾遗”卷),并有戚雄的大量评点。在序中,戚雄云:“吾观近时名公所辑《金华文统》及《正学编》援古证今,义例森列,长篇短帙,搜抉无遗,其用心非不勤也,但其去取之间时有异同,晚生末学多所未喻,他姑未暇深论”,可知,戚雄虽肯定赵鹤《金华文统》的价值,但《婺贤文轨》的编纂也有出于对《金华文统》等选本的不满,具有超越《金华文统》的潜在意图。尤其是对文章的作者而言,戚雄更能秉持一种较为客观的态度,不以人废言,选取唐仲友等与朱熹交恶之人的文章,表彰其文其学,并认为“文章吾儒公共之物,义理无穷,一得之愚,人人得效其见”,编选此书“以致景仰私淑之意”。这使得《婺贤文轨》在呈现金华文统方面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客观性。
第二,编纂人物记、方志或给方志作序。浙东不少文士有着人物传记的写作经历,或是参与过方志的编纂,通过对方志中文人传记的撰写来梳理文统。在一地的历代文士小传的书写中,夹杂着对其著述、文风,乃至师承等方面的叙述。这虽不像编文学选本那样更为直接明晰,却是浙东文派成员梳理浙东文统不容忽略的一种方式。宋濂撰写《浦阳人物记》、章懋纂修《兰溪县志》、谢铎纂修《赤城新志》等。宋濂的《浦阳人物记》,为浦阳一邑的人物作传,分为忠义、孝友、政事、文学、贞节五大类,“上而忠君、事亲、治政、讲学,下暨女妇之节,可以为世鉴者,悉按其实而列着之”。宋濂“不因喜愠论人,亦不以穷达观人,但察其贤否为何如尔”,按照此标准选择人物,并为其撰写传记。在《浦阳人物记·文学篇》中,宋濂对宋至元末的浦江文统进行梳理,对浙东文士具有示范作用。
宋濂之弟子方孝孺欲编纂宁海一邑的人物传记,并尽力去搜集相关文献材料。在写给王修德的信中,方孝孺谈到“欲搜辑邑里遗事,成一小书。上以昭扬贤士君子之潜德,下以为劝于将来,俾后生小子有所慕而为善。盖举古闾师党正之职尔,非敢妄窃褒贬之柄,而冀其传也”。方孝孺对此书的编纂体例有着深入的思考和独特见解:“忠节好友笃行之人,既各为之传,其他文学贵显者,欲析而二之,则其迹虽有隐显之殊,而其志行学术初不相远。以仕者为宦达,既非所以尊之,俱目之曰儒林,则亦有以政事称者。今不敢僣为区别,通谓之先达列传。但以时世分先后,而不以仕否为重轻。窃意如是,庶乎不失其序,而无抑扬去取之嫌。若夫治邑之大夫,其有惠政及民,如陈长官、胡汲仲,亦不可使其遗事日就亡失。今为立《良吏篇》以处之,凡名姓称于吏民之口者,皆得附见焉。”方孝孺不断向友人打听、询问宁海先贤的生平事迹材料,如在写给王修德的信中,便问他“前所问数公,不知曾得其事状否?”后来,因故未能完成此书。
数十年后,谢铎继承方孝孺之遗志,编纂《尊乡录》以记载台州的乡贤。谢铎《尊乡录序》云:“又数百年,逊志方先生始欲搜辑邑里遗事为先达传,而卒亦未就。自是以来,寝复放失,凡我后人生长其地者,殆莫知尊慕向往而其厪一世以为心者,亦几于无传矣。可胜慨哉!”成化十一年,谢铎据实以书,编成《尊乡录》四十一卷,后惧其太繁,编为节要四卷、拾遗一卷。谢铎不但在秘阁中抄录嘉定《赤城志》,而且亲自编纂《赤城新志》以存台州文献,保存乡邦文献的意识非常强烈,“吾台千数百年之文献于是乎不至于无征矣”。谢铎在修《赤城新志》之际,对于台州的历史人物取舍标准是“人物不分隐显,惟行业、文章可取者则书之。其见存者但书履历,不敢辄加褒贬以为终身未定之论”,可谓是突出了文章在人物取舍中所占的比重。
章懋为东阳杜储所编的《东阳文献录》作序,称“昔潜溪宋先生于浦阳一县之人物,既尝为之记矣,又取其人之所述作纬俗经邦、可传于后世者,类而集之,以为文艺录焉。使夫一言一行之善,皆得以垂于不朽。其所以表先哲而厉后人者至矣。浦阳文献之足征,盖潜溪之力也”。杜储此书“得唐宋以来诸君子遗文逸事,必手录之,虽片言半简之仅存者,亦所不废。凡其邑之所产,孝者、忠者、节义者、勋业者、文学者,悉著其行能与出处大略,列诸卷首,然后录其所作,若乐府、若诗赋、若序记书疏之属,各以类分,而他邑之人,其文有为东阳而作者,亦附见一二,总若干卷,合而名之曰《东阳文献录》,盖亦祖述潜溪二书而为之者也”,对保存东阳地方文献具有重要价值。此书亦专门列“文学”一个大类,对唐宋以来的东阳文士作传予以记载。
Moreover, some circuits[17, 18] generate a reset pulse by a comparator, which results in a complex circuit structure.
章懋编纂的《兰溪县志》,为兰溪现存最早的一部县志。在编纂此部县志中,章懋回顾先贤吴师道《敬乡录》所起的作用,“邑先正礼部吴公尝著《敬乡录》,略识前代硕儒、才士、名卿、贤相之本末,而附以诗文,又取祠庙碑志及乡进士题名等记,以存是邦之故实”。在《兰溪县志序》中,章懋云:“予惟是编之成,岂徒存故典、表先哲以昭示无穷而已哉?将使后之观民设教者,于是而求其故,以尽更化善治之道,论世尚友者,于是而稽诸古以为多识畜徳之资,亦未必无小补焉”。章懋编纂的《兰溪县志》不但有保存地方文献之意,还有强烈的教化之意在内。正如研究者所认为的“通过阅读方志,只需一个简单的名称,就能使身居其间的人们理解这些人物的历史含义”。对于文学来说,这种梳理地方文统的方式,虽然具有碎片化、零散化的特点,却也能在字里行间见出浙东文派成员的良苦用心。
第三,刊刻乡贤文集与纂修宗谱。乡贤是一地的代表人物,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在地方的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古以来,浙东文士便重视乡贤,尤其注意搜集、整理与刊刻他们的著述。在明代,这种传统得以继续发扬光大。对浙东文统的重视,不但体现在梳理浙东不同时期的文章统绪,还在于对乡贤著述的搜集与整理。王应麟是宋元之际浙东著名学者,著述丰富,然散佚也较多。郑真辑《四明文献集》,对于保存王应麟的著述贡献良多。同样是宋元之际的戴表元,以文章名世,号称东南文章大家。在戴表元去世后,其著述湮没不彰。到明洪武年间,在宋濂纂修《元史》之际,其著述才得以为文士所熟知。这要归功于宋濂对他的重新发掘和表彰。现存的宋濂文集中有《剡源集序》一文,详细记载了宋濂刊刻戴表元著述的情况。在此文中,宋濂谈到自己师从黄溍学文,戴表元是黄溍极为赏识的文士。黄溍称道戴表元,宋濂想法设法搜集、编刊其著作。宋濂“日购先生之文,绝不能以多致……乃属使者入鄞遍求之……曾未几何,有司果以《剡源集》二十八卷来上”。得到戴表元的《剡源集》后,宋濂负责刊刻并作序。对此,戴洵《重刻剡源文集序》谈到他知道有祖先的《剡源集》,“宋景濂学士为司业时,尝序而刻之太学”。宋濂所刊刻的《剡源集》,我们今天虽难以见到,但其效果却是非常明显的,“于是学士大夫既知有先生,而又知有先生之文矣”。从黄溍到宋濂,这也在无形中体现着对戴表元接受的过程,是值得注意的文统承绪的变化痕迹。
方孝孺《逊志斋集》的传抄与编刊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作为一代文章名家,因十族被诛,其文遭到禁毁。《逊志斋集》能够流传至今,与浙东文派成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存其文字密切相关。在这样的情况下,浙东文统彰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现略述如下:
靖难之役后,方孝孺文字被禁,与其有关的话题亦是触犯忌讳之事。面对此种情形,义乌王稌辑方孝孺遗文为《缑城集》。临海侯卿,字邦彦,号抑庵,致力于方孝孺文集的收集与整理,“时收藏方正学先生遗文之禁未解,莫敢裒集,邦彦博求四方,得姑苏陈编修鉴家藏遗文二百六十篇,归授友人赵廷节授梓”。赵洪(字廷节,临海人)得到侯卿所授方孝孺遗文后,“复采集士大夫家之所记诵共诗文三百六十篇,捐赀锓梓,以传于世”。侯卿、赵洪的行为受到后人的敬重,清康熙间洪若皋修《临海县志》对二人多所表彰,认为“二公距藏方文之禁已六十年,此时不辑则几乎息矣。后成化庚子宁令郭绅刻于宁海,正德庚辰郡守顾璘刻于郡斋,嘉靖辛酉学使范惟一重刻之,华亭徐阶为之序,皆归重赵教谕,首事之功则廷节洵不可及也”。对于赵洪搜集与编刊《逊志斋集》的情况,现存天顺七年四月其所作的《新刊正学方先生文集序》中有着详细记载。此后又有宁海县令郭绅刊刻四十卷本《逊志斋集》,谢铎、黄孔昭分别作序以表彰之。谢铎称“先生之文,非吾台所敢私,亦非予小子所得而赞,特以著令尹之志于不忘,且以告夫天下后世知诵先生之文者”,把刊刻《逊志斋集》的价值由台州一地,扩大到天下,既是赞美郭绅,也是表达对方孝孺的景仰之情。作为生活在浙东大地的一位文士,黄孔昭自幼便浸润在浙东文化环境中,成为浙东文统承传链条中的一环。他谈到“自幼闻先生之名于乡……既长,稍知向慕,求先生遗文而读之”,但孝孺之文不易见到,“其遗文散佚天下,仅见赵教谕刻本。孔昭与谢侍讲铎日加访采,而其邑之秀彦,犹能各以所藏来告,遂合叶、林二亚卿,王、李二中书,与李常州之所得者,汇次之,而是编成焉”。谢铎、黄孔昭所搜集的诗文交给宁海县令郭绅,由郭绅负责刊刻,加上郭绅在宁海所搜访到的诗文,刊刻而成。这便是流传于今的明成化郭绅刻本。此后,在不同的时期均有相关文士对《逊志斋集》进行刊刻,使得方孝孺的文章得以顺利保存到今天。总之,浙东文派成员对方孝孺《逊志斋集》的搜集与编刊,是浙东文统的重要方面,具有不容轻忽的价值。刘宗周称“《逊志》一编,卓然系斯文之统,传之无穷”,于浙东文统,乃至整个明文统绪而言,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明前期浙东文派成员对宗谱文献体现出浓厚的兴趣,不少成员为宗谱作序,或者有编纂宗谱的设想,乃至实践。宋濂、方孝孺等多位成员均撰写了大量的谱序文章,如宋濂《桂氏家乘序》《方氏族谱序》《俞氏宗谱序》等。在这些宗谱文献中,不乏文学名家。尤其是浙东宗谱文献中,所记载的文学名家,可以看作是在家族这个单位对他们进行的描述与呈现。如宋濂所作序的《桂氏家乘》中,便有桂彦良、桂慎等文学大家。家谱一般由家族后裔编纂,每隔一段时间修谱一次,增添相关文献,不少家族会附有相关艺文作品。而名家所作的谱序,一般会从该家谱的始祖开始讲起,家族中的名人也是必谈之内容,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一篇谱序文章,相当于一个家族简明扼要的发展史。这其中涉及到诗文家的记载,无形中是对家族“文统”的梳理,而无数这样的文章则汇聚成了浙东文统。因此,纂修宗谱,甚至是为宗谱撰写序文,也是浙东文统梳理的一个方面。
第四,给浙东文人别集或地方总集作序,也是值得注意的梳理浙东文统的方式。宋濂作《华川文派录序》梳理义乌历史上的骆宾王、宗泽、黄中辅、喻良能、何恪、陈炳等文章名家,并向曾保存地方文献的黄应龢、吴师道致敬,称吴师道“昔者乡先达吴公师道悯前修之日远而遗文就泯,乃集婺七邑名人,所著为《敬乡录》二十三卷”。无论《敬乡录》,还是《华川文派录》,其作用不仅是保留文献与裨益教化,还在于呈现文学承传的历史轨迹。这对于浙东文统的梳理与建构具有较为重要的价值。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浙东文人在文章创作中对前辈观点或者作法的继承。如胡翰的《井牧》,戚雄认为“此篇《井地》规模亦多取说斋井田纲领之意而润色之”,点出其与唐仲友文章的关系。邵廉《送金华黄叔信序》云:“金华浦阳为东南文献之邦,与吾越邻壤,国朝大儒宋景濂先生之乡邑也”,表达对宋濂的仰慕之情,并点出黄叔信“生于名邦而私淑艾景濂先生之教”。文学观念的传承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环,塑造着浙东文人的文学旨趣和文学宗尚。浙东文统成为联结本地文人一种厚实的文化资源,不断出现在诗文书写中,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意识。浙东文人对本地文统的建构对于地方文学书写的崛兴具有较强的影响。
二、文学创作的自觉意识与浙东文学书写的兴起
浙东地方文学书写的兴起,与他们具有自觉的文学创作意识密切相关。浙东文派成员具有较为自觉的文学创作意识,并追随古文大家拜师学习文章创作。宋濂《赠梁建中序》谈到“余自十七八时,辄以古文辞为事,自以为有得也”。王袆《宋太史小传》生动地记载了这一细节,宋濂为举子业,课试屡次居诸生之右,胡翰劝他学习古文辞创作,即“其友胡君翰曰:‘举子业不足为,景濂盍为古文辞乎?’遂与俱往浦阳,从吴莱先生学”。戴良亦有类似经历,据赵友同《故九灵先生戴公墓志铭》记载戴良“初治经,习举子业,寻弃去,专力为古文。时柳文肃公贯、黄文献公溍、吴文贞公莱皆以文章鸣浙水东,先生往来受业门下,尽得其阃奥”。拥有这种意识,经常与志同道合的友朋切磋,比较容易提高文学创作的水平。
浙东地区文学书写的兴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拥有一支数量庞大、水平一流的文学创作群体。他们既是浙东文派的成员,也是明代前期文学创作的杰出代表。刘基长孙刘廌在为丽水吴从善的《青林文选》作的序中,谈到浙东的文学创作与明代的文治之兴,称:“天朝首兴文治之初,而金华、括苍之君子为多。余先祖诚意伯居开国文臣之首,肇赞化机,聿兴典礼。时则有若翰林承旨金华宋公景濂、待诏王公子充,俱以文章弥纶黼黻一时,典、谟、誓、诰、制、册、诏令皆出其手……礼部尚书天台陶君中立,相继膺显擢。既而,若翰林编修苏君平仲、张君孟兼、刘君养浩、吴君从善,又皆金华、括苍人,彬彬然接武乎其后。一朝文运之隆,非数先生作之于前,而诸君子踵之于其后,其能耸世德于汉唐之上哉?”因此,浙东文派的文学书写无疑为其他地区地域文学的兴起提供一个良好的示范,推动明代文学地方书写的兴起。
除了宋濂、胡翰、王袆、戴良等金华地区的文人外,还有许多浙东其他地区致力于地方文学书写的文士。金华地区因宋濂、王袆等人声名卓著,影响遍及全国,远远超过浙东其他地区的文士,带动整个浙东文学书写的兴盛。展读浙东文人别集,不难发现浙东的山水、人物、风俗、民情、历史、传说等大量出现于他们的笔下。浙东文派成员以真实的生命体验赋予此地山水以灵气。山川激发文士的才情,诗文彰显山川的魅力。
为研究的方便,现把浙东文派的成员按其影响力简单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宋濂、刘基等文坛领袖式人物;第二层次为刘廌、王稌等中等影响力的人物;第三层次为胡应瑞、高恩等影响基本局限于县域的文士。现对三类文人的地方景观书写略作考述,以见其梗概。
第一层次,以宋濂及其故乡浦江为例,来看这种地方文学书写的情形。宋濂在浦江青萝山下建青萝山房,刘基作《青萝山房歌寄宋景濂》,宋濂作《萝山迁居志》。还有其他地区的文士,如刘崧作《青萝山房诗为金华宋先生赋》、贝琼《青萝山房歌并引》等。此为仅就青萝山房而言,便有如此多的名人撰写文学作品。对于青萝山旁边的玄麓山,宋濂就该山之上的飞泉作《飞泉操》;就山西的桃花涧而携郑彦真等众多文士进行修褉活动,诗文酬唱,作《桃花涧修褉诗序》;就山上的桃花涧、凤箫台、钓雪矶、翠霞屏、饮鹤川、五折泉、飞雨洞、蕊珠岩而分别作诗,经宋濂等文士的歌咏,已成著名的“玄麓八景”。对于浦江名山仙华山,宋濂更是在众多诗文中频繁提起,如《重建龙德大雄殿碑》《混成道院记》等。方孝孺在浦江从游宋濂,获交当世天下文士,诗文酬唱,是生命中美好而愉快的时光,令他回到宁海后也久久难以忘怀。在他写给苏伯衡的信中便谈到“溪上从游乐甚,于人不忘。自归田庐,取倡和之什观之,意未尝不在仙华山水间也”。在此,仙华山水不单纯是山水了,而是具有某种象征,已然成为方孝孺的重要情感寄托。郑义门是宋濂、方孝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一草一木,皆有深情。对于郑义门,有两首著名的诗歌,一是宋濂作《别义门》,诗云:“平生无别念,念念只麟溪。生则长相思,死当复来归”;一是方孝孺《郑义门》则写道“史臣何用春秋笔,天子亲书孝义门”。郑义门也因宋、方等人的表彰而愈加闻名天下。同时,宋濂还为浦江本地历史人物作《浦阳人物记》,不少人物因宋濂此书而为人所熟知。
第二层次,以刘廌及“八景书写”为探讨对象。在现存的文献中,以刘廌所在的青田为中心,保留下来两卷唱和诗文,这些唱和主要围绕盘谷八景为中心,颇具价值。提起盘谷,唐代李愿是无法绕过的一位文士。韩愈的古文名篇《送李愿归盘谷序》正是为李愿而作。李愿将要归隐盘谷,韩愈作此文以赠之。李愿的盘谷在太行山下,刘廌的盘谷则在浙东青田。正如郭伯载《盘谷序并歌》所说的“昔之盘谷以李愿得名太行之阳,而今之盘谷以刘氏得名括苍之中,信所谓两山秋色气势两相高者矣”,但刘氏之盘谷诚有李氏之盘谷所难以媲美的地方,即“披襟茂树,濯缨清泉,茹山之美,食水之鲜,若盘谷者,无处不有焉。至于结窝著皇极、闭户草太玄,下者入黄土,高者出苍天,斯刘氏所以乐其乐,而李愿未之尝言抑且余不能知矣”。
对于盘谷唱和,刘廌云:“盘谷唱和诗者,括苍芝田、南田山,闲闲子与濮阳耿介生诸友之所作也”。闲闲子为刘廌的号。盘谷是刘廌在青田鸡山下所筑的住处,其周围的风景,被誉之为盘谷八景。盘谷八景为鸡山晓色、龟峰春意、北坞松涛、西冈稼浪、双涧秋潭、三峦夜月、松矶钓石、竹迳秋斋。据刘廌《盘谷唱和诗序》中所谈到的“闲闲子洪武二十四年以诚意伯爵贬秩归农,二十六年拟筑室于旧宅之西鸡山之下居焉。其地山水盘旋,故名盘谷”。他看淡了人生进取、仕途荣辱,虽建文、成祖皆欲用之,他力辞之,归隐于盘谷。盘谷的基本情况是“谷之东有草庐三楹,颇幽静,因以礼聘耿介生馆于兹,以训二子。”在青田,刘廌徜徉山水之间,时常与三五好友一起饮酒酬唱,留下了不少描写浙东风光的诗文作品,尤其以盘谷八景的文学书写最为引人注目。书写盘谷八景诗的文士有刘璟、刘廌、郭伯载、沈原昭、魏守中、刘道济、卢廷纲、谢复、周景辰、耿介生、蒋琰、张宜中、祝彦宗、常叔润、徐思宁、俞廷芳、杨守义、叶履道、朱逢吉、赵友士、邹宏道、姚文昌、莫士安、叶庭芳、张秉义、王尹实、王仲章等。上述文士留下的大量盘谷八景书写塑造了青田的文学景观,成为文坛一个独特现象。
在宋濂、刘廌之后,谢迁以诗文名于天下,晚年致仕家居余姚,书写绍兴地方文学景观,相关诗文集中收录于其《归田稿》中。他应邀为建平(今为安徽郎溪)吕文郁编辑的胥溪八咏诗作序,这代表着其他地域的文士对浙东文派的认可。此序是应吕文郁之请而作。胥溪八咏是吕文郁因思其亲,而就胥溪八景所创作的一组诗歌,“士大夫交于君者,从而和焉,久之而成巨帙”。谢迁谈到吕文郁登甲第、官郎署,而父亲吕仲和却已不在,胥溪之胜景尚在,“古者孝子思其亲于居处,笑语志意,乐嗜必极其想象形容之真,文郁之于胥溪,其能一日已于情乎?此八景之诗所由作也。此诸君子所以继声而不容少靳也”。谢迁所阐发的观念,既有孝养父母方面的,也有景与人之关系,“嗟夫!胜景之在天地间,不幸遇非其人而沦没于荒烟宿莽之中者多矣,胥溪之胜,固以翁而胜,然非文郁为之揄扬,则有声之画摹写逼真,又未必若是其工且富也”。谢迁关于八景书写的文学观念,不但会被吕文郁看到,一般情况下,书刻印完成后,会给相关和诗的文士寄送的,还会被和胥溪八景诗的文士看到,也有可能为后来的文士所注意,这些均推动浙东文派成员关于地方文学书写观念的传播和流行。
第三层次,值得关注的还有一些不如宋濂、刘廌有名气的文士,他们的浙东书写也有着独特的价值。以台州为例。闻伯阜,天台人,洪武开科进士,有文名。吴昊,字彦钦,天台人,工诗文。胡应瑞,名玲,字应瑞,号倥侗子,“感时触事必于诗发之”。陈宁富,字好礼,号用拙,临海人,南斋陈昌言之孙,受业于赵靖轩,“长于诗”,“与其友胡应瑞辈结诗社自娱”。陈宁富在明初所结诗社,影响颇大。据洪若皋《临海县志》卷九《高纨》谈到其祖高恩,号牧庵,“与陈用拙、胡倥侗辈十有八人结诗社自娱,一时高之,呼为十八学士”,可知参加者有高恩、胡玲等十八人。这在当地是一个声势较为浩大的文学创作群体。上述不同层次的文士的文学书写,共同推动浙东地方文学书写的兴起。
三、结语
明前期百余年的时间内,浙东地区涌现出了大批文士,成为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在科举考试方面,定海张信为洪武二十七年状元(奉化戴德彝中此科榜眼),周旋是正统元年的状元,商辂为正统十年的状元,谢迁为成化十一年的状元,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其中商辂为三元及第,并担任内阁首辅,明代所罕见。在科举考试成为士人主要入仕渠道之际,状元集中出现的浙东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另外,黄淮、谢迁等人亦担任内阁首辅,具有重要影响力。在此一时期,许元、陈敬宗、谢铎、章懋等人亦曾担任国子祭酒(或南京国子祭酒,或北京国子祭酒),在士林具有较高威望。一般谈到洪武年间的文武官员,浙东文士与淮西武将是最为核心的部分。在文学创作上,浙东文派引领着主流文坛的潮流。即使在永乐至成化年间,浙东文士依然数量巨大、影响深远。他们经常往来于京师与浙东,文学活动频繁倡起。同时,浙东文派成员多位文坛名家有着长期致仕家居的生活经历。在这样的情况下,浙东文士得以有较为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书写地方文学景观。文学领袖式的人物对于地方文学书写的助推作用尤大。宋濂之于金华、黄淮之于温州、商辂之于严州、谢迁之于绍兴、陈敬宗之于宁波、谢铎之于台州,在当时形成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坛风景。黄淮、谢迁等留下不少归田家居的诗文作品,影响着当时和其后的文学写作。
明代浙东文统的发掘及其地方文学书写的兴起,对于其他区域的文学书写具有重要意义。江右派是明代实力雄厚的地域文学流派,也是胡应麟所标举的“五派”之一,以杨士奇、解缙等为代表。杨士奇师从浙东文派成员王叔英,并受其举荐。王叔英“一日出郊迎使,遇杨文贞公士奇于旅舍,索而见之,倾盖如故,即以王佐之才荐于朝”,杨士奇对王叔英则执弟子礼,始终以门生自居。关于此事,谢省亦有记载,“若吾静学王先生,国朝仕至翰林修撰,西江杨文贞公,实先生之所举者”。只是后来靖难之役爆发,王叔英自经于玄妙观,建文诸臣成为防嫌触讳的话题。解缙之父解开师从元代浙东文派成员黄溍等人,而解缙本人亦师从浙东文派重要成员苏伯衡,登朝后,“以所为文求正于平仲苏先生”。廖可斌先生的《论浙东派》对浙东派形成的历史条件、理学渊源、文学主张和艺术风格进行考察,并考察了浙东派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变迁的关系,认为“浙东派衰落后,其文学思想却继续被奉为正统,为紧接着兴起的江西派所继承”。因此,在江右派的文学创作,乃至地方文学书写中,或多或少地受到浙东文派的影响。
同时,浙东地方文学书写的大量出现对明代文学的演进而言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是因为浙东文派的多数成员,不但是浙东地区的杰出文士,而且在全国文坛深具影响。《明史·文苑传》:“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宋濂、王祎、方孝孺以文雄,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著。其他胜代遗逸,风流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已。”就此处所胪举文人的地域而言,在明初,文章之盛首推浙东;浙东文人刘基在诗歌创作方面亦具有重要影响。清人薛熙选明代诗文两千余篇,成《明文在》一百卷,其为该书所作的《序》则把有明一代文章的兴废皆归到宋濂身上:“明初之文之盛,潜溪开其始;明季之文之乱,亦潜溪成其终。盖潜溪之集不一体,有俊永之文,有平淡之文,有涂泽之文。洪、永以及正、嘉朝之诸公善学潜溪者得其俊永而间以平淡,此明文之所以盛也;隆、万以及启、祯朝之诸公,不善学潜溪者得其涂泽而间以平淡,此明文之所以乱也”。此说虽不免有夸大之嫌,然作为浙东文派重要代表的宋濂在有明一代的影响可见一斑。
明清时期文学地域性的增强,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浙东地区是一个典型代表。浙东地区不仅出现宋濂、刘基、方孝孺等大量描写浙东山川风物的作品,还出现一系列诸如《金华文统》《婺贤文轨》《赤城诗集》等展现地方文学创作实绩的文学作品,以及搜集、整理与编刊乡贤的作品,这使得浙东地区有大量的文献得以保存下来,在全国也是引人注目的。加上浙东文派成员之间相对稳定的师承等关系,紧密地把成员团结起来,形成独特的“浙东文人集团”,以及当时的浙东文派成员在中央文坛的领袖地位,使得浙东地区的文学创作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不同于吴中、岭南等地。应该说,在地方文学书写中,对其他地区也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具有不容轻忽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