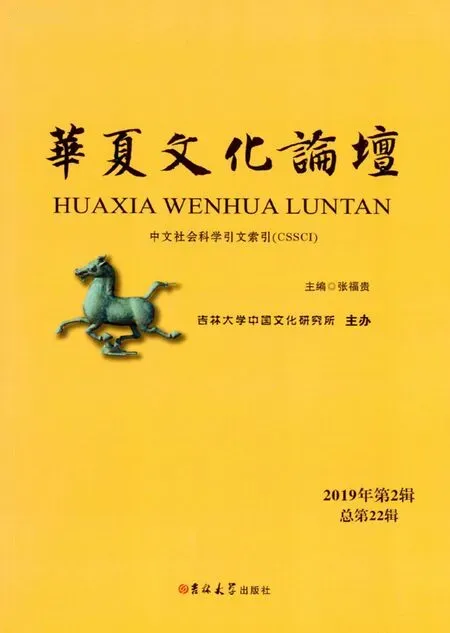明清时期采参习俗的传承与变异
2019-11-12赵春兰
赵春兰
【内容提要】历史悠久的采参习俗一直为学界所关注,虽然产生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但采参习俗的发展脉络始终不清。由文献史料来看,明清朝代更迭是采参习俗发展的关键节点。满族入关之后,东北涌入大量汉族移民,采参方法重复实践,但由于采参人的民族成分发生变化,采参习俗崇奉对象也随之发生转换。入关前采参人信奉多神观念的萨满信仰,入关后山神成为采参人信奉的主神,后来又产生了行业神老把头,二者并祀。
一、研究现状述评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采参习俗研究日益受到关注,产生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1981年富丽在《中国民族》发表《满族采参》,1982年王佩环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清代东北采参业的兴衰》,这两篇文章从经济史视角切入,尚未涉及满族采参习俗信仰对象和采参方法,但启发我们去思考挖参习俗的发展源流,推动了采参习俗研究。1987年金宝忱在《民俗研究》发表《长白山挖参习俗》,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长白山采参时间、采参成员的分工和采参工具、采参时如何观景和压戗子、采参习俗信仰和应遵守的山规、寻找人参时如何排棍和发现人参时如何喊山、如何挖参打包砍兆头,这篇文章为我们全面了解满族入关后的长白山采参习俗事象做出了很大贡献,遗憾的是缺少纵向深入,未深入探究长白山采参习俗形成于何时,如何发展与变异。孙文采于同年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长白山挖参习俗之巫术观》,从巫术的角度分析了长白山挖参方法和习俗信仰,努力探索采参习俗的形成原因,启发我们从不同视角探讨采参习俗。2013年李爽在《满族研究》发表《满族采人参生产中的信仰文化》,阐述了采参过程中的人参崇拜、火崇拜、山神和老把头崇拜及占卜,若说满族采参生产中崇拜火、崇拜人参、崇拜山神还能令人接受,但把老把头崇拜也归为满族采参的信仰对象真是张冠李戴。
就目前研究现状来看,采参习俗源流脉络仍然不清。采参习俗古已有之,其世代流传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但到了明清易代之际,随着世居长白山区的女真--满族入主中原,历史悠久的采参习俗发展也随之出现重大转折,这尤其值得我们深入探讨,让我们一起来考察明清时期采参习俗如何传承与变异。
二、采参方法溯源
《本草纲目》“人参”条目集解引弘景曰:“高丽人做《人参赞》云:三桠五叶,背阳向阴,欲要求我,椵树相寻。椵音贾,树似桐,甚大,阴广则多生,采作甚有法”。《本草纲目》对人参的“采作之法”没有详细介绍,我们可通过其他线索了解“采作之法”。丰富的长白山动植物资源是明末女真崛起的重要经济支柱,女真--满族和采参习俗的关系非常密切。女真--满族属于肃慎族系,其先祖肃慎、挹娄、勿吉、靺鞨世居长白山区,在原始氏族部落时期都以采集渔猎为经济来源。东北古代民族最早把人参作为贡品进献给中原王朝的是黑水靺鞨,开元十四年(726年),唐朝置黑水都督府,自此黑水靺鞨和唐朝贡使不绝,往来密切。仅从726年至815年的九十年间,靺鞨朝贡达二十五次,每次来朝均携带金、银、牛黄、人参等珍贵的工艺品和土特产。如唐玄宗七年(748年)三月,“黑水貊赫、黄头室韦、和解室韦、如者室韦、赂丹室韦并遣使献金银及六十综布、朝霞绸、鱼牙绸、牛黄、人参”。此时黑水靺鞨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采集渔猎是他们主要的劳动方式之一。
粟末靺鞨建立的渤海国也向唐朝廷朝贡人参,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二月,“渤海国王大諲譔遣使裴璆贡人参、松子……。”《渤海国志三种》也明确记载:“贡献品曰鹰、曰鹘、曰马、……、曰人参、曰松子、……。”因为渤海国进献过人参,故宋德胤认为“今天流传于白山黑水满族中的采参习俗,实际就是渤海国的采参习俗的历史传承物”,但宋德胤并未对这一观点展开论述。笔者分析,渤海国各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均衡,因而渤海国的社会制度呈现着复杂状态,在渤海国西部和五京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封建制,主要从事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渤海国中部有山间盆地,东部和北部地区山高林密,气候酷寒,人烟稀少,有的地区还处在原始公社制末期,有的正在向奴隶制过渡,如怀远府、安远府、安边府和铁利府。中部盆地、东部和北部这些地区采集和狩猎还占据主要地位,当时的采集狩猎活动是以氏族或部落为生产单位集体进行,朝贡的人参应该是出自这些地区。
从粟末靺鞨和黑水靺鞨朝贡人参的数量、频率及产出地来看,我们可以确定唐朝时长白山采参习俗已经形成,考古发掘曾发现过渤海国采挖人参的工具。在俄罗斯滨海地区南部的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新戈尔杰耶夫卡等渤海遗址中出土八件用动物肋骨制作的采挖人参的小钎子,“它们是扁平的,稍有弯弧,在其中一些小钎子的末端上部有直径0.3厘米的悬挂孔。挖参的一端被削尖或被用得稍钝。长度为13-34厘米,宽0.9-1.7厘米,厚0.1-0.5厘米,表面光滑”。靺鞨的采参过程尽管没有载入文献,但经过世世代代采参者的体化实践被社会所记忆,被辽代和明代的女真人传承,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又不断得到丰富、完善。
明代的女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以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为主,他们采集大量的人参向明朝朝贡,而且借朝贡之机在北京销售获取暴利。此外,女真人还把大量的人参销往辽东马市和中朝边境,据明档记载,万历十一年到十二年在镇北、广顺二关的交易中,海西女真出售的人参一项就达三千六百一十九斤,计值白银三万余两。天聪二年十二月(1628年),后金同朝鲜互市,“出给人参四百八十余斤,责换毛青布一万九千余”,采集人参成为女真人“赖以为生者”。《重译满文老档》第五卷天命元年(1619)至二年六月:“听说边境的尼堪人(汉人)越境,侵犯诸申地方,汗说:‘尼堪人每年越境、挖银、采人参、采集松子、木耳、蘑菇,侵犯的事件很多,为禁止这样的乱行,曾立界碑,杀白马,立誓了。尼堪人违背誓约,不论什么时候偷越边境,我们便杀死那个人,也没有罪。’派达尔汉虾在相遇的地方,依次杀了越境的尼堪五十人。”由这条史料可知人参对于明朝女真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
建州女真的基本生产单位叫穆昆塔坦,《满文老档》中的穆昆塔坦档记录显示:第一穆昆有十二塔坦,第二穆昆有十三塔坦,第三穆昆有十二塔坦。刘小萌认为:“穆昆的本义是族,并非是血缘组织性质,而是以传统社会组织为其外壳的权力组织,他实际上已经成为部落联盟的核心”。“塔坦”原指“野外行走人的止宿处”,就是住在野外的窝棚。满族集体行围“不论人之多寡,各依族、寨而行”,分散采参游猎则划分为更小的劳动组合,“每一幕 (即塔坦 )三四人共处,昼则游猎,夜则困睡 ”,采参狩猎在野外连续生活有时长达二三个月。
随着建州女真政权的发展,塔坦又成为“兵民合一”的行政组织牛录的构成单位。《重译满文老档》第四卷乙卯年(1615年)记载:“十一月,淑勒昆都仑汗把聚集的众多国人,都平均划一,三百男丁编一牛录,一牛录设额真一人。牛录额真以下设置代子二人、章京四人和村领催四人。四名章京分领三百男丁编为达旦(塔坦),无论做什么事情,去什么地方,都规定达旦成员同行,轮流做同样的事情,预先订立一切制度。”于是,一个编制严密紧凑的牛录就这样形成了。在牛录的基础上组建固山,1615年完成八固山(八旗)制度。牛录组织特点与金代猛安谋克一脉相承:兵民合一,“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 ”。这种“兵民一体”的采集狩猎组织性质使采参者如同行军作战似的采集人参,采参者必须遵守的劳动规定流传后世,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采参习俗中严格的山规和行规,这从清初的文献史料可窥见一斑。杨宾的《柳边纪略》记载了康熙朝流民的采参方法:“凡走山者,山东、山西人居多,大率皆偷采者也。每岁三四月间,趋之若骛,至九十月间乃尽归。其死于饥寒不得归者,盖不知凡几矣。而走山者日益多,岁不万余人。凡走山刨参者,率五人为伍,而推一人为长,号曰‘山头’。陆行乘马,水行驾威弧,沿松花江,至诺尼江口登岸,覆舟山谷间,乃入山相土,‘山头’坐而指挥,四人者剥树皮为窝棚。又择一人炊,三人樵苏,夜则燎火自卫。晓食已,人携小刀一、火石包一、四尺长木铲一、皮袋,随‘山头’至岭,受方略,认径路,乃分走丛木中,寻参子及叶,得则跪而刨之。‘山头’者时时立岭上,作声以呼其下,否则迷不能归矣。日暮归窝棚,各出所得交山头,乃洗剔而煮,贯以缕,悬木而干之。日惟晓夜再食,粮尽则五人均分而还。”“山头”相当于塔坦达,五人组成的参帮相当于一个塔坦组织,采参劳动听从“山头”统一指挥。民俗具有传承性,清初流民的采参劳作就是对明朝女真采参方法的重构和再现,并作为一种实践记忆流传下来,被长白山区世世代代的放山人重复操演。
三、采参习俗信仰对象的传承与变异
采参习俗是满族先民在历史悠久的采参劳动中形成并世代流传的风俗事象。满族先民自古崇奉萨满信仰,他们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和崇拜祖先。萨满信仰形成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原始社会落后的生产力水平限制了满族先民的认知能力,他们不能科学地解释某些自然现象,于是对自然界产生敬畏心理,认为自然界存在一种超人的力量,这种超人的力量就是神灵。原始人类希望神灵能够保佑他们安全顺利地进行生产劳动,为他们的日常生活驱灾除邪,而萨满具有绝地通天的超级本领,是人类和神灵的媒介。每个穆昆组织都有自己的萨满,有的族长或酋长自身就是大萨满。萨满祭祀活动是穆昆活动的重要内容,穆昆的全部成员必须参加。萨满信仰伴随着原始社会采集渔猎的经济基础产生,这种意识形态对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从事采集渔猎的满族先民有着重要意义。
萨满信仰流传传到“肃慎之地”的靺鞨仍然有着深厚的基础,形成于唐朝时期靺鞨的采参习俗自然传承了萨满信仰。粟末靺鞨建立渤海国后深受唐朝的经济文化影响,佛教盛行,但佛教只是盛行于渤海国的上层社会和发达地区,在那些依赖采集渔猎经济的偏远地区仍是以萨满信仰为基本宗教思想。黑水靺鞨的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于粟末靺鞨,完全以采集渔猎为生业,更依赖萨满保佑他们的采集渔猎活动顺利进行。辽代的女真族生活在靺鞨的故地,继承了靺鞨的传统文化包括萨满文化。萨满信仰在女真族建立政权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完颜部就是借助萨满信仰发展壮大,但女真族在1115年建立金政权后吸收借鉴中原传统文化,萨满信仰的某些现象同统治阶级的现实利益、政治经济制度发生冲突,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可萨满信仰在民间仍然普遍流行。长白山是女真族的发祥地,山神在采集者心目中的地位非同寻常。在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发现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是金代皇家山祭遗存,出土金代各类遗物五千多件。另外,女真的天神崇拜观念非常强烈,所以采参习俗主要是信仰山神和“拜天”,“拜天”是祭拜日月星辰。
明代的女真族在建立政权之前,单纯完整地继承了萨满信仰传统,尽管在努尔哈赤统一各部的过程中,“掠祖像神器于贝勒马前”,意图使人们对旧社会体制无所依附,在思想上统一各部落,使萨满信仰的形态发生变异,但采集狩猎习俗信仰仍然传承了萨满信仰传统。采集者出发前必须净身并保持充沛的体力,进山后通过占卜决定行走的方向和采集目的地。采集者到达目的地后先点起篝火,向篝火里敬酒,之后搭建窝棚。采参前用于占卜的工具是在进山的路上临时获取的,俗称“现请现卜”,也就是在进山的路上遇到那种动物就猎取种哪动物的骨头作为占卜工具,采参人认为这种动物是神灵选好了给他们送来的,用它的骨头占卜最为灵验,而且还能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若干采参人在塔坦达的带领下,晚上在星星出齐之后面向北斗,或在早晨太阳升起之后面向太阳,虔诚地叩头祷告,然后塔坦达用“现请”的骨头占卜,众人沿着占卜的方向行走去寻找人参。
1644年满族入关,东北“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在清政府采取了开发东北的移民政策之后,东北居民变为以汉族为主,人参采集牲丁的民族成分亦随之发生变化,所以人参采集者的供奉对象也发生转换,不再信奉萨满信仰,由多神观念走向单一化,山神成为采参人信奉的主神。自然崇拜思想形成于原始人类社会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开发长白山的历史进程中,山民不仅寻求自然神灵的护佑,还把本行业有影响的人物给予神化,加以崇奉。长白山区的采参人最崇拜的行业神是老把头,传说老把头是挖参人的始祖,名叫孙良,是山东莱阳人,清朝末期闯关东来到长白山挖参,后来饿死在长白山里,化为采参人的保护神,人们便把他与山神并祀。采集者“每出游至深山绝涧,类皆架木板为小庙,庙前竖木为杆,悬彩布置香炉,供山神位,亦有供老把头者,大约因山多猛兽,祈神灵以呵护之也。”清末刘建封的《长白山江岗志略》对此也有所记载:“老把头名称,放山、打牲、伐木各有把头,以其为首领故也。东山一带奉为神明,立祠与山川神并祀。或称为王姓名稿者,或称为柳姓名古者,皆不可考。然窥其祀之之意,亦系干山利禄者之不忘本耳。”
纵观采参习俗的漫长发展史,明清易代是采参习俗发生转折的关键节点,我们目前见到的采参习俗正是满族入关之后的采参习俗的变异事象。厘清采参习俗的发展演变脉络,就揭去了采参习俗的神秘面纱,对于提高文化自觉意识,更好地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