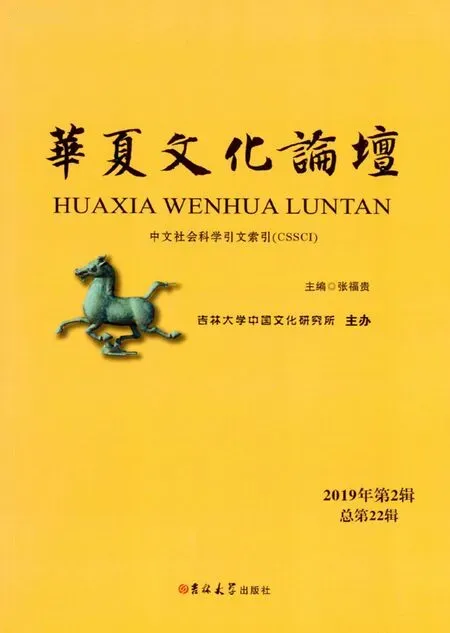星汉灿烂 若出其里
——写在《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修订版)外译之际
2019-11-12梁骏
梁 骏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李彬教授《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修订版)一书的再解读,藉以对当下新闻传播学界的研究现状予以分析点评。文章认为,李氏所倡导的“以人为本位、以问题为主导、以想象为法门”的研究旨趣,或许有助于解决当下新闻传播学界日益内卷化的研究困境。此外,李氏著中所涉及的有关邮驿系统和民间传播的讨论,亦有助于重新激活学术研究的想象力,进而让我们看到以前从未关注过的历史景象。
日前,欣闻李彬教授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修订版)一书得到国家外译项目资助,并将由英国麦克米兰公司出版,这对于传播中国古代灿烂多元的社会文化,展示意蕴深远的华夏传播智慧,无疑具有特别意义。欣喜之余,不禁感叹:一部以博士学位论文为主体的研究专著,何以历二十年而不衰,如今还入选欧美权威出版社选题?值此成书二十周年,又躬逢外译之际,笔者不避愚陋,冒昧成文,以期抛砖引玉,激发学界更多同道之讨论。
一、“大题大做”与“庖丁解牛”
观今日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之研究现状,一个鲜明的特点和趋势便是个案研究越来越多,“深井”越打越深,是谓“小题大做”,往往力求如外科手术一般,划小切口而深入,迅速准确地解决问题,进而推动学术的发展。若以此为据,李氏此著似乎稍显“落伍”,因为《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一书(第一版1999年,修订版2014年),无论是从断代史还是专题史研究的角度来看,都是一个相当宏大的研究命题,在学科日趋专业化和研究日益精致化的时代,看上去多少有些“平淡无奇”。然而,所谓研究问题的大小,本无高低上下之分,更多体现的还是研究者自身的眼光格局和研究旨趣。前些年李金铨教授曾针对当下的研究现状,不无忧虑地指出:“学者抱住一个小题目,在技术上愈求精细,眼光愈向内看,问题愈分愈细……其结果是不但忘记更大的关怀,更阻碍思想的创新。”
史学家严耕望在《治史三书》里,也专门谈到过这一话题。在他看来,主张专精一派(研究小问题)和倡导通识一派(研究大问题),二者皆有道理,应当互为补充,只须谨防他们各自走入极端,因为“前者走到极端,势必走上钻牛角尖一途,发生瞎子摸象,见树不见林的毛病。后者若走极端,又很容易走上束书不观……肤浅浮薄的一途……”故此,他建议研究者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在人生治学的不同阶段,尝试研究不同的学术命题:“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大做;老年时代,要做大问题,但不得已可大题小做。”
如是观之,李氏在年近不惑之时完成的这部具有“开拓意义”(丁淦林语)的“垦荒之作”(陈业劭语),恰好对应了严先生所谓中年时代要“大题大做”:全书第一次对唐代新闻传播活动进行了全景式考察,通过对浩瀚的古代典籍和近世论著的爬梳清理、裁断汲收,从整体上探究了隋唐五代新闻传播的来龙去脉,以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有机统一的方法,揭示出唐代新闻传播在中国历史中的独特地位。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这样一个断代史研究的大专题,李氏并没有汲汲构建于宏大复杂的叙事框架,更没有一味罗列史料、堆砌事实,而是举重若轻,通过对“官方传播”、“士人传播”和“民间传播”这三种当时最基本的新闻传播与信息扩散渠道的考察,以灵动的笔触和深邃的分析,将唐代新闻传播的主要方面娓娓道来:从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主体,到信息的呈现形式和传播渠道,再至不同的新闻思想和传播观念,进行了钩沉索隐的研究和翔实可信的阐述,进而在最大程度上,复原了唐代新闻传播的壮美画卷。
近年来,时常听闻学界呼唤学术“想象力”,然则何谓“想象力”却一直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就笔者个人而言,落实到中国新闻史学界的知识语境,黄旦教授的体悟深得我心:“‘想象力’”是一个人内在的修为,是一种关怀人、关怀世事的气度,是一种‘身在此山’,而又能由此及彼,‘在远近高低各不同’中辨认其‘面目’的眼力,不是现在人们热衷的技术、策略或者方法。”李彬教授之所以能够庖丁解牛般地回应如此宏大复杂的研究命题,除了因其可贵的学术勇气和深厚的学术功底之外,也在于其当年倡导“以人为本位、以问题为主导、以想象为法门”的研究旨趣。试想如果没有这种依违于文史两界,涵泳乎新传之间,兼具考据与义理的整体史观,恐怕李氏也难以在卷帙浩繁的史料中徜徉自得,更不会有如今这本气魄宏大,读来颇有曹孟德“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之感的力作。
二、人文主义的历史观
近代中国史学,自清代训诂考据以降,曾一度汇入西方兰克史学之流,即提倡“科学的史学”,“不但史家自身个人的主观思想不许混入史学研究之内,而且历史上已经客观存在过的抽象东西,如精神、价值观之类的也一律要划出史学范围之外。”与此相应,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也曾陷入史料的迷宫而无法自拔,往往重考据而少义理,甚至有些干脆成为编年体或起居注,这就不免造成新闻与历史的双重隐退。而如上文所述,李氏的研究旨趣显然与此有别,他在论及唐代新闻传播及其历史意义时,曾有一段话或可更加直白地表明其意:
“无论中西,史学都经过一条从历史科学到历史哲学的递进之路。前者犹如好奇的儿童,恨不得把每桩史事的来龙去脉都问清楚,后者已是饱经风霜的老人,‘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在纷纭驳杂的历史表象上驰骋其智慧的灵思。历史科学的派别不管怎样千差万别,无不立足于“经验的现象”,而历史哲学显然已不满足于这类‘如史直说’(兰克),其旨趣在于从历史中追寻‘先验的或超验的意义’。或者说,历史哲学不着眼于再现历史的形态,而着眼于复活历史的神态。”
正因如此,本书作为迄今为止第一部考察唐代新闻传播活动、思想的学术著作,除了其史料价值上的拓荒意义之外,更在于其人文主义历史观的彰显。科林伍德曾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实际上其思想的内核也正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历史观。在科氏看来,历史事件可分为“外在”和“内在”两种,前者包括史事的物质状态,后者则主要指史事中人物的思想状态。史家只有深入史事的内在一面,方能把握历史的脉搏。因此,他认为史家最重要的本领是能够“设身处地重演古人的思境”。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黄宽重先生,在评析宋史专家邓小南的著作《祖宗之法》时,亦曾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冀欲勾勒抽象的文化概念与其意象转变,必须返求于当时代人具体的行为反应之中”。
细读《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不难发现,李氏孜孜以求的也正是如此。在厘清唐代的官方传播实践之后,本书重点探究了唐人的新闻思想与传播理念,他以唐代开朗奋发、自由解放的时代精神起笔,认为这是理解唐人传播思想的重要背景;接着从《贞观政要》入手,考察唐朝“人格化身”的李世民之纳谏兼听,在显示开放包容的时代语境之后,自然而然地展现出当时“通达”的传播理念,并通过陆贽“去蔽求通”观和刘知几“才、学、识”理论的分析,让唐代的新闻传播思想与今日的新闻实践产生共鸣。同样,在唐代的士人传播和民间传播的考察中,李氏也是通过对庞杂史料的爬梳寻觅,竭力复原当时士人传播和民间传播的历史情状,进而在信息流布的具体语境中,分析出士人传播和民间传播的主体特征、传播方式、重要影响等。简言之,李氏正是以一种人文主义的历史观,激活了“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这一学术命题的内在张力,从而为我们呈现出这样一部鲜活生动的历史话剧。
三、余论及两点思考
行笔至此,本想就此书的行文叙述再做一番评析,然则考虑到李氏文风早已自成一脉,为学界诸位师友所熟知,若是再议,恐怕非但不能“锦上添花”,反而会“画蛇添足”。用李彬教授经常在论著里援引的话来说,便是“擦粉太厚,未必是美”,故而就此作罢。不过,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脑海里一直萦绕的两处思考,或许可以拿来求教于各位方家。
其一,李彬教授开篇对“邸院与驿传”的探讨,在我看来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李氏认为,作为帝国最重要的官方传播网络,驿传系统堪称帝国的“生命线”,它们可以决定整个唐代官方新闻传播的面貌与特征。实际上,这不仅与哈罗德·伊尼斯的观点颇为相似,更在于其关注到了此前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中常被忽视的一个命题:邮政系统。按照伊尼斯的观点,帝国必须立足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而连接时空恰又是传播所具有的天然属性,因此,伊尼斯把“帝国的概念作为传播效果指征”的比喻,实则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帝国不仅因传递和传播而存在,帝国正存在于传递和传播之中。然而,过去无论是我们的新闻史研究还是传播史研究,似乎都没有充分考虑过邮政系统的重要性,大多数研究者的目光始终逃不出报刊之外,这就不免造成研究成果的碎片化和同质化。直到近年来,德布雷(媒介学研究)、周永明(“路学”研究)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引入中国或者相继问世,人们才开始对此有所重视。依笔者愚见,围绕帝国的邮政系统这一命题,再通过与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的交流互济,或许可以为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重新开拓一片天地。
其二则是其对民间传播的关注。长期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过于关注所谓精英文化的历史书写,但对普通大众却鲜有着墨。这其中,自然有史料难以找寻的客观原因,但恐怕多少也与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有关。正因如此,李氏能在二十年前便将目光“下移”,对农人、伶人、商贾、僧道、医卜、渔夫、樵子、工匠、歌妓等普通大众的传播情状予以描摹,着实难能可贵。法国哲学家丹纳曾提醒我们注意,不要在大家响遏行云的独唱中,忽略了大众嗡嗡作响的合唱与伴唱,因为正是“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近年来,章清、卞冬磊的阅读史研究,周海燕、沙垚的读报小组研究,实际上已经开始关注起“那些来自不同阶层、散落于社会、各式各样的大众的想法和心情。”或许,让长期作为“缺席之在场者”的普通民众重新回到历史舞台,不仅会为学术研究激发新的活力,更可以让我们看到以前从未关注过的历史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