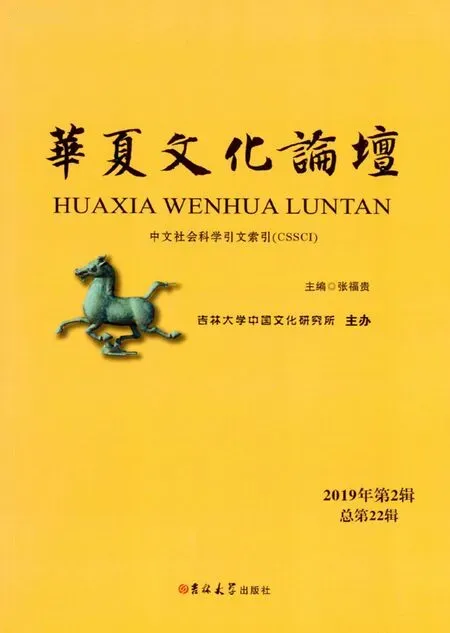论林纾《春觉斋论文》的文论思想
2019-11-12李永贤
李永贤
【内容提要】林纾是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古文家,享有“古文殿军”之美誉。《春觉斋论文》是他的文论专著,该书在吸收前人理论、总结自己古文创作和批评心得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全书分为“述旨”“流别论”“应知八则”“论文十六忌”“用笔八则”“用字四法”六个部分。前三部分是从宏观视角对一些根本问题进行论述,后三部分则从微观入手讨论一些具体的技巧和方法。整体来看,该书的理论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即宗旨论、文文体论和艺术论。本文即从这三个方面,对林纾的文论思想进行归纳和分析。最后的余论部分,主要对《春觉斋论文》中的古文技巧和方法进行了评价。
林纾是近代著名的翻译家,也是古文大家。他的《畏庐文集》《畏庐续集》《畏庐三集》收文近400篇,其数量和成就即使置于古代文章大家之列,也未遑多让。在古文创作之外,他还选编评点了大量的古文选本,并通过开办讲习所、函授班等方式广收生徒,为后学指示古文写作的门径和方法。文论方面,他有《韩柳文研究法》《春觉斋论文》《文微》等专论,这些著作在吸收前人成果、总结自己在古文创作和批评心得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系统的文论体系。可以说,他在文章写作、选评及理论等方面都有突出成就,他之被称为传统古文的“殿军”是实至名归的。
《春觉斋论文》是林纾文论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该书部分内容曾以“春觉生论文”为题在1913年的《平报》上连载。1916年由都门印书局以《春觉斋论文》为题出版。该书分“述旨”“流别论”“应知八则”“论文十六忌”“用笔八则”“用字四法”六个部分。与诗话、文话、随笔、札记等传统文论零碎片段的论证方式不同,该书在体例、结构与内容安排上,都遵循了既定的原则,并体现了严谨的逻辑,形成了完整自足的体系,是真正意义的文论专著。
《春觉斋论文》六个部分中的前三部分,大多是从宏观层面对一些根本性问题进行的讨论,后三部分多为具体的作文技巧和法则,是对前三部分宏观问题的佐证或展开。该书理论整体上可概括为文章宗旨、文体和艺术三个大的方面,本文的主体也拟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对《春觉斋论文》的文论进行分析和总结。在最后的余论部分,再对该书关于古文“技法”的论述稍加讨论。
一、《春觉斋论文》的文章宗旨论
文章宗旨主要回答为文的目的和功能等问题,这是文章创作论中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但对此问题的回答往往见仁见智,归结起来,不外“明道”与“致用”两大端。
“文以明道”的观点萌芽于《荀子》,后经西汉扬雄的接续发挥,到刘勰得以确立。此后,唐初大儒王通明确主张:“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将文之道与儒家之道贯通起来。唐宋以来,随着理学的兴起以及文学领域中古文运动的蓬勃开展,“文以明道”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如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自述其成长经历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韩愈的弟子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也认为:“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宋代理学家周敦颐首次提出“文所以载道”的观念。此后,元、明、清历代的文章理论关于文章宗旨的讨论,都带有浓烈的“明道”色彩。
“文以致用”的观点出现也比较早,《左传》中就有“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的说法。东汉王充《论衡·自纪》从实用的立场提出:“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将“文以致用”表述得十分清楚。曹丕以帝王之尊,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体现的是上层统治者的文论观。中唐时白居易则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看待文章与现实的关系,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强调了文学对社会人生的书写和干预现实的责任。
宋代之后,明道与致用两种意识常被文章家关联起来。比如明初宋濂《文说赠王生黼》提出:“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可以辅俗化民之谓文。斯文也,果谁之文也?圣贤之文也。非圣贤之文也?圣贤之道充乎中,著乎外,形乎言,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也。”其论虽有浓厚的道学色彩,但将明道、立教、辅世三者统一起来,在明道之外也强调了文的实用功能。宋濂的高足方孝孺继承乃师的观点,在《答王秀才书》中也提出“凡文之为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的主张。作为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和经世致用风气的开创者,顾炎武也从明道与致用两方面来论文章,他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古文家魏禧也认为:“惟文章以明理适事,无当于理与事则无所用文。”
林纾在文章的宗旨、功用方面,也受到传统的“明道”“致用”观念的影响。他在给姚永概的信中谈到对文章的理解,“古人因文以见道,匪能文即谓之知道。盖古文之境地高,言论约,不本于经术,为言弗腴,不出于阅历,其事无验。唐之作者林立,而韩,柳传,宋之作者亦林立,而欧、曾传。正以此四家者,意境义法,皆足资以导后生而进于古,而所言又必衷于道,此其所以传也。”他非常赞赏宋濂关于文章明道、立教、辅世功用的主张,认为“三语尽文之能事矣”。但是,在林纾的文章理论中,他谈“明道”并不多,而较多的是谈“明理”。比如,他说:“盖文者,运理之机轴;理者,储文之材料,不先求文之工,而先积理,则亦未有不工者。”“综言之,古文者先义理而后言词,义理醇正,则立言必有可传。”“明道”与“明理”虽一字之别,但意义却大不同。“明道”强调对道的执守和传扬,“道”是目的,人对“道”是被动接受;而“明理”虽也离不开“明道”,但更注重对道的运用。由“明道”转换为“明理”,最终就落实到人的能力和见识上,这就不仅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的接受和消化。所以,林纾在谈“明理”时,一方面强调要读书,另一方面又强调增加阅历、提高能力。“学者能溯源于古,多读书,多阅历,范以圣贤之言,成为坚确之论。”“则欲去虚枵之病,必读书明理,准以儒先之道,不得实际,不敢为坿会之词,亦不至有浮夸之失。”“去俗本无他法,但有读书、明理、宗道三者而已。读书多,则闻见博,无委巷小家子之言;析理精,则立言得体,尤无饰智惊愚之语。至于以文明道,则位置逾高,可以俯瞰万有。凡猥二字不特无几微之染,亦并不知有所谓凡猥者。”林纾将“明道”转换为“明理”,其意义还表现在对理学家文道观的反拨上。有些受理学家“明道”思想影响的文章,出现填塞或照搬先儒语录名言的情况,林纾对此十分不满。他曾这样解释《文心雕龙·征圣》中的“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这一句的意思,“何谓正言?本圣人之言,所以抗万辩也。何谓体要?衷圣人之言,所以铸伟辞也。”他认为,遵守圣人之言,不是简单的记诵,而是正确的理解和运用。所以,在文章中引用或发挥圣人之道,不等于在文章中填塞语录,另外,也不是所有的文体都适合讲儒家之道、理学之言,“文至于语录,成万古正言之鹄,皆能一一施之文间耶?……古之文章家,本尽备各体,不必各体中皆寓以理学之言。”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林纾所强调的读书,主要指儒家的经典著作,但也不限于儒家经典之作,虽然,他并不主张泛滥杂家,“欲察其识度,舍读书明理外,无入手工夫。若泛滥杂家,取其巧思,醉其丽句,则与‘识度’二字愈隔愈远矣。”但从他在《春觉斋论文》所引用的书目看,其中不乏《庄子》《史记》《论衡》《淮南子》等这些非儒家的经典著作,也就可以知道他的读书与明理的范围是并不狭隘的。
综上,林纾对“明理”的理解,既包含了传统的“明道”内容,也包括了“致用”的成分,他把读书、明道、阅历、能力统合起来,拓宽了传统“明道”观对于“道”的认识和理解;通过对人生阅历和个人能力的强调,也把文章的“致用”功能吸收进来。既不把“道”视为人被动接受的内容,让道成为外在于文的客观对象;又将观念意义的“道”与现实意义的“用”打通,体现了对“道”在社会实践中的现实指导意义的尊重。
值得注意的是,林纾的文章宗旨论,在“明道致用”之外,还把表达情感作为文章的根本性要求而纳入到其统摄范围之中。一般而言,中国诗论比较重视情感的意义。尽管对于情感内涵的理解多有不同,但把情感视为诗歌的本质性要求却是一种共识。而对于文章,一般是把议论说理、状物叙事等视为其根本性特征。因此,林纾将抒情的使命赋予文章,这是他的文章理论的特别之处。比如,他赞赏《离骚》之文的“情深而语悲”;认为 “《骚经》之文,非文也,有是心血,始有是至言。”“试观《离骚》中句句重复,而愈重复愈见其悲凉,正其性情之厚,所以至此。”他论屈原的《九章·惜诵》:“由积愫莫伸,悲愤中沸,口不择言而发。惟其无可伸诉故沓,惟沓乃愈见其情之真;若无病而呻,为此絮絮者,便不是矣。”认为其文反复倾诉,似乎一意重复,但正因为情感强烈而真实,其反复倾吐,反而情愈真,文愈妙,“不实不真,佳文又胡从出哉?”
如果说楚辞一类的文体接近于诗,故强调情感也有其必然性,那么,对于叙事性的文章,林纾也同样看重其情感性。他举《史记·外戚世家》中窦皇后与其弟窦广国事为例进行阐述道:
文帝召见问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复问他何以为验,对曰:“姊去我西时,与我决于传舍中,丐沐沐我,请食饭我,乃去。于是窦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呜乎!史公之写物情,挚矣。今试瞑目思窦姬在行时,迨将入代。而稚弟恋姊如母,依依旅灯明灭中,囚首丧面。窦姬知此行定无可相见之期,计一身与稚弟相聚一晷刻间,即当尽一晷刻手足之谊,不能不向从者丐沐而请食。下一“丐”字、“请”字,可见杂沓之中,车马已驾,纷纷且行,窦广国身随其姊在行中,直一赘旒,不丐且不得沐,不请且不得食;沐已饭已,匆匆登车,亦不计弟之何属。此在情事中特一毫末耳,而施文之中觉窦皇后之深情,窦广国身世之落寞,寥寥数语,而惨状悲怅,已尽呈纸上。此即所谓“务似而生情”也。且“似”字亦非貌似之谓,直当时,有此情事,登之文字中而肖耳。
对于欧阳修的《泷冈阡表》,归有光《项脊轩志》,林纾也是从叙情而各有特点入手探讨其妙处,认为“琐琐屑屑,均家常之语,乃至百读不厌,斯亦奇矣。”“《阡表》步步叙悲,悲尽,皆其得意处,《项脊轩记》亦步步叙悲,然名位去欧公远甚,不能不生其萧寥之感,综之皆各肖其情事。”而对张惠言《先妣事略》“极意欲书其悲怀,然写情实不如震川之挚”提出批评。
林纾强调文章的情感性,是以作者本人的情感真实为基础的,如果作者没有真实的情感,无病呻吟,矫揉造作,文章也不会有感人的力量。“盖屈原怀忠而死,不得志于世者,往往托为同心,犹之下第之人,必寻取下第之人,发舒其抑郁之气……盖必循乎古义,有感而发,发而不失其性情之正。因凭吊一人,而抒吾怀抱,尤必事同遇同,方有肺腑中流露之佳文。”文章中的情感,除了要以作者情感的强烈真实为基础外,表达的方式也很重要。比如林纾重视文章的声调,但他不是从纯粹的声律角度来谈,而是和情感内容相关联。“讲声调者,断不能取古人之声调揣摩而摹仿之;情性厚,道理足,书味深。凡近忠孝文字,偶尔纵笔,自有一种高骞之声调。”因为情感深厚,遣词用语自然毕肖其情感口吻,读之自然声调和谐,情韵悠长。他举《史记·聂政传》为例对此加以说明:“政姊闻政死时,以妇人哭爱弟,其悲凉固不待言。然试问从何入手?而曰‘其是吾弟欤? ’其字一顿,是吾弟一顿,欤字是指实而不必立决之辞。继之以‘嗟乎’二字,实矣。‘严仲子知吾弟’五字,真声满天地矣。呼严仲子者,姊弟同感严仲子也。‘知吾弟’,吾弟断不能不为之死。……故善为声调者,用字不多,至复耐人吟讽。”所以,他不是从个别性的要求来看待文章的情感,而是从普遍性和根本性的要求上来谈论文章的情感特性的。
不过,林纾并未深入分析文章中的抒情与诗歌中的抒情在内容、方式和要求上有何不同,这是他在理论上的一个缺憾,不过,从他所列举的例证看,文章中的抒情一般是通过议论和叙事来完成的,或许,在林纾看来,这与诗歌抒情一般要避开叙事和议论,其差别是不言自明,无需讨论的吧?
二、《春觉斋论文》的文体论
文体论是文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自曹丕《典论·论文》首先提出文体的区分,以后经陆机、挚虞等人的努力,到刘勰《文心雕龙》和萧统《文选》,文体论逐渐成熟。在此后的文论发展中,随着文体的分化和新文体的不断出现,文体区分日趋细密,理论探讨也愈加深入。
林纾《春觉斋论文》中的“流别论”是文体论的专论,他吸收了前人在文体学方面的成就,并结合文体发展的实际,对十五类文体进行了全面的讨论。这些文体包括骚、赋、颂赞、铭箴、诔碑、哀吊、史传、论说、诏策、檄移、章表、与书、赠序、杂记、序跋,虽然类别不是太多,但基本包括了古文中最常用的文体。他的文体论基本沿袭了刘勰《文心雕龙》中“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阐述模式,对每类文体,都首先确定其内涵和特征。比如,“赋”这一文体,他先借鉴刘勰的界定,“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随后补充道:“一立赋之体,一达赋之旨。为旨无他,不本于讽喻,则岀之为无谓;为体无他,不岀于颂扬,则行之亦弗庄。”明确指出赋的两大基本要求:一是形式上的铺张扬厉;二是内容上的讽喻劝谏。
其次,结合对代表性文章的分析,对文体源流发展的过程进行梳理,并讨论各个时期文体的特点和得失。因此,“原始表末”与“选文定篇”是合在一起。比如“诔”这一文体。林纾先考察“诔”之起源说:
诔之最古者,凡两见于《左传》:一为鲁庄公之诔县贲父,一为鲁哀公之诔孔子。顾县贲父之诔,不详于篇;而孔子之诔,则用长短句,不尽出于四言。柳妻之诔惠子亦然,……今读其文,哀恻而多韵,今人之制哀辞者恒仿效之,盖诔之变体也。扬子云诔元后文亦四言。然则,四言实通用之体。
林纾认为,“诔”最早是见诸于《左传》的鲁庄公《县贲父诔》和鲁哀公《孔子诔》,前者原文已不存,后者以四言为主,兼用长短句,非纯粹的四言体。此后有柳下惠妻作的《柳下惠诔》,亦非纯粹的四言体,其文哀恻而多韵,后人制作哀词时多效仿此文,林纾认为后人的此类哀辞实为“诔”之变体。此后,扬雄作的《元后诔》用四言体,成为“诔”之定制。接着,林纾又讨论了诔在后世的发展,特别提到西晋文学家潘岳,“刘勰盛推潘岳‘巧于叙悲’,愚按《黄门集》所登哀诔之作,颇赡于他集”,认为他的诔成就最高,并连举四例加以证明。如评其为晋武帝司马炎所作的《世祖武皇帝诔》为“恋恩之情,溢言表矣。”为其岳父、荆州刺史杨肇所作的《杨荆州诔》为“自叙交谊,不期沉痛。……黄门以深情为人述哀,自能动听。”为其妻侄杨经所作的《杨仲武诔》,“夹叙风物,触目成悲,所谓叙悲之巧,或在此乎。”为马敦所作的《马汧督诔》,“尤悲愤有余音,且琢句奇丽。”从“诔”的发展情况看,魏晋时期是此类文体的高峰,潘岳又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林纾在此重点围绕潘岳的作品进行论述,是比较准确的。唐宋之后,诔的创作不多,且乏名篇传世,所以,林纾对唐宋之后的诔未加详论,而以“六朝有韵之文,自有不可漫灭处,不能以唐、宋大家之轨范绳之”一语作结,其态度是明确的。
在对每一种文体讨论的最后,林纾一般都会对此种文体进行总结,来说明此种文体的写作要求和原则,这相当于《文心雕龙》文体论中的“敷理以举统”。比如“流别论六”论“哀”“吊”两种文体,对“哀”的总结是,“综言之,哀词者,既以情胜,尤以韵胜。韵非故作悠扬语也,情赡于中,发为音吐,读者不觉其绵亘有余悲焉,斯则所谓韵也。”强调了“哀”体的写作要求是情韵兼赡,情为基础,韵为目标。对“吊”的总结是,“盖必循乎古义,有感而发,发而不失其性情之正。因凭吊一人,而抒吾怀抱,尤必事同遇同,方有肺腑中流露之佳文。”强调了作者必须与所吊之人有相同的遭遇或相同的情感共鸣,旨在借他人之事抒己之怀抱。总体来看,这些总结性的论断一般都言简意赅,切中肯綮。
林纾对于文体的论述,往往能结合文体发展的实际,将文体分化整合的具体情况予以条分缕析。比如,“记”这一文体,本身应用的范围就比较广泛,其下属的子类也很多,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分化也最复杂。林纾在讨论这一类文体时就不拘泥前人的类别划分,而能根据文体的实际情况灵活对待。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属于“记”体的文章统统和“书”放在一起讨论,而林纾则是把其中的“奏记”一类和“书”(林纾又称之为“与书”)放在一起,因为“记,奏记也。汉公府用奏记,郡将用奏笺,今则笺记己屏不用,通行者但名‘与书’。”奏记在后世已经并入“与书”,故可以放在一起讨论。而对于其他的“记”体文,则单列“杂记”一类。因为“杂记”与归入“与书”的“奏记”已经分流,另外,杂记一类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分类也较为复杂,具备单独成类的条件。林纾论“杂记”一类的具体情况是,“勘灾、溶渠、筑塘、修祠宇、纪亭台,当为一类;记书画、记古器物,又别为一类;记山水,又别为一类;记琐细奇骇之事,不能入正传者,其名为书某事,又别为一类;学记则为说理之文,不当归入厅壁;至游宴觞咏之事,又别为一类:综名为记,而体例实非一。”可见,“杂记”之中有很多都属于唐宋之后的新兴文体,它们在体例上的差别虽然较大,但在内容上又都有记事记物的特点,且无法归入其他文体,就将其统归“杂记”一类。
还有一些古代的文体在后世发展过程中使用了新的名称,林纾也会特意加以说明,如论“章表”说:“窃谓章表即今之奏议,古谓‘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今之体裁,唯伸贺谢恩,则仍用表式;其余奏议,通曰奏折。”此外,林纾还注意对某些文体古今的差别进行客观分析,以引起学习者的注意。比如他评价古今奏议的不同说:“古之奏议取直,今之奏议取密。直者,任气抒忠,以所言达其所蕴;凡德不聪,佥壬在侧,乱萌政弊,一施匡正,一加弹劾,不能以格式拘,亦不必以忌讳避。至于密之为言,则粉饰补救,俾无罅隙之谓,偶举一事,上虑枢臣之斥驳,下防部议之作梗;故必再四详慎,宜质言者则出以吞吐,故作商量,宜实行者则道其艰难,曲求体谅,语语加以骑墙,篇篇符乎部式。此安得有佳章表?”再比如“与书”,该类文体本来“辞主驳诘”,意在辩难,而到清代则成为“考订辨析学问”之具,林纾对此加以论述道:“清初大老,崇尚朴学,则以与书一门,为辨析学问之用,洒洒千言,多半考订为多;文家沿用其体,凡意所不宣者,恒于与书中倾吐之,读者几以名辈与书一门,为寻检遗忘之具,较之汉、唐规律,颇有同异。”这些论述都能切中要害,属于林纾文体论中颇有价值的部分。
三、《春觉斋论文》的艺术论
林纾论文重义理,强调内容醇正,这是他文论的一个显著特色。但他并未因为重视文章内容而忽视文章的艺术价值,相反,对文章艺术的讨论在他的文论中占据相当大的分量。他的文章艺术论多有独到之解,成就很高,是其文论中引人注目的部分。
《春觉斋论文》的艺术论主要集中在“应知八则”部分,根据对这部分所涉及的八个艺术理论问题的详细考察,我们认为可以将其整合为意境论、情韵论、神味论、趣味论四个方面,以下就此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意境论
一般而言,意境是诗词艺术理论讨论的重点。意境指作者在诗词中创造出的具有独特艺术效果和审美价值的情景浑融的艺术氛围,是诗词艺术价值和艺术创造成就的集中体现。在诗词意境理论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国维,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境界说”,认为“而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可见,王国维境界理论的核心是情感,真挚的感情是营造诗词境界的基础。而将意境作为文章艺术的追求目标,这是林纾古文理论的创见。他认为“意境者,文之母也,一切奇正之格,皆出于是间。不讲意境,是自塞其途,终身无进道之日矣。”在对意境的理解上,林纾与诗词理论家略有不同。诗词意境比较注重情感的内涵,而林纾文章学的意境则比较重视意,“文章惟能立意,方能造境。境者,意中之境也。”“意者,心之所造;境者,又意之所造也。”他看重意境的高洁,“故意境当以高洁诚谨为上着。”而要达到意境的高洁,就需要从“意”的培养做起。首先要读书,通过读书来培养学养,净化思虑,从而“把灵府中淘涤干净。”因为,“凡学养深醇之人,思虑必屏却一切胶轕渣滓,先无俗念填委胸次,吐属安有鄙倍之语? ”心胸得到了净化,心意才能远离鄙俗。当然,林纾注重的“意”,与理学家强调的“道”并不是一回事,因此,他提到的读书,不是记诵理学语录以充门面,而是沉潜涵泳于古人的经典,陶冶心灵,培养学识,即“泽之以《诗》《书》,本之以仁义,深之以阅历,驯习久久,则意境自然远去俗氛,成独造之理解。”可见,林纾提倡读书,并非死读书,读死书,而是与人生的阅历结合起来。读书而不运用于实践,就不能转化为一种真正的认识社会的能力,林纾称这种能力为“理解”。何谓“理解”?林纾认为:“理而曰解,即庖丁解牛之解,游心于造化,故能不触于肯綮”。也就是通过读书而培养起来的识见、学养、胸襟、气度,这是人的一种综合能力。所以,林纾强调的“意”不是一般意义的人的心意,而是“析理”与“镕裁”,是对人世间道理的审择裁断和融会贯通。因此,在林纾看来,主意即是主理,意与理相通。“凡无意之文,即是无理。无意与理,文中安得有境界? ”
但是,有了意不等于文章就有意境,还要考虑如何将“意”施之于文。林纾反对以“工巧”为文,“‘工巧’二字,亦文中一种伎俩,惟云言理,以工巧行之,自然至于着力。”一着力,就会显得矫揉。要“立言得体”,不仅文章的结构安排要自然,言理叙次也要不露痕迹。从这个意义上论文章,就要求文章有自己的个性和面目,而不必遵循固定的模式。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求文章的意与文章的体制相称,作者的个性与文章风格要应,不管是“海阔天空气象”,还是“清风明月胸襟”,都能“还他恰好地位”。而能到此地步,自然就能造境。因为,“不能造境,安有体制到恰好地位?”
从以上讨论可知,林纾的意境论主要的着眼点在于“意”,而非“情”,这是他的意境论有别于诗词意境论之处,带有鲜明的“文”的特色。此外,林纾的“意”建立在作者的修养,胸襟、学识和能力等方面,这与一般文章理论所强调的“道”也有不小距离。他把意所包括的这些内容又称之为“理”或“理解”,因此,在它看来,“意”与“理”是相通的。在意境的营造上,他特别强调文章中的“理”与文章体制及风格的相称,追求不落窠臼、不露工巧的自然之美。这都是理解林纾意境论的关键。周振甫先生对林纾意境论和王国维境界论曾进行比较说:“以意境为文之母,也和静安的论相合。不过讲意境而欲求进于道,这便和静安的见解不同了。静安以境界为止境,是言志派;琴南讲意境而求合道,是载道派,这是两者根本的差异点。”应该说,周振甫先生这一论断对理解林纾文章意境论的特征很有帮助,不过,将林纾简单的归入载道派,或许有意无意间忽视了其意境论中对文章艺术探讨的理论价值。
(二)神味论
文章而有神味,是对文章艺术魅力或艺术效果的极高要求。“论文而及于神味,文之能事毕矣。”按照林纾的解释,“神者,精神贯彻处永无漫灭之谓;味者,事理精确处耐人咀嚼之谓。”可见,文章的神味,是基于文章的内容,而又表现为文章的艺术的一种恒久的精神魅力和令人回味的审美享受,如古人所说的“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换句话说,文章神味的获得,既出于文章的思想,也源自文章的艺术,但最终达到的却是一种艺术的高度。如果读后言尽意尽,毫无余思,则文章不可能有神味。因此,神味的第一要求就是“藏锋不露,读之有滋味。”文章含蓄,耐人咀嚼;意不说尽,却能品味而出。但是,在林纾看来,含蓄也要讲究方法,遵循一定的原则,“临文兜勒,故说一半,留其一半在渺冥惝恍之中,令人摸索,直同猜谜,亦可名为味乎? ”也就是说,如果欲说不说,故作神秘,让人捉摸不透,文章就不是含蓄,也不能有味。另外,神味还源自作者内在的涵养,“积万事万理,撷其精华,每成一篇,皆万古不可磨灭之作。”作者的涵养,首先体现在道德修养之上。他赞赏韩愈“养其根而埃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烨,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数语,认为:“此数语得所以求神味之真相矣。”其次体现在学识之上,“观以下书辞,历无数辛苦,始归本乎仁义之途,《诗》《书》之源,乃克副乎前所言者。”另外,还体现在阅历和能力上,“纯从道理上讲究,加以身体力行,自然增出阅历。以道理之言,参以阅历,不必章絺句饰,自有一种天然耐人寻味处。”“不过味者,不悖于道理,不怫于人情,言皆有用之言,又皆可行之实。”因此,文章的神味,不可轻率而得。神味虽是文章艺术上的体现,但归根结底却是对作者素养能力的要求。不仅在表达上要含蓄,而且还要求作者在修养上下功夫,除了加强道德培养之外,还要多读书,多实践,道理深厚,事理精妙,文章才能令人心悦诚服,有涵咏不尽的神味。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林纾谈文章的神味,还主要偏在“味”的方面,而对 如何达到“神”却所言甚少。在具体的论述中,又主要偏重从作家的修养和文章的思想等主观方面来谈神味,而从艺术营造的技术层面(如用词、句法、章法、修辞、艺术手法,等等)谈论神味并不多,另外,谈神味而不离事理和教化,也过于正统和保守,比如他说:“《六经》《语》《孟》之言,匪不有味,亦以融汇万理万事,衷之以道,故亘万世不能轻易其一字。”“不知言神味者,论行文之止境也,至于明道、立教、辅世成俗,则道德发为文章之作用,又非但言文、法矣。”不仅把儒家经典视为神味之作的范本,而且,又与理学家的文道观扯上了关系,显出他在理论上的矛盾和局限。
(三)情韵论
情感是林纾对于文章宗旨的根本要求,但至于如何由对文章情感的强调而达到文章“情韵”的目标,则属于艺术论要关注的问题。他引《玉篇》“声音和曰韵”和《正韵》“风度也”来解释“韵”。风度本用于指称人的外在气质和仪态,是人的内在素养的外化,后逐渐用为文论术语,指文章用辞造语、声韵节奏的形式之美与情致意趣的内容之美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整体性的气度和风采。有情韵的文章自然也有风度。林纾认为,文章要获得这种艺术之美,首先情感必须平和、温厚、纯正,“然必有性情,然后始有风度,脱性情暴烈严激,出语多含肃杀之气,欲求其情韵之绵远,难矣。”“凡性情不正者,决亦不能有此正声。”其次,情感要真挚感人。“非本之真情,万无能动之理。”杨慎评欧阳修的文章是“清音幽韵,如飘风急雨之骤至”,林纾认为这是对欧文的误解。“凡情之深者,流韵始远,然必沉吟往复久之,始发为文。若但企其风度之凝远,情态之缠绵,指为信笔而来,即成情韵,此宁知欧文哉?”情感要经过反复的沉吟酝酿,才能有悠远绵长的韵致。此外,林纾认为,文章的情韵还要建立在内容充实,表达自然的基础上,反之,内容空洞,叙情草率,则不会有情韵之美。“盖述情欲其显,显当不邻于率;流韵欲其远,远又不至于枵。有是情,即有是韵。体会之,知其恳挚处发乎心本,绵远处纯以自然,此才名为真情韵。”“若临文时故为含蓄吞咽,则已先失自然之致矣,何名情韵?”
为了说明情韵的特征,他引汉元帝报贡禹的诏书来说明:
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鱼之直,守经据古,不阿当世,孳孳于民,俗之所寡,故亲近生,几参国政。今未得久闻生之奇论也,而云欲退,岂意有所恨与?将在位者与生殊乎?往者尝令金敞语生,欲及生时禄生之子,既已谕矣,今复云子少。夫以王命辨护生家,虽百子何以加?传曰:亡怀土,何必思故乡!生其强饭慎疾以自辅。
贡禹是汉元帝时代大臣,以直言敢谏深得元帝赏识,后贡禹以年老子少为由欲辞官回乡,元帝遂下此诏予以慰留。文中情感温厚真挚,情韵深长,感人至深,林纾对此文大加赞赏,“观此诏中语,宛转温裕,若慰若勉,数行中回环往复,挹之无尽,情韵何若,读者当自知之。”认为这样的文章才符合他心目中的“情韵”的要求。
除了从文章的情感内容方面谈情韵外,林纾还从语言的角度谈情韵。“须知情者发之于性,韵者流之于辞。”文章的情韵除了决定于情感内容外,还与文辞的使用大有关系。《宋书·谢灵运传论》称:“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他解释其原因道:“《汉书》中之情韵,虽偶然涉笔,亦断非他史所及。孟坚喜用“矣”字,“矣”字之下恒蓄无穷之思。”当然,班固长于情理之说的原因不止于此,林纾在此不过但举一例而已,但起码说明了文章语言的运用对情韵的意义。他分析“矣”字的用法说:“鄙意虽名决辞,言外须有沈吟惋惜之意,则用‘矣'字方有余味。”又引《汉书·食货志》中“矣”字的使用说:“《食货》一传屡用‘矣’字,只加议论,令人醰思,言外皆有不足时政之意,深可寻绎。”比如,“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一句,林纾认为:“此结束上文农夫苦况,取贷商人,商人不耕而坐吸农夫之膏血,朝廷不能禁,用两‘已’字,足以两‘矣字,生出无穷慨叹之意。读者似认为本文之顿笔,实则非是;用一‘矣’字,即所以动朝廷恤农之心也。”我们且不讨论这里对商人的批判是否合适,只分析这句话中两个“矣”字的作用。“矣”在这里虽是表达语气的虚词,但在这句话的特定语言环境中,的确体现了作者的一种情绪和愿望,蕴含着对农民疾苦的无限同情,对商人不劳而获,盘剥渔利的愤怒以及渴望朝廷能够体恤百姓的期望,情感强烈而鲜明,意蕴婉至而深厚,读来有令人回味悠长的效果。林纾认为,这种对文字使用的讲究,正是班固长于情理之说的一个重要原因。
《春觉斋论文》的“用字四法”是讨论文章用字方法的专论,体现出林纾对于遣词用语的重视,虽讨论的是一些具体而细微的用字问题,但反映在文章的艺术创造上,却大多与文章的情韵有关。所以,在这一部分的最后他特别提醒说:“以上诸条,语极细碎。然留心古文者,断不能将虚字略过。须知有用一语助之辞,足使全神灵活者,消息极微,读者隅反可也。”除了“用字四法”之外,林纾还在“用笔八则”和“论文十六忌”中,通过对用笔技巧以及文章应避免的文病的讨论,也涉及到不少与文章情韵相关的问题,限于篇幅,此不赘言。
(四)风趣论
一般而言,风趣属于一种文章艺术风格,但在林纾的文章理论中,风趣却被视为一种普遍性的艺术标准,特别对于某些特定的文体而言,这种要求更强烈和突出。
林纾认为,“凡文之有风趣者,不专主滑稽言也。”文章之风趣,不同于滑稽。像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这类文章,虽寓含讽喻,但专以幽默为目的,与风趣不是一回事。文章的风趣不能刻意和勉强得之,须作者见地高,有精神,把握运用文字的能力强,又能“在不经意中涉笔成趣”,方为妙手。他引《史记·窦皇后传》中窦皇后与其弟相认时,“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一句分析说:“悲哀宁能助耶?然舍却‘助’字,又似无字可以替换。苟令窦皇后见之,思及‘助’字之妙,亦且破涕为笑。求风趣者,能从此处着眼,方得真相。”林纾认为这个“助”字之所以用得巧妙,正在于它似得之于不经意间,又不可替代,但又饶有风趣。在文章风趣方面最为林纾称道的是班固,认为“其风趣之妙,悉本天然。”比如《汉书·陈万年传》记万年临终前病榻上教导其子陈咸,语至半夜,陈咸困极瞌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耳。’”对此,林纾分析道:“乍读之,似万年有义方之训,咸为不率之子,乃于‘教’下着一‘谄’字,吾思病榻中人亦将哑然失笑,矧在读者。此盖以一字成趣者也。”陈万年是西汉宣帝时大臣,善于谄媚逢迎,其临终教子,本一极庄重严肃之事,而班固在此用一“谄”字,且借其子之口道出,细思其意,实寓极丰富之内容,不仅令读者知晓其教子之方,且于冷峻的语调中饱含讥讽之意,极具风趣之妙。可见,文章有无风趣之妙并非取决于文章所叙内容本身是否有趣,而取决于作者的能力,即使是严肃的内容也可以显出风趣。比如《汉书·王尊传》记王尊之言曰:“五官掾张辅,怀虎狼之心,贪污不轨,一郡之钱尽入辅家,然适足以葬矣。”王尊斥责五官掾张辅贪腐之状,直欲将一郡之钱尽攫囊中,罪不容诛,班固在此不用“杀”而用“葬”字,不特显出张辅罪孽之重,且从侧面说明张辅自以为聪明却反误其身的事实,“使罪人寒心,复能使旁人解颐。此等词令,求之唐以下不能有也。是能于严冷中见风趣者,尤不易辨及。”由此可见,风趣确为文章的一种艺术要求,它不像“规模间架”等外在形式那样有迹可循,易于模仿,而取决于作者的艺术能力和水平,所以,林纾也不能不感叹“风趣之妙尤不易学。”
当然,对一般作者来说,文章之有无风趣有时也确实存在文体上的差异,故林纾也承认“当因题而施”,大致上说,篇幅较小的文章比篇幅宏大的文章更适合风趣。以苏轼为例,虽然风趣是其诗文艺术的突出特征,但如果从其创作的具体情况看,在题跋一类篇幅较小的文体上,这一艺术特征体现的更突出,所以,“大篇文字宜本庄重,虽东坡通才,亦当恪守规矩。”但是,对于有些人而言,却往往不受这种限制,比如班固。能够“于史传中作趣语,而又不碍于文体,此所以独成为孟坚也。”所以,在这一方面,班固在林纾心目中的地位要高于苏轼。这也说明,风趣确为艺术上之极高要求,非一般人可以达到。
另外,林纾认为,追求风趣应该本之自然,以“见诸无心者为佳。”如果刻意追求风趣,“便走入轻儇一路。”像公安派的袁宏道,一生病痛正在于此。
四、余 论
通过对《春觉斋论文》六个部分具体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其文论的建构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展开的。大致上说,前三部分属于宏观问题的论述,后三部分则是微观问题的分析。比如第一部分“述旨”,基本上围绕文章写作的目的和宗旨这一根本性问题进行阐述,这一部分也可以视为林纾文章理论的总论。第二部分“流别论”,主要是对不同文体的特点及写作原则的论述,确立了林纾文章理论的体系框架。第三部分“应知八则”,主要是对文章艺术基本问题的讨论,这是林纾的文章艺术论。而其中的“意境”“神味”“情韵”“风趣”四部分是其艺术论的主干,“识度”“筋脉”“声调”“气势”四部分则是前面四个核心内容的补充和展开。比如“识度”主要讨论文章的立意、炼意、达意,是对“意境”理论的补充。“筋脉”讨论文章的脉络与篇章结构的安排;“气势”讨论文章“敛气蓄势”的原则,两者都与文章艺术论中的“神味”相关联。而“声调”则围绕文章语言与抒情的关系进行论证,是艺术论中“情韵”论的进一步展开。
《春觉斋论文》后三部分大量讨论的具体细节问题,主要涉及文章创作与批评的一些具体技巧和方法。比如“论文十六忌”主要分析文章写作中常见的问题以及如何避免这些问题。“用笔八则”主要探讨文章内容的层次安排,包括起承转合、衔接停顿、补充收束、繁简搭配等问题。“用字四法”则主要介绍一些具体的用字技巧。这三部分的内容,是林纾文章创作与批评实践的经验总结,在论述过程中,还结合了大量的例证,非常便于读者的接受和理解,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只有理解了林纾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进行理论建构的结构特点,才能抓住《春觉斋论文》理论体系的实质与根本。
《春觉斋论文》中所讨论的这些技巧法则,是该书中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内容。一般而言,文论家们都不太重视技巧法则的总结,认为太过关注具体法则会对学习者造成约束和局限,从而使文学失去创新的动力,这也为历史上很多文学思潮或流派最终走向衰落的事实所不断证实。但林纾却并不讳言技巧法则,他自言“若不讲行文之法及文之意境,则先无去取之能。即有先辈之名言,古书之辞义,亦何从使之道达得出?”他对法则的重视,一方面出于他在长期文章实践中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也出于“延古文一线”的使命担当的意识。身处新旧文学激烈交锋的历史旋涡,他清楚地意识到古文在未来必然走向衰落的命运,但作为传统古文的殿军,他又不甘心自己所热爱的古文从此被时代抛弃,所以,他才极力想通过一己之努力来担负起挽救古文的重任。他的《春觉斋论文》对于古文理论的建构,以及其中大量的技巧法则则的总结,就是这一努力的具体体现。正如他的弟子朱曦胄评价他的《春觉斋论文》说:“皆先生自揭其生平辛苦所创获,而尽宣之于世,将使世之诵法古人者,咸审乎立言取径之道。”客观来说,他的这些法则,有些确有失于琐碎或武断之处,但从总体上看,对于研习古文者的阅读和写作,还是有一定的帮助和指导意义的。
除了文章理论的阐发之外,他还选编评点了大量的古文选本,如十卷本《中学国文读本》;二卷本《左孟庄骚精华录》;十卷本《古文辞类纂选本》;十五册十六种《林氏选评名家文集》,一套六册《浅深递进国文读本》等,作为学古文者阅读及写作的指导和参考。另外,他还举办各种形式的古文讲习班,广召生徒亲自讲授古文,并发行《文学常识》《文学讲义》《史记讲义》《文章流别》《文学史》等函授教材。可以说,他是一位真正集理论、创作、讲授、普及于一身的文章大家,虽然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变革中他站在保守的立场,未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而且,他的复兴古文的理想也未能实现,但若从文化的保存和总结的意义上来审视他的工作,则他的付出仍是有意义和值得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