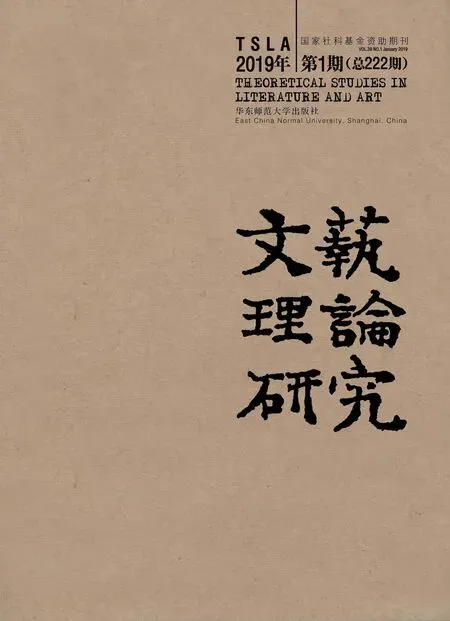文化研究的物质回归: 托尼·贝内特治理性视域下的文化与社会
2019-11-12徐小霞
徐小霞
英国著名学者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是当代文化研究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学术思想已成为文化研究的又一个重镇。贝内特依托福柯后期的“治理性”政治思想,提出“文化治理性”和文化政策研究,为当代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成为文化研究从事实践操作的重要立论依据之一。近年来西方人文社科领域整体出现回归物质主义的趋势,贝内特立足后现代立场,引领推动的文化研究新物质主义转向,尤其需要给予一定重视,因为正是贝内特率先在文化研究领域建构的关于新物质主义命题的系统理论话语和方法论,敦促物质文化研究获得了独立性。贝内特对文化研究新物质主义转向的重要建树以及系统思想往往为国内外学者忽视,为此,本文全面挖掘梳理贝内特新物质主义议题的全貌,并对之作出辩证的评析和思考。
一、缘起
由于治理性视角化了的“文化”被贝内特界定为“既表现为管理的目标,又表现为管理的工具”(“置政策”99),前者意指艺术审美形式,后者是宏观层面的人们的生活方式,联接两者的节点则是治理权力。为此,阐明治理性、社会交往(the social,又译为“社会层面”)和文化三者间的具体联系机制是贝内特进一步深化其文化政策思想面临的理论任务,同时,也是将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的联系起来的关键。更重要的是,在对“文化”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解决上,贝内特还开创出既富含物质与实践内涵又不同于政治经济学模式的另一种“文化生产”思路: 视文化为人类与非人类各异质因素动态聚合产生的结果,强调文化的物质性动态生成过程。贝内特将这一生成过程称为“聚合中的文化”(Assembling Culture)。
解决治理性、社会交往和文化三者的关系,涉及以治理性视角重新赋予“文化”和“社会交往”(the social)新的含义,重构两者间的关系。具体而言,贝内特将法国后结构主义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简称ANT)与福柯的治理性融合一起,提出“聚合中的文化”(Assemb-ling Culture)观点,以突出“文化”和“社会交往”的动态物质生成过程,赋予两者更具物质性和实践性的含义,揭示文化实践如何借助知识-权力的毛细血管调控和形塑社会交往和社会行为。这就与以意义和意指实践为基础的当代文化研究主流模式拉开了距离,显示了贝内特不满文化研究基于语言-符号学模式的文本唯心主义及其诱发的政治后果,积极探索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深度模式的新物质主义和历史化研究的决心:
我的定位是唯物主义的,它的含义一如布赖恩·穆恩(Brain Moon)所提出的:“物质主义的”这个词语现在应当“在一种有限的意义上展开,以表明一种分析方式,它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基础放在历史条件之中,而不是去建构一种在更为基础的原因之上的普遍的效果和表达。因而它与历史唯物主义不同,这里重在强调偶然性,即多种历史条件和力量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社会生活和形式,而非遭受任何普遍决定力的制约。”“赞成这种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的文化研究,便是赞成文化研究将自己的关注点细致化、分化,具有一种密度历史的意味: 去关注文化和权力具体关系的特定构成和功能,将它们理解为复杂的相互作用的条件和结果,以及引起的弥散的和复杂的组织效果。”(Bennett,Culture
:A
Reformer
’s
29)贝内特的新物质主义定位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回应当代文化研究第二次范式危机作出的应对策略和理论范式调整。20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理论范式自霍尔以降兴起了“文化转向”,“文化转向”一味夸大建基于语言表意系统的话语实践对社会结构的自足性和建构性,逐渐悬置了对经济分析和社会物质存在等根本问题的思考,抹杀了“社会”“社会交往”“文化”三者的界限,呈现出非历史主义的唯文本、泛文化的唯心倾向。文化研究的第二次范式危机其实质与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归属这一核心问题有关,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最初得益于马克思的思想,从这个角度而言,文化研究是关于意识与经济(存在)、文化与社会间关系的研究。由于文化研究内部倚重的各种理论视角不同,对“文化”与“社会”这两个术语的理解存在着许多相互冲突的认识,“对文化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解释从来就不是一致的或固定的”(《本尼特》11)。
纵观文化研究对文化与社会(society)及其关系的探讨,实则是一个为反对经济决定论、不断扩大文化自足能动性而稀释“社会”的物质实在性的过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社会形态理解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的有机整体,经济基础的性质变化决定着上层建筑和社会形态的变化更替。虽然马克思承认文化和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但认为它们依然最终受到作为结构性存在的、超个人的社会有机整体的决定和制约。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里,“社会”(society)既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有机体和不同构成层次相互关联的总体结构,也意味着一个与自然世界不同的属人的世界,它表现为一种以物质生产关系为基点的物质性存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蕴含着深刻的客体与主体间的实践辩证法,但这种深度等级决定论模式的逻辑预设沿袭了西方哲学传统思维与物质的二元结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暗含着人类与自然、主体与客体间二元性预设。
阿尔都塞力图进一步释放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物质效力和相对能动性,把马克思的“社会整体”结构说重新阐释为一种关系性构成而非实体存在,赋予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和文化以相对自治的地位,认为文化与意识形态渗透在社会大厦各部分间,具有胶合剂的作用,它维系并再生产社会关系。虽然阿尔都塞突出了文化与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结构各层次的复杂关联和相对自治,但他仍然坚持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力这一深度模式。他说,马克思的社会整体观是“某种复杂性构成的、被构成整体的统一性,因而包含着人们所说的不同的和‘相对独立’的层次。这些层次依照各种特殊的、最终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规定,相互联系,共同存在于这种复杂的、构成的统一性中”(107—108)。
同样,雷蒙德·威廉斯进一步强调文化的相对自主性与实践能力以规避刻板的经济决定论,呼吁一种“文化唯物论”,但他还是坚持文化依附于并被阶级关系所决定,而后者源自生产关系的经济结构。雷蒙德·威廉斯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明确了文化的物质实践性和自主性。与文化属于精神、意识等形而上层面,物质则是实在、存在的形而下的这种二元观念相反,威廉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强调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物质或一个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理解形形色色的物质、文化和文学等的生产。我把这种立场称为文化唯物主义。”(Marxism
5)威廉斯认为不但实物的生产是一种劳动实践,而且智性活动和作为想象性产品的文化的生产也是一种劳动实践,它们也具有改变、影响、介入人们生活的物质作用。威廉斯的文化唯物论强调文化在改变和影响社会生活方面所具有的物质实践力量和能动效应,强调文化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间的复杂关联性。“社会”对威廉斯而言同样是一个结构性总体概念,文化塑造阶级意识的同时也被社会总体结构所规定。威廉斯指出,“文化”概念融合了“两种反应: 其一是,承认某些道德与智性活动实际上有别于那些推动新社会发展的力量;其二是,强调这些活动——作为集中体现人类兴趣的领域——其地位不仅高于那些注重实效的社会判断过程,而且它们本身还具有缓冲和整合后者的作用”(《文化与社会》6)。威廉斯既强调文化改变和影响现实社会的物质实践性和能动性,又看到了社会与文化间的区别,以及社会对文化一定程度的规定性,使文化唯物论富含合理的辩证色彩。威廉斯的文化唯物论依然为经济基础最终决定上层建筑这一深层模式留出了适当空间,实质上未能彻底摆脱物质与意识二元关系的旧逻辑;并且,在威廉斯的文化唯物论中,实现文化的物质实践效能主要依托意义和意识为中介,由此强化了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批判地位,开启了英国文化研究的文本性方向。
威廉斯、汤普逊和霍加特等人在批判刻板的经济决定论同时,格外推崇文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能动作用,这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传统。随着霍尔等人用葛兰西霸权理论对英国文化研究“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范式之争作出调停之后,英国文化研究在80年代受到各种“后学”思潮的冲击和影响,逐渐转向“后现代”,密切关注身份政治问题。
霍尔从福柯、拉克劳等人的话语理论中汲取了相应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又兼取德里达的“延义”思想,构筑出以语言—符号学为基础的一套理论话语,如“表征”“接合”“身份政治”等,将文化理解为符号、表征系统或“意义之图”,认为社会、经济、政治都是通过文化意义得以界定和建构,各社会集团间的利益之争便是利用符码和意义定义自身、他人的位置以及为世界争夺命名权益的意义之争。文化在霍尔等人那里发挥更重要的建构作用与自主性,具有能动地塑造和组织经济、社会、政治关系的实践能力,甚至文化的自主能动性被抬升到第一位的“准决定”地位上,“文化总是一种在场,并且是第一位的,存在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实践之中,还从内部构建它们”(《本尼特》204)。在此,社会结构对文化的制约性和规定性似乎已荡然无存。可以说,霍尔几乎悬置了“社会”(society)而不论,代之以基于符号-语言论模式的文本性构成的“社会交往”(the social,又被译为“社会性”)概念: 由话语和意义建构的身份位置和其随一定语境变化而不断被链接、再链接的一套变动不居的社会关系。
在此,有必要简要厘清society和the social的词义及指涉。此二者词义十分复杂,甚至有时被混为一谈。威廉斯在《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指出,“society”现在有两个主要意蕴,“一方面,它是一个普遍的用语,用来表示一群人所属的机制(institutions)与关系(relationship)。另一方面,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用语,用来表达这些机制与关系被塑形的状态”(446)。这里,“society”的普遍用语接近于“the social”含义,即人们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它的抽象含义则接近马克思、阿尔都塞等人的社会总体结构概念。从社会学角度而言,这两个词具有各自的适用范围与含义,虽然词义的变化会依据不同学者的视角而有所变化。社会学通常将“社会”(society)作为一个统一的、有着确定边界的实体,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而“社会性”(the social)只是作为这个物质实在的一个层面而存在,“social”强调社会的集体性范畴而与个人“personal”相对,强调“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社会互动模式与社会关系模式”(阿雷恩·鲍尔德温等7)。因此the social又被译为“社会关系”“社会范畴”,均指涉构成“社会”的一个虚拟维度而与“the economy”“the political”“the national”并置。
霍尔的“the social”也指涉人们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但这种关系主要是以符号和意指系统为基础的“身份位置”关系。霍尔宣称:“然而我却要说,社会(the social)‘如’语言般运作。当语言之比喻是重新思考许多基本问题的最佳方式时,就会有一种从认识其效用和力量到认为它实际就是如此的滑移。”(霍尔 陈光兴)霍尔意义上的“社会关系”融入文化意义上的、变动不居的一套意义关系之中,由此抽空了“the social”概念中非意义指向的人们的实际社会行为和物质实在性,结果是,不但文化建构着且规定着“the social”,而且基于变动不居的意义关系之上的“the social”取代了社会(society)和社会结构等实体存在纬度。霍尔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为规避经济决定论,以意义为基础的“the social”消解了实体结构的“society”的本体地位,在思维与物质的两极上走向主观的意识层面这一极端,夸大了文化和意义对社会、经济、政治等的建构作用和能动性,完全抹杀了经济和社会对文化的结构性规定作用;并且由于将“文化”指认为一种表征实践,它仅在抽空了历史条件的语言符号层面在运作:“文化的功能像一种语言,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个意义生成机制”(《本尼特》213),抽离了“文化”自身形成和运作的具体历史条件,致使文化研究走向唯文本和意义分析的唯心主义认识论。不但使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陷入范式危机,而且带来的直接政治后果是把注意力放在文本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上,将文化完全归结为政治,社会政治被贬斥为文化政治而缺乏实际有效的政治行动和政治干预能力。
二、回归物质
针对文化研究理论范式面临的文化唯心主义危机,贝内特以福柯的治理性为视角,重构文化与社会交往(the social)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将文化、社会交往的理解重新置于物质性、实践性的方向上,试图扭转文化研究的唯心主义误区。不过这一回归由于立足于后现代立场,它拒斥社会与文化或者说物质与思维间深度模式的二元论和决定论,赞成平面模式一元论的物化生成实践过程。
首先,贝内特对“文化”与“the social”概念的思考全部纳入福柯的治理性视域,对它们的含义重新语境化,呈现“文化”和“the social”如何参与治理权力的控制与实施,并成为治理性的一部分,或者说成为治理统辖的重要领域。福柯认为现代统治的主要形式是治理性:“我们生活在一个治理术的时代[……]治理术的问题和治理技术已成为唯一的政治赌注,已成为政治斗争和政治竞争的唯一真实的空间。”(福柯92)“治理性”概念指“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以及使得这种特殊然而复杂的权力形式得以实施的计算和手法组成的总体,其目标是人口,其知识形式是政治经济学,其根本的技术工具是安全配置(apparatus of security)”(福柯91)。治理性用政治经学之类的科学知识分析和管理人口,它依据不同对象,设置相应的特定目标,采取尽可能精微准确的策略和手段,反思或分析可作用于个体或集体的行为的可能性领域的一种“引导性”行为方式(徐小霞,“简析福柯”65),即对行为的引导(the conduct of conduct)。治理性是一个充满实践色彩的术语: 它既是在思想意识层面对治理实践的体系性反思(福柯称之为“治理理性”),其自身更是一种具体的物质性活动与实践——针对人口的行为的可实施领域的各种权力技术活动,这些权力技术活动是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发挥作用,“在一个复杂的组织、实践、计划和集合的过程中”建构主体和具体的社会结构(《本尼特》206)。为此,治理性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必然要落实在具体的物质存在中,它在一个具体的技术框架里组构人、位置、文化资源、建筑环境,并且在身体、行为方式、存在方式等具体物质层面建构主体,改造人们的社会行为。
以霍尔为代表的新葛兰西主义虽也吸收了福柯权力观,但主要吸收了话语分析理论,贝内特认为霍尔对福柯的话语理论的吸收并不全面。霍尔将福柯的话语分析与语言学的意指系统所发挥的作用结合起来,以支持自己的文化赋予世界意义和建构世界的认识,却没有注意到福柯的话语分析背后有一整套技术、知识、权力、机构等的实践性干预和物质支撑,正是后者在建构主体性和社会交往、赋予世界意义方面发挥着至为关键的作用。贝内特认为,有效的文化分析应当从话语受到的一整套权力技术干预层面而非仅话语的意义表征起步,这些权力技术、知识在具体历史情境下“建构了具体的人,并且同样重要的是,建构了标准相同的某种具体的社会结构”(《本尼特》206)。
如此,贝内特便把文化和社会交往的探讨从思想意识层面的语言、表征这一问题域转移到话语和表征得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上。换言之,如果说文化研究坚持话语创造现实和建构主体性的话,贝内特却认为话语和表意系统反而是权力统治现实的技术手段之一。对贝内特而言,这个权力便是“治理性”,语言和文化不仅仅是一种释义现象,它们更是治理的智性技术,文化即治理技术和治理手段之一。主体性的构成是治理技术与知识以及程序、手段的结果,重点应该是对这些技术、程序和手段以及运作机制做出历史性描述,而非解释语言在建构身份和位置差异关系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文化是什么,它怎样运作: 必须把这些问题与具体的历史关系中的文化实践的运作相对比之前回答它们。”(《本尼特》205)
与此相应,“the social”也不是霍尔等人认为的为文化和意义所建构并被文化表征的差异性身份关系,相反,它是治理性借助各种技术(包括文化技术)针对的一系列关系和行为领域,这些关系和行为领域依据特定治理目标以特定方式而被问题化,成为治理的对象和领域(Bennett,Critical
Trajectories
78),“社会交往在此被解释为某些问题——态度和行为——的一个具体的‘星丛’(constellation),它起源于与众不同的统治策略”(《本尼特》212)。被问题化的关系和行为源自多个源头: 真理游戏、嵌入它们中的社会装置和一定的治理规划。这些被问题化的关系和行为构成了具体专业知识运用各种技术形式以针对的平面。因此,社会交往(the social)依据不同的治理规划和不断被问题化的行为领域而境遇性、历史性地变化着。贝内特这里的“the social”是指治理性视角下的、被问题化和需组构的社会行为领域,与福柯对“the social”的界定一致。福柯认为“the social”指“为谋求某一群体人们的福祉和社会保障而应该被加以组织的社会行为。”贝内特与福柯意义上的“the social”强调治理性与社会行为领域,具有境遇性、弥散性、实体性的特征,霍尔的“the social”虽也是境遇性、弥散性的,但侧重于语言意义层面建构的人们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缺少社会行为的物质维度。相比霍尔,贝内特将“the social”概念重新落于境遇性的实体坐标系上,豁显其物质性内涵。
那么,如何说明治理性视角下的文化与社会交往的关系?贝内特认为,文化首先是一套对社会交往(the social)产生影响,进而改变某些社会行为的自我治理技术。而社会交往则是一些依据不同治理目标和策略而不断发生变化的、被问题化的态度和行为。文化之所以能作为治理技术,是因为以人口的生命、健康、福祉为目标的治理性是现代主要的统治形式,它必然也需要文化(狭义的文化含义如高雅艺术等)为治理的手段。对贝内特而言,文化被铭刻在一套内在于制度的管理网络的历史始于福柯所言的具有管治(police)特征的现代社会,管治将与人口和生命有关的一切如生存状况、存在方式、行为模式、思维方式、习俗逐渐纳入一个积极而庞大的管理网络,文化是管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文化既是管治治理的手段技术,也是管治治理的目标。当文化概念纳入有关治理性的思考中,那么“文化的概念及其与社会交往的关系正是由此而得到分析”(《本尼特》209)。因为,文化的人类学意义(人们的整体生活方式)使文化与社会交往的关系以一种不变的和适应所有历史和社会的形式而被理论化: 正是在“文化即人们的整体生活”这一预设下,治理性才能以“文化”(高雅艺术等狭义意义上的文化含义)的名义依据不同的治理目标,不断将某些被问题化的社会行为(the social)纳入需要文化(狭义的文化含义如高雅艺术等)去治理的范围内。因此,“文化是一套特定的技术,通过具体目标对社会交往起作用”(《本尼特》212)。在这意义上,文化是治理技术: 它作为“一套独特的知识、专门知识、技术和组织实现的,它通过与权力技术相关的符号技术系统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通过自我技术的机制的运作——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社会交往起作用,并在这种关系中与其结合”(《本尼特》214)。
文化作为治理技术与其他治理技术相比,有自己较为突出的特征: 文化技术是与统治技术相关的符号技术与自我技术的融合。贝内特围绕“文化”,对福柯关于真理游戏采用四种主要技术来理解人类自身的相关论述作了进一步发挥,指出福柯对“文化层面”(the cultural)的探讨与符号系统技术、权力技术和自我技术联系了起来。福柯认为任何技术包括符号技术并不能独存,它们只有与其他技术尤其权力技术关联才能运作,“这些技术都是训练和改变个体的特定方式,不仅改变某种技巧而且要求改变某种态度”(Foucault 225),它们使主体客体化进而影响社会交往(Critical
Trajectories
81)。据此,贝内特指出文化层面便是“自我技术”,即“个体以自己的手段或借助他人的帮助,对自己的灵魂、身体和存在方式发挥作用,达到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者不朽的状态”(Foucault 225)。但文化层面的自我技术必须与符号技术与权力技术融合才能运作,换言之,文化主要是自我技术,它借助符号技术通过对自我的行为的改变而最终作用于社会交往。治理性视角下的文化技术机制的运作主要是与符号技术和一定治理规划相关的,它对自我行为的可能性领域(the conduct of conduct)施以影响进而改变社会交往。
确定了治理性视域下文化与社会交往的关系,以及文化作为治理性的自我技术的特征后,贝内特还需在理论上进一步说明文化作用于社会交往的具体机制,这个问题实际涉及文化领域内的微观权力-知识与宏观的社会(社会交往)层面如何联系问题,也即微观权力-知识如何建构出宏观的文化对社会交往的干涉界面。福柯的经验研究核心论题主要探讨权力与知识的共谋关系,但他没有在理论层面阐明知识是如何与权力结合的,更未对微观的权力-知识与宏观的文化与社会交往的联系机制给予明确说明。在文化与社会交往联系机制问题上,贝内特面临着福柯遗留下的难题。
法国学者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简称ANT)对科学知识实践的运作和对社会交往的建构等议题为贝内特思考知识、文化与社会交往三者的联系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撑。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启迪下,贝内特以治理性视角完成了以下两项工作: 首先,把文化和社会交往看作动态的物质生成实践过程,在本体意义上赋予两者更具物质性和实践取向的含义,提出文化是人与非人等各异质因素聚合过程的生成结果,贝内特将这一过程称为“聚合中的文化”(Assembling Culture)。其次,阐明知识实践行为建构文化层面与社会层面,以及文化作用于社会交往的具体机制运作原则。贝内特在后现代立场,重申文化的物质主义,以平面一元论取代了威廉斯、霍加特等人深度模式的二元论文化唯物主义,又在本体论上挑战了霍尔等人视文化为经验、表征等精神层面的主流观点,拓展了“文化”的物质与实践内涵;在文化研究领域建构了关于新物质主义命题的系统理论话语和方法论,推动了“文化研究的物质转向”;同时就权力理论创新而言,在文化研究领域深化发展了福柯关于知识-权力这一核心论题。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是法国拉图尔(Bruno Latour)、卡龙(Michel Callon)、和约翰·劳(John Law)等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巴黎学派提出的一种新理论纲要。行动者网络理论站在人类与非人类一元论立场探讨本体的生成过程而非固化的实体存在。其核心体认,任何个体,无论有生命的人类还是无生命的物质,包括人、实验仪器、机器、植物、动物、文本、建筑……都以各自的存在和活动积极参与到对社会交往(the social)和现实世界的建构生成中,生成过程是一个包含着自然、人类社会等多元系统的多实体,多结构的复杂系统。行动者网络的问题域主要围绕科学实践展开,它将科学实践理解为一个动词,一个在实践中的建构过程和各种异质因素聚合的动态网络。在这个异质因素集合的网络建构过程中,人与自在自然都以行动能动者的姿态积极介入、相互磋商、彼此依赖,重塑客体和主体,安德鲁·皮克林提出:“我们应该把科学(包括技术和社会)看作是一个人类力量和非人类力量(物质)共同作用的领域。在网络中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相互交织并在网络中共同进化。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图景中,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是对称的,二者互不相逊。”(11)这种异质性聚合的网络总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其中每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导致整个网络的变化,各因素通过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变化而被不断重新界定,为此这个网络总是偶然的、际遇性、多变的、历史性的和多样的聚合。正是通过这种建构过程,知识、社会、自然的区分开始形成,并暂时性地稳定化。
拉图尔反对将人与非人、科学与社会强行划分为不同的领域,而是需要保持对两者的对性态度,其中任何一方都没有绝对优先权,“因为一个争论的解决是社会得以稳固的原因,因此,我们不能用社会来解释一个争论是如何解决和为什么解决了的。我们应当对吸收人类资源和非人类资源的努力加以对称的考虑”(《科学在行动》418)。拉图尔反对视“社会性”为一个固有不变实存的传统观念,认为所谓的“社会性”是科学知识建构的结果而非原因,在知识实践建构过程中很难区分何者为自然因素何者为社会因素,它们彼此交融互构,构成一个异质因素集合的动态网络。为此,分析的重点不应是用社会或自然的结果说明科学实践,而是追踪科学知识的行动和形成中的社会,说明科学实践如何重构社会与自然的生成过程。行动者网络理论以整体论的视角重构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认为科学与社会是共生互构、不可分割的无缝整体,这为分析两者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有益视角。它鲜明的实践辩证维度和对整体性、物质性、历史性的强调,为贝内特扭转文化研究的文化唯心认识论,从物质与实践的角度审视知识、社会交往与文化三者间的联系机制提供了立论依据。
贝内特在ANT和知识科学研究视角的启示下,突显“文化”与“社会交往”的被建构过程和偶然性生成而非既定不变的实存之特点,认为两者都是一个实践辩证的生成过程的概念,一个物质和人类等为能动者互动共构的生成过程,处在自然、社会、技术等异质因素聚合的无缝动态网络中。在这个异质因素的聚合过程中,各种人与非人的异质因素相互作用、磋商再通过转译逐渐获得了暂时性的稳定状态,也即获得了文化层面与社会交往层面。这就是说,不能从结果而要从生成过程本身认识文化与社会交往的含义,文化不是由表征、意义、言说等文化材料构成的,社会交往也不是社会实体,而是各种异质能动者的聚合和建构的结果。文化的出现是人与非人等行动者相聚合的产物,正是这一聚合过程使文化成为有别于社会交往、经济的构形,这便是贝内特意义上的“聚合着的文化”概念:“[……]文化的聚合(assembly)也与经济的生产有相似的机制: 用约翰·劳的话说,这种聚合是一个在物质形态上异质因素的网络,由零碎的谈话、建筑、身体、文本、机器等等构成,它们相互作用来建构和表现为‘文化’,并组构文化与经济、社会交往和政治等层面的关系。”(“Making Culture” 617)
由于文化、社会交往、经济、自然等都是人与非人行动者的异质聚合过程建构的结果,因此它们间的区别不是本体论的而是公共组构所致: 其聚合与再聚合的不同方式、地点使得事物、人类、文本、建筑、技术等的相互关系发生变化,从而引发了各因素彼此关系重新被界定并由此生产出不同的领域——文化、社会交往、经济等等(“The Work Of Culture” 5)。在生成文化的同时,也相应生成了与文化有关联社会交往、经济及其相互关系。整个过程中,知识起着准动力的重要作用: 拆解旧的聚合组织,发动新的聚合过程,而新聚合过程中的客体发动一定的权力以相互博弈、协商,不断建构或重塑出文化、社会交往、自然、经济等等层面及其相互关系。
就文化与社会交往的关系而言,“聚合着的文化”的生成过程不仅建构重塑出“文化”,它也同时依据不同的治理目的,建构出“文化”可以作用于社会交往的某个现实界面,或者说生产文化的同时也生产出被知识格式化的、依据具体治理规划,使得文化以特定方式作用于社会交往及其文化可以针对治理的社会界面的一个过程(“Making Culture” 625)。例如,美学作为一种知识实践,它的生成过程便是通过文化聚合网络,建构和发动起艺术品和艺术实践,起到为达到某种治理规划而去改造问题化了的某些生活方式的作用。可以说文化知识实践等智性活动界定和等级化了各种文化实践的不同价值,例如“文化批判”作为智性实践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文化知识话语(人类学、艺术史、物质遗产研究、民间文化研究、考古学、历史、自然科学、美学、文化等等),这些知识在话语∕机构的使用与部署中,通过文化批判这一智性实践的操作、技术程序,构成一个物质与非物质,人类与非人类聚集的异质性网络,按照不同的治理规划和策略,生成出某种特定的文化实践与形式,用以规约个体的身体践行,卷入被治理所问题化了的社会交往的关联中。总言之,知识实践通过异质性因素的聚合网络,捕获和建构活生生的现实,也建构出“文化”“社会交往”及其两者的相互关系,“从科学研究角度看,新的社会能动者的生产和‘作用于社会交往的界面’都源自具体知识体系中的智性和技术程序”(“Making Culture” 626)。
知识实践如何具体建构被文化格式化(作用)于社会交往的界面?贝内特对此并未再予以详细的理论阐述,只是勾勒了几条简要的原则纲要:
1. 从实践过程本身而非存在结果看待“文化”与“社会交往”及其区别。文化与社会交往的区别不是已然成形的文化材料或社会材料,相反,两者都是人类与非人类能动者异质聚合网络过程的生成结果,其区别主要是因公共组构的方式、地点的差异而形成的不同层面,这并非本体论上的差异。这样,贝内特不但把文化、社会交往理解为人与物质、文化与社会相互渗透的实践过程,还将两者置于同一平面上,而非一个是前景(文化)一个是背景(社会)的深度模式的关系,也非一个是表征一个是现实的镜像关系,这不但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与文化的二元对立,也与威廉斯、霍加特为代表的文化唯物主义保持了距离。
2. 制作“文化”并使之区别于“社会交往”的关键因素是机构的作用(如博物馆)。因为正是在机构内,文化被生产并被文化知识格式化为可作用于社会交往的界面。机构内的一系列手段如分化、排序、积累等编码行为,赋予某些特定的材料与实践以“文化性”。贝内特强调机构是文化聚合网络的“必经点”,起着核心作用,即在文化聚合过程中,各种异质因素资源通过“转译”,其角色定位、位置关系、兴趣利益被重新问题化并组合、界定、构成文化性的形式与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机构是各异质行动者成功转译,成为文化性形式的必经之点。“转译”和“必经之点”都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关键概念,用来说明网络连接的具体方法,“转译将两者完全不同的存在形式——自然和文化——混合起来”(《我们从未现代过》12)。转译是角色的转换和界定,“只有通过转译,行动者才能被组合在一起,建立起行动者网络,在网络之中,行动者之间被期望能建立起稳定的关系”(郭俊立106)。“必经点”是转译过程和转译能否成功的必然条件,它能汇集各种因素和资源,动员各种转译方法达成改变各因素角色、塑造新的角色位置的目标。拉图尔曾说“给我一个实验室,我能举起世界”,这意味着实验室对拉图尔而言是整个社会的必经点。同样,贝内特也认为文化机构是文化领域的必经点,在文化生产过程中有着本体的地位而非无关紧要的环境背景。
3. 一旦文化通过聚拢过程暂时获得静止的制度化形式,便与和它有别的社会交往相关联起来: a.实施聚拢的文化知识同时也形塑所聚拢之物的文化特征。b.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和技巧为了解、探刺和格式化社会交往的界面提供了可能,并为作用于社会交往的行为提供了可能。c.文化和社会相关的知识实践生产出可运行于社会交往的现实界面。如胚胎科学数据通过辨别和分析男性酗酒者,直接改变了英国的家庭社会(“The Work Of Culture” 6)。
三、反思
相比文化研究以往的文化观,贝内特的作为异质聚合过程和动态网络的“文化”,其特征何在?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本体意义上打破人与物的界限,突显人类与非人类的物质间共融互构的整体性、能动性、过程性,强调文化构成中的物质因素的能动地位,如机构、技术、建筑、仪器……,它们不但是文化的本体构成因素,而且还对文化、社会、主体乃至世界具有直接的生成作用。以往文化观包括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虽承认有着物质载体的文化符号有建构世界的物质效用,但这一效应的实现与发挥则需仰仗意义和主体意识为中介才能实现,“文化”在本体上仍属于精神范畴的意义、经验、表征、话语等。相比文化研究的文本主义,贝内特的文化观在本体论上更突出了物质实体性。
其次,贝内特把“文化”与“社会”看作一个动词,一个在实践中行动的过程,一个知识实践参与其中的生成过程,在这动词中,文化和社会即是人与物等异质因素聚合的动态网络,网络“这个概念比系统更加韧性,比结构这一概念更富历史性,比复杂性这一概念更富经验性”(“The Work Of Culture” 4)。这与以往文化认识论从结果和成品来理解文化和社会概念的观点截然不同。前者瓦解了物质与思维、人与物的二元对立的深层结构模式,强调文化与社会的历史性、境遇性、偶然性、多变性、偶然性和实践性,后者秉承近代西方哲学物质与思维二元性的逻辑预设,视文化与社会为固定不变的既定成品和实体。在此意义上,贝内特的文化与社会概念更具历史性和实践取向意味。
再次,在权力分析和文化政治上诉诸治理实践的合理性,“文化”和“社会”生成过程中赋予物质以行动元地位和直接参与治理权力的实施和控制的能力,突显具体机构和知识实践的各种物质操作对于建构和调适文化、社会和政治的节点作用,如此一来微观的日常实践和宏观的社会经济层面在人与物质的无缝循环中被有效链接,解决了福柯遗留下的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难以弥合的理论问题。在此意义上,相比局限于文本性的意识形态批判政治,贝内特勾勒出更具有实践参与性质的机构政治。
虽有上述理论突破,并不意味贝内特治理性视域下的“文化”与“社会”议题在学理上不存在问题。最突出的是对“文化”和“社会”的界定及两者关系问题上存在逻辑上的断裂和理论缺陷。贝内特为了引入治理性视角,分别吸收威廉斯的文化观和福柯对“the social”的解释,前者又分别指涉人类学意义上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一般意义上的高雅艺术,按贝内特对文化的理解: 文化既是治理的工具(高雅艺术充任治理的工具手段)也表现为治理的目标(改造人们的生活方式以适应治理规划);后者(福柯的“the social”)意指为谋求某一群体人们(population)的福祉和社会保障而应该被加以组织的社会行为,贝内特强调“the social”是某些被治理规划所问题化的人们的社会行。如此,日常生活方式意义上的文化概念便与治理目的有关的“the social”概念相重合,为前者所包容,唯一区别是有无被治理权力所捕获干预。但是威廉斯意义上文化主体是“人们,the people”,这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其内涵还囊括了人们的思想、意识、情感、经验等方面。福柯在论述治理性概念时指出,治理术是近代以来为谋求人口(population)的福祉而采取的知识、技术、手段等,换言之治理术施与的主体是“population”,福柯的“the social”的主体也是“population”,福柯理解的population(人口)属于经济学、统计学等知识话语的专有名词,一个量化客观的范畴,它被知识话语所捕获和现实化时仅指涉人数,不包括经验、情感、思想等主观内化因素。众所周知,“文化”不论指涉人们的生活方式还是高雅艺术,其得以成立的前提依然侧重经验、情感、思想意识等方面。贝内特为引入福柯的治理性概念,突显文化的物质纬度,混淆the people和population的用法,更未在理论上解决两者可能存在的关联性,如此一来,不但“文化”概念丧失了其存在依据,而且也使治理性视角化的“文化”与“the social”间的关系变得问题重重。
另外,贝内特将文化、社会、经济、自然等看作一个无缝之网的整体,一个处于同一平面的异质因素聚合的动态网络和生成过程的暂存性结果:“文化、社会、经济的区别不是实体性的,而是部门性的,聚合过程中的所有物质碎片在本体上都是物质碎片,都由同样的异质因素构成。”(“Making Culture” 19)这虽然瓦解了上述各领域间的鲜明界限和深度等级模式,认为“文化”与“社会”“经济”在本体上一样,它们的区别仅是临时性的,由于生成过程中的组构的方式、地点的差异造成各自的区别。即便如此,贝内特未在理论上阐明“文化”与“社会”“经济”间相互区别的临时性界限何在以及具体体现等问题。
最后,文化政治诉求上,贝内特以福柯的治理性建构自己的机构政治,完全取消了文化政治的核心问题: 意识形态。贝内特反对文化研究领域文化研究的表意政治,认为它不足以解释文化形式和文化事件的制度背景,指责文化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是一种意识政治,由此转向文化治理性的运作机制、手法策略等条件。马克思主义并非仅是意识政治,它用意识为手段最终反抗的是基于经济不平等的生活工作等的物质状况。(徐小霞,“作为治理技术”139)贝内特完全抹杀意识形态批判的政治功能,表明他的文化政治存在一定的偏颇与不足之处。
结 语
贝内特为扭转文化研究的文本唯心论,在人与物无缝融合的动态网络中考察物质、文化事件、社会功能之间的循环过程,不但丰富了文化研究领域关于“物”的内涵,还积极建构了关于新物质主义命题的系统理论话语和方法论,拓展了文化研究物质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路径。
贝内特融合治理性视角和行动者网络理论,以知识实践如何作用于文化与社会交往为问题核心,在文化研究领域沿着福柯的知识-权力的思路,在理论上开创性地探讨了权力与知识如何结合、两者如何作用文化与社会交往等具体机制,给当代学界在知识-权力这一重要议题上以一种新颖视角。同时,贝内特的文化生成观绕开经济生产路径,另辟蹊径地从知识、权力、异质因素聚合的动态产网络入手,这种不同于政治经济学模式的文化生成论,为文化研究从经济政治学模式之外思考文化生产提供了新的线索。
注释[Notes]
① 关于文化治理性的详述见拙文“作为治理技术的博物馆: 托尼·贝内特的博物馆政治思想”,《上海大学学报》1(2016): 128—39。
② 马克思关于“社会”的思想,本文参考了肖瑛的观点,见“回到‘社会的’社会学”,载《社会》5(2006): 1—56。
③ the social在本文中被译为“社会交往”,这一译法沿袭王杰等人在《本尼特: 文化与社会》中的译法,但笔者认为,the social译为“社会性”更为精准些。
④ 对the social的这一认识参考了肖瑛“回到“社会的”社会学”一文的观点及文中注释5,载《社会》5(2006): 1—56。
⑤ 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是福柯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有着丰富复杂的外延和内涵,篇幅所限此不赘述。详见拙文“简析福柯的‘治理性’概念”,《文化与传媒》6(2013): 64—68。
⑥ 参见王杰、徐方斌:“美学·社会·政治: 托尼·本尼特访谈录”文中的注释2,载《文化研究》3(2011): 101。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路易·阿尔都塞: 《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Althusser, Louis.Reading
Capital
. Trans. Li Qiqing and Feng Wenguang.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1.]阿雷恩·鲍尔德温等: 《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2004年。
[Baldwin, Elaine, et al..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
. Trans. Tao Dongfeng, et al..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4.]托尼·贝内特:“置政策于文化研究之中”,《文化研究读本》,罗钢,刘象愚主编。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2—110。
[- - -. “Putting Policy into Cultural Studies.”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 Eds. Luo Gang and Liu Xiangyu.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0.92-110.]- - -: 《本尼特: 文化与社会》,王杰等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Bennett, Tony.Tony
Bennett
:Culture
and
Society
. Trans. Wang Jie, et al..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7.]Bennett, Tony.Culture
:A
Reformer
’s
Science
. Sydney: Allen and Unwin; London and New York: Sage, 1998.- - -.Critical
Trajectories
:Culture
,Society
,Intellectuals
.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2.- - -. “Making Culture, Changing Society: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Studies’.”Cultural
Studies
21(2007): 610-29.- - -. “The Work of Culture.”Journal
of
Cultural
Sociology
1.1(2007): 31-48.米歇尔·福柯: 《安全、领土和人口: 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7—1978》,钱翰、陈晓径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Foucault, Michel.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
ège
de
France
,1977-1978
. Trans. Qian Han and Chen Xiaoji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0.]Foucault, Michel.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Essential
Works
of
Michel
Foucault
,1954-1984
. Ed. Paul Rabinow.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郭俊立:“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及其哲学意蕴评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2007): 104—108.
[Guo, Junli. “Actor-Network Theory of theParis School and an Analysis of Its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2(2007): 104-108.]斯图亚特·霍尔 陈光兴: 《后现代主义、接合理论与文化研究: 斯图亚特·霍尔访谈录》,2008年5月6日。2017年10月12日。〈http://staffweb.ncnu.edu.tw/hdcheng/articles/postmandcs.htm〉
[Hall, Stuart and Chen Kuan-Hsing. “Postmodernism, Theory of Articul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6 May, 2008.12 October, 2017.〈http://staffweb.ncnu.edu.tw/hdcheng/articles/postmandcs.htm〉]
布鲁诺·拉图尔: 《科学在行动: 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刘文旋等译。北京: 东方出版社,2005年。
[Latour, Bruno.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 Trans. Liu Wenxuan, et al.. Beijing: Oriental Publlshing House, 2005.]——: 《我们从未现代过: 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等译。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
[- -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Essays
on
Symme
-trical
Anthropology
. Trans. Liu Peng, et al.. Suzhou: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2010.]安德鲁·皮克林: 《实践的冲撞: 时间、力量和科学》,邢冬梅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Pickering, Andrew.The
Mangle
of
Practice
:Time
,Agency
,and
Science
. Trans. Xing Dongmei.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雷蒙·威廉斯: 《文化与社会》,高晓玲译。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
[Williams, Raymond.Culture
and
Society
. Trans. Gao Xiaoling. Changchun: Jilin Publishing Group Co., Ltd., 2011.]——: 《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5年。
[- -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 Trans. Liu Jianji.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5.]Williams, Raymond.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徐小霞:“作为治理技术的博物馆: 托尼·贝内特的博物馆政治思想”,《上海大学学报》1(2016): 128—40。
[Xu, Xiaoxia: “Museum as a Governmental Apparatus: On Tony Bennett’s Politics of Museum.”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1(2016): 128-40.]——:“简析福柯的‘治理性’概念”,《文化与传媒》6(2013): 64—68。
[- - -. “A Brief Analysis of Michel Foucault’s ‘Governm-entality’.”Culture
&Communication
6(2013): 6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