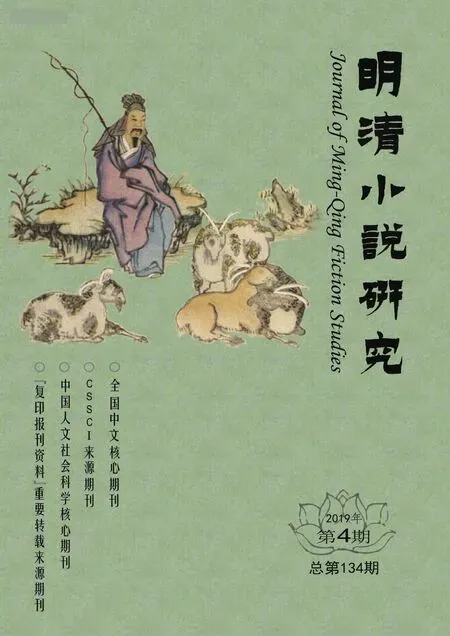《宣讲博闻录》:圣谕宣讲小说的集大成者
2019-11-12周宝东
·周宝东·
内容提要 自康熙的“圣谕十六条”颁布后,雍正又颁布了阐释十六条的《圣谕广训》,并将宣讲圣谕作为一项制度确立下来。为了使宣讲更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就出现了一批文学作品。《宣讲博闻录》就是其中成就较高的一种。本文从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入手,深入文本,对《宣讲博闻录》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进行了分析,尤其是该书在“重写”方面所进行的尝试,可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丰富的经验。
《宣讲博闻录》是清末民初的一部短篇作品集。该书由广东西樵云泉仙馆藏板,光绪十四年(1888)调元善社辑刊,广州板箱巷翼化堂承印。《宣讲博闻录》共收59篇作品,其中除《郑板桥寄弟保坟书》为收录之郑板桥书信外,其余58篇均为短篇小说。这部作品集的出现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和鲜明的时代背景。
一、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
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原先处于文化边缘的满族统治了中国二百多年,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当然得益于清朝统治者对汉文化的认同与阐发。而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却被忽视了,那就是一场持续了二百余年的圣谕宣讲活动。这场全民参与、旨在“化民成俗”的文化活动对于传统文化的保存与发扬起到了关键作用。
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宣讲活动已经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隐而不彰。除非是专门研究清史或近代史的人,当代已很少有人知道还曾经有过这样一种由国家发起、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文化活动。即使是在清末民初,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不断加剧的时候,圣谕宣讲活动也没有中断,甚至在溥仪退位后,有一些地方还在坚持进行类似的活动。
清朝的圣谕宣讲制度是在顺治、康熙和雍正祖孙三代里逐步完善的。清朝建国后,很多制度都承袭了明制。明朝自开国皇帝朱元璋制定“六谕”后就建立了宣讲制度。顺治九年,顺治将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六谕”照搬过来颁发。顺治十六年,建立乡约,并举六十岁以上德业素著之生员(秀才),或素有德望六七十岁之平民统摄,每逢朔望,申明六谕,旌表善恶。此为清代“宣讲圣谕”之始。顺治还御制《劝善要言》一书行世。康熙九年,康熙颁发了较之“六谕”更为详尽的“圣谕十六条”,作为化民成俗的根本。这十六条是:
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
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
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弥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
康熙“圣谕十六条”一开始颁布时并没有着意进行宣讲,而仅仅是让一般民众周知,故而还谈不上时间问题。“特颁上谕通行晓谕八旗包衣、佐领并直隶各省督抚转行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务使军民咸知尚德缓刑之意。”到康熙十八年,浙江巡抚陈秉直呈奏折,一是报告自己“恭绎上谕,逐条衍说,辑为《直解》一书”,同时恳请皇帝将此书刊印,分发天下,“州县有司,每逢月朔集在城绅衿耆庶亲为讲究”,远在四乡僻野之处的人,则“令其地方之品行端方之士各就公所,每逢月朔集讲一次”。康熙同意刊刻《直解》,但对于宣讲并没有给予明确答复。在康熙二十四年的陈廷敬的奏折里提到“虽一经张挂晓谕,而乡村山谷之民至今尚有未知者”。从中可以看出,很多地方并没有宣讲,而仅仅是进行张挂,所以崔维雅在《讲读圣谕以宏教化事宜》里提到了这一问题,认为“圣谕十六条”虽好,但如果好东西写在书本里,人民因为不识字看不懂劝惩至理,也听不到对于“十六条”的讲解,等于将朝廷的一番美意束之高阁,起不到实际作用了。可见,在康熙年间,虽有部分地方进行了圣谕宣讲,但是仍处于一种自发的忠君爱国意识,圣谕宣讲还没有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这一点还可以从雍正五年的一道上谕中看出来,“想来谕旨颁发各省者,不过省会之地一出告示而已,而州县各处并未遍传,至于乡村庄堡偏僻之区更无从知之矣”。于是到了雍正七年,皇帝正式下谕旨,每月朔望宣讲两次。同时规定,要在全国各地成立讲约之所。从此,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活动走上了正轨。
雍正元年秋间的时候,雍正就开始将十六条逐条注释,并准备在次年的秋冬颁发。加之在披览奏章的时候,雍正发现许多命案中,多以小事而起,酿成命案后,当事人追悔不及。“此皆由于愚贱乡民不知法律,因一朝之忿,贻身命之忧,言之可为悯恻”。意识到康熙十六条里“讲法律以儆愚顽”一条具有更为强烈的现实意义,所以着刑部将《大清律》内殴杀人命等条摘出,并加以说明,刊刻散布全国张挂。而《圣谕广训》的刊刻传播成为当务之急。《圣谕广训》是将康熙圣谕十六条逐条进行衍说,将原本的112字扩充为万言。到了雍正七年,皇帝正式下谕旨,每月朔望宣讲两次。同时规定,要在全国各地成立讲约之所。最后定下“每月朔望,齐集乡之耆老、里长及读书之人,宣读《圣谕广训》,详示开导,务使乡曲愚民,共知鼓舞向善”。从而将宣讲圣谕十六条及《圣谕广训》作为一种国家制度确立了下来。
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时局的动荡激发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忧国之思,他们纷纷寻求走向富强之路,许多人还梦想着通过《圣谕广训》来指导民众的生活。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就设想把圣谕宣讲作为“训俗”的重要手段,并且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情况,即城邑、乡村和“海外通商各埠”。在城邑逢三、八宣讲,在乡村,三百户以上就设立公所,而在海外通商各埠,则就地建立书院,“或由领事延聘达人,或由领事自莅,每逢朔望及礼拜日期逐条宣讲”。同时一要做好听讲者的参加情况,二要为听讲者提供免费的饭食。还特别强调了宣讲之人既要品学端粹,又要辩才无碍,方能建功。
郑观应的对策设想固然没有可能在那个时期实现,但是在现实中,却有很多地区在自发地践行着他的设想。如在四川和岭南,圣谕宣讲活动开展得就较为成功,影响很大。并催生了一种小说类型,出现了“圣谕宣讲小说”。“圣谕宣讲小说”这个概念首先由耿淑艳提出。她认为“这类小说以康熙颁布的圣谕十六条为主旨,通过敷衍因果报应故事,使百姓潜移默化地接受圣谕的思想观念。这类小说是宣讲圣谕十六条时使用的故事底本,或是在宣讲圣谕的基础上加工编撰而成”。姚达兑则称其为“圣谕小说”,并将其与解释《圣经》的传教士小说合称为“圣书小说”。
在晚清刊刻的这类书籍,较为有影响的不下三十种。这种小说刻本在很多地方都有留存,而其中成就较为突出者,当属岭南。岭南因为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处于边缘地位,到了清中期,岭南文化崛起。到了晚清,尤其是鸦片战争后,许多小说家从事了圣谕宣讲小说的创作工作,“试图利用中心文化中最具权威、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作为武器,来抵抗外族入侵,消除内部动乱,从而达到维护岭南完整的目的”,也确实取得了较高成就,而其中文学成就较高的,当属《宣讲博闻录》。
二、《宣讲博闻录》的思想内容
《宣讲博闻录》作为圣谕宣讲小说系统的组成部分,在思想内容上,既有该类小说的一些共性,又有自己的独特性。
第一个特点是强调发挥小说“文以载道”的社会功能,为推动中心文化做贡献。这是圣谕宣讲小说最大的共性。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在明清兴盛起来,有相当一部分作家认识到“文不能通而俗可通”的道理,自觉将小说作为一种劝善惩恶、化民成俗的工具,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社会作用。而小说有时也确实能够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如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中说:
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宣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
在《宣讲博闻录》的序言中,整理者将这个主旨说得非常清晰:
天下古今之事,情理而已。顺乎人情,合乎天理,其事以传,其人其地亦与之俱传。《圣谕十六条》括典谟训诰之全,理义灿陈,而情文无不曲尽,家喻而户晓之,诚化民成俗之极轨矣。然尽其鼓舞之神,必兼微求乎往事,自来宣讲劝化所以首将圣谕开其端而继及于因果报应之事也。夫世情好尚,大都厌故喜新。坊刻诸篇每以习见习闻而忽略,本集所辑非敢惊为新奇,第博采往事之传闻于理有不刊、情无不尽者,引伸其说加以断论,一以劝善,一以惩恶,于化民成俗未尝无小补云。
小说的辑录者认识到了“圣谕十六条”的价值,如果每个人都能将此十六条作为言行标准,那么就可能出现民风淳朴、民德归厚的理想局面。同为西樵云泉仙馆编的《善与人同录》中论及《宣讲博闻录》时说:
圣谕十六条,垂为典则,大邑通都,家喻户晓。诚欲天下苍生,各尽乎人生当行之道,天下苍生,恭行圣训。尽乎人,不必惑于神;尽乎人,自能格乎神。长治久安之功,基于此矣。
编辑者希望这些劝惩故事成为国家治理的辅翼,为长治久安奠定基础。《宣讲博闻录》也正是秉承着这样一种社会责任感,力求最大程度地发挥小说的教化功能,终极目的是“为国家兴教化,为万世植纲常,为乡党端风俗,为宇宙正人心”。这也是在那个国家动荡的年代,还有那么多有识之士主张宣讲的一个重要原因。只不过当时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已经陷入了列强环伺的局面,宣讲活动已经处于无力的衰退期了。
第二个特点是体现出编纂者对“孝悌”思想的偏重。《宣讲博闻录》以“圣谕十六条”为分类标准,被分为16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不同篇目的作品进行支撑,但篇目分配并不均衡。每一部分篇目的多寡,显示出作者们根据当时的社会实情和需求所做的判断与取舍。在这16部分59篇小说里,第一条“敦孝弟以重人伦”占了9篇,之所以会出现这个局面,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原因的。清朝强调是以孝治天下,康熙还亲自做过《〈孝经〉衍义》。其实满族在入关前就有很好的孝悌传统。康熙年间太平府繁昌县知县梁延年刊刻了宣讲类书《圣谕像解》,得到康熙肯定,作为官定本分发各省。该书也是按“圣谕十六条”进行分类,共20卷,其中第一条“敦孝弟以重人伦”独占5卷,篇目共80条。剩下的15卷所含篇目加起来一共180条。由此可见清朝对“孝”的重视与提倡。
第三个特点在于表明了一种儒、释、道三教杂糅,三教并尊的思想观念。该书由云泉仙馆编,云泉仙馆本为吕洞宾的道场,属于道家。但是编纂者却并没有将内容局限于道家,而是将三教并尊。
本馆同人,何以重视此书?盖以其能救人心于陷溺,挽狂澜于既倒,而内容则以普渡众生为主题,举凡各界,均有启示……将此人道做到尽头处,在儒则为圣,在道则为仙,在释则为佛。
从内容上看,广引三教经典。如儒家的《孟子》《礼记》《尚书》等,佛家的《坛经》,道家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吕祖》《武帝宝诰》《太上感应篇》,并叙述吕祖、关帝感应事迹。在《夜行万里》一篇中,虽是写关帝显圣,却引用《孝经》《孟子》《尚书》《左传》等儒家经典。也有专写六祖惠能的《孝子成佛》。这些都表现出整理者兼收并蓄的宽阔胸怀。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整理者有着非常清醒的观念,对那些“阴窃释道之名”的假和尚、假修行人也给予了抨击与揭露。如《正吉邪兄》,就写了许多假和尚的故事。
第三个特点是《宣讲博闻录》富有广东地域特色。书中写广东或和广东有关的篇目有18篇,占了总篇目的三分之一,分别是:《夜行万里》《事母异闻记》《苦节保孤》《难兄难弟》《义农一子承双嗣》《顺母桥》《乞儿奋志》《孝子成佛》《正吉邪凶》《犯法根于贪》《雪糕石饼》《守正兴家》《拐嫂》《诚心感弟》《狱中义卒》《匿粮谋产》《济施化盗》《轻言陷命》。这些篇目主要写的是广东人的故事,个别也有外地人在广东的故事。有些甚至就是身边人讲述的故事,如《犯法根于贪》的开篇就说:“里人蔡子厚,谓其客北江时,韶州城有冯日新者,贩毡、绸,往来曲江、南雄各埠。”可以断定,蔡子厚是广州人,整理者就是从他那里听来的这个故事。《顺母桥》则一改以往关于“顺母桥”的传闻,起到了溯本清源,以正视听的作用。

三、《博闻宣讲录》的艺术价值
较之于以往的圣谕宣讲作品,《宣讲博闻录》在艺术上的成就更为显著。
第一,作品编纂时有特定的体例。基本体例为:圣谕、《圣谕广训》、圣谕诠释(即“总论”)、小说(中间穿插一些评论,姑且称之为“断论”)、综论。以第一部分为例,共有《林氏家谱》《孝友家风》等9篇小说。目录之后即为“总论”。这9篇小说每一篇前都对应一篇“总论”。这些“总论”是小说编撰者结合圣谕与作品进行的一种“导读”,提醒读者或听讲人要关注哪些重点。如《林氏家谱》的总论,以“孝”的三条标准为主要论述内容:
夫孝有三:生则致其养,病则致其忧,祭则致其诚。斯之谓礼。
接着对这三条进行逐一解说,而这些和《林氏家谱》的内容有一定的联系:林志刚怙恃尽失后,忽然发现父母遗像,于是尽心供养,事死如事生,真正做到了“祭则致其诚”。又有其庶母庄氏抱病,他担心庶母撑不过去,为了能让她见三孙媳一面,林志刚“急为完娶”。这些内容都和“总论”有一定关系。有的“总论”更是直接点出小说内容,如在同属这一部分的《夜行万里》的“总论”里,论说父母生养子女不易,生命无常,人子要善体亲心,竭诚奉养。果能如此,苍天不负孝子。
即至出人意料之外者,无不所求如愿。夜行万里一事,可取证矣。
这些已经直接论述小说内容了。
“总论”之后即为小说文本了。在文本中,根据所写的不同叙述层次,时有“断论”,如小说集序中所说,“引伸其说加以断论”。这些“断论”有两个作用,一则深化主题,阐明主旨。如写林志刚季子林俊良娶亲之日,恰遇洪家娶亲,因风雨大作,迎娶之人误将洪家新妇抬回。林俊良因为夜已经很深了,就没打扰父母,将女子安顿好后,自己则“秉烛中庭,咏诗待旦”。
在这样的叙述节点,作者要将作品的思想主题进行申发,已达到劝善惩恶之目的。
妻非原聘,误入吾家,珠翠盈头,又胜己妇,况当洞房花烛,未免有情。他人处此,或将错就错,贪一夕之欢,贻终身之祸矣。俊良趋避于外,赋诗达旦,不愧秉烛通宵,又能安祖母之心,不惊双亲安寝,信乎德性坚定,少年老成,金玉君子也。
“断论”的第二个作用是解惑答疑,即对于小说中容易引起疑惑、误会的情节进行解说,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这种“断论”颇类似于传统的小说评点。
如林志刚的母亲岑氏临死前,托孤于庄氏。她并不反对庄氏改嫁,只是说请她改嫁之前,现将林氏血脉抚养成人。庄氏则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改嫁。最后岑氏哽咽难宣,指口而逝。针对这一情节,作者提出“断论”。
岑氏所嘱,一字一泪,虑付托之无人,信庄氏之可靠。其云“汝有异志”者,特反言以决之,非疑之也。庄氏素有肝胆,故一闻所嘱,直下承当,亦语语从血性流出,读之令人泪下。
原来岑氏用的是“激将法”,而庄氏也是一个奇女子,故而才能牺牲自己,保全林家宗嗣。而下一个“断论”更能明显地体现这种解惑性质。林志刚发现父母遗像,就将其置于室内,进行供养,每到祭日,还要隆重地祭祀一番,当日粒米不食。岑氏对此很担心。“断论”里对庄氏与志刚的行为进行了解读。
庄氏搁泪,远虑早识,诚恐自己哭坏,抚孤倍难。不知者以为忘忧,其知者以为有养。志刚披遗像而痛哭,平日不知多少慕思,郁而勃发,如汉明帝谒光武原,观太后镜奁中物,伏而悲泣,左右莫敢仰视。百官称其孝。今志刚年少如此,孝思尤为恳切。
一者对庄氏的行为给予了解释,另一方面则引用典故,对志刚的孝行给予肯定。
在《加惠农人》中,写林氏为了养活婆婆和三个儿子,耍手段赚得柳封翁银子四十两,作者在“断论”中两次为柳氏辩解。
林氏孝妇岂真爱惜余生,致此中途改节?但念姑老儿幼,使无权宜之计,则全家饿殍,更难为情者。看者当谅其苦心也。
林氏所为,似近串骗,然用心苦则机关出。使不通变行权,则姑子之存亡,有难逆料。亦俟后日之图报而已。乃或从而议之曰:“媒与林氏之言,两不相对,何难寻觅媒媪,质证是非。”而林氏有此奇智,料其出门时,曾与媒媪关说,著(原文如此,疑为“嘱”)其预为引避,且逆料柳翁忠厚,纵事后访知其伪,亦能曲谅苦衷,是林氏不特以节孝见重,而且以才智见长矣。
此处对柳氏行为背后的苦衷与大义给予了肯定,而且对故事中的疑团进行了解释,消除读者的疑虑。
在每一篇作品的最后部分,都有作者一段“总断”,结合作品中的具体人事,阐明义理,生发出符合“圣谕”条目的议论,或阐发儒、释、道三家的学说。有的篇目还说明了选录原由。如《郑板桥寄弟保坟书》只是简单介绍了郑燮的号与籍贯,然后照录了他的《寄弟墨》,最后简要地说明了郑板桥人生的境况,“后公登乾隆进士,官山东潍县知县。”紧接着就是最后的总结。
曲存无主孤坟,示子孙以永祀,比世之占坟盗葬,及霸冢灭骸者,其心术之异,相去何啻人禽。忠厚为怀者,自有心田福地,其发福可信之天理,不专凭地理也。此虽一事之微,与上篇存坟代祀,其忠厚相似,故并录之。
这篇简要说明了人应心存忠厚,自有福报。同时故事的作者或整理者会不时地露面,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是“圣谕宣讲小说”的一大特色。
第二,小说素材的来源丰富,《善与人同录》中说它“或取前书之所记,或采近日之传闻”,此评言简意赅。“或取前书之所记”,指从已经成书的作品中采撷素材,比较明显的是从《史记》《玄怪录》《坛经》《聊斋志异》《解人颐》《关帝圣迹图志全集》等作品集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在“取前书之所记”的过程中,又分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基本照搬。故事的主体情节不变,只是根据需要在某些细节方面做了适当调整。如《郑板桥寄弟保坟书》就属于照录,而其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夫妻贤孝》《正气诛邪》与《河伯娶妇》。

《夫妻贤孝》讲述陈锡九夫妇的传奇故事。和《陈锡九》相比,作品有以下几处改动:

《正气诛邪》来源于唐朝牛僧孺所撰的传奇小说集《玄怪录》,讲述郭元振为太原除猪妖的故事。作品对故事的时代背景和郭元振的性格进行了铺垫,先写太原“地方好神,有所祷必多方许愿,务投神之所好以媚之”,复写郭元振“素有胆气,每与人谈,以祸福死生,置之度外,正论侃侃,人皆畏之”,然后举了一个小故事作为引子,“未第时,尝读书寺中,僧于夜间,模为厉鬼以相吓。振猛声叱之,僧惊病而死。”然后才引入正文。
《河伯娶妇》来源于《史记·滑稽列传》讲述西门豹治邺时破除迷信的故事。作品改变了原作的叙述顺序,更符合一般读者的接受心理。开篇就交代故事背景,“战国时,邺都巫觋辈,伪言漳河有一神,名河伯。每年要民间为娶一妇,可保年丰,若不择女以献,必致河水泛滥,漂溺人家。百姓惑于巫言,皆畏水患,不敢不从。”接着又叙述了具体的河伯娶亲仪式,富人可以财帛赎免,贫民则无以自保,结果是“百姓有此奇费,又有爱女者恐为河伯所娶,多逃避远方”,造成了邺人烟稀少的局面,为西门豹的出场做好了铺垫,从而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
第二种是将古代的诗词曲赋或者典故插入文中,化为小说中人物的创作,少则三言两语,多则百八十字,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这些插入文本基本为劝善或醒世类,从中可以看到编者明确的价值取向。如上文提到的《夫妻贤孝》中的诗,就是导人向孝。而古代许多类似的读本就成为这类化用的重要来源,如《解人颐》《悦心集》《传家宝》《明心宝鉴》等书。在这里面又有三种情况:
一类为根据需要,截取原文的部分内容,如《能屈能伸》中引用王文成公的《戒好讼诗》。原诗共有十二句,这里只截取前四句,告诫人们不要轻易打官司,否则得不偿失:


公文中有云:“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诸神传赞不已。
一类基本为原文,只在个别字句上进行了修改,并不影响整体的意思。如《夜行万里》中的于保所“作”的诗:

原诗为前两句为“难道形容似去年,今年亲已鬓毛斑”。通过替换“难道”“亲已鬓毛斑”为“莫道”“亲鬓已斑然”,文字上更加浅显,读起来更加上口,有利于文本的传播和接受。
又如《构讼终凶》中的两首诗也出现在《解人颐》中:



第三种中作品的创新性较强,和“前文本”有较大区别。也就是佛克马所说的对古代经典故事的“重写”。这种“重写”在集中占了一定篇幅。佛克马认为:

佛克马认为“重写”包含三种情况,一种是删削,即原作较长,进行了缩写;一种是添加,即原作较短,进行了扩写;一种是变更,即重写后的作品与原作长度相似,但是改变了原作里面的一些叙事要素,如时序、情节等。
当然,一般的重写文本很少单一运用某种方法,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在一篇作品里往往三种方法并存,本文仅就其大略,粗分为三种。
第一类为“删削”,即缩写。如写惠能的《孝子成佛》就是对《坛经》的缩写,除此之外,在作品的最后,整理者又加入了关于惠能的一些最新情况叙述:
自唐宣宗时,至元六百有余年,肉身俱存,香烟薰腹而如漆光。至元丙子年,汉军以刀钻其腹,见心肝如生,于是不敢犯。
第二类为扩写,代表作《夜行万里》,乃是将《关帝圣迹图志全集》中一篇450字左右的《于保还乡》敷衍成几千字的作品,是整部《宣讲博闻录》重写水平最高的一篇。《于保还乡》的故事原文如下:

本来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孝顺夫妇的故事,在《夜行万里》的作者笔下却焕发出了动人的光彩。原因即在于重写者采用了几个叙事技巧:
首先,通过增设了于保夫妇的相关情节,丰满了二人的人物形象,深化了他们的性格。开篇就用故事把于保的“性至孝”描绘了出来。
家寒微,性纯厚,以卖菜为生,侍亲极孝。父母俱嗜酒,每卖菜归,必沽酒以奉。有新出时物,亦必买奉亲尝,不计价之昂也。己体无完衣,而亲所用之物,莫不常给。……里中有不孝者,其父母窃叹,且泣曰:‘何不看于保?’其令人钦慕如此。
其次,通过插入一些诗词,扩充了作品的深度,增强了感染力。如前文提到的“莫道形容似去年”诗和石成金的《莫恼歌》等。

第三类重写为“变更”,重新整合前文本之要素,在情节与主题上,有承继,有创新。代表作品为《渔仙隐迹》。此篇是对《聊斋志异》中《王六郎》的重写。
《王六郎》讲的是王六郎与一许姓人相交的故事,重点突出王六郎的仁义和许姓人的重情。而在《渔仙隐迹》中,则将许姓人替换为“吴志人”,将王六郎替换为“范家诗”,将王六郎的一次仁义之举,改为范家诗的三次仁义之举,最后吴、范双双成神。其间,又把吴志人的故事进行扩充,将其塑造为一个知足常乐、心怀仁义的渔仙形象。
“或采近日之传闻”则更具有创新性。如序言所说,“夫世情好尚,大都厌故喜新。坊刻诸篇每以习见习闻而忽略”,而这些“近日之传闻”就具有更强的新鲜感,为读者与听众带来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如《犯法根于贪》的开篇就说,“里人蔡子厚,谓其客北江时,韶州城有冯日新者,贩毡、绸,往来曲江、南雄各埠。”可以断定,蔡子厚是广州人,整理者就是从他那里听来的这个故事。而《顺母桥》一篇更具有现实意义,其开篇就说:
省城西关有顺母桥,讹传谓一孝子,因其母每夜间涉水以就奸夫,孝子觉之,遂填石桥,使母得安步以渡,不致涉水之苦,人故名之曰顺母桥云。噫,此即孟子所谓齐东野人之语,彼无知者之妄传无怪矣,可惜有识者,亦啧啧口实,信以为然,谬甚妄甚。试思既是孝子,知其母有秽行,自当几谏,岂有陷亲不义、反造石桥以重母之过、扬父之羞?其父有灵,九泉且为饮恨,尚得为人子乎?稍有血性者,未必若是之愚。然相传之讹,未始无因,若不详言之,则孝子抱百世莫白之冤矣。
该作品写了伊猷卓浪子回头的故事,其间多得母亲及妻子之助。在文末,作者写道:
(伊猷卓)将所获赀在省广行阴骘,更营生理,后积赀数十万,宅后建园,使母在此安享,以娱暮年,故名晚景园。濠有木桥,母从楼上窥见行人倾跌,命易以石,故名顺母桥。今晚景园街户,原伊猷卓故宅。故街名仍曰晚景园。当时单坤成,恶党虽欲施害,而势不能与敌,忮之,故捏言顺母桥,谓创为其母往就奸夫者。此小人阴恶之术,如毒蛇不能咬人,犹欲喷毒以伤人。小人斯为小人也。
原来流传的有关顺母桥的传说是个讹误,是仇家为了泄愤所编造的谣言,却混淆了试听,并对世道人心产生了不良影响。此篇则正本清源,起到了正人视听的效果。
第三,《宣讲博闻录》采用多种技巧,一是打破某些类型小说的套路,二是注意增加细节描写,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如《正吉邪凶》类似于公案小说,但是不同于以往公案小说的写法,如《龙图公案》《三侠五义》等,而是悬念重重,步步惊心,直到最后才揭示谜底,从而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可读性。《孝友格亲》则基本采用书信体,可以看作是后世书信体小说的先声。《事母异闻记》则用喜剧的笔法写了“二子争孝”的故事。
在细节方面,《宣讲博闻录》多有称道之处。如《义农一子承双嗣》中,描写连汝芬找不到儿子之后的举动,就特别逼真:
汝芬不见其子,心自惊慌,遍市寻访无踪,归店告知其友,友即着店伙各处找寻,杳无声影。汝芬捱至天晓,仍四路访寻一遍,无奈回家。行至门前,不敢入室,立在门外,探影听声,测其子有回家否。妻方欲出汲,迫得踏脚入门。
《顺母桥》中伊猷卓在赌场上背着家人将妻子作为赌注,结果输了。待他回家时,家人并不知道已经发生了这样一件恶事,这时作品写道:
(伊猷卓)一路寻思,母及儿女向凭妻养,今无辜拆散,一家食指何依?念及此不觉寸衷欲断。徐步归屋,已属更深。妻尚挑灯夜织。扣门而入,妻见之恼,即携灯入房,羞与觑面。猷卓独坐庭间,俯首泪滴。其女见之,低声告母曰:“爹爹不知何为洒泪。”姜氏曰:“他或苦饥耳。然吾恼他,汝不能恼他。当问其曾食饭否。”猷卓闻之,触动恩爱心情,泪下如雨。适其女来问曰:“娘亲说爹爹曾食饭否?”猷卓愈加感触,哽咽不能感声,惟点头而已。妻窃窥其状,不觉酸心,出扪其首而抚其背曰:“腹得毋饥乎?抑寒风致疾乎?抑负赌债而为强梁殴迫乎?”猷卓皆摇首,曰:“不是。”妻复曰:“抑或穷途悔悟、触境伤悲?然往事不堪回首矣。如能知悔,夫妻勤俭,犹可支持,何必悲苦?”猷卓仰天叹曰:“今而后始知朋友中炎凉世态,究竟夫妇真情,吾过矣。”言之泪涌。
可谓一波三折,感人至深。
除此之外,《宣讲博闻录》塑造了一批性格发生改变的人物,正符合“改过迁善”的教化目的。一般文学作品里,人物的性格基本不会有太大变化,在《宣讲博闻录》中,却可以时常看见这种人物转变的闪光。如《诚心感弟》中的潘月槎、《忘仇认弟》中的施善权、《顺母桥》中的伊猷卓,都带有浪子回头、弃恶从善的特征。
结 语
当然,限于整理者的水平和一些故事流传的年代较为久远,《宣讲博闻录》在细节上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讹误之处,如把蔡君谟执政的地方由福州改为扬州,同时还有个别雷同的情节,如《诚心感弟》和《疯妓》的“巧试妓心”情节如出一辙。但瑕不掩瑜,整体看来,《宣讲博闻录》主题鲜明,叙事曲折,人物生动,语言雅俗共赏,堪称圣谕宣讲小说的集大成者。
注释:
①②③④ 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507、508、511、512页。
⑤ 郑观应《盛世危言》,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216页。
⑥ 耿淑艳《圣谕宣讲小说:一种被湮没的小说类型》,《学术研究》2007年第4期。
⑦ 姚达兑《傅兰雅小说征文与梁启超小说界革命》,《读书》2017年第6期。
⑧ 耿淑艳《从边缘走向先锋:岭南文化与岭南小说的艰难旅程》,《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3期。
⑨ [清]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载孙逊,孙菊囩编《中国古典小说美学资料汇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
⑩ [清]西樵云泉仙馆编《宣讲博闻录》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