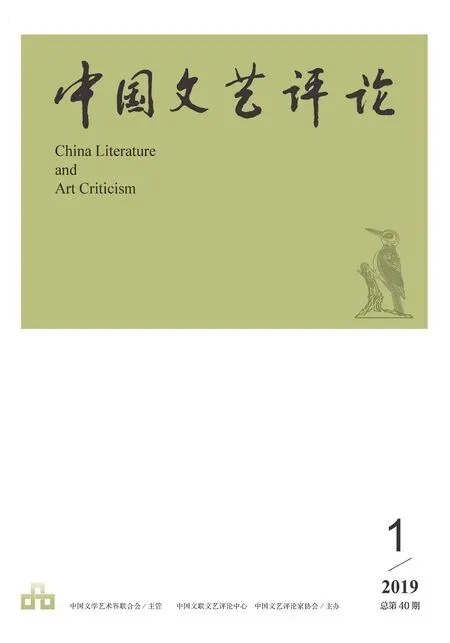“梨园魔法师”遇《樱桃园》导演
——梅兰芳与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莫斯科的会见
2019-11-12欧唐玛铁AUTANTMATHIEU周丽娟译
[法]欧唐·玛铁(AUTANT-MATHIEU) 周丽娟译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诚恳谦和的态度鼓舞着我,也深深地铭记在我的脑海里。回国后,我时时回忆起这位艺术上的伟大的创造者,他的坚持不懈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梅兰芳
1935年的春天,梅兰芳来到了莫斯科,他的戏剧让布莱希特、特列季亚科 夫(С.М.Тpeтьякoв)、爱 森 斯 坦(С.М.Эйзeнштeйн)等先锋艺术家们着迷,当时他们正在为创立新的“非亚里士多德式”(布莱希特)、程式化〔梅耶荷德(B.Э.Мeйepxoльд)〕、视觉的和模仿〔泰伊罗夫(А.Я.Тaиpoв)〕的戏剧艺术的呈现形式而探索着。这些艺术家们在讨论发言和发表的文章中无一例外、毫不掩饰地表达着自己的赞美。爱森斯坦更是用生动形象的语言称梅兰芳为“梨园魔法师”(«Чapoдeй гpушeвoгo caдa»)。实际上,他们确信梅兰芳的艺术会对苏联戏剧产生巨大的影响。
事实也的确如此,就戏剧领域来说,1935年9月25日,梅耶荷德排演《智慧的痛苦》(«Гopя oт умa»)的第二个版本舞台剧上演,在演出海报中写上了献给梅兰芳的字样,在这个版本中留下了梅兰芳 “舞台节律”安排方面的印记。看过了梅兰芳的演出,俄罗斯戏剧界的同行们明白了,他们自己还不会运用手势、眼神、节奏等元素及有效地支配时间和舞台上的空间,他们在舞台上堆砌了许多毫无意义的布景和道具。
然而,就在京剧团巡演的第二年,残酷的镇压猛烈地冲击到了苏联的戏剧界(1936年,大批的被指责为形式主义的艺术家遭到起诉和逮捕),阻碍了梅兰芳演出后开始的戏剧改革的进行。
虽然梅兰芳在苏联巡演的辉煌和全面的成功没有能够很快地转化为成果,但是梅兰芳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К.С.Стaниcлaвcкий)在莫斯科的会见,在中国戏剧艺术与西方舞台表演形式的交流方面仍然具有标志性作用。
1. 1935年3月,莫斯科
1935年3月,正当梅兰芳在苏联巡演的时候,人民委员会通过决定,批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开设自己的歌剧—戏剧学校。当时,这位在艺术剧院越来越成为批评对象的老艺术家,就在这所学校里暗中进行着培养演员—歌手的探索。令人惊异的是,这恰好发生在京剧团的演出在舞蹈、歌唱和造型艺术方面以自己极致的尽善尽美让苏联观众大为震惊之时。在歌剧—戏剧学校里,歌唱和表演技艺的传授同时进行,通常这些专门的技能在西方戏剧中单独存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其戏剧体系中尝试,重点关注身段动作和外在特征,最主要是对体系做了些修改。他认为,演员表演的推动力是通过身体动作的轨迹,而不是通过体验来实现的,过度地将自己封闭于心理领域的探索,会导致表演失去其在空间的表现力,因此,梅兰芳巡演结束几个月以后,在歌剧—戏剧学校的一次排练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把梅兰芳作为运用音乐和姿态动作富于节奏的榜样。建议学生们:“要学习梅兰芳表演技艺的精确性”,这不是偶然的。
梅兰芳来到了对西方“纯说话的戏剧”有浓厚兴趣的国家,那时良好的俄中关系促成了这次活动,增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在俄罗斯,梅兰芳发现了导演的艺术,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他观看了契诃夫(Чexoв)的戏剧《樱桃园》(«Bишнeвый caд»)。他还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同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歌剧院观看拉辛的《塞尔维亚的理发师》(«Сeвильcкий циpюльник»)一剧的排演。
两位大师不止一次地见过面,而梅兰芳受邀来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家里,这一事实意义相当重大。这样两位艺术家可以不受严格的正式会见的礼节规定的限制交流观感和设想。
从苏方来看,聂米罗维奇·丹钦科(B.Heмиpoвич-Дaнчeнкo)(他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共同领导艺术剧院)认为梅兰芳是“难得的天才人物”,他高度评价了梅兰芳的表演技艺、他演出的节奏感,但是他没有体验到京剧虚拟表演中真正的乐趣,也没能参透其中的象征性含义。梅兰芳的戏剧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立即产生浓厚兴趣的与其说是表演的最终结果(在舞台上动作、姿势总的编排情况),不如说是梅兰芳表演的编排机制,及为取得在细节上精雕细琢的效果而必须进行的训练。
在对艺术的理解方面,这不是形式起着支配作用的两种相接近的美学观点的交汇。这是两位艺术家、演员和教育家的会见,他们潜心思考着戏剧法则的本质特征,思考着在不损害前辈的创造、保留其生机勃勃活力的前提下,怎样复兴和传承艺术传统。也正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回答了某些观众对梅兰芳戏剧表演的编纂时刻都处于变化之中的惊奇:“梅兰芳的表演是有艺术规则的自由动作”。
在培养演员和传承戏剧传统方面,俄罗斯、中国的这两位艺术家以下的交往具有象征意义:1937年1月11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第一部分﹝《演员的自我修养》(Работа актера над собой
)﹞在美国翻译出版,斯氏请翻译伊丽莎白·赫帕古德给相识不久的梅兰芳寄去一本,另一本寄给了交往多年的马克斯·莱因哈特。他们是该书的第一批国外收件人。这种关注的表示对梅兰芳很重要。1937年5月12日,他写信感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称他的书是一部伟大的著作,称斯氏永远是他的导师及他的所有同行的表率。然而,由于中俄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梅兰芳的交往在苏联长期没有引起关注。1974年,尼古拉·西比里亚科夫(Hикoлaй Сибиpякoв)出 版 的《斯 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世界意义》(Мировое значение
Станиславского
)一书中连捎带着都没有提到中国,在这本书中作者详细地梳理分析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巡演在国际上的影响及斯氏体系的博大精深。当时的中国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而他的著作也被“忘却”了。2. 翻译和误读[3] 该部分依据伏伟峰(Фу Bэйфэн)的文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中国戏剧学校中应用的历史与经验》艺术理论的副博士论文,圣彼得堡图书编目СПб, СПГАТИ, 2009.
当梅兰芳在苏联巡演之时,中国对苏联的戏剧究竟有多少了解呢?在中国话剧的历史中,1916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名字是与新戏剧的诞生和契诃夫《海鸥》(«Чaйкa»)一剧的上演联系在一起的。斯氏后来逐渐地主要是作为演员和教育家被提及,他帮助表演者在工作上、在体验自己扮演角色的现实主义精神中加强自身修养。中国的评论家们特别准确地观察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演员们不是模仿生活,而是表现生活的本质、生活的精神。这也许是梅兰芳在观看《塞尔维亚的理发师》一剧排演时得出的结论,当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建议表演者:“坚持不懈地寻找其内在的作用,真正的、长时间的、有效的,适合于目的的……创造人类的精神生活,乃是我们的目标所在。”
著名导演黄佐临给予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描述是比较准确的:这种艺术外在的特征(流畅性、伸缩性、雕塑性和程式化)与隐含的生活的本质、身段动作、语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30年代的中国渴望建立现代戏剧,因此,他们在艺术剧院中寻找适合演出现代戏剧的样板。艺术剧院是导演的剧院,它的创作是建立在集体的基础上:乐师、舞台艺术家和服装设计师均参与到戏剧的创作中。在这里化妆和服装艺术尤为重要,无论是现代戏剧,还是历史戏剧,能够上演的全部剧目是艺术剧院的基础。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依靠的是剧作家的作品(这与梅耶荷德剧院创作的话剧不同,在他的剧院中,导演就像“编剧”一样重写剧本),也就是说艺术剧院能够成为中国演员学习西方“话剧”的样板。
1941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活》(Моя жизнь в искусстве
)一书被译成中文,该书让中国人明白了,俄苏戏剧的起源及其创作基础。在书的《手册》的《导读》中可以学到西方演员的表演技能,中国的实践者们关注到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另一本书《演员的自我修养》,该书是从英文转译过来的,该英文译本是斯氏教育方法和思想的有些争议的翻译缩减本。在中国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诸多问题的解读竟然是和那些没有具体案例、难以弄明白的复杂概念,如“体验”“任务”“贯串动作”“情绪记忆”“超意识或下意识” 等抽象的教学内容联系在一起。进入角色,从自身条件出发,在第四堵墙内表演——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做,对东方戏剧演员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他们不习惯于投入任何一种心理学的,任何一种个性特征到自己的表演中,因为他们所面对的观众——是欣赏程式化的内行,看戏对他们来说是消遣开心,而不是体验角色情感的。及至到了50年代,在俄罗斯实习的中国演员才有机会在实践中掌握斯氏体系。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缺乏真正合格的教师,致使学习期特别的短,但还要取得成效,故对心理活动过程的各个阶段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中国体验派很难存在下去,中国传统的戏剧是表演的戏剧,是符号化和程式化的戏剧。
3. 美学体系千差万别,但训练的方法是相似的
梅兰芳说,艺术是向前发展的,他拒绝将京剧视为永久保留着僵化形式的集合体。这位中国艺术家对待本民族艺术的态度与他的俄罗斯同行的观点有什么不同吗?
在梅兰芳的戏曲学校、在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学校里,两位艺术大师与教师一起在小组内把本流派知识传授给学生及其校外的追随者。在出演重要角色之前,学生先从群众角色、次要角色开始演起。
教师示范,学生模仿。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示范”一直相当著名且经常可以取代语言。这项训练工作是长期的、艰难的、需要不断地重复再重复,直到手势、动作准确地表达的不止是理性的、而且是下意识的。演员的任务不在于简单地模仿,而在于塑造形象。需要把握人物的灵魂和精神。因此,演员的手势、眼神、动作、表情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在36年至37年,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排演《哈姆雷特》的时候,他对演员说:“首先应该理清脉络,尽力地感受作品总的意向,以看不见的触角深入到剧中每一个出场人物的内心,为此要寻找眼神,适应剧中人物、贴近自己,找出其中的纽带和桥梁。”
的确,表演技艺能够呈现人物的精神状态,但它不排斥内在的情感。表演就意味着把外在的特征,无论是程式化亦或写实的演技——和内在情感(精神)联系在一起。演员应该去体验他所扮演角色的感情。梅兰芳写道:“当我扮演这样或那样的角色时,我应该像他,观众看到的我,已经不是我本人了。”如果演员能够成功地做到让观众忘记了他并把他当成剧中的人物,这是相当成功的。最后一个阶段是进入到神魂颠倒之境(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或者无意识的状态(梅兰芳),当那个神秘时刻到来的时候,所有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无法理解这是怎么回事。
两位艺术家都对绘画、服装样式和舞台布景感兴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著名艺术家〔西莫夫(Симoв)、多布任斯基(Дoбужинcкий)、伯 努 瓦(Бeнуa)、勒 里 希(Pepиx)〕合作、梅兰芳本人也从事绘画,两位艺术家的目标是——美、和谐、轻盈敏捷。动作和对白服从于节奏(包括音乐、身段动作和声音)。
梅兰芳没有接受现实主义美学,但他认为重要的是了解历史语境,这样才能更好地感受自己所塑造的角色。
总体上说,两位艺术家都认为,对戏剧艺术进行创新和推动艺术“向前发展”,剧目问题至关重要。
4. 结语
1935年,梅兰芳剧团在俄罗斯巡演,让我们看到了无论是现实主义的拥护者,还是程式化戏剧的捍卫者,都存在着可能接近的那些共同点。我不妨做这样的假设,对梅耶荷德来说,这次会见能够早些实现就好了,因为在当时,他正在探索象征主义剧目的呈现方式。符号化的中国戏剧是社会上各类人物典型特征的专门化(即根据演员的特点固定扮演专门的角色),在演出中,角色的念白伴着音乐,自始至终都有音乐,其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动作和念白的节奏,在这里演员说着所扮演角色的话走上舞台变成“一个艺术作品”,中国戏剧对演出梅捷林科(Мeтepлинк)、索洛古布(Сoлoгуб)、布洛克(Блoк)的戏剧能够给予梅耶荷德有价值和辅助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梅兰芳为俄罗斯与中国戏剧艺术教育的交流开辟了道路。
1956年,在俄罗斯后斯大林主义解冻初期,俄文杂志《外国文学》马上就发表了梅兰芳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感谢信,在信中有感谢斯氏赠送《演员的自我修养》一书的话。1963年,梅兰芳的著作《舞台生活四十年》(Сорок лет на сцене
)在苏联翻译出版。梅兰芳来到莫斯科之前,在中国就有少量的戏剧理论与实践的书籍。常常是学生演员只是按照本行当开列的姿势进行系列练习,但是没有任何解释,为了达到需要的效果,应该怎样训练。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书来教授演员和导演现代和现实主义的西方戏剧的精神,尽管有误读,时而被认为是最好的方式、时而是最差的方式、时而受到追捧、时而又遭到压制,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长时间里是唯一完整的演员培养方式,这种方式在中国的戏剧教育中留下了印迹。正是梅兰芳把接力棒从莫斯科传到了北京。
译者的话:
1935年梅兰芳剧团访问苏联是迄今为止戏曲文化对外传播最成功的一个案例。当时正在为创立新的戏剧艺术呈现形式而探索的苏联戏剧家们对梅兰芳的演出充满着期待。苏联观众对戏曲艺术独特的魅力及梅兰芳等精湛的表演技艺反响热烈,双方艺术界对戏曲文化本质特征等重要问题的探讨体现了高度的理论思维的自觉性,其后在实践中的相互借鉴更是对世界戏剧艺术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国际戏剧界的杰出代表,他所建立的体系是世界上最具系统性和科学性的表演体系之一;梅兰芳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中国乃至东方传统戏剧文化的化身和特定符号,故巡演期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梅兰芳在莫斯科的对话极具研究价值。2015年中国戏曲学院戏曲研究所召开了“纪念梅兰芳1935年访苏演出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法国国家学术研究中心主任欧唐·玛铁提交了论文《“梨园魔法师”遇〈桃园樱〉导演——梅兰芳与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莫斯科的会见》,对两位艺术大师的交往、相互理解和借鉴、理论和实践在对方国家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探讨,突出地分析了他们在演员表演技艺等问题上的一些相似的看法和理解。现将论文译出,供研究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