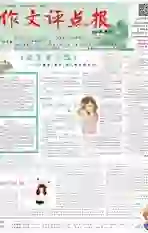我的坚强与柔软
2019-11-07于娟
于娟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分外坚强的人。
2009年的最后一个星期,我被救护车抬进上海瑞金医院,放置在急救室。
病理室主任看到我那浑身黑漆漆的CT后,问了一句话,病人现在用什么止痛?
我的老公,那个可爱的光头男回答,现在还没有用任何的止痛药物。
那个四十多岁的主任,倒吸一口凉气,一字一句地说:“正常情况下,一般人到她这个地步,差不多痛都能痛死的。”
他们进行这段对话的时候,我只是屏着气,咬着牙,死死忍着,没有死,也没有哭。
在急救室待了三天两夜。医生不能确诊是骨癌、肺癌、白血病还是其他癌症。
急救室应该就是地狱的隔壁,一扇随时开启的自动门夹杂着寒冬的冷风,随时有危重病人被送进来。
我身边的邻居,虽然都躺在病床上,但精神似乎都比我好很多,至少不是痛得身体纹丝不动。然而,就是这些邻居,夜里两点大张旗鼓地送进来,躺在我身边不足两尺的地方,不等我有精神打个招呼,五点多就会被某些家属的哭声吵醒,看到一袭白单覆住一个人的轮廓。不用提醒,我知道那个人匆匆忙忙地走了。
如此三天两夜,心惊胆战。我没有哭,表现得异常理智,我只是断断续续用身体里仅有的一点力气,录了数封遗书,安慰妈妈看穿世事生死。
后来,一天两次骨髓穿刺。骨髓穿刺其实对我来说,并算不上疼痛,光头在旁边陪我,面壁而不忍再看,妈妈也已经濒临精神崩溃边缘。
我的痛苦在于,当时破骨细胞已经在躯壳里密布,身体容不得一点触碰,碰了,真的就会晕死过去。那种痛不是因为骨髓穿刺,而是来源于癌细胞分分秒秒都在啃噬骨头。
我还是没有哭,不是因为坚强,而是因为痛得想不起来哭,那个时候,只能用尽全力顶着。如果稍微分神,我就会痛得晕厥。我不想家人看到我的痛苦。
当2010年元旦我被确诊为乳腺癌四期,也就是最晚期的时候,我长舒了一口气,没有哭,反而发自内心地哈哈大笑。
因为这个结果是我预想的所有结果中最好的一个。
既然已然是癌症,那么乳腺癌总是要强一点。
至于晚期,我早已明了。全身一动不能动,不是扩散转移,又能是什么。
发现太晚,癌细胞几乎扩散到了躯干所有重要的骨骼。
我不能手术,只能化疗,地狱一样的化疗。
初期不良反应很大,呕吐一直不停。
当时我全身不能动,即便呕吐,也只能侧头,最多四十五度,枕边、被褥、衣裳、身上,全是呕吐物,有时候呕吐物会从鼻腔里喷涌而出,一天几十次。
其实,吐就吐了,最可怕的是,吐会带动胸腔震动,而我的脊椎和肋骨稍一震动,便有可能痛得晕厥过去,别人形容痛说刺骨的痛,我想我真的明白了这句中文的精髓。一日几十次呕吐,我几十次痛到晕厥。
别人化疗时那种五脏六腑的难受我也有,只是,已经不值得一提。
那个时候,我还是没有哭。因为我想,坚持下去,我就能活下去。
此后六次化疗结束,我回家了。
儿子土豆刚十九个月,他开心地围着我转来转去。
奶奶说,土豆唱支歌给妈妈听吧。
土豆趴在我膝盖上,张开嘴居然奶声奶气地唱道:“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
话音未落,我淚先流。
也许,就是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我的孩子,就变成了草。
于丹说:一个人的意志可以越来越坚强,但心灵应该越来越柔软。
无意之中,我做到了这点。这才发现,这两者是共通的。
(选自《此生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