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医 ” 问题反映利益博弈能力
2019-11-04黄清华
文/黄清华
调查显示,普通患者群体最缺乏医改利益博弈能力,要解决新医改面临的难题,必须首先在程序上解决普通患者群体利益博弈能力最弱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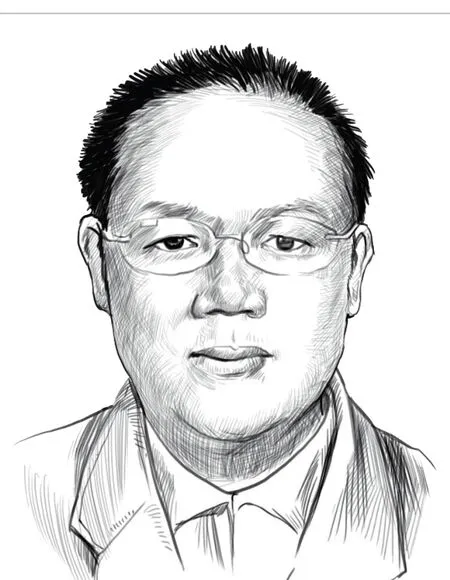
如前所述,新医改的目的是要解决群众即普通患者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以保障群众看得起病、病有所医。但是,从医疗、医药和医保“三医”领域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来看,相当部分群众离这个目标的距离并没有拉近,甚至有不少群众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罕见”现象,可从医改所有利益相关人的博弈能力找到合理解释。
从医改利益博弈的角度来看,新医改发生于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其本质,就是要在卫生健康领域,调整政府、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医药企业、医保经办机构和作为普通患者的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格局,是他们之间围绕中国卫生健康体制改革所涉各种利益问题,为各自集团、群体的利益进行的长期博弈。改革的好的结果,应当是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
在这一过程中,新医改以来,政府、政府相关部门、医药企业、医疗机构和医生、医保经办机构都可以有组织地发声音,参与涉及本群体、本集团利益的医改政策的制定和/或执行,唯独普通患者或者群众,即社会一般公众,没有专门的病人(权利)组织(Patient Groups)等健康相关社会组织,能够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依法有组织、有计划、有程序并且经常性地代表这一最广大群体的利益开展活动,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监督政府相关部门、医疗机构和医生、医药企业和保险经办机构的活动。反观其他群体在新医改中的作为或表现,不得不承认,医院、医护群体、药企、医保机构,他们的利益博弈能力很强,对医改决策或者决策执行影响甚巨,而普通患者群体的博弈能力,则很弱,最终导致一次次利益失衡,甚至严重失衡。
在医疗服务关系中,按博弈能力的强弱:医院>管理者>一线医护>普通患者(个体)。“相对于被医疗体制压榨的一线医护,比他们更弱势的只有患者了。”绝大多数医闹暴力或者伤医事件,正是发生于这样的社会背景和体制机制框架下。这一点,必须被认识到。因此,治理医闹暴力事件,正确的做法,应当围绕建设病人权益本位的中国卫生健康体系展开,引入患者权利组织等健康相关社会组织的有效参与,以此调整医患关系,平衡医患双方的利益,实现医患和谐关系。
在医药行业、药企与患者的关系中,按博弈能力的强弱:医药行业协会>药企>患者(个体)。这种博弈能力,明显反映在医改政策的制定上。例如,关于如何解决药价虚高问题,以《医改意见》(又称“医改方案”)的出台为例,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医改方案”征求意见期间,中国医药商业协会组织全国的药品流通企业,进行了多方面的公关,通过写信、约谈有关部门官员等办法,影响医改方案的制定,于是,征求意见稿中的“推行在药品外包装上标示价格制度”这一明显有利于控制药价虚高的政策条文被删除。而有关基本药物招标的政策表述,征求意见稿与“医改方案”终定稿的明显区别,也反映了医药行业企业的博弈能力。
在基本医疗保险关系中,“医保局掌握了资金的流向和预算,可以控制总费用;医院和医生在运营面对压力,无法保证自己盈利时,法律又没规定它们一定要接诊,一定要用性价比最好的方式,治疗好患者的任何疑难杂症,况且医学知识那么专业,外界根本无法和它们进行理论和博弈。”因此,“四方话语权的强弱,依次是医保局>医院>医生>患者(个体)。”这导致在基本医疗保险关系中,普通患者的命运,几乎任人摆布。
以湖南湘雅二医院公开拒收长沙市医保患者事件为例,2016年下半年,湖南省中南大学附属湘雅二医院公开拒收长沙市医保患者。通知中说:“长沙市医保病患,除危重病人外,只能提供门诊就医,暂不能办理入院就医。”原来,湖南省医保局对省内公立医院的结算模式,是在“总额预付制”模式下,医院先垫付,再去医保经办机构申报结算,经历3~6个月的时间后,医保款项才到账。当时已经拖欠了这家医院2700余万元,影响了医院的资金回笼。在等待资金到位之前,医院选择将压力传递到患者身上,干脆拒收了事,只欢迎自费的患者。
以上说明,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商业利益是阻碍新医改顺利进行的三大因素。过去在“以药养医”的机制下,医院、医生、药品流通环节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新医改实行药品统一招标,就是为了打破这个利益链,缩短药品从药厂进入医院的流通环节,把虚高的费用以及灰色收入挤出来。很自然地,新医改从一开始就遭遇了“以药养医”体制机制下的各种既得利益者的阻力。这种阻力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腐败性力量,只有通过民主的力量结合司法的力量才能有效根除。质言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良好的卫生健康体系,离不开民主的政治体系和公正的司法体系的支撑,而患者组织等健康相关社会组织,是在卫生健康领域建设民主的政治体系和公正的司法体系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
从博弈行为来看,医药行业、企业的博弈主要是写信、约谈有关部门官员,而医疗行业、医院、医生群体的博弈行为,无疑就更加“丰富多彩”了:这个群体所拥有的地位、身份、专业知识、经济实力、信息和社交渠道,所属的学会或协会,加上这个群体确实也有前述委屈之实情,使他们具有很强的博弈能力。
相比之下,普通患者群体能够做什么呢?除了个人提提不招人待见的意见和建议,什么也不能做;除了极个别胆大妄为者对医务人员暴力相向,什么也做不了。这就是普通患者群体在涉及“三医”的社会关系中,利益博弈能力最弱的真实写照。而这种超弱的利益博弈能力,又反过来可迫使极少数人“铤而走险”,在医患关系中使用暴力。对此,有学者认为:“医患冲突普遍、持久存在的现实情况使人们意识到,医患矛盾不再是个案纠纷,患者遇到的麻烦不再是他个人的麻烦,而是患者群体的麻烦,需要把患者作为一个群体来应对。”
不仅如此,医改这么多年,新医改复又十年,在政府一些相关部门的潜意识中,普通患者群体或者公众,只是管理对象而不是照护对象,甚至连一个“中国家庭健康大会”,讨论的都是“患者管理”而不是如何尊重患者、如何实现病人(健康)参与。以这样的思维思路,新医改焉有成功之理?!这恐怕是中国当前在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的情况下,紧张的医患关系难以根本改善体制机制上的原因。基于上述分析,有充分的理由作出这样两个基本判断:
其一,要解决新医改面临的难题,必须首先在程序上解决普通患者群体利益博弈能力最弱的问题。为此,在政策法律上,确有必要明确地支持患者依法组建各种类型的患者组织等健康相关社会组织,使之能够有组织地合法地参与医改利益博弈。
其二,解决“三医”领域的上述问题,指导思想上应当明确,中国卫生健康体系政策法律的制定,需要确立以公民健康权利-患者权益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而不是价值不甚明了,甚至价值混乱的各种修修补补。
当然,这种制度建设,丝毫不否定“三医”领域从业人员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合法权益。因此,中国卫生健康体系良法善治问题,其实质主要是“三医”领域的社会建设问题,必然要求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建设规律办事,即各种利益相关人能够在法治框架下,通过其组织或代表对医改决策和决策执行践行真实的有效参与,如此方有可能在卫生健康领域建设民主的政治体系和公正的司法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