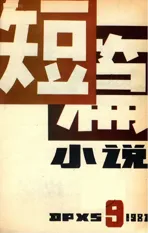雁过无痕
2019-10-14侯宏博
◎侯宏博

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
——泰戈尔《飞鸟集》
一
我推着自行车一进村口,老远就望见朱大贵的那辆黑色宝马停在村子中央的老槐树下,大腹便便的朱大贵晃动着他那颗秃脑袋,踱来踱去,给坐在碾盘上、圪蹴在墙根下乘凉闲谝的老少爷们敬烟。阵阵说笑声混合着夏日街道里发酵后的粪土味,滚滚热浪似的朝我扑面而来。
朱大贵是我的发小,上小学四年级时往女生书包里放癞蛤蟆,挨了老师一顿批评后,狠狠地一脚踹倒老师,跑出了校门,就再也没进过学校。老槐树下的人都说,这娃日后能有出息,太阳就从烟囱出来了。太阳当然永远不会从烟囱里冒出,但二十年后的朱大贵出息成了省城有房,屁股下有车,还坐着飞机周游过世界的大老板。
“大贵,你上次说咱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那苏联还没有咱大?”圪蹴在碌碡上背靠老槐树吃晚饭的三德爷放下手中的粗瓷老碗问。他老人家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但心里却装着整个世界,地球上犄角旮旯根根茎茎的事都想琢磨个明明白白。
“好我的爷呀,还提苏联哩,苏联早就在赫鲁晓夫时代解体了,分成了巴掌大的几个小国家。”朱大贵哈哈大笑,摆出一副满腹经纶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神气。
“哦,赫鲁晓夫,这人我知道,就是当年的苏修头头么。”三德爷美滋滋地咂了一口烟杆一端的玛瑙嘴儿,不无得意地吐了口白烟,接着又问,“你刚说的解体是个啥?”
“解体就是……”朱大贵摸了摸秃脑袋,猛地一拍脑门,说,“就是老子管不住儿子了,几个儿子闹腾着分了家,就像村东头的老何家一样。”
“哦,是这么回事。那真是活该!”三德爷在碌碡沿磕了磕黄铜烟锅脑中的烟灰,鼓了鼓腮帮子说。他曾和村东头的老何为地畔吵过一架。
大伙品咂着朱大贵发的香烟,回想着老何家三个儿子当年分家时头破血流的打闹场面,打心底里对朱大贵的见多识广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个个都满脸的深信不疑。
“咱中国才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哩。”我听了刚才这番高论,在一片槐荫下撑放了自行车,忍不住插了一句。
大伙的目光一下子都聚向了我。若是在课堂上,这齐刷刷的目光会令我感到无比欣慰,但在这老槐树下,只会令我惶恐不安。果然,那几十双大眼小眼中隐藏了多少诧异和不以为然呀。
“你放学回来了。”朱大贵挺着肚子踱到我跟前,掏出了一支中华烟。
“回来了。你也刚回村?”我打了个招呼,摆摆手说,“我戒了。”
“戒了?戒了好啊,戒了就更像先生了。”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国土面积仍然是世界第一。”我没有接朱大贵的话茬,只是继续着我的话,“而且北美洲的加拿大也比咱中国大……”
“你说的加拿大我去过。”朱大贵似乎一下子兴奋起来,打断了我的话,“那地方的树叶全是红的,比咱这里秋天的柿子树叶还要红,漫山遍野像着了火一样。”
大伙儿都瞪着眼睛,静静地聆听着这异国他乡的神奇和美妙,一脸的敬佩和羡慕。
“苏联也不是在赫鲁晓夫时代解体的,而是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我实在不想扫大伙儿的雅兴,但职业习惯又迫使我多啰嗦了一句,毕竟,错误摆在那里,就像秃子头上爬了一颗滚圆的虱子,谁见了都会产生用指尖抿死它的冲动。或许,这也是我的职业病吧。
“什么劁夫?没听说过。”三德爷取下先前别在耳朵背后的那支中华烟,横在鼻下闻了闻,梗着脖子说,“阉猪的,还是骟羊的?这样一个货能统管好那么大的国家!”
全场“嘭”的一声,爆米花似的哄笑起来,惊飞了老槐树枝头一群吵嘴的麻雀。每一张面孔都是那么夸张和扭曲,犹如漫画一般。只见朱大贵那一身肥膘在笑声中富有节奏地上下颤动,似乎马上就能抖落下一坨肉油来。
为了掩饰尴尬,我也附和着呵呵了两声,摇摇头,扬手在自行车座垫上拍了一巴掌,推车走了。
“连赫鲁晓夫都不知道,还当老师!”
“加拿大再大,能有咱中国大!”
“大贵坐飞机飞遍了全世界,啥能不知道?”
“对,飞机上往下一望,谁大谁小一清二楚。”
“这水平把娃们都教成了浆糊罐罐!”
……
身后又是一阵哄笑,暴风雨般气势逼人。连那辆黑色宝马也被震得吱哇吱哇怪叫了两声,耀武扬威地宣示着胜利。
我一点儿也不奇怪,也不气愤。十多年来,老槐树下的笑声就像村口涝池里的蛙鸣一样,早晚声声如潮。然而,我的心底又飘出了一丝悲哀,犹如这傍晚的炊烟,若有若无,如梦如幻,浮游在生我养我的这个小山村上空,风也吹不散。
二
进家门时,家里那头肥猪不知啥时拱开了圈门,暴发户似的懒洋洋地横躺在巷道阴凉处,挡住了我的路。看着它那滚圆的胖肚子,我头脑里不由得闪出了朱大贵,就朝猪尻蛋上狠踢了一脚。它嗷的一声滚身爬起跑进了圈。
听到猪叫声,妻从屋里探出头来:“你一进门,踢它干啥?掉了膘,今秋种地的化肥种子靠谁呀?”
我没言语,将自行车提起来,咔的一声撑停在院子那棵核桃树下。
“给儿子学校的生活费打过去了?”妻边问边把一大盆洗过衣服的污水泼到猪圈里,猪圈立即腾起一股尘烟。那猪则倒在泥水里蹬着四蹄翻滚,无比舒服地享受着泥浴带来的凉爽。
“打过去了。”
“那咱爹上个月在村诊所看病欠下的钱咋办?人家刘大夫已经催要过两回了。”
“等下个月工资到了再清吧。”
“你倒真会给没影儿的钱安腿儿。”妻冷笑了一声说,“你晚上吃啥饭?”
“在学校灶上清汤寡味一周了,你烙两张烫面油饼子吧。”
“啥?烫面油饼子?”妻受了惊吓似的,“你一个代理教师,还想吃油饼子,你还真把自个儿当先生哩!”
我顿时觉得心凉身疲,像一摊水似的倾倒在床上,浑身无力。妻再问我时,我说:“那你就歇一歇,啥也别做了。我不饿。”
也许是我的肉臭,刚一躺下,很快就吸引来了几只苍蝇。我对苍蝇的厌恶程度远胜过蚊子。蚊子美滋滋地吸食饱了血,就哼着曲儿躲藏在阴暗的角落消食去了,顶多给你的皮肤上留个红红的吻痕。苍蝇则讨厌极了,它哭丧似的在你的周围盘旋,待落在你身上,先将两只后爪在翅膀背后搓一搓,再用前爪在你的汗毛上挠了又挠,用舔吸式口器在你的皮肤上舔了又舔,这种痒比痛更难受,闹得人心神不宁,坐卧不安。
窗外渐渐黑了。我睡意全无,摇着蒲扇思量着朱大贵到底给大伙灌了什么迷魂汤,满嘴的胡说八道大家却都相信。上次他在老槐树下说,日本人之所以霸占咱的钓鱼岛不还,是因为日本人爱吃鱼,而站在钓鱼岛边,随便一竿子下去就能钓上一条肥鱼来。听得三德爷溅着唾沫星子大骂,日本鬼子咋不让鱼刺扎进喉咙给卡死去。朱大贵还说,他姓朱,谐音虽不大中听,但在明朝却是国姓,皇帝老儿也姓朱。他说这有啥难听的,辽代皇帝还姓野驴哩,名叫什么野驴阿抱鸡。众人一阵狂笑后,朱大贵解释说,这就叫贵人贱名,你们都不懂。
三
夜静了,屋子里闷热得像个蒸笼,我披了衣服走出家门。
村子街道寂阒无人。月光下的麦草垛、粪土堆和电线杆都半明半暗,身旁拖着各自丑陋的影子。朱大贵的宝马停在他家门前,瞪着一双大眼睛,活像一只发怒的蛤蟆。
老槐树下,这个村子里白天最热闹的舞台,现在曲终人散,只有那青石碾盘和碌碡静卧在浓荫下的黑暗中,睡着了似的。这碌碡原本在碾盘上滚动了无数岁月,如今废置在老槐树根,成了三德爷的专座。他老人家的一日三餐几乎都是圪蹴在碌碡上下肚的。
我脱下一只鞋,垫在屁股下,坐在碾盘上。月光透过密密匝匝的槐树枝叶,将星星点点的光斑洒在我的胳膊和腿脚上,让我变成了一个白癜风患者。
“你也没睡?”
我回头一看,是朱大贵来了。他将背心卷到双乳上,露出了孕妇似的大肚皮。斑驳的月光也使他患上了白癜风。
“喝些酒。”朱大贵把半瓶啤酒举到我面前。
“我不喝。”
他却伸手脱下我的另一只鞋子,垫在他的屁股下,和我迎面而坐,灌了一口酒,笑嘻嘻地说:“皮鞋没法垫着坐,还是你这布鞋垫屁股舒服。”
一只蚊子在我耳畔哼哼唧唧地骚扰,我扬手拍了一巴掌,蚊子没打着,却给了自己一个清脆的巴掌。
“你还记得咱俩小时候在这棵树下摔跤吗?”朱大贵见我不言语,寻思着话题。
“咋不记得,你没赢过一回,输了就哭,眼泪比尿水还多。”
“那咱俩现在摔一跤,再比试比试。”
“现在?瞧你这一堆肉,压不死我也能捂死我。”
朱大贵嘿嘿一笑,用手来回抚摸着大肚皮,还啪啪地拍了两下,好像一个凯旋后得意扬扬的将军。
“咱说正经事。”朱大贵点燃了一支烟,盯着我的眼神说,“我想明天去咱那学校看看。”
“那有啥可好看的?又没有加拿大火海似的红枫叶。”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啥药,仍戏谑着和他打哈哈。
“我打算为学校捐建一栋教学楼。”
“怎么?”我着实吃了一惊,但很快就认为他是酒后出狂言,或是拿我寻开心,就没好气地说,“你是血多得难受,想放一放,还是财神发起了菩萨心?”
朱大贵猛咂了一口烟,再从两个鼻孔徐徐喷出,真像吐出了两根白白长长的象牙。过了许久,他说:“你知道,我当年踹了老师一脚跑出了校门,后来我娘拧着我的耳朵把我往学校拽,耳岔根拧出的血直流到了下巴,也没把我拽进学校的门槛。”
“这我都知道,你是怕老师揍你……”
“不是。”朱大贵厉声打断我的话,一仰头,咕咚咚喝光了酒瓶里的酒,“我是怕……怕再看到老师的那双眼睛。”
“老师的眼睛?”我的脑海里一下子闪过了无数双老师的眼睛。有课堂上神采奕奕的眼睛,有唱歌时月牙般微笑的眼睛,有监考时目光如炬的眼睛,有讲故事时会说话的眼睛,甚至想到了她因孩子发高烧一夜未睡来给我们上课时红红的眼睛,唯独没有搜寻到朱大贵所说的那双可怕的眼睛。再说朱大贵是啥人,我心中有数,他穿开裆裤时,就把菜花蛇当蚯蚓玩,什么东西还能让他害怕?一双眼睛!鬼才相信他说的这话哩。
“你是不知道,老师被我踹倒后,她一手撑着地,一手攀着桌沿,教本掉在了地上,粉笔断成了三截,那双眼睛闪着泪花,还闪着……怎么形容呢,还闪着羞辱和无奈吧,我也说不清楚,就像庙会上卖羊肉泡馍的摊主将要宰杀的那头老绵羊的目光。”朱大贵扔掉已快烫到手指的烟蒂,双肘撑在盘着的腿膝上,两只胖手捂着秃脑门,又过了许久,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踏进过任何学校半步。真的,现在我女儿的学校开家长会,从来都是我媳妇去,我一次也没去过。谁若骗你,就是猪!”
我看见月光下,朱大贵的那双眼睛亮晶晶的,但他很快又埋下了头。
“我还打算为学校再捐一批电脑,连接上互联网,让咱村的娃们都能看看大山外面的世界。”朱大贵重新仰起脸,望着我说,“我要让他们都敬重文化,敬重像你这样有文化的人。”
我抬起头,看见碎密的槐叶缝隙,月光星星点点,犹如万千偷窥的眼睛在注视着我们。一阵风吹过,老槐树枝叶摇曳,窸窸窣窣作响,像谁在嗤嗤地笑,又像谁在低低地哭。
我真没想到朱大贵会倾吐出这样一番肺腑来。看着月光下盘腿坐在碾盘上的朱大贵,突然觉得他肥头大耳的秃脑袋和坦胸露乳的样子,真像一尊佛,不过,是一尊喷着浓浓酒气的俗世佛。
四
周末的校园静悄悄的,三两只百灵鸟在花木间轻快地跳跃追逐,娇巧的身影在浓密的树荫中时隐时现,啾啾的鸣叫声依旧那么清脆悦耳。
朱大贵在我的带领下,终于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跨进了他二十多年不曾跨越的学校门槛。尽管这所山村学校的面貌几乎和二十多年前没啥两样,但我从朱大贵说话时的颤抖中,能真切感受到他波澜起伏的心潮。
“以前总觉得咱这学校很大,很大,现在怎么变小了?”朱大贵拍了拍操场边一棵白杨树粗壮光洁的树干,口里喃喃,“校舍变小了,操场变小了,只有这一排白杨树长得高大了。”他走到第三棵白杨树下,绕了树干一圈,就像一个母亲端详眼前久别重逢的孩子,满眼的亲切。突然,他回过头,深深地望了我一眼。
“对,就是这一棵。”我明白他的眼神,知晓他的心思。这棵树是我和朱大贵当年一起栽种的。那年春,学校购回了一批白杨树苗,老师安排我们男生两人一组栽种一棵。我从家里带来了镐头,大贵带来了铁锨,我们一起挖坑,培土,浇水,又一起盼着小白杨扎根,发芽,长叶。老师说,等小树苗长成参天大树的那天,你们也就成人成才展翅高飞了。
我一直以为,只有像我这样苦守穷乡的人,才会时时擦拭岁月,盘点往事,就像在寒冬的夜晚拨弄一堆灰烬,试图寻找未燃尽的点点星火,给心灵取暖。真没想到,平日里大大咧咧胡说浪谝的朱大贵,心底竟然也挺立着这棵白杨,二十多年不曾丢失。
一只蝉隐匿在白杨树浓密的枝叶里,振翅高歌,鸣声响彻校园。我们穿过操场,走向那一排红砖青瓦的教室。
这些教室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所建,起初是土木结构的大瓦房,“普九”那年,将前后檐墙换成了砖墙,但教室里一直没有吊顶,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挂着白炽灯泡和蜘蛛网的人字大梁。
我推开四年级教室油漆斑驳的木门,一群从房檐缝隙钻进教室的麻雀在房梁上栖成一排,叽叽喳喳地吵闹,突如其来的开门声,惊得它们全都扑棱棱飞钻回檐缝,探头探脑地张望。房梁正下方的那排课桌上,留下了一片白花花的鸟粪。
朱大贵只是站在门口看了看,并没有进教室。我知道,这就是他当年踹倒老师的那间教室,是他的懊悔地。尽管光阴流转,物是人非,但那些粗笨破烂的桌凳见证了当年的一切,他依然心有余悸。“走吧。”朱大贵猛一转身,似有一阵往事不堪回首的决绝与悲戚。
走出校园时,操场白杨树上的那只蝉依然一声紧过一声地高鸣不已。它是在诉说什么呢?无人知晓。我只知道,我在这山村小学站了整整二十年的讲台,当了整整二十年的代理老师。其他老师都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走了一批又一批。这所学校,不过是新分配师范生的一块跳板,或是城里教师为评职称来支教“镀金”的场所而已。而我的坚守,活生生把自己站成了一棵树,迎着山风,守望着蓝天。
五
我和朱大贵一起去见村长。村长一听朱大贵要捐资建校,当即一拍大腿,说:“好啊,这可是咱村开天辟地头一桩大善事!”并说他会立即给乡上汇报,让大贵的心愿早日落地生根。
朱大贵捐资建校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犹如向涝池里丢了块半截砖头,扑通一声,波涟不已。村头巷尾,田间地边,沟沟峁峁,只要有三两人聚在一起,谈论的必是这桩喜事。
我也为这事高兴得日夜睡不着,憧憬着教学楼拔地而起的盛况,想象着孩子们坐在电脑前的一张张笑脸。就连妻也啧啧地夸赞:“瞧瞧,大贵咋那么有钱!咱想盖三间房,愁了几年也没盖起来,人家上下嘴唇轻轻一碰,就捐了整栋楼;我想买台洗衣机都要从嘴上捋,牙缝里省,人家捐那么多电脑,眼也不眨一下。”
然而,老槐树下的议论却出乎我的意料。那天早上,我正要去学校,看到三德爷圪蹴在老槐树下的碌碡上吃饭,一伙子闲汉也手捧饭碗,围了一圈。
“大贵就是牛啊,一出手就是上百万的高楼。”
“那是拿钱打水漂哩,学校建得再好,咱这山窝窝里还能飞出个凤凰?”
“我看大贵就是个烧包。有那钱,还不如修修自己爹娘的坟,光宗耀祖!”
“大贵不简单呀!”三德爷拖着腔,一副世事洞明的样子,“他捐资建校,是想让学校的娃娃们和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记住他的好,留下万世名哩。”
我听了只觉好笑,心里暗自感慨,这世上真是好人难当,善事难做啊!
没想到中午,我正在上课,妻急急火火地跑到学校,让我吃了一惊。结婚这么多年,她从没有来学校找过我,她总认为,一个大男人挣那点微薄的工资是没面子的事。不知今天日头怎么从西边冒出来了?
“你快去听听,他们都说的啥?”妻气喘吁吁,面红耳赤,“他们说,大贵捐钱建校,是你在背后撺掇!”
“他们爱咋说就咋说去,甭理会!”
“还说,你见大贵发了财,眼红,教唆着他把钱往沟里扔!”
“谁说的?”
“他们还说大贵捐钱建校,是你想从中捞一把!”
“捞什么?”
“捞一个铁饭碗!”妻气愤得快哭了,“说你让大贵给乡上谈条件,把你转成公办。”
“什么?! ”
“现在都说是大贵中了贼计,吃了哑巴亏!”妻捂着嘴,呜呜地哭起来。世间哪个女人甘愿别人往自己男人头上扣屎盆子?
我听得两眼冒火,扔下粉笔要去找他们理论,却被妻一把紧紧地拽住。“巴掌再大,也难捂众人口!你找谁去说理?你还是让大贵别捐这款建这楼了。咱背不起这黑锅!”
六
山里的天,小孩的脸,说变就变。那阵子还骄阳似火,不一会儿,便雨横风狂。我还是按捺不住,蹚着雨水急急地回村了。我没进家门,就去找朱大贵。
我并不是像妻说的那样,去劝阻大贵。和捐资建校这样的义举比起来,我所受的那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更何况,中伤我的又全是无中生有的流言蜚语。我只想和大贵说说话,吐一吐心头的郁闷,舒一口气。
朱大贵听了我的倾诉,一点也不惊讶,反倒呵呵一笑。“你先擦擦头上的雨水。”他递给我一条毛巾说,“亏你还是个教书先生哩,又在村里待了这么多年,还是不懂啊。”
“不懂什么?”我蒙了,不知他说什么。
他见我依然愣着发呆,给我倒了杯热茶,按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说:“我刚出去打拼那年,身无分文,饿着肚子跑回了家。我娘却得了急性阑尾炎,痛得她黄豆大的汗珠子从额头往下滚。为了给我娘看病,我借遍了这个村子,遭了不少白眼,却没借下一分钱。后来碰见你刚从学校回来,把刚领到手的五十六元工资全部借给了我。”
这件事我也记得,为这事,我还和妻大吵了一架。那钱本是我打算买化肥的,但看到他火急火燎的样子,就全借他了。那年夏天,我没往苞谷地里施一粒化肥,哄了庄稼地,到了秋天,包谷棒子只有鸡蛋那么大,欠收了不少粮食。冬天正是肥猪蹾膘的时节,可我家那头猪缺食少料,没养肥就送收购站了。直到现在,每逢给苞谷田里施肥,妻仍旧叨叨当年这事。我不仅亏欠了庄稼一料子,更亏欠了妻一辈子。
“后来,我时来运转,空手套白狼,发了家,就有人满脸堆笑地找上门来,或求我帮忙给孩子找工作,或向我借钱。乡里乡亲的,只要我能办到,就从不说二话。”朱大贵一脸平静,好似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可是,我帮得了他们这些,却帮不了他们除掉身上的那股子风气。”
“哪股子风气?”
“你还不明白?”朱大贵顿了顿,像在思索,又像在等我回答,末了,见我不言语,便接着说,“你穷了,他便笑你,用指头戳你的脊梁骨;你富了,他便妒你,用唾沫星子想淹死你。”
“但我见他们现在都夸你,捧你,你说啥,他们都当真理听哩!”
“呵呵,那只是表面罢了,你还没吃透骨子。”朱大贵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咱投资建校,多好的事呀,背后招来的却是一片风凉话。肚皮里的那颗心不是明摆着?”
我仔细琢磨着朱大贵的这番话,回想着老槐树下的是是非非,真有醍醐灌顶般的感觉,心里的那种憋屈似乎也烟消云散了。
“在咱村里,我唯一敬佩的人就是你。”朱大贵给我的茶杯里续了些水,说,“你从不卑贱人,也不吹捧人,平平静静地教书,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本来日子就紧巴,孩子上大学,老人看病,都自己硬扛着,牙缝里没给我透一丝气。”
“那有啥可说的?是福自己享,是罪自己受。”
“咱老槐树下的娃娃们将来都能像你这么正气就好了。”朱大贵说着,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对了,今早上碰见卫生所的刘大夫,听说你欠了六百块钱医药费,我已替你清了。”
“这不成,咋能让你替我还账?”我连忙摆摆手,但我知道现在我的兜里别说六百块,就连六十块也拿不出,只好说,“我后面一定还你。”
从朱大贵家出来时,早已风停雨住,村子西边天际铺满了红红的火烧云,锦被一般层层叠叠,蔚为壮观。天放晴了。
七
朱大贵捐资建校的计划最终还是落空了。
村长从乡上回来,水也没喝一口,就找我和朱大贵。他说:“县上已经开始整合乡村教育资源。咱村这小学马上就要被撤并到河湾小学了。”
河湾小学在十多里外的邻村,那里学生多,老师也多,而且教学楼、微机室一应俱全,还是县上的山区示范校。
朱大贵却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懊恼地一言不发。我理解他的心情。一口烧红了的大锅,猛然浇了一桶凉水,后果可想而知。
“那大贵捐资建校的事咋办?”话刚一出口,我就觉得自己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只是觉得不问个明白便辜负了大贵一片好意,“难道喝凉水还真塞牙缝,这样的好事也办不成?
“能办成。咱这儿离河湾小学十多里路哩。”村长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那路也得好好修一修了。”说着,他瞅了瞅朱大贵,像在期待着什么。
朱大贵听明白了村长的意思,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摇了摇头,转身走了。
村长叮咛我去做做大贵的思想工作,并说,只要大贵愿意捐资修路,村上为他披红戴花、树碑送匾都行。
“我又不是慈善家,捐什么款,修什么路?”朱大贵一副八头牛也拉不回来的架势,还没容我开口,就回绝了我。
“那你先前为什么要捐资建校?”我问。
“你又忘了,我在学校有块心病!”大贵一下子激动起来,大声地回答我,“还有,就是想让娃娃们学好文化,学会做人。”
“可那条路就是咱村娃娃们的求学路呀!”我也大声起来,“你去看看那条路,翻梁过峁不说,光就牛鼻山那段,不知多少大人下雨天滑到山沟去了!那么小的娃,怎么经过?”
朱大贵只是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烟雾缭绕在他的秃脑袋四周,一声不吭地任由我去说。我从未见过一向潇洒的朱大贵如此纠结。
“是不是又心疼钱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算了。你开你的宝马,坐你的飞机,走你的阳关道;娃们在山沟沟里摸爬滚打,过他们的独木桥。各有各的命,两不相干!”
忽然,朱大贵扬起胳膊,把手中的烟蒂砸在地上,一脚踩灭,厉声说:“球,修路!”
八
三月后,正是学校秋季开学的日子。一条平坦的水泥路修成了,玉带一样缠绕在半山腰,一头连接着老槐树下,一头连接着河湾小学。
村里人在大路口敲锣打鼓,举行隆重的剪彩仪式,就连县上的领导也来了,但主角朱大贵却没有到场。村长略带几分尴尬地向众人解释:“我早叮咛过大贵了,再忙也得赶回来,披红戴花,亲手剪彩。”说着,村长又去拨打朱大贵的电话,可是依然关着机。或许是他忘了,或许是他不想参加。谁又知道呢?
就在这天,我离开了村子,离开了老槐树,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路。两校合并,师资充裕,已不再需要我这样的代课老师了。我没有丝毫的失落,反而就像拥塞在袖管里的衬衣袖子一下子被扯展了,心里舒舒坦坦,妥妥帖帖。
在村口,妻把一个布包塞到我手里,热乎乎的。我问:“里面装的啥?”
“烫面油饼子,你最爱吃的。”
我心里顿时一阵酸楚,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是叮咛:“别忘了,还大贵的六百块钱。”
“你放心,等猪一卖,我就去还。”
忽然,听到头顶一声长鸣,抬头看时,蓝天碧宇中,一只孤雁正伸着脖颈,扇动翅膀,奋力向南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