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向切入的断面呈现:碎片、关键词、话题、词条
2019-09-28谢端平
文/谢端平
萧相风这样解释《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以下简称《词典》)的创作:“是生活碎片化的结果。不单是与现代工业相关的生活,其实现代社会的一般生活是琐碎的、混沌的。尽管在全媒体时代,人们了解更多听到更多,但是生活充满了关键词。”“一开始,我写了一个‘打工’词条,作为第一个词条自然牵引出另一个或两个,就这样,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词典了。其实散文形式更适合用词典的形式。同时,我借用ISO标准中系统文件的做法,在各词条间建立联系。”“每一个词条都是一个话题,我的想法是如何将个人经历与公众话题相互结合。”(见《萧相风:记录词典中的南方》,《中国改革》2013年第4期)从碎片到关键词再到话题进而形成词条,四十六个词条中除了ISO、QC、走柜等几个词条属于外延较广的工业生活外,其他皆与打工生活有关。《词典》对打工生活进行了高度概括和升华,不仅是了解深圳的一个窗口,而且对整个时代,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数以亿计的以打工为目的的人口流动,作了非常精细的记录,正如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奖的颁奖词所称:“从无可置疑的个人体验出发对这个时代工业生活做出了大规模表现和思考。”
在《词典》中,打工不再是生活所迫的结果,而是在工业中劳作和生活的自然存在,就像柴米油盐一样实在,有苦必定也有乐。这种对待打工生活的态度在打工作家中是非常特别的,难能可贵的。“集体宿舍”词条中老贾觉得集体宿舍挺好,经常带老婆来睡觉。“我”回来后细想,这个老贾也真的是集体惯了,大概喜欢在集体宿舍里吹牛海侃,可以和众工友窝成一圈斗地主,顺便可以和老婆开火车。至今“我”觉得他的手势很潇洒:“各位兄弟,没事!将就了。”词条结尾将一首诗送给流水拉,似乎流水拉是他的故友或新朋。陶潜歌颂田园,彭斯歌颂土地,哈亚姆歌颂美酒,李白歌颂大自然,而萧相风歌颂以流水拉为典型物象的工业生活,每个时代都有独有的文学,也都有独有的作家。对一些不平等或不合理社会现象,《词典》作了独到的分析,“摩的”字条中摩的是穷人的工具,也方便了大众,摩的禁止后升级版和低碳版电动车上路,“我”坐电动车和三轮摩托车的经历有惊无险并充满趣味,“我”断言摩的无法在珠三角大地上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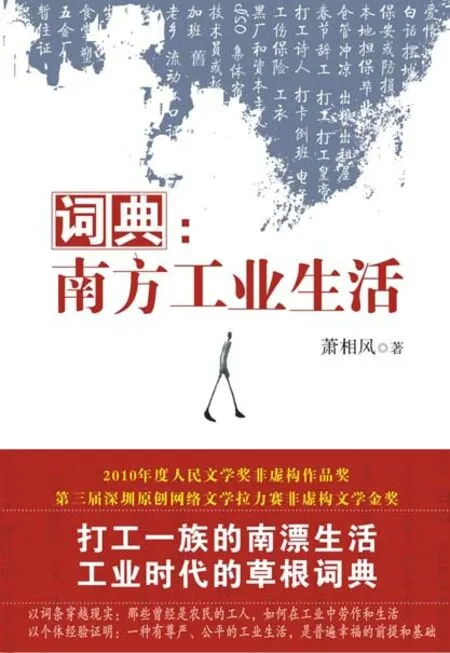
萧相风对诗歌情有独钟,著有《中国现代诗歌普及十讲》,自印诗集《噪音2.0》。《辞典》中穿插了他的四首诗,用婉转曼妙的诗意化的语言,表达了他自己对南方工业生活的深切感受。“这样诗化的语言,是一种写实中的亲切与坚韧的魅力。”(见《体验的现场/读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文艺争鸣》2011年第3期。)很多词条就是充满激情的诗,“技术员或扳手”词条中扳手不再是冷冰冰的钢铁物品,而与他相融、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扳手是一件多么诗意的工具,在诗歌中我多次使用到它,我用它拆掉那些陈旧的比喻和繁冗的句式,再拧紧我身体里那些松动的螺丝。”他在一线生产员工岗位做了五年多,后来做的管理工作也与一线生产紧密关联,见惯了太多的钢铁设备,这些设备在他笔下都成了温暖的存在,赋予了生命和活力。“螺丝只是机器里无处不在的助词,不,是连词。也不,是标点符号。螺丝构成大工业,构成世界的存在。”“每天不断地弹动,受压,再弹回,弹簧被赋予了最坚韧的品质。”“机油又是另一个温柔的元素。”“流水拉”词条有考据有见闻,并联想到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和唐诗宋词里欸乃一声的渔船,动情吟咏:“在流水线上没有转折符号、顿号和逗号,流水线就是一篇没有标点符号的文言文,甚至一气呵成而没有句读。” 试图对工业生活作出概括,必然要涉及丑恶事物,可《词典》刻意隐恶扬善。“老乡”词条歌颂了纯洁的老乡情:“在异乡的土地,我们似乎找到了一盆家乡盆景,大家共同的方言聚在一起,拢成一片故乡的云。”“老乡是一个出门在外的生词,一双漂泊异乡的布鞋,一顶土祠或公社时期的破帽毡,是一粒临时抵御乡愁的安定。”该词条坚决否定“老乡老乡,背后一枪”说法,认为放枪是人性问题,与是否“老乡”无关。
《词典》致力于记录与表现,以素描手法临摹现实或真实。萧相风自称进行了“纵向切入”,“非虚构作品与小说相比,它的取胜点在哪里?虚构的魅力是多么不可抗拒,对于作者而言,可以大开大合,选择不同的叙述视角,利用丰富多样的技法,挥洒自如而淋漓尽致,结构自己的文本;对于读者而言,可以在阅读期待中获得更多的传奇、巧遇和戏剧性。而非虚构呢?的确,非虚构作品的魅力是真实,但是难道仅仅在于真实吗?如果这种真实没有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真实就会沦为一种平庸的真实。在立足于有限真实的基础之上,它需要作者更多的艺术构造能力和付出。撇开写作能力不谈,首先需要在取材上获得较大优势,这是决定非虚构能否成功的首要条件。尽管现实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题材,但是如果不与之主动建立广泛而巧妙的联系,作者就无法自觉地发现美、成型美。因此,‘介入’和‘行动’成为目前非虚构作品的关键词,行动力也就被提上了日程。”(见《从〈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出发》,《文艺报》2011年4月20日) 《词典》是来自内部的书写,表现之一是作者身处“内部”,二是以“内部”的姿态,而不是高高在上地审视。“‘现场’,在这里是一种被记录的‘现场’,而这种记录,又是体验中的记录,故这种现场感的获得,是记录现实与体验现实相结合的产物。‘行动’,顾名思义,是要以实际行动代替‘书斋式’的空想,代替一叶障目式的书写,离开数字化、电子化的媒体和信息来源,到真实的‘现场’去体验、去感悟、去书写,用‘行动’进入文学的‘现场’,再用‘非虚构’的方式把这种原生态或者说粗粝的‘现场’体现出来。”“他以自己丰富而典型的打工经历为主要内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南方工业生活场景,一个他所亲身经历的南方工业生活的场域。这种极具‘现场’感的叙说,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真挚的生活体验、蓬勃的生命气息、向上的进取与探寻状态。正像有人所说的,萧相风不是到现场去,而是本身他就浸泡、裹挟在这种工业生活中,对生活是零距离的感悟。” (见《体验的现场/读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文艺争鸣》2011年第3期)
一直以来,打工文学存在“概念化”的问题,但《词典》基本上走出了概念化的泥淖,人物和故事情节复杂多样,打工生活丰富全面,看法比较客观,并带有一定的历史观。“打工诗人”词条中批评了打工诗歌中普遍存在的“苦难叙述”嗜好:“大概不直白、不愤怒、不宣泄苦难就不是打工诗歌,甚至在部分打工诗歌界内部也形成这样的认识误区。”“打工作家”词条这样分析:“有趣的角色转换让打工作家有别于传统作家,即创作者与创作对象是同一的,自己写自己。打工者写打工者的生活,无需他人代言。”“保持自己的个性和生活的血性,是打工作家必须坚持的一点精神。进步和包容不是向某个方向媚俗。” 打工文学至今已经35年,打工作家作了多方面的探索,《词典》以别具一格的方式纵向切入改革开放,切入工业生产现场,切入打工生活,切下的碎片(细节和观点)金光闪闪,组成的关键词林林总总,建立的话题沉重而新鲜,成就的词条各有春秋。贺绍俊认为《词典》是“非常有创意的一部作品,不逊色于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词典》在打工文学史上具有象征意义,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意义将更显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