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山日长
2019-09-20久久
久 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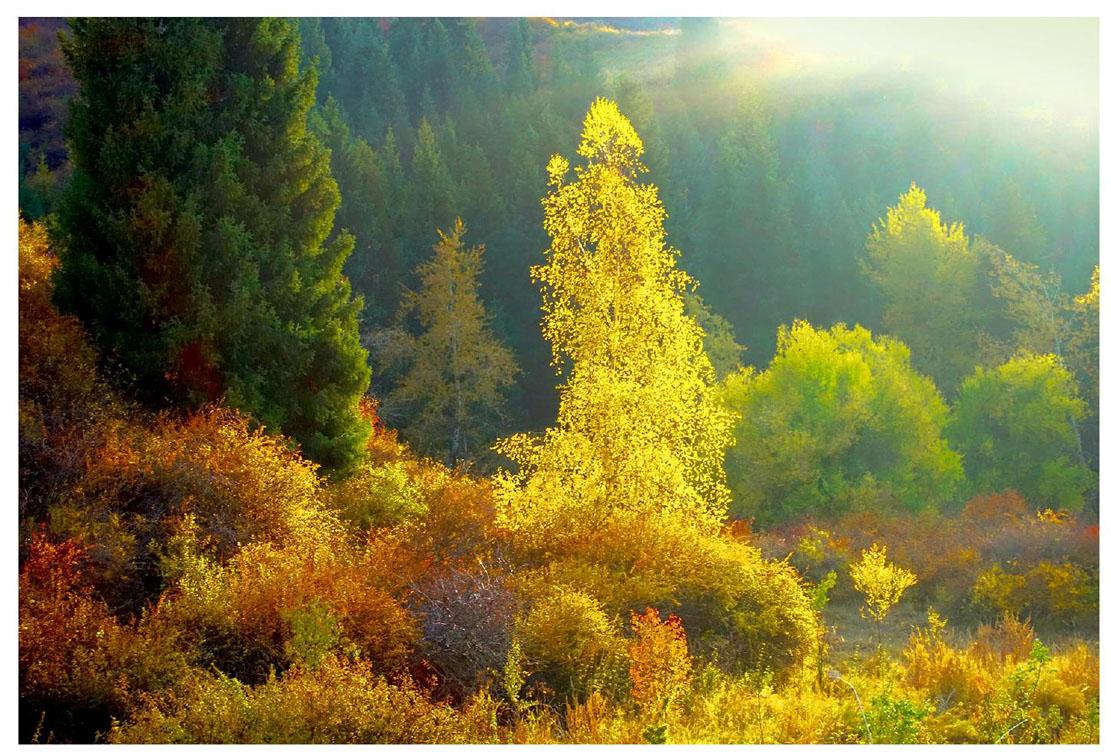
山,是几百万年前就有的山,它的样子一开始就这样,今天还是这样。孩子每年都会长一点,据说山也会长,如今的高度是多少,不得而知。谁能说那么准呢。
静,是山给我最深的印象。在乡村的麦场上,或者自家的院子里,或者从八楼办公室偌大的窗玻璃望去,山总是那么安静,似乎自己发出喧闹的声响就是对它的冒犯和不敬。
这个山,普通得很,是地球上众多山系之一。可这座山细说起来就不普通了。不普通是说在整个亚欧腹地,它雄踞其中,东西绵延达二千五百公里,而南北最宽处则有八百公里。
山不仅是山,最为关键的是山上有雪,这可是很金贵的东西,说它是乳汁有点俗气,可事实上,山中溪流发源而成的河流,滋养了整个欧亚大陆,这么说,稍有地理常识的人就能理解,因此一点也不过分。
它太庞大,我是从它其中的一段看它的,准确地说就是从东天山的博格达山窥视它的。
更多时候,我和我周围的人,说山的时候都指向博格达山。
一
近,是我小时候对山的认知。觉得它离我很近,手一伸就捉住了它高高的帽子。我说是帽子,有伙伴们说是皇冠,三个高高的山峰极像神话故事里王后的皇冠。
一场春雨过后,我在一条三四米宽的乡村小路上,向它奔跑而去,我想摘下那顶皇冠,戴在自己的头上。这时候,我有八岁了,可以戴着它,骑上爷爷饲养的那匹红色的马,向更远的地方而去。
我想象着戴着银光闪闪的皇冠,骑着高贵的马,我是尊贵的公主。
小路的尽头就是山,只要一直沿着小路跑下去,一定能到达那里。我从没有怀疑过,会有另外的路通向那里。
山,看着并不遥远,依我的体力,完全可以跑到那里,我兴奋的眼睛,发出银色的光芒。我相信我得到了山神的护佑,不会遭遇猛兽的袭击,而顺利登上山顶。虽然我早已听爷爷说,那里有雪豹、有狼、有熊、有野猪等。听起来很可怕,我没有见过它们,对它们也没有畏惧的心理。
拦住我的不是这些猛兽,是一条怀抱着五彩石头的河。这条河我不陌生,母亲常来这里挑水,我也在河边玩耍嬉戏捉鱼。
我愣住了,河水像是生气了,清澈的河水,怎么混沌成黄色,怒吼的声音,吓到我了,惊恐中,我向后退去。
如果不是这条河拦住我,定能跑到山那里。对此我很确信。
我坐在河边不远处的一块泛着绿色的石头上。我想,也许过一会儿,河水就恢复了原来的样子,那样我就可以过河了。水至多到我的膝盖处,哪怕再高一点,只要我能过河就可以了。
我双手托着下巴,目光捉住山的眼睛,问它会不会等我,问它会不会逃跑。半天也不见它回答,我有点急了,跺脚哭出声来。往日温顺的河欺负我,那么你也要欺负我不成。我把头伏在膝盖上,哭得声音更大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哭声惊扰到了河水。咆哮的河水声居然变小了。我站起身子,再次向河边跑去,忽然,那山顶有两条半圆状彩色丝带清晰耀眼。
我顾不得脚下,径直奔向河中,我不能再等了,这么大,我第一次见到两条彩带,平常多是一条,还犹豫什么?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一匹马,勇敢的小马!我不曾畏惧什么,只想勇往直前。
事实上,我刚踏入河中,就被汹涌的河水推翻打到,滚入浑黄的河水中,顺着河向下而去,我无力呼喊和挣扎。身子失去了重量,跟蝴蝶的翅膀一样那么轻。
一只粗大有力的手抱住我的身子时,我已经说不出话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来时,是在一张白色床单的床上,床边站着爷爷、母亲等人。
他们一脸的不安,这我能读懂。他们总是对我不放心,似乎我跟家里那条小猫、小狗一样,跑出去后,总担心会被人抱走,或者迷路,找不到回家的路。
我都八岁了,怎么能跟猫猫狗狗们一样呢。我想不通,这样的担心。偷偷会笑他们。当然不能让他们看到,看到了,又会说我傻。
我不傻,这我知道。如果我傻,就会跟那个在村里四处捡垃圾吃的人一样。可我从来没有随便在地上捡东西吃。凭什么他们就说我傻呢?
有人喊母親去地里干活。爷爷留在身边。
液体输完后,爷爷抱起我。他的手指干瘦,但却很有力量。我爬在爷爷的肩头,想去骑马。便对爷爷说了。
爷爷拍拍我的身子说,傻丫头,身子这么虚弱,还要骑马?真是不要命了。等过几天,爷爷带着你去骑马,你说去哪里都行?
真的吗?我问。
爷爷什么时候骗过你?说说看。
想想,爷爷真是说话算数的。带我去县城赶集,带我去省城人民公园坐木马,带我去更远的东山挖野蒜。
那好,带我去把那顶皇冠摘下来,我想戴在头上。
说着,我举起右手指向那白色的博格达山。
它一直都在那里,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也不管是春天,还是冬天。似乎它一直在等待我的到来。
爷爷的目光顺着我的手望去,只停留了那么几秒钟,目光收回落在我的脸上,哈哈大笑起来。河水一样的笑声明朗欢快,夹在风中奔腾而去。
爷爷的笑把我的好心情拦腰砍断,我撅着嘴,头一歪,把手装进衣服口袋。眼睛低垂什么也不想看。那一瞬间,我有点难过。最亲的爷爷也不理解我的心情。我只不过是想要一顶皇冠而已,我没有要粉色的裙子,红色的皮鞋。干吗要笑我。
细想着,眼睛就发热起来。每当这个时候,泪水就不请自来。我管不住它,它也从来不听我的。想来就来了。
泪水从眼眶一路流下来,吧嗒吧嗒地钻进爷爷肩头的蓝色褂子里。我细微的抽泣,让爷爷心疼起来。爷爷语气柔和放慢说,等下次去红山商场,给你买个发夹,戴着一定很好看。那个皇冠呀,别急,你还小,等长大了,再说。
我已经长大了呀,我抹一把眼泪说。
嗯,你是长大了,等再大一点才能去那里。你看着很近,其实远着呢,坐汽车都要好几天。爷爷说。
对爷爷的这个回答,我有点怀疑。还不是怕我掉进河里,才这么说的。
我趁着爷爷回屋的空档,顺着木梯子爬上了屋顶。这是家里最高的地方。这样就不怕树挡住我的视线,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山了。
这个时候,我觉得山有点像爷爷,慈祥平静。我能清楚地看到它脸上的一道道深浅不一的皱纹,还有一块一块大小不一的阴影斑点,像是爷爷脸上的老年斑。
难道它真跟爷爷一样,那么它会不会像爷爷一样也生病住院呢?会不会像邻居爷爷死去,被埋在东山高高的山岗上。
忽然我为洁净如玉的博格达峰担心起来。
这种担心让我睁开眼睛就想看到它。早晨起床飞跑到院子,看它安然无恙,便安心去吃饭,背着书包去上学。
刮起狂风时,我又担心起来,会不会把它裹走。心怦怦乱跳。直到风停下来,看它好好的,我才会踏实睡去。
这样的担心一直伴随着度过整个童年时光。
日子一天天过去,山没有变,我长大了。院子里的树长高了,
二
从米东区柏杨河一路向上,在独山子村一处算不得高的石壁上,我看到了许多岩画,岩画的图像以动物居多,马、羊、狗、牛、鹿等。
这样的岩画散落在整个天山山脉,博格达山的岩画是其一部分。
乌黑发亮的石壁,如果不仔细看,很难发现这些画的踪迹。三千多年的风蚀日晒,最初鲜亮的模样,早已被时光偷走。如果遇到水,生动鲜活的画面就会跳出来,说不准,会吓到你的眼睛。
有一年,我陪采风的作家和摄影家抵达这里时,已经是晌午了,好在太阳不大。将矿泉水瓶里的水,洒一些,一幅幅千年游牧生活场景流淌进视线。许多人跟我一样兴奋,目光牢牢锁住画面,不时听到有人惊叹的唏嘘声。
画中的羊有的犄角弯曲,胡须飘然,健壮肥硕,形象逼真。不难看出这是北山羊。
还有一幅图刻画的是一位牧人,做拉弓箭状,身体微微前倾,弯弓搭箭,似在射猎一只惊恐驻足的小鹿。
每一幅图都是有故事的。这些画作的原创者是曾经活跃在天山的塞人。这个曾经称雄一世的彪悍的游牧部落,我是从考古文献中获得那么一点信息。他们戴着高高的帽子,喜欢金饰,骁勇善战的塞人,逐水草而居,连绵的高山草场,山下是流淌不息的水磨河,在此生息,可谓天然福地。
今日,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族牧民,从更北边的阿勒泰迁居而来,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我好奇的是,塞人既然在此游牧生活过,除了这些岩画,是否留下墓地呢?那里一定有更多塞人的信息。
我在长长短短的沟里走访牧民时,都会问一下情况。多半都是摇头。当然从文物部门得到的消息是,这里发现过古墓,但不是塞人。
那么这些塞人去了哪里?我又追问。翻阅资料获悉,新疆的古塞种人,在漫长的历史中被其他部族征服,逐渐融入其他民族中去了,今天分布在新疆的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族是古塞种人的后裔。
一晃就是三千多年,听起来很遥远的事情。我倒不觉得。在第一场秋雨过后,我信步再次登上了刻有岩画的石山。
在一幅刻有马的岩画前,我停下脚步,端详了好一阵。腿有点发困,我索性蹲下身子,坐在岩画旁一块长有青苔的石头上,潮湿柔软。岩石上的马昂首,前蹄跃起,精神亢奋状。我想这是一匹年轻的马驹,才这么意气风发。看着看着,我笑起来,好像自己是个老练的相马人,只那么一眼,便知马的全部信息。
在村子里,爷爷喂马,十几匹马,秉性我熟记于心。
我曾在本地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上过班,在那里见到更多的马。但离真正的相马人还有差距,不能说,知道马的秉性就算熟知马。这里有大学问。
马,我骑过。最初是爷爷带着我。后来,我一个人骑一匹马。马跑起来的感觉如飞一样,有种梦幻的感觉。这是一匹马。那么如果是几十上百匹,或是几百上千匹马同时飞驰,又是什么样的景象呢?
这些塞人,不,还有那些以马为伴的游牧民族,在马的承载中,自由奔放,洒脱豪迈,自然而然就融入血液中,不管过了多久,基因强大的繁殖能力,会让这一品质,一代一代继承下去。
万马奔腾,气势浩荡。不管是三千年前,还是今天,同样会撼动人心,触及人的灵魂。人要有精神气,大概先要向马学习。那一刻我有了这样粗浅的顿悟。
忽然,一声马的嘶鸣,将我从岩画的想象中拉回来。我扭头寻着声音而去,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骑着一匹油光黑亮的马,在山脚下,向我投来打探的目光。
我举起双手,放在嘴边,做一个喇叭状,大声说,我在看马呢!
那黑油发亮的马,身子转了一圈,马侧着脸,那神情似乎在说,活生生的马不看,看一个不会呼吸的马,真是莫名其妙。
奇妙的事情很多,远不止这些岩画
我从山上下来,顺着一条羊肠小路下到水磨河边。
把鞋子甩在一边,光脚蹚进河里,冰凉入骨,心猛地揪到了一起,也只是那么一会,适应水温后,却觉得极为舒服。
脚掌踩在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鹅卵石上时,我觉得时间跟水一起在倒流,回到了成吉思汗蒙古大军西进的那个时代,他的儿子察哈尔在封地上经营着自己的部落,便在那高高的山岗上,垒砌了一个飘着五彩经幡的敖包。一处山湾过去,平坦的坝子上修建起一座宏大的喇嘛庙。一时间,香火鼎盛,让寂静的山湾活络起来。骑馬的,赶车的,步行的人,在他们认为重要的日子,不远百里千里都要来虔诚地向菩萨上炷香,许了愿,祈求菩萨的护佑,寄托自己的精神。
这个过程少则一二日,多则三五日。他们便收拾好行囊,将马喂饱饮足,肩挑夕阳,头顶星辉,再一个个向各自的牧场而去。
时间继续向后退去。吟诵着明月出天山的诗仙李白,马蹄驰骋,长鞭飞扬,他是不寂寞的,高山长河,红日落霞,无不触发他的情志,以诗表意的名篇佳句便流传至今。
镇守西域的瀚海军的将士们必定翻越天山,跨过诸如水磨河这样的源自天山某一沟壑的河流,自东向西,或自南向北,将王朝的旨意一级一级传达下去。
蹿天的烽燧烟火,驿站的昏黄油灯,古城的飞檐角楼,清晰的车辙大道,疾风的狂舞大雪,一次次又出现在岑参饱含激情的诗中。
水,是让人有追忆的意境。闪着银光的水波从峡谷中飞奔而来,击醒石头一样坚硬的记忆。
随手从河中捡起一块石头,是那种淡绿泛青的圆石。令人眼亮的是,在石头的顶端有两个圆圈,一大一小,像是变魔术的人,戴着一副夸张的眼镜,站在观众面前,期待那扣人心弦的一刻。
继续往前,一块手掌大红色的片石上,一道海浪状的白色波纹印刻在其间。似乎我就在滚滚巨浪中穿行,而这片红石就是我的护身符。
左右手各拿一个石头,在清澈的河水中慢行,我想,已经回到了最远古的时候,因为我手里有那个时代记忆的信物。
三
当雪裹住大地的时候,一切都安静下来。
雪后的柏杨河村格外地乖,连平日里的狗吠声都缩回去了。我散漫地在村里游荡,心想,能与一头花牛,或者两头黄牛相遇,看看它眼里的山,是不是还是绿色。至少可以跟一只穿了新棉衣的大尾巴羊,狭路相逢,问一下,它产的那只小羊,这几日是不是已经不害怕黑狗的叫声了。
对了,那头灰驴还去圆疙瘩山下吃草吗?
圆疙瘩山上有一株树,是一株榆树。谁种的?什么时候种的?没有人知道准确的信息。在此居住了七八代的郝氏家族德高望重。我的二姨说,这棵树,在她爷爷那辈子就有了。
这么说,在一百多年前,这棵树就在山上扎下根。那么遇到干旱少雨的年份,山坡上的草,统统都干枯而死,唯独这棵树,似乎得到了神灵的护佑,跟没事似的,顽强地活着,只是枝干不曾像身居河谷的榆树们,那么粗壮敦厚。
这样神奇的一棵树,被山里视为神树,有三三两两的善男信女们,彼此相中,许了终身时,便到那棵树下,在树枝上系上一条红色的丝带,寓意爱情如这个树一样,经久常青。
村里最威武的那几匹枣红马,常在河边吃草,今天怎么不见了?我任性踢了一脚路边的雪疙瘩。飞溅出去的它落在一块不规则石头上,石头毫无伤痕,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刚才的一幕。
静逸的村子,需要有点声响。常常在树林中飞上飞下的喜鹊、麻雀跟商量好似的,集体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一个都不露面,真是邪乎!你们真要是赖得出来溜达,我是要走一走的,不然辜负了从容淡定的雪,她可是走了一夜的路程,才赶来的。
一路向东,坡度越来越大,扯开厚厚的云朵,太阳也是越来越大,不过半个钟头,路上的雪开始有融化的迹象。柏油路边缘的雪,渐渐发黑,不多时,路面有了湿漉漉的印迹。
过了老牧中,从医三十多年的表哥跟我聊起当年在新地梁拾麦穗的情景。天不亮就来,到下午,整整一麻袋的麦穗,一个人扛在肩头,一口气走几公里的路程,额头脖颈面颊都是豌豆大的汗珠,撩起衣襟擦一下,又急忙赶路。在整个割麦的日子里,十几岁的他跟家中几个姊妹们都加入拾麦穗的队伍中,这多出来的麦子,将是他上高中时带到学校去的口粮。
边说边走,转过一个山湾,眼前是一排排整齐的哈萨克族风格的砖房,牧民定居点的落成,让表哥很难将这里与曾经大片大片的旱田联系在一起。
馒头一样的山丘已经被平整出来,一栋栋白色的房屋如雨后的蘑菇,立在天地间。
表哥手搭凉棚,向远处的山峦望去,层层叠叠的山后,是清晰俊朗的博格达峰,时光在变,曾经的山丘夷为平地,再变,而唯独屹立万年的山没有变。
长大的人,如今把家安在山里,就是想与山厮守一辈子。
院子里木质秋千椅孩子们喜欢,我也喜欢。坐在秋千椅上晃来荡去,抬眼可以看天,那种蓝得简单纯粹的天。可以看山,就是从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窥见它的博格达雪山的最高峰。在一个夏日的清晨,我依靠在椅子里,东方飞出藕粉色的朝霞,这是你送给我的衣裙。欢喜中,把你藏在天山上的云里,不让别人看见。
太阳走过一条优美的弧线,当我将一枚籽粒饱满的西红柿送进胃里时,四周便沉入一种期待已久的暮色中,我摇动着秋千椅,在惯性的作用下,一种飘荡的快感,让人充满遐想。此刻,从肃穆的博格達峰后,羞答答探出月牙的眼。以为她只那么一看,会心闲安稳地睡去,哪知道,怕我在秋千上孤独,不管不顾地猛地一跃,露出饱满温润的脸。寂静空旷的夜幕下,蝉鸣悦天耳,南风柔如水,我向它狂奔而去,生怕黎明的曙光,蒙住我的眼和脸。
久久,本名段蓉萍,女,汉族,新疆乌鲁木齐人,新疆作家协会会员,爱读书,喜旅行,闲暇写作,有散文、小说先后发表于《回族文学》《西部》《绿洲》《清明》《红豆》《山东文学》等。
作者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