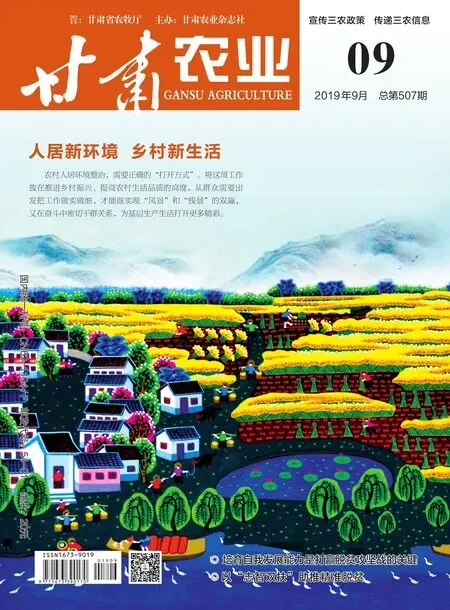从《故园往事》看农村百年变迁
2019-09-19张远欣
张远欣
我生于1971年,12岁前生活在河南农村。1978年前,父亲在兰州工作,母亲带我们四个孩子留在老家。当时还未包产到户,童年的记忆,常常吃不饱,总是期盼早点吃饭。1978年,农村包产到户,我家也分了十几亩自留地,盖了三间瓦房。吃饱饭已不成问题,但经常吃粗粮,麦收、过年或有事情招待人时,才吃白面馒头。1983年,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农转非,我们全家迁往西北省城兰州,从此成了城里人。中学毕业,考取中国石油大学,1993年毕业,回到兰州,在一所高校当教师,1996年结婚,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
爱人家在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宝积乡下的一个小山村——窎沟。婚后第一次随他回家,是我时隔十几年后再一次接触农村,也是第一次体验甘肃农村生活。甘肃农村与我童年生活的河南农村有很多不同。甘肃的村子与村子相距太远,我第一次理解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感觉,从兰州坐班车经过靖远、平川,爱人说快到家了,换乘农村的手扶拖拉机。破旧的车子离开城镇 ,颠簸在乡间砂石土路上,满眼是田地或荒地,大片干旱的黄沙地面有着一片片稀薄绿色,铺不满土地。而河南夏天的乡下,满眼都是绿色,一眼无际的田地里生长着适合那个季节的多种作物,玉米、芝麻、高粱、棉花……
进村子,看到很多树,尤其是果树。那是八月份,苹果、梨、枣挂满枝头,西瓜、黄河蜜瓜、高粱、玉米也生长得很茂盛,生机勃勃。看来只要能浇上水,土地里就能长好庄稼。
爱人家的房子边是黄土山,房子也都是黄土建造,从后面看,低矮的土墙,下半截用石灰涂成白色,平顶, 诧异这么低矮的房屋怎么也能养育出几个那么高大的汉子。
门口黑狗叫着,迎接我们进了院子,地面也是黄土压实的,平平展展,干干净净。西边开出有一片园圃,种着玉米、波斯菊和几棵香水梨树。正面几间房屋,中间一间最大,是正房,河南叫堂屋,这间正房大约等同于三间普通房屋,正房东侧是大炕,公公婆婆住的地方,炕头靠墙有床头柜,被子都整整齐齐叠放在柜子上,炕上铺着竹席和布单,炕边铺的人造革塑料,便于打扫。堂屋正中墙面悬挂着狄水池、陈伯希先生的书法作品,靠墙摆放一张写字台,上面有花瓶、收音机之类物件。堂屋西侧区域是“客厅”,也是用餐区,有两个单人布沙发,一个低矮的方桌,几个小板凳。屋内地面用砖铺成,已经二十多年,坑洼不平,但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婆婆与很多农村妇女一样,未必知道《朱子家训》说的“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但她们每天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扫卫生。
正房两边是两间“耳房”。这个词我第一次接触,想想还真贴切,“耳房”分布两边,比正房小得多,真像两个耳朵。这座院房子1974年建成,当年是村里最好的。当时爱人不满6岁,二弟4岁,三弟刚出生,所以奶奶给他取的小名叫“院院”。按照农村传统习惯,东为上,东厢房是大儿子婚房,西厢房归二儿子,三弟将来娶媳妇住哪呢?院子东边是厨房,有两大间,用墙隔开,厨房带的那间房子归三弟结婚用。这虽然是玩笑话,但很多农村兄弟多的人家大都这样分配。
我和爱人在老家住了一周。婆婆在属于我们的东厢房门上贴了红对联,房子内就一张简易的铁床,这还算是比较洋气的家具了。一年后,二弟结婚。过年时我们都回老家,各自住在二十多年前父母规划好的地方,二弟夫妇住西边耳房,有一张炕,婆婆把炕烧得很暖和。我们夫妇在东边耳房,里面架了铁皮炉子。三弟住在厨房附带的那间屋子,也有炕,暖和。那时他们弟兄三人都在兰州、白银工作,家里的房子也就过年回家时住那么几天,热闹热闹。
慢慢地,我对这个大家庭有了了解。公公1940年在窎沟出生,属龙,他有一个哥哥、姐姐,五个弟弟、两个妹妹,总共七男三女。农村条件苦,家里集中力量供公公的大哥念书,公公就要挑起家庭重担,从小放羊、务农。公公的弟弟妹妹都念过书,只有他没进过一天学校,但他从未抱怨过。
婆婆是山西乔家大院后人,清朝末年,她的祖上因经商迁到甘肃。婆婆11岁就失去了母亲,在她的奶奶、姥姥和父亲呵护下长大,婚前没有干过太重的农活。1959年,公公19岁,婆婆17岁,他们结婚。之后公公参军,在部队学会开车,后来复员,在乡上开车。那个年代,驾驶员是乡里人羡慕的差事。公公婆婆婚后8年才陆续生了四个孩子,婆婆在家,屋里屋外,田间地头,忙忙碌碌。公公长年累月在外奔波。改革开放初期,他和一帮年轻人创办砖瓦厂,忙乎很多年,创业以失败告终。所幸,他的四个子女都很争气,全部脱离农村,各自都有不错的工作和家庭。大姐高中毕业后,通过农村信用社招考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用。爱人和两个弟弟都上了大学。上世纪80年代末期,农村供养几个大学生还是很吃力的,公公婆婆种瓜种庄稼,含辛茹苦,从土地里刨钱,硬是供出了几个大学生,在十里八村传为美谈。
公公没上过一天学,但是自己通过《新华字典》认识了不少字,喜欢看书看报,喜欢和村里的干部们高谈阔论,讨论时事政治,心里装着天下事。婆婆仅上过两年学,但她颇有大家闺秀气质,性格温和,与人为善,是典型的贤妻良母。1997年,婆婆进城给我们带孩子,公公一个人在老家。婆婆牵挂家里,有时把孩子带回乡下,我们在城里和乡下不断往返。2000年,我们在兰州有了第二套房,将公公婆婆接到城里生活,基本上脱离农村。但故土难离,情系家乡,公公本来就有看书、“写作”的习惯,到兰州后,时间宽裕了,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撰写“回忆录”,作为精神寄托。他这样饱含深情介绍窎沟的历史和风土人情:“……屈吴山向西,分布着许多沟沟壑壑,绝大部分在下游被冲成干涸的沙河,偶有泉眼流出,维系着‘河’的存在。这里处于黄土高原与腾格里沙漠的接壤地带,距黄河尚有30里,透过1030米的黄土层就是岩石层,岩石层下面是条地下河,村里最早的井就是挖出来的,形似蜗牛壳。春天肆虐的风沙时刻在提醒着这里就是腾格里沙漠的边缘,天灾随时有可能降临。早先来此垦荒者都住在窑洞里,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损毁了大部分窑洞,也带走了许多挣扎的生命,这场天灾给人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于是,先辈们开始注重盖房了,至少,在窑洞口搭建‘门房’,形成半房半窑的建筑结构,这样住的人也能多些,老人和小孩住在窑洞里面,其他人就只能在‘门房’安歇。后来窑洞彻底退出居住范畴,只作为库房、粮仓。在有记忆时,大人们就给小孩灌输地震的前兆与危害知识,震前震后也作为断代记忆存续了好长时间……在用井水灌溉之前,农作物只能靠上天赐予水;逢上突发的暴雨,片刻间水就填满整个干枯的沙河,山水携石夹泥惊天动地咆哮而来,勤快的、有准备的人就能提前修好半截拦河坝,在山水小些时就能引水浇上地,来年的收成多少也会有保障。在河沟口或黄土丘陵的边缘地带,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台地,稍加平整就成良田。于是,大大小小村庄便坐落在这些台地上。窎沟村就是这样的一个村子,就人口而言,也算一个大村子。窎沟村位于旱平川南端,属黄土高原地带,土山不大,习惯叫山,其实是土丘,形状好像摆放在那里的一串大馒头。窎沟的地理条件非常好,坝地、川沟、沙地,各种土地齐全,再加上土地面积大,在靠天吃饭的年代,粮食都不太紧张。沙地最可靠,除了绝收年份,每年长一茬庄稼是有保证的。窎沟原为没有人烟的荒地,后被冯家开荒,驻扎于此,渐渐成了村落。最初,冯家是官家移民过来的,最早只有山西大槐树的记忆,再以前就无可追溯了。一开始的落脚地在冯家园(现在的冯园村),是当地人(蒙古人后裔)的佃户,蒙古人的后代不久没落衰败并且汉化了,逐渐地,冯家人成了土地的主人,并进行大量的开荒平地,按惯例谁先占到就是谁的。占有的标记也许就是堆几个土堆,也许就是几块石头,并很快将荒滩野沟变成平整过的土地。当拓荒到窎沟,由于效果好,便留了下来,扎根于此。窎沟村子北面几百亩大片田地,就是公公的曾祖爷爷毕其一生用双手开垦的,过世时手蜷成握着铁锨把的形状,怎么也掰不直。这里地处古代边境地区,连年战祸不断,属地不断变化,加上地震、干旱、瘟疫等天灾,这里人口一直起伏不定。清同治年,冯姓家族遭到土匪洗劫,不知有多少口人被杀。解放初期人口发展到百人以上,是当时甘肃省三大户之一。其实户大家虚,虚有名气,是人们所说的人口财东。”


看书、写作成为公公婆婆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们常常戴着老花镜,不停地写啊写,桌上的手稿越摞越厚。最初,我不经意地翻翻,慢慢地,被他们笔下的那些人、那些事吸引住了,仿佛看见近百年来的甘肃乡情往事如一幅幅画卷,徐徐展开。通过他们朴实的文字,我了解到了那个艰难岁月中的艰难生活。公公记忆力好,他记录了听说或经历的七十余年乡村历史中的人事,读来让人感动。公公这样写他的少年生活:“我能清楚的记事从1946年开始,回想那时候人们的生活那个穷苦样子,人只要把肚子填饱,怎么都能过去,吃不饱肚子不好往过熬。解放前农村普遍经济困难,买日用品得到十几里路外去。就这样的环境人们还是得想方设法生活,没有盐就在崖根或窑洞挖碱土,叫盐呱呱,泡成盐水解决吃盐问题,也可以用盐水熬雪花盐,酱醋从来都是自家制作。布匹更紧缺,一般家庭的娃娃10岁以下穿裤子的为数不多,更说不上有鞋穿,为了遮体保暖,人们还想方设法织布,做衣、裤、袜。我家就有一架织布机,用纺车把棉花纺成线,用白面合成团,再用清水洗,最后只剩面筋,把面水烧热洗棉线叫浆线,晒干绕在织布机的绕线辊子上,就可以织布了。在当地这还算是先进些的织布机,还有一种织布法,把线拉在两个桩上拉展,人坐小凳子横线是手过来过去喂,喂过一次用织布刀往齐剁一次,织出来的布和现在的麻袋粗细相似,那种布穿上照常遮体保暖,比光屁股强得多。我12岁前没穿过现在最差的细布衣服。当时火柴也是紧缺物资,时常脱销,买也得到城里去买,再说没别的事儿不可能跑50多里路买几盒火柴,火柴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每天要用几遍。在那样不方便的情况下,还是自己想办法制造火种,找块硫磺,用铁勺搭在火炉上使硫磺熔化,再用剥了麻的麻杆,折成三寸长的节子,把熔化的硫磺溅沾在一头,使用时有一块火蛋就行,把沾硫磺的一头往火蛋上一挨就起火苗,比火镰取火方便得多。”公公还写了窎沟临近解放时的情景:“1949年盛夏,解放大军打到西北,马家军开始乱套,记得从宁夏过来的散兵三五成群、络绎不绝地向南走,都没带枪。家里大人都躲到山里住,只留奶奶和一帮娃娃看门,那些散兵过来求住或吃喝,并不害人。有时奶奶不肯让他们住,实在支不走,就让他们住上一夜,第二天早五更就走了,看来他们害怕碰上大部队又把他们抓去,不敢走大路。老百姓知道什么,看见穿军装的就跑,消息紧张的那段时间,年轻人都不敢在家里待,赶上牲口住在山里,自天一边干活一边提高警惕防军队。我的主要任务还是负责一群驴,除了害怕,也害怕碰上军队。因为在战乱时期,军队过来,碰见牲口就拉去替他们驮运物资,青年抓去当兵或当差,老百姓能有什么办法,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1950年窎沟庄算是多事之年,土匪洗劫两次,八头驴被狼咬死。”他又满怀喜悦地记录了解放后的新气象:“1950年因已解放,人心大快。春节前夕,村里唯一的知识分子赵某,利用晚上休息时间,组织青年以他们家的羊圈作场地,练习秧歌,村里大人全然不知,以为娃娃闲得没事干,聚集在一块儿玩耍,都没当一回事。1950年正月初一,吃过早饭,秧歌队由赵某带领出演了,全庄老小仍然像往年一样过年,突然出现了什么秧歌队,都觉得惊奇地了不得,不但没见过,就连‘秧歌’这个名字也很少有人听过。”“1951年,靖远县土地改革在东湾乡搞试点,部队文工团来作宣传演出,话剧《白毛女》是当时最盛行的剧目。我们一伙青年娃娃跑去看,我还是第一次看话剧,正碰上南头村没收来的地主财产,在一块场地给穷人分配。1953年国家稳定,农村适龄儿童要求上学念书,我们家三弟、四弟都上了学,家里的负担基本落在我和父亲二人身上。天不亮去犁地,下午放牲口。我们的牲口多,每天得出去牧放。1954年春,国家提倡扫盲,没有条件念书的青年男女和壮年都组织上夜校学习文化,当时群众学习文化积极性很高,我的这点文化就是上夜校打的基础。1955年冬,我们这里组织入了社,过起了集体劳动的生活。1956年全面进入农业合作化,土地归集体所有,从此长达20多年的农业合作化。社员的思想都比较单纯,男女老少显得特别活泼,劳动量小,摔跤成了风气。”“社员由各组长带领劳动记公分,制度是早晨天亮出工,干到九点左右吃早饭为一段,2分工;早饭后到中午一段4分工。休息两三小时,下午到天黑4分工。男全劳一天10分工,女全劳8分,半大子娃娃按大小评工。” “上世纪50年代的人总觉得比较活泼,那时候搞文艺活动都是自发组织,1956年扭秧歌已经淘汰,我们组织演戏,所需道具服装都是就地取材,坑席搭个棚子就是戏台子。那时候乡村没有女演员,扮演女角得借女人服装,都是自己想办法。”

……
婆婆几十年来家务缠身,晚年提笔写文章有些困难。但是,她依然认认真真地回忆,书写,尤其详细地写了童年时她母亲生病、去世前后的经历。读来令人动容。婆婆善解人意,积极乐观,也是受到了家族前辈的熏陶。例如她这样写她的奶奶:“回忆起奶奶,很值得一提,她很早就掉了牙,但是精神很好,个性特别活泼,性情开朗,眼明耳亮,爱和我开玩笑,经常做些怪动作、说些怪话惹得我好笑。她生气的时候,咬紧牙关,因为一颗牙都没有,嘴就成了一个窝窝,鼓得那个劲儿,看她生气的劲儿,我就笑得很开心,她的那个样子把谁都能惹笑,奶奶就气消了也跟着我们一起笑。我和奶奶在一块儿乐乐呵呵,因为从小跟着奶奶长大,无论到哪儿,只要是奶奶,感觉上没有抵触性。”
通过她对过去生活的回忆,让我了解到,当年年轻时的艰辛生活有了切实感受:“1961年开春,队长派我去犁地,全是妇女,每六人一组,犁地这活我没干过,又是个难题,再难也得干,跟上学吧。我正好和侄儿媳妇分到一组,她和我同岁,她是本村姑娘,虽然个子长得小,但是什么活都能干,我不如她,还差得远着呢,就连自己每天吃喝的驴,一到圈里我就认不出来,可是侄儿媳妇她能认出来,我叫她给我拉驴,每天都让别人拉,时间长了能不好意思吗。没办法,我就把驴脖颈鬃毛扎几个辫子做记号,结果因为各种原因,它把辫子弄没了,又认不出来。不过我和侄媳妇相处得很好,她能认出来,只能求她给我帮忙,又给驴尾巴上编上辫子扎得结结实实,它照样早上拉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不知咋的,一圈驴我看着都一样,可拉出来就是不一样,我就是认不出来,没办法,只得求侄媳妇每天帮我找牲口,同时她还起得早,她路过叫我一起走。我早早起来等着,我一个人不敢走,非等她一叫我才敢出来,把家当背上和她一起到驴圈里去吃喝驴往地里走。上午犁地,下午挖渠或铲沙地边。挨饿的日子总算过了,起码有糜子炒面吃。麦面少,吃馍馍自然就少。1960年秋,队里简单收了些糜子,无论咋说也是个补贴,吃粮问题不是那么严重了,在那个年代只要不挨饿就非常不错,哪里还谈上吃细粮粗粮,只要吃饱肚子就很好了。再说窎沟这地方靠天吃饭,能给啥粮就吃啥粮。”
那时候年轻妇女的生活真让人感慨万千,我在那个年龄时还在无忧无虑地念书,而婆婆稚嫩的双肩却承担了那么重的担子。婆婆对孩子关爱备至,但不求任何回报,子女不经意的小小举动都让她满足欣慰:“……随着时光的流逝,不知不觉过了几十年,虽然他们都是40以上的人了,我总觉得还带着孩子气,无论哪个啥时进门都先喊妈,我是多么高兴啊,心里总是热乎乎的。有这样的儿女值得骄傲,希望他们在工作上一帆风顺,健健康康地成长在祖国的大地上,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我就知足了。儿女就是父母的精神支柱。”这种思想境界,用“高风亮节”来形容,也不为过吧。
公公婆婆居住在大城市多年,但念念不忘故土。他们的根在窎沟,窎沟是他们一辈子魂牵梦绕的地方,故乡的一切已溶入到血液之中,他们不时回家乡。每次总能带回一些乡村的见闻。例如,他们说到一位乡邻李正义,妻子身患多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李正义既要务农活,又要精心服侍妻子,他的妻子逢人就说:如果没有李正义,我的命早都没了。
《甘肃农民报》记者得知消息后到窎沟采访,还报道了李正义的事迹。
还有很多家长里短的事,都温暖人心,也折射出那片土地上人们的质朴、善良。
我偶尔随爱人回家乡,也看到了农村的变化,感受到农村蒸蒸日上的发展状态。现在全家孩子考上大学的现象比比皆是,七叔的两个儿子都考上大学,参加工作,七婶到城里帮着带孙子。七叔一人在家忙里忙外,很像当年公婆为我们带孩子的情景。七叔虽然辛苦,但他总是那么乐观,热情,村里谁家有事他都主动帮忙。
堂弟玉泉比爱人小一岁,前年刚刚建起了一院新居,农闲的时候,自己贴瓷砖,用水泥铺院子,新房高大、明亮、宽敞,处处透着气派。院子东侧是厨房,灶台、地面都是新崭崭、亮堂堂的瓷砖,干净、利索。院子一角是厕所和卫生间,厕所设计得可以水冲,卫生间有淋浴,房顶上带的太阳能,我慨叹十几年来家乡的变化,这不就是别墅吗?更令我羡慕的是,堂弟家有两间大车库,他现在还没有汽车,停放的是拖拉机。他家养了匹马,马厩都挺用心设计,院子前面是菜地,黄瓜、茄子、西红柿、辣椒长得极其精神。他们吃的是自己种的放心蔬菜,天总是那么蓝、那么晴,庄稼、牲口被他们侍弄得服服帖帖,日子过得蒸蒸日上、井井有条。现在农村不交公粮,农民有医疗保险,没有后顾之忧,只要勤劳就有好日子。
公公婆婆只要有机会就回家乡,走亲访友,了解新的信息后,回到兰州又不断增补。十几年来,一遍遍补充、修改、誊抄。他们的笔迹歪歪扭扭,但不潦草,极其认真、虔诚。我们原来打算打印装订几本,作为留念。阅读过程中,我们发现其中有类似“口述史”的珍贵资料,或许对社会有些贡献,就取名《故园往事》。
《故园往事》出版后,在亲朋中有较大反响。公公婆婆又在原稿基础上陆陆续续增加一些新的内容。2018年6月,公公生了病,加之年事已高,我们决定出版第二版。2019年3月12日,《故园往事》第二版出版。四天后,公公因病去世。叶落归根,葬于窎沟小南山,长眠于他从小生长的故土,从小放羊的那面山坡。感人至深的是,在举行葬礼过程中,窎沟的亲朋乡邻不约而同前来悼念、送别,他们淳朴的表情和行为,让我们非常感动。我与爱人常常说,以后如何报答这些善良厚道的乡亲呢?
现在的农村与我童年生活的农村相比,有了翻天覆地变化。如今的窎沟有四通八达的水泥路,自来水,好多家烧液化气,几乎家家门前都停有汽车,住房、院落,越来越气派。远离院落,有专门的猪圈、羊圈、鸡圈,院子就是花园、果园,干净利落。解放初期就宣传的“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犁地不用牛,电灯不用油”、“坐小卧车”,当时以为天方夜谭,而现在,这样的日子都实现了。公公没进过一天学校,婆婆仅上过两年小学,公公在劳动之余自学认字,婆婆在经年累月的操劳中把那点有限的文化也未丢失殆尽,谁能想到他们竟然耗时十几年,合著了一本书!
我经历的历史,从《故园往事》看到的历史,亲身感受到的农村生活与现代人们的道德风尚,感触颇深。时代在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巨大改善,在这种日新月异的变化中,人们的厚道、质朴、诚恳、善良等等优秀品质,并没有丝毫蜕变,相反,越老越显出美丽动人的光芒。作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我由衷感恩那片土地,感恩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