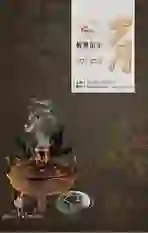久违了,“雅量”
2019-09-16高深
高深
“雅量”者,雅人之量也。就是为人要有宽宏的气度。在待人接物方面休休有容,不斤斤计较。雅量一词的内涵外延甚为广袤。恕我直言,如今真正有雅量的人,似乎很少了。
早几年,一个县召开党代会,在选举县委委员时,上一届的县委书记丢了五票。按说二百多位党代表,只丢了五票,应当算“高票当选”,相当不错了。可是这位后来又连任的书记,对丢掉的这“五票”不依不饶,兴师动众,非让组织部门查个水落石出不可。查出来又能怎么样呢?组织部门当然只能敷衍了事,走走过场拉倒。
也是早几年,我发表文章批评某作家的一篇短文夸大事实。我并没有在文章中指名道姓,责编朱先生觉得拙文所言属实,且言之成理,字里行间充满善意,就点出了那位作家的大名。不料这位作家对此耿耿于怀。他在鲁迅文学院学习过,该院建院50周年时,聘请我编一册纪念文集,我在给这位作家的打印约稿信上,又特意手写了一段话,诚恳地约他写一篇纪念文章,结果他毫不理睬。尤其是发表那篇批评文章的报纸,后来的七八年间,该报再也没见过他的大作。以前可不是这样,因为那家报纸的副刊颇有影响,他差不多几个月就见报一篇散文或随笔。
恐怕可举的例子还有不少,几乎人人都有过类似的遭遇,或类似的耳闻。古人有箴语:“雅言难入,而淫言易听;正道难从,而小道易用。”这大概就是人性天生的弱点吧。
说起来也不尽然。有雅量的人容得下至言、苦言,有时即使是怒言横语,雅量之人,也能从中吸取有益的成分,闻之则喜,不无悦意。北宋执政吕蒙正被提为参政大臣,初入朝堂那天,身后有个朝士指着他的脊梁骨嘀咕:“这种人也做得了参政?”吕蒙正听见了佯装没有听见。他的属下不依,一定要追查此人姓甚名谁,吕蒙正赶忙制止说“如果知道了他的姓名,恐怕终生也不会忘记,不如不知为好。”这是何等雅量!
《世说新语》载,褚裒由章安令调任太尉庾亮的记室参军。他早已名声很高,但官职低,因此多数人还不认识他。一次他东行,乘商船送他以前的几个属吏,投宿到钱唐亭。当时吴兴人氏沈充任县令,要送客人去浙江。客人到了后,亭吏把褚裒赶到牛栏旁去住。涨潮时,沈充起来漫步,问:“牛栏旁是什么人?”亭吏说:“昨天有一个伧父来亭中投宿,因有贵客,权且移到那边。”沈充乘着几分醉意,便远远地问:“伧父想吃饼不?姓什么?可以聊聊天。”褚裒便挥手答道:“我是河南的褚季野。”沈充久聞褚裒大名,听了极为窘迫,不敢叫褚裒过来,便去牛栏旁递上名片拜见褚裒。随宰鸡杀羊准备宴席,送到褚裒面前。褚裒与沈充对饮,言谈神色如常,好像什么误会都没有发生过。这也是一种难得的雅量。
还有一件我亲历的事情。2006年《文汇报·笔会》举办创刊60年征文,应征者十分踊跃。我也写了一则短文,其文不是讲“笔会”的好话,主要批评若干年前“笔会”刊载的一篇文章有个明显的错误。
建国之初“笔会”发表了若瓢和尚的《回忆郁达夫》一文,1996年“笔会文粹”结集出版《走过半个世纪》,也选了若瓢和尚的这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引用了一首诗: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若瓢和尚误说这是苏东坡的诗,并于文中强调“我最喜欢苏东坡吟西湖的诗”。从发表在报纸上,到选人50年“文萃”中,经过报社和出版社多少道“关口”,竟然无人发现这个明显的错误。其实这首描写西湖六月风光的诗,是南宋诗人杨万里写的一首七绝:《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我的文章写好后,家人说:“人家举办笔会,60年征文,有那么多好文章你不谈谈,偏偏挑刺儿找毛病,寄去也不会登出来。”我想也是。可文章业已写成,还是寄出了。没想到,笔会不但很快在显著位置发表了拙文,还给我评上了征文一等奖。看来我们这个社会、在我们的生活中,“雅量”这种品质与气度还是有的,甚至不少,只是有时你没遇上而已。
编辑/独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