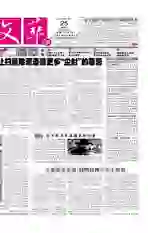在柴米油盐中守护诗和远方
2019-09-10王小圈
王小圈
1970年,赞比亚修女尤肯达给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太空航行中心的科学副总监施图林格写了一封信,信中问道:目前地球上还有这么多小孩子吃不上饭,怎么舍得为远在火星的项目花费数十亿美元?
同理可问——
中国还有一些小孩子念不起书,我们为什么要发展载人航天?
中国还有一些人得不到足够的医疗,我们为什么要在贵州省平塘县搞个500米口径的望远镜看星星?
以上都是同一个问题:如果还没有照顾好当下,我们为什么要追求远方?
什么叫当下?什么叫远方?当下和远方并非割裂,而是连续的弦上的两个端点。
“我今天晚上吃什么”,这是当下。
“我明天晚上吃什么”,这就比当下稍微远了一点。
“非洲儿童今天吃不饱,我们要援助”,这是当下。
“非洲儿童明天吃不饱,我们要援助”,这是远一点的当下。
“人类未来可能吃不饱,我们要开发太空殖民地”,这是更远一点的当下。
那么远方到底在哪里?
“远方”是肚子已经填饱的时候,精神家园的寄托。
“宇宙最终基于什么规律在运行?如何将宏观和微观规律统一?”这属于远方。
“人类最终将归往何处?”这属于远方。
施图格林诚恳地回答了这位修女,在回信中他表示:
1.在太空探索的过程中,大量技术被发明,大量原理被发现,这些技术和原理被广泛应用于民生相关产业,大大解放了生产力,能让更多小孩子吃上饭。
2.太空探索让人类意识到自身的渺小和地球的珍贵,使人类珍惜地球,让地球更加美好。
由于那位修女的語境始终在“当下”范围内,所以他回复的也只是“当下”的功利部分。
实际上火星探测还具有相当非功利的部分——因为我们向往远方。
当爱因斯坦思考物理大一统公式时,当“先驱者10号”搭载着刻满人类信息的光盘飞向宇宙深处时,当音韵学家研究某个汉字在唐朝怎么发音时,当哲学家思考人生时,他们的心态是一样的——他们都在追求心中的梦想,他们都在不计功利地探索未知的领域。
因为好奇,所以探索;因为探索,所以发现;因为新的发现,世界变得更美好。他们未必带着解放生产力的任务,他们的本意只是想知道更多。
或许人很难摆脱琐碎烦扰的生活去追求高高在上的纯净信念,我也并不期冀有人这么做。但活在一地鸡毛的“当下”,徘徊于朝九晚五的打卡机前,如果能让“诗和远方”融入其中,大概能摆脱几分无聊与乏味。
(摘自《如何成为一个有趣的人》 电子工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