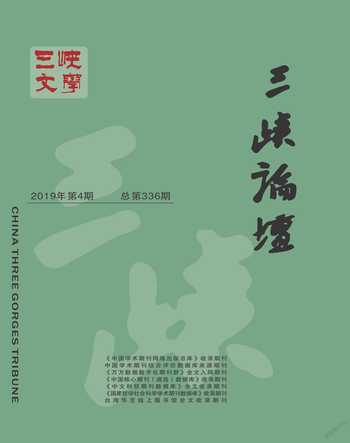语言魔线与存在之夜
2019-09-10景立鹏
景立鹏
摘要:由于意识形态话语的长期宰制,汉语新诗话语失去语言本体性和自觉性。新诗回到语言,就是要超越社会、历史等“非诗”话语对诗歌语言的束缚,通过对语言系统的“逃逸”揭示个体经验和存在的秘密。新诗通过持续的“逃逸”和本体话语生成,形成一个开放的话语空间,进而抵达存在的内部。但是这一经验的表达又有其内在的极限,超越了语言的这个极限,诗歌的有效性也就丧失。在语言的极限与诗歌有效性的界限之间存在一种悖论关系。
关键词:现代汉诗;语言魔线;存在;悖论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9)04-0041-05
当德勒兹用他开放而深刻的哲学眼光对写作和语言进行“临床诊断”的时候,这种思考除了与其精神分裂、欲望、块茎等哲学思想范畴相关和一种修辞学上的考量之外,更是对二者关系的一种隐喻:一方面指认了语言之于写作的基础地位,另一方面暗示着语言与写作之间的“非正常”关系。也正因如此,他说,“文学似乎是一项健康事业”。而对现代汉诗来说,语言的基础性地位就更加明显了。自晚清以降,黄遵宪们就开始了新诗的探索过程,但始终无法摆脱古典诗学的“辖域”,而直到胡适祭起“白话诗”的大旗,从语言入手才使其逐渐获得合法地位。而后的早期象征主义、新月诗派、现代派,及至新诗潮都在诗歌语言的道路上获得了坚实的成绩。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诗歌始终没有摆脱历史、社会、文化的浸染与宰制。诗歌的语言沦为一种工具性的发声装置,而不是发声方式,诗歌本身也被纳入到社会、历史、文化的普遍性机制中。虽然新时期以来,文学的自律性得到张扬,但是从语言本体的角度来看,诗歌只是摆脱了粗暴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捆绑,同时却陷入了另一种现代化的理性陷阱中。中心化、科层化、总体化的权力机制依然渗透在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诗歌的危机与语言的危机日益暴露,反思和回归诗歌本体语言特征的呼声日隆。在一个一切都被纳入理性权力网格的时代中,如果诗歌还能成为可能的话,回到语言,重启诗歌与生存的对话既是一个契机,又是一个挑战。
一、回到语言
关于诗歌回到语言的话题,韩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说法似乎依然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诗歌以语言为目的,诗到语言为止,即是要把语言从一切功利觀中解放出来,使呈现自身,这个‘语言自身’早已存在,但只有在诗歌中它才成为了唯一的经验对象。”如果说,这一说法当时突出的是诗歌通过语言实现对功利主义的“逃逸”的话,那么韩东在关于“他们”文学社的《艺术自释》中的表达则从正面阐释了“他们”诗歌创作的语言观:“我们关心的是诗歌本身,是诗歌成其为诗歌,是这种由语言和语言的运动所产生美感的生命形式。我们关心的是作为个人深入到这个世界中去的感受、体会和经验,是流淌在他(诗人)血液中的命运的力量。”语言本体的个人化自觉可以说是对20世纪40年代艺术本体论的继承与发展。其意义在于他们开始从语言内部来思考个人生存经验。所谓“口语写作”“民间写作”等诗学旨趣的转向正体现了这种立场。诗歌语言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个人化的创造,是扭断语言脖子的个人言语。语言是建立在语法、秩序、规则、习惯基础上的共识性结构,可通约的工具性是其基本特征,客观、中性的信息是其基本内容,而诗歌话语则是拒斥规则、习俗、成见的开放性结构。基于个人体验的陌生化是其内在要求,普鲁斯特说:“美好的书是用某种类似外语的语言写成的。”所谓“回到语言”就是回到语言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世界与个人独特经验的互动与敞开中去。比如韩东的代表作《有关大雁塔》:“……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昔日文化传统中的神圣的象征性符号,被一种散淡、轻描淡写的个人化的口语所消解。
但是,由于第三代诗对于前代诗歌观念与立场的反叛性和后来对于“诗到语言为止”的庸俗化理解,使得“回到语言”的艺术追求并未实现。因为这策略性的反思还是在“弑父”情结的二元对立的理性框架内展开的,因此,他们对于语言的反思并没有真正抵达语言复杂性和多元性的极限,而是发明了另一种带有明显的现代理性专制特征的语言策略。这也就造成“第三代”诗歌,甚至90年代以来的诗歌或依然在理性化、现代化的生存经验中重新组合着焦虑的个人感受,或陷入精英化、技术化的智力操练的泥淖。这样造成现代汉诗虽然在对语言的反思与回归上取得了较大进步,比如张枣、臧棣等,但是总体来看并未形成突破性的景观,难怪有评论家指出,当下现代汉诗创作呈现的是一种“繁而不荣”“有高原没高峰”的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对诗歌语言的探索有关。可见,“回到语言”不应是仅仅以语言为手段或者目的,而是敞开语言与诗歌的哲学关系和美学场域,在语言的“逃逸线”中接通个人经验与诗歌的临近区域,在语言的不断生成中,逼近生存之夜。
而诗歌语言问题从更具体的角度来讲也是技巧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技巧是一种效果上的技巧而非主观上的技巧。写作的技巧对写作而言是根本性的,对此马·肖勒甚至有一个更为极端的表达,“经验以外的都是技巧”“技巧是使艺术素材具体化的唯一方式;因而也是评价这些素材的唯一方式”“技巧就是尺度”。语言的技巧问题构成诗歌经验、标准、困境等诸多问题的网结。只有把诗歌还给语言,让语言在个人经验的裂缝中自由生长、穿行、奔突,才能获得诗歌语言魔线与生存之夜的双重敞开。而这也是现代汉诗语言的活力与动力所在。
二、随“诗”潜入“夜”
诗歌是一个敞开的空间,这一点构成了它解放个体生存的前提。个体生命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的多重分割、摔打、组合逐渐被抛入无名之夜。诗歌语言的生成性使得个体生命的火种可能冲破理性暴力带来的历史尘垢和精神包袱。而且这种生成本身也是开放的,“生成并不在于达到一种形式[辨认、模仿、摹仿],而是找出邻近的、难以辨别的或未区分的领域,人们再也无法区别于一个女人、一个动物或一个分子:不是模糊的,也不是笼统的,而是无法预见的、非事先存在的,他们因为在一个种群中显现出独特性而更加无法在形式上被确定。”个体生存的晦暗之夜因为诗歌语言的开放性生成而成为一个流动的、无限的、敞开的“块茎”,语言在一种无限的生成与“迂回”中抵达个体生存的疆域。“生成”与“迂回”指向的是对语言极限的持续性突破,突破的过程也构成对生存之夜祛魅、解蔽的过程。诗歌语言的这种开放性包括两个向度的敞开。
(一)开放与灯
作为光源,灯与太阳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存在权力的支配性和绝对性维度。太阳是唯一的、绝对的生命之源,而灯则是语言之光流动的起点,开灯、关灯,台灯、吊灯,路灯、头灯……它是一个开放性、可能性的光的起点。它与夜不是权力的支配关系,而是相互敞开、生成的关系。因为有光,黑暗之夜得以澄明、敞亮;因为有夜,灯才成为一种需要与肯定性力量。而诗歌语言对于个体生存而言就是这种隐喻关系的本体。诗人写作的过程即是抛洒语言魔线的过程,他摆脱了白昼的暴政,摆脱工作、交通、写字楼,在黑暗的角落里摊开稿纸,从身体里、脑袋里、衣服里抽出词语的“叛徒”。他乘着灯光向着自我的黑洞中飞去。他的愤怒、悲喜、孤独、忧郁都被语言的魔线一起抖落出来、释放出来。在语言之光的飞奔中,诗人切近了生存的真实体验。例如昌耀的《斯人》:
静极——谁的叹虚?
密西西比河此刻风雨,在那边攀缘而走。
地球这壁,一人无语独坐。
1985.5.31
在“静极”与“叹嘘”之间,在此岸与彼岸之间,在风雨攀缘与“无语独坐”之间,在地球与一人之间,诗人通过语言魔线飞跃理性、抒情的机制,丈量了个人、世界与生存之间的可能性关系。所谓“斯人”,既是个人的生存体验,更隐喻着人类的普遍处境。当生命摆脱了层级、理性、规则的制约制约后,万籁俱寂,唯有悲响。破折号与问号在此既是气氛的转折性延宕,又是一种绝望。在这宿命性的前提下,第二节的多重精神场景的对置就成为对这“静”之“叹嘘”的确证。“无语”是不必“语”,还是不可“语”?诗人对语言与经验给予了进一步敞开,这也构成了个人生存的双重隐喻。
如果说,诗歌通过语言魔线表现出对社会、历史、文化成规以及语言成规的“逃逸”,实现的是一种对于权力关系的解构性开放的话,那么,诗歌语言自身的动态组合和持续流动则构成其内在的本体开放性。艾柯把这样的作品称为“运动中的作品”,一种通过句法、语法、文字排印的多重动态组合实现的开放的作品。这种表达的可能性同时捕获的是经验的可能性,感知的可能性。回文诗、具像诗都是一种“运动中的作品”,比如台湾诗人陈黎的《战争交响曲》,全诗三节,每节十六行,第一节由“兵”字组成豆腐块式的矩阵,表现整齐浩大庄严威武的军容,第二节由“兵”的排列组合过渡到“乒”“乓”组合成的矩阵,通过文字象形表现战争之惨烈,随后一节是有“丘”字組成的与第一节对应的矩阵,表现战争结束尸横遍野的场面,为了更加形象,在此将第二节呈现出来:
兵兵兵兵兵兵兵乒兵兵兵兵兵兵兵乓兵兵兵兵兵兵兵乒
兵兵兵乓兵兵乒兵兵兵乒乒兵兵乒乓兵兵乒乓兵兵乓乓
乒乒兵兵兵兵乓乓乓乓兵兵乒乒乓乓乒乓兵乓兵兵乓乓
兵乒兵乒乒乒乓乓兵兵乒乒乓乓乓乓乒乒乓乓乒兵乓乓
乒兵乓乓乒兵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
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
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
乒乓乒乓乒乓乒乓乒乓乒乓乒乓乒乓乒乓乒乓乒乓乒乓
乒乓乒乓乒乒乓乓乒乓乒乓乒乒乓乓乒乓乒乓乒乒乓乓
乒乒乒乒乒乒乒乒乓乓乓乓乓乓乓乓乒乒 乒乒乒 乓
乓乓 乒乓乒乒 乒 乓 乒乒 乒乒 乓乓
乒乒 乓乒 乒 乓 乒 乓 乒乒乒 乓 乒
乒乒 乓 乓乓 乒 乒 乓 乒 乓 乒
乒 乓乓 乓 乒 乓
乒 乓 乒 乓 乓
乒 乓
书写战争的诗歌很多,但是陈黎充分调动文字、声音、排列和结构的诸多因素,使诗歌语言在一种狂欢化的舞动中逼近战争体验的现实。在这种“块茎”式的诗歌空间中,战争的枪声、搏斗的姿态、尸横遍野的惨烈都呈现出来了,而且这首诗还有相应的音画呈现方式。这些元素充分调动出诗歌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感受与言说方式的开放性与可能性。可见,诗歌语言的开放性也是经验的开放性,通过对语言极限的持续突破,个体生存的声、光、色、影方能穿透存在之夜的晦暗地带。也许这种对语言的极限挑战存在某种局限性,但是诗歌语言却正是在这种不断地“逃逸”中创造新的可能,确立自身价值的。正如德勒兹所言,“当语言中创生另一种语言时,整个语言都开始向“不合句法”“不合句法”的极限倾斜,或者说同它自己的外在展开了对话。极限不在言语活动之外,它是言语活动的外在:它由非语言的视觉和听觉构成,然而只有言语活动本身才能令这些视觉或听觉成为可能。”
(二)诱惑与光
当诗歌如灯,照亮生存之暗夜时,语言之光构成对于读者永恒的诱惑。因此诗歌的流动与开放不仅仅在于作为“写作”的开放,还在于对阅读的诱惑。读者面对来自写作者和语言的艺术光焰的逆向飞翔,既使读者自身的生存之夜敞开,又是对诗歌与写作之光的内在肯定;而这种诱惑在这逆向飞翔中,既是无限逼近,又是永难抵达的。这构成经验、表达、阅读之间的三重张力,也决定了经验与表达的根本性孤独。在光的诱惑中,读者与诗人处于一种充满张力的永恒的对望中。正如布朗肖所言,“诱惑人的是那种孤独的目光,那种永不停息、不可终了的目光,在这目光中,瞎仍是一种视觉,即那种不再有可能看得见,但不可能看不见的视觉,这种不可能性体现在并永驻在不会终了的视觉中:呆滞的目光,成为永恒的视觉幽灵的目光。”虽然这种光的诱惑无法抵达、无外形、无深度,但是恰恰这种“否定性”特质为读者的阅读、感受、理解提供了开放的艺术和精神空间。作品的生成性在诗人的写作中并不会一劳永逸地完成,而是成为一个永恒的进行中的事件,这也是作品之为“作品”的本质意义。读者根据自身的历史、社会、文化经验和个体生命的神秘知觉,对作品进行持续性的靠近、赋形、认知,生成另一种个人化的形象,成为另一意义上的“作品”,此时重要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作”,是诗歌在语言中从诗人到读者的不断漂移。在这一过程中,诗人与读者之间是中性的、摆脱了压迫性的时空观念的关系。他们在作品的孤独中,在时空的不在场中感受着自身的存在,从而继续着各自的独立“写作”。“写作,就是去肯定有着诱惑力威胁的孤独。就是投身于时刻不在场的冒险中去,在那里,永无止境的重新开始是主宰。”现以昌耀的《紫金冠》为例进行说明:
我不能描摹出的一种完美是紫金冠。
我喜悦。如果有神启而我不假思索道出的
正是紫金冠。我行走在狼荒之地的第七天
仆卧津渡而首先看到的希望之星是紫金冠。
当热夜以漫长的痉挛触杀我九岁的生命力
我在昏热中向壁承饮到的那股沁凉是紫金冠。
当白昼透出花环。当不战而胜,与剑柄垂直
而婀娜相交的月桂投影正是不凋的紫金冠。
我不學而能的人性醒觉是紫金冠。
我无虑被人劫掠的秘藏只有紫金冠。
不可穷尽的高峻或冷寂唯有紫金冠。
1990.1.12
整首诗围绕着“紫金冠”开始,在一种辐辏结构中,诗人的经验与情感得到不断聚集、强化,从抽象的“完美”、“神启”到“仆卧津渡而首先看到的希望之星”“壁承饮到的那股沁凉”,再到“人性觉醒”“秘藏”“高峻或冷寂”,这种从抽象到具体体验再到无名之“在”,都暗示了经验与表达的不断漂移、后退。“紫金冠”到底是什么,诗人没有说,或者已经全部说出,又或者它什么都可以是,什么又都不是。正是这种持续的表达与后退,使得“紫金冠”放射出万丈充满诱惑的艺术之光,从而照亮生存之暗夜。当读者进入这首诗时,即是在进入自我经验本身,他看到了什么,“紫金冠”也许就是什么,或理想,或美,或信仰……他阅读的时候就是敞开的时候,就是再次“写作”的过程,“就是从魅力的角度支配语言,并且通过语言,在言词之中同绝对领域保持接触”的过程,“在这这领域里,事物重新成为形象,在那里,形象,从对象的暗示成为对无形的暗示,并且,从对不在场描绘的形式变成这个不在场的不成形的在场,成为当不再有世界,当尚未有世界时对存在着的东西的不透明和空无的敞开。”《圣经》中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当上帝把光明与黑暗截然分开时也就意味着其通过有限创造剥夺了“存在”更多的可能性和复杂性。而诗歌中,语言的魔线却提供了沟通理性与生存之夜的通道。经验通过对被理性与规则强暴的语言的拯救敞开了无名经验,而读者通过对语言之光的折射嵌入到个体生存之“夜”。当诗人与读者在语言的“块茎”上相遇时,必然需要某种能够为双方共同识别的“踪迹”,这就出现了经验与表达,“逃逸”与回归之间的矛盾。
三、极限与界限:经验与表达的悖论
语言,只有回归到一种“块茎”组织的时候才存在“写作”的可能性。“块茎”结构的无中心、无意指、多维度的异质混成性使得写作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写作,构成块茎,通过解域扩大你的地域,延长逃亡路线,直到它变成一部抽象机器,覆盖着整个黏性平面。”现代汉诗通过多重语言魔线的逃亡,逐渐摆脱了规范化理念的制约,解放了个体生命经验的陌生化表达。但是诗歌语言在对于表达极限的持续扩展中一旦突破必要的界限就可能变成个人的独语,陷入技术自恋主义的泥淖,从而使经验表达失效。因此诗歌语言的个人化创造面临一个限度问题,语言的极限决定了诗歌的极限,同时也决定了生存的极限,“诗”与“非诗”的区别有时就在一线之间。这就造成现代汉诗经验与表达之间的悖论性关系。
新诗语言的困境与危机也许也在这一点上:既要保证诗歌语言作为摆脱普遍化规训的语言魔线的开放姿态,又要保证对个体生存之夜的敞亮与澄明。对此,艾柯的观点似乎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在他看来,诗歌语言包括传达功能与启示功能。就传达功能的句子而言,当读者“面对一个需要相当统一的理解模式的、传达明确含义的句子,每个人对他所传达的东西或者带有的情感的理解都不同,理解的模式也是个人化的,每个人都会使它带有个人的特殊色彩。不同的理解造成的‘实用性’后果就不同。”但是,同時它们又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对于单一的具有明确涵义的认识上。这一明确涵义即是语言的基本外延,而正因为对于这种外延的基本界定,句子的启示功能才成为可能。例如,对于“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这句诗而言,产生启示作用与美学刺激的触点是“梅花”,而不是桃花、杏花。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诗歌语言的开放才能成立,诗人与读者的对话才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现代汉诗面临的一个问题还在于很多创作并没有摆脱一种总体性、普遍化话语方式和逻辑的规训,只不过由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训变成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形形色色时髦理论的规训,说到底,仍然被一种隐含着各种权力积弊的理念限制。所谓“网络体”“梨花体”“垃圾派”“下半身”“废话体”,其背后都站着各种主义的影子。因此现代汉诗的写作依然要回到语言,从语言本体出发不断突破体制化的经验、主义、思想和语言,回归到语言魔线与生存现实的互动敞开中才能渴望新的突破。也只有真正地能够有效冲击语言的极限时,界限的问题才有意义。最后,我愿再次引用布朗肖的话来表达对现代汉语诗歌的期待:
“诗歌是起始,而话语本身永不开始,但它总是重新诉说并总是重新开始。”
注 释:
[1] [法]吉尔·德勒兹:《批评与临床》,刘云虹、曹丹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2] 所谓“辖域”是德勒兹哲学体系中的一个范畴,指的是理性、规则、等级等制度性概念对事物的种种限制。
[3] 韩东:《自传与诗见》,《诗歌报》,1988年7月6日。
[4] 徐敬亚、孟浪、曹长青、吕贵品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
[5] 洪子诚、程光炜主编:《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第十五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
[6] [美]马·肖勒:《技巧的探讨》,选自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7] “块茎”是德勒兹哲学体系中的一个核心范畴。“块茎”思维是相对树状思维的等级系统而言的,强调无中心、非中心化、非总体化,反对理性、规则、封闭体系,主张连接和异质混成原则,繁殖原则,无意指断裂原则,绘图和贴花原则。
[8] 昌耀:《昌耀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9] “运动中的作品”是艾柯用来描述“开放的作品”时提到的一种开放类型,指的是在艺术作品中,诸要素可以自由组合,从而产生不同的意义和美学效果的作品,在音乐作品,尤其是造型艺术中更为明显。参见[意]安伯托·艾柯:《开放的作品》,刘儒庭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
[10] 陈黎:《战争交响曲》,选自奚密编选:《二十世纪台湾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1] [法]布朗肖:《文学空间》,顾嘉琛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
[12] [法]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陈永国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
[13] [意]安伯托·艾柯:《开放的作品》,刘儒庭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