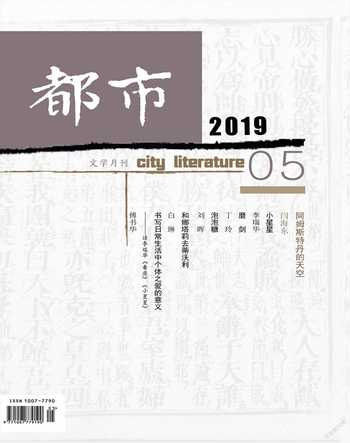看房
2019-09-10李瑞华
李瑞华
她把昨天早上剩下的半碗豆浆和一个豆包加热,做为早餐,慢吞吞吃下。丈夫照例不在家吃,他要出去吃街上的豆腐脑,他总是不亏待自己,总是这样。
她吃早饭的时候,他背着包,换好鞋,站在门口,脸上带着对她慢速度的忍耐。如果是往常,他会抱怨几句,不过今天他没有。然而她还是略微加快速度,并且在吃完以后没有洗碗,把它们放到水槽,迅速去刷牙,拿包,换鞋,出发。在她刷牙时,他开门走出去,拎着一袋隔夜垃圾,说先去楼下扔垃圾去。她嗯一声,牙刷里传出的声音不像她自己的。
他五十二岁,她五十岁。不够老,也早已不年轻。出发前,她在门口照照镜子,站定,自嘲地笑一下。的确,她不漂亮,不年轻,唯一可以自傲的瘦,也渐渐消失,被下垂的赘肉所掩埋。瘦,在年龄增长后,一度让她的脸部凹陷,两腮尤其严重,发福之后,这凹陷没有被填充起来,反而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越发向下,成为被岁月泥沙不断冲袭过的沟壑,成为坑洞,严重影响了年轻度;赘肉让脸变长,小腹变突,腰部失去线条,大腿松弛粗笨。不过她仍然持有自信,她喜欢不像以前那样总是生气的自己。她对目前的现状很满意。
除了房子。
没有他的催促,她下楼速度又慢吞吞,刚才,她分明是在给他表演,正如他常常这样表演给她看,表演是融合剂,是给对方面子,也许对方对这些把戏心知肚明,但都不去戳破。少些冲突,多些迎合,正是为了便于在更多的时候,各坚持各的。婚姻自有玄机,高手过招,招式眼花缭乱,却是在用心过。用心过招,说明彼此对家庭,对对方,都有让步。让步是婚姻的最大美德。
她家住在六楼,两个卧室都在东面,她年轻时,最喜欢每天充斥在房间的阳光味道,阳光照得人身体发痒,七色阳光曾经有好几年让她对生活产生严重误解,以为未来会充满希望。后来,令人沮丧的失望之旅开启后,真实人生列车载着家庭沉闷向前,阳光强烈时,她习惯选择关上窗户,拉上窗帘,把一些不合实际的希望遮挡在外面。失望是希望带来的,正如离婚原因是结婚。同理。
下楼时间,不是在某一天变长,是越拖越长。当初买房时,他们已经有孩子,从租的房子搬到这里,他们多么快乐,他们三个飞快上楼,跟踩着云朵一样飞快,女儿两岁,胖乎乎,时常被他抱着上来,不算个事。
年轻,快乐,那时是这样。
她自嘲地笑了笑。这时她已经下到二楼,腿有点不听使唤,下楼都有点累,上楼就更累得厉害。这个砖混结构120平米的房子,质量一般,当时贪着楼层高价格便宜,买的顶楼,这会儿,后悔也来不及。年龄越大,上下楼越是吃力。年轻人蹬蹬蹬上楼,声音先是在他们身后,然后就跟他们擦肩而过,他们都自觉停住靠在一边,让那些年轻的脚步先走。
有那么几次,他不服输快步冲上,想要一鼓作气走到六楼,她跟在后面,拿着买菜的篮子,看着他离开自己,超过自己,他气喘吁吁的声音让她心惊,他站到门口,确实是比她快了那么两三分钟,可是他喘息着,手脚都抖,半天连钥匙都拿不出来,有一次,他在四楼绊了一跤,滚落到三楼,右腿骨折,在家休息好长时间,他几乎憋疯,每天想下楼,可她一个人,怎么能把他弄到楼下,即使找邻居帮忙背到楼下,那么又需要找人再把他弄回去,这年头,谁愿意干这些体力活,欠人情的事,他们自己也不愿意做,他们都是普通的人,拿什么去还别人的人情呢?他们一穷二白,没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帮助别人。
后来上楼,他们俩都会小心翼翼,走累了,休息一下,再往上走。他性格急,可是也不再快步走,受伤后在家待了将近一百天所带来的煎熬,对他是个教训和警示。
所以当他终于提出重新买房时,她没有理由反对。
理由其实也有。比如,钱。
钱怎么办?她仿佛自语地说。她自己没有私房钱,家里所有的钱他都知道。够买一个差不多的房,可是,那大都是她兼职所得,是早已计划过,给女儿以后买房时添补。女儿已经在上海就业,成家,还没有房子。所以,女儿女婿结婚四年,还是不敢要孩子。
他皱眉。他不是不想管女儿,他认为这件事应该由女婿家那边负责。
“给他们添上点,也不能全给他们。”他皱着的眉头没有松开,电视里,一头鹿正被一头壮硕的狮子肢解,她扭过头,手里拿着一件旧睡衣,准备去洗澡。
她觉得自己是那头鹿,被他撕扯,他除了赚死工资,什么来钱的地方都没有,她恨这个。
可是,她又何尝不是被女儿女婿撕扯,她这么想了一下。这么想让她有点罪恶感。
买个二手房吧,她提议后,懊恼地低下头去,忽然就不想洗澡了。她来到洗手池旁边,拿起拖布准备拖地,可是努力半天后,客厅里的地板砖依然暗淡无光,怎么也拖不出来本色,她泄气地把拖布扔到桶里。
他的身體摆放在沙发上,和赘肉、下垂的脸、半秃的前额,一起在沙发上释放重量。他没有回头,他认命地回答,不然呢。这三个字,代表对买二手房的无奈和认定。
于是,他们不得不去看一个又一个二手房。今天,也是这样。
到了楼下,她已经看到他在掉好头的车里玩着手机。她走近车,从后窗到副驾驶,他没有抬头,她明明在打开车门上车的一瞬间看到他在手机上打字聊天,不知道跟谁,可是一待她上车,他已经切换到游戏。他和别人聊天,和她却无话。每天上下楼的疲惫让两个人的力气都消失殆尽了吗?
手里的游戏以失败结束后,他发动车。他忘记了刚才还在催她快走。
他穷,年轻时有的,就只是力气。没有孩子之前,他背着她走路,抱着她过河,用一句流行语就是,一言不合就举起她,抱起她。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是一个爱撒娇的人,她在他面前,娇滴滴的,以各种借口赖着少走路,少干活,把出力气的活计全交给他来做。他也乐颠颠全部都接受。主动,快乐去接受。
有了孩子后,他就背孩子,抱孩子,她也不再让他背让他抱。她独立起来,强大起来。有一天,她做好饭,洗好碗,拖完地,去给孩子辅导作业,惊觉他从接孩子放学后进门起就一直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吃饭时都是把碗端到那里去看。
什么时候,这一切成为了习惯?那天天很热,家里还没有安空调,她累,又热,有点眩晕,感觉恍若梦境。
他们现在去看房。
说过看房后,他们已经看了很多房子,但都不合适。第一个房,房主不出现,交给中介公司来交涉,房子是早年装修好的,一直对外出租着,他们去看房时,租客窝在沙发上看电视,冷冷地接待了他们,正是中午,是午睡时间,虽然觉得不合适,但租客说只有这个时间他才在。
三室一厅,一间门被出租人上锁,一间靠北的床上躺着一位午睡的老太太,眯着眼睛,听不到她的呼吸,身上盖着一个粉色花团锦簇的旧毛巾被。可能是这位年轻租客的母亲。第三间空落落的,摆着一个窄而滑稽的柜子,一个铺着油腻床单的双人床。凌乱的阳台上晾着四件衣服。没有一件衣服有女性属性。她搞不明白,这个家里为什么没有年轻的女主人,也没有孩子。但不方便問。他们致谢,说了抱歉打扰,就离开。
价格要得不低,装修却很烂,不合适。
他们定位是高层,有电梯。二手,价格便宜,安静没有噪音。就只这三项,可一直没有达成心愿。总是这样那样不合适。他渐渐急躁,不像她一样不温不火,他却还为她不温不火感到恼火,仿佛没有合适的房子是她的错。也许真是这样,有个房子,他真的觉得可以,但是她认为不行。那所他认为可以的房子,如果买下的话,那就得把她计划内给女儿的三分之二都要截掉。她怎么忍心。
女儿出生时,全家在租的房子里住,房东就在对面,是个年龄在六十岁左右的离异男人。老婆带孩子和存款走后,给他留下一套房子,拆迁时,一座房子变成了两套,在一楼,面对面。两套新房,他没有钱全部装修,就把西面这套租出去,自己把东面简单装修后住进去。
西面就是他们的婚房。结婚时,他们把地上铺上廉价的地板革,地板革上印着棕色方格花纹,墙上滚上白色乳胶漆,客厅和卧室都在墙上钉几个钉子,挂新婚照片,后来又挂上女儿百天、周岁时的照片。房子里只放着几件简单家具,连梳妆台都没有,连镜子都没有。房东在过道里一面墙上安装了一个长长的穿衣镜,她每天上班前,都在那里匆匆地看看自己。她总觉得,那边独居着的房东,会从猫眼里偷窥她。她像个小兔子一样在镜子那里逗留一下,便飞快地从镜子里一闪而过。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证明她的猜测是有道理的。
那天他开早会,六点多走了。她七点起来,吃过早饭,把昨天买的红色连衣裙穿在身上,从家里走出来。她要照镜子,照镜子是对新衣服的起码尊重。
她站在镜子那里,比平时站得久了些。陶醉在自己的小虚荣中,以至于她并没有听到隔壁那个六十岁的房东什么时候开门出来的,他从她身后把她拦腰抱住,胳膊把她抱得紧紧的,她挣扎着不能喘气,只有他们两个人,除了她自己,谁也不能救她。她臀部被顶得生疼,她叫喊,挣扎,都无法挣脱,带着霉味的气味在她身后升腾起来,是这个独身男人常年在自己房间里捂出来的味道,和厕所里的蛆虫一样,让人浑身不适,剧烈厌恶。有个瞬间她看到那男人出现在镜子里,半张着嘴像要吃掉她的某一部分。她怕得发抖,不过很快那男人就溜走了,她听到他忽然松一口气,飞快地松开她,闪向东面,啪的一声关上房门。
镜子里又是她一个人,仿佛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她本应该立刻逃回自己的房间去藏起来,可她还仿佛在一场噩梦中醒不来。她看着镜子。镜子不因它所照射过的高尚而高尚,也不因它所照射过的龌龊而龌龊。新裙子皱了,她下意识伸出右手在后面摸了一把,立刻摸到了黏黏的东西。
这件事她没跟他说过。她得忍下来。她后来每次上班下班都尽量和他一起回家。他说她变得黏人了,她也不解释。她也知道该搬家,可是,找同样租金和地段的房子,哪有那么容易,况且,搬家也是要花钱的,她折腾不起。
他说跟着他委屈,她说,我愿意。说这话时,是结婚第一天,听她说完,他背着她在屋子里绕了足足有十圈。五十多平米的小房,总共走不了多少步,可她还是心疼她。她让他放她下来,可他说,不累。
他们都是死工资,家都在外地,家庭条件都一般。生女儿后,双方父母各自错开时间来住了几天,分别离去,都不习惯这里的热,的确热,没有乡下凉快。她怀孕后辞掉工作,到女儿两岁半全托时,才重新找工作,工作之外,又找了兼职。她一步步这样往前走,谁不是这样呢?她这样想。但也知道很多人其实不是这样。可她又想,大部分人不都是这样吗?于是她就继续这样走下去。抱着一条道走到黑的决心和坚韧。
二十分钟后,他把车驶进一个半新不旧的楼盘,他带着不耐烦的小心,刻意的小心,很多年少见的小心对她微笑,眼角皱纹越发明显。她不知道他这态度因何而起,他很少因为她赚钱多而对她抱着尊重,反而很是不平。他只有在利用她时,才有这份小心。她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这样。
最初,是这样吗?是她愚钝吗?年轻时,她认为自己虽然不漂亮,但睿智,聪明,认人不至于出太大错。他虽然没有钱,没有太大能力,但是,他纯粹,他对她,实心实意。找个对自己好的也行,她这样想。没有钱可以赚,没有能力,可以磨练。谁生下来就什么都会呢。她把自己嫁给了他,跟着他往前走。她没有预料到,她看人的眼光确实是对的,但她对事物发展的走向却判断不力,没有钱,缺少能力,在他两鬓斑白时,还是没有改变,对她好这一项,如果她不想彻底认输和承认失败的话,那么算还好吧,没有家庭暴力,没有放弃责任,他心里,总归是有这个家,每个月,工资都是往家里花。
这是对人生的总结吗?她其实是好强的人,不愿意承认失败,不愿意认输,她告诉自己一切还好。就是因为如果她说了不好,承认了不好,她的人生就成了蔫掉的黄瓜,黄拉拉干枯了,败相很难看。撑着不断,不烂,还是很难看。她不想面对这个结论。她有权利给自己的人生下结论和做注解,除了她自己,她认为谁都没有资格。他也没有。
他们走进这座半新不旧的建筑,走进某个单元,在东边,几单元的痕迹已经模糊看不清,她注意到楼下角落里放着一个黄色的三轮车,似曾相识。她没去多想。她看到单元两个字样,心里想起女儿,她女儿小时候,总是把单元两个字认成草原,女儿好可爱,让她忘记很多烦恼,像陀螺一样围着孩子劳作。一直到她长大,时光飞逝,她考入上海一所大学,二本。又在那里就业,恋爱,结婚。
想到这里她又开始陷入忧愁。女婿是外地人,家境一般,房子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她原本想着,把自己现在住的六楼卖掉,再加上攒下的钱,都给女儿,自己租房去住。可是现在,他不肯这样,要换房子,要买房,即使是二手房,也得费一番周折,简单收拾,搬家,置办新的东西,什么都得花钱。现在的六楼是老房子,卖不上价钱,如果换房,恐怕还得贴补进去一些房钱。她想租房,现在就租房。可是她尽量顺从,尽量照顾他的自尊心和想法,她一直是这样跟他相处的。她不想麻烦。
女儿去年怀孕,谁都没告诉,自己一个人去医院把孩子打掉。打掉回来住了半个月,让她一起瞒着女婿,只说工作累,想在家休息几天。因为没房,女儿不敢生孩子,她很生气,可女儿说,怎么可以让孩子一生下来就吃苦,怎么可以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女儿总是这种论调。好多人都是这样论调,让人恼怒又无理由解释和化解。她只怪自己没本事给女儿好的起跑线。她不怪他。她自己选择了他,他也是她的另一条起跑线,她不承认输。她沿着这条道走着。继续着。
看房之初她就不热心,看了两套,三套,四套,五套之后,她更失望了。他们的车就是个二手车,当初他软磨硬泡非要买,女儿大学快毕业时,她把自己辛苦攒下的一点钱拿出来,买了车给他。现在,又得重新买房,又得动她的钱,她无奈。她任由他带着他进入一个又一个二手或者三手的房子。她每次都充满期待走进去,她想象着里面住着的人,一对年轻的夫妇,有一个儿子,并且是会弹钢琴的儿子。她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当然认为是个儿子。也许她骨子里,希望有一个儿子,可是她不敢生,儿子需要花更多的钱,她哪里敢?
在她臆想中的那个家,儿子可爱又调皮,在练习钢琴的时候,他才会安静下来,会很专注,她自己年轻时,也非常热爱音乐,在录音机一遍遍播出的世界名曲中,有过浪漫梦想。
想象中,弹钢琴男孩子的父母,年轻夫妇,一个是教师,另一个,是公务员,都干净,体面。看房时,按过门铃,房门被彬彬有礼地打开,穿着连衣裙的女主人笑意盈盈请他们进去,男主人沏好茶,邀请他们坐下。
不急,男主人笑着说,喝完茶以后再看房。
于是,他们边喝茶边聊房子的事情,他们说,房子很好,刚买下两年,因为工作调动,因为孩子上小学买了新学区房,因为他们养了一只狗,要去别墅区住,那里有院子,总之卖房的理由都是诸如此类。她希望是这样。
她舒服地坐下来,接受一杯又一杯热气腾腾的绿茶。直到黄昏来临,霞光照在阳台一丛丛绿意盎然的绿植上后,他们才站起来,由女主人领着看房,男主人在客厅,他指点孩子弹琴,琴声在房间里多么好听,多么温馨,他们在琴声中走进主卧,里面有一张大床,两米的那种,有一个没有任何装饰的大衣柜,纯木质,柜门上没有任何可笑图案,接着是窗台,巨大,虽然不是落地窗,可上面铺上格纹的粗布,放着古朴的软垫,还有个可爱的小桌子,放着零食,切好的水果放在绿色的玻璃盏中。窗户被擦得一尘不染,别致的一些小饰件在房间错落有致地摆放着。她依依不舍地出来,到了另一个房间,这是客房,同样素净,简单。接着是书房,书柜足有两米,是装好不能动的,发现这一点她十分高兴,这是她的私心,搬来可以直接用上。她喜欢看书,她需要这样一个房间。大书柜有专用的梯子,可以随便拿书来读,在书房大书桌上,桌面显示出高档的红色,椅子不是转椅,是个放在木地板上的靠椅,舒适,结实,好看。
接着是厨房。不是那种华而不实的开放式。这厨房是独立的,它被玻璃推拉门隔离开,里面有锃亮闪着金属光芒的炊具,刀具,锅碗瓢盆都各自有最恰当的位置,她走近灶台,打开天然气,蓝色火焰无声无息。除了钢琴声,什么都是安静的,抽油烟机带走一些声音,做饭时声音是和谐的,是安静的,只要不是噪音,她就可以将其归为安静,属于灵魂的安静。
女主人带他们去参观卫生间,黑白两种小墙砖和地砖和谐,洁净。热水器常年开着,热水随时可以出来,一个大大的木桶在卫生间里等待注入热水,等待身体的休憩。木桶旁边的盒子里,放着玫瑰干花,牛奶,薰衣草味道的沐浴液。她此刻就想赤着脚,进入其中,让水汽萦绕在自己的周围,闭上眼睛享受这美妙的一切。
噢,她的眼睛,简直要被这想象中的热气迷惑。然而,事实是怎样呢?她从来没有遇到过一间这样的房子,一次也没有。幻想多么傻啊!
有一次,打开门的是一位老太太,随着门开放的,是扑鼻的老人气,那味道酸腐,艰涩,使得她倒退了几步。他早就皱起眉头。他们走进去,里面光线灰暗,也是个上午,外面阳光好得让人重新滋生妄想,可一进入屋内,暮气沉沉,客厅是暗的,卧室是暗的,连对面人的脸色,也是暗淡的。中介没有来,但他告诉过他们这里住着一对老年夫妻,他们身体不行了,要去儿子家里住。老头瘫痪好几年,老太太一直照顾着,现在,老太太查出来癌症,是胃癌。所以两个人要一起去儿子家,接受儿子的照顾。不管愿意不愿意,她想,不管儿子愿不愿意,不管老头老太太愿意不愿意,都必须这样。他们都必须去投奔儿子,把自己像两个包袱一样带去给儿子处置。
尽管有思想准备,可是房子境况还是令她感到惊心,感到诧异,感到痛苦和窒息。厨房内,马桶内,客厅内,都肮脏不堪,两间卧室,同样弥漫着将死之气。老头躺在其中一间卧室里,隔一会儿,就需要老太太去拿痰盂过去,吐一口浓稠的痰。老头瘫痪的是下半身,她忽然想,如果瘫痪的是上半身,是不是就没有吐痰的要求了。然而她又想起下半身瘫痪会有屎尿和暗疮,她不禁反胃起来。她还是忍,强忍住。
照顾病人是痛苦的事情,她知道这个。他父亲死于突发心脏病,而母亲是脑梗,发作两次后,就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在医院住了半年后,去世。这期间他经常就在医院泡着,是女儿考大学的那一年。她也很疲累。照顾女儿已经让她疲惫不堪,她下班后做饭,他带饭去医院,她陪女儿吃过饭后洗碗,做家务,兼职的公司还有一大堆活要做,活是计件,不做,一分钱都没有。她做兼职,他从来没反对过,就是在他母亲住院期间,他也没反对过。不因她忙得很少去医院而和他赌气。她的钱,每一分都贴补到家里,她很少买衣服,很少给自己买爱吃的零食,医院需要钱,她给,女儿需要买营养品买复习资料买水果买肉,也是她出。他的那点工资,每月还公积金贷款,交电费水费,所剩无几,每一分钱,都來得太艰难,太累,谁也懒得抱怨谁。尤其是她,看到他因为总去医院,全勤奖加班费被扣除,她也不能说什么。只有这样撑着。
亲人去世后他老得很快,仿佛补缺,他变成老人,老态龙钟,走路蹒跚,每天上六楼,成为他特别辛苦的劳动,买面,买米,那更是可怕,他喘息着,和一个肚子巨大的蛤蟆一样喷吐着浊气。可是他也坚持着。如果是送上门那种,要加钱,他还是自己背回家划算。
看完房,告别老太太出来,她开始害怕老,害怕死,害怕不能健康老死,害怕不得好死。她听自己母亲说,好死的人,都是修下的,比如那些猝死的,被车一头撞死的,得心脏病一下死了的,高处有个花盆忽然掉下来砸死的,这都是好死。恶死的人,都是作下的,必须狠狠遭一番罪受一通折磨后,阎王才收。她想到刚才在遭罪的老头,遭罪的老太太,暗暗为他们感到忧心。
她不知道自己最后会怎么死。她希望是说死就死,不遭罪的死。不连累别人,自己也不痛苦。
现在,他们已经走进走廊,电梯显示在十二楼,需要等一会才来。他说十二楼是顶层。
我们不要顶层了,顶楼太热,他说。
他对她笑了笑,几乎让她以为是错觉。他通常都在皱眉,一筹莫展的样子,他很少微笑,她都快忘记他多久没对她笑过。他父母去世后,他狠狠消沉了一段时间,直到女儿考上大学的通知书到来时,他都没有缓过来,他对生活有气无力,他对未来得过且过,只有在看《动物世界》时,她才觉出他年轻过。
电梯里面空无一人,专为他们而来。里面传来一股生肉的骚味,像牛肉或者驴肉。这令她不快。她的记忆中,曾经非常非常厌恶这种味道。她想起来,那是令她耻辱的记忆。
他常对着父母照片发呆,她把照片收起来,放到柜子里去,每年过年初一的时候,才拿出来,摆在一个桌子上,放上四样水果,四碗菜,放好筷子,点上香,和他一起磕头,然后在初二这天下午,烧纸,把纸的灰烬收起来,由他拿到某个十字街口倒掉。他沉闷,少言。女儿大学住校后,家里更加死寂无声。他开始经常去喝酒,他没什么朋友,交朋友是需要花钱的,他没有闲钱。他到夜市上,一个人叫上几大杯扎啤,叫上二十或者三十串羊肉串,有时候还要吃一碗饸烙面,然后才半醉着回家。于是每天,他都帶回来一股孜然、烧烤香料、辣椒面的味道,还有肉串散发的一股骚味,听说假羊肉在羊尿里泡过,也许是真的。她躲在自己房间不出来,她起初睡不着,后来能睡着了,被惊醒之后,她再睡。她疲惫。依然是吵架都懒得吵。
他开始整夜不回家后,她才隐约觉出不对劲。有一天晚上,她并不是十分有目的和刻意地走出门,去找他是一闪念的想法,那时已经十二点多了,她去他说过的老地方去,见到角落里,他落寞地对着几个空啤酒瓶子发呆。穿肉的铁钎零散在桌子上扔着。她在不远处的一棵树背后看着他,站了很久,连腿都快僵了。终于,看到他站起来,她以为他往家走,可是他没有。他走到那卖羊肉串的女人身边,帮她收起了摊子,他做得很熟练,显然这么干很久了。他边做边跟那个女人聊天,大部分是他在说,听不清说什么,只看到他嘴巴在欢快地动。他不误手中的活,肉在一个箱子里,铁钎在另一个箱子里,其他的馍片,蘑菇、鸡排,鱿鱼什么的,都穿好了,在第三个箱子里。木炭发出幽暗微火,还没有彻底熄灭。炉子被他一把就扛了起来,在车上安置好。最后,所有东西都放到黄色三轮车上。女人骑着,他坐到后面,坐在某一个箱子上,从她视线里渐渐远去和消失。这时已经很晚,没有几个食客,没有人注意他们。除了她,没人注意这一切。麻辣烫老板也正准备收摊,见怪不怪的样子。她走过去,要了一份麻辣烫,老板说,这些摊子,数羊肉串老板有钱,都买了三套房了。她一个字都不多问,觉得没有尊严,怕引起老板怀疑,怕走到路上,麻辣烫老板认出她,笑话她,轻视她,把她当做谈资讲给某些来历不明的食客听。她怕这个。
他一夜未归。
第二天白天,他中午回来吃饭。用后脑勺对着她,把一碗焖面吃完。电视里播放着一场动物厮杀。老虎吃掉了斑马,他嘿嘿笑一声。血腥场面没有使他不快。广告时间他去厨房盛饭,他又吃掉满满一碗。她第一碗饭还没有吃完,想着跟他说点什么。后来,她放下筷子,走到电视机那里,把电视机关掉,他瞪起眼睛,准备要和他理论,他理直气壮问为什么要关掉电视,愤怒起身打算重新打开电视,以此来捍卫尊严,他的动作很大,差点把茶几上他没来得及送的空碗打翻,碗在茶几上打了个转,一只筷子掉在地上,碗又牢牢定格在茶几上。
她眼睛转向他面前的空碗,不再看他,她说:以后,不要再去烧烤摊了。
又说:家里也有很多活要做。
他愣住,不敢说话,她去餐桌上吃饭。他没有开电视,走到厨房,默默去洗碗。
电梯在十楼停住,他们一前一后从电梯里出来,他手里拿着一把房主给的钥匙。他打开门,她吃了一惊。这是新房,是毛坯房。
90平米,他得意地告诉她,手上扬着钥匙圈。房子的确大,每一间都阳光充足,她可以按照她想象的任何风格来装修。她很意外,向他投去征询的目光。
他得意又有点讨好地对她说:房子是他表亲多年前的顶账房,人家有房,不住,原价给他们,不用多花一分钱。
她从来不知道他有个表亲,多年来从来没有一个属于城市的亲戚露面。这个表亲是谁?
她提出疑问。但他没有回答。
对这个房子她很满意。看过那么多二手房,三手房,她已经失去信心。她还有多少年可活呢,她想有个便宜房子来住。她不是没想过买个新房,自己来装修,可是房价居高不下,她怎么敢想?现在,这么好一个机会摆在她面前,她有点不敢相信,可她也想赶紧抓住。
他始终没有回答对他表亲的疑问,而是明确房子价钱。他说出的数字令她心中暗喜,按照这个价格,她卖掉以前六楼120平米的房子,除了把给女儿的那部分留下,还可以付这个新房的房款,如果计划得当,还能勉强够装修这个房子的费用。这真是意外惊喜。她不敢想,不相信。生活中,早就没有什么大喜事可言,这叫人怎么相信?
空荡荡的房子又弥漫起那股骚味,牛肉、驴肉、羊肉混合的,像尿液一样的味道。这味道越来越强烈,她忍不住想呕吐,在他貌似关切地靠近她时,她把他往远处推了推。她拿出一张纸巾捂住嘴,把恶心猛烈地咽下去。什么不可以忍受呢?她抬头,仔细打量着这个很适合自己的房子。
他们很快卖掉房子。他去银行,给一个账号付了全款。接下来装修,她包揽下来。装修是件麻烦的事。第一件是砸墙,工程交工时,都是敷衍,用最差的材料。墙皮必须砸掉重新灰一遍。她去市场找工人。没想到工人这么紧俏,好容易找到一个,对方说半个月后才能开工,等到半个月后,工人带了一个徒弟来,拿着锤子一通乱锤,墙皮轰然片片落地,里面露出一个个大石头,透出可怖的缝隙,从这边能看到那边。到电视墙那里,墙体变得牢固,这是最牢固的一块,工人说,要是全屋都像这里一样,就不必砸墙。可是只有这里牢固,不砸掉,也不行。单剩这里的话,重新灰墙时怕留下不平整的痕迹。于是用电钻和锤子再突击,用了两天时间,才把墙皮砸完,她灰头土脸回家,在房子里站得腿都僵了,他熬了米汤,拌了黄瓜,她知足地吃了半个馒头,一倒头就睡着了。
接下来,墙体整体灰了一遍,找的另外一个工人,加上之前砸墙,她已经花了一万块。每一分钱她都花得心惊肉跳,没想到会这么贵。同事梅姐跟她很要好,刚装修完房,把给自己装修过的工头介绍给她,说活干得好,价钱也不胡要。这样,她就省却了找散工的麻烦,很快,房间里的电走好了。工头姓周,大家都叫他周老板,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瘦子,话不多,看上去很靠谱。她把自己的设计方案告诉周老板,又把自己的经济状况说了一下。为了让周老板能够尽心,她还叫梅姐和周老板一起吃了个饭。基本都是她在说,她叫上自己的老公,可是他说,装修的事,都交给她,一来家里钱大都是她赚,都是她掌,二来这样不起冲突,不吵架。周老板和梅姐相视一笑,她的脸热辣辣的,她觉得人家看不起她,也看不起她老公。她硬着头皮,把那顿饭坚持下去。
每天他都会做好饭等她。她从工地上回来,吃完饭,尽量把兼职的活再赶一些,就倒头睡。第二天,再早早去工地。房子渐渐按照设想完成着。按照花最少钱出最好效果的初衷,勉强成形。壁纸是特价,木地板是特价,家具家电是特价,她在每一家店里都据理力争很久,并且要多要一个锅,一个体重计,一套餐具等,才肯付款。她的嘴巴上每天都起着皮,眼睛里布满红血丝,头发好几天不洗,她瘦下来,同时更老,像一个六十岁的老太太。
快要装修完时,出了一件事。那天,她正在指挥工人装一台空调。旧房子里没有空调,她想在新房安装一个,立式的,格力的。好空调,格力造,这广告词蛊惑了她。她要奢侈一下,还有个私心,女儿女婿在上海住惯了,每天在单位吹空调,如果他们回来住,没有空调哪能行,如果他们有了孩子,把孩子热着,又怎么得了。
就在这时,门外进来一个人,门没锁,那人径直进来,问谁是主人,她点头后,那人又问,多少钱买的房?
她以为是个邻居,或者,是个同样看房的人。那人瘦,脸色疲惫。身上穿着一件污浊的半袖,并且,散发着一种调料的味道,是一股类似孜然的味道。
这味道竟然让她立刻警觉起来。她含含糊糊地说了句,很贵。
那人不罢休,说,很贵,是多少。他的语气有点不礼貌,有点冲。她往后退了一步。
空调工人完成最后的安装,打开电闸,试验成果,凉意直吹到毛孔里去,她认识到自己需要冷静。
房子是我老婆卖出去的,我并不知道。所以我来问问,是不是你在她手里买的。
她忽然明白了他是谁。空调师傅告辞要走,她沉着地付余款给他们。那人仍然站在门口等,等她回答。
送工人到门口,她脑子里飞快转着各种念头,想着该怎么回答。她知道不能说那个价格。她早就知道那个价格意味着什么。这个时候,她选择和她老公,和她老公的情人,达成默契,达成共谋,达成共识。
她反问他,你老婆没跟你说多少钱吗?
他回答,说了。
他又说,不过,我还想来问问,你的分期要多久。
她立刻明白了一些,他老婆跟他说的数目,绝对要高。一定跟市价一样。她继续保持冷静,想着怎样说才能滴水不漏。她迅速整理语言,她要成功入驻这套房子,成功打发走这个可怜的,满腹狐疑的男人。
她说,这样吧,我让你看看转账记录。
她这么说完,立刻佩服起自己的智慧。她当着男人的面给自己老公拨通电话,对他说,房主找来,请他把转账记录给她发来,她让他看看。
他会明白。他知道怎么处理。他和他的情人,肯定有着某种约定。
他让她把电话给那个男人,他在电话里告诉那个男人,转账记录原本在,不过在家,如果需要,他可以下班后回家拍照片给他。
他又告诉那男人房子买的时候付了多少钱,是市场价。男人听后,刚才绷紧的身体完全舒展,疑云消除,男人客气地在电话里说,不用不用,我就是问问你们分期的事,你们刚装修,一次付清是有些难,原本我是反对分期的,不过我老婆已经跟你们说好了,我就没意见了。
他挂断电话,跟她客气几句,走了。
她靠在门口,空调把她吹得睁不开眼睛。这个夏天,不断冒出丝丝冷气。
他俩谁都没再提起这件事。
最后的工作完成后,她叫上他,把新房里全部打扫了一遍,把自己买来的十五元两盆的几盆小吊兰摆在客厅和卧室,打开窗户往外看,风徐徐地吹进来,简直和她小时候在山里吹过的风一样充满青草香味。他从背后走过来,抱住她的腰,和泰坦尼克号里面那个经典动作一样,接着,他把她的身体扭转过来,拉着她跳起慢悠悠舞步。她身体很软,热泪滚滚落下,周身再没有什么力气。力气顺着窗户跑出去,身体变得空荡荡,一所房子對她的身体和心灵的损耗比她想象的要多。她微笑着停下舞步,示意自己要坐到沙发上去,他有点调皮地做了个请的动作。
她坐下,无力地闭上眼睛。太累了。这个时候她需要一点依靠。可他还在独自一个人跳舞,嘴巴里哼着过时的舞曲。她想,随便谁都行,她只想找个人,靠一靠,如果可以的话,再睡上那么一小会。
这时,她的手机响了。包在沙发上放着,就在手边。她睁开眼睛去拿手机,是女儿打来的。女儿问她,房子怎么样了。
她掩饰不住欣喜,说,今天全部竣工。
女儿很少打电话回来。装修期间,她也没有回来过,她想给女儿说一下自己的兴奋,让女儿回来看一眼她精心装修的房子。
可是女儿打断了她。女儿的声音很委屈,说,妈妈,你们都换房子了,我们都还没有自己的房子住。
女儿说,她现在又怀孕了,这个孩子不敢再打掉,医生说高龄产妇,再流产怕怀不上。
女儿说,他们看好了一套特价房,不过还差些钱。限定半个月之内交钱。如果不交,就交给其他人了。
“为什么是特价房呢?”她愣愣问了句。她想自己装修都是用特价的东西,特价的东西,并不十分好。
特价也好。女儿说,特价是因为这是二手房,里面死过人的,当地人忌讳,可外地人,哪有资格忌讳?很多人都想买。他们抢先交了定金。
哦。她明白了。他也走过来,凑在她面前听电话。
妈,我公婆家给了一些,我们又贷了款,不过还缺钱,你和我爸千万给我们凑来,要不,房子让别人抢走,定金也拿不回来。
差多少?她问道。
女儿报出数字。她惊呆了,而他已经扑通一声跌坐在沙发上。她看一眼自己的新房,觉得这房子如此不真实,仿佛不是她的,可明明是她精心装修过的。床,她还没有睡过。淋浴,她还没有用过。厨房里,她还没有做过一顿可口的饭。仿佛再没有机会。窗外风开始热起来。已是中午时分,窗外是烟囱似的高楼,哪里有青草?她是糊涂了,高兴糊涂了。
她的眼角还有泪痕,那是刚才包含兴奋滋味的泪水。现在,这泪水滑落下来,在她脸上的沟壑里停留一下,就掉到地上。
卖房。她喃喃道。旧房子里的家具现在在租来的一个地下室放着,卖掉房,他们别无选择,得和那些家具一起在地下室容身。她擦擦眼泪,挺起身体,已经做好一切准备。